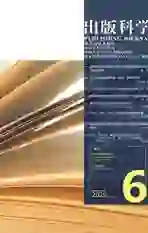泛在网络背景下出版空间优化占位研究
2020-01-08张弛
张弛
[摘 要] 泛在网络背景下的出版空间优化占位,既需要新媒介技术支撑,也需要媒介文化理论指导。出版空间优化应该基于文化地理学和媒介地理学推动构建新型出版地域空间占位,基于媒介理想主义推动构建恒常在线的泛在出版网络空间占位,基于语义主义的“超文本”推动构建万物皆媒的新媒介和全媒介空间占位,基于文化组学和用户画像推动构建满足作者和读者个性化需求的市场空间占位。出版空间的优化占位的目标是整体优化和系统构建新型的出版空间链。
[关键词] 泛在网络 出版空间 优化占位
[中图分类号] G2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0) 06-0019-09
In the Context of Ubiquitous Network Publishing Space Position Optimization Study
Zhang Chi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Law Humanites and Sociology, Wuhan, 430070)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ubiquitous network, publishing space position optimization requires new media technologies and media culture theories. Cultural geography and geography of media promote to configure novel publishing regional space position. Hypertext promotes to configure new media and full media space position. Cultureomics and personas promotes to configure market position optimization. Publishing space position optimization is for integral optimization and novel publishing system space chain.
[Key words] Ubiquitous network Publishing space Optimizing position
自富士施乐公司(Xerox)帕拉阿尔托研究中心(PARG)的马克·维瑟(Mark Weiser) 博士提出“泛在”(Ubiquitous)一词后,泛在网络(Ubiquitous network)概念应运而生。泛在网络是新一代网络的集成,涵盖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1]。泛在网络派生了泛在学习(Ubiquitous Learning)、泛在环境(Ubiquitous Ledge)、泛在商务(Ubiquitous Business)和泛在出版[2]等一系列新的泛在形态,这些泛在形态尽管各有特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具有5A (Anyone、Anytime、Anywhere、Anyway、Anything)的全时空特征。在泛在网络背景下,出版行业和出版机构面临着业界内和业界外激烈的市场空间争夺,这种激烈的出版空间竞争表现为三大主要变化,一是由出版人竞争转变为人人竞争(Anyone),二是由有限时空竞争转变为全时空(Anytime、Anywhere)竞争,三是由单媒介竞争转变为全媒介(Anyway、Anything)竞争。因此,出版业和出版机构的生存发展空间必须基于泛在网络进行空间优化占位。从人类活动的理性来说,任何产业的生存发展既需要有不断创新的新技术运用,又要有对产业发展基本问题的理论分析。本文试图从基于文化地理学的出版地域空间优化占位,基于媒介理想主义的出版网络空间优化占位,基于语义主义“超文本”的出版媒介空间优化占位,基于“文化组学”的出版的市场空间优化占位四个方面来思考泛在网络背景下出版空间优化占位问题。
1 基于文化地理学的出版地域空间优化占位
“文化地理学”代表人物盖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d)认为,空间具有无限性和有限性双重属性,它随着人自身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重组[3]。文化空间涵盖出版空间,出版空间问题自然是“文化地理学”及其分支“媒介地理学”所关注的研究对象,邵培仁指出:“媒介地理学是以人、媒介、社会、地理四者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4]出版空间从单一的地域空间或物理空间向网络空间或虚拟空间的拓展,正是这种空间存在形式多维性的现实表现。在泛在网络背景下,出版产业和出版机构的出版空间优化占位也必须在多维度展开。
泛在网络背景下出版空间争夺的主战场虽然在网络空间,但地域空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一直是出版产业和出版机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从本质上讲,尽管网络泛在趋势日益加快,但只要产业分工存在,地域空间的价值意义就不会丧失。
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在泛在网络背景下,出版地域空间的要素流动不断加速,由此形成的极化空间形态和扩散空间形态都为出版地域空间的优化占位创造了条件。按照产业经济学理论,一个产业的空间分布状态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与产业分工密切相关,二是与产业要素流动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因此,产业空间结构会出现两种空间形态:一是极化空间形态,表现为产业从欠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的转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用“回波效应”来形容这种情形,赫尔曼(Herman)则用“极化效应”来形容这种空间位移。二是擴散空间形态,表现为产业从发达区域向欠发达区域进行梯次转移,赫尔曼用“涓流效应”来形容这种情形[5]。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的存在说明出版产业的空间要素流动也是一种常态,只要抓住机遇,出版机构都有发展的机会。从实践上来看,出版界熟知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在1986年靠借贷27万元白手起家,虽然本部位于老少边的广西地区,但靠空间扩张,目前分别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发达区域设立了分支机构,还于2014年收购了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于2016年收购了英国ACC出版集团,其空间版图扩展已经抵达国内发达地区和国外发达国家,其产业版图已经涉及图书、期刊、电子、音像、网络等出版物的出版发行以及知识服务、文化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以及教育培训、会展、咨询、旅游、艺术品、房地产等诸多领域,形成了跨地域、跨领域发展的地域空间优化占位。
其次,从文化学的角度讲,在泛在网络背景下,虽然泛在学习和泛在阅读与日俱增,但其中的快餐文化消费并不能排斥和代替理性阅读,打造书香社会和全民阅读的社会文化行动为出版地域空间优化占位提供了条件。一方面,从阅读情景上看,人的感性和理性决定了阅读具有感性体验和理性体验两种情景,浏览式的快餐文化阅读符合一部分人的文化消费心理和文化消费习惯,沉浸式的品味阅读也符合一部分人的文化消费心理和文化消费习惯。出版物终究是给人看的,感性阅读和理性阅读都是符合人性的,两者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认为,出版等媒介技术的进化要“不断追求保存并继承自古以来人在延伸方面的突破,恢复人在自然交流环境中丧失的人性要素”[6]。这里的“人性要素”是自然状态,包括感观认知、空间移动、族群关系等自然状态下的各种习性。这一点与麦克卢汉(Mcluhan)的“媒介即人的延伸”[7]的观点相吻合,麦克卢汉和莱文森都坚持媒介理想主义信念,坚持符合“人性要素”的“总体体验”,这个总体体验不仅要更快,还要更高、更强。现阶段更快的阅读体验主要来自于泛在网络,而更高、更强的阅读体验既来自于浏览式的快餐阅读,更来自于沉浸式的理性阅读,而两种情景阅读的存在和发展为出版地域空间优化占位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另一方面,从阅读选择上看,人的文化属性决定了阅读具有空间地域性和时间选择性。新文化地理学强调文化的空间属性,其代表人物彼得·杰克森(PeterJackson)和丹尼斯·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形成,文化即空间形成过程的媒介。”[8]文化都具有空间地域性,都以具体的形式存在于一定的地域空间中,正是因为文化具有空间地域性才有了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而文化的世界性由其民族性赋予。在泛在网络背景下,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出版物具有更多的表达形式和呈现方式,但万变不离其宗,人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出版物的文化属性,出版的形式和媒介可以变,但其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本质没有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泛在网络不仅不是出版地域空间存在和拓展的障碍,更应该是地域空间版图不断扩张和优化的推动力。据世界教科文组织2016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犹太人平均每人每年阅读68本书,俄罗斯人平均每人每年阅读24本书。这表明在泛在网络背景下,犹太人喜欢读书的文化秉性并没有变,因此,依据文化属性优化出版地域空间占位既有历史根据又有现实条件。
2 基于媒介理想主义的出版网络空间优化占位
以莱文森和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理想主义者在强调“媒介即人的延伸”的价值观的同时,主张现代人要找回长期失落的“感觉总体”,感觉总体既包括视听说,也包括知情意,感觉总体追求的不是单个感官的满足,而是感觉总体的平衡。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和AI技术的泛在网络为实现感觉总体平衡提供技术支持和媒介条件。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指出,空间是一种语境假定物,一般意义上的空间都表示了物质的客观形式[9]。在传统的理解中,“作为物质的客观形式”的空间一般都是指地域空间或物理空间,但随着网络空间的泛在化,事物的存在空间既具有地域空间或物理空间维度,同时也具有网络空间或虚拟空间的维度。泛在网络为出版网络空间优化占位既提供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网络空间是存在空间的现代表现,相对于地域空间的现实特征来说,网络空间是虚拟空间,是空间存在的新形式。随着网络的泛在化,网络空间已经从单一的互联网发展成融合各种业务的万物皆可控的网络空间。泛在网络的泛在性有四个主要含义:一是网络连接泛在。泛在网络连接包括物理空间在内的所有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而且泛在连接在时间上是动态、即时和连续的。也就是说,虚拟网络空间与现实物理空间虽然各有特质,但两者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泛在网络的泛在连接同时也包含物理空间要素在内。二是通信活动泛在。泛在网络通过大数据技术和云空间不仅连接所有实体,还融入实体信息活动的所有环节。三是嵌入智能泛在。这主要是通过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泛在物联网来表现的。四是反馈控制泛在。有人的活动就有控制和反馈,依托泛互联范式,反馈控制就更即时,更動态、更具有精准性和针对性[10]。从泛在网络的上述含义来看,出版网络空间优化不仅仅是要优化互联网出版空间占位,而是要系统优化泛互联出版空间和智能出版空间占位。
首先,泛互联出版空间优化是要全方位优化互联网出版、移动互联出版以及物联网出版空间占位。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空间占位来讲,优化出版空间占位就要提高信息占位能力并以此提高信息占有的数量和质量。在传播学意义上,出版属于信息传播大类,出版空间占位可以说就是信息占位。在泛在网络条件下,海量数据既存在于现实空间,也存在于虚拟空间,因此,泛在网络背景下的出版并不是缺少信息数据,而是缺少挖掘处理信息数据的能力,没有信息数据挖掘处理能力,身边的信息数据就都成了“数据废气”和“数据垃圾”[11]。AI领域著名代表人物赫伯特 · 西蒙(Herbert Simon)曾指出:“信息消费了什么是很明显的:它消费的是信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越丰富,会导致注意力越匮乏……信息并不匮乏,匮乏的是处理信息的能力。”[12]因此,优化网络出版空间占位要借网民井喷增长之势,运用大数据信息处理能力挖掘用户数据,进行用户画像,增强用户黏性,用优质出版产品和服务吸引消费者注意力。从某种程度上讲,消费者黏性就是市场占有率,市场占有率就是出版空间占位。同时,作为泛互联出版空间系统优化的一部分,物联网出版空间占位也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譬如青岛出版集团就与海尔集团合作,在海尔冰箱门屏幕上演示菜谱视频[13]。这种物联网形态的出版物比之原来的纸质菜谱书籍更具有即时性和现场感,这种出版方式应视作泛互联出版空间占位的有益尝试。
其次,智能出版空间占位也是出版网络空间优化的重要内容。在工业4.0时代,虚拟空间到实体空间的无缝对接从三方面为智能出版优化空间占位创造了条件。一是智慧通路的构建。在泛在网络和全媒体条件下,读者可以通过不同媒体接触到相同或相似的内容,读者兴趣很容易从一种媒体转移到另一种媒体上去,要留住读者,就必须留住读者兴趣,这就要求基于大数据进行用户画像并构建兴趣图谱,一方面在媒体选择上为读者提供智慧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兴趣引导帮助读者构建从碎片化阅读到深度阅读的智慧通路。二是智慧社区的构建,智慧社区是实现人人智能互联,通过泛在网络和各种媒介将各种兴趣的人和各种经历的人构成社区族群,在不同社区提问和讨论各自不同的问题。三是智慧场景的构建,智慧场景是在特定情景下创新知识和解决问题的场景。按照DIKW结构,数据场景、信息场景、知识场景、智慧场景呈现金字塔结构,智慧场景是转知成慧的顶层空间存在形式。智慧场景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是数据场景、信息场景、知识场景的升华,也与智慧通路和智慧社区无缝连接,同时,智慧场景还与互联场景、移动场景[14]、物联场景共同构建形成工业4.0时代的智慧出版空间,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万物皆连和万物皆媒[15]。
3 基于语义主义“超文本”的出版媒介空间优化占位
“超文本”最早由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提出,其设想的“超文本”是一种超链接的、将不同空间和不同格式的数据和信息组织起来的网状文本。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r)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arrida)等语义主义者从语义分析出发,强调语义的非线性和歧义性,语言表达过程中表达方式的差异和语境的变化都会使语义产生歧义,即“能指会滑向另一层所指,所指也会滑向另一层能指”。表达方式和语境的复杂化,使语义也会由原来单一线性的结构演变成复杂的非线性结构。语义主义的“超文本”设想只是一“理想文本”,真正意义上的“超文本”是随着泛在网络的出现才得以实现的。信息传播是以人为对象的,而人对信息的接收和理解都是以语言和语义理解为基础的。在泛在网络条件下,作为出版传播对象的读者的阅读已经由原来单一平面介质的文本阅读拓展为文字、图表、图片、音频、视频等立体交互的多介质阅读,阅读文本已经由原来的单一平面文本进入到“超文本”时代,以至于“媒介不再是讯息,它是讯息本身”[16]。基于泛在网络的“超文本”一方面改变了读者单一线性的平面阅读方式,通过“感觉总体”的视听说交互式体验阅读实现了读者随时可读随处可读的全时空愿望,另一方面“超文本”的全媒介结构也要求改变出版原有单一线性的平面出版方式,使出版呈现全媒介特征。正如詹姆斯·罗尔(James Rool)所说:“人类有能力以改善其利益的方式参与、阐释与利用媒介技术和文本。”[17]
首先,泛在网络的发展驱动全媒介空间优化占位。泛在网络对出版空间拓展的重要表现是全媒介的出现,按照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观点,媒介不仅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存在内在联系,而且媒介在空间上与人的存在具有同步性和共生性。随着新媒介不断涌现,各种媒介的深度融入和无缝连接使得人类的空间感由实向虚、由直接体验向间接体验转换。这种广泛而深刻的空间转换形成的新型空间是电子的、去中心化的、流动的全球空间[18]。与人类活动空间转换相适应,媒介空间存在发展的人际区间、组织区间和国家区间”[19]也发生了变化,媒介空间拓展出现了全媒介不断创新融合的趋势。
按照传播学解释,媒介是指运用介质存储数据信息和传播信息的工具和载体。而媒体则是指传播信息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包含媒体,全媒介包含全媒体。作为传播信息工具的泛在化,全媒介包括纸介质、磁介质、光电介质等传播信息的媒介,也包括通信类、广播影视类以及网络类等传播信息的技术设备、组织形式和社会机制。按照媒介理想主义者的愿望,全媒介是靠符合人的“感觉总体”平衡的媒介形式。而按照语义主义的观点,全媒介也符合其“超文本”设想。
其次,泛在网络的发展促进多媒介融合。随着泛在网络的发展,媒介出版空间优化占位已经在两方面全面展开。一个方面是传统出版机构从单一媒介向新媒介出版的拓展,从而优化出版空间占位,从发展路径上讲,这种空间拓展类型是内生性的。如中信出版集团在传统纸质图书基础上,出版了“E-only”产品以及数字版Mook。这种类型的媒介出版空间拓展要坚守一个原则,即出版产业是内容产业,不管传播媒介如何发展如何创新,归根到底媒介传播的是内容,内容为王是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行业的不二法则,纸媒作为出版内容的承载物是不会消失的。文化产业从事的是精神生产,精神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的区别在于其满足的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这种精神文化产品是要入脑入心的。因此,平面媒介向全媒介的转变,不是像搬家一样将老的、纸介质的内容拷贝到新型媒介上去,这种运用传统出版思维嫁接新媒介技术的做法在本质上并没有真正理解新媒介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结果只能是换汤不换药。因此,传统出版机构的出路并不在于简单将纸介质内容通过图片、音频、视频等格式和光电介质、网络介质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要在不断创新出版内容的基础上运用新媒介技术。其实,新媒介之所以“新”,并不是仅仅表现为在传播形式和技术上能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超文本”集于一身,更关键之处在于它从现代传播学意义上消解了传播者和受众主客二分的二元身份。美国《在线》(Online)在定义新媒体时指出:“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受众不再是单纯的、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受众同时也是传播主体。”[20]
另一方面是通过媒介跨界融合优化出版媒介空间占位。“全媒介出版是一种整合多种媒体形式对同一内容进行多媒介同步发送的全新出版理念”[21]。多媒介跨界融合突出表现为一体三维媒介空间构造,一体指出版内容,三维是指纸质版+网络版+手机版的三维媒介,“在大数据时代,出版业基于纸质版、网络版和手机版三个媒介空间(三维空间)产生的数亿级友好关系和流量,将是出版业未曾开垦的巨大财富”[22]。三维媒介空间的出现, 使媒介之间以及媒介与用户之间关系更加复杂,媒介空间关系由原来的现实空间关系变成了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关系。从关系基础上讲,现实空间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网络空间和手机空间关系都是基于现实空间关系的镜像化映射。正如戴维·杰倫特(David Gelernter)在“镜像世界”中所说:“互联网的终极世界是‘镜像世界——物理世界虚拟映射。”[23]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空间是现实空间的现代延伸,即使是泛在网络条件下的虚拟空间也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空间。从关系发展上讲,虚拟在线的网络空间和手机空间又突破了现实物理空间的局限性,使现实空间人际关系的直接的“强”关系变成虚拟空间间接的“弱”关系。
在泛在网络条件下,纸质版、网络版和手机版三个媒介空间并不是彼此分隔的,而是一体三维的空间关系链[24]。一体三维的媒介空间优化占位体现的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一体是内容,三维是表现内容的媒介形式,从这个意义上,传统出版机构的现代转型既应该坚持并发挥自己出版内容优势,丢掉了内容优势,就丢掉了自己的立足之本;同时又要创新运用新媒介技术,没有新媒介呈现内容,再好的内容也不能实现即时、快捷、多界面的自主阅读。在出版实践中,时代出版集团融合线下线上多媒介,形成图书、期刊、数字出版、网络出版、电子书包、手机阅读、手机动漫、手机彩铃、iPad阅读等多媒介的融合出版格局,还开发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全民数字阅读、云教育服务平台、专业电视频道、App玩具教学等共享型出版平台。类似的出版集团集资本、地域、出版优势于一体,有的还向金融、地产、文旅领域拓展空间,将媒介空间优化占位一步步推进到更广泛的领域。
4 基于“文化组学”的市场空间优化占位
“文化组学”[25](cultureomics)是一个复合词,其提出是源于用基因组分析方法研究图书数据库,其创始人艾略兹·利波曼·埃顿(E.Lieberman Aiden)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是进入谷歌庞大的图书数据库系统对1000余万种图书进行数据挖掘,将文字或单词等关键词作为文化基因,运用大数据技术挖掘发现随时间推移文化如何发生改变的量化指标。将“文化组学”具体运用到图书出版中的典型案例是苹果公司收购书灯(Book Lamp)的“图书基因组计划”(Book Genome Projet)[26],该计划通过分析处理每个读者的购书浏览记录和支付记录来了解读者的阅读兴趣,通过用户画像给读者绘制“专业图谱”和“兴趣图谱”,据此对读者进行“智能分组”,针对每一个读者进行基于“图书基因组计划”的“私人定制”和“量身定做”。这种“量化人性”[27]的量身定做能使对出版对象的深描进入到量化分析的量子层面,具有典型的“文化组学”基因。
“文化组学”基于“量化人性”的“私人定制”式出版方式与媒介理想主义者主张媒介技术要符合“人性要素”的理想具有相通之处,莱文森坚信媒介技术是人的发明,人类在创造一种新媒介时应该对前一项技术的缺陷以及造成的负效应进行补救,这也就是莱文森等人主张的媒介技术发展的自我补救路线。在现代的大数据和泛在网络背景下,“量化人性”和基于“人性要素”进行媒介技术补救的愿望已经具有理想实现的技术基础和条件。具体到出版领域,“私人定制”和“量身定做”对个性化的出版方式和出版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出版空间占位方面则表现为越来越个性化的自出版和分众市场营销。相比于通信运营商和网络公司,出版界的优势并不在于掌控新媒介,而在于掌控作者和读者。“出版的目的不在于‘出版,因为更为广阔的利益回馈是通过出版衍生更多的关系和交流”[28]。
首先,基于泛在网络抢占底层市场空间,从微观个体的层面优化出版空间占位。一方面,利用泛在网络的普及性和“量化人性”的精准性扩大面向草根平民阶层的作者队伍,优化出版资源的基层空间占位。在泛在网络条件下,出版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的专利,平民草根也能利用多媒介进行碎片化、主体化、个性化和网络化的出版,全媒介的多媒体表现形式能将很多“大隐隐于市”的草根作者开发出来。另一方面,在泛在网络条件下,基于读者和作者个性化需求的按需出版已成为现实。按需出版包括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根据内容和作者要求的按需出版,二是根据读者需要和市场容量的按需印制。按需出版某种意义上说是碎片化出版,如亚马逊旗下的出版公司创建的创意空间、互动式小说活动等平台就是为了吸引众多来自不同层次的人参与其中。俗话说“高手在民间”,通过拓展写作和出版空间,更宽广的空间舞台为草根平民进入出版领域打开了大门。按需出版的个性化意义在于,一方面,出版机构要发挥专业出版、专家出版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在泛在网络条件下,人人皆可成网民,出版机构要把出版资源开发于人人可用人人皆用的网络,为草根平台等基层大众提出个性化的定制服务,真正实现出版业服务大众的社会价值。当然,新媒体出版还有一些缺乏规范,其中有大众流行文化和资本运作助推的因素,“随着大众流行文化的助推、资本市场的介入以及商业化的运作,IP还表现为一种文化产业领域热门的商业模式,即将优质内容资源为入口集聚受众,形成情感众筹,进而利用粉丝经济实现情感的货币变现”[29]。并且,诸如微出版中的微版权问题日益突出,仅仅依靠政策法规维权力不从心,业界正在积极探索基于区块链技术进行版权的确权授权和维权[30]。
其次,基于“读者图谱”优化读者市场空间占位。读者图谱和用户画像的绘制是基于“量化人性”的“数据分层”。大数据的数据挖掘和处理能力能高效处理非结构性的人际交往数据,为数据分层提供了量化工具。马丁·克鲁贝克(Martin Kluberk)指出:“量化分析就是使用不同层级的信息数据、指标、信息和其他量化指标讲述故事。”[31]数据分层是深描用户需求,构建读者图谱的依据,读者图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读者专业图谱”,另一类是“读者兴趣图谱”。读者的专业阅读需求往往是刚性的,是读者完成学业和专业技术发展的需要,而兴趣阅读往往具有某种弹性,专业图书的刚性市场相对固定,而兴趣阅读的弹性市场则是市场空间竞争的主战场。因此,洞悉读者的潜在需求,将读者浏览行为转变为实际购买行为,在厘清读者阅读兴趣“基因”后,基于阅读图谱拓展市场空间[32]。读者熟知的“推豆儿”就是一款根据读者兴趣图谱进行精准市场营销的资讯推荐引擎工具,其运用算法优势,运用文章热度、内容相关度、读者兴趣关注度等多维度计算读者与文章的匹配度,从而实施满足读者个性化需求的内容的精准推荐,并运用读者浏览和购买行为数据实时分析描绘读者的兴趣图谱进行用户画像。因此,泛在网络和大数据条件下的出版市场空间优化占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兵团作战和经验式营销,而是建立在数据分层、知识图谱[33]、兴趣图谱、用户画像、算法推荐等基础上的精准营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泛在网络背景下的市场空间占位应该从对每一个读者的行为数据的精准分析开始,出版空间优化占位已经移步到微观层面的每一个人身上,通过每一个人的分众精准占位来实现宏观层面的出版整体占位。
5 结 语
泛在网络的出现,表明信息社会已经进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融合各种媒介的新时代。人与器物的万物皆媒、人与人的恒常在线、人与空间的泛在阅读要求出版业不断调整自身的存在空间、媒介空间和活动空间。网络的泛在性将出版存在空间由传统的地域存在空间拓展到现代的网络存在空间。泛在网络衍生的多媒介将出版媒介空间由传统的一维纸媒拓展到现代的全媒介空间。泛在网络所依托的大数据、云计算和AI将出版市场空间中的作者活动和读者活动进一步量化细化,将出版市场空间推进到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精准层面。总体而言,出版地域空间,网络空间、媒介空间和活动空间并不是分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統一空间整体,出版空间优化占位所要实现的是出版空间链的整体优化。
注 释
[1]文浩.无处不在的终极网络:泛在网[J].射频世界,2010(1):44-47
[2]马小琪.泛在学习驱动下泛在出版概念形成及对业界的启示[J].出版发行研究,2012(7):24-27
[3][德]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489
[4]邵培仁,杨丽萍.媒介地理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18
[5]多淑杰.产业区域转移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77
[6][美]保罗·L莱文森.软利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51
[7][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8]周尚意.文化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
[9][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20
[10]刘永谋,吴林海,叶美兰.物联网、泛在网与泛在社会[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6):100-104
[11]赵国栋.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56
[12]英文原文为:“What information consumes is rather obvious: it consumes the attention of its recipients. Hence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creates a poverty of attention ...The scarce resource is not information;it is processing capacity to attend to information. Attention is the chief bottleneck in organizational activity.”—Designing Organizations for an Information—Rich World,Simon,1971
[13][15]陳洁,蒋三军.5G时代的数字出版变革与创新[J].编辑学刊,2019(5):6-11
[14]丛挺等.移动场景下学术期刊跨平台传播的实证研究[J].出版科学,2019(3):74-8
[16][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68
[17][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化的路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36
[18][英]戴维·莫利.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5
[19]侯亚丁.数介产业的价值生态[J].出版科学,2015(1):51-58
[20]曹疆.从内容为王到用户至上[N].中国产经新闻报,2013-04-14
[21]王丹丹.全媒体时代我国出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J].出版科学,2011(5):62-65
[22]程忠良.大数据时代出版业“三维空间”关系链一体化经营策略分析[J].编辑之友,2013(9):36-3
[23]David.Gelernter :《Mirror Worlds: The Day Software Puts the Universe In a Shoebox...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at It Will Mean?》[M]. Oxford Press,1991:112
[24]万智,杨兴兵.基于媒介链接技术的融合知识服务系统构建[J].出版科学,2019(4):5-8
[25][美]艾略兹·利波曼·埃顿.数字化图书的定量文化分析 [J]. 科学,2011(1):176-182
[26]爱德华·诺沃特卡.极具创意的图书基因组计划 [EB/OL]. [2018-06-11]. http ://www.bookdao.com/article/27706/.htm
[27][美]埃里克·西格尔(Eric Siegel)著;周昕译.大数据预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59,235,149
[28]白志如.国内众筹出版项目的内容分析与发展建议[J].出版科学,2014(5):74
[29]陈维超. IP热背景下版权运营的变革与创新[J].科技与出版,2017(9):69
[30]陈维超.基于区块链的IP版权授权与运营机制研究[J].出版科学,2018(5):18-23
[31][美]马丁·克鲁贝克.量化:大数据时代的企业管理[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1
[32]戴盈.数字化时代读者的选书智慧和阅读兴趣图谱构建[J].中国出版,2014(3):51-55
[33]余世英,陈芳芳.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电子书研究分析[J].出版科学,2015(1):89-94
(收稿日期:202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