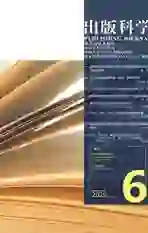胡适、张元济、商务印书馆与新文化运动
2020-01-08张志强
张志强
[摘 要] 柳和城所著的《挑战与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就新文化运动对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应对进行了研究,是第一本研究该问题的著作。本文补充了该书中未涉及的胡适与商务印书馆发生关联的经过、胡适与张元济熟悉的过程、胡适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等内容,同时纠正了该书中的一些细节错误。
[关键词] 商务印书馆史 胡适 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 G23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0) 06-0118-07
Review 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Zhang Zhiqiang
(Academy of Publishing &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a new book by Liu Hecheng, studied the impact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on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This is the first book about this topic, and deepens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 Shi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 Hu Shi and Zhang Yuanjis familiar process, Hu S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etc., and corrects some errors in the book.
[Key words] History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Hu Shi New Culture Movement
众所周知,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著名的出版机构,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的开端。从成立后到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作坊变成出版重镇,树立了较好的口碑,赢得了社会的称道。正如1921年胡适在考虑是否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时说的:“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1]十五年后,当胡适为辞世的高梦旦写小传时,回顾当时,他依然还是这一评价:“我绝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2]这些话,也可以看作时人对商务印书馆的肯定。为什么商务印书馆能得到当时学者这么高的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商务印书馆曾遭到进步人士的抨击,商务印书馆是如何面对这一挑战,并将这一挑战转化成机遇,为后面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的?“五四”前后,商务印书馆刊印了大量古籍,为何没有被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攻击?柳和城先生新出的《挑战与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一书,较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1 一点评价
《挑战与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挑战与机遇》)的作者柳和城先生,致力于商务印书馆史研究已有三十余年,成果累累。此前已经出版了《张元济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孙毓修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著作,并参与编撰《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著作。本书是他长期研究商务印书馆史的新成果。虽然此前已有吴相的《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杨扬的《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李家驹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史春风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著作,从不同角度对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及其文化贡献进行了研究,但专门就新文化运动对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应对来进行研究的,本书是第一本。毫无疑问,本书深化了对商务印书馆史的研究。
创办于清末的商务印书馆,在“五四”前经过近20年的發展,已具有了较好的基础。虽然此间也经历了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1912年的“教科书危机”,但商务印书馆继续成长壮大。1916年开始的劳资纠纷引起的罢工,经营中“滞销书刊”的增多,显示着商务印书馆发展中的暗流。而1918年9月《新青年》杂志刊登的陈独秀的《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1919年2月陈独秀再次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直接挑起了新旧文化的论战;1919年4月,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上发表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进行了点名批评。这些事件导致的后果,直接带来了《东方杂志》和商务其他杂志销量的骤减。正如该书所指出的:“杂志最能及时反映出舆论和知识界的风向,故在‘五四时期的出版活动中,杂志最为活跃。”[3]正是这些内忧外患,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该书将商务印书馆发展的视野放在出版与社会两个层面,对这些挑战进行了具体分析。
在分析挑战的基础上,该书将重心放在商务印书馆的应对上,探讨商务印书馆如何将这些挑战转化机遇。这中间,既有内部的改革,如张元济北上北大取经、改组杂志编辑部、出版共学社、中华学艺社等团体的书籍等;也有外部的支援,如邀请胡适来商务印书馆考察、聘请王云五到馆工作等;更有内容的革新,将新文化运动中的“德先生”与“赛先生”融入到出版物内容中,使“德先生”与“赛先生”随着商务的发展而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这一系列改革的结果,不但使商务印书馆平安度过了危机,而且进一步壮大了商务印书馆的实力。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是相对旧文化而言,是反传统的。但商务印书馆却在1919年开始出版《四部丛刊》之类的古籍。该书专辟一章《“整理国故”与商务古籍印行》,对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工作做了分析,认为“胡适、梁启超等一批学者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是五四新文化思潮的一部分。胡、梁两人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不平凡关系,……成就了商务这一新文化运动后期传播中心的奠定,其中包括古籍印行。”[4]这一分析,同样令人信服。我的同事徐雁平先生在《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5]一书中对此问题也有所讨论,可以参看。
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世纪大变革。在这场大变革中,商务印书馆直面挑战,在时代变化中把握潮流,“激动潮流”,从而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带动了自身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柳和城先生以敏锐的视角、深厚的功力,游刃有余地将这一出版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完整地作了阐述,深化了商务印书馆史的研究。
2 一点补充
《挑战与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通过征引张元济、王云五、胡适等当事人的书信、日记等,再现了当时的场景,体现了历史的真实。但一些细节,仍可补充。如胡适与商务印书馆是如何发生关联的?是谁首先提出邀请胡适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的?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张元济等人意识到商务印书馆急需改革,引进新人。尤其是高梦旦,“认为不懂外国文字的人,对于新文化的介绍,不免有些隔阂;因此屡屡求贤自代”[6],提出辞去编译所所长之职。由于胡适的国学根基与留学背景,喜交朋友的个性,使胡适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首选。商务印书馆曾极想延聘胡适到编译所担任所长。但由于胡适自己认为:“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7]胡适婉拒了商务印书馆的邀请。商务印书馆仍不死心,邀请胡适南下考察,冀望通过考察能使胡适回心转意。于是有了1921年7月胡适一个半月的上海之行。胡适在沪上交游访友的同时,对商务印书馆进行了认真考察。期间,胡适自己虽然再次表示不愿意到商务工作,但当商务征求他对物色的另一个人选—南京高等师范史地部主任刘伯明的意见时,胡适却断然否决。最后,胡适推荐了他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老师王云五来代替自己。虽然王云五曾办过公民书局,有一些出版经验,但商务印书馆高梦旦等人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王云五此人。王云五自学成才,既无留学背景,又无学术成就,但由于是胡适推荐的,商务印书馆也就接受了。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后,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时代,奠定了他在出版史上的地位。同时,胡适考察商务印书馆时的一些建议,也经王云五之手得以落实。商务印书馆能平稳应对“五四”前后来自北大帮的挑战,与商务印书馆当时的掌门人张元济先生与当时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先生有密切的私人之谊有关,也与胡适为商务的出谋划策有关。如果说在蔡元培的牵线下,商务印书馆因此与北大有了良好的合作,与北大帮结下了良好的友谊的话,胡适则直接推动了商务印书馆人事与制度的变更,从而推动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因此,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商务印书馆得到发展的幕后推手,也是商务印书馆发展中的功臣之一。这也难怪1946年,当李拔可代总经理以健康原因提出辞职,张元济又在董事会上提出聘请胡适继任总经理,但后来胡适“返国过沪,表示未能担任”[8]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才推选了朱经农。
胡适出生于1891年,而张元济出生于1867年,比胡适大24岁,可以说是两代人。那胡适与商务印书馆是如何发生关联的?不知情者总以为张元济是通过蔡元培才认识的胡适。张元济与蔡元培是同乡兼同科进士,私交甚密。蔡元培执掌北大后,商务与北大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张元济也在1918年6月专门北上取经,期间多次与胡适见面。此后,张元济与胡适保持了长时间的友谊,诗书唱和,直到1949年后[9]。柳和城先生的《一代学人 一对挚友:张元济与胡适的交往》中,并没有说清张元济与胡适是如何相识的。同样,本书在谈到1921年商务拟邀请胡适来编译所工作时,只说:“1918年北大之行张元济对胡适留下了深刻印象”[10],也容易使人误解为张元济是通过蔡元培才认识胡适的。
其实,张元济最早知道胡适是通过蒋梦麟。蒋梦麟与胡适都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杜威的学生,都是1917年完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后回国。只是蒋梦麟获得了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就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而胡适暂未获得博士学位,且隐瞒了这一事实到北大工作。胡适与蒋梦麟有同校、同门之谊,且维持了终身的友谊。张元济1917年10月29日日记中就有“蒋梦麟来访”的记录,并另起一行,记载了“胡适,字适之,与梦麟甚熟”[11]。这是张元济日记中第一次出现胡适之名。1918年2月2日,张元济日记中又有“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前寄行严信,允千字六元。此连空行在内。与梦翁商,送五十元。”并有“7/2/5复信留稿。7/2/15有回信,谢收到润资五十元。存。”的記载[12]。胡适的这篇文章,后发表在《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五六期,题为《惠施公孙龙之哲学》。该文自序中说:“吾允许张菊生、章行严两先生为《东方》作文而苦不得暇。此次乞假归娶,新婚稍暇,因草此篇……”。可见,此前张元济与胡适已有了往来。二十多天后的3月1日,张元济的日记中又有胡适寄《庄子哲学浅释》稿。7月2日日记中又有下午访胡适的记载。但不知这是不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章行严(章士钊)曾为商务董事,张元济日记中最早出现章士钊是1917年。张元济与他也有多次面谈与书信往来。从1918年2月2日的日记内容来看,可能是张元济托章行严向胡适约过稿。1914年8月,胡适译完都德的小说《柏林之围》后,寄给《甲寅》杂志,顺带也给章士钊写了信。该小说后刊登在1914年11月的《甲寅》第4号,章士钊也在1915年3月14日给胡适回信。从信中询问胡适“近在新陆所治何学”[13]及告诉他在日本的地址可看出,这应是他们交往的开始。此后胡适与章士钊建立了联系。因此,张元济在与蒋梦麟的交谈中对胡适有了了解,并在与章士钊的交谈中加深了印象。
那么,聘请胡适到商务印书馆,是张元济的主意还是高梦旦的主意?或者说是谁先有这一念头?《挑战与机遇》中说:“高梦旦决意辞职,以避贤路,他理想中的人物是胡适。这一想法与张元济不谋而合。”[14]其他的一些出版史著作也持这一观点。如叶再生先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中说:“高梦旦在与张元济商议后,曾南谒梁启超,北访胡适之,商议采取改革措施,力图跟上形势。……高梦旦的北访胡适,导致了王云五进入商务,并受到重用。”[15]台湾地区也是这一说法。王云五的哲嗣王学哲与万鹏程合著的《勇往向前: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1897—2007)》中说:高梦旦“有感于时代的进步与改变,决心为编译所寻找一位合适的接替人选。他看中了提倡科学与民主、主张使用白话文等新文学运动的胡适博士。”[16]但事实上,最早起这个念头的人是张元济,而不是高梦旦。高梦旦只是落实了张元济的这一想法。
据张元济之孙张人凤相告,张元济1919年4月5日曾致信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孙壮,“再,闻大学风潮近日更甚,新旧之争势所难免,并闻人言,胡适之诸君将离去大学,免惹成新旧之争,不知果有其事否?胡君能融贯新旧,至可钦佩。昨与梦翁商,如胡确有暂时韬晦之意,拟邀入本公司办事。在社会上办事,总不至如在大学之易招诽谤。虽有时亦不免有所顾忌,然外界干涉之力总比在北京为轻。此时未得确信,不敢冒昧直陈。闻筱庄先生与胡适翁极熟,可否请其代达此意。倘惠然肯来,敝处极为欢迎。如何之处,鵠候示复。”[17]可见,张元济密切关注着时局,要求商务北京分馆经理孙壮去找陈筱庄探探胡适的口风,如胡适自己想避避风头,请他来商务工作。1919年4月张元济就有了要聘胡适的念头。1919年4月8日,张元济日记中又有“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三百元。”[18]1920年3月8日的日记中又有“余与梦翁谈,拟设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之,请其在京主持。每年约费三万元。试办一年。”[19]1920年3月9日的日记记载:“本日会议席上将拟约胡适之事告知翰卿。”[20]1921年5月15日,张元济在致胡适的信中说:“适之先生惠鉴:高梦翁返沪,询知贵体复元,起居康吉,至为欣慰。敝公司从事编译,学识浅陋,深恐贻误后生。素承不弃,极思借重长才。前月梦翁入都,特托代恳惠临指导,俾免陨越(黑体系引用者加黑)。辱蒙俯允暑假期内先行莅馆。闻讯之下,不胜欢忭,且深望暑假既满,仍能留此主持,俾同人等得常聆教益也。弟来月拟入都一行,或可先在北方相晤。”[21]将上述日记和书信连起来看,显然是张元济提议在先。之所以误认为是高梦旦邀请胡适到商务印书馆的原因,在于胡适1921年4月27日日记中的记载:“高梦旦先生来谈。他这次来京,屡次来谈,力劝我辞去北京大学的事,到商务印书馆去办编辑部。他是那边的编辑主任,因为近来时势所趋,他觉得不能胜任,故要我去帮他的忙”[22]。1936年王云五回忆高梦旦的文章——《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也采用了这一说法:高梦旦“他看中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师胡适之先生,盼望他能够俯就商务的编译所所长。”[23]因此,如果单看胡适的日记,很容易形成是高梦旦产生了聘请胡适的念头。
3 一点疑惑
《挑战与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在书中一开始采用周纵策先生的界定,将“新文化运动”的下限延伸到1930年代末。但作者在书中为了体现延续性,将一些出版事件及其影响延续到1930年代之后。这当然未尝不可。但某种程度上也稀释了本书的研究。尤其是第七章“整理国故与商务古籍印行”,为了说明商务印书馆古籍出版的连续性,将商务1935年的《图书集成初编》和1934—1935年间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1938年的《孤本元明杂剧》都列入了,与全书的议题有点偏离。
商务印书馆的员工构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圈,李家驹曾从“认同”和“交流”两个角度来分析这种以“乡缘、地缘和学统等关系为主要的组织纽带”[24]的群体来如何形成凝聚力。《挑战与机遇》为了说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人员社会关系,作者查找各种资料,做了“表4-1 1915至1925年进入商务编译所部分人员一览表”[25]。该表对了解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具有极大的辅助作用。但一些细节或许仍需注意。如该表将“郑贞文”进入商务印书馆的介绍人填作“高梦旦”,或许为了说明他属于“福建帮”。但根据郑贞文自己的回忆录,他1913年去日本时经过上海,得以认识张元济和高梦旦,中间的介绍人是陈承泽(慎侯)。1918年秋日本毕业回国后进入商务工作,被张元济聘在编译所理化部当编辑[26]。而陈承泽同样是福建人,且是日本留学生。郑贞文回来时他已在商务工作。所以,郑贞文自己的回忆是可靠的。张元济1918年6月12日的日记有“与梦商定,聘用郑贞文,月薪百五十元。”[27]从这一记载中,也看不出是高梦旦先生介绍的。笔者为此询问了张元济先生的贤孙张人凤先生。张人凤先生特意查了他手边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人录”,内有:“郑贞文 福建长乐 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科大学 七年七月来 十年二月去厦门大学 七月复来”。但介绍人、在何部工作、薪水栏都是空格,该名录上没有介绍。同样的还有郑振铎。该书130页同样介绍他是“高梦旦”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的。但根据郑尔康的介绍,郑振铎是“由沈雁冰介绍,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28]。沈雁冰(茅盾)与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会骨干,沈也已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并主编《小说月报》。因此,郑尔康的这一说法也是可信的。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人录”的记载是:“郑振铎 福建长乐 铁路管理学校 十年五月十一日到所 介绍人高梦旦 薪水数陆拾元 国文部”。此处只能存疑。
1921年7月的胡适上海之行,在考察过程中,胡适写了一个报告,但回北大后才完成,后来提交给张元济[29]。仝冠军曾有长文《张元济的改革焦虑与胡适的〈商务印书馆考察报告〉》[30],对这一经过进行了分析。但他也没有说清张元济与胡适如何相熟,也没有说清胡适的《商务印书馆考察报告》原本并没有《商务印书馆考察报告》这一题目。胡适的这一报告是何时交给商务印书馆的呢?《挑战与机遇》中说,1921年“9月下旬,张元济为处理公务上北京,胡适闻讯加紧补做商务的报告,于10月1日上北京饭店看望张元济,当面递交了自己的报告”[31]。但查胡适的日记,1921年10月1日并没有相关的记录。那天,胡适“上课,西哲史讲十八世纪。孟罗博士来大学参观。他的病已好了。下午补做《章实斋年谱》。七时去看孟禄,不遇”[32]。再查张元济日记,该天张元济“给源侄二十元。本日由源侄代向京馆取洋一百元”[33]。也无面见胡适的记载。但《张元济年谱》记载1921年10月1日“胡适送来商务改革报告书”[34];《张元济年谱长编》该天的记载也是“胡适探视先生,送交商务印书馆考察报告书”[35]。这是怎么回事?再查胡适9月30日的日记,上有“补做商务的报告,完。拟明天送交菊生,以完一事”。可见,上述的错误均来自于胡适这一记载。胡适又在该年的10月4日日记中记载:“看张菊生,他股上生一肿毒,前日在德国医院割治,故我去看他的病。他谈及我的报告,说我的提议都是很切实可行的,没有什么大难行的。这确是我的本意;我不曾存什么奢望,故仅针对事实,处处求其异行。”[36]虽然张元济在这天的日记中没有胡适到访的记载,但从他在10月2日日记所记:“是日出中央医院,进德国医院。”[37]胡适该天的记录与张元济的日记能够吻合。根据张元济日记的前后记载,张元济赴京后,9月26日,臀上小疔发作,“竟不能坐,入夜痛甚”[38],但还是忍着疼痛去汤山处理公务。29日回到北京后立即去中央医院看病,并一直住到10月2日。因此,胡适将他的报告送给张元济先生,最合理的时间应该是10月4日,地点也不是北京饭店,而是德国医院。
瑕不掩瑜。《挑战与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在深化了商务印书馆发展历史的同时,也对当今的出版工作具有启迪价值。该书在分析商务印书馆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挑战而得以成功时说:“一个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必须始终保持自我反思的机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商务印书馆成功的秘诀之一也在于此。”[39]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总结,值得我们好好牢记。该书中提及张元济、高梦旦等人在这种大变动中能舍“小我”、着眼于国家与民族未来的“大我”,则体现了那一代出版人的高尚情怀,更值得当今的出版人好好借鉴与学习。(《挑战与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柳和城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9月出版,277页,定价68.0元。)
注 释
[1][7][22]胡适1921年4月27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1919—1922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226
[2]胡适之.高梦旦先生小传[M]//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51
[3][4][10][14][25][31][39]柳和城.挑戰与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42,241,99,129-131,112,42
[5]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42-43
[6][23]王云五.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M]//商务印书馆.1897—1987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与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40,40
[8]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464次会议上的提案[M].//张元济.张元济全集 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44
[9]柳和城先生另有专文《一代学人 一对挚友:张元济与胡适的交往》。见:柳和城.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501-516
[11]张元济1917年10月29日日记。张元济.张元济全集 第6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72
[12]张元济1918年2月2日日记。张元济.张元济全集 第6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23
[13]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3卷[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369
[15]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二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337-338
[16]王学哲,万鹏程.勇往向前: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1897—2007)[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7:66
[17]张元济致孙壮信,已收录于张人凤编的《张元济全集补编》,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8]张元济1919年4月8日日记。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7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0
[19]张元济1920年3月8日日记。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7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92
[20]张元济1920年3月9日日记。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7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93
[21]张元济1921年5月15日致胡适信。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536
[24]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2
[26]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M]// 商务印书馆.1897—1987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与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01
[27]张元济1918年6月12日的日记。张元济.张元济全集 第6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69
[28]郑尔康: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M]//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65
[29]胡适1921年11月14日日记。曹伯言:胡适日记:1919—192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517
[30]仝冠军.张元济的改革焦虑与胡适的《商务印书馆考察报告》 [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3):112-123
[32]胡适1921年10月1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1919—1922[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89
[33]张元济1921年10月1日日记。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7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69
[34]张树年.张元济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13
[35]张人凤,柳和城. 张元济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636
[36]胡适1921年10月4日日记。曹伯言:胡适日记:1919—1922[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91
[37]张元济1921年10月2日日记。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7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69
[38]张元济1921年9月26日日记。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7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68
(收稿日期:2020-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