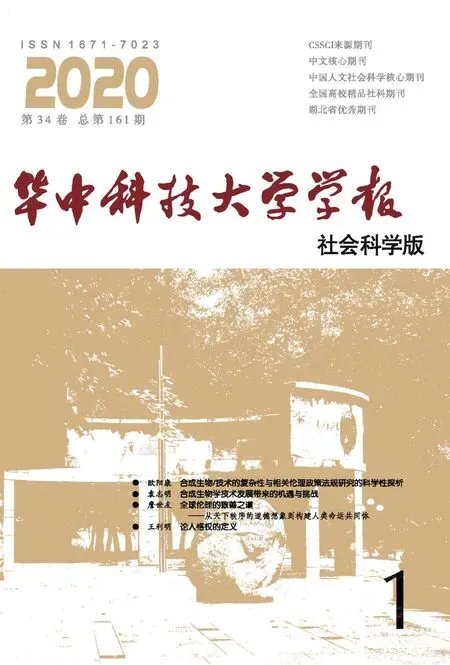道德典范示范效应再检视——一种基于美德伦理学的分析
2020-01-08韩燕丽
韩燕丽
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解释如何促使道德行为者成为一个好人,以及道德行为者怎样获得好人这种状态,美德伦理学也不例外。对于美德伦理学来说,树立道德典范是道德行为者达成好人状态的必经途径。道德典范遵循人性,自愿地给出美德行为,其他道德行为者通过效仿道德典范的行为,选择道德典范的生活方式。换言之,在美德伦理学中,树立道德典范是道德行为者获得美德,拥有美好生活状态,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重要途径。
但是,学界对于道德典范在道德实践中是否存在以及其践行机制一直存有争议。本文旨在对道德典范示范效应相关讨论再检视,通过澄清美德伦理学视域下道德典范的践行机制,对道德典范示范效应的可行性给出阐释,并对伦理学研究方向的转换做出论述。
一、关于道德实践中道德典范是否真正存在的已有讨论
日常道德生活常识似乎默认了道德典范示范效应不是问题。道德实践中存有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道德典范。但是,接受道德典范的存在与承认道德典范的示范效应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的存在不等于对后者的认同。概而观之,学界对道德典范在道德实践中是否存在的讨论,以及道德典范在道德实践中如何有效地发挥典范作用,都有待于进一步澄清。
道德典范在道德实践中是否存在,这一问题首先被表述为道德实践中是否存在真正的道德典范。日常道德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实践中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道德典范,遵循这种逻辑,道德典范的真实性及可模仿性值得怀疑。究其本质,我们怀疑的是道德实践中道德典范的定义与标准,道德因素在道德典范中的限度与高度。即,当我们在宣传以及弘扬道德典范时,我们对道德典范的标准是否存有一致规定,道德典范是否等于道德圣贤,如果不是,道德典范身上所承载的道德因素界限又在哪里。
具体来说,学界关于“道德典范在道德实践中是否存在”这一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认为道德典范不是指真正的道德行为者,而是指善的原型,人们模仿的对象并不是具体的人;一种认为道德圣贤的形象是种虚假存在。
第一种讨论,主要在人格理论指导下对道德典范示范有效性给出讨论。按照人格理论代表人物康德的说法,在现实道德实践中,人们可以模仿的只能是善的原型。而善的原型与道德典范之间总存有裂隙,这样道德典范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的被模仿对象。道德理性以及道德实践才是我们确立道德原则以及践行道德原则的终极因素,只有在实践理性上构成的道德原则,才是我们行动的绝对命令。很多学者追随这一逻辑,对道德典范的有效性给出分析。比如吕耀怀在《道德榜样三要素及其局限》中,以康德对道德典范的分析为例,说明基于道德理性的道德典范不可能成立。他关于康德道德典范的分析,本质上是道德理性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指导道德行为者,他认为我们之所以给出某种道德行为,是因为理性。但这一想法有待商酌。我们依据理性给出道德行为,或者说康德陈述的实践理性,是我们构建某种行为的最终依据,这与道德典范是否可以引导道德行为并不相悖。因为道德典范试图引导我们的道德行为,不等于必须规范我们的行为。也就是说,道德典范的作用仅仅是通过某种具体的道德情景来感化人、影响人,而并未预设道德行为者一定可以促成道德行为的践行。
持有第二种观点的人,指出道德典范与道德圣贤的区别,宣称道德圣贤是一种虚假的存在,我们需要谨慎地将道德圣贤与道德典范分开讨论。这一讨论主要依据当代美德伦理学复兴运动中现代道德哲学家苏珊·沃尔夫(Susan Wolf)的主要理论,她在《道德圣贤》(Moral Saints)一文中,从道德常识出发,刻画出两种道德圣贤类型,仁爱圣贤(loving saint)与理智圣贤(rational saint)。前者指出于仁爱一心一意促进他人幸福而忽略自身福利的圣贤,后者指出于“道德原则的某种其他智识上的理解和承认的圣贤。”[1]79她指出不论是何种圣贤,他们总是可敬而无趣。这种可敬而无趣的道德行为者不应该是我们推崇的道德典范。同时,她通过道德圣贤与道德理论关系的分析,指出现代道德理论对道德圣贤的推崇,事实上是在鼓励人们追求道德上一个可能永远达不到的标准。道德在道德圣贤的生活图景中“不恰当地占据支配地位”“道德倾向于起支配作用的那种方式特别地令人不安,因为它似乎要么要求一种可识别的、人的自我的缺位,要么要求否认这种自我的存在”[1]79。这种分析的意义在于,它扭转了现代道德理论的方向,现代道德理论不应该总是要求人们道德上完美,而应该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多维度、专业维度的完善。苏珊·沃尔夫进一步宣称,“我们不妨把我们考虑何种生活是好生活、我们自己和其他人成为何种人是好的这类问题的观点称作个体完善的观点。”[1]79换言之,我们应该反思,在现代道德理论中,道德以及自我到底应该处于何种位置。
笔者认为道德典范不等于道德圣贤,道德圣贤是一种虚假的存在这种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不完全成立。“以道德圣贤为道德典范并不可能”并不意味着“道德典范不可能”。因为,现实道德生活中道德典范并不等于某些美德伦理学学术讨论中所默认的道德圣贤。道德理论中道德典范与道德圣贤之间的区别,正是我们讨论道德典范有效性的切入点。其具体方式我们将在考察道德实践中道德典范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部分展开分析。
如前所述,目前学界对道德典范有两种不同的界定:第一,道德典范不是具体的人,而是善的原型,所以道德实践中不存在道德典范;第二,道德典范是人,进一步而言,是十全十美的道德圣贤,道德圣贤的形象是一种虚假的存在。上述两种界定都面临着激烈的批评,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道德典范设置了过于严苛的标准。很多学者意识到这点,指出“我们可以体察到,道德苛求理念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它的由来有着传统的、当代的等多方面的印记,它会消减道德榜样的作用,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必须在选树传播学习道德榜样等各个环节,有针对性地减少道德苛求理念的影响,真正使道德榜样的作用不断提升。”[2]13-18换言之,上述问题均由我们设定严格的道德典范标准导致。这种严苛的标准是否合理,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同时,标准严苛并不意味着道德典范没有实际地发挥作用,而是可能意味着,道德典范本来就不是通过那么极端的方式发挥作用的。
另外一种可能是,道德典范既不是善的原型,也不是十全十美的道德圣贤,而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存在。确实存有某种观点认为,实际的道德典范不是道德圣贤,也不是善的原型,而是生活中让人感动的、具体的、鲜活的道德行为者。道德典范并不是没有任何道德瑕疵或者其他问题的人,他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卓越者。这种卓越既表现在专业技能方面的卓越,也表现为道德品质的卓越。比如,社会生活中被普遍赞扬的各行各业的敬业者。这些卓越者身上彰显的美好品质、道德风范、美德力量,促使大家效仿道德行为者而学习美德。道德典范的这种解释,既缓解了自身的道德负担,也增添了自身的真实可靠。我们生活中确实存有不少这样的卓越者、敬业者,他们当之无愧是道德典范。在这种层面上,有学者指出道德典范本身即是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是道德行为者的道德普遍主义的诉求①不少学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比如:廖小平.论道德榜样——对现代社会道德榜样的检视[J],道德与文明,2007(2):74.。换言之,道德典范身上承载的美好品质是值得我们每个道德行为者欲求的目标。这种品质不仅仅局限于道德实践中的品质,而是某一种品质的卓越。
与之类似,还有学者指出,道德典范是现实道德生活的升华,是一种道德理想承载者,这种道德理想的承载由一个个具体的行为得以彰显。“伦理道德就是这样,在人们的平凡生活的一件件小事的感动和不断感动中凝聚成长而来,并在一个个“英雄”的具体行为的示范中得以见证和校正。感动的行为以及其所示范、彰显出来的德性,慢慢影响开来,流传下去,成为风范和传统。”[3]66
在这种解释中,道德典范不是被苛求的道德对象,而是一个个普通的道德行为者。这些普通人用一个个普通的、具体的行为,彰显着美德的力量,形成一种美好的道德风范与良好的社会风尚。进一步推论,这种阐释事实上预设了,道德生活不是行为者的全部生活,道德典范以自身的道德行为为公众树立典范,同时亦有自己的非道德生活。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明确道德典范的定位有极大推动意义。比如,有学者指出“而这一道德理想中所包含的现实道德生活绝非也不可能是道德榜样的道德生活的全部。同时我们应该明白道德生活也绝非道德榜样的全部生活,而只是其生活的一部分。”[4]37遗憾的是,这种推论将道德生活局限于私人领域,明确了道德生活的限度与界限,仅仅就示范而示范,对道德典范如何起到示范作用、如何实现道德理想承载者的过程并未分析。
在现实道德生活中,鲜活的道德行为者可以是我们效仿的道德典范。孔子美德伦理学就将道德典范处理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可能有道德瑕疵的道德行为者,进而试图通过教化、示范,引导其他道德行为者追求美德品质,成为美德行为者。
上述论断与我们对来自于道德实践的道德圣贤推导并不矛盾。现实道德实践中,我们在理解和运用道德典范一词时,预设了道德典范等同于道德圣贤。以孔子美德伦理学中的颜回为例,孔子曾对弟子颜回称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5]85在这一表述中,我们看到颜回持有达观、安贫乐道的美德品质,但孔子并没有表述颜回是十全十美的道德圣贤,只是在历史推演中,颜回被后世推断臆想为道德圣贤。道德圣贤的这层含义是传统文化观点规定的,而不是当代个别专家学者重新赋义的。换言之,在我们历来的道德语境中,道德典范与道德圣贤本来就有着不同的适用场域,只是我们自动忽略了这一区别。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学界已有讨论中将道德典范等同于道德圣贤的相关讨论有失偏颇。
同理类推,我们推崇效仿孔子,但是并不知真实的孔子到底是何等尊容,我们只是从《论语》具体道德语境中知道他的处事原则,比如如何对待朋友,如何对待双亲。换言之,后世真正模仿的是“作为圣贤、被弟子们记载的孔子”,而不是“真实的孔子”。当我们在推崇孔子,或者孔子美德伦理学中所提到的各种道德典范时,我们真正推崇模仿的是美德品质,或者说是美德品质的道德风范。这些被称赞的道德风范,会引起其他道德行为者的情感共鸣,进而促进其他行为者认同并效仿拥有这种道德风范。再进一步,道德行为者自我教化以及教化他人的过程,形成某种礼俗,进而构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范,由此呈现个人的道德风骨和社会道德风尚。
二、道德典范践行机制的已有探讨
如前所述,道德实践中道德典范真实存在,但道德典范在实践中到底如何发挥作用,即道德典范的践行机制,有待进一步阐释。
有学者将道德典范的践行机制表述为道德典范如何发挥作用的叙事陈述,仅仅陈述道德典范对社会良好风气、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作用,而忽略对其实践机制的直接阐释。比如,树立道德典范是执政政府的基本伦理态度,道德典范对社会核心价值观以及整合多元价值观均有促进作用。“对于政府而言,将具有示范意义的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树立为道德榜样,并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实质上表明政府的基本伦理态度,那就是要通过赏善罚恶的道德回报机制鼓励人们弃恶从善,以期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①与之相类似,还有很多论述,比如还有学者对道德典范的价值进行了总结,认为道德典范既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又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积极的道德观),还是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者。“未来理想道德代表着人类社会道德发展和进步的方向,而道德榜样恰恰体现了未来理想道德的基本精神、历史趋势和理想道德人格,并在道德实践中创生着新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引领社会道德风气,是社会理想道德人格的化身和未来新道德的开路先锋。”廖小平.论道德榜样——对现代社会道德榜样的检视[J],道德与文明,2007(2):75.[4]37类似的这种表述,多对道德典范的作用给出正面陈述,但这种表述仅仅停留在叙事陈述,并未直击道德典范示范效应的真正作用方式。
还有学者在描述道德典范作用叙事的基础上,对其践行模式给出一种情感式解读。这种解读认为,道德典范之所以可以在道德实践中发挥作用,是因为道德典范的模范事迹与其他道德行为者产生共情。进而在情感的带动下,道德行为者效仿道德典范的行为。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当代美德伦理学代表人物琳达·扎戈泽波斯基(Linda Zagzebski),她认为叙事与模仿是道德教育与美德培养呈现道德事件发展的重要途径。她以“地图之喻”来比喻承载道德信条与道德实践的道德理论,以美德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来阐释道德典范。具体来说,她认为道德典范之所以可以发挥作用,是因为人们对道德典范的情感钦佩,通过这种情感钦佩可以产生对道德典范行为方式的认同。很多学者将这种理论归为一种语言哲学以及道德心理学的综合统一②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可参考:叶方兴.扎戈泽波斯基的典范主义德性理论[J],哲学动态,2016(6):82-83.。
与之类似,国内学界有学者将上述的情感钦佩表述为人格魅力激发,通过对道德典范人格魅力的渲染,激发道德行为者的道德情感。有学者从美德论视域对道德典范如何可以体现楷模作用给出分析,指出道德典范是理想人格的典范,是群体实现自我价值的承载者,它可以激发人们道德情感(知情意行),促使人们效仿道德典范,同时以道德典范为效仿对象,是处理好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一种个人选择。比如,“从这个意义上,处理好个体与共同体,拥有德性与品格,这些作为人之为人的稳定的道德特质,将以现代人的身份标志,恒久地存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品格中。”[6]93
综上所述,对道德典范作用的叙事论述与实践机制论述并非截然二分,这种论述是否彻底也没有明确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道德典范被当成了一种道德示范的标志物。依赖道德典范,我们似乎可以清晰明了地知道什么样的道德行为是值得做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值得做的。但是这种解释往往引来很多批评,比如,道德典范可以引领社会风气,并不等同于我们会真正按照道德典范号召的那样去做。我们推崇赞扬雷锋同志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现实生活中真正像雷锋同志那样,做到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的同志并不多见。
此外,上述学者们推崇道德典范的角度或对道德典范功效角度的论述,恐怕并不能让人信服。其原因是这种方案没有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当我们在评判道德行为者受道德典范的影响、给出美德行为时,到底什么是真正意义上受到道德典范的影响并无标准。道德典范树立了一个方向或维度,人们只要在这个方向或维度上增进了自己的道德行动,就是受到道德典范的影响。换言之,道德行为者受到道德典范影响的程度与意义并无定论,这二者均需要进一步界定。第二,如果在某个道德情境中,道德行为者完全按照道德典范的标准去行动,并不能保证这一行为完美无瑕。一种让人担心的情况是,现实道德生活中真正的模仿道德典范可能会出现“精神分裂”的恶果。斯托克·迈克尔(Michael Stocker)在《现代伦理理论的分裂症》一文中,曾经指出,“一种好生活的标志就是一个人的动机与其理由、价值观与辩护根据之间的和谐一致。道德行为者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所看重的东西驱动,而是受自己不看重的东西驱动,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这样一种疾病或一类疾病,可以被恰当地称为道德分裂症,因为道德行为者的行为动机与理由处于分离状态。”[7]27那么在某个道德实践情境中,我们按照道德典范的要求或者价值观去行动,如果道德典范与道德行为者的价值观又相左,这就会导致道德行为者的行动理由、动机与价值观、辩护根据之间的不和谐,甚至分裂,这与斯托克指出的“现代伦理理论精神分裂”并无区别。
基于此,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解决道德典范实践机制过程中的上述困境,需要进一步讨论。
三、道德典范践行机制的可能性解读
如前所述,道德典范可以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动的道德行为者充当。在现实道德实践中,一种比较常见的道德典范是孔子伦理学中的君子。郝大维和安乐哲曾对君子这一道德典范示范效应给出如下陈述:“君子既是知的榜样,也是仁的典范。他通过对传统和周围事件的独到认识,进而传播其最优秀的部分,而获得他的典范地位。正如我们讨论思时所谈到的,知并不是有意识地接纳所有的可选择性;虚拟思辨不是它的基础。君子的榜样行为依靠这一事实,即我们因仁而不惑。它的实现不是因为思想和行动选出了一条最好的路,而是在可能之域中达至一个特定的关注点,从而不再有惑。”[8]君子作为道德典范,是道德行为者为人处世的模仿对象。这一模仿对象之所以被选定,是因为他秉持的各种美德品质。值得再一次强调的是,这些具有美德品质的君子不是道德圣贤,也不是不可被模仿的善的原型,而是某些方面的卓越、优秀普通人。换言之,美德不仅仅是仁、义、礼、智、信各种品质,而且是一种卓越、优秀的道德实践能力①对于这一论断的解释,笔者会在另外一篇论文“如何理解孔子伦理学的美德”中,进一步解释。。
此外,孔子美德伦理学对道德典范践行机制给出了一些探索。在孔子美德伦理学看来,美德品质或者说美德风范之所以可以对道德行为者的行为起到引导作用,是因为美德品质带有极其重要的实践理性维度。这种实践理性维度是指孔子仁学及其核心美德品质都带有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和理性态度,这种理性精神以及态度是人们选择美德品质的根本原因。这种理性精神和态度也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无数人“无意识的集体原型”。换言之,孔子伦理学在处理问题时倾向于现实生活中问题的解决,倾向于现实道德实践的引导,而不是理论问题的探究。李泽厚先生曾经就美德品质的这种清醒理性维度给出说明,他指出,“孔孟在后世终于并称,并不偶然。但所有这些派别,无论是孟、荀、庄、韩,又都共同对人生保持着一种清醒、冷静的理知态度,就是说,它们都保存了孔学的实践理性的基本精神。”[9]99他甚至对美德品质的这一实践理性维度给出过这样的论述,“一切都放在实用的理性天平上加以衡量和处理。”[9]99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说,在孔子伦理学中,道德行为者选择道德品质的原因考量中,现实冷静地对待周围世俗传统后,道德品质是一种理性选择。换言之,他们意识到,美德会产生个人福祉或公共福祉。一人有德,则造福身边的小环境,可以处理好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人人有德,则造福整体大环境,比如国家、天下,尽管这一论断有待进一步详细阐述。
我们可以推论,有些道德行为者在模仿以及学习道德典范的行为时,可能并未真正达到完全明晰的道德自觉,没有达到道德圣贤纯粹高度,而是出于理性的考虑给出美德行动。看到道德典范出于美德的行动产生的一些福祉,从冷静的、现实的、合理态度出发,去给出美德行为。尽管这一过程中他并未完全洞悉美德践行机制,但是美德品质在这一过程中被理性地给予重视。换言之,在有些道德行为者看来,美德并不晦涩难懂,美德就是同情互助,就是在实践理性的维度下必须发展的一种美德品质。道德行为者在美德品质实践理性的角度中,对美德的福祉有着清晰认知后才会选择修德,才会选择追寻道德美德。
进一步,孔子美德伦理学研究者默认了,培养美德品质或者说修德是道德行为者获得幸福生活(道)的重要因素。“天有其道,世间万物也各有其道。但万物之德是天道在每种特殊事物中的表现,并使之成为万物之道。”[10]也就是说,孔子美德伦理学认为,万物都承载了天道。对于道德行为者来说,得道就必须要修德,德是道在行为个体中的具体体现。换言之,只有通过修德,道德行为者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君子,才能体现天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11]孔子美德伦理学默认了,具体的道德典范而不是抽象的道德概念可以为道德行为者提供规则。在道德实践中,有些道德行为者具有很好的道德敏感性,在学习道德规则的过程中可以比较敏捷地学习并运用道德规则。有些则相反,不具有很好的道德敏感性或者“权”的能力,在某些道德情景中很难抉择运用何种道德规则。这导致他们很难学习,或者更确切地说很难赞同并加入践行道德规则,所以只能参考道德典范的处事方式,进而逐渐体悟其中的道理。
如果上述推断是正确的,那么一个潜在的推论是,智识上相对平庸的人若是想要获得美好生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行为和情感的表层模仿典范。行为和情感的模仿只是表象,道德行为者效仿并参与道德典范行为的内驱动力是一种实践理性下的综合考量。在此意义上,美德伦理学实质上仍然是一种规范伦理学,就像现代美德伦理学家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指出的那样,美德伦理学仍旧提供一些道德规则,模仿道德典范是洞悉简单道德规则和追求表层福祉的折中产物。
四、余论
美德伦理学认为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以及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似乎已经是学界常识,但是这一常识背后更深层次的意蕴仍有待进一步探究与阐发。就道德典范示范效应而言,这涉及三个问题:道德行为者为何会效仿道德典范给出美德行为;道德行为者效仿的是何种美德品质;道德行为者怎样效仿道德典范来给出美德行为。本文集中处理了前两个问题并指出,美德伦理学认为道德行为者之所以会效仿并参与道德行为者的美德行为,是因为美德行为是道德行为者出于实践理性的考虑。道德行为者之所以效仿、模仿道德典范背后的君子人格,是实践理性综合考量的结果。道德行为者效仿的美德品质,不仅仅是指仁、义、礼、智、信等美德品质,也包含各种其他因素的优秀以及卓越的道德实践能力。
在美德伦理学复兴的中国伦理话语史上,上述结论有着更深层的意义。
这种意义首先表现在我们对道德典范的正确认知,即道德典范示范效应之所以不是问题,是因为道德典范对道德行为者“完美个人”的认同,苏珊·沃尔夫(Susan Wolf)提出的我们要注重区分道德完美(perfectly moral)与完美个人的观点(perfect of view of individual)。这一区分意在指出当我们在回答“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时,务必要明确是成为“道德上的完人”还是“完美的个人”,前者是指在道德实践中将道德的份额无限扩大化,后者是指将行为者的某种品质,比如敬业品质视为人生目标。如果这种区分具有价值,那就意味着我们在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时,在进行道德评价以及道德要求中,道德不应该被分配过多的份额或位置。如果想要拥有幸福人生,或者更有价值更加有意义的生活,那么你必须充分意识到道德上的完美与完美个人的区别。依照威廉姆斯所言,生活是由一个个丰富多维的厚概念组成,你必须拥有道德追求之外其他的追求。我们需要明确,生活中的道德典范确实存在,且可以由一个个鲜活的道德行为者承担,这并不等于道德行为者在生活所有维度都是完美的存在,道德典范不是道德圣贤,只是他或她的某些品质或才能比较优秀、卓越,这种异于常人的某方面品质和卓越的才能是他们异于常人、是他们值得我们敬佩并效仿的主要原因。他们也许有或多或少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他们可能是道德实践中我们身边真实存在的你、我、他,他们平凡却真实,他们可能有一些瑕疵,但抹杀不了他们某一种才能卓越。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对道德行为者某种专业技能优秀、卓越的称赞,是对道德行为者追求完美个人的认可。
如果上述推断是正确的,这一论断还意味着在伦理学角度的另外转变,即从以他人为中心的伦理学转为以道德行为者自身为重心的伦理学。我们通常认为道德是与他人相关的,这点毋庸置疑,但这并不等于将他人在道德中给予过高的位置或份额,与他人相关的仅仅是我们道德生活的一部分。换言之,道德生活应该是关注道德行为者本身,应该是指向道德行为者自身,应该是自律。对于道德行为者而言,道德典范蕴含各种道德要求,但这种道德要求不应该成为我们苛求道德典范的理由。我们应该意识到,道德典范是道德行为者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人格理想,而不是一味地对他者提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