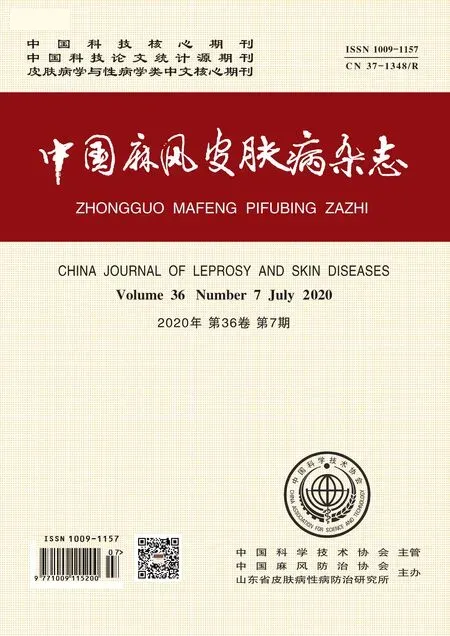瘢痕疙瘩发病机制及术后放疗研究进展
2020-01-08黄晶晶于静萍
黄晶晶 蒋 英 于静萍
1大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大院,116044;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常州,213000
瘢痕疙瘩(keloid disease,KD)是皮肤结缔组织过度增生和透明变性所形成的超出原损伤范围的良性皮肤肿瘤[1],皮肤真皮层中成纤维细胞是创面愈合、瘢痕形成、增生和挛缩的功能性细胞,其增殖、活化和分化的异常直接导致KD形成[2],KD常继发于外伤、感染及术后等,易发生于皮肤高张力或反复受伤部位,如胸骨旁、耳垂、上臂和耳后等区域,但在手掌,阴囊,阴茎和上眼睑较少见,与白种人相比,KD在黄种人和黑种人中常见,发生率分别为5∶1和15∶1[3]。KD存在基因易感性,表观遗传调控作为遗传学分支学科,对基因的表达、调控、遗传等有重要意义。
1 KD的发病机制
1.1 KD相关的表观遗传学机制 表观遗传学指除DNA序列本身改变外的任何基因表达调控机制。一些表观遗传改变,如DNA甲基化,除改变了DNA的结构,还可在细胞减数分裂中遗传,其解释了细胞表型持续改变的一种机制,其他表观遗传机制包括非编码RNA、组蛋白修饰等。表观遗传修饰是近年来研究KD分子机制的一个新领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表观遗传改变可能在诱导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keloid fibroblasts, KFs)的持续激活中发挥重要作用[4]。
1.1.1 DNA的甲基化(DNA methylation) DNA甲基化是最常见的表观遗传修饰,甲基化最常见于胞嘧啶-磷酸-鸟嘌呤(cytosine-phosphate-guanosine, CpG)二核苷酸,是指腺苷蛋氨酸的甲基在DNA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 DNMT)的催化作用下转移到DNA分子胞嘧啶环的5号碳原子上的过程[4]。有学者发现,通过降低DNMT1的活性抑制相关基因的甲基化可影响TGF-β信号通路,从而抑制KFs的增殖、促进其凋亡,因此,DNMT抑制剂有可能成为治疗KD的新选择[5]。Jones等[6]使用人类甲基化芯片对KD及正常皮肤标本进行全基因组分析发现在685个差异的甲基化CPGs中510个甲基化水平降低,175个甲基化水平升高,190个CPGs位于启动子区域,495个在非启动子区域,与癌症甲基化不同,KD低甲基化多于高甲基化,且多位于非启动子区,这种不同为KD表观遗传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1.1.2 非编码RNA(non-coding RNA, ncRNA) 非编码RNA是指不编码蛋白质的RNA,包括rRNA、tRNA、snRNA、snoRNA和miRNA等多种RNA,这些RNA的共同特点是在RNA水平上就能行使各自的生物学功能。近年来针对KD miRNA的研究逐渐开展,miRNA是一组短的非编码RNA,与目标基因互补配对并使该基因沉默,因此,它能负调节靶基因的表达,而miRNA在KD中被解除调节,一些研究人员在KD和正常组织中进行了miRNA表达微阵列芯片分析[7,8],与正常组织相比,KD组织中的miRNA上调或下调。目前有关miRNA-199a-5p、miRNA-21、miRNA-146a、miRNA-1224-5p、miRNA-31、miR-152-5p、miR-152-3p等的研究显示了表观遗传学药物在KD治疗中的潜力[9-11]。
1.2 KD的相关信号通路
1.2.1 TGF-β/Smad信号通路 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定位于染色体19q13.1,其大多数生物学功能是通过与TGF-β受体结合激活Smad细胞通路实现的。具体过程为TGF-β2与II型受体结合,招募并磷酸化TGF-βI型受体,I型受体使 Smad2和Smad3磷酸化,与Smad4结合形成Smad2/3/4复合体聚集于细胞核内,参与靶基因特别是KFs增殖的调控。TGF-β1、TGF-β2被认为伤口纤维化愈合的主要细胞因子,KFs对生长因子的高敏感性被认为与细胞表面受体增多有关[3]。KD有类似于肿瘤的缺氧微环境,研究发现缺氧可通过激活TGF-β/Smad3信号通路诱导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增加真皮成纤维细胞胶原的合成[12]。Wang等[13]发现索拉菲尼可抑制KFsTGF-β1的表达和Smad2/3的磷酸化,进而抑制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胶原合成。Shi等[14]发现IL-10可抑制TGF-β/Smad信号通路导致I型胶原和II型胶原的合成明显减少。TGF-β/Smad信号通路在 KD发病机制中至关重要,该通路信号分子的靶向和免疫治疗将可能在KD的治疗中获得一席之地。
1.2.2 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 TLRs)信号通路 炎性反应是导致KD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TLRs可激活炎性反应,免疫细胞上的TLRs在内源性脂多糖的刺激下启动损伤相关分子模式,介导炎症介质TGF-β、IL-13、IL-4的释放,使TGF-β信号通路持续激活,导致组织的过度纤维化[15]。皮肤损伤后,细胞外高迁移率族蛋白B1诱导TLR2/4介导的成纤维细胞活化,通过ERK1/2和PI3K/AKT途径激活TGF-β 样纤维化作用,最终将导致上皮间质转化样改变,从而引起KD组织中异常的细胞外基质积聚[16]。
1.2.3 mTOR信号通路 mTOR属PI3K蛋白激酶类家族成员,mTOR是细胞生长和增殖的调控因子,处于多个信号通路的交叉点[17]。mTOR活化至少要磷酸化两个位点: p70S6K和4E-BP1,这两个位点的磷酸化会导致乏氧诱导因子-1a (hypoxia-induced factor-1a,HIF-1a)表达上调,HIF-1a参与KD的多种生物学过程,包括上皮间质转化[12]、糖酵解[18]、血管形成[19]等,mTOR信号通路是调控I型胶原蛋白生成和ECM沉积的关键通路[20]。mTOR的活性形式(phospho-mTOR)在KD中过度表达,但在正常皮肤中却没有表达,雷帕霉素和其他mTOR抑制剂可以有效抑制KD角质形成细胞[21]。Syed等[20]发现用mTOR信号通路抑制剂P529能有效的抑制KFs中HIF-1a、Akt、mTOR基因的表达,从而发挥抗瘢痕作用。mTOR抑制剂可抑制KD组织内的多种细胞,临床前的体内外研究表明,抑制mTOR信号通路药物的研发将是未来治疗KD中较值得关注的领域。由此可见,KD的形成是由多种信号分子调控的复杂疾病,因此单一的治疗并不能取得很好的临床效果,容易造成KD的复发。
2 KD的治疗
KD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冷冻治疗、激光治疗及联合治疗等,单一治疗复发率极高,单纯手术切除KD的复发率可高达100%,且复发后通常比原病变更为严重,因此不推荐使用[22,23],有学者尝试了KD的联合治疗方案,许多关于KD的长期回顾性研究说明了手术联合放疗的重要性[24,25],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回顾了9048例治疗过的KD,发现术后放疗的复发率低于单纯放疗(分别为22%和37%,P=0.005),而需要干预的严重并发症低于1%[24]。多项研究表明,放射性同位素高剂量率(high-dose-rate,HDR)近距离照射治疗能有效地预防和治疗KD[25,26],特别是那些对外照射放疗或糖皮质激素药物抵抗的患者,复发率可降至4.7%~21%,手术联合HDR近距离放射治疗明显降低了顽固性KD的复发率,良好的美容效果获得了86.9%的满意率。以上研究结果均表明手术联合放疗能明显降低KD的复发率,缓解患者痛痒症状,证明了术后放疗的有效性。目前对于手术联合放疗治疗KD的机制研究并不多,了解KD术后放疗的机制在制定放疗方案方面至关重要。
2.1 KD的术后放疗机制 目前认为,人类皮肤KD来源的成纤维细胞具有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性,被认为是一种良性皮肤肿瘤[27],Wulandari等[28]也指出KD具有侵袭性生长、不会自发消退、复发率高等肿瘤类疾病的特征,在KD和肿瘤之间最关键的相似之处是它们具有相同的细胞生物能如无氧糖酵解、上皮间质转化等生物学行为,KD微环境和肿瘤类似,因此放疗作为肿瘤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样适用于KD。
放射治疗是利用射线照射组织,在组织细胞内产生次级电子,通过直接或间接电离作用破坏DNA的分子结构,从而抑制细胞的分裂和增殖[29]。放疗抑制KD的机制是多方面的,首先,放疗能抑制术后切口成纤维细胞的迁移、增殖和胶原合成分泌等功能;其次,大量研究表明,炎症是KD形成或复发的重要因素,放射治疗可通过削弱免疫细胞功能和减少功能紊乱的血管形成而强烈抑制炎症反应[30,31];当KD患者单纯接受放射治疗时,皮损发红几乎立即改善,此后KD逐渐变平,且内皮细胞比成纤维细胞对放射线更敏感,因此有理由认为放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抑制血管生成通过防止功能失调的血管形成,减少炎症,从而抑制瘢痕疙瘩的发展起作用的[32,33];最后,电离辐射引起的细胞凋亡也是放射治疗抑制KD的重要机制之一,通过放射治疗可降低局部组织TGF-β的含量,KFs生成减少,细胞外基质和胶原纤维的合成也随之减少,从而抑制KD的复发[34]。2016年Li等[35]首次报道了 KD放疗的相关分子机制,发现mir-21/smad7能促进I型胶原的合成,而电子线照射可以通过改变mir-21/smad7介导的p38活化而减少KD胶原的沉积,但放疗作用于KD的确切分子机制仍不清楚,值得更深入的探究。
2.2 KD术后放疗剂量 因KD患者病情的不同,利用射线治疗KD的有效率也不尽相同,文献报道KD放疗的生物有效剂量(biological effective dose, BED)>30Gy时可将KD的复发率降至10%以下[36],目前认为KD放疗在30 Gy以内是安全照射剂量,几乎没有证据证明KD或周围健康皮肤暴露在30Gy的浅表照射剂量下会癌变[37]。但放射治疗会引起皮肤色素沉着、血管扩张、溃疡等不良反应,因此还是应严格把控放疗的总剂量,采取分割照射模式比单次高剂量照射更可靠,可降低色素沉着和其他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Kal等[38]认为最优化的放疗方案是术后前三天每天以6 Gy放疗,既能达到30 Gy的生物有效剂量,又能有效预防放疗带来的副反应。BED的计算方式为1次照射剂量×照射次数×[1 + 1次照射的剂量/(α/β)],KD组织的α/β值约为10 Gy,而KD术后放疗的α/β值较低(平均为2.8 Gy),因此,在短时间内以高剂量照射KD是有效的,单次5 Gy的剂量可有效的诱导成纤维细胞放射分解[33],王庆国等[39]运用两种不同照射剂量治疗107例KD患者,术后24 h内开始放射治疗,结果显示照射剂量5Gy组的有效率为90.7%,剂量为4Gy组的有效率为66.7%。我国KD临床治疗推荐以下两种放射治疗模式:(1)低分割照射模式。总量控制在17.5~20 Gy/ 4~5次/4~5 d。(2)高分割照射模式。总量为18Gy/2次/1~2周,可尝试用于难治性和高复发性的KD术后复发的预防。2种放射治疗模式间的差异有待于更多临床实践加以证实[40]。也有学者建议根据KD发生部位的不同给于不同的放射治疗模式[41],KD的放疗方案的制定需要综合多因素考虑,包括KD的严重程度、手术方式、部位、易复发情况等。
2.3 KD术后放射源的选择 KD主要发生于真皮,病变部位较为表浅,在放射物质的选择上尚没有统一的标准。常用的放射源主要有3种:①X射线治疗机及各类加速器产生的X射线;②各类加速器产生的电子线、中子、负P介子、质子及重粒子等。③放射性同位素产生的α、β和γ射线。由于X射线穿透力强,对周围组织损伤大,现已基本不用,目前放射性同位素射线及加速器产生的电子线较多用于KD的放疗。
2.3.1 电子线 电子线与光子和传统的深部X射线相比,具有优越的放射物理学特性,电子线在入射面至一定深度范围形成较均匀的剂量分布,而在此深度以后剂量迅速跌落,因此可以用电子线放射治疗取代传统的X射线治疗[42]。Shen等[37]报道用6 或7 MeV电子线对568例患者的834处KD进行放疗,其中826处KD是术后放疗,局控率可达88.25%。用电子线治疗KD,在产生生物学效应的同时,可以有效的保护深部组织及靶区周围组织[43]。
2.3.2 铱-192近距离放射治疗 由于皮肤表面和放射源之间的距离变化,电子线难以对位于不平坦皮肤表面上的KD术后切口施加均匀的放射剂量,而铱-192近距离放射治疗提供了一种对病变进行更集中照射的替代方法。大部分文献报道用铱-192近距离放射治疗术后KD,复发率平均低于15%[44]。钟亚华等[45]分别千伏X线、电子线和铱-192对KD切口进行放射治疗,其有效率分别为81.4%、86.6%、92.7%,但不同放疗射源治疗KD的疗效比较仍需更多的临床研究。Kuribayashi等[46]通过制造与术后切口适形的放射性同位素施源器,即使切口过大或表面不平坦,高剂量率近距离浅表照射治疗仍可提供均匀的辐射剂量,较适用于下颌,肩膀,胸壁和腋下皮肤的切口。近距离放射治疗增加了对正常组织的保护,与之前提到的治疗方法相比,低剂量率(LDR)和高剂量率(HDR)近距离放射治疗都是可耐受和有效的,HDR近距离放射治疗的平均复发率低,优于LDR近距离放射治疗[47]。KD可发生于全身各处皮肤,需要根据KD切口的大小、位置、周边器官情况及医院设备,选择合适的放射源。当然发明结构简单、便于弯曲调整形状、保证射线剂量均匀分布于KD术后切口的新型施源器也将是未来的目标。
2.4 KD术后放疗的时间窗 正常条件下,成纤维细胞的倍增时间是43.5 h;然而,在KD中,其倍增时间减少到29.5 h,快速分裂和增殖的细胞对放射线敏感,为了抵消生长因子的加速繁殖作用,目前推荐术后应尽快对KD开始辅助放疗[33]。Van Leeuwen等[47]对KD术后放疗时间进行系统性回顾分析,发现手术切除KD后7h内开始放疗比24 h后放疗的复发率低,Jiang等[48]6 h内对术后KD行首次放疗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KD切除术后24 h内,切口处的纤维母细胞和不稳定胶原细胞占大部分,对放射线敏感,而纤维母细胞24 h后转化为成纤维细胞,因此术后24h内放疗是治疗瘢痕较好的时间选择[49,50]。
KD放疗后复发和很多因素有关,如KD的大小、部位、手术方式、采用放射源的类型、术后放疗的时间和剂量等,因此,根据不同病人KD术后切口采取合理的放疗方案,进行精准的手术联合放疗是重要的。
3 展望
目前,对KD多采用联合治疗的方法,术后放疗被证明是疗效较好的方法之一。随着对KD发病及放疗机制的深入研究,相信对KD的放射治疗将会进入到针对特定分子生物学靶点进行个体化放疗的阶段,如可通过某一机制来增强KD的放疗敏感性从而达到更好的抑制,KD处于乏氧状态,乏氧会诱导组织产生HIF-α,而乏氧又是放疗抵抗的核心因素,有学者正进行抑制HIF-α信号通路来增加KD放疗敏感性的研究,相信因个体差异实施个性化的精准放疗将成为今后KD放疗的新趋势[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