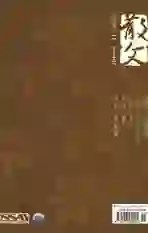植物学家的女儿们
2020-01-07闫文盛
闫文盛
风尘
想象中的旅行总是比脚踏实地的旅行多,这就对了。因为理想始终在徘徊,我们难得居于其上。而旅行最根本的动力也是与旅行的匮乏相关,为了使动止之间如参商,我们才放下一切架子。在旅途中我们尤其是一个过客,不可能始终端庄肃穆。
船长的五六月份
时间收纳盒后来行销海外。船长对我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已到人生的暮年。我不知道他们当初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但是我记得每年的五六月份,当我们集体回到舱中休眠的时刻,许多人都会对愚钝之人突然的灵魂出窍心怀疑惑。收纳盒对我们有一个特设的中止功能,只要按下暂停,无论当时我们的处境如何,都一概会与时间的运行剥离。但当时间恢复的时候,那些被无痕衔接的部分看起来总是如此明亮。那时的日子同现在一样,也是灰突突的。船长来自乡下,他并不喜欢海上的月色。因为夜月思乡,会格外消耗他的疼痛。他的居处总是藤蔓缠绕,如同迷宫,让人恍兮惚兮,总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我们在每年的五六月份的起点和终点见面,交流各自在世间漂泊十月的观感。甚至交换身份。他的信息处理仪在这两个月中同我的持守是混合的。我有时会在梦境中长长地“苏醒”。我知道,这种与休眠背离的状态对我没什么用处。但说不定,通过梦中观察船长,我有可能会发现他每一次诞生时的秘密。舱下即是深深的水源。远古的神兽在轻快地漂游,它们随时都会注视到两个静止如磐石的人。但是,幻觉和水流的侵袭却不会改变什么,因为时间的坚壁是既定的,它们尖利的角骨既无法渗透,久而久之,也就无法忍受。神兽徘徊的水域周围,有一颗水中的小太阳在竟夜不息地照耀着。翩翩作舞的水草是美丽的,它们宁静的身体上书写着独属于它们的静止。我记得愚钝的人灵魂开窍前,总是需要下潜至水域的下方。他们或许比我们休眠的时间更久吧。利用水的浮力冲击自己的身躯,在一片忘形的睡眠的集群中将他们脱离于时间轨道的灵魂打开。很多舱中的画师执迷于实现他们的职业理想。他们分脊剥骨地描绘,将那些神奇的涡流记录下来。舱中的五六月因此成为一个复数,它们是隐蔽的存在因此没有被割裂。造就这一切的原始人已经彻底消失了。后来船长同我谈起他们在海外的业绩时会顺便谈到这一幕。“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失控,秩序总还是有的。”我注视着船长的面孔,每次都在想:他经历了又一次诞生。神兽窥伺他但无法取而代之,那些因为想攻克某种空虚而形成的角骨也从来没有发生作用。水下岁月永远是葱茏的,有着使人浑身精湿却沉湎迷恋的感受。时间收纳盒被发送出去后,我浮出海面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涟漪。但我一直无法确定的是我真正的出处到底是哪里。船长苍老的声音从深深的水源处传来,我看了看他,时间的形影将他脱胎于神兽的角骨凸显在黎明的光亮之中。他总是有着与我们聚散无常的负重。
植物学家的女儿们
他先造出她们的芳唇。当明亮的日色凝聚为晨露中的绿意时,他开始造就她们的身体。他造出一个梦及另一个梦,在茫茫行旅的中途,他造出日色、植物和必需的沟渠。他顺着流水的纹路造她们的躯干,直到一切在她们的峰顶聚拢。女儿们芬芳扑鼻,因此他能安心隐居,造他的新绿。他造那些园圃,以他从远古珍兽中发掘的新元素。一切似乎都是这样的:他所造就的女儿们扎根于那种湿润而沉实的泥土,那些形形色色的藤蔓植物守卫着他为她们开拓的疆域。他研究梦境,但一直找不到它的源头。那种纷繁袭扰的早晨也让他有揪心的苦痛。只有在观察雨水的时刻他才能与自身的宿命贴合。他欣赏着女儿们的生长过程,他必须安心于他的旧梦。他造那些木头机器,与激情洋溢的水母相遇的时候,他的眉毛胡子已经都白了。一只狸猫跳上墙头,他步履平稳地走向它。植物的生长序次在他的心头循环滚动,他担心猫爪损坏园圃。他不急不躁地驱逐着一切外来者。在缓慢流逝的时光中他一天天地老了。植物的节候、雨水的浓度落在他的心头。女儿们芬芳的笑声有时穿透夜幕而来。在布谷鸟聚集的谷地,他造出自己的园圃,女儿们围绕着他盛开。他浇灌她们的蓓蕾形成日月同辉的花朵。他以他明静的心浇灌她们,使她们形成没有阴霾的花朵。
疆域
那擎天的柱子在白色瓷器城的边缘生长,万物被透明地照彻。那些游走的鼠类渐渐停止了生育,它们看到的擎天的柱子可以折射一切被它们所忽略的行为。那小蛇也有明敏的视觉,被擎天的柱子照彻。它们再也无法隐身于任何事物背后。整个城池贯通了天空,那红彤彤的火焰透明的纹理都在万物的注视中绽开。从某个局部的窗口望去,洒水车的厢体透明而又芬芳,它们被某种广大的润湿之物照彻。因为一切打开的物体无法合拢,所以风像瀑布一般四处垂挂下来。那崩裂的山峰也是透明的,只要注視一下它,就能看到其中的化石生出一丝丝虬结纷杂的根部线条。我们的行走和栖息都完全没有隐秘,是透明的。天空的疆域包含那透明生长的垄亩,万物之重使一切倒影类如色泽虚无的繁星。雨水和泥泞也都是透明的,只是为了便于区分,那造物者将它们各自的凝结悬挂在柱子涂饰的最上端。最初的时候,在擎天的柱子周围,漂浮着情愿不死的生物,但随着透明时日的增长,这样的生物已经越来越少。通透的疆域因而渐渐广大,柱子也变得单薄,渐渐趋向宁静和空旷。在一切注视都消失的那天,白色的大城揭开了它隆重的回声嘹亮的帷幕。无际的环形堡垒都消失了,风像瀑布一般涌来。那划分开天地的手臂现在看起来也像一个虚影。那在无知觉中孶生的小小幻虫从一个未知的端口攀爬上来,风像瀑布涌动,将它冲向透明天空中云霓的深处。整个疆域里的风涌动,将一切悬浮的尘土吹向天空中云霓的深处。此刻潇潇雨歇,白色的飞扬的宁静弥漫在整个疆域里透明的云霓的深处。
回声
在敞着的窗子那里,我看到你。多少年世事飘摇,你一直在那里。走远了的只是那些流萤,但你的火焰茁壮。初次看到你的时候是在高高的楼顶,窗子同样敞开。浮云悬挂在空阔之处,看似并不着形,也不着力。我们缄默无声。饥饿的漏斗声穿透云层,在动荡的街头落下。在窗子那里,戏剧开始上演了。欢乐的吟诵洞彻了你的肺腑。我知道你的悲欣。但落叶松的叶子变黄的时候,窗子那里已经阒寂无声。我写了几个字在你曾经伫立的画幅上面。你看看那些云层多好啊,袅娜的更鼓声混合着炊烟升上去了;你亲耳聆听的那些云层多好啊。房子里的气味大极了,当这里变得空荡时,那些不知所云的气味会更加浓重,如久远的旧物件。活着而能记忆这些多好啊。你不用过意不去。我时时刻刻都知道你曾经站在那里。晓星夜月,你别无蹉跎之处。你也别无风声。只是当这里的一切被翻过了一页,骏马奔腾,草木凋枯,我才在你露宿的时空中刻了一块石头。睡在赤裸大地上的,就是你啊。我记得起初日出红似火,而你在高高的窗子下,容颜如古。我呼唤过你的名字,你没有应声。现在我不再呼唤你了。那里一座钟楼上,铭刻着你最早的名字。我记忆中最明晰无误的,就是你的名字。
恐龙
我们智力的顶点,便是死亡。在那些荒郊野外,草木凋零的顶点与亡者的坟茔融合为一物。如果在最早的晨曦中有车辆驰过,你应该会发现在它的车辕上驮着累壞了的恐龙。垮掉的恐龙的脊骨就生长在车辕上。
你的言语声不能将睡着的恐龙惊动。晨曦中的露水和生长期的落花都空荡荡的。蚁群飘过田园,它们以最小的力量扇动着微风。穿过那些树木组成的南方林带,你有时会看到一个驯兽的老人在描绘他亡妻的面容。
你不知道的消散就长在那里。沉着地种树的老人和大声驯兽的老人都深入山脉腹地,与上古的生命、造物者遗留在溪流中造山的器具融合为一物。你看过了那些大大小小的花脉,都是存荣没哀的意思,都是生死无穷已的意思。
沿着一条缓坡北上,直到群山之巅。水珍珠在雾气中长出来,会飞的蛾子落在泥土的深处,使它们的亡魂长出来。阳光之下总会有生物往还,你瞧见北山愚公橘黄色的锄柄了吗?恐龙在他的身后筑巢,他们共同播植着春草。
没有一个人会成为他们的整体。有很多柴火也变得阴潮、落寞。也没有烈士烽火。在最西端的大河空阔处,年轻的龙王沐浴表里,看起来如英姿飒爽的俊杰。
恐龙飞过无人的大地时会发出噗噗噗的破空之声。不存在的聆听就种在你的心里。在许多年里,老迈的万物的鬼魂也都不出来活动。只有恐龙飞过无人的大地时所发出“噗噗噗”的破空之声。
那些袖手藏匿龙衣的道人还没有出世。但是,如果恐龙的速度过快,会打乱生死的节奏冲撞那莫名的幻觉。有时的确会有斟酌着离开地表的人性虫子。不要同它们大声说话。它们都是人类的旧物。
早晨也会与黄昏暮雨交织在一起。最初只是淅淅沥沥地播洒,后来才改成了大雨倾盆。龙山上的腾腾雾气,正跃跃欲试地长成。还有,锣鼓喧天的幻觉也会惊动恐龙。总之,它们并没有一次飞行的路线是重复的。它们的飞行都是唯一的,单独的,冷静的。
显影
很多人的生存和梦境都是一个整体。尽管只是局部腐烂,但也不会比时间所寓示的更多或者更少。在完全意义上的造物者看来,你也只好如此,因为风雷有限,它不可能递给你所有的寓言之书。将幻觉和事物归拢一处,就像储藏食物一般,你既能够满怀信任,又总是不失小心地这里捏捏,那里看看——你瞧,这是只有建筑师才能进去的屋子。他把整个设计的归类等同于时间的流逝。自始至终,他就住在那里啃噬着。木头上的血痕也是他写下的。他觊觎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细小之物,但驿站里的工头却是大度的。你根本不需要同他接近,因为万物自有机理。建筑师的名姓已经流入忘川,但是整体看来,你曲折的散步也能触发他设下的机关。明白一个人的生活,理解他死亡和文明的方式,都有助于你形成新的道路。在那里种上绿树,躬身测量那里的海拔、湿度和气温变化——环抱着你所爱和所失去的——都有助于你的未来完成。但是,在雨水经过悬崖降落在岸的时候,你应该站定位置为你必然的死亡默哀。那些生物芬芳馥郁,你的声音既悦耳动听,又富于出色的见解,那么,一切无所见的便在你的心里显影。
光芒的弧度
朗读也是一种沉睡,是提花行路。是秘密的思忖来世,而那些已然记录成稿的孤独的行旅泛着光芒。光芒的弧度如此突出。
朗读是信念的洋溢,是生存的能力和游戏。朗读使人困倦地想到未来与星河。朗读是词语的自足。不足为外人道也。
仅仅是词语的自足吗?反复的惊醒、入寐与困倦。朗读是驾驶拖拉机的人日日体验到的“突突”之声。而夕阳晚月,不过是无尽的重复而已。
朗读是爱的火焰吗?那么荆棘中长出的花鸟也是爱的火焰吗?那么那密密麻麻惆怅如许的今生就是爱的火焰吗?
我们活着并被朗读裹挟,就是爱的火焰吗?
清澈
我似乎已经过了河上的桥。我挪动脚步在我所在的此处。黎明的风声与别处一样,也与我的爱等同。如果我的梦就止于山巅的寂静,那我的未来与我的此刻都不会悬浮。我对于寂静和悬浮的观念是颠倒的。我对于未来和此刻的观念是颠倒的。但是没有人回应的天空也并非只是神的居所。它空空荡荡的。在并无一只鸟儿飞过的阴雨的天空,我已经盘旋而上的心也是空空荡荡的。每个梦境里其实都有山巅,但它多皱的曲折之上不可栖止。梦境终究得离开,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购买过一切我所祈愿的事物。我以我卑微而虔诚的心挽回它们的伤悲。我购买过一切我虚妄的热情。在渐渐冷静下来的早晨,我路过那个异域的城。我从未去过那里,但我总是路过。它苦涩的墙头长满了枯萎的禾木。如果是仲春三月天气返晴,我还能带着我逃脱了危险的梦一同前往祭奠,并种下自己梦寐的种子。我起用我的日常岁月并将它置于前一年度的融雪之上。我觉得自己没有返回。我只是时刻都在命运的左边。我时刻都能看见那些融雪。它与我的约期不变。
但是我最珍贵的清澈的东西在哪里?我已经不能完整地取回我的病症。我有时会感到身体局部的疼痛。我有时举步维艰。有时,我会悲悯地注视你。我从不修饰。无论时间是什么,我都知道在它最沉默的钟鼓中有太多负重的生命诞生。我们现在就到那里了。我们现在就在国家的边疆。那无处不在的流离也是珍珠。我们在外面但没有真正的离开故土的感觉。我们的故土,有时也与陌生的异域交错难分。
这个季节里一定有太多的珍珠手环。它拘禁你的力量始终是不变的。有时我们养育它是为了缓解心头的疼痛。有时泥土里也会露出一种蓬勃的时间的行踪。有时我们就耽于这种无法明晰的错误。它的存在和孕育珍珠的环境是不可分辨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发掘珍珠。埋葬他们的,是奋发的世间里越来越陌生的身怀异禀的人。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