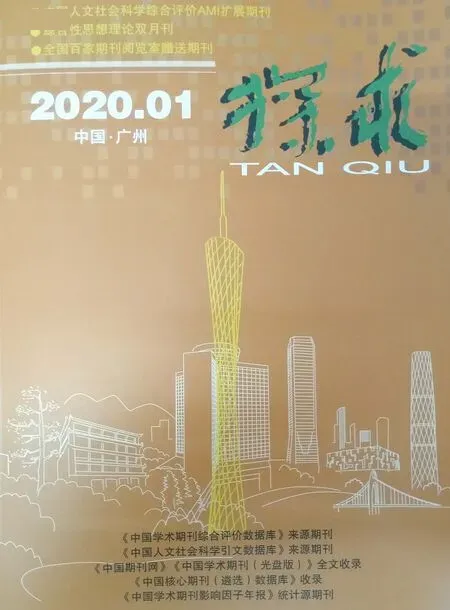广州乞巧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试论民间、学者与地方政府的相互作用
2020-01-07曾应枫
□ 曾应枫
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民间又称“乞巧节”、女儿节,广东人俗称“拜七姐”或称“摆七娘”。这个民俗节庆源于一个传说,那就是传诵上千年的牛郎与织女、天上与人间悲欢离合的神话故事,节俗传颂着故事,故事印证着节庆,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祖国两岸三地,在日本、韩国,“七夕”节流传下来。广州地区过七夕与其他地区最大的区别是,广州人将一个久远的民间传说演化为“摆七夕”,女子们将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幸福婚姻爱情的向往化为具体的行动,用巧手做出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摆出一台台小巧玲珑的供案,娱神娱己,丰富的内涵难以言说。2001年,广州各大媒体报导湮没了近半个世纪的“摆七娘”复苏了。2005年,天河区办起广州乞巧文化节。近二十年来,经过天河区、黄埔区、番禺区、荔湾区等民众的努力,乞巧节成为广州地区民俗文化的名片。本文以广州乞巧民俗文化近二十年发展为例,对珠村乞巧文化节与黄埔区、番禺区乞巧文化节的实地调查和多年学术探索,试图探讨地方民俗文化与民间工艺的发展,分析如何处理民间社团、专家学者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使民俗文化与民间工艺共享与发展。
一、民间力量、文化学者在乞巧复苏中的价值肯定
对广州乞巧文化的认知得从2001年初说起,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收到一份来自天河区沙河文化站的请柬,邀请协会的学人去珠村看看“摆七娘”。七月初六傍晚,在珠村村民潘剑明的带领下,一众学人进入该村的以良潘公祠。一进祠堂,眼前的景象只能用“惊艳”二字来形容,几张乒乓球桌拼成的大供案摆着琳琅满目、似真似假的巧制工艺品,有三支半米多高的芝麻梅花香,还有七个“斋塔”,两边摆有七姐秧和拜仙菜,中央有个珠村牌坊,里面摆有牛郎与织女在“鹊桥相会”的造型,还有“花木兰巡营”等一套套传统故事人物及众多工艺花果。四周摆着各式谷花、米花、瓜子壳花、珠花、珠片花等等,展品小巧而精美,目不睱接。眼前的景物,正如欧阳山在小说《三家巷》中对广州民国七夕乞巧节的描写,学者们不禁兴奋道:“广州乞巧回来了!”
南粤大地是什么时候有乞巧的?有南宋诗人刘克庄(1187—1269)诗作为证:“瓜果跽拳祝,喉罗朴卖声,粤人重巧夕,灯火到天明。”该诗写出了南宋粤人通宵乞巧的情景。古代人过七夕(也称拜七姐或摆七娘)是广州地区(包括城乡)传统的女儿节,可近代以来,受到了三次猛烈打压甚至禁毁。第一次是民国时期消除封建迷信行动,第二次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四清”运动,第三次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每次政治运动中乞巧节都以封建迷信为由被扫荡。直到1998年,国内吹起了改革开放的春风,珠村以良潘公祠的几位老人谢丽霞、黄彩余、陈宝好等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情怀,相约一起,悄悄地在家中“做乞巧摆七娘”。眼看着一盆盆小巧的五谷花在手下盛放,一个个戏剧小人在眼前栩栩如生,一台乞巧供案在眼前重现,她们很高兴,却不敢声张,怕重蹈之前被人践踏的悲剧,只是局限于在村中姐妹间观赏。1999年,她们得知邻近的黄埔区的横沙村、茅岗村也在悄悄摆七夕,便约上几个老姐妹,在夜深人静时到邻近的黄埔几个村落去看看。到了2001年,珠村东南社的黄彩余、陈宝好、谢丽霞等老巧姐成立七娘会,贴街招(海报)筹款,村中妇女争相参与,并打算将“摆七娘”搬到村中宗祠“以良潘公祠”。声势一大,惊动了本是局外人的潘剑明,他对母亲及老巧姐如此热心的乞巧民俗从此上了心,通过农民作者姚瑞英等,邀请了广东省、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学者前来珠村睇七娘,希望得到学者们的肯定。
经过考察,学者们认为是时候拨乱反正,为乞巧节的恢复摇旗呐喊;还要动员社会的力量,借用传媒的强大优势,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参与。于是学者们分头找资料写文章,通知广州地区各大传媒,将珠村复活乞巧节的信息广为传播。
2001年农历七月初七,广州《羊城晚报》率先刊登了文史学者龚伯洪在“晚会”版写的《关灯穿针来乞巧》一文,紧接着几天,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广州电视台、广东电视台的记者们纷纷下到珠村采访,接着几天,在《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信息时报》等要闻版上图文并茂地大幅刊登了《东圃又见“七姐诞”》《“七娘会”又回来了》《摆七娘,有意思》等报道。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从此村干部及区有关部门开始关注珠村乞巧节。2001年七夕期间,闻风前来看珠村祠堂看乞巧的人员达一万多人。湮没了近半个世纪的广州乞巧习俗,从此进入大众视野。
此后,珠村“摆七娘”蓬勃发展起来了。2002年,珠村东南社的老巧姐谢丽霞出资赞助制作了专供“摆七娘”的妇女统一服装,整齐华丽的服饰使珠村的巧姐、巧婆们亮丽了许多,前来观看乞巧的人们争相与她们合影,镜头前的巧姐巧婆们的神情已从当年的惶恐转化为自信。《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信息时报》等图文并茂作了大篇报道,广州近代史博物馆派人到珠村摄像,直到今天,2002年的那张巧婆巧姐们的合影仍摆放在珠村的宣传栏上,成为“经典”。2002年,由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牵线,珠村的乞巧摆到了广州西关仁威庙,引起了轰动,勾起了许多老西关人的回忆。2003年,由珠村村民谢丽霞、潘剑明母子制作的乞巧微型工艺品《喝水不忘挖井人》、《航天火箭扬国威》被推荐参加广州市政府的文艺评奖,获得了“第四届广州文艺奖二等奖”。
经过民众和学者的努力,广州市委宣传部批准,从2005年起,珠村乞巧从自娱自乐的七夕民间节日提升为“广州乞巧文化节”,成为天河区及广州市民俗文化的一个品牌。天河区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区委宣传部主办每年乞巧节,珠村村委从此每年分别对每台“大七娘”给予1万元的资助。珠村文化站还整理了礼拜七娘仪式,进行对外展示。从2005年至2015年“广州乞巧文化节”在珠村举行开幕式,时任省、市、区的领导出席开幕式,媒体蜂拥而至,珠村乞巧习俗成为扬名海内外的广州乞巧文化品牌。
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先生对此评价道:“天河乞巧遗产在濒危状态下取得抢救性保护的成功经验,在充分尊重广大民众保护乞巧文化遗产的主体地位前提下,全力以赴支持民众(特别是妇女)保存系统完整的乞巧文化传承机制;同时积极鼓励民众(特别是妇女)与当地专家相结合,广泛传播丰富多彩的乞巧传统‘文化记忆’和‘手工技艺’。”[1]在此,乌丙安先生提到了广州乞巧文化复兴的民间主体、社团的专家学者和地方部门在传统文化发展中的主要因素。
二、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与民间力量合力创佳绩
2004年以政府(文化部)为主导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在全国各省有序地付诸实施。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11年,以珠村为代表的广州乞巧习俗成功入选国家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珠村乞巧文化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广州周边乡村的乞巧文化,广州乞巧民俗文化的空间得到拓展。
番禺凌边村的乞巧历史久远,除了“文化大革命”那几年,一直都有摆七夕。黄埔横沙村的巧姐巧艺手工早就有名的。历史上的乞巧文化含有斗巧、赛巧成份,再一溯源,现分属广州天河、黄埔、番禺几个行政区的村落,清代以降都隶属番禺县,黄埔区横沙村与珠村还同属番禺鹿步司管辖。珠村与黄埔的横沙乡很近,从田野小路走,步行约半小时。为推动广州市乞巧文化蓬勃开展,广州市民协与天河区政府共同在珠村举办“广州乞巧赛艺会”。2008年,“广州乞巧文化节”首次将天河区、黄埔区、番禺区和荔湾区的乞巧精品汇聚珠村,集中到珠村小学,同台“摆七娘”,共同打造广州乞巧文化品牌,使广州乞巧文化节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广州”乞巧节。此届乞巧作品创意大赛以“天上人间,情缘七夕”为主题,结合牛郎织女的传说,由各村巧姐发挥创意,制作相关作品参赛。黄埔区的刺绣品和农耕文化、珠村的牌坊、车陂村的纸通花、番禺潭山村的屈大均主题场景、荔枝湾的风情文化图等精致乞巧贡案令人目不暇接。除了传统的乞巧工艺,首次动员大学生、小学生、幼儿园小朋友加入到乞巧工艺创新制作的行列中,既有传统乞巧摆制的腊梅花、水果、鹊桥、人物等,也有用废旧材料如汽水罐、泡沫、废纸盒等制作的工艺品。
此后,在每年珠村举行的乞巧文化节,都举行“乞巧赛艺会”,以集体奖励为主,让珠村与黄埔区、番禺区的民间乞巧联合体有良好的交流平台,促进技艺与文化的发展。
黄埔区的横沙村、茅岗村等团队每年铆足了劲,在创作题材、材质、技艺等方面有所创新,展示的七夕供案特别吸引人。番禺区潭山村的乞巧作品更是突出,2010年8月七夕在东莞市望牛墩镇举办的全国首届七夕风情文化艺术节,番禺潭山村制作的大型立体乞巧供案《长生殿》获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2014年七夕,第十届广州乞巧文化节的“赛艺会”吸引了广州天河区、黄埔区、番禺区,广东湛江市、东莞市,还有台湾台南市等地乞巧人前来珠村,15台供案齐聚珠村“斗巧”,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乞巧供案表现了强烈的地域特色。黄埔区带来了4台乞巧供案参展,数量最多,展示雄厚的创作实力。天河区车陂村巧手造的小型龙舟很有特色,手艺人李光华把传统纸通工艺重新恢复,造出一件件作品来参展斗巧。来自湛江的供案,用的是贝壳、螺等海洋元素,作品展示本地非遗项目如人龙、醒狮、石狗、雄鹰等。来自台湾台南的供案展示当地的十六岁成年礼习俗及一台“七娘妈塔”。珠村只摆2台贡案参展,其他的6台在村里各社区祠堂摆。15台乞巧作品亮相斗巧,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前来观看,各大传媒前来争相报道,此次大赛还为在珠村筹办“广州乞巧博物馆”提供了丰富的展品。
2014年,是广州乞巧文化节举办第十个年头,广州乞巧文化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天河区政府在珠村的文化设施加大投入,建起七夕广场、七夕公园,开通了七夕路,公交车进村等,珠村广州乞巧文化节被评为“全省群众性文化活动优秀品牌”,珠村分别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中国乞巧文化艺术之乡”;广州黄埔区被评为“广东乞巧文化之乡”;广州番禺的潭山也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之乡”。这些佳绩的创造,是由地方政府支持、专家学者指导、民间团体共同努力的成果。时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乌丙安先生2014年参加广州乞巧文化节开幕式,在讲话中提到:“广州市和天河区倾力把广州乞巧文化节成功举办了十届,使它成为岭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民俗节庆文化空间保护与发展的最佳典范。对港、澳、台乃至全球华人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传承与发展的几种模式
回顾广州各区十来年的乞巧文化发展,各地区都在探求文化传承路上的可持续发展,既可保持蓬勃生机,也可保持传统文化的原真性一面,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一)从政府主导转到公司介入
以珠村乞巧文化为例,经过十多年的打造,政府有关部门主导的乞巧文化品牌相当成熟。每年的乞巧文化节,既有在村中姓氏祠堂与会所的传统供案,有珠村小学的传承作品,还有层出不穷的热点供媒体报导。近年来,似乎有点事与愿违,政府有关部门想方设法把乞巧摆到闹市中心的正佳广场甚至广州塔内,可珠村的乞巧人却提不上劲。也许是因为乞巧的民间主力军老了,有的还故去,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做乞巧的人越来越少,村民的积极性远没有前些年高涨。在每年举行的乞巧大赛中,珠村乞巧作品的创意并不多。华南农业大学2016级城乡规划学院林淑敏等同学近年深入珠村,撰写的《原真性视觉下岭南乞巧民俗文化的传承状态——基于广州珠村的调查研究》也尖锐地提出珠村人的乞巧热在减退这一问题,并引用珠村村民、乞巧传承人潘先生的话:“从2014年开始,珠村的旅游热潮就慢慢退却了,”[3]潘先生用“少得可怜”来强调,可见珠村游客数量减少这一现状也值得深思。据林淑敏等同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参与乞巧节活动的主要人群是小孩、中年人与老年人,而青年人参与度较低。参与活动的居民中有38%的人是因为对乞巧表演活动感兴趣,而因乞巧习俗文化来参与的村民仅占14%。可见,部分居民对于乞巧的文化认同感并不强烈,特别是年轻一辈。而珠村是“城中村”,大部分居民为外来务工者也是原因之一。
近年广州(珠村)乞巧文化节的组办政府也由先前直接主导到退出,发配给参与投标的文化公司。公司考虑首先是市场效益,他们努力想把乞巧工艺品打造成文化产业,把创意产品推广出去,赛艺会着重于搞文创产品设计大赛。请看“2019·广州乞巧文化节赛巧会民间工艺大赛”赛制规定:“本次大赛均以个人身份报名参加,不接受2人以上的集体作品报名;也不接受集体供案参赛。”大赛制定者完全是外行,传统的赛巧会成了工艺大赛,传统的集体供案作品不参赛,只要个体的创意作品。这真让一向从事传统乞巧的村民无所适从。好不容易做了些他们认为有创意的作品去参展,与其他的作品同台相比,就分出高下了,尽管珠村作为主办方终会有一作品会获金奖,但其作品含金量却被其他同行非议。
乞巧文化是民俗文化,历年是巧姐们集体制作的供案摆在村中祠堂祭拜七姐。近年来主导的文化公司把乞巧赛艺会的主会场搬出珠村,到广州市地标的广州塔或天河商业中心正佳广场的一个角落,目的是向更多市民展示乞巧文化的丰富性、活动的趣味性,但效果还不如在本村展示看的人多。后来这几年,就连在珠村七夕广场举行的广州乞巧文化节的开幕式地点也改到大剧场举行,节目让文化公司承包给某文艺团体,除了保留有领导讲话、颁奖仪式,启动仪式,开幕式成了场文艺秀,只有少数村民代表能参加开幕式。
珠村乞巧的问题,乌丙安先生似乎早有预见,他曾提出:“我于2014年到广州市天河区参加第十届广州乞巧文化节,我在会上提出要努力修复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传播机制,让文化生态整体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相结合,逐渐从各式各样不定期的非遗活态展演或定点博览,陆陆续续都能够达到自然而然地回归民间。”
(二)文化部门依靠学者与基层骨干一起努力
相比之下,黄埔区和番禺区的乞巧文化节一直扎根于村落祠堂文化的土壤上。近十年来,黄埔区通过举办每年一度的乞巧文化节,分别在12条村挖掘了一大批热心的乞巧文化传承人,乞巧活动得到了有效的继承和发展。这里必须要提到黄埔区民间文艺的带头人黄应丰,二十年来,他为黄埔乞巧的发展尽心尽力,得到区政府的重视与乡村巧姐们的尊重。黄埔茅岗村民恢复摆七娘活动始于1988年,说来比珠村还早十年,当时没有张扬,后来也没有评上省市的非遗项目,可该村年年七夕坚持在本村“摆七姐”。2004年9月,广东省文联、省民协举办的第一届“广东民间工艺精品展”,黄应丰组织茅岗村制作的工艺水果和花卉、横沙村制作的珠绣和微缩横沙书香街模型等20多件乞巧作品参加此次展览。这是她们的乞巧作品首次在省工艺展览上亮相。此后几届“广州民俗文化艺术节暨黄埔‘波罗诞’千年庙会”,乞巧供案也摆进南海神庙,为黄埔巧姐的赛艺会搭建多方平台。
黄埔摆乞巧的村落众多,巧姐的人数也多,队伍相对年轻,手工技艺精良。每年黄埔区的乞巧文化节12个祠堂都摆上乞巧供案,还组织优秀作品参加市乞巧赛艺会,年年获得的奖项最多。前十年,黄埔区文化经费投入与天河区相差很远。近年,经过民间团体、文化学者和文化部门的共同努力,黄埔区赶上来了。从原来只有二三千元经费,到如今,黄埔区文化馆每年乞巧节分别给12个姓氏祠堂和一间传承小学的资金是1万元,另每年区出资10万元举办区乞巧节大赛,以各村姓氏祠堂为参展单位,奖金最多是集体供案,也奖励有创意的个人作品,让茅岗村、横沙村、庙头村、双岗村等12个姓氏祠堂的七娘会的人员发挥积极性,创作好作品参与广州乞巧文化节。
(三)来自民间,立足本村
番禺化龙镇潭山村和凌边村的乞巧文化发展模式是从民间来,到民间去。资金是村委资助,依靠民间做,让村民自娱自乐。潭山村委每年的七夕贡案是在本村的许氏大宗祠里摆,乞巧贡案之大令人惊叹,乞巧公仔之多令人击节。一个祠堂贡案分设几条长桌,每条长桌有23米长,1.2米宽,一条长桌又由若干张桌子组成,全都放上了密密麻麻的乞巧工艺品,每一台就是一个微缩戏台,包括有古代戏剧故事人物及当代新创造的主题场景。这些作品大多出村中巧哥许冠其之手。七夕期间,村里不但有贡台摆设,还搭棚做戏,邀请亲朋好友前来,热闹得很。潭山村民相信有花自然香,摆七夕供案是自己喜欢的事,要坚持下去。每年到村里看乞巧的人很多,从早到晚高音喇叭开着,从祠堂到村里都是人,非常热闹。
番禺石碁镇凌边村的乞巧低调而绚丽。二三百年来,乞巧节成为凌边村民最踊跃参与的民俗节庆。番禺凌边村1979年就恢复摆七夕了,可说是广州地区最早恢复乞巧节,原因是该村党支部书记凌就威与妻子都是制作七夕工艺的好手,由于他们“根正苗红”,带动村民摆乞巧也成了团结村民、促进生产的好由头。1992年七夕,凌边人的摆乞巧就有创新,将摆在祠堂里的乞巧工艺品搬到一辆辆板车巡游,创新了乞巧巡游形式。七夕游行中,队伍中有扮演小喜鹊,或扮成七仙女和牛郎,边游行边表演《银河会》歌舞,在村里足足游了两个小时。到晚上,村里请人前来演场大戏(粤剧)庆贺。老书记凌就威去世后,新一代的村委接着担起来,让每年乞巧节继续,因为乞巧节是凌边人自己的节日。那几天,村民呼朋唤友到村里看乞巧,吃大餐看大戏,自娱自乐。近年凌边人很少拿作品到市参展参赛,前些年拿过作品来参赛,作品很不错,但获奖名额有限,总拿不到大奖,以后他们便不出去了,认为摆乞巧是自己喜欢的事,在村里摆照样有人来看。乞巧有村委支持,给每个祠堂2千元补贴,钱不多,他们就因地制宜去做。村组织七夕大赛另有奖金,村委还将一台台乞巧供案摆在凌边小学礼堂,方便人们集中观赏。每年的七夕,专程到凌边村看乞巧的人一如既往地多。
四、从“地方群体”到“文化共同体”
综观二十年来,广州三地(天河珠村、黄埔、番禺)乞巧文化的发展,地方民俗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三个平台,政府部门、文化学者与民间群体的相互配合与支持。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遗”命名的强调:“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即要尊重社区文化的原有历史文化脉络,也包括对民间信仰与岁时节庆习俗的沿袭。哪些地方部门做好了,那里的地方文化就发达。发展地方的乞巧文化,政府部门不仅是一个指挥者、支持者,更应该是推动者,通过文化学者传播,从“地方群体”发展到“文化共同体”,让人们获得认同感与幸福感。客观地讲,前十年做得不错,后几年,情况有所改变,角色有所变换,这就需要各方群体在行动上,从“利益相关者”转向“多元行动方”的角度,确立“文化共同体”的观念。
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乞巧民俗与手工技艺的发展要注重培养传承人。要将其文化内涵与技艺价值保护好,不可把民俗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方式,变成单纯的手工创意大赛。
第二,合理控制行政力量在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的比重。大部分的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论是传统节日还是传统仪式,几乎都是约定俗成并在民间自主传承的,政府的引导、鼓励和调节固然能起到积极作用,但必须把握好度。
第三,正确处理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商业开发的关系。这有一个度,要以维持民俗原有风貌来开展相关活动,既为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展示机会,又促使其与文化传统相承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动态历程,会随着历史传承而不断地汲取适时的文化形态,如广州传统乞巧文化本是女子做手工品以祭祀神祠、祈求美好姻缘,现在动不动就提开发,发展成为文化产业,事实上难以做到,甚至会连原真性也失去了。
第四,“民间事、民间办”,这是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序传承的重要规律,学者要做文化引导,政府要推进与支持,鼓励传承人与广大群众参与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3月至4月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召开了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的专家会议,并于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通过了12条原则,其中有两条:社区、群体和或有关个人应在保护其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首要作用;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力而继续进行必要实践、表示、表达、知识和技能的权利应予以承认和尊重。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工作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广州乞巧文化在各自地域有自己的特色,在保护传承中,要注意不过于强调形式的创新,而是要让传承人获得认同感与幸福感,从而让本土民俗文化成为一种超越地方群体的共享文化,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