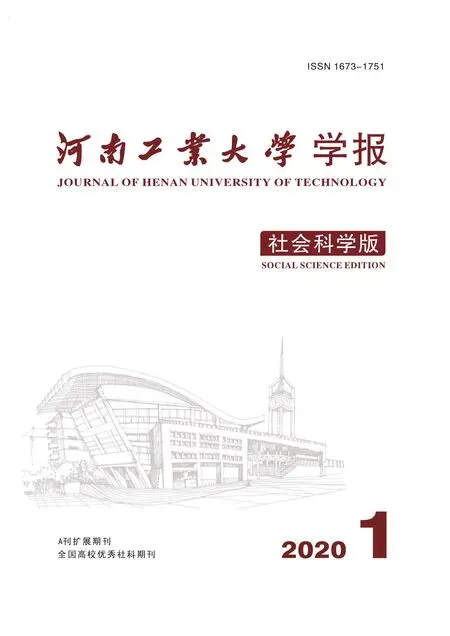审美趣味与饮食偏好:粤港澳大湾区饮食文化属性的人类学阐释
2020-01-07阎方正
阎方正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旨在将地理位置具有邻近关系的广东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机勾连起来,发挥三者在经济发展、交通往来、文化建设等方面各自的原有优势,进而解决三区域现今发展过程中各自遭遇的瓶颈与挑战。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重点介绍了该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光明前景,希望借此打造“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流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1]然而,任何经济区域共同体概念的构建都绝非是单一的经济问题,原有区域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身份认同等,都是新区域组建时必须妥善处理的问题。饮食是一个民族或集体文化属性的具象表达,在当代人文学科转向日常生活的趋势之下,它成为人们考察特定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文拟借用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方法,系统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现有的饮食偏好,发掘三地饮食特殊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因素,为新区域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参考。
1 审美趣味与人类学的交融:粤港澳大湾区饮食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趣味”(taste)是西方美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谈论过相关问题。“一个有味物就是一个可触着的事物:所以味觉不须经由任何外物为之间体(介质),以操持其功能,而触觉也正就是这么的。”[2]这里强调味觉的产生是同对象接触的结果,它是触觉进一步的发展,虽然没有直接加以说明,但接触的器官肯定是口腔,这在此后理论家的思想中有着越来越清晰的表达。近代西方“趣味”研究的代表人物包括哈奇生、休谟和博克。作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对“趣味”的生成基础、概念内涵、意义价值等问题都进行了回答。能够引发“趣味”体验的感官分成内外两部分,外感官指的是那些能够直接接受事物刺激、作出相关反应的器官。例如,舌头通过和入口食物发生接触,能够感受到食物本身的味道浓淡、材质软硬、数量多少,所依靠的都是舌头本身具有的生物功能。虽然咸淡、软硬也是人类器官在漫长的劳动实践过程中逐渐确立的感觉,但至少它仍然是围绕食物产生的体验。内感官则明显不同,它通过接收外感官对事物的直接体验,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调动主体情绪、想象等内在能力,往往能够体验到超越食物原本面貌的滋味。哈奇生认为,内感官会受到后天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增强对事物品味的深度[3]。休谟则就“趣味”的具体含义作出相对清晰的界定:“对饮食的口味和对精神事物的趣味非常相似……如果器官细致到连毫发异质都不放过,精密到能够辨别混合物中的一切成分,我们就称之为口味敏感,不管是按其用于饮食的原义还是引申义都是一样。”[3]趣味存在于入口的食物中,也存在于主要依靠精神品位的文化现象里,它是主体的生理味觉同精神味觉针对食物及文化现象反复品尝、细致探查产生的结果,能够精准感受出事物由内而外蕴藏的各种特性。到此为止,西方味觉理论涉及的表层和深层含义基本定型,此后相关的学理探讨总是围绕上述两方面的其中之一展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的先后开展,完成了对西方神学色调的祛魅,理性主义迅速蔓延开来,短时间内就成为西方主流的哲学及社会思潮。受其影响,西方的“趣味”理论也开始表现出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最有代表性的是康德系列理论,调和了原本处在激烈对抗中的理性与经验的矛盾。当康德将趣味判断和审美判断进行联系的时候,“趣味”概念的内涵再度发生置换,此时“趣味”具备了“美”所有的基本属性,它被视为是主体纯粹、不带有任何功利的一种感受。参照康德分析审美判断时涉及的质、量、关系、样式四方面,趣味判断具有的属性包括下列几点:第一,趣味是主体的情感体验,因而每个个体出现趣味感的状态不会全然相同,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第二,趣味判断带有普遍性,审美共通感、理想美的存在,使得某一类群体可能形成高度类似的趣味倾向,趣味具有主观性的同时显示出普遍性;第三,康德认为审美判断最显著的特征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主体对美的感受应当是源自美自身,绝非事物身上带有的其他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求的特性,人能够感受到美,是因为和“先验”完成了有效的契合,趣味判断同样满足这一特征。趣味出现时,主体总是首先和事物形式发生关系,他清楚认识到了这点。康德的整个美学体系同科学、伦理学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哲学体系,因而他认为道德会直接影响趣味的形成。总体来说,康德对“趣味”问题的探讨是在他庞大的哲学、美学框架下进行的,趣味原先包括的主体直接接触事物引发的体验(主要是指外在感官)被舍弃,完全成为一个形而上的美学或哲学概念。现当代的理论家针对这点多次展开过批判,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全新的“趣味”理论。布尔迪厄却将趣味的探讨由哲学领域带向社会学领域,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等基本方法采收有关趣味的信息材料。例如,他在写作《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Iadistinctioncritiquesocialedu jugement)时就使用了数据:“这项工作基础的调查是在1963年,在一项通过深入访谈和人种志考察进行的预调查之后,围绕巴黎、里尔和一个外省小城的一个692人的样本进行的。为了拥有足够多的人数,在1967—1968年从事了一项补充调查,由此把询问人数提升至1217人”[4]。通过调查掌握社会大众对某项问题持有的态度已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社会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布尔迪厄将其引入至“趣味”这个美学话题的探讨中,甚至特别留意到调查人数和调查结果准确度的关系。除去他本人进行的调查工作,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民意调查公司”等机构采集到的居民收入、职业、生活条件、文艺实践情况等多项数据同样给予他研究巨大的协助,可见社会学调查方法对布尔迪厄美学研究影响的深刻性。二是以社会学理论阐释涉及趣味的系列问题。首先,趣味塑造出文化贵族,背后隐藏着主体持有的审美意识,不同的趣味彰显出个体或群体间差异性的意识,影响文化贵族趣味形成的因素包括教育水平、资本收入、生活世界等多个方面。其次,经济生产和趣味生产联系紧密,趣味是主体内部的相关经验,它不是一种实体的存在,充当物质生产的经济活动创造出商品,通过流通交换实现价值的转化。趣味的形成依赖主体掌握的财富数量,因为达到趣味的满足不是虚无缥缈的凭空想象,必须通过物质载体才能落实。同样,趣味的变动会反作用于经济生产活动,使产品更符合消费者的偏好。再次,趣味将社会中的不同阶级、种族、地域进行区隔,成为真正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审美概念。此后的阿苏利等学者沿用这一模式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审美问题,陆续诞生出新的成果。到此为止,趣味通过与当代社会学的结合完成了对于康德精英主义美学的解构。要想走近它,不仅需要深入厨房获得一手的味蕾体验,也需要提升内在修养,品味食物以外广阔辽远的滋味。
当代文化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审美趣味与人类学的结合是一种必然,二者的理论属性、研究目标均存在共同点。田野调查是现代人类学基础性的研究方法,它的目标在于“调查者长期生活于调查的社区,使他能够相当熟悉当地发生的事件;长期与当地人相处,有可能获得当地人的信任并得到他们的宽容;观察者得到不是他人转述的第一手材料……通过参与性调查,调查者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地社会的结构以及社会文化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功能关系”[5]。研究者通过深入文化的发生现场,有效加强自身关于阐释对象的理解,充分彰显出人类学学科鲜明的经验主义色彩。面对当代趣味问题发生的社会学转向,历史上从哲学高度试图替这一概念找寻普遍性内涵的研究视角逐渐被区域、阶级、民族等特定范围的问题取而代之,它不再是抽象的哲学话语,而是有着清晰明确的所指对象,大量涉及趣味的经验数据成为研究的基础材料。这种情形下,审美趣味问题可被视为人类学研究的子对象,人类口腔及大脑的有机运行是其出现的生物学基础,社会文化的习得同样具有高度的影响力,采取宏观立场将审美趣味视作人类学聚焦的问题合理可行。布尔迪厄的“趣味”学说破除了近代哲学、美学过分重视思辨、轻忽经验的特征,它从经济、政治、阶级等角度回答问题,带有明显的社会学色彩。正如趣味不只是哲学问题,它同样不是纯粹的社会学问题,而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行为,通过借鉴人类学的方法或许能够为这个问题找寻出真正合理的文化学答案。就实际状况来看,探讨趣味理论的多数学者大多持有“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他们聚焦西方社会出现的相关现象,鲜少考察东方或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对象,当趣味问题被纳入人类学范围后,这种现象逐渐改变。格尔兹认为,人类学主要的考察对象是“地方性知识”,但他并没有就此作出清晰的界定。后世学者认为,人类学的考察对象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域特征的知识或知识体系;二是指在知识的生成与发展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6]。前者强调地理学意义的区域概念,后者则是从文化特质角度划分出“地方”,因而理解“趣味”问题回归特定区域变得顺理成章。“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纽约、旧金山、东京各建有世界一流大湾区,它们所在的陆地与隔岸城市所在的陆地中间恰好构成半开放的海域,为湾区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珠三角、香港和澳门,恰恰符合这样的地理条件。此外,近代特殊的历史因素令三地文化各不相同,恰恰符合了人类学对特殊性的强调。除了地方性概念的引进之外,人类学考察趣味问题时对材料的收集还应尽可能将承载经验信息的物质与非物质证据都纳入进来,并尽可能地从多个视角解读饮食偏好形成的原因。以人类学的方法重新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的饮食习惯,可以揭示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体质状态、民间信仰等与之存在的内在关联。在此过程中,这一新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具有的文化属性会被充分认识,会为其将来的建设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 “淡”“鲜”“甜”:粤港澳大湾区饮食偏好蕴藏的审美趣味
中国当代的饮食文化提出“八大菜系”的概念,通过持有地域空间的思维方式将那些各有特色的饮食偏好做出比较明确的划分。按照多数人的理解,菜系概念的生成是根据它们烹饪过程中采用的手法及食材、调味料组合方式的差别衍生的结果。但是,菜肴本身呈现出的味道仅仅构成菜系最表层的意义,它还需要历经多年的交流传播,才能积淀成为区域性的文化符号。八大菜系不止包含食物的滋味,更是一种文化的滋味。从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饮食风味的实际情况来看,“淡”“鲜”“甜”是最主要的三种审美趣味。
2.1 “淡”的饮食偏好
相较于其他菜系,“淡”构成粤菜口味上最明显的特质,它没有川菜、湘菜浓郁的辛辣味,也没有鲁菜看重的油色,以至令不少初入南粤大地的北方人难以适应。粤菜的“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少盐;二是少油。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海洋,令南粤地区早在商周时期就开始出现专门的煮盐行业,作为主要的食盐产地,该地菜肴的烹饪过程却极尽可能减少盐的用量。如广府名菜“白切鸡”,烹饪全程只添加葱姜片,不加除此以外的任何调料,食用前虽提供包含盐、生抽、糖的小碗佐料,食用者可根据喜好进行蘸食,但多数广东人仍是选择直接的食用,体现出对调味料的淡漠追求。粤菜少油的特征体现为对煮、蒸等烹饪技法的偏好,同时青菜在广东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粤语流传着“三日不吃青,两眼冒金星”的说法,无论是广府菜、客家菜还是潮州菜,均频繁出现青菜的身影。比起其他菜系中以炒为主的制作方法,直接使用清水白灼菜心是岭南地区的特色,其主要目的在于减少油腻感,保持青菜原有的清淡口味。这种“淡”的饮食偏好形成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由于“珠江三角洲气候炎热,且热的时间长,令人无法接受油腻的食物”[7]。这种说法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解释,却并不充分,马来西亚的气候比起岭南更加炎热潮湿,但当地“娘惹菜”却热衷酸辣、香气浓郁,显然气候对饮食的影响并未达到决定性的程度。中国古典美学体系里,“淡”是重要的范畴之一,先秦时期老子作出“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8]的论断。老子认为“大道至简”,好似食物清淡到尝不出任何滋味。结合他谈论五官感觉时直接提及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8],明显可以看出道家对浓烈食物滋味引发味觉冲击的批判态度。先秦以后,“淡”逐渐成为一个超越饮食领域的文艺范畴,陶渊明、孟浩然的诗作,董其昌的绘画,袁宏道的小品文,都鲜明地带有这种特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淡”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扮演的角色远非食物口味或者文艺风格,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早已烙刻在中华民族的骨血深处,成为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各民族显要的标志之一。荣格在解释文化演进发展问题时,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意图揭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与原始文明间的关系。“集体成员的认同感和从众性是集体无意识产生的心理基础,集体成员之间的感染、暗示作用是集体无意识得以产生的内在条件。”[9]当前粤菜在审美趣味上表现出“淡”的偏好,是一种对民族价值观的确认和传承,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相应地位。
2.2 “鲜”的饮食偏好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审美趣味方面具有的第二项偏好是对“鲜”的追求。按照段玉裁的解释:“鲜鱼也。出貉国。按此乃鱼名。”[10]该字的初始意义不是泛指食物口味上显示出的某种特点,而是特指一种鱼类,可见鲜同鱼类不可分割的关系。现代汉语里,“鲜”字经常同“美”字搭配使用,表明二者意义的相近。古代汉语中的“鲜”“美”二字就已存在着联系,从六书归属看,它们都类属会意字,它们不像形声字那样有着明确的声旁、形旁之分。这种情况下,“鲜”原本被推测的声部“羴”也承担一定的表意功能,跟字体构成中包含“羊”的“美”字就有了共同点。关于“美”的解释,文艺理论界向来争论不一,但是文字学界则比较认可许慎对该字的解释。“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中主给膳也。”[11]在他看来,美是一种甘味,这种甘味源自体态肥硕的羊类。据此可以推测,“鲜”在食物味道意义上应当是类似鱼羊肉的滋味,而这种滋味能够诱发出主体对美的相关体验。地理位置上,粤港澳大湾区临近南海海域,捕鱼业和养鱼业是其传统的经济活动,该地区具有喜食海味的饮食特性,名菜包括“清蒸鲈鱼”“生油水母”“白灼鲜虾”“清蒸鲍鱼”等。就烹饪技巧而言,为了有效保持不同海产品原有的鲜味,往往采取差异的制作方式。蚝类及扇贝,清蒸是最常用的烹饪方式,这种做法能够有效地将汤汁与食物锁住不流失;至于虾蟹,则主要白灼或制成羹粥,白灼虾蟹搭配一小碟酱油,水蟹与大米历经数小时的烹煮,其目的也是将食物的鲜味口感最大化;红衫鱼之类的鱼类则多采用红烧或煎炸,充分展示鱼肉具有的韧度、细腻等多方面的特点。虽然整个大湾区少有食用羊肉的习惯,但营养价值、肉质纤维口感均相似的牛肉却在该区域大受欢迎,广州、深圳、珠海乃至港澳等地区随处可见“潮汕牛肉火锅”的店铺。相较北方以红烧、卤制为主的牛肉加工方式,大湾区标称的牛肉火锅使用的底料非常简单,一锅清水、几段玉米、数片葱姜是其全部的精髓。重庆火锅鲜红光亮的辣油难觅影踪。因为粤港澳地区的食客认为,精心挑选的牛肉本身就带有鲜甜的滋味,如果任意添加其他的调味料,便会破坏牛肉的鲜香,清水窜烫、裹沾麻酱便是食用牛肉的全部技巧。不同于“淡”最终发展成为超越饮食、成为普遍意义审美趣味的情况,从始至终“鲜”都只归属饮食美学的内在体系。造成粤港澳大湾区饮食风格对于“鲜”的强烈追求的原因可能包括两点。一是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先秦至晚清,不管朝代如何更迭,国家中心城市始终在咸阳、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内陆城市来回移动,受制于运输技术,除了皇家贵族,海鲜难以真正推广开来。即使用于交易,也只是在本区域内进行,交易后的剩余部分只能端上餐桌。“鲜”不只是食物的味道,也是食物的状态,南粤高温天气提升了食物发生腐坏的概率,无疑强化了生活在该区域的人类对“鲜”的敏感度。二是岭南人特殊的性格气质。有学者认为:“岭南人在思维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实体性……追求直观的、感性的、本能的文化形态”[12]。高度发达的感性思维令其味觉系统能够充分体会食物包含的滋味,“鲜”的偏好正是岭南民众经过漫长的劳动生活形成的符合感性认识的饮食趣味,它在整个大湾区的文化结构中成为个性鲜明的岭南本土文化象征物。
2.3 “甜”的饮食偏好
长期以来,“甜”被视为八大菜系中“苏菜”“浙菜”的典型风格,单就菜肴具有的甜味程度而言,非其二者莫属。但除去正式菜肴外,粤港澳大湾区饮食对“甜”的喜好与之旗鼓相当,具体表现在茶点和饮品两个领域。当前大湾区的城市均有“食早茶”的习惯,广州的陶陶居、莲香楼、荣华楼,香港的翠园、胜兴茶室,澳门的龙华茶楼、大龙凤茶楼,均以经营早茶闻名一方。早茶核心并不是“茶”,而是各式“茶点”,包括粥品、面食、肠粉等数个不同的品种,近年来还增添了蛋挞、菠萝包、炸鸡翅等西方特色的食物。早茶茶点除了对“鲜”的追求外,还表现出对“甜”的热烈追求。钵仔糕、糖不甩、榴莲酥、叉烧包、莲蓉包等,不加掩饰地将传统南粤地区对甜食的热爱展示出来。港澳两地由于受到欧式生活方式的影响,形成了“下午茶”的饮食习惯,兰芳园、华星冰室、快船廊等是名气较大的几家场所。早茶多是传统东方糕点,下午茶则多为西式甜点,鸡蛋仔、番茄通粉、菠萝油、多士等都是欧洲日常饮食经常出现的食物品种。除了茶点外,大湾区在日常饮品的消费习惯方面同样对“甜”情有独钟。传统习惯上,广式甜品被称为“糖水”,它并非白糖或者红糖与水的融合物,而是南粤地区以甜为主的传统饮品的统称。从椰汁红豆、龟苓膏、西米露到芝麻汤圆、杨枝甘露、双皮奶,该地区的甜品种类不胜枚举,以致全国各地纷纷出现模仿广式糖水的盛况。港澳两地则将欧式奶茶、咖啡、朱古力等作为日常主要的消费饮品。能够看出,整个大湾区存在一种关于“甜”的审美趣味,导致这种美学追求的原因也较为复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西敏司(Sidney W.Mintz)曾经就糖类食物迅速蔓延英国社会的原因做出解释:“一、茶及其他的新兴饮料,如咖啡与可可,都含有效力强大的兴奋物质,而这些饮料都要加糖;二、当时英国劳工阶级都有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含有高热量的糖,便让人们主动或不自觉地爱上它;三、人类显然普遍天生就喜爱甜味;四、如果情况允许,在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社会里,人们总是想仿效上流社会的生活;五、‘新奇’本身可能也有其影响力;六、烟草与具有兴奋作用的饮料,有助于缓解劳累的工业生活。”[13]近代港澳两地分别处在英葡殖民统治的状态中,被统治的港澳民众无意识里便对国力更强盛的统治者产生膜拜情绪,继而通过模仿他们日常饮食等具体的文化实践,实现心理层面民族身份认同的重塑,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至今两地正式社交场合仍以咖啡作为主要饮品。另一方面,传统糖水在南粤地区的流行同该地炎热潮湿的气候特征存在某种关联,在这种环境中,劳作出汗量明显增加,身体内部热量消耗更大,通过食用含糖成分较高的饮品,能够有效补充体能。“甜”的偏好形成既是该地区人类因地制宜创造出的生存手段,同时也带有显著的外来文化痕迹。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饮食偏好背后审美趣味的形成,彰显出该地文化具有的多重性格,成为该地未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立足点。
3 坚守、对话、融合: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属性的现况与未来展望
后现代社会语境中,饮食不再只是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物质产品,它被视为文化的一种日常表征。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所形成的“淡”“鲜”“甜”三种不同的审美趣味隐喻着中国传统、岭南本土与现代西方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设立“大湾区”的经济学意义在于通过构建相对自由、开放、包容的区域环境,提供各种生产消费要素良好的流动条件,推进商业资本的转化和经济产业的升级转型。近年来,各种关于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在国内学界反复上演,经济决定文化的观点被一种平等互动关系所取代。随着消费者文化水平的提升,他们已不再是被动的产品消化对象,带有明确目的性能动地选择消费品,成为新的趋势,而消费观念的形成本身就是特定文化建构的结果。只有了解大湾区现有文化属性,制定符合区域实际的发展策略,才能真正达到“密切合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升国际经济合作”的目标。
从区域饮食偏好的角度,能够看出中华传统文化、岭南本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在大湾区所呈现的特点。第一,中华传统文化仍居于内核。传统文化是指“我们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14]古往今来,由于“中原中心主义”观念的影响,始终存在着对南粤文化的偏见,甚至将南粤视作蛮夷。事实上,粤文化的诞生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而来。表面来看,“淡”只是当前南粤饮食呈现出的偏好之一,但是“淡”的美学早已出现在中华文化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如“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人际交往准则,“欲淡则心虚,心虚则气清,气清则理明”的处世态度,“非淡泊无以明志”的人生信仰,等等。除了践行“淡”的美学,拜关公财神、练武术、划龙舟等当前中原城市难得一见的传统信仰、技艺、民俗活动等,在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地都保存良好,彰显出中华传统文化在整个粤港澳地区具有的重要地位。第二,岭南本土文化日渐式微。不同于“传统”持有的总体性立场,“本土”概念重点强调的是文化拥有的区域、种族及民族特性。西方国家极力向第三世界推动符合自身利益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一段时间以来“本土”被视作落后保守的代名词,仿佛只有摒弃那些具备显著本土特色的元素,才能实现乡土社会的转型进步。文化人类学界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指出:“本土常识需要从‘传承’的角度去理解,但它绝非硕果仅存的‘遗留物’,而是当下中国社会之现实基本事实的一部分,而且它也确定无疑地会在未来的中国社会里连绵不绝”[15]。面对全球化趋势甚嚣尘上的21世纪,西方社会有意通过推广带有显著资本主义社会特质的文化符号,形成普世的价值观念,为抢占经济利益铺垫先决的文化条件。岭南文化具有的“本土性”色彩宏观层面体现为它所具有的海洋性质,大湾区形成“鲜”的饮食偏好是临近海洋的地理优势给予丰富物产的结果,还隐喻着岭南地区原始的海洋崇拜。广州的南海神庙、香港的佛堂门天后庙、澳门的天后宫等现存的宗教建筑,成为佐证这一观点的实物证据。饮食崇拜的形成,是原始思维的产物,人类通过选取食物表象呈现的某种特征,连接与之存在关联性的非实物的理念。就像石榴多籽因而成为生殖崇拜的对象一样,海鲜源自海洋,是妈祖在内的海洋诸神灵性的承载物,岭南人期待通过饮食能够分享海洋的神性。随着商业文明的迅速蔓延,当前粤港澳地区虽然还保留着喜食海鲜产品的饮食习惯,却只是追求纯粹的味觉体验,背后的文化信仰逐渐模糊,那些仅保留在少数岭南民族、聚落的本土文化形态面临着更大的困境。第三,西方现代文化影响深刻。特殊的贸易地位及百余年的殖民统治,令整个大湾区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印记。以澳门菜为例,其菜系组合、烹饪方式乃至装盛用具都带有浓重的葡国风格;港式茶餐厅的创立也是英国贵族社会生活方式被香港民间效法的结果。就当前现状来看,茶餐厅在广州地区的流行,表明殖民地的日常生活受到普通内地民众的追捧。不可否认,港澳两地遭受的殖民统治,推动了西方现代文明在国内的传播,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等欧美社会核心观念推进了区域商业的蓬勃繁荣,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通过分析三种文化形态在粤港澳大湾区当前的发展情况,未来区域文化建设一系列的方向目标逐渐浮现出来。
开展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中华传统文化、岭南本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三者的关系,对此应当持有“坚守、对话、融合”的总体态度。首先,应当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作用。包含九座不同城市、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大湾区”构想形成的关键在于它们都受到中华传统文化长时间的浸润,相似的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令彼此具有亲近关系,中华民族是一致的身份认同。大湾区采取开放的态度,旨在吸引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投资者,无论如何开放,它仍然是中国经济实践的试验区,是国家形象、综合实力的展现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6]。未来在推动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多地采取各种形式彰显灿若星河的优秀传统文化,使该区域不只成为中国当代经济的浪尖,更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潮头。其次,应当努力开拓岭南本土特色文化。文化的“本土性”通过富有特色的社会制度、仪式、宗教信仰、艺术等方面展现出来。针对目前大湾区本土文化日渐没落的现实,重新审视岭南文化诸方面的特点,将之同当前区域整体建设目标有效对接,是一条值得尝试的发展道路。以宗教信仰为例,马凌诺斯基提出“人类永生的信仰乃是祖先崇拜、家内祭祀、丧葬仪式及灵物二元论的基础。这种信仰是产生于人类社会构成的本身,特别是产生于社会生活的基础——即家族和亲属关系”[17]。岭南地区修建了大量祠堂作为祭祀场所,除供奉先人的灵位,还会将家训、家族法则、祖先的荣光事迹刻在其中。这种祭祀场所的设置在马来西亚的峇峇族群、越南的明乡族群、泰国的洛真族群都有类似的呈现。大湾区可以尝试组织富有岭南本土文化特色的民俗活动,拯救处在危机中的地域文化,同时吸引东南亚、北美等地的华人华侨回国投资。再次,应当推进西方现代文化在地融合。现代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外来文化充斥着强国附加的意识形态,相对主义仍应是大湾区持有的基本立场。新区域共同体尚未完全成型,各个结构仍在演变,学习借鉴他国的优秀文化对其发展大有裨益。西方现代文化的诞生拥有特定的内外条件,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粤港澳大湾区”应当在充分熟悉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摒弃其中的消极因素,并将积极因素同区域实际情况巧妙结合。只有这样,解决中国当代社会问题才不是隔靴搔痒,才能在长期的实践中持续不断地发挥效能。
富有鲜明地域色调的大湾区饮食偏好,是地理形态、自然气候、宗教信仰、社会经济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微观的“饮食”角度切入粤港澳大湾区现今的文化生态,其价值不只体现在学术研究的理论层面,也为处在初始期的经济区域建设提供了发展指南。不论研究或开发,都应突破单一的经济立场,在思考区域文化共同体构建方式的同时,坚持走中国道路、彰显中国特色,努力通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8]的理想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