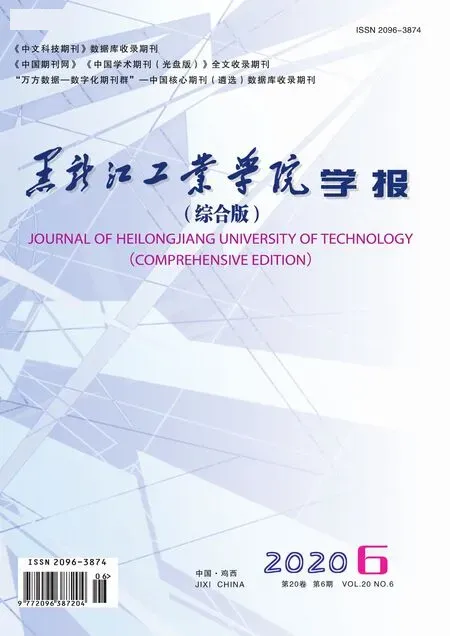争论中的村两委“一肩挑”模式与乡村治理的发展
2020-01-07李淇,李斌
李 淇,李 斌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成为题中之意。当下,乡村治理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治理模式,即村两委“一肩挑”模式,这一模式正在逐步发展和推广。所谓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指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的党组织书记由同一人担任,即村级自治组织党政“一肩挑”。但是,结合对这一治理模式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对相关学术成果的考察,不难发现对这一模式仍然存在许多争论。本文将试图对这些争论进行归纳和总结,并透过这些争论来深度思考这一治理模式以及乡村治理的发展。
一、争论之一:程序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2]。由相关法律法规和现实实践可知,村民委员会和村级党组织皆由直接选举产生。并且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村级选举中涌现出了十分丰富的民主实践模式和相关制度,比如“一票制”[3]“观察员制度”“定岗制”等等[4]。法律上的硬性规定和实践上的政治规矩共同决定了村级组织的选举充分具备了民主性,但是民主性在选举中可能意味着不确定性,村级组织选举中的不确定性就集中体现在选举可能产生的意外结果[5]。村两委“一肩挑”模式要求村的党组织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为同一人,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人选的不确定变为确定。简单来说,这种确定就是要求村级组织的党组织负责人成功当选为村民委员会负责人,或者村民委员会负责人成功当选党组织负责人。
但是,村级组织直接选举的制度安排是“一人一票”,并且在村民委员会的候选人推举过程中普遍实行“两推三选”,此外选举票中还有“另选他人”一项,凡此种种制度安排皆无法确保村的党组织书记顺利成为村民委员会主任,或者村民委员会主任成功通过组织考核并当选为村党组织书记。在此情况下,若要推行村两委“一肩挑”模式就需要消除这些不确定性。由此各地为了推进村两委“一肩挑”模式产生了种种程序安排,比如先实行村委会换届选举,再进行村的党组织换届来实现“一肩挑”或者先通过进行村的党组织换届选举,再进行村民委员会换届来实现“一肩挑”,还有将村的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换届时间交错来实现“一肩挑”。但是,“这些方式是否合规、妥当,可以研究”[6]。另外,还有学者指出这一模式的“选举办法与相关法律法规存在张力”[7]。而这种讨论关注的焦点在于村级组织的选举是否应该受到干预、受何种力量的干预、干预的程度允许有多深。
总而言之,村两委“一肩挑”模式争论中的程序问题集中体现在村级组织的选举程序问题,因为推进村两委“一肩挑”模式需要一人同时或先后通过两次民主选举。但是在民主选举过程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村两委“一肩挑”模式能否排除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就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通过强力推进这一模式以确保选举结果就更是一个问题。
二、争论之二:权力问题
村级组织,主要是指村的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长期代表着或行使着村庄内部的最高权力。尽管村级组织并不是一级政府机关,但是公共的属性以及村庄是国家—社会连接点的独特地位,共同决定了村级组织权力的公共性和支配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8],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实践史已经为阿克顿勋爵的这句话作出了无数注解。这些注解共同揭示了一个道理,凡是权力就有存在变质乃至腐败的风险。诚如许多“村官”腐败、小微权力腐败的报道一样,村级组织的权力也可能存在许多问题,并且这些报道往往能够出人意料。因为由于村级组织用来牟私的权力较小,单次腐败的影响亦较小,从而导致民众的腐败感知度较低,进而展示出对其较高的容忍度,另外,“法不责微”的“习惯法”又使“微腐败”在司法领域失之宽、失之松、失之软[9]。
因此,村两委“一肩挑”模式下“一肩挑”人员的权力问题就成为了关注的重点。村两委的分离本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两委之间的相互监督,但是“一肩挑”使得村级组织党政主要负责人为同一人,在某种程度是融合了村两委从而有利于村两委工作的运转。但是这种融合有可能导致“一肩挑”人员独揽大权、滥用职权,甚至产生村庄内部“一言堂”问题,这些为滋生权力腐败提供了条件[10]。此外,亦有学者认为如果强行推行“一肩挑”模式会诱发民众的焦虑情绪,从而容易导致对“一肩挑”模式的信任危机,而一旦产生信任危机,对权力的信任也有可能产生危机,其中最大的危机主要集中在权力的集中[11]。这种权力的集中暗含了对权力的深度思考:这种权力来自于谁,是基层政权还是村民群众?由谁问责,是基层政权还是村民群众?
概言之,村两委“一肩挑”模式争论中的权力问题主要是指村级党政组织“一肩挑”人员的权力问题,这种问题集中体现在该人员权力集中导致的潜在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有权力的腐败和变质、权力的信任危机以及权力的集中导致的村两委的关系变质。深入思考后不难发现,权力问题的实质乃是权力的限度问题以及权力的属性问题。换言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村两委“一肩挑”模式下“一肩挑”人员手中的权力,以及如何确保这种权力能为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深入探究的问题。
三、争论之三:职责问题
村级组织作为连接国家政权和社会自治的一个公共组织,所需承担的职责也就兼顾了“国家”和“社会”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体现在既需要完成来自国家政权机关下派的行政任务,比如经济发展、计划生育等由政权机关制定的政策和规划;又需要落实村民提交或反映的村庄公共问题,比如村庄的公共交通问题、水利问题等。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村级组织存在职责“超载”的问题[12]。换言之,未实施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的村庄本就存在职责“超载”的风险和可能,因为村级组织承担的职责实在太多,那么,村两委“一肩挑”模式就更有可能存在职责“超载”问题[13]。
另外,在乡村治理中乡村治理的好坏,村干部是关键[14],这意味着实行村两委“一肩挑”模式对这一模式下的“一肩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当下乡村存在着“人才不足、能力不济、威望不高”[15]的问题,这无疑给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抛出了更大的难题。
换言之,村两委“一肩挑”模式争论中的职责问题指向的是村两委“一肩挑”模式在减少人员的情况下能否承担得起繁重的职责。并且,这一模式对“一肩挑”人员赋予了更多的期待,这种期待体现在道德、能力、群众感等方方面面,能否选出这样的人,既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和配合,又要取得政权机关的认可和赞赏,是一个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职责问题除了有个人方面的因素,职能的落实和责任的承担才是重中之重。
四、争论的实质:行政抑或自治?
上文梳理了村两委“一肩挑”模式面临的诸多争论,透过这些争论不难发现这些争论的实质乃是乡村治理的未来和发展要面向行政还是自治?换言之,村民自治制度乃至乡村治理的未来是要以行政为导向还是以强化自治为导向。比如,“程序问题”背后的选举问题,支持基层政权干预选举的似乎更赞同行政,强调村庄内部选举自主性的更赞同自治。再如,“权力问题”背后的权力来源问题、权威问题,主持村级组织权威主要由基层政权赋予的更偏好行政,反之则为自治。
村两委“一肩挑”模式及其相关争论的产生是有时代背景的,这种背景就是伴随着国家资源下乡、扶助三农等一系列惠农政策而带来的政权下乡[16],由此导致了“行政下乡”与“自治下沉”[17]。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模式就被视为这种背景的产物,这个产物折射出了村民自治制度以及乡村治理手段的争论,即行政抑或自治?如何看待这一模式的争论就反映着我们看待村民自治制度以及乡村治理的态度。
1.行政与自治的关系
在思考这一问题之前,需要简单梳理一下行政与自治的关系问题。行政和自治是解决公共事物的两条基本路径。行政是政府公共行政的简称,它的意思是指“由国家的代表级政府根据法律规定所实施的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18],由此可见,在行政这一治理之道中政府的力量是关键,是主导力量,是重要推动者和资源来源者。自治是社会自治的简称,它的意思指“个人或团体管理自身事务并对其行为负责的一种治理形态,它既是社会治理的一种高级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价值目标”[19]。显而易见,自治的要求是“主体性”和“自主性”,在自治这一治理之道中个人的投入、社会的组织化以及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关键。
从二者的定义就可以看出这二者的异同,异在主导力量,同在目标导向。不同学者对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发表了不同看法,在乡村治理领域,这二者的关系大体来看可以分为三种观点:其一,“行政中心论”又谓之“政府中心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共事物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还是政府,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力量推进社会发展,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有丁丁和汪锦军[20]、王文烂和陈建平[21]等人。不难发现这些学者都着眼于当下村庄内部的资源匮乏、人才流失、个人原子化状态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依靠行政力量解决乡村治理问题似乎成为上乘之选。其二,“自治中心论”亦谓之“社会中心论”,这一观点认为社会既有能力也有诉求来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依靠自治不仅可以节省制度成本,而且具有独特的社会和政治价值。此观点的学者颇多,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徐勇和赵德健[22]、刘伟和刘瑾[23]、谢安民[24]等人。不难看出这些学者普遍认为村民自治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因此,不能轻易否定反而需要大力推进和发展。此外,村民自治的关键在于发挥村民的主体性意识和主体性作用,村民有能力实现自治,制度有保障推进自治。其三,“耦合论”又谓之“嵌入论”,赞成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治理领域自治和治理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可以互动的、共生的、共存的,因此重要的不是行政和自治之分,而是要努力耦合自治与行政,该观点的主要代表学者有袁方成[25]、马卫红[26]、景跃进[27]等人。仔细思考就能发现,这一观点是说行政代表一种权力或者治理策略,自治也代表一种权力或者治理策略,这两种权力或者治理策略一直处于互动之中,也恰是这种互动才导致行政与自治两者间的平衡与发展,而当下乡村的复杂性以及村民自治几十年来的发展恰恰需要这种平衡与发展。
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可以发现,对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的争论正好反映了以上不同的观点:是相信村两委“一肩挑”模式能够促进乡村治理的发展还是否之?是信任村两委“一肩挑”模式背景下的“权力”,这种权力无论是下沉而来的政权还是村级组织集中化的权力,抑或否之?不同的回答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偏好与策略选择。
2.迈向耦合:村民自治的发展方向
毋庸置疑,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的再次出现与蓬勃发展昭示着国家政权下沉的事实,村级治理的行政化发展亦是事实,但是诚如贺雪峰所言,“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必然结果是村庄公共性的消逝以及资源下乡的低效甚至无效。离开对农民群众的动员,仅强调为农民服务,不组织农民,仅仅帮助农民,结果可能造成村级治理的失败”[28]。由此可知,仅依靠行政手段来解决乡村治理的问题是不够的,仅依靠自治手段来进一步发展乡村治理,亦是不可。因此,“耦合”就成为了当下村民自治发展的不二方向。
所谓耦合,是指“强调两个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合力”[29],那么乡村治理中的耦合就是指行政和自治两个变量相互作用并形成合力,从而推进乡村治理的发展,村两委“一肩挑”模式作为进一步连接国家政权和村民群众的治理模式或许可以成为耦合这两种治理策略的连接点。一方面,需要基层政权积极作为,尤其是在一轮又一轮乡镇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改革的背景下加快构建服务型政府[30];另一方面,需要村民进一步提高自觉意识,积极主动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使乡村治理迈向“参与式”发展[31]。除此之外,村级组织以及村两委“一肩挑”模式背景下的“一肩挑”人员也要积极探索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
五、结论与余论
文章基于对乡村治理领域出现的新兴治理模式,即村两委“一肩挑”模式,争论的考察发现当下乡村治理发展方向,即实现行政与自治的耦合。这种实现需要行政主体、村级组织、自治主体三方力量共同努力。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当下无论哪种村民自治模式都需要在法治、德治与自治三者融合的背景下运行,“法治、德治、自治”也就给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的实践定下了总的基调。
透过这一模式进行进一步思考,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折射出了行政和自治之争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政治学理论中的“强国家”和“强社会”之争,自由主义与法团主义之争,乃至于发展到民主与非民主之争等等。但是无论是哪种争论,个人持何方观点,我们都必须明白行政抑或自治都属于政治手段,而政治的任务是提供一个优良的秩序和服务于良善的生活。也许,明智之举是抛开这些争论,一切“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32],让政治为人民服务,为现代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