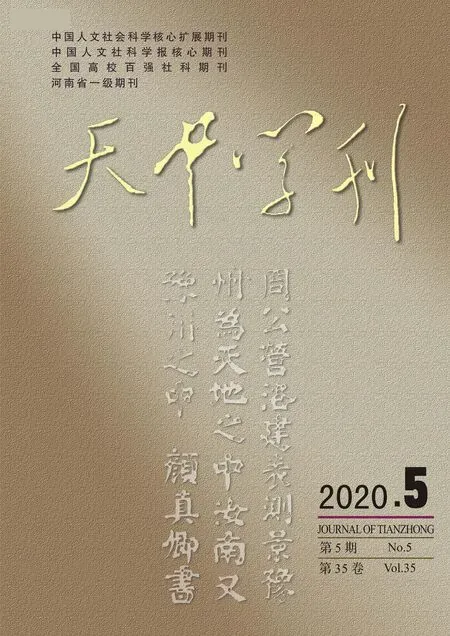从鲁智深到贾宝玉——从互文叙事视角看《水浒传》《红楼梦》的“赤子”文化意蕴
2020-01-07魏颖
魏颖
从鲁智深到贾宝玉——从互文叙事视角看《水浒传》《红楼梦》的“赤子”文化意蕴
魏颖
(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受中国传统“赤子”文化的影响,施耐庵和曹雪芹不约而同地在其小说的主要人物身上倾注了“赤子”情怀:《水浒传》中的鲁智深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都秉承“赤子”之心,以“狂”或“佯狂”的姿态张扬人的本真美,彰显不受拘滞的自由精神和激烈的反正统、反传统思想。在互文性视域中观照鲁智深与贾宝玉,追寻两人在文化基因上的相通性,不仅能揭示《红楼梦》与《水浒传》的渊源关系,而且能从中挖掘人物形象丰富的精神意蕴与文化特质。
互文性;鲁智深;贾宝玉;“赤子”
《水浒传》中的鲁智深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个是行侠仗义、浪迹江湖、五大三粗的“花和尚”,一个是怜香惜玉、至情任性、风流俊秀的“怡红公子”,虽然两人的外在形象大相径庭,却存在诸多的内在联系。运用互文性视角观照鲁智深与贾宝玉,会发现两人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文化纽带,构成一种影射关系。本文在互文性视域中追寻鲁智深和贾宝玉在文化基因上的相通性,不仅能揭示《红楼梦》与《水浒传》的渊源关系,而且能从中挖掘人物形象丰富的精神意蕴与文化特质。
一、互文性与互文叙事探赜
“互文性”作为理论术语是由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她认为“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1]。“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交织与融合,从而打破了文本孤立、自足、封闭的状态,揭示了文本意义的交互性和转换生成性。
《红楼梦》的创作早于克里斯蒂娃提出“互文性”理论约两百年,虽然在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没有西方“互文性”的理论概念,但值得关注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就指出:“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2]所谓“事类”,就是修辞学上的引用手法,即文章援用典故或引用古事、古语来明理征义,而援用的典故与现实中的道理常常发生关联,“事类”显然与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有相通之处。另外,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的“点铁成金说”曾在古代文学史与文艺批评领域产生过深远影响。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云:“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3]“点铁成金说”揭示了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条艺术规律,即学问达到高度圆融的境界,就能“陶冶万物”,即使运用古人“陈言”,也能熔铸新意,构造新境。古诗中点化前人诗文以成佳句的例子不胜枚举:杜甫《望岳》中的“一览众山小”即从《孟子·尽心上》中的“登泰山而小天下”衍生而来;张先《天仙子》中的“云破月来花弄影”脱化于唐氏谣《暗别离》中的“朱弦暗度不见人,风动花枝月中影”;文天祥《南安军》中的“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化用了杜甫《春望》中的“国破山河在”等。诸如这类暗用典故、点化前人诗文的“点铁成金”之法,其实就是使当前的文本与前文本构成一种互文关系,读者在巨大的互文审美空间中鉴赏文本,不仅能扩大读者的视野,而且能更好地理解文本意义的交互性与流动性。
借用西方的“互文性”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事类”“点铁成金”说来观照《红楼梦》,会发现小说中明引、暗用或化用前代经典的互文叙事比比皆是。例如,第22回叙述薛宝钗过生日,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贾宝玉说自己“从来怕这些热闹戏”,薛宝钗就告诉他那戏中有一支《寄生草》辞藻极妙,并念给贾宝玉听: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①
《寄生草》是清初昆曲《醉打三门》之《点绛唇》套曲中的一支曲子,为鲁智深拜别师父智真长老时所唱。这支曲词不仅成为《红楼梦》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暗示了贾宝玉后来出家的命运,与小说构成互文叙事,即“在本文中嵌入另一与本文有关联、可参照的文本”,“且嵌入的文本对本文的情节、主题、人物具有暗示、隐喻、影射等功能”[4]。曹雪芹在《红楼梦》文本中嵌入《寄生草》文本,而《寄生草》又取材于《水浒传》第4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鲁智深在五台山剃度后,不守清规戒律,一日下山打禅杖和戒刀,闻到酒肆狗肉香,遂强买狗肉豪饮,烂醉后乘酒兴打坍半山亭子,打破寺院大门,还打坏了金刚,因此被师傅驱逐下山。《红楼梦》通过人物对话以重复先前文学文本的情节和人物,实现了小说文本间的互文性。
二、鲁智深与贾宝玉的互文性
《水浒传》与《红楼梦》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作为经典性作品,其必要条件“就是具有深厚的哲学和文化背景,具有思想上的普遍意义。这种普遍意义,就是作品具有经典性的力量之源”[5]。基于哲学和文化上的普遍性意义,《水浒传》中的鲁智深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不仅在命运结构上相互呼应,在“赤子”精神境界上彼此契合,而且在理想追求上具有内在的相通性,主要表现在:
(一)从“下凡历劫”到“由色归空”的命运结构
鲁智深与贾宝玉的社会身份与人生遭际迥然不同,来历却都是“下凡历劫”,并且殊途同归,经历了红尘纷扰后,皆以出家成佛的方式归位。鲁智深是被天师封杀的108天罡地煞星中的“天孤星”,因天数使然,俗缘未尽,由洪太尉从“伏魔之殿”放出,替天行道。为救金老父女,鲁智深(原名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被迫避祸出走,剃度五台山,但这只是表面形式的出家,他内心真正皈依佛门是在经历了一番除暴安良的打杀之后,宿于浙江六和寺,半夜听得钱塘江上潮声雷响,恍然大悟师父智真长老的偈语“听潮而圆,见信而寂”,遂沐浴更衣,写下开悟偈后坐化于大刹。贾宝玉本是赤霞宫的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绛珠仙草(林黛玉的前生),因“凡心偶炽”,与绛珠仙草一道下凡历劫。经历了与黛玉、宝钗、晴雯、袭人、芳官等众女儿的梦幻情缘,并遭遇抄家变故后,贾宝玉悬崖撒手,随一僧一道出家,归位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
不谋而合的是,鲁智深与贾宝玉都是在功名唾手可得之际觉悟,走向让人解脱的彼岸世界。鲁智深擒获叛贼首领方腊立了大功,却不愿接受封赏,拒绝了宋江提出的到京城还俗为官或住持一个名山大刹的建议:“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②在经历了江湖上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争斗,目睹了众兄弟为朝廷卖命九死一生之后,鲁智深夜闻潮声而彻悟,坐化于六和寺,归还其本来面目。圆寂前他做了一偈:“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金枷玉锁”象征着功名利禄的束缚,比之于宋江、卢俊义为“金枷玉锁”所累而不得善终,鲁智深挣脱名缰利锁而圆寂正是其了身达命、修得善果的表现。如果说鲁智深擒方腊是为了报答宋江的知遇之恩,贾宝玉赴科场应考则是为了博得功名报答亲恩:“母亲生我一世,我也无可报答,只有这一入场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太太喜欢喜欢,便是儿子一辈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如同鲁智深擒方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无挂碍圆寂了,贾宝玉也以中举的方式完成了维护贾家的责任,随一僧一道归彼大荒。
④在河(沟)道常流水河床以外范围,配置步道、亲水平台和绿化美化等人水相亲设施,提高河(沟)道的休闲娱乐功能。
(二)“赤子”的精神境界
所谓“赤子”,即绝假纯真,具有外坦荡而内淳至的真性情,《寄生草》唱词中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是一种文化隐喻,既象征了不受世俗羁绊,无一丝一毫粘滞挂碍的佛家境界,也是老庄、孟子、罗汝芳等所推崇的“赤子”的文化隐喻。
《水浒传》多次描写鲁智深“赤条条”的形象:第一次是在醉闹五台山前,鲁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来,把两只袖子缠在腰里,露出脊背上花绣来,扇着两个膀子上山来”,但见“裸形赤体醉魔君,放火杀人花和尚”;第二次是为救刘太公之女免遭小霸王周通凌辱,鲁智深李代桃僵,赤身坐在销金帐子里等小霸王,小霸王不知其中有诈,被鲁智深一顿暴打,大喊救命,众人看时,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赤条条不着一丝,骑翻大王在床面前打”;第三次是在二龙山巧遇杨志,杨志见鲁智深脱得“赤条条的,背上刺着花绣,坐在松树根头乘凉”。“赤条条”的形象象征了鲁智深正直无邪的“赤子”之心:他率性而为,三番五次地破戒,一次大醉后将山门和金刚都打坏,不仅愤激批判了只知恪守清规戒律、独善其身的僧人难以成佛,而且斥责、抨击了腐败不堪的黑暗现实;他不计得失,义薄云天,既可以为萍水相逢的金翠莲父女、刘太公一家拔刀相助,也可以为朋友林冲等两肋插刀。因此,鲁智深虽然喝酒、杀人、放火,却以直面担当的方式悟道,修成了正果。
“赤子之心”也是贾宝玉的精神追求,这主要表现在贾宝玉不随流俗、不矫情方面。他对待周围的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和阶级出身,都赤诚相待,给予世俗人无法理解的爱与平等。他的朋友既有高雅的公子王孙如北静王之流,又有粗俗的纨绔子弟如薛蟠之辈,还有优伶蒋玉菡、浪子柳湘莲等。对待女儿,无论是贵族小姐,还是丫鬟戏子,他基本都能做到发自内心的尊重,且关怀备至,不受封建等级秩序和教条的羁绊。关于“赤子之心”,贾宝玉和薛宝钗有过一番辩论:
(宝玉)微微的笑道:“据你说人品根柢,又是什么古圣贤,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我们生来已陷溺在贪嗔痴爱中,犹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说了,不曾提醒一个。既要讲到人品根柢,谁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宝钗道:“你既说‘赤子之心’,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离群无关无系为赤子之心。尧舜禹汤周孔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若你方才所说的,忍于抛弃天伦,还成什么道理?”
在上述辩论中,贾宝玉以老庄学说解释“赤子之心”,而薛宝钗则用儒家学说解释“赤子之心”,显然两人的思想冰炭不投、背道而驰。贾宝玉所理解的“赤子之心”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即没有经过世俗陈规沾染的“肆行无碍凭来去”境界。这在《红楼梦》第22回中有所演绎。因史湘云说唱戏的小旦“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儿”,惹恼了林黛玉,贾宝玉从中劝解,结果将林黛玉和史湘云都得罪了。袭人前来宽慰,宝玉道:“什么是‘大家彼此’,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遂提笔占偈后填了一支《寄生草》:“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其中的“肆行无碍凭来去”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赤子之心”互见文义,表现了贾宝玉心无挂碍的落拓、自由与逍遥。
如果说鲁智深爱打抱不平,是出于不存私心杂念和无条件帮助弱者的“义”,那么贾宝玉尊重、呵护、关爱女儿则是出自不带占有目的和皮肤滥淫欲望的“情”。无论是鲁智深的义,还是贾宝玉的情,都是不附加任何功利主义目的、纯真无伪的“赤子之心”的表现。
(三)对“净土”世界的向往
“净土”信仰在佛教中分为往生极乐世界的西方净土思想和心净土净的唯心净土思想。西方净土信仰是通过神话传说,描述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妙,介绍现实世界众生“按照佛教的要求修善持戒,或思念那里的教主阿弥陀佛,甚至只是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获得灭罪消灾的功效,死后往生到那里,享受人间难以想象的极乐生活”。唯心净土思想则源于禅宗中的《六祖坛经》,认为自我具足一切,所谓“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存在于自己心中,因此,“觉悟和解脱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不能凭借任何外部力量达到”[6]。在鲁智深和贾宝玉的内心,都有自己向往的“净土”世界,鲁智深的“净土”世界是以“义”为主导秩序的梁山泊;贾宝玉的“净土”世界则是以“情”为主导秩序的大观园。无论是梁山泊还是大观园,都表现出与现实世界相对隔绝的封闭性,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作家对浊世恶俗的不满与批判,且两者都抵挡不住现实世界的冲击,最终归于幻灭。这也是《水浒传》与《红楼梦》的共同悲剧。
鲁智深一生颠沛流离,先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麾下从军,后在渭州经略府做提辖;因三拳打死镇关西,为躲避官府缉捕而落发五台山文殊院;因醉闹五台山被逐往东京城大相国寺做“菜头”;又因搭救林冲,不得已落草二龙山;三山聚义后加入梁山泊,方如鱼得水。梁山泊方圆八百里,汇聚了诸多江湖好汉、英雄豪侠,他们成瓮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在梁山泊,不仅没有官府欺压,没有苛捐杂税,没有不公平的剥削和压迫,而且性格迥异、地位悬殊的人可以超越彼此之间的差异,形成亲密平等的人际关系。梁山泊物产丰富,自给自足,第20回描写梁山泊好汉庆功时,介绍了梁山泊的富饶:“众头领大喜,杀牛宰马,山寨里筵会。自酝的好酒,水泊里出的新鲜莲藕,山南树上自有时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枣、柿、栗之类,鱼、肉、鹅、鸡品物,不必细说。”梁山泊是鲁智深的理想栖居之地,宋江想招安,鲁智深一语中的:“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鲁智深将朝廷统治的社会现实比作染黑了的直裰(袍子),反衬了梁山泊的“干净”。鲁智深拒绝招安,但无济于事,从表面上看,是梁山泊的头领宋江亲手毁掉了梁山好汉的理想家园,但实际上梁山泊好汉即使不接受招安,也终究会毁灭——官军的征剿和梁山好汉的文化水平整体较低、缺乏理性的自觉和反省以及行动的盲目、无纪律性等都决定了梁山泊作为理想家园其实是乌托邦。
作为女儿清净之地的大观园是贾宝玉的精神寄托所在,也是其“事业”所在。尤氏曾评说贾宝玉:“谁都像你,真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玩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大观园的女儿大多才貌双全,性灵聪慧,即便存在宝钗、袭人这样心有城府、劝人热衷功名的女儿,比之于男人世界里的阴险奸诈之徒仍是一股清流。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谈道:“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何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7]大观园世界具有理想性,是“清”“情”与“真”的象征;大观园世界同时具有乌托邦属性,其清净性唯有在近乎与世隔绝,且生活无虞的状态中维持,一旦遭受世俗恶势力的渗透、侵蚀,或失去了外部的经济支撑,大观园的清净质性便烟消云散。
不谋而合的是,鲁智深与贾宝玉都经历了理想“净土”被毁灭的痛苦。《水浒传》中,宋江接受招安后,梁山泊义军便受诏破辽,后去平定江南方腊。在讨伐方腊的战争中,梁山泊义军损兵折将,108位好汉只剩得36人。经历了梁山泊好汉群聚的热闹与繁荣,再遭遇诸多兄弟纷纷阵亡的生离死别,鲁智深终于了悟凡尘,在六和寺坐化了。异曲同工的是,在《红楼梦》中,因绣春囊事件大观园被抄检,贾宝玉眼睁睁看着晴雯、芳官、四儿等被逐却无力保护,到后来林黛玉仙逝,他便有了“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觉悟。
三、“赤子”的文化源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鲁智深与贾宝玉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关系和传承关系,即在这两个人物身上,都流露了作家对“赤子之心”的认同和佛禅文化的意绪。不同的是,鲁智深的“赤子之心”是和杀伐心联系在一起的,属于霹雳手段、菩萨心肠的“狂禅”文化典型;贾宝玉的“赤子之心”则更多地融入了老庄逍遥游的自由思想,是“庄禅”文化的代表。值得追问的是,施耐庵与曹雪芹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在其小说的主要人物身上寄托其“赤子”情怀?在施耐庵与曹雪芹的“赤子”情怀中,又有着怎样的心理动因和文化根源呢?
关于“赤子”的提法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老子。老子在《道德经》中谈道:“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8]这里的“赤子”指婴儿。老子认为婴儿虽然无知无欲,但精气充盈,他们纯朴自然的心态符合万物之本“道”的规定,是顺乎天理、合于自然的最高的“和”的象征。庄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赤子”这一概念,但庄子所追求的游于天地大化之间,放浪形骸之外的自由人格与“赤子”的内涵具有相通性。孟子则正式提出了“赤子之心”的概念:“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9]孟子所指的“大人”是德行“充实而有光辉”的人,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注曰:“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10]朱熹指出“赤子之心”具有质朴无欲,纯一无伪的特征,与“不为物诱”的大人之心是相通的。至明代,罗汝芳对“赤子之心”做了进一步阐释:“夫赤子之心,纯然而无杂,浑然而无为,形质虽有天人之分,本体实无彼此之异。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时,与天甚是相近。”[11]225“今日不患天则之不中,惟患天心之不复;不患天心之不复,唯患所见之不真。其见既真,则本来赤子之心完养,即是大人之圣。”[11]228罗汝芳认为“赤子之心”是人心的原初状态,是与生俱来、浑然至善、纯然无杂的“天心”“本心”或“真心”。受后天影响,人之本心被世情利欲所遮蔽,“赤子之心”则不复可见,若能保持“赤子之心”不失,便能成就“大人之圣”。因此,孟子强调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其实是揭示了“人性之善”的道理,即“赤子之心”是性善之本心。李贽则提出“童心”说,与老庄、孟子、罗汝芳的“赤子”思想一脉相承:“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2]李贽认为“童心”是未受社会污染的“最初一念之本心”,世人的心已经被虚伪道学和义理所蒙蔽,而“赤子之心”未被闻见知识教化蒙蔽和控制,才是“真人真心”。
老庄、孟子对“赤子”的表述虽各有侧重,但都张扬了内心的赤诚与人格的自由独立,强调只有保持一种纯真素朴的心态才能悟道。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与李贽的“童心”说则是对老庄、孟子“赤子”之喻的重要继承和发展,以对抗假道学的社会风气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受传统“赤子”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施耐庵和曹雪芹不约而同在其小说的主要人物身上倾注了“赤子”情怀:鲁智深与贾宝玉都秉承“赤子之心”,以“狂”或“佯狂”的姿态张扬人的本真之美,彰显不受拘滞的自由精神和激烈的反正统、反传统思想。鲁智深的“狂”表现在虽是剃度和尚却不守清规戒律,不仅喝酒吃肉,而且杀人放火,贾宝玉的“狂”则表现在试图冲破礼法伦常和封建贵族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与平等;鲁智深习武是为了除暴安良,并非为了功名利禄,贾宝玉读书则是为了追求个体精神自由,而非为了仕途经济。殊途同归的是,鲁智深在杀伐中悟道,贾宝玉则以情悟道,两人最终都“破执”,不受封建礼教和封建传统的束缚,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境界。
综上所述,《红楼梦》与《水浒传》这两部奇书积淀有人类共通的精神元素和文化元素,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虽然施耐庵与曹雪芹的生平经历大相径庭,但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两人都有着“补天”的“赤子”情结和佛禅思想。《水浒传》创作于元末明初,连续持久的社会动荡以及弱肉强食、黑暗腐败的政治现实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的儒学信仰,透过《水浒传》,可以看到施耐庵立足元末明初,借写宋事以诉不平:一方面,作家对“官逼民反”的造反精神是认同的,另一方面又希望以忠义伦理补救北宋王朝摇摇欲坠之“天”。鲁智深圆寂不仅昭示了“替天行道”理想的破灭,而且寄托了作家抗争世俗、坚守素志的赤子情怀。《红楼梦》创作的清代前期,旧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依然处在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正在加速腐朽,新的思想意识在潜滋暗长。曹雪芹不仅亲身经历了自己家族从钟鸣鼎食的繁华到瓦灶绳床的衰败,也耳闻目睹了与不同政治集团有瓜葛的名门望族在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中被抄家,甚至被关、被杀的黑暗现实。贾宝玉出家既表达了曹雪芹由色入空的觉悟,又寄托了曹雪芹“补天”无门、愤世嫉俗的赤子情怀。可以认为,通过塑造具有“赤子之心”和佛禅文化意绪的鲁智深与贾宝玉,施耐庵与曹雪芹在其小说中一方面寄托了批判社会现实,向往走自由人生之路的理想;另一方面也暗喻了这样的悲剧主题——面对运终数尽的封建末世现实,任何志在补天济世,试图挽救没落封建社会秩序的理想,都是梦幻泡影。
① 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均出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版)。
② 本文所引《水浒传》原文,均出自施耐庵《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2版)。
[1] 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M].史忠义,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87.
[2]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1.
[3] 黄庭坚文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475.
[4] 李清宇.论张爱玲“以戏为题”的互文叙事:从话剧《秋海棠》的启示说起[J].文艺研究,2016(9):59–68.
[5] 阎真.经典的叙事和叙事的经典:我的文学观[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87–90.
[6] 魏儒道.中华佛教史:宋元明清佛教史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160–161.
[7]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36.
[8]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149.
[9]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204.
[1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272.
[11] 吴震.罗汝芳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2] 许苏民.李贽评传:上[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02.
From LU Zhishen to JIA Baoyu——The “newborn baby” Metaphor inandin the Light of Intertextual Narration
WEI Y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Influenc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oth SHI Naian and CAO Xueqin embody the “newborn baby” idea into the main characters of their novels: LU Zhishen in theand JIA Baoyu in. They all have the spirit of fighting for freedom and longing for kindness, pure and beauty. To research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we can trace their similarities in cultural genes, reveal the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orks and explore the rich spiritual implications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racters.
intertextuality; LU Zhishen; JIA Baoyu; “newborn baby”
I207.4
A
1006–5261(2020)05–0090–07
2019-12-23
2019年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改项目(2019JGYB045);2019年中南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2019JG035);2018年湖南省社科规划办成果立项项目(18CGA006)
魏颖(1971―),女,湖南长沙人,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