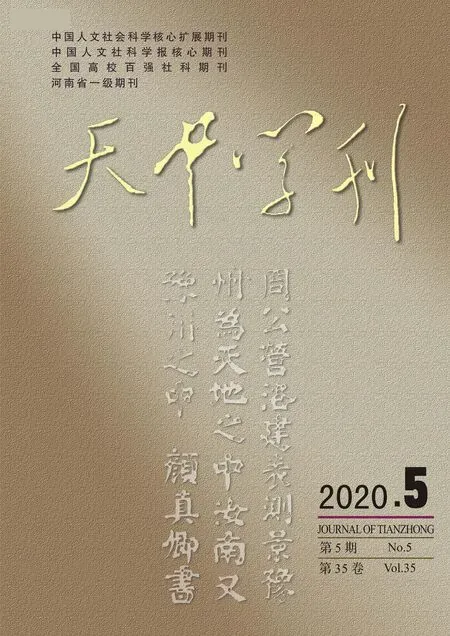论中华先祖部族文化融合轨迹——兼论中华古玉器渊源传承
2020-01-07李国忠
李国忠
论中华先祖部族文化融合轨迹——兼论中华古玉器渊源传承
李国忠
(河南省驻马店市委 编委办公室,河南 驻马店 463000)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既是中华先祖部族文化融合的过程,又是一段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人类文明史起源于新石器时期,而中国与其他文明迥异之处是,中国还有一个明显的玉器时代,并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高度重合。从考古发掘来看,遍布全国的文化遗址,诸如东北红山文化遗址、浙江良渚文化遗址、中原龙山文化遗址、安徽凌家滩文化遗址、陕西神木石岇文化遗址等,普遍存在于距今约8000~4000年的玉文化阶段,可称为没有文字记载的玉器文明时期。被视为我国古代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实际上也是通过故事化和韵文化进行口耳相传的,并没有文字记载。《诗经》《楚辞》《古诗源》的有些乐歌,作为韵文化遗存的补证,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中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侧面证实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存在。5000年中华文明史是众多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文化不断传承融合及转化创新的过程。
中华先祖;融合轨迹;古玉器;三皇五帝;楚辞
人类文明史应该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距今约10000年。维尔·杜兰特所著《世界文明史》称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中国是世界曾存在过的五大文明发源地。《全球通史》提及“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四块地区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1]。英国BBC广播公司的大型纪录片《文明的轨迹》将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称作世界四大古文明发源地。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国际上认可为公元前1500年的殷商时期,其主要依据是殷墟发掘成果。国内学者也只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夏朝建立。其中有不少恶意缩短中华文明存续时间的假说,甚至有受历史虚无论影响的中华文明“西来论”。
在考古学不发达时期,对中华先祖历史的研究,较少器物印证,大多依据史籍传承,辅以推断假设,把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概称史前,即在夏朝之前或说大洪水之前。而《春秋》《国语》《史记》等文献详细记载了上古世系以及各种文明的创造。直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发现时代越晚,上古史记载越丰富完整,提出“古史层累说”[2],认为各朝各代在历史记载中自觉不自觉地增添了自己的想象和解释,从而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历史体系,但无法构成新的历史体系。近代考古学引入中国是在20世纪20年代。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直到20世纪末,考古工作者才建立起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并先后开展了考古区系类型学研究的文化历史分析,初步认为史前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多元文化彼此交流逐渐形成一体。他们对上古史的重构,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探讨的科学基础。
一
在中国历史上,考古学界研究循用世界通用的所谓“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分类法。为了研究那些时代的遗存,考古学界把分布于一定范围,延续了一定时间并具有共同特征的考古遗存称为一种“文化”(这里特指考古学文化)。在历史学、考古学上对某一文化的命名,习惯上多使用最初发现这种文化的地名,例如仰韶(河南渑池仰韶村)文化、龙山(山东章丘龙山镇)文化。按地理区域位置,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由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和燕辽文化区六大文化区组成。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期,距今约10000-4000年。
在古代,“中国”常常是一个文明的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有明确国界的地理观念。古人心目中的“华夏”是“中国”的同义词,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古代先民自称“华夏”,他们认为自己位居中央,四边为蛮夷戎狄,自称“中国”,即中央之国。之后各部落联盟都自称“华夏”。从黄帝到尧舜禹时代,史学界一直认为持续了500年。但笔者认为,这是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的成文,从出土玉器所证可知这一时期应为1500年,即距今6000-4500年。也就是说,以大约5600年前进行的炎黄蚩尤大战为契机,中华民族开始大融合。以此为界,之前中华民族为红山部落集团、炎帝蚩尤部落集团、黄帝部落集团,之后相继形成中原黄帝集团、海岱东夷集团、良渚祝融集团。傅斯年从历史文献角度提出的“夷夏东西说”甚有道理。实际上,从五帝时代到虞夏商周时代,前期是各部落联盟争雄时代,后期是部族联盟成为区域性盟主,开始建立国家王朝的时代。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其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仅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3]512,至殷墟发掘后提前到公元前1300年。对于之前的历史,学界在认识上存在分歧。这段历史常有王无年,因而出现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不正常情况。为此,国家于1996-2016年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个工程对中华文明历史渊源探索意义非凡。但不足之处在于两个工程把虞朝排斥在外,其内在原因应为内囿于中原中心说的先入为主,外在原因则是片面依赖于考古挖掘。而且,考古学一般都把重点放在遗址建筑格局、功用和器物技艺上,往往忽略这些器物的形制、渊源、传承和刻画纹饰所揭示的信息内涵。王国维认为,考古历史文化须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印证,缺一不可。
二
旧石器时代以打制石器为文化标志,新石器时代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文化标志,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大体是一致的。世界文明的发展轨迹大同小异,我们的祖先同其他人类一样,从长期的采集、渔猎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在种植五谷、驯养牲畜的同时,人类先是学会了打造石器,然后学会了磨制石器,进而学会了磨制玉器,并懂得了用黏土制作陶器,从此人类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玉器鲜明的传承关系和独一无二的历史传统,成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明史所独有的。
从瓷器史上看,原始陶器大体有红、灰、黑、白之分,“著名的彩陶属于泥质红陶,工艺美术讲究装饰和造型。原始陶器的装饰之美集中体现在彩陶,造型之美突出体现在黑陶”[4]。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大体是使用器,主要有饮食器、贮存器、汲水器、炊器、酒器等类别。特别是黑陶文化,可以对应玉器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但不具备复杂的礼仪专用之器。由于陶器的地方特征比较显著,考古工作一般把陶器作为识别文化类型的依据,却忽视了玉器可作为文化划分类型的更重要依据——玉器器型变化较慢,而形制的继承性、过渡性、连续性都比较强。
新石器时期的玉器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早期源头分为东北和东南两大区域。炎黄大战及炎黄与蚩尤的大战是华夏民族第一次大融合,从而形成中原部落联盟,奠定了中华主体民族的形成基础。制作精美玉器与陶器的前提必须是“定居”,所以人类定居生活的逐渐巩固,为后来铜器、青铜器和铁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玉器发端于东北区域,最悠久的玉器是东北平原上距今约9000年的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计有67件。之后是距今8200-7400年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玦等装饰品。用玉石作装饰品,说明当时已有发达的农业和长期定居的环境。在距今6000-45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制玉工艺水平达到了至今也难以企及的高度。东南区域的洞庭湖流域是传说中炎帝的故乡,也是中国最早的水稻种植地。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省中部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有玉玦、管、环、珠等装饰品。一个在东北,一个在江南,两个史前部落均有玉玦出土,同时河姆渡文化遗址与红山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鸟陶盏几乎一模一样,而且玉玦的形制、大小、薄厚及用途基本一致,说明有人从东北平原越过燕山,沿着渤海、黄海和东海海岸来到南方,南北民族融合从此开始。
7000年前,河姆渡玉文化及白陶刻绘技术随水稻种植技术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辐射产生了马家浜玉文化、大溪玉文化、高庙玉文化。其中,大溪文化遗址是玉玦由东向西沿长江流传最远的地方。在距今6400年前后,炎帝南方部落东进北上,在黄河下游和淮北地区,取代太昊氏部落成为地区霸主。
相对于东北和东南区域,黄河流域玉文化发展较为滞后。距今8000-5000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传说是伏羲和女娲的故乡,有高超的细石器加工技术和制陶技术,又称先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距今7000-5000年。仰韶文化的上千处遗址中出土玉器极少,装饰性玉器的佩戴和使用也十分有限,没有形成一定的系统或规模,这说明该区域农业生产水平低于东北和东南区域,并且缺乏玉石资源。
山东文化区域在距今7500-6400年之间孕育了北辛文化。北辛文化遗址出土的大汶口彩陶显示出黄河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东传的痕迹,而且彩陶中常见的八角星太阳纹明显又受洞庭湖流域长江中游文化的影响。这说明多种文化基因促进了大汶口文化迅速成长。
在距今6000年前,东北平原的红山文化已经相当成熟;以炎帝为代表的南方部落实力雄厚,积极东进北上,并取代太昊部落成为地区霸主;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部落也十分强大。当南方部落联盟由南向北与中原部落联盟由西向东扩张相遇于黄河下游时,南北文化的和平交流演变为冲突。在距今5600年左右,炎黄大战爆发。《山海经》载:“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5]430黄、炎争夺华北,黄帝久战不敌,退守燕山、太行山一带。关键时刻,炎帝部属蚩尤兵变拥立少昊。无奈之下,炎帝求和于黄帝。炎黄共同与蚩尤作战仍然不能取胜。于是黄帝只好求助于西辽河平原的玄女之国,称女魃,大破蚩尤于涿鹿之野。蚩尤死后,黄帝乘势夺取河北、河南、山东,居淮北都于彭城,遂成天下共主。炎帝去帝号居淮南,少昊居山东,均受制于黄帝。
《易经》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流域的河洛地区,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说法。双槐树遗址位于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华文明形成初期阶段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专家称之为“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是呈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现存有大型夯土基址、3处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址、人祭遗存等,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出土了精美彩陶及与丝绸制作工艺相关的骨针、石刀等。而且,周边的青台、汪沟、秦王寨、伏羲台,洛阳的苏羊、土门、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等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了拱卫之势,使其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有关于黄帝时代“一百年,地裂,帝陟”[6]401的记载,唐代瞿昙悉达主编的《开元占经》也有“黄帝将亡则地裂”的记载,这表明黄帝部落迁都他处是因为双槐树遗址处发生了地震。而在对双槐树遗址发掘时,考古现场发现了多处有明显地层错位的地震裂缝遗迹,经确认其震级可能在6.0级以上。由此可判定,双槐树都邑应为黄帝之都。
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内发现的由9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表明古代中原先民对“北斗天象”的观测非常精确,已经有了较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遗址发现的用野猪獠牙雕刻的“牙雕蚕”是中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与青台遗址、汪沟村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相互印证了5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养蚕缫丝。双槐树遗址发现3处墓葬区1700多座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其中一个墓葬区被外壕、中壕围成一个独立区域,应是中国早期帝王陵寝兆域制度的雏形。值得一提的是,墓葬中殉葬品没有发现玉器,其他殉葬品很少,即使规模很大、等级很高的墓葬依然如此,这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特例。这说明首领掌握军事权和祭祀权,但宗教色彩不浓郁,具有明显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特点。
距今5600-5300年的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有大量玉器,玉敛葬规模惊人。玉器器形有铲、斧、钻等用具类,钺、戈等礼仪类及环、璜、玦、璧、镯、鹰等装饰品类。王用的河图洛书(包括玉版、龟筒)、玉冠和神职贵族所用玉龙、玉人等尤其令人惊艳不已[7]。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具有南方炎帝部落的文化特色,应为退守淮南的末代炎帝家族的用器物。
传说炎帝死后葬湖南炎陵,其子祝融葬于南岳衡山。“南岳”隋前在安徽西部霍山,并非湖南衡山,距今5600年左右这里还存在着太湖崧泽文化、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和潜山薛家岗文化。潜山薛家岗遗址出土了具有明显凌家滩文化特色的玉琮形器、玉璜形器和玉镯,特别是在凌家滩遗址中从未出现过的玉琮,可能产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北方民族向南方移动和扩张的过程之中。
在距今约5300年前,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华北有帝喾,江南有吴回氏祝融集团。天下兵戈初息,但是黄河总是在华北平原上决口泛滥,治河成为北方王朝头等大事,而吴回氏所居太湖地区则欣欣向荣,来自东方少昊氏和南方共工氏的精英云集,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当时独领风骚。
公元前3250年,吴回氏、重氏祝融部族集团吸收了凌家滩文明成果,在长江流域建国良渚。良渚国号虞,定都余杭,历时1100年左右,是中华大地第一个王朝。东夷重氏家族是山东半岛最古老的家族,炎帝时重氏担任神职,炎黄大战后又为黄帝所用,帝颛顼时担任“司天”之职。良渚人的始祖吴回是重黎之弟,在帝喾时继任祝融一职,他同样属于重氏祝融家族。当时良渚集团武力强大,天下无敌,战国古籍《鹖冠子》记载:“泰上成鸠之道,一族用之万八千岁,有天下兵强,世不可夺。”[8]良渚虞国空间分布在环太湖流域,中心面积约3.65万平方公里,以良渚城为中心。现考古存在有良渚古城、良渚水坝、反山河瑶山遗址。其中,“良渚古城由宫殿区(40公顷)、内城(280公顷)、外城(约350公顷)呈向心式三重布局组成,内城和外城布局跟中原地区城市建造一脉相承”[9]。由此可推测,良渚文明与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仅大件琮璧玉器就有上千件,各类玉器达万件之多。其中用具类有斧、铲、凿、纺纶等,装饰品类有璜、镯、玦、管、珠、带钩、佩、觿、串饰等,礼仪器类有钺、璧、琮、冠形器、锥形器、三叉形器等。玉器上雕刻的“兽面纹”和人兽结合的“神徽”等纹样,表现出统一而强烈的宗教崇拜意识。大量同类玉礼器的存在说明该地区存在一个具有同宗、同盟、同礼制、同意识的多层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邦国集团。在出土玉器中,黄河流域的玉锥形器成为仅次于玉琮的法器,说明良渚文化虽师承凌家滩文化,却不属于炎帝集团,而是属于南下讨伐共工氏的黄帝一族后代。
礼器是礼制的物质表现形式,它在祭祀、朝聘、宴享等活动时使用,“器以藏礼”[10]873,用以“名贵贱、辨等列”[10]44,区别贵族内部等级。良渚文化遗存中的玉礼器具有青铜礼器的功能,更多用于宗教祭祀,说明当时等级和阶层区分鲜明。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只有贵族大墓才随葬玉器,随葬玉礼器众多者中还发现有头盖骨,说明有奴隶殉葬。由此可见,良渚文化宗教气氛浓厚,神权大于王权或掌握王权,礼制和贵族名分制度已形成,奴隶制社会初具雏形,大虞良渚古国初步形成王朝,进入文明古国阶段。
良渚国的支柱产业是农业、丝织业、渔业和盐业。贵族集团以神的名义发布历法,建立最早的戍边制度和屯垦制度,普遍使用最先进的石犁、石刀、石锛和石斧。良渚手工业异常发达,除了上述玉器外,陶器、漆器、丝织品等也十分精美。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玉柄象牙梳媲美商代妇好墓玉梳,嵌玉漆杯较春秋战国毫不逊色;出土的玉带钩表明良渚贵族普遍穿着丝绸缝制的袍服。良渚原始商业贸易活跃,中国最早的集市和商业码头在此出现。
良渚国鼎盛时期,势力远达苏北及山东边界。传说禹祖先鲧因治水不力被尧治罪,尧借良渚祝融之手杀死鲧,鲧葬于东海羽山。在良渚内部,重黎吴回祝融家族争斗纷起,政权时时更迭,有虞氏舜在家族继承中屡受打击。帝舜有虞氏家族属良渚贵族重黎一脉,其祖先分别是颛顼、穷蝉、敬康、句芒、蟜牛、瞽叟。舜弟“象”继父职位后,舜为逃避迫害,率有虞氏一支向北方逃亡。由于有虞氏祖传高超的制陶技术,北逃的舜先是担任陶正负责制陶,再任虞官管理山林,后来逐步进入帝尧集团权力核心,并成为尧的女婿。
舜进入帝尧权力核心后,与夏后氏共同为帝尧治水。舜获得巨大的信任权力后,率部进军长江流域,南下攻击三苗人。三苗人是南方种植水稻民族的总称。据《山海经》载,三苗人并不是南方炎帝族人,而是早已定居南方的黄帝子孙。战争相当残酷、激烈,传说舜、禹皆死于与强大的三苗作战之中。作为战胜方,中原王朝成为正宗。
传说帝尧晚年时欲“禅让”于舜,三苗之君强烈反对,所以良渚战败后亡国已不可避免。三苗战败后大量被俘的良渚人被迁徙到了西方“三危”之地。《史记》记载:“舜归而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3]28“三危”之地传说在甘肃、宁夏或者青海。这就是齐家文化出土玉琮的原因,反过来也证实所谓三苗人其实大部分就是良渚人或者太湖人。除了少数极品外,齐家文化遗存出土的玉琮大都是光素无纹的,这说明三苗人到了西北以后不再强大和富裕。
中国的史学界对夏朝的起源疑窦丛生,但由于没有文字证明,我们只能从遗址遗物中寻找蛛丝马迹。发掘的史前遗址显示,夏代之前和夏朝后期的遗迹都很完备,但夏朝早期遗留和出土玉器都不足以证明其身世和血脉。大家对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毫无争议,但二里头夏文化明显属于夏代后期。那么,我们只有从夏代玉器中寻找“家传”。二里头夏代遗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有两类,一是礼仪兵器类,如玉圭、玉璋、玉钺、玉戚、玉刀、玉戈、玉璇玑等;二是饰物类,如管、珠、镯形器、柄形饰等[11]。这些玉器中既没有红山文化代表器玉猪龙、勾云形玉佩、马蹄形器,也没有南方玉文化的璜、璧类,只有两件玉琮残片,而且其中一件又改作他用,这说明二里头出土玉器与良渚文化无关。夏代玉器最显著的特点是,由兵器转化而来的大件礼仪玉器很多,玉礼仪兵器都装饰有扉牙,并呈兽首状。夏代玉器体现了王权的至高无上,而不是神的权威。
夏代玉器在国内出土最早的是山东海隅龙山文化玉器。山东龙山文化存续于距今4500-4000年间,只有它才能证明夏民族最初的形成及后来向西方的迁徙。目前山东龙山文化存世有明确出土记录的是3件牙璋。对照二里头出土的牙璋,它们没有扉牙,这表明它们比二里头的夏代牙璋更加古老,同时也证明夏民族起源于海隅,用的是山东海隅文化玉器。山东海隅文化玉器包括长条形玉刀、玉牙璋和玉牙璧等,都由渔民常用工具进化而来。长条形弧刃或直刃玉刀是剖鱼工具;牙璋是原始剖蚌刀造型;玉牙璧(玉璇玑形佩饰)是渔民织渔网或修补渔网用来割断网绳的工具。夏代玉礼器很多,但唯有玉刀、玉牙璋和玉牙璧始终保留着山东海隅民族的特色。
山东日照市五莲山是一座东夷时代的神山,或叫“五连山”,即五峰相连日出之山。后来中原地区出现的玉礼器,如玉钺、玉牙璋、玉圭、玉刀、玉筒式镯、玉牙璧(玉璇玑)、龙山玉琮等,均可在五莲山或日照地区发现祖型。
对于夏后氏起源于山东,《山海经》记载有北海之神禺疆和东海之神禺虢的传说。在5000年前,山东人将渤海称为“北海”,将黄海称为“东海”,将东海称为“南海”。山东半岛是“隅夷”活动的地区,鲧、禹的祖先颛顼从西方来到山东半岛而取代东方少昊氏。鲧被杀于羽山,著名的新沂花厅良渚文化遗址就在其附近。“隅”“禺”通禹,禹的祖先鲧死于这一区域,其后代分三支逃亡避难,一支向北逃至辽东半岛,一支向西南入川,一支向西到陕西榆林神木石峁。
中国有一句民谣叫:“黄河百害,唯利一套。”黄河河套平原不仅有万顷良田,而且没有水害,神木石峁文化遗址就在此。该遗址存续年代距今4300-4000年,遗址面积超4平方公里,出土有127件玉器。其中,礼器类有璧、圭、牙璋,仪仗类有钺、戚、戈和多孔刀,装饰和艺术品类有璜、玉璇玑、人头像及蚕、蝗虫、螳螂、虎头等[12]。据放射性碳-14测定法断代,它们均属于夏代纪年范畴。值得一提的是,神木石峁文化遗址出土的牙璋,制作精细,形制宏大,年代稍晚于山东龙山文化而早于河南二里头文化。玉戈、玉戚的出土证明该器型起源于夏初,应该可以肯定神木石峁遗址就是夏早期都城。另外,遗址附近的一个祭祀坑出土了玉器36件,其中有两件故意对剖成四件,玉器分六排刃口朝下插在坑底,明显是以玉祀神。神木石峁遗址可以解惑许多史前历史。《山海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5]472此帝应为天帝。黄帝、颛顼可称“天帝”,而尧是“众帝”,故鲧应为尧之前时代人。而且,治罪的原因也不是治水不力,而是“不待帝命”。由此可推断,鲧是黄帝的后代,却不是帝颛顼的儿子,出身于颛顼一族;禹不是鲧的儿子,两人年龄相差至少300年,禹应为鲧的后代。鲧被杀之后,其一支后代逃往河套平原,300年后在神木石峁建立了最初的大夏国。
龙山时代陶寺遗址被称为中原龙山文化最大的城址,学者们公认它出现的年代早于河南二里头文化时期。考古发现,陶寺遗址建于公元前2300年左右,面积达58万平方米,公元前2100年前后扩建成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城址附近有一平面呈大半圆形特殊遗迹,复原显示其夯土有意留出四道缝隙,分别对照的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时太阳照射位置,史学界一致认为这是观测天象和祭祀的场所[13]。《尚书·尧典》中尧“观象授时”的记载对此可印证。陶寺遗址出土有最早的空腔铜器,并发现了能够确定为文字的材料。出土玉器可分为礼器、仪仗、装饰品三类,多质朴无纹,工艺既不及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玉器精细,也不及神木峁集中宏大。特别是兵礼仪玉器只有钺一种,戈、刀、戚阙如,而且同一种器物如琮、梳、瑗等,往往是石玉并用,不加选择,这表明玉料的缺乏和琢玉水平的低下。一方面城址巨大,王权尊贵;一方面玉器制作水平较低,这似乎有中原王朝文化的影子。陶寺遗址城址规模巨大,功能分区明显,出土有象征身份等级、军事权力的钺,表明城内统治者已拥有“王”权,疑为二头联盟执政之王城,亦有夏早期都城和虞舜龙兴地之说。
三
中国的上古时代,指有文字记载出现以前的历史时代,即一般所指的夏及其以前的时代。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可知,在距今5000年前中华大地就已出现了国家。由于上古时代没有文字,主要凭借口耳相传的记忆,而增强记忆的方法就是把抽象平淡的知识赋予情节变成故事,以便深入人心,传诸久远。因此,上古神话传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确凿可凭,只是时过境迁,这些传说被后人当成了匪夷所思的神话。文史典籍所载的史前神话传说大多是历史传说的故事化遗存。《山海经》是我国唯一一部史前史书。从文史典籍中查找史实痕迹,虞夏商周四朝脉络清晰,跃然纸上,可以佐证中华文明的起源与传承。
三皇五帝实际上是上古时期出现的为早期人类做出贡献的部落联盟首领,三皇五帝时代,又称“上古时代”或“神话时代”。“三皇五帝”构成了神话传说时代的历史系统,关于他们的传说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然而“三皇”“五帝”究竟对应哪些传说人物呢?实际上有多种说法。“最为久远也最为模糊的三皇,大抵是创世神话中的神人,史前人类的象征,关于它的说法竟有六种之多:(1) 天皇、地皇、泰皇;(2) 天皇、地皇、人皇;(3) 伏羲、女娲、神农;(4) 伏羲、神农、祝融;(5) 伏羲、神农、共工;(6) 燧人、伏羲、神农。”[14]9“三皇”所处时代,基本对应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此后的五帝大抵是一些部落联盟的杰出领袖,已经较为具体,但也有三种说法:(1) 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2) 太皞(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皞、颛顼;(3) 少皞(少昊)、颛顼、帝辛(帝皞)、唐尧、虞舜。”[14]9“五帝”所处时代,对应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或玉器时代。
炎帝、黄帝,被中华民族尊为共同的“人文初祖”,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就是对共同祖先的尊崇。炎帝,就是神农氏。他和他的部落发明了农业、医药、陶器。由于生产工具的局限,当时的农业处在“刀耕火种”阶段,所以原始农业和火有着密切的关系。农业社会中,炎帝后裔烈山氏、共工氏分别被后人尊奉为社神、稷神,受到人们普遍祭祀,以后便把“社稷”引申为天下、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稍晚于炎帝的黄帝,号有熊氏,似乎是以熊为图腾的部落。相传他率领民众作战时,指挥熊、罴等六种野兽参战,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其实是指挥以六种野兽为图腾的部落参战。“黄帝的发明是多方面的,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他发明冶炼,铸成铜鼎;铸造十二铜钟,和以五音,可以演奏音乐。用树木制造船、车,用于运输;发明缝纫,制作衣裳;发明历法,派人到四境观察天象,确定春夏秋冬四季,按照四季的变化来播种百谷草木。”[14]10当时社会组织已经有了尊卑之别,人们已知道利用蚕丝编织衣料,并用服饰区别等级。把这些事实与铸造铜鼎以及由12个编钟演奏显示权力威仪的音乐联系起来分析,国家雏形隐约可见。
根据考古挖掘资料,笔者认为从黄帝到尧舜禹时代持续了1500多年,而不是500多年。这1000多年是虞朝立国建国与中原王朝并存的时期。其间,夷人部落与羌人部落先后加入中原部落联盟。当时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或称“华”“夏”,但“华夏”作为一个概念却出现得较晚。“楚失华夏”[10]1390是关于中原即华夏大地的最早记载,说明关于“华夏”的记忆由来已久。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对“华夏”注释时说:“华夏为中国也。”此时,华夏部族联盟已不再以血缘纽带为联系,而是建立了地缘性联盟,形成了以地缘为纽带的国家雏形。联盟议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讨论重大事务,推举联盟首领。在距今41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达到与海岱东夷地区相当的水平,于是出现了历史学上的海岱东夷集团与中原华夏集团的联盟政权,具体表现为以二头盟主共同执政的禅让制。
传说尧年老时,在联盟议事会上提出继承人选问题,众人推举了舜。舜之后,由于禹治理洪水有功,联盟议事会又推举禹担任首领。这就是尧、舜的“禅让”故事,传贤不传子,被后人传为美谈。尧舜相承为帝之说也有“舜逼尧”[15]406的另外一说:“舜放尧于平阳”[16],“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3]。而禹年老时却想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启,暗中培植启的势力。联盟议事会先是推举皋陶,皋陶死后又推举伯益。禹死后,启杀死伯益,继承了禹的职位,于是出现了“家天下”的夏王朝。夏朝的建立,开创了由一家一姓世袭统治王朝的先例。
从部落氏族到阶级社会有个过渡时期,此间氏族制逐渐解体,社会内部分化日益严重,阶层出现,并逐步向国家发展。这些特征在神话上的反映,就是天地通路隔绝和天帝出现。天和地既然有所谓隔绝,就一定有不隔绝。“人之初,天下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17]生动地反映出阶级划分以前人们的平等关系。人类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神话上的反映就是天和地通路隔绝。“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5]402“皇帝……乃命重黎绝地天通。”[18]320“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19]562韦昭注《国语·楚语》说:“言重能举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远,故不复通也。”
人类社会划分是怎样出现的呢?推想起来,必定和氏族解体时期军事首领在部落联盟中建立的酋长世袭制有关。军事首领由于世袭了酋长职位和发动掠夺战争而日益扩张其权力,反映在神话上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天帝。但那时候传说的天帝却不止一个,而是一大群。在《山海经》里,黄帝、女娲、炎帝、太皞、少昊、颛顼、帝俊、帝尧、帝喾、帝舜、帝丹朱、帝禹、帝台等,都是当时传述的天帝,而所谓众帝、群帝和当时混居中原的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并非一个的实际情况是大致相符的。后来国家形成,阶级划分,建立了威慑四邻的王朝,先前世袭的军事酋长这时摇身一变成为国王,反映在神话上就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天帝的出现。“我国古代西方民族神话传说中的上帝,就是黄帝、颛顼;东方民族神话传说中的上帝,就是帝俊。”[20]33
《山海经》中的黄帝,兼有部落酋长和上帝的形象:黄帝在与蚩尤之战中是部落酋长的形象,在严厉惩罚神国内讧的肇祸者时是上帝的形象。“帝之下都”昆仑山庄严宏丽和四周神异景色的叙写,也是上帝形象的具体表现。“从《山海经》所记的神谱看,不但很多著名的天神,如鲧、禹、禺虢、禺强等,就是下方许多民族,如欢头、犬戎、北狄、苗民等,都是黄帝的子孙,黄帝因此成了人神共祖。这便在原有英雄崇拜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祖先崇拜的意识。这也是神话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必然发生的演变。”[20]34
传说帝颛顼王朝历20余世,存续了350年。此说较之将颛顼仅视为一人一帝,传世只有一代的说法更为可靠。帝颛顼取代山东少昊氏集团后占据华北,并将少昊家族迁至西方,东方的少昊遂成为西方的帝,之后颛顼氏任用一些原炎帝和少昊集团的精英分子担任重要职位,包括负责治水的河伯、修订历法和主持宗教事务的祝融、负责土木工程的共工以及负责开垦土地的后土。
帝俊在《山海经》中和黄帝一样是非常显赫的,他是东夷民族奉祀的上神,也是殷民族奉祀的始祖神。《山海经》中所记帝俊的地方共有16处,少于黄帝的23处,与颛顼的16处并重。《山海经》关于帝俊的记载有三个特点:一是所记皆为片段,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二是仅见于《大荒经》;三是帝俊之名仅见于《山海经》,其他先秦古籍甚至连屈原的辞赋里都没有。《山海经》关于帝俊的记载材料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接近原始状态,刘歆认为其内容荒怪,记录凌杂无序,故“逸在外”,到郭璞注《山海经》时才将之注释收入。从内容看,《山海经》中这一部分材料的成书年代最早。虞、舜、帝俊和夋都是一人,“舜妻登比氏生霄明,烛光”,可见舜作为天帝的神格。舜的子孙为国于下方,有臷国。“臷国在其(三苗国)东”,“巫臷民盼姓,食谷(稻)”[5]371。臷国又叫巫臷民,居住在一个得天独厚的人间乐园,这里百谷自生,鸾凤云游,人死可以复苏。“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5]371–372,渲染了天神后裔的优越性,这和良渚虞朝重巫、美服及居住地理环境高度一致。
《山海经》是一部被忽视和低估的历史记录,共18卷3万1千余字,其中神话资料为我国传世典籍之最,自古传为大禹伯益之作。禹之时代尚无文字,不可能有《山海经》这样完善的著述。但《山海经》其书是像图以为文,先有图后有书,因此却不妨碍其图来历甚古。朱熹就称此书是摹写图画而成。今本《山海经》所有附图皆为《山海经》古图亡佚后,后人根据经文附会之作。其《大荒经》中的四方风名和四方神名见于殷墟卜辞。《大荒经》反映的四时观象制度可与《尧典》所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及舜“巡守四方”“望秩于山川”之事相印证。《大荒经》以山峰作为坐标观测日月次舍以确定时节和月序的方法是《周髀算经》盖天说的滥觞,说明《周髀算经》的天文历法体系和《大荒经》《海外经》一脉相承。《周髀算经》记载的实测数据有着古老来历,有的数据观测时代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21],而这正处于传说中的虞夏时代。
《山海经》为古代巫祝的祭典,书中大量的神话故事确实为上古史实的口耳相传,光怪陆离的神仙实际上是原始先民对自然和祖先的祭祀形式,是人类早期思维的投影,折射出先民们对祖先的图腾崇拜。书中的肃慎、匈奴、犬戎、氐人是秦汉时还在北方活动的古族。《海外北经》记载的炎黄两个部落战争反映了炎黄两个部落融合共同构成华夏族的史实。不论是海内还是海外,射箭者都不敢向轩辕台引弓,可见黄帝作为华夏始祖在先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山海经》中还详细叙述了炎帝、黄帝、舜的世系,这对研究上古文明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海外南经》记载了中土本部之外的南部文明,这一部族是传说中流放的部族,有人认为是帝尧长子丹朱的后代。三苗部族基本是南方良渚部族,在舜帝时遭到围剿。《海外南经》中还记述了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以及尧帝时十日并出,植物枯死,羿射落九日,为民除害的故事,影射了羿平定九部落之事。另外,《海外南经》记载帝尧和帝喾都葬在海外的狄山,这表明南方已是中华较发达的地区。《海外西经》记载了巫咸、肃慎等少数民族的名字,表明了上古部落大规模长距离迁徙的可能性。《海外北经》关于欧丝之野的记载反映了我国丝织业的悠久历史。《大荒东经》记载了少昊和帝俊的国家已经脱离采集渔猎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驯化野兽定居农耕。《大荒南经》记载苍梧是帝舜葬身之所,季禺国是颛顼后代及后羿射杀凿齿的神话。《大荒西经》关于夏启《九辩》《九歌》来历的说明,内容可与屈原的《离骚》《九歌》相印证。
我国最古老的历史书《尚书》,记载有从尧舜到周代初年的若干历史文献资料,虽然真伪杂出,亦可以与《山海经》《舜典》等神话传说材料相互补充印证。《周书·尝麦篇》关于赤帝、黄帝和蚩尤的神话材料“和一般神话传说或历史传说所说的有些不一样。一般所说的是,先是黄帝和炎帝在阪泉战争,然后黄帝和蚩尤又在涿鹿战争(其实阪泉、涿鹿都是一地),蚩尤是炎帝的后裔,故黄帝和蚩尤之战,无非是黄炎战争的继续。这里的说法却有异于以上所说。是蚩尤要把赤帝(即炎帝)从涿鹿赶逐出去,‘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黄帝这才‘执蚩尤杀之于中冀’的。黄帝、炎帝原是和睦相处,毫无争端,倒是炎帝见逼于蚩尤,向黄帝求救,黄帝仗义,为解炎帝之厄,才将蚩尤擒杀于中冀。这是黄炎之争的异说,也值得做参考”[20]63。
《左传》是春秋时期的史书,所载传说入史材料很多。如《襄公四年》所记有穷后羿兴亡史、《宣公三年》所记禹铸九鼎、《昭公元年》所记主辰主参、《昭公十七年》所记少昊挚事等,都有助于我们探讨古史,了解神话。司马迁在《史记》中也采取了一些神话材料入书,“本纪”“世家”“列传”乃至“八书”里都有,如《五帝本纪》说黄帝“教熊、罴、貔、貅、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等。
据传帝颛顼死后,高辛氏夺取帝位,是为帝喾。帝喾命颛顼氏裔孙重黎氏祝融率部追剿南方共工氏。重黎先是攻克安徽含山凌家滩,后因作战不力被杀。于是,帝喾任命重黎之弟吴回继续担任祝融,率兵追杀共工。此时距离黄炎大战已经过去了300余年。吴回是黄帝集团南下攻渡长江第一人,显然战功超过哥哥重黎,功高盖过帝喾本人。但是,战争亦使吴回部落重创。《山海经》记载,吴回本人失去了右臂;吴回跟踪追击共工氏余部来到江南,不再北返。南宋罗泌《路史》说帝喾封吴回于太湖之地,今江苏之地古称为“吴”即始于吴回,吴回遂成天下吴姓始祖。不久,吴回在良渚建虞国,定都余杭。千百年后有虞氏舜出走,良渚虞国反被舜灭,流落为三苗,后“虞”之名逐步为舜所据用。
四
学界在虞朝问题上有两点误区:一是认为虞不是单独朝代;二是把虞误作舜,认为唐尧虞舜,唐尧不是朝代,虞舜当然也不是朝代。实际上,虞作为一个朝代,与夏商周为上下三代同为四代的概念应该在周初已是共识,但汉后却湮灭于史。“三代”是一个随时代迁移而变动的概念,春秋时期,由于当时西周已亡而东周尚存,谈话时若要明确周亡或周续时,就分别使用“夏商周”和“虞夏商”两个“三代”概念。新出战国时代的郭店楚简亦有《虞诗》。《左传》《国语》中虞夏商周四代连称的文句不胜枚举,且多为转述春秋时人的对话。比如,《国语》中孔子回答吴国使者说的“汪芒氏之君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19]213。甚至连各种礼器也都是四代相比,如数家珍:说到车则是“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说到旌旗则是“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22]610;说到尊则是“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着,殷尊也;牺、象,周尊也”[22]611;说到黍稷器则是“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簋”[22]615;说到俎则是“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22]615。当然,由于虞是第一个朝代,礼器不甚完备,如爵、马、勺、豆就只有夏商周类比了。
最明确的是《左传》所证史墨的话:“社稷无常奉,群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10]2079春秋时期仍为周朝,姬姓仍是嫡姓,“于今为庶”就是说虞夏商三后在周前都是天子其姓为嫡,由于丧失天子地位而为庶姓。“于今为庶”的三后明显指虞夏商三代,“三后”中夏商二代均为独立朝代,那为什么虞代不是独立朝代?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由于虞朝与夏商无异,西周建国后还对其后裔予以特别礼遇,“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10]1359。与宋、杞合称“三恪”同受周人客礼待遇,乃是虞、夏、商三个朝代的确证。由此可见,关于虞夏商的三代概念早在西周初年已是共识。否则,周人按照周世“尊贤不过二代”只备杞、宋二恪即可,而不须备足陈、杞、宋“三恪”了。如果虞为唐尧虞舜之虞,那么又为什么不将封于祝的黄帝之后裔和封于蓟的尧之后裔一并增入而合称“五恪”?原因显而易见,汉代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虞虽为独立朝代,却不是中原王朝所建,不属于正统且被中原王朝当作蛮夷剿灭,因而无意或故意将之湮灭于史罢了。
当然,这时的王朝不能和秦以后的王朝等量齐观,《吕氏春秋》说“天下万国”,《左传》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国”自然是夸张,反映的不过是指夏朝是松散的诸侯邦国联盟而已,虞朝也是如此。虞、夏、商、周与此后朝代不同是因为,一方面它们是王朝更替、互相衔接的朝代,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四个同时并存的部落集团。按照《史记》所说,夏商周三代祖先均在尧舜政权机构中服务。《山海经》多次提到昆仑山是万山之宗,黄河是万河之祖,对我们认识华夏民族起源地意义重大,但受成书者的黄河中心局限,长江流域被划到夷苗之列。
五
《诗经》《楚辞》是古代历史传说韵文化遗存。《楚辞·九歌》保留了一些古氏族祭歌颂歌,保存了我国远古部族图腾神话,从中可以窥见中华古文明的起源与传承。由于上古时代没有文字记录,所有的知识系统包括历史知识都是凭借口耳相传。而保有记忆的机制和诀窍最常见方法就是韵文化,即把历史和知识编成朗朗上口便于传诵的歌谣,或变成让人喜闻乐见的神话故事。中国历史传说韵律化虽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系统的著作流传下来,但在《诗经》《楚辞》《古诗源》中大量存在。古氏族祭歌和民间传唱之“风”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传说韵文化遗存。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大类共305篇,产生年代约为春秋及之前,由孔子整理。它大体反映了周代的社会面貌和思想感情,也是一部周族从后稷到春秋中叶的发展史,但又不局限于此。《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总集,收楚人屈原、宋玉等辞赋17篇。“楚辞”是春秋末年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人民以口头形式保留的诗歌样式,其中《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堪称经典。尤其《九歌》是在楚国民间祭祀乐曲基础上的记录创作。“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屈原放逐……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俚,因为作《九歌》之曲”[23]。可见其词曲由民间口口相传,反映了古历史文化的端倪。
《古诗源》是清人沈德潜选编的古诗选集,其中卷一“古逸”收集先秦诗谣百余首。其中《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是神农时期的腊祭歌,应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歌谣,《礼记》亦载之。《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是《古诗源》开篇之作,传为尧出巡时见一老者拍其土壤而唱之,表现了尧时的无为而治、天下太平,也符合早期社会统治权力不集中时的社会形态。《康衢歌》“立我臣民,其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与《击壤歌》主题截然不同。据《列子》记述,尧治理天下50年后,有一次微服游于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东部一个叫康庄的地方听百姓传唱,看到百姓怡然自足,非常高兴,于是“召舜,禅以天下”。《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传为舜所作,《尚书大传·虞舜篇》有载,也是复旦大学的校名来历。《尧戒》“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出自《淮南子·人间训》,是中华民族第一条座右铭。《夏后铸鼎繇》“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传为夏后铸鼎之文,曾见于《墨子》。如此等等,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诗经》中有两篇“感天而生”的神话故事,分别是商始祖契和周始祖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出自《诗经·小雅·北山》,据说首次出于帝舜之口。《诗经》还不止一次歌颂了大禹治理洪水而缔造山川的功绩。《诗经·国风》中“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描述了太昊、炎帝之都陈国宛丘的情景。《诗经》中“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言顾之,潸焉出涕……或以其酒,不以其浆。鞙鞙佩璲,不以其长……”[24]477记述了东夷诸侯国臣民讽刺中原王室只知搜刮财物,奴役人民,不顾东方人民苦难的事实。
《楚辞》中有很多神话和历史材料。《天问》就是一篇史诗,用一百八十余个问题叙述当时所有的上下古今知识。《楚辞·远游》“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和《九章·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是关于黄炎舜的记载。《楚辞》中的《招魂》和《大招》是两首巫歌。《招魂》是招人魂的,《大招》是招鬼魂的。两首巫歌中所描写的四方,非出自巫觋杜撰,皆有所依本。《九歌》是屈原作品中最美、最精、最富魅力的诗篇,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是远古流传的乐曲,对此《左传》《离骚》《天问》《山海经》都有记述。“九歌”只是神话中的乐曲名称,屈原在楚地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改作加工成《九歌》。特别是《九歌》保存的图腾神话成为认识远古部族文化和史实的重要窗口,它对部族文化的转化创新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考古资料和出土玉器表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农业生产水平低于长江流域,从黄帝至大禹1500多年的上古中国史,基本上是东夷史。长江下游东(南)夷由于良渚被尧舜灭国后湮没于史,夷的传说也就以黄河下游东夷虞舜为主导。东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处在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其先进性在文化上的表现,便是东夷集团太阳神话丰富、音乐艺术繁荣,并有自己的部族史诗、颂诗《韶》的流传。《韶》是上古虞舜之乐,又称《大韶》《韶箾》《箫韶》。《说文》曰:“韶,虞舜乐也。”《虞书》曰:“箫韶九成。”《周礼·大司乐》曰:“九韶之舞。”原始九韶是南方百越民族的巫歌,舜帝韶乐在其基础上加工而成,并具有娱人、教化功能。该乐在《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古乐篇》《汉书·礼乐制》中均有记载。孔子于公元前517年在齐国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并评论其“尽美矣,又尽善也”。可以说《韶》乐是到目前为止可以基本考实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区域民族史诗。
东夷集团以太阳为图腾,以虞族首领帝舜(俊)为太阳神,能够“使四鸟”和驱使虎豹熊罴,即是统帅以四种鸟和动物为图腾形象的部落。古文献中所描写的《韶》乐就记载了这些内容。“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回答说:“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8]28“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18]50。这与《东皇太一》《东君》和《礼魂》祭祀太阳神的记载高度契合。“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25]52–53“縆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翾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25]72–73。
在《韶》乐中有关东夷有虞族祖先崇拜的内容,在《九歌》中却没有保存。主要是因为长江下游东夷良渚文化已经灰飞烟灭,黄河下游东夷龙山文化后来演变为岳石文化,而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飞速进步,演变至王城岗龙山文化、新砦文化。表现形式便是中原华夏族的禹启父子,破坏部落集团联盟“禅让制”,建立夏族“世袭制”。《韩非子》载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15]340
为了从根源上掌握参加联盟的各氏族部落的神权、族权、兵权、政权,禹启父子命令各氏族部落“铸鼎象物”,铸成“九鼎”,并将他们所崇拜祭祀的天体神灵与祖先神灵图像铸在“九鼎”上。禹启通过宗教手段独占了各族的兵器和生产资料及各族沟通神灵的权力,并特别针对有虞族夺取其“宗庙之典籍”,其中就包括《韶》乐。这个事实保存在“启始歌《九招(韶)》”的神话传说中。“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5]414。这是说夏后启从天神那里得到《九辩》《九歌》,实际上是以神的名义宣布《九辩》《九歌》是夏族的祭歌颂诗,是夏族神权、族权和政权的象征。
“开焉得始歌《九招》”,肯定了两点:(1) 始得《九招》说明夏族以前是不准歌舞《九招》的。(2) 既然启从天神那里所得的是《九辩》《九歌》,那么人间歌舞也应该是《九辩》《九歌》。而《山海经》“开(启)焉得始歌《九招(韶)》”说的是得到了虞乐《九韶》,而不是夏乐《九歌》。这显然矛盾百出,不打自招,从而坐实了夏启夺取虞族《韶》乐,又将其改造成《九歌》的事实。把《韶》乐中反映东夷族祭祀日月神的《东皇太一》《东君》保留在《九歌》中,就是夏启夺取东夷有虞族《韶》乐而改造成《九歌》的直接证据。日月天神是天下共神,将夷族祭祀太阳神的内容及仪式据为己有,不算违背“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10]377的原则。于是“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原来的掠夺就变成天帝授予了。
实际上,《九歌》即《夏歌》《虬歌》,因为中原夏族以虬龙为图腾。“禹,从九从虫,九虫实即句龙、虯龙也。句、虯、九,本音近义通。”姜亮夫、杨宽考证《九歌》之九实为虬龙之“虬”。世人不明就里,以为《九歌》之“九”是篇,今存《九歌》11篇,争论不休。《韶》乐又称作《九韶》实因《九歌》之影响而致。
《九歌·东皇太一》《九歌·东君》《九歌·礼魂》本身就是夷族的祭歌颂诗,是保存最早的原始宗教祭歌,其内容宗旨属于东夷集团。考古学上的东夷分为黄河下游东夷和长江下游东(南)夷。黄河下游东夷地区先后创造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长江下游东(南)夷先后创造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在这些考古学文化序列遗址中,有关太阳神崇拜的遗物蔚然大观。良渚玉器上的太阳神形象,大汶口大陶尊上的日月山刻纹,龙山文化鸟形陶鬶和鸟足陶鼎太阳鸟图腾等不胜枚举。“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5]340;“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5]344;“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5]260。“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5]354;“有黑齿之国,帝俊(舜)生黑齿”[5]348,“有人曰凿齿,羿杀之[5] 372。”这些记载一方面说明东夷是崇拜太阳的民族,从地理上证明“汤谷”“扶桑”“十日”神话只能是东夷民族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从帝尧时就开始了对东夷的战争。
下面再分析一下《东皇太一》《东君》和《礼魂》的唱辞。《东皇太一》是《九歌》中的首篇,是东夷祭祀春神的乐歌。前文我们说过,东夷一直信奉句芒为神,句芒就是春神、东方之神和农神,良渚玉器上普遍可见对句芒神的崇拜。《东皇太一》全诗分三节。首先写春天良辰吉日,怀着恭敬的心情祭祀东皇太一,以使春神降临人间,带来万物复苏。“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25]51。其次写祭祀场面宏大,祭品丰富,歌舞欢快。最后写春神降临。“偃蹇兮姣服”写出春神外表动人,舞姿曼妙,“芳菲兮满堂”昭示春神带来了春天的气息。祭祀的人们也满心欢喜,钟鼓齐奏,笙箫齐鸣,祭祀气氛达到高潮。祭诗层次清晰、场面盛大、气氛热烈、描写生动,充分表达了东夷先民对春神的敬重与欢迎,希望春神能够赐福人间,给人类生命的繁衍和农作物的生长带来福祉。《东君》是歌颂太阳神的祭歌。万物生长靠太阳,东夷诸族对太阳神(日神)的崇拜和歌颂最虔诚,当然也最热烈。“暾将出兮东方,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撰余辔兮高驰翔,杳冥冥兮以东行。”[25]73–74《东君》篇中由一位觋扮演太阳神领唱,众觋扮演观者伴唱,开篇和结尾是对太阳神的想象,中间描述祭祀过程。太阳神驾着神车,从东方扶桑出发就是白天的开始。于是,见到了热闹隆重、鼓瑟钟鸣的祭祀场景。夜晚,太阳神并未随暮色回返,而是举起长箭射去贪婪成性妄图称霸的天狼星,操起长弓防止灾祸降临人间,以北斗为壶觞,斟满美酒,为人类赐福,然后驾车前进,直到第二天再次从东方升起。对于《礼魂》,人们有不同的说法:一是认为《礼魂》是十篇共用的“乱辞”,也就是说为前十篇祭祀各神的总送神曲;一是认为该歌诗是屈原对英雄祖先的祭祀,不属九歌之列。笔者认为《东皇太一》和《礼魂》都属祭歌,既然有迎神曲,那么肯定有送神曲,因而《东皇太一》就是迎神曲,《礼魂》就是送神曲。“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25]85《礼魂》由女巫领唱,男女青年随歌起舞。全诗寥寥数语,却将一个盛大的集会场面描绘得激越恢弘。
既然《九(虬)歌》原是指《夏歌》,那么它除保留《韶》乐中《东皇太一》《东君》《礼魂》等的内容外,也应有夏族自己的祭歌颂诗。《河伯》《云中君》便是夏族《虬歌》的遗存,也是夏族自己的祭歌颂诗。
“河伯”是黄河之神,商周之后被列为天子祭祀,称为“河神”。“河伯”之名最早见于《庄子·秋水篇》。按照神话传说,河伯原名“冯夷”,也称“冰夷”。“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5]316中原部族一直在黄河流域,夏族继承的也是黄河文化,因而河伯就是黄河之神,“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25]75–76。“骖螭”即驾驭螭龙,“九河”即黄河,螭龙、黄河就是中原部族和夏的图腾。“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灵何为兮水中?”[25]76黄河神放荡不羁,妻子是洛水女神宓妃,黄河沿岸曾有“河伯娶妇”的恶俗。诗歌以河伯洛神游戏情歌作为娱神祭辞。河伯本专指黄河之神,战国时,人们将各水系河神统称河伯。
《云中君》是祭祀“云神”的辞赋。在我国古代神话故事中,云神名叫丰隆,又称“屏翳”。马茂之认为,“丰隆是云在天空中聚集的形象”。中原王朝一直崇拜云神,黄帝部落“云官而云师”,主要是中原夏族农耕生产祈求风调雨顺。这首辞前半部分写人们沐浴更衣,虔诚地迎接神的到来:“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25]54后半部分写云神从云中来到人间,光芒遍及九州,踪迹纵横四海:“灵皇皇兮既降,焱远举兮云中。览冀洲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25]55“冀州,位于九州之中,即所谓中原地带”,“正中冀曰中土”[26]312,“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5]430。郭璞注:“冀州,中土也。”“龙驾兮”“览冀州兮有余”显然是对中原夏族而言,应为夏族所祭祀的天体自然神。“极劳心兮忡忡”写出了中原人民对云神的崇敬和膜拜。
屈原《九歌》中有《大司命》和《少司命》两篇。司命神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均供奉,因此,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司命神的综合祭歌。《湘君》《湘夫人》《山鬼》是长江中游东(南)夷人后裔楚地楚族流传久远的山川祭歌颂诗。《国殇》是楚国的爱国战魂祭歌。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段没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考古学者按照人类使用工具的器质,把人类早期历史区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但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有一个明显的玉器时代。东汉袁康《越绝书》引用战国时代风胡子的话,认为传说中的三皇时代是石器时代,从黄帝开始的五帝时代是玉器时代,禹以后的夏商周三代是铜器时代,春秋战国进入了铁器时代。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对《越绝书》的这个分期法给予了高度评价。然往昔言史者言史,说文者说文,考古者必发掘,究籍者曰考据,说陶瓷、青铜及玉器者更只是就物论物。本文从玉论史,以玉证史,兼及古籍、传说、诗歌佐证。中国史前玉器固非中国史前文明之全部,却是史前中国文明之精华。从玉器的起源传承轨迹论及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从考古学意义上的新石器时期之后,8000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众多氏族部落、部族、民族文化不断传承融合与转化创新的过程。先秦时期,由氏族部落林立到部族联盟而逐渐形成多部族文化联合体。从虞开始形成松散的诸侯邦国联盟形式的国家王朝,与中原部族联盟对峙。虞亡后进入中原东夷二头盟主联合执政,直到夏结束联盟执政,过渡到商周。即使到周朝时仍为分封诸侯国联盟体制。秦统一中国至汉以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更大范围内的民族碰撞对话中最终形成。
[1]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第7版修订版.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M]//古史辨自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 叶喆民.中国陶瓷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 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 古本竹书纪年[M].济南:齐鲁书社,2010.
[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8] 黄怀信.鶡冠子汇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 刘斌,王宁远,陈明辉.良渚古城考古的历程、最新进展和展望[J].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0(3):26–35.
[10] 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8.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12] 神木市石峁文化研究会.石峁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14]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 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6] 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84.
[17]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M]//定庵续集:第2卷.光绪三年(1877)万本书堂刻本.
[18] 尚书[M].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320.
[19] 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978.
[20] 袁珂.中国神话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21] 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153.
[22] 礼记[M].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
[23]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48.
[24] 诗经[M].王秀梅,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
[25] 屈原,宋玉,等.楚辞[M].吴广平,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
[26]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K87
A
1006–5261(2020)05–0116–15
2020-04-10
李国忠(1963―),男,河南上蔡人,高级经济师,硕士。
〔责任编辑 赵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