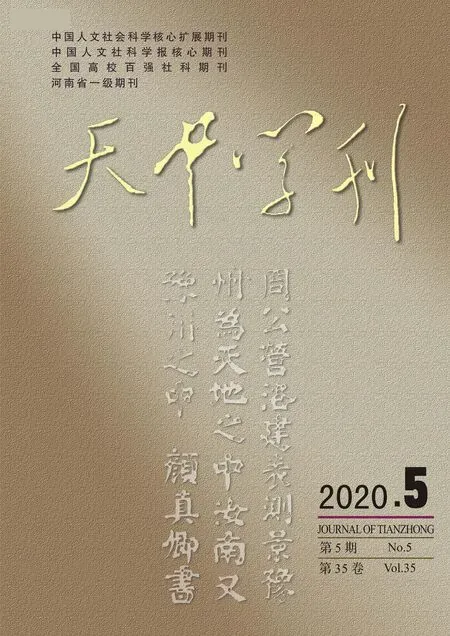诗礼文化视域中的婚礼之于家道的整全意义
2020-01-07赵国阳
赵国阳
诗礼文化视域中的婚礼之于家道的整全意义
赵国阳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男女经由婚姻之礼而结为夫妇,形成生命共同体;婚姻之礼,谋合的是“二姓之好”,这意味着婚姻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包含着伦常秩序的社会行为。《诗经》中的相关婚姻诗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夫妇一伦是社会伦常关系正常展开的前提和基石,夫妇双方要明确男女有别,各尽职分,既亲爱又敬慎,以礼齐体,通过礼乐的教养而形成一个人伦的天地。
婚姻之礼;《诗经》;家道;生命共同体
婚姻之本义,是指缔结了姻亲关系的两个家庭。《说文》释“婚”曰:“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1]259《说文》释“姻”曰:“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1]259婚指女方之家(妇党),姻指男方之家(婿党)。可见婚姻的缔结,不仅仅是男婚女嫁的个人之事,更与家道之成有着重要的关联。本文将结合《诗经》中关涉婚姻之诗篇加以阐释。家道的整全有赖于夫妇双方谨守伦理职分,以礼齐体,经由礼乐教养而共同塑造有德性的人伦生活空间。
一、婚姻之道宜家人
(一)《桃夭》中的“妇德”与“家人”
婚姻是生命繁衍有序的纽带,“昏以合男女”,婚姻是为人事之大者,婚姻之道在于能固两姓之好。夫妇牉合则成家,家具有生生不息的道性,是对男女整全生命的成就和延续。《周南·桃夭》一诗歌唱了女子出嫁,女“归”于男,并能咸宜家人之德;娶妇之家,既以继嗣为虑,亦以“宜家”为先。盖《桃夭》之女子素有贤名,故诗人见女子嫁人而美其如此。首章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喻女子之年时“少壮”,其容色如华之盛。观其为女之时,又能得其时而嫁人,知其能为良妇也。二章言桃实,毛传曰:“非但有华色,又有妇德。”[2]56–57是何妇德,毛传郑笺皆未言明;但毛传对于“妇德”的训诂值得留意。若非有妇德,如何能藩育桃“实”?又如何能开枝散叶、“宜其家人”?诗篇反复咏叹“桃之夭夭”,且每章末句都落在一个“宜”字上。毛传训“宜”曰:“宜,以有室家无逾时者。”[2]56郑笺云:“宜者,谓男女年时俱当。”[2]56传笺两说皆言婚时,朱熹认为:“宜者,和顺之意。”[3]6王先谦则引《说文》释“宜、室、家”三字之义而认为:“‘宜其室家’,犹言安其止居。”[4]42总的看来,男女婚姻嫁娶以时,夫妇和顺,其室家与家人自然能安乐和顺。“宜”字与“桃之夭夭”的舒展之貌形成了紧密的呼应,“叹其女子之贤,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3]6。
《左传》曰:“男有室,女有家。”室、家不仅仅是居住的空间①,更承载着生生不息的道性。毛传释“家室,犹室家也”。郑笺释“家人,犹室家也”。传笺未将“室家”“家室”“家人”详做区别,恰恰说明了三者之间的关联:室家一体,夫妇一体,共同构了“家人”的重要元素,是“家人”延续不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析言之,《桃夭》首章言“室家”,其文义重在“家”,这是于女子而言,“生以父母为家,嫁以夫为家”②,嫁人后有了自己的“家”。二章言“家室”,其文义重在“室”,这是于男子而言,而此室又为育桃“实”之居室。男与女,阴阳和合,夫妇和顺,共同组成了家。而家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道性,乃因其是生命孕育和成长的地方,是美德的集中地和社会伦理的发源地。故《桃夭》末章言“家人”,在夫妇和顺的基础上,一家之人皆能相“宜”,生命共同体得以生发,是以有“其叶蓁蓁”之貌,有枝繁叶茂、家人蕃盛之意。《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5]夫妇一伦,为人在天地间打开了一个伦常有序的空间。
在《桃夭》之诗所呈现的“家”空间中,由桃华而桃实,由桃实而桃叶,彰显了“乾坤芳淑”之义,贯穿于其中的是一咏三叹的“之子于归”一句。女子嫁人,是联结两个家庭、延续生命的纽带。《大学》独引《桃夭》诗末章而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就把“之子于归”的女子嫁人放在更广泛的“家人”“国人”的主体意义上来谈。《易》家人卦之彖辞曰:“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6]138其卦象曰:“风自火出,家人。”风自火出,有内外相成之义。夫妇室家,内外一体;家人国人,内外一体。夫妇一伦,实乃王化之基。是故毛序从后妃能内修其化、襄助君子的方面认为“《桃夭》,后妃之所致也”[2]54。孔疏曰:“致使天下有礼,昏娶不失其时,故曰致也……此虽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内赞之致。”[2]54而王者之治天下,莫大乎于人伦。而夫妇乃为人伦之所始端,故“夫妇为王化之原”[4]11,可以化及四方。《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此之谓也。
《桃夭》不仅呈现了生命长养繁育的空间——“家”,还呈现了一个整全的生命成长时间。在时间上,灼灼其华中蕴藏着生机的勃发,桃花盛开,桃实收获,桃叶开散,在开放、收敛、再繁盛中,生命的“翕辟开合”通过时序上的阴阳和合而呈现。在空间上,之子于归,男女各得其“所”——室与家,终宜其家人。夫妇室家,形成空间上的内外一体。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开花结果,讲究天时,阴阳交感,互根互养。在时间与空间的交互中,《桃夭》代表的是一个整全的、繁盛的生命共同体的衍续。与《硕人》《韩奕》描述婚姻嫁娶的盛大场景不同,《桃夭》对此并无所道,只是言其能“宜室家”“宜家人”,这就把“之子于归”女子嫁人的重点放在了“妇德”上,为妇如此,方是内外兼备的“至贵至美”。
“妇德,阴德也。”[7]14《桃夭》对出嫁女子的妇德并没有具体的直接描述,而是通过桃的意象来映衬其德。《诗经》中同样以“桃(李)”指称女子并称赞其德的还有《何彼襛矣》一诗。该诗中描述的出嫁女子身份显贵,但能“犹执妇道,以成肃雝之德也”[2]120。首章从“襛”之颜色、“唐棣之华”光、“肃雝”之声音,具象到“王姬之车”上,以此映托王姬敬和肃雝的德行,并道出其显贵的身份。可见,显贵的身份虽然系之于“平王”“齐侯”所代表的妇党妻族,但王姬自身人品厚重,无挟贵傲矜之象,有敬和肃雝之德,这才是诗人称赞她的缘由。妇德之为阴德,是因为它无须通过大张旗鼓来虚张声势,而是要把它沉淀到生活中,落实在生活中,并通过生命的长养来练就其德行。婚姻之本义,从字源说事关两个家庭;婚姻的健康与否,则与夫妇双方的德行伦理及职分定位紧密相关。
(二)婚姻中的夫妇伦理
《白虎通·嫁娶篇》关于婚姻的界定则是从时间及男女主从关系上说的,其曰:“婚者,昏时行礼,故曰婚。姻者,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诗》云:‘不惟旧因’,谓夫也。又曰:‘燕尔新婚’,谓妇也。所以昏时行礼何?示阳下阴也。昏亦阴阳交时也。”[8]491–492之所以昏时行礼,既取“阴阳交时”之时义,又彰显了“示阳下阴”之男主女从、夫唱妇随的阴阳互动关系。男女经由婚姻而结成夫妇,夫之得其为夫者,妇之得其为妇者,阴阳合德,刚柔健顺,各正其位,此人伦之所以正。夫妇伦常关系是阴阳之道具体而微的显现,夫妇之家是一小天地,天地之道是“大”,是夫妇要效法的对象。“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夫妇之间,在于能相互扶持。
夫妇一伦在五伦中尤为重要,夫妇之间既有父子亲亲伦常之义,还有君臣尊尊之义。“妻事夫有四义:鸡鸣縰笄而朝,君臣之礼也;三年恻隐,父子之恩也。图安危可否,兄弟之义也;枢机之内,寝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纯以君臣之义责之。”[9]195以夫妇喻君臣,是因“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10]164此理与君臣之义同。以夫妇喻兄弟,“兄弟谓昏姻嫁娶,是谓夫妇为兄弟也”[2]501。《诗》云:“宴尔新昏,如兄如弟。”《列女传》亦曰:“执礼而行兄弟之道。”以夫妇喻父子,则强调了夫妇之亲亲的伦常关系。“夫妇之结合而能白头偕老,其必然性可以说就建立在父子之伦的必然性上。”[11]但是夫妇一伦,与父子之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夫妇并非天然的血亲关系,“妇之于夫,非天亲也”[7]16。一方面夫妇一体同心,讲求尊尊但不可害亲亲之义;另一方面,夫妇之间有阳主阴从之理,讲求亲亲又不可害尊尊之义。而且,夫妇双方所能达成的“内在相知与存在上之共同一体,连血脉相连、共同生活之父母子女都无法超越”[12]。《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对齐景公论及五伦之义曰: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
夫妇伦理的要求是夫义妇正,“义”与“正”的要求是一种双向的互动,非单向只要求夫行“义”或妻行“正”,在要求妻子的同时,首先丈夫要能做好表率。夫妻双方积极尽己之能,行己之义,立身行道,报施一体,生命在成长中趋于真实饱满。《樛木》讲的就是上施下报之情,“报施之情”可根据樛木与葛藟之“履”迹而“考祥”。樛木高木能下曲,葛藟攀附而上“犹能庇其本根”[13],上施下报,故能福履安之以“绥”、盛大而“将”、就之以“成”。需留意的是,葛藟是有根植物,并非无根的缘求与攀附。樛木下曲能施,葛藟上攀而报,施报之情乃“人道之常”,正是施报之情不绝,夫妇相辅相成,才能“乐只君子”,有福禄可安。毛诗是从“后妃逮下”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的,但落脚点依然在“逮下而安”。唯有内治安,由内而外,君子门外之治方成。
(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的人伦与礼法
男女结合成家,要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一种经由人伦共同体、礼法社会共同体而加以确认的、族群性认可的象征。这与恋爱的情感不一样。恋爱讲的是无心之情感,而婚姻是人伦,人伦是讲秩序的。经由婚礼而成家,这是由情感进入了秩序的共同体。父母之命,代表的是“家”这个人伦共同体的认可;媒妁之言,是礼法社会共同体的象征。父母代表的是“家”,家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居所,它还是时间意义上的伦理存续之所,家具有生生不息的道性。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齐家”是以“宗法社会”及“封建社会”相结合的“大家族”意义上的“家”,是由己身联结的,上至高曾祖父、下及子孙玄曾的群体之“家”。“家”的纵贯维系,横穿和依赖是的人伦之常。正是有了伦常,家才成为一个情感的归所、一个交流和永续的基础。婚姻之礼,谋合的是“二姓之好”,这意味着婚姻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包含着伦常秩序的社会行为。《郑风·将仲子》中提到了“父母之言”不可不畏:“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然而关于该诗的主旨,毛传以为是刺庄公也,他面对公叔段的失道之举而不制止,也没有听从祭仲的劝谏,故意放任其弟段失礼失道;朱子《诗集传》则认为该诗是淫奔诗,与庄公等无关;方玉润则从诗本义出发,认为该诗或为民间夫妇相爱慕之词,其诗义“有合于圣贤守身大道……惟能以理制其心,斯能以礼慎其守”[14]204。三说立意不同,但都突显了“以礼自持”的主旨。面对权势或情爱的迷惑,父母至亲或有不敢欺,是故“欲念顿消,而天地自在,是善于守身法也”[14]204。《齐风·南山》亦有诗言:“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毛传释之曰“必告父母庙”[2]403。郑笺云:“取妻之礼,议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谓告。”[2]403这说明了娶妻必告启父母,议于生,告于庙。具体来讲,婚礼六礼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前五个程序都是女方在“家庙”接待媒人,此前还要先为神摆好案几,安神尊命,然后迎接媒人并“听命于庙”[15]1182。婚礼六礼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亲迎”,男子承父命前往亲迎,女子父亲会先在家庙为神设几,而后在家庙门外迎接,“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15]1183。因此,娶妻必告父母的背后是对人伦共同体的追溯、对生命伦常的敬重,要在家庙祖先的见证下慎重地对待。
此外,父母为子女选择的良配,主要从“孝悌”德行上来考量。《大戴礼记·保傅》云:“谨为子孙娶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嫁女、嫁侄女,为后人提供了嫁女择婿之率范: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论语·公冶长篇》)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公冶长篇》)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嫁,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篇》)
孔子嫁女,不问富贵地位,皆论其德。论及公冶长,不过曰“非其罪也”,更见公冶长行为之恒。论及南容,赞许其谨言明哲,其他不论,因为一家之内,言语不慎则喜怒无常,君子知言为心声,见南容三复白圭,恐言有玷,其慎如此,既是修身之理又是齐家之义。孔子择婿以“尚德”之君子为标准,真可谓择婿之表率。从孔子择婿不仅可见嫁女之道,更可见修齐之理。察乎人伦,以得其理。故,父母之命不可不慎择。
媒妁之言所代表的社会礼法,其作用在于引导人的性情得其中正。《周礼·地官》有“媒氏”一职,“掌万民之判”。贾疏曰:“‘掌万民之判’者,谓治百族昏姻之事。”[16]1033可见媒氏作为“特掌其礼法政令”[16]1033的一种官职,不仅是“合二姓之好”的婚姻媒介,更重要的是合法婚姻关系缔结的重要礼法保障。通过借助“媒妁之言”,“谋合异类,使和成者”[17],也避免了男女草率结合等行为,《士昏礼》郑注说:“皆所以养廉耻。”[18]68《齐风·南山》一篇言道:“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此用“兴”法,以析薪非斧不能,来兴娶妻必有“媒”方可,“男女无媒不交”[15]1002。若是无媒而交,则是丑耻的一种行为。同样的,《豳风·伐柯》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诗句表达:“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毛传曰:“媒,所以用礼也。”[2]618使媒用礼则得妻,这是婚姻缔结的重要礼法保障。《卫风·氓》中的女子一方面也明白“良媒”的重要,但仍抛却了礼法与男子私奔,终落得被弃的下场,这也从反面强调了“媒”在婚姻关系中的重要性。《鄘风·桑中》一诗讽刺男女相奔而“不待媒氏以礼会之”的社会乱象,这种乱象是由于卫国公室淫乱致使政教衰败、民俗流散而导致的。
父母之命代表的是社会秩序的伦常形态,媒妁之言代表的是社会秩序的礼法形态。孟子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可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成就幸福婚姻的两个必要条件,若不依礼而奔则为妾;依礼而结成的夫妻关系对彼此和家庭有道德使命和义务驱使。夫妻关系,是人伦之始,是王化之端,人伦之常要经由礼法社会的联结确定,而融入更大的族群生命延续与繁盛中,进而移风易俗,化王道之成。
二、婚礼之义宜有别
(一)婚礼之“别”与“合”义
婚姻是男女两性建立生命共同体的标志,是一个人具备合乎礼法的社会身份的标志及社会生命的确定。男女经由婚姻之礼而结成夫妇,夫妇关系乃人伦之本,故而婚姻之礼于社会各种伦常关系的稳定非常重要。《礼记·昏义》开篇就道出了婚礼的功用:“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15]961昏礼之用,在于合两姓家族之好,非合男女二性之好;昏礼必告祖宗,也是宗祖的衍续,这是一种“共生、共长、共好”的生存原则,由此也可见夫妇关系的形成对于人类生命繁衍存续的重要意义。
婚礼谋合二姓之好的前提是要明“别”。首先,明人禽之别。《礼记·曲礼》曰:“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15]6圣人制礼,使人明礼,远离“父子聚麀”的禽兽之行。其次,明男女之别。男女要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族群性共同体的认同方能结为夫妇。人之情以男女之情尤甚,男女若无防则性情散乱,故圣人制礼复其性,对待婚礼要“敬慎重正”,即要敬谨、审慎、郑重、规正地对待婚礼。《礼记·经解》曰:“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15]955明男女之别,不是对男、女本身的限制,而是基于他们都作为“身之为人”的共同前提下,寻找并实现两性差异所蕴含的“和合与共”的人性生存意义。明晓男女之别,也就明了夫妇之义,这就需要通过恰当的人文形式,即婚礼来体现,“婚礼享聘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19]。夫妇是至亲,越是如此,越是要明确夫妇间应有的界限,这个界限涉及夫妇在家“内”领域与社会“外”领域的角色与职分等。“礼者别宜”[15]725,夫妇有别,要依礼而行,明分才能使群,家内之治与门外之治各有分工。若婚姻之礼废,夫妇不依礼而行,“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也”[15]956。所以,“礼始于谨夫妇……辨外内”[15]545。明辨内外,各自分工,循其名责其实,才有利于人伦共同体的发展。
婚礼是其他社会仪礼和伦常关系的根本和基础,冠礼是成德之始,两者皆不可以童子之道论;“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15]1185。这从五个方面标举了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常规礼仪,其功用分别是“始、本、重、尊、和”。婚姻之礼,其慎重如此,是因为“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15]1182。婚礼之所以是礼之要本,在于它是社会伦常关系的逻辑起点。夫妇为人伦之本,男女只有通过婚姻关系才能确定在人伦共同体和礼法社会共同体中的归属。
(二)《大雅·大明》一诗中的婚姻六礼
“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2]360婚姻之道通过嫁娶之礼明其规制。礼为天地之序,“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20]。人之性情得以通过礼乐而润泽,生命就不再是漂泊无依,而是与礼乐连接,并经礼乐润泽的生命。昏礼之名,是因为以昏为期,故名之。之所以以“昏”为期,取其“阳往而阴来”[18]68之义。婚姻之六礼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唐代杜佑《通典》提道:“燧皇氏始有夫妇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五帝驭时娶妻必告父母,夏氏亲迎于庭,殷迎于堂,周制限男女之岁,定婚姻之时,亲迎于户。六礼之仪始备。”[21]《大雅·大明》一诗就简要而又集中地展现婚姻六礼。其诗曰: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
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孔疏据毛传郑笺之义将此八句训为“准行六礼之事”[2]1138。文王赞美“大邦有子”,大邦之女宛若“天之妹”,是赞美女子有贤德。既知其贤,便“求昏”。此“求昏”是指婚姻六礼程序之初礼——“纳采”,男方通过媒氏向女方提亲,行采择之礼。郑笺下云:“既使问名。”[2]1136据《仪礼·士昏礼》,纳采初礼过后,即请问名,“摈者出请,宾执雁,请问名。”[18]72可见纳采、问名两礼在同一天进行。下言“文定厥祥”,郑笺云:“问名之后,卜而得吉,则文王以礼定其吉祥,谓使纳币也。”[2]1137娶妻占卜的目的是“卜女之德,知相宜否”[8]472,结果是“祥”,则纳吉,继而纳征。孔疏曰:“昏以纳币为定,定此吉祥,唯纳币耳,故知文王以礼定其吉祥,谓纳币也。”[2]1137下言“亲迎”,则“请期”之礼可知也。文王亲迎于渭水,并造舟以为桥梁,可见敬慎郑重。郑笺云:“欲其昭著,示后世敬昏礼也。”[2]1137婚姻六礼,依次渐进,有渐卦之道,犹然待礼而渐进也。婚姻六礼,不贞而能之乎?男女结为夫妇,要依礼而行,循礼渐进,急欲躁进者如《氓》之女子而未能有终。
婚姻六礼,以亲迎为重。孔疏引郑玄曰:“天子虽至尊,其于后犹夫妇也。夫妇判合,礼同一体,所谓无敌,岂施于此哉!”[2]1139《韩奕》一诗也讲到了诸侯亲迎:“韩侯迎止,于蹶之里。”韩侯娶妻,亲迎至蹶里。然春秋以降,礼崩乐坏,亲迎之礼渐废。《春秋》隐公二年九月,“纪履緰来逆女”,公羊传讥“始不亲迎也”[9]38。按《春秋》书法,外逆女不书,然此事被书之于册,乃因纪国国君未行亲迎礼,而是派遣纪国大夫履緰前来。国君不亲迎此前已有,然公羊传文讥讽“始”不亲迎,乃是因此这是入《春秋》后的首例不亲迎之事,故虽此为“外逆女”,仍书之。何休解诂曰“民所以必亲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9]39。此事托为《春秋》不亲迎之例始,是为了彰明王者行教化之端义。“《春秋》正夫妇之始也。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和,君臣和则天下治,故夫妇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9]40
《著》是一首描述婚礼现场的诗。毛序以为该诗刺“时不亲迎”,即《著》从正面描述了婿至妇家亲迎之礼;三家诗无异议。然而新郎所俟之处(“著、庭、堂”)不一,所着冠服之饰异,毛传以为是亲迎之人身份不同,分属士、大夫、人君;三家诗认为是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诗篇错陈三代亲迎之礼;郑笺则以为三章俱述人臣亲迎之礼;而朱熹引吕祖谦言认为,新郎没有亲迎,“故女至婿门,始见其俟己也”[3]67。王先谦结合三代礼制的分析认为,《著》之三章分述三代婚礼之制。虽三代婚姻礼制不同,但《著》分章历陈,足见“其礼端严之盛自见,列代崇重之义自明”[22]。而这也是《著》要表达的主题,即以三代亲迎礼制讽刺齐俗之时衰,以刺时失。
亲迎之礼如此重要,首先是因为夫妻是亲人,“敬而亲之”,既是对妇的重视,也是对妇的尊敬。《礼记·郊特牲》曰:“婿亲御授绥,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敬而亲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15]500新郎亲自为妇驾车,是要表示夫妇之间的相互亲爱之情。尊敬并亲爱亲人,先王以此推而广之并得到了天下。整个亲迎礼,是特别能表示夫妻之敬的。其次,表示男刚女柔、夫唱妇随、阴阳和合的夫妇伦理。《礼记·郊特牲》曰:“男子亲迎,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15]500刚柔相济、阴阳和合、明夫妇相扶之意,如此“刚来而下柔”,配合得当,自然会有“动而说”的良效。再次,要端正人伦之始。“亲迎之道,重始也。”[23]479夫妇乃人伦之本,天子亦亲迎,就是要表示对妻子的尊重,夫妇一体。在《礼记·哀公问》中,鲁哀公认为戴着冠冕身着礼服去亲迎,岂不是过于隆重了吗?孔子正色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15]962《列女传》有“宋恭伯姬”一则,记载伯姬因宋恭公不亲迎之故,不肯听命行夫妇之道,习鲁诗之刘向赞其“守礼一意”。
婚姻六礼中,除“纳征”用币帛外,其他五礼均用雁,取的是彰别、相从之义。《礼记·郊特牲》:“执挚以相见,敬章别也。”[15]500执雁以为礼,表示对妇的恭敬,同时彰明男女之别。《白虎通》曰:“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8]457这是根据大雁随阳之习性而寄望夫妇和谐,夫唱妇随,明礼有序。纳征之礼是男女成婚的关键一步,《礼记·坊记》曰:“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15]1002其用“玄纁束帛、俪皮”作为聘礼。纳征讲求的是“币必诚”,即“币帛必须诚信,使可裁制,勿令虚滥”③。这代表的是一份诚意和信诺,“信”意味着“诚”的落实,是扎扎实实的生长之德。经由纳征之礼男女婚姻关系初步正式确立,为即将结成的夫妇生命共同体长养出扎实可信的生命力,故“昏礼者,礼之本也。”[15]1185
(三)《召南·行露》之贞女谨礼守志
礼是实现人与人美好关系的仪则,礼的背后彰显的是分寸节度。“婚姻之际,非礼不可。”[2]364通过庄严恭敬的婚礼,使人们的“习性”转化为“德性”。《召南·行露》一诗则讲述了女子因夫家婚礼不备,拒不肯往,结果招致狱讼,但依然持节守义、“亦不女从”的坚定态度。毛序释诗旨曰:“《行露》,召伯听讼也。”[2]93毛诗认为在衰乱之世,因被泽文王之化,“贞信之教兴,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2]93,该诗重点在德行教化。三家诗的解释重在贞女谨守礼制方面,强调了对婚姻礼制的坚守。其中,《韩诗外传》明确指出该诗是女子许嫁之事:“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然而未往也,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故举而传之,扬而歌之,以绝无道之求,防汙道之行。”[24]男子“一礼不备,一物不具”,是财礼不足。妇道之宜,即是能以礼自守,持志不从。《齐说》也认为是关于婚礼之讼:“婚礼不明,男女失常。《行路》有言,出争我讼。”[25]刘向在《列女传》中为这首诗安排了一个具体的故事情节:召南申女乃申国女子,被许嫁给丰城的一位男子,因夫家“轻礼违制,遂不肯往。”[10]155毛传亦曰:“昏礼纯帛不过五两。”朱子沿用此说,认为是“媒娉求为室家之礼初为尝备”[3]13。可见,该狱讼的起因是男子纳征之币不足,女子谨礼持志而不从。
《行露》之女子能谨礼,谨的是室家之礼。纳征之财礼,并非仅仅是物,也是“诚”的表征。《礼记·郊特牲》曰:“币必诚,辞无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26]《行露》之女子并非贪财的女子。“昏礼纯帛不过五两”,可见求为室家亦易备礼,但男子为什么不备礼呢?《行露》虽然借女子之口来谈婚礼不备的问题,其实也是在谈强暴之男的德行问题。“礼,毋不敬。”夫妻一伦,是敬亲相加。既要相亲爱,又要能诚敬。亲爱与诚敬是一对阴阳的关系,没有诚敬,何谈真正的亲爱;没有真正的亲爱,所谓的诚敬也是一句虚言。婚礼作为夫妻伦常关系的开端,源头清明,根基方正,《易》曰:“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行露》之女子注重的是室家之礼背后的夫妻伦理,也是“爱身”的表现,是敬身自重。《礼记·哀公问》曰:“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15]962敬身,是因为己身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是天地之间的生生之物,是通过自己与父母、天地的关系而达成的,它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专属。是故,敬身,才是爱身。
《行露》之女子能守志,守的是大贞之志。《易》之屯卦九五爻辞曰:“小贞吉,大贞凶。”[27]19对于《行露》之女子而言,小贞是名节,大贞是作为人的尊严。屈从小贞,就不会招来狱讼,是为“小贞吉”;坚守大贞,被讼而狱,是为“大贞凶”;这是从“利”的角度进行的判断。然而,从“义”的角度来看,“凶,义也;吉,非义也。”[7]11坚守大贞的结果虽是凶,但此举是合乎“义”的。屈从小贞的结果虽为“吉”,但却是不义之举。狱讼之事会伤其名节,一般人可能会选择屈从。但《行露》之女子宁失小贞之名节,也要坚守大贞之志,不违礼而从。固然,她会因为招惹狱讼而有损名节,但她“亦不女从”的抗争是在捍卫她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大贞者,保己而不保物者也。”[7]11其为“大贞”者,真正保全自己的心志而不汙于身,不畏世俗,奋起抗争,选择将活但不活于苟活。
女子尚能谨礼持志,男子亦要自省其身,《行露》之男子也该有所警醒。《易》之讼卦六三爻辞曰:“食旧德,贞厉,终吉。”对女子而言,坚守其志不畏世俗眼光,以保全其有,是因为她能“食旧德”,以本性之德为本,守住中正之道,虽然过程危险,但结果可能呈现吉象。对男子而言,要能够“守素分而无求”[27]31,回到自己的生命本身来思考,甚至是无讼,而不是凭势诉讼。“无讼在于谋始,谋始在于作制。”[6]28若男子按婚姻六礼之制迎娶女子,则无讼而吉。此外,方玉润认为该诗恉是贫士持志,“士处贫困而能以礼自持”[14]104,从男子的角度以启示。不论《行露》一诗的主人公是“贞女”还是“贫士”,在他们身上都展现出谨礼持志的一点。“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陷溺。”[23]479礼,乃人行走的节律,失其礼节,必陷其困。《史记·外戚世家》:“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28]夫妇一伦,乃人道之开端,而婚姻嫁娶之事就显得尤为慎重,“所以传重承业,继续先祖,为宗庙主也”[10]155。
总体而言,《行露》之女子,坚守礼制,迎险而健行,为的是大贞之志。行其当行,不以利害,行其可行,走从容的“中道”。“天地合而万物兴焉,人以昏姻订其礼。”[15]500男女需守礼而结成夫妻,敬慎亲爱,并通过礼乐的教养形成一个人伦的天地。这样的人伦天地形成的家国具有文明的教养,是一个有礼义的人伦共同体。而夫妇之礼,彰显其义。如《鹊巢》篇从正面呈现了一个有礼义的共同体生活,所有的礼乐生活是围绕共同的空间展开的。鹊建巢,鸠居之,比喻夫妇相比而居,将之成之,共同孕育、建设新的家庭,这是一个整全的婚姻家庭生活。诗中反复出现的“百两”,是“文之备也”。这与《行露》中的“室家不足”“一礼不足”形成鲜明对比。
婚姻之礼乃“礼之本也”[15]1185。婚姻之礼是男女结成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礼法保障,对于家道的整全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而并非简单的系列程序。“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15]985文之以礼乐,通过礼乐恰当地表达情感,通过情感表达自返其性,这是一种通往“复性”的生活状态。“人之自然生命之生与婚姻及死,皆在礼乐中,即使人之生命不致漂泊无依。”[29]而男女经过婚姻之礼结为夫妇,进而奠定政治社会生活的伦常基石,也标志着一个新的人伦共同体的诞生。
① 朱熹将室、家从空间上做了阐述:“室,谓夫妇所居。家,谓一门之内。”参见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6页。
② 见《公羊传·隐公二年》“妇人谓嫁曰归”注。
③ 见《礼记正义》(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1页。“币必诚”,这与今日聘礼虚高形成强烈比照。
[1] 许慎.说文解字注音版[M].徐铉,校定.愚若,注音.北京:中华书局,2015.
[2] 毛诗正义[M].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 诗集传[M].朱熹,集注.赵长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
[4]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吴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9:24.
[6] 王弼.周易注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
[7] 王夫之.诗广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 陈立.白虎通疏证[M].吴则虞,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9] 春秋公羊传注疏[M].何休,解.徐彦,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 绿净.古列女传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11] 林安梧.血缘性纵贯轴:解开帝制重建儒学[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6:38.
[12] 简良如.诗经论稿:卷1[M].台北:Airiti Press Inc,2011:174.
[1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551.
[14] 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5] 礼记[M].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16] 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 周礼注疏[M].郑玄,注.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71.
[18] 仪礼注疏[M].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9]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44.
[20]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2880.
[21]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333.
[22] 王礼卿.四家诗旨会归[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28.
[23]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4] 韩婴.韩诗外传集释[M].许维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2–5.
[25] 徐芹庭.焦氏易林新注[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320.
[26] 礼记正义[M].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949.
[27] 程颐.周易程氏传[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
[2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3893.
[29] 唐君毅先生复牟宗三先生书[M]//牟宗三.人文讲习录.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7.
The Complete Meaning of Marriage to Family in the View of Poem and Rite
ZHAO Guoya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The men and women become couples through the rites of marriage, and then form a community of life. The rites of marriage cooperate with “the good of two surnames”, which means that marriage is not an individual behavior, but a social behavior that contains the ethical or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s the premise and cornerstone of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social ethics. Couples should make clear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so that to do their best with love and respect; and in the end to form a world of human relations through the upbringing of rites and music.
the Rites of Marriage;; family Tao; community of life
G02
A
1006–5261(2020)05–0139–09
2019-12-16
赵国阳(1986―),女,河南南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