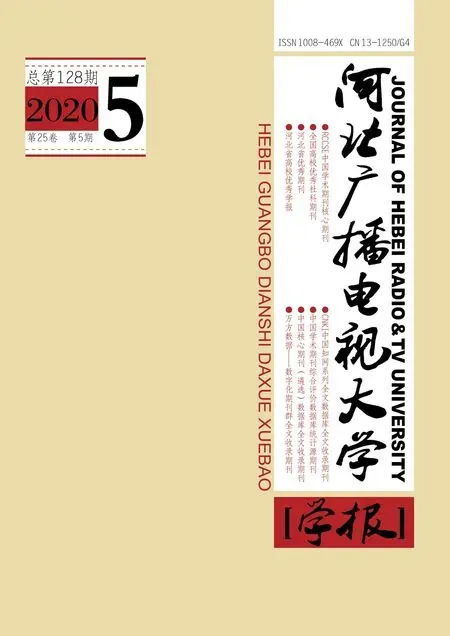韦斯· 安德森电影中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时空观
2020-01-07徐斯然
徐斯然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文化学系, 中国 香港 999077)
韦斯·安德森是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独立制片运动的重要成员,他的电影深受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电影学者华伦·巴克兰德(Warren Buckland)认为韦斯·安德森的电影“与后现代主义密不可分且相得益彰”[1]。后现代主义在电影时空的表现上往往展现出其时间的无序性、时空的杂糅性,在时空的链接上“它不主张去旧更新,不斩断与传统的联系,在中心二元对立中进行拆解和间离,从而消解现代理性的权威”。[2]在其电影重叠时空的往复中,又试图建立一种“游荡者的时空观”:“创造出一种错位的时空关系,他在代表现代性和当下的时空中游走,但却总是在往后、往过去看。他总是想要回到自己的记忆中去,而拒绝所有机械复制的图像所提供的、所呈现的过去。”[3]
所以韦斯·安德森的电影中常常采用叙述倒置的手法,将当下和过去的多层时空置于对读的状态之中,使人物所经历的外在时空转化为自我的时空之中,其中包含着强烈的主观性与虚构性,但也正是如此,他的电影中深化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在看似散乱的时空结构中,寻找一种真正的链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个人情感交流。
一、媒介回溯产生的“深层时间”
在韦斯·安德森的电影中,他经常以不同的传播媒介作为时间回溯的工具,这些媒介包括戏剧、电影、书籍等。他以媒介介入的方式进行不同时间的堆叠,形成时间的套层结构。在他的电影中,时间绝不仅限于现在进行时或过去进行时这样单一的线形时间结构,他通过时间的不断回溯创造出一种“深层时间”,这意味着故事在复合历史的发展中不存在一条基本线,你可以越出这条线而去寻找其他的星丛。并且这种套层结构也并非简单的叠加,在深层时间的框架内,他们展现出强烈的流动性:其具体表现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相互追溯、过去与过去之间的交互感染,这种戏剧性的追溯模式模糊了时间的界限,在打开故事时间深度的同时,也扩展了时间的维度和广度。
1.重建历史逻辑的小说想象
韦斯·安德森善于将电影的故事放置在一本小说的框架之中,以此来进行异质空间的想象。比如:《布达佩斯大饭店》中第一层叙事结构始于一本名为《布达佩斯大饭店》的书;《穿越大吉岭》中的杰克是一个作家,他构想的小说不时地穿插在整个故事之间;《天才一族》更是把整个故事置于一本书的不同章节之内。韦斯·安德森以小说的方式进行故事前史的回溯和创造。究其原因,小说与历史的相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不断地被重写、修改。韦斯·安德森以小说的形式,利用人物的主观视角重建了历史的顺序与逻辑,所以他的故事消除了垂直的历时分界线,用大量的跳切镜头来阻断叙事的连贯性,让人们在故事的真实性和虚构性之中游走。
《穿越大吉岭》讲述的是三兄弟在错置时空追寻心灵之旅的故事,这是韦斯·安德森第一次将家庭创伤作为探讨的对象。与其他影片不同,《穿越大吉岭》一直以线性时间的发展模式作为电影的基本时间线,剧中唯一一次时间倒叙发生在他们参加落水男孩葬礼的途中。这一时刻,影片回溯到了他们关于父亲葬礼的集体记忆,正是这一“回忆”藏匿了他们彼此痛苦和不信任的根源。然而在此之前,杰克的小说已经埋下了戏剧性的伏笔,在电影前半段的游历过程中,杰克向两兄弟介绍了自己新写的小说:德国空军汽车公司,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杰克一再向他俩重申书中故事的虚构性。但当回忆重新上演,这个虚构的故事却成为记忆中的真实,在参加父亲葬礼的途中,他们在德国空军汽车公司上演了一处戏谑的表演。它既是记忆,同时也是虚构性的戏剧表现。
一方面,小说可能是这次事件的戏剧化表达,但也可能是真实记忆的自我反省。那一次,他们见证了父亲葬礼中母亲的缺席,发现了大哥在家庭关系上有所隐瞒,翻出了父亲行李箱中那本还未被打开的书——杰克的《隐形墨水及其他故事》。小说的故事似乎看透了他们悲伤的深渊,对于这些角色而言,这些真相是不可避免的痛苦根源,当杰克一再重申故事作为小说的虚构性时,他其实是用小说掩饰其内在的伤疤。所以现时的心灵之旅无法解决他们记忆中隐藏的矛盾,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随时间回溯到过去,直面创伤才是疗愈创伤的必要前提。
在《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小说则建构了一个新的叙事层次,这部电影可以说是韦斯·安德森电影中最复杂的构图形式。他在这部影片中进行了深入的时间开掘,最深层是主体的故事事件,向上一层是老门童Zero(零号)的回忆,再向上一层是作家对于故事的戏剧创作,最后是女孩阅读之后的主观理解。此时,“作者、读者、世界、文本等要素得到了综合体现,产生了复杂但有机的内在关联”,[4]虽然观看过程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但在经过层层人物主观地无意识加工后,真实的故事性显然已经被小说化了。
所以布达佩斯大饭店本身是一个充满象征符号的、被重建现实逻辑的虚构的世界。“后现代主义电影空间一大特点就是深度的削平,即从本质走向现象,从深层走向表层,从真实走向非真实,从所指走向能指”,[5]这种深度的削平不是空间的压缩,而是对宏大叙事的消解。所以韦斯·安德森将厚重的历史表达集中于人物真实发生的情感关系之上,他讲述了艰难社会中文明个人的故事:Zero(零号)经历了欧洲战前文化褪色的最后辉煌,在面对难以置信的混乱、暴力和贪婪的世界中,他们却拥有一套自我的内心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使他们得以用纯粹的态度表达自己对事物的正确理解,形成一种不以权力评判体系为标准的信任。古斯塔夫相应地提供了某种优雅文明的外观,但正如台词所说:“古斯塔夫的世界早在他步入前就已经逝去了,是他用超凡的魅力维持了这种假象。”他所在的酒店系统也是灰暗之中的明确光线,无条件地成为他越狱行动的精准指南,他们之间有一种深入的链接,即志同道合的人共享着一份职业。除此之外,古斯塔夫与Zero(零号)形成了跨越种族、跨越阶级、跨越是非评判的真正友谊,他们在这个灰色世界中建立了最真诚的沟通,情感对于苦难的缓冲,才是韦斯·安德森穿透重叠历史空间表达出的真正渴望。
2.戏剧舞台主观性的时间拓展
韦斯·安德森的电影中常常出现一个一体化的假定性戏剧舞台,它可以荒诞和假定对真实世界的书写。纪录片在它的电影中也被伪造成戏剧空间,使真实和虚构形成一组悖论。对于舞台空间上的含义,韦斯·安德森的电影更善于展现其时间上的延伸,戏剧舞台也包含着一种主观演绎,具有亦此亦彼的开放性。相对于小说创造了一个想象的空间,舞台或者具有舞台感的纪录片形式则是一个实在的观看空间。这种观看空间包含着双层时间,一个是舞台表演的物理时间,它是线性的有序的;一个是主观的心理时间,它是非线形的无序的,但它可以超越物理时间,将人物内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限放大。
《水中生活》讲述了一个海洋纪录片导演的故事,电影的开篇以舞台形式的画面作为开场,红色的幕布完成了空间的视觉闭合,假定性的戏剧舞台是链接当下与回忆的一个媒介,影片的开始意味着将视角引入回忆之中,在观众的“集体性注视”下,纪录片导演史蒂夫(Steve Zissou)拍摄的影片《美洲豹鲨第一部》上演了。史蒂夫(Steve Zissou)的影片真实记录了他充满创伤的一次出海经历,他的挚友伊斯特(Esteban du Plantier)在和他出海寻鲨的过程中被鲨鱼咀嚼吞下,在这次航行中牺牲,也为这部影片贡献了最大的噱头与争议。
在“集体性注视”的剧院模式中,他的回忆性创伤接受了全体观众的审判,形成了他与观众沟通之间的不可调和,观众理性的冷漠造成了他心中的二次创伤,他不得不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与伤痕,同时也造成他与回忆间的不可调和。他再次以同样的路线出海寻鲨,进行《美洲豹鲨第二部》的拍摄。这一过程其实是史蒂夫(Steve Zissou)寻找对抗和疗愈心理的方法,它使得时间向未知的未来延伸,也向相似的过去回溯。
相比《水中之书》中纪录片电影呈现出的回忆写实主义,电影《青春年少》的戏剧舞台则更多体现着一种对未来时间的想象。《青春年少》中的麦克斯是戏剧小组的导演,他对于戏剧情节的编排带有一种现实无法满足的期待感。戏剧舞台切割了现实时间,存在着强烈的英雄主义情节,每一句台词都要出现在对应的剧情当中,不能有丝毫的偏离,从而形成一出完美戏剧。
可现实中事情的发展却常常背离他预设的轨道,他将戏剧想象中的剧情带入现实,却常常深陷逻辑不合理的泥潭。他一直以戏剧中的节奏等同于生活中的节奏,戏剧中的时间等同于生活中的时间,所以当他试图将影片中的海洋生物带入真实中,为心爱的人建一个水族馆时,他失败了。他唯一和解的办法只能将自己再次带入虚构性的戏剧空间中,他在生活中的遗憾,不被认同的梦想以及少年炙热的爱情理想,最终在他导演的戏剧中得到了实现,他用戏剧和自我的欲望交流,在未来的戏剧时间中满足了现实时间无法达成的期待。
二、“间性空间”融合的情感联结
韦斯·安德森电影中的人物故事总发生在一个个独立的空间之中,但是这个空间却也不是单一的、密封的空间,空间之间也进行相互的交流,是一个文化混杂的“间性空间”。“间性空间”这一后现代性概念是由哲学家霍米巴巴提出的,他“从承接索亚的第三空间入手,认为文化的所有形式都持续不断地处在混杂性的过程之中,但恰恰是这种混杂性的第三空间才使得其他各种立场避免二元对立思维而得以出现”。[6]所以在韦斯·安德森的电影中时常出现多重空间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既包括空间的流动,即空间的“里”与“面”形成的物体内外的接触与碰撞;还包括空间的组合,即“俄罗斯套娃式”的空间嵌入结构。
众多关于韦斯·安德森的电影研究理论都倾向于探讨其电影中独立空间的结构意义,将间隔感披上神秘的外衣,疏远观众观看的空间距离。但个性空间的塑造绝不意味着孤立,他包含着多元的文化中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个体,正如迈克尔·夏邦所说:“距离并不意味着令我们远离情感,而是让我们以更多的理性去思考和认识它,使我们看到情感的整体性。”[7]
1.“里”与“面”的空间交流
空间的流动性是韦斯·安德森电影的突出特点,通常如果剧中人物静止,那么相对人物所处的空间就会移动;如果空间静止,那么人物就会流动;假使是静止空间中的静止的人物,摄影机的视觉镜头就会移动。这种流动的状态,塑造出空间与人物开放界面中的交流感。
移动的交通工具是空间运动的最佳载体,它往往包含着“里”和“面”两层,内外空间在相互接触时会发生交换和交流。《穿越大吉岭》的梦想专列、《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城际列车都是以火车作为流动空间的移动工具。火车本身有固定的轨道,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规则的行进方式,但是两部电影中的人物都没有通过火车到达预定的终点,列车在运行途中由于不同原因戛然而止。《穿越大吉岭》的火车偏离了轨道,行驶到一片荒芜的沙漠之中,《布达佩斯大饭店》的火车两次被军队拦下,因为Zero(零号)的移民身份而被迫中止行程。在火车停止运行的时刻,火车内部的“里”和外部的“面”发生了接触和碰撞,里面是他们的心理秩序,外面是世界的客观秩序,单独的某种秩序都无法形成完整生命的真谛。
所以,当意外悄然而至,“里”和“面”有了对话和冲突,他们才能从独立的个体变成交互的整体,人物之间的内在交流才真正形成。在《穿越大吉岭》中他们走下列车,卸下与父亲行李的不舍纠葛,脱下各自身份的面具,三人为参加葬礼一袭白衣走在沙漠中时,真正的情感互换发生了,三兄弟第一次出现在统一的镜头中,他们迈着相同的步伐向前走,歌词成为情感交流的媒介:“我们不是两人,我们是一个人,你我来自同一个地方,那里是被抛弃者的故乡,所以我们同走在一条路上,我们不用说什么,直到到达最后的宁静。”《布达佩斯大饭店》中的交流形式则略显沉重,火车的“里”是文明世界最后的秩序,火车的“面”是摧毁秩序的战争体系,第一次文明与野蛮的交锋是文明占了上风,第二次文明与野蛮的交锋则是文明的最终摧毁,可是古斯塔夫与Zero(零号)的情感正是在这两次交锋中得到了深入的连接,古斯塔夫的自我被建筑到Zero(零号)的内心中,得以在未来延续下去。
2.“个体”与“整体”的空间感染
韦斯·安德森电影中的空间是一个个体量不一、彼此独立又互相依存的空间段落。空间的叠加和错层形成了不同空间之间的套层结构。当个体空间之间产生了重叠,就会形成空间感染,促成不同个体空间的交流。
这种“空间感染”的框架结构在韦斯·安德森电影中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形成了他电影风格的主体性,他也借此来表达情感的多样性。在《月升王国》中,它被用来展现疏远的亲属关系。卡拉与父母分别处在三个不同的空间内,在影片的开场时刻,一组纵深镜头以叠加的方式将三个空间放置在统一整体内。但是,整体的有机结合,却并未形成三个人的整合,反而更加凸显了个体间的孤独与陌生。他们只是被血缘包裹的孤立个体,彼此缺少交流,更无法融入。
差异化空间截面的展示和组合也能形成空间之间的感染,《水中生活》的空间截面是船上的不同船舱,《布达佩斯大饭店》中的空间截面是酒店的各个房间,《穿越大吉岭》中的空间截面是火车的节节车厢,这些具有差异性的空间最终都被组合到同一整体中。用空间的叠加建构了“叙事起止的结构性符号,空间在不断被割裂的同时又被多次粘合,同舞台的分幕/换场一样,每个独立空间指向不同分幕的舞台空间,人物角色的行为与关系随空间流变,又让叙事不断变奏,造就了不同空间内景观与叙事的独立,形成了不同情景内的融合与联系”。[8]
另外,眼睛也是一种空间交流的界面,它将物体分隔为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通常来说,眼睛的看都不是纯粹客观的观看行为,它包含着主观价值的观看视角。所以当不同的人看向同一物体时,观看的结果可能出现不同的差异,所以不同视角的观看本身就可以构建出框架中的复合关系。当个人的观看视角变为重叠的观看视角时,就会出现“空间感染”,从而形成不同个体间价值观的碰撞。《穿越大吉岭》中的皮特就有着双重的观看视角,他佩戴着父亲留下的眼镜,所以他的观看行为中便加入了父亲的部分,他的自我认同必须借助于父亲的形象才能得以进行。这种跨越了时空也跨越了载体的空间感染,必然指向的是内心深处的和解与沟通,他们最终都无法脱离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连接,在遗憾和苦涩中追寻温暖与安慰。
三、结语
后现代性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哲学命题,他与电影的溯源大概开始于20 世纪90 年代,凭借其多元性、去中心化、深度削平等特征成为电影导演施加隐喻的重要场域,这些视觉符号的运用以及电影结构的创新都极大地调动了创作者与观者之间的主观能动性,对现代社会的不同切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韦斯·安德森电影中也展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精巧的结构、程式化的风格,现实与虚幻交织、严肃与荒诞共存,尤其通过深层化、重叠化的叙事手法,在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对时空关系的理解。
但由于其碎片化的镜头语言风格,以及跳跃性的叙事节奏,使人们通常把观看视角集中在结构本身,而忽视了其中的情感内核,它们虽包裹着戏谑的表象,但无不隐藏着情感关系中的失落与遗憾。在看似错综复杂、杂乱无章的时空结构中,韦斯·安德森也在电影的创作中治愈着自我的缺失,以独特的电影视角表达着对世界的脉脉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