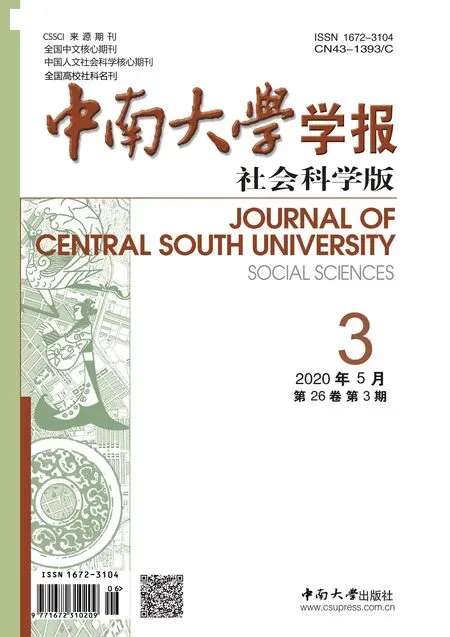“缘何愉悦”
——当代西方恐怖艺术悖论研究
2020-01-06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一、精神分析论
20世纪80年代,面对迅速发展的恐怖小说与恐怖电影,如何解释恐怖艺术的悖论成为西方学界新的研究热点。然而恐怖这一领域一直以来都是西方“美学的边远地带,且为标准的美学著作所忽略”[2](264),即使其出现在部分哲学或美学著作中也是蜻蜓点水,并未形成如悲剧(tragedy)、崇高(sublimity)一样系统的理论架构。面对理论依据的缺乏,作为恐怖哲学先驱的精神分析学派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与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点来建构恐怖哲学体系,并解决恐怖艺术悖论。
弗洛伊德在1919年发表的论文《论神秘和令人恐怖的东西》②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恐怖是压抑的释放。弗洛伊德认为:“令人感到神秘、恐怖的是隐秘的、熟悉的东西,这些东西受到压抑,最后仍然显现出来,所有让人感到神秘恐怖的东西都符合这一条件。”[2](294)该论文的另一突破是将医学上分析神经症患者的“强迫性重复”概念引入恐怖分析领域,弗洛伊德认为凡是让我们联想到这种内心的“强迫性重复”的事物都可以被看作是神秘而恐怖的存在。
虽然弗洛伊德谦虚地表示这并不是第一篇从心理学角度对恐怖进行论述的论文,但是他对于恐怖根源解读的详细程度却超过了以往的任何研究成果,这使得他的这篇论文成为精神分析学派建构恐怖哲学的理论基石。
以弗洛伊德“恐怖即压抑的释放”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恐怖哲学研究者们大都着重于完善和发展“压抑论”,对恐怖艺术为何具有吸引力这一关键问题或回避,或阐释模糊,如朱莉娅·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与罗宾·伍德(Robin Wood)。朱莉娅·克里斯蒂瓦强调对恐怖的本质——“卑贱物”进行研究,其论述恐怖的名作《恐怖的权力:论卑贱》(Powers of Horror:An Essay on Abjection,1980)主要对受到压抑的“不遵守边界、位置和规则的东西”[3](6)(如尸体、粪便等)进行了分析;美国恐怖电影评论家罗宾·伍德在弗洛伊德“压抑论”的基础之上将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基本压抑”与“剩余压抑”概念融入对于恐怖的分析之中,证明恐怖是剩余压抑的回归[4](63−84)。虽然两位精神分析学者的论述十分严谨,但是均忽略了对于恐怖艺术悖论的解读。弗洛伊德研究专家莎拉·考夫曼(Sarah Kofman)、玛丽·特柔克(Maria Torok)与尼古拉斯·兰德(Nicholas Rand)涉及“压抑论”的研究成果如《万事开头难》(It's Only the First Step That Costs,1991)与《弗洛伊德的疑问》(Questions for Freud,1997)也存在这一现象。
尽管也有少数学者尝试依靠“压抑论”对恐怖艺术悖论进行解读,如芭芭拉·克里德(Barbara Creed)就参考朱莉娅·克里斯蒂瓦对于卑贱的定义,认为在恐怖艺术中卑贱物(身体的排泄物)的出现会唤起一种打破规则与禁忌的愉悦感,以及一种仿佛回到幼儿时期无忧无虑状态的轻松感[5];道夫·奇尔曼(Dolf Zillmann)等人提出的“激发转移理论”(Excitation Transfer Theory)认为恐怖艺术中的愉悦来自对于压抑的宣泄[6]。但是总体来看,以“压抑论”为理论基础的学者关于恐怖艺术悖论的阐释仍比较少,论述较为简略,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争议,如芭芭拉·克里德对于愉悦范围的阐释就被部分研究者认为过于狭隘,而道夫·奇尔曼等人的宣泄论则无法解释那些以悲剧收场的恐怖电影吸引观众的原因。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弗洛伊德写作《论神秘和令人恐怖的东西》这篇论文的初衷是扩大其精神分析理论的适用范围,对恐怖涉及的诸多问题如恐怖艺术悖论并没有考虑或有完全清晰的认识,所以他提出的“压抑论”与恐怖艺术悖论中的“愉悦感”之间存在着矛盾,当平日被压抑的创伤与痛苦被释放到意识表层之后,恐怖将成为压制性的主导力量,愉悦将无从谈起。其次,弗洛伊德在文中对“压抑论”的论证并不严谨,弗洛伊德自己也认为此理论存在缺陷,如在范围上不能同时适用于现实恐怖与艺术恐怖,在逻辑上“证明我们假说的几乎每一个例子都能找到反例来加以驳斥”[2](294)。这就导致以“压抑论”为出发点的恐怖哲学研究对于恐怖艺术悖论的解读十分艰难。
少数研究者另辟蹊径,以弗洛伊德对于“强迫性重复”的阐释作为理论根基。伊丽莎白·考伊(Elizabeth Cowie)在其论文《真实的噩梦:创伤、焦虑和恐怖的伦理美学》(“The Lived Nightmare:Trauma,Anxiety,and the Ethical Aesthetics of Horror”,2003)中单独辟出一节“恐怖中的非愉悦与愉悦”(“Unpleasure and Pleasure in Horror”)来讨论恐怖艺术悖论。伊丽莎白·考伊认为在恐怖艺术中,“愉悦不是由非愉悦产生,而是来自对于非愉悦的终结”[7](31),在弗洛伊德宣称的充满压抑的、不断重复痛苦经历的“强迫性重复”之外还存在着一类可以缓解压抑与焦躁的“焦虑的重复”。焦虑一方面是恐惧艺术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能以不断重复恐怖的方式来逐级缓解恐怖自身。然而伊丽莎白·考伊所提出的“焦虑的重复”只具有缓解作用,能否使恐怖艺术的体验者产生愉悦感却令人生疑。
拉康的“凝视”理论也被部分研究者作为理论基础来解释恐怖艺术悖论。拉康从镜像阶段的论述中引申出由主体发出的、作用于客体、作为欲望追求与秩序隐喻相结合的“眼睛”与由客体折返主体目光而来、具有逃离秩序指涉的“凝视”之间具有复杂的辩证关系。凝视无处不在且包含了未满足的欲望的幻象,因此“凝视是一种欲望的投射,是一种于想象中获得欲望满足的过程”[8](157−158)。卡罗尔·克罗弗(Carol Clover)的《男人、女人与链锯:当代恐怖电影中的性别》(Men,Women,and Chainsaws:Gender in the Modern Horror Film,1992)就将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的“单性系统论”(one sex model of sexuality)与拉康对于凝视与欲望关系的分析结合在一起来解读好莱坞恐怖电影对于男性观众的吸引力。
托马斯·拉克尔认为男性与女性的身体差异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具有相同结构的类似物系统,只不过男性的性器官在外部显现,女性的则在内部。据此,拉克尔陈述了两个方面的推论:一是作为高级的、可见的男性集合是作为次级的、不可见的女性集合的映射;二是男性可以有男性的身体,但是拥有女性的心理认同,即“男性的女性认同趋向”。卡罗尔·克罗弗主要借用了托马斯·拉克尔的第二个推论,她认为作为恐怖艺术观众主体的男性的凝视分为两类:一类是男性对剧中女性角色的“凝视”,这是一种从摄像机视角出发具有攻击性的凝视;另一类是男性因自我的女性认同而从女性受害者的视角出发观察自己如何被摧毁的“受虐者凝视”。卡罗尔·克罗弗在分析了大量的好莱坞恐怖电影后认为,电影中的女孩最后普遍通过对怪物进行各种形式的“阉割”而存活,“阉割”行为本身往往又得到男性观众的认同。卡罗尔·克罗弗进而得出结论,恐怖电影的男性受众不仅在本质上是虐待狂,而且是身体中蕴藏女性气质的受虐狂,恐怖电影因迎合了他们的虐待但更主要的是受虐倾向而带来愉悦感。
精神分析论者将对于愉悦成因的探讨严格限制在压抑、重复、欲望等传统领域中,这就导致其对愉悦范围的理解以及针对悖论给出的答案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在当时极度缺乏理论支撑的学术环境之下,精神分析论不仅“填补了理论需要的空白,提供了最初的研究基点”[9](24),还启迪了一大批后来者,开启了西方学界关于恐怖艺术悖论的论辩。
二、好奇论
不满于精神分析论的恐怖艺术悖论解读方式,诺伊尔·卡罗尔(Noël Carroll)将“好奇心的满足”(satisfaction of curiosity)作为观众在恐怖艺术中获得愉悦的原因。
《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对于艺术愉悦、悲剧与求知欲的阐释都直接启发了诺伊尔·卡罗尔,“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所做的解读正是我想要去尝试的”[1](8)。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对于艺术愉悦及悲剧悖论的模糊态度③,一方面,卡罗尔将恐怖艺术的悖论作为他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卡罗尔对于悖论原因的解读是清晰且从一而终的。这也使得卡罗尔的《恐怖哲学,或,心灵悖论》(The Philosophy of Horror:Or,Paradoxes of the Heart,1990)一书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本完整且详细的恐怖艺术悖论解读专著。后来的研究者或继续扩展诺伊尔·卡罗尔理论的适用范围,或针对诺伊尔·卡罗尔理论中的争议之处进行论辩。可以说,诺伊尔·卡罗尔是当代西方恐怖美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理论家。
诺伊尔·卡罗尔对于恐怖艺术悖论的解读主要以叙事型恐怖艺术为样本。在诺伊尔·卡罗尔看来,审美距离的存在是产生恐怖艺术悖论的前提条件,生活中的恐怖会带来真实的威胁,会对我们造成惊吓,而艺术中的恐怖由于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伤害所以可以使观者在安全的范围内享受恐怖。在确定悖论产生的前提之后,诺伊尔·卡罗尔认为,首先,怪物(monster)是叙事型恐怖艺术的标志物,但是这种怪物首先必须是被现今科学证明不存在的超自然生物,这样观者才会产生对怪物的好奇心,然后进入艺术世界并在叙事中寻找答案;其次,怪物还应该是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其《纯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1966)一书中从生物学范畴出发所谈到的“矛盾的”或“不完整的”生物④,具有威胁性(threaten)与不洁净(impure)两个特征,这样才能使观者产生恐怖与恶心的情绪体验。
诺伊尔·卡罗尔所言的好奇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本质上并不存在的生物设定(包括形象、习性、弱点等)的好奇,其二是与这种怪物紧密相关的叙事的好奇。诺伊尔·卡罗尔更强调后者,即叙事情节的重要性。诺伊尔·卡罗尔运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欲望理论,认为好奇(curiosity)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欲望,“所有的叙述可能都包含了对于知识的渴望——想要知道情节中各种突出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1](182)。在叙事型恐怖艺术“怀疑—求证—确认—解决”的侦探式叙事模式的伊始,观者的好奇心被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怪物激发,并通过各种细节、证据被强化,最后在连续的叙事中得到满足。当艺术接受结束时,观者因好奇心被满足而产生一种认知型愉悦,这种愉悦超过了在接受过程中怪物威胁衍生的恐怖感,恐怖艺术的悖论便得以解决。诺伊尔·卡罗尔认为,恐怖艺术的接受者并不渴望厌恶与恐怖,但是二者是恐怖艺术的观众寻求真相、满足好奇心所必然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因此,诺伊尔·卡罗尔又将恐怖艺术悖论称之为“心灵悖论”(paradoxes of the heart)。
诺伊尔·卡罗尔对于恐怖哲学的建构十分完整,对现实恐怖与艺术恐怖的范围、恐怖的本质及恐怖艺术悖论都有所解读,但是他对于叙事型恐怖艺术的界定标准(超自然怪物存在与否)以及好奇心的所指(怪物设定与叙事情节)引起了西方学界的争议。
在与他人的论辩中,诺伊尔·卡罗尔辩称,在没有超自然元素出现的现实题材的恐怖作品中,杀人者也被有意刻画为貌似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怪物,所以其对于恐怖艺术的界定以及恐怖艺术悖论的解读也适用于以人为恐怖源的现实的恐怖作品,但是辛西娅·福瑞兰德(Cynthia Freeland)在其《现实主义者恐怖》(“Realist Horror”,1995)中还是坚持认为,诺伊尔·卡罗尔以情节为重的“古典恐怖哲学”更适合运用在超自然的恐怖艺术中。对于现实的恐怖作品,辛西娅·福瑞兰德以好莱坞“砍杀”电影为例,她表示这类电影情节平淡且具有随机性与重复性,不会激发观者的好奇心,作为怪物的杀人者与血腥场面的描写才是观众观看的动力,“我们被怪物与恐怖的奇观所吸引,精心策划的暴力行为带来一种矛盾的兴奋感”[10](287)。怪物与奇观是辛西娅·福瑞兰德解决恐怖艺术悖论的答案。
辛西娅·福瑞兰德笔下的怪物不同于诺伊尔·卡罗尔的超自然生物,那些无法与周围的人群建立联系的普通人在极端状态下会化身为现实的“怪物”,而残肢遍地与血浆横飞的血腥场面则是辛西娅·福瑞兰德所说的“奇观”。在辛西娅·福瑞兰德的论述中,怪物与奇观拥有共同的特点,即它们确实会出现在现实社会中但普通人很少能遇到。辛西娅·福瑞兰德更强调血腥场面对于观者的吸引,正是对于这种很少能遇到的奇观场面的好奇心得到满足才使得观者产生愉悦感。从本质上来讲,辛西娅·福瑞兰德的解读仍然侧重于观者好奇心的满足,只是好奇指涉的范围由形象与情节转变为来自从未见过的场面的感官刺激,诺伊尔·卡罗尔所强调的情节则成为连接各个奇观的纽带。
辛西娅·福瑞兰德对于恐怖艺术悖论的解读影响广泛,美国匹茨堡大学电影研究领域的专家亚当·洛温斯坦(Adam Lowenstein)便是辛西娅·福瑞兰德的支持者,他在《美国恐怖电影的重视》(“A Re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Horror Film”,2011)中再一次强调了辛西娅·福瑞兰德所说的“奇观”。他认为精细的摄影画面以及巧妙设计的血液飞溅都是一系列引人入胜的精致恐怖奇观,对于充满好奇心的观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11]。
诺伊尔·卡罗尔与辛西娅·福瑞兰德关于恐怖艺术悖论的类型化解读是西方恐怖哲学细化的重要标志,卡罗琳·克斯梅尔(Carolyn Korsmeyer)在《美学:重大问题》(Aesthetics:The Big Questions,1998)中论述恐怖时只选取了这两位学者的文章作为样本,这也充分说明二人的思想在恐怖哲学领域的代表性。
在诺伊尔·卡罗尔与辛西娅·福瑞兰德之后,保罗·纽曼(Paul Newman)虽然没有对恐怖艺术悖论进行哲学层面上的系统解析,但是在其专著《恐怖:起源、发展和演变》(A History of Terror:Fear &Dread Through the Ages,2000)中,保罗·纽曼从生物学角度出发论及了好奇心之于恐怖艺术接受的意义。首先,保罗·纽曼认为,恐怖在化学成分上与好奇心比较接近,“因而许多所谓恐怖的事物对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12](VIII),这种吸引力也是为什么恐怖可以作为娱乐产业的原因。其次,保罗·纽曼暗示了好奇心的另一种指涉可能,即人类曾经惧怕但现在已经战胜的恐怖之物。保罗·纽曼举出狼人、麻风病人等多个经常出现在恐怖艺术中的典型形象试图证明远古时代人类会在好奇心的推动下探索恐怖,而在近代,当人类能确保自身安全时就会在恐怖艺术中继续探索、想象并娱乐化曾经的恐怖之物,以满足人类自身的无穷好奇心,并获得愉悦。
尽管对于好奇心的具体所指存在分歧,但是好奇论已经成为当代西方解读恐怖艺术悖论的主要观点之一。近年来也有研究者开始从人类学、历史学等多个角度出发探讨好奇心的可能指涉。
三、多元路径论
无论是以弗洛伊德与拉康理论作为基础的精神分析学派,还是具体观点存在分歧但是都以好奇心的满足展开论述的诺伊尔·卡罗尔等人,这些研究者都试图找到解释恐怖艺术悖论的“那一个”根本原因。而以斯蒂芬·金(Stephen King)与拉斯·史文德森(Lars Svendsen)为代表的研究者则认为在恐怖艺术中观者获得愉悦的路径是多元的,无法用某种单一的原因加以概括。
作为恐怖艺术的杰出生产者,斯蒂芬·金将自己的恐怖小说创作理论整理成《骷髅之舞》(Danse Macabre,1981)出版,书中他认为读者从恐怖小说中获得愉悦的原因是多重的。
首先,愉悦来自成就感,即读者战胜书中所描写的恐惧,证明自己比他人更加勇敢。斯蒂芬·金暗示,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拿起恐怖小说的那一刻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勇敢,随着阅读逐渐深入,这种战胜恐惧的成就感会逐渐加强,并在合上书本时达到高峰⑤。
其次,愉悦来自恐怖艺术参与者对于平庸生活的暂时忘却。一方面,这是一个优秀故事所带来的阅读沉浸感,读者沉湎于恐怖小说以逃避无聊的琐事。斯蒂芬·金在多年之后的自传《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On Writing:A Memoir of the Craft,2000)中也强调了“一个好故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读者会在小说中重拾儿童时期的美好。如斯蒂芬·金所 言:“恐怖小说家的工作就是让你在小说中再次成为孩子。”[13](455)斯蒂芬·金在其恐怖小说中常会塑造少年英雄形象,他认为这种少年英雄形象会使读者在经历恐怖时能够摆脱成人世界的复杂,重新体验儿童时期的纯真与善良。
最后,愉悦来自信心的收获。斯蒂芬·金认为恐怖小说之中的混乱世界与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强烈的对比中,读者可以重拾对现实世界的信心,减少对于社会现状的不满,这也是恐怖小说“吸引保守的穿着三件套的共和党人的原因”[13](55)。斯蒂芬·金基于恐怖小说的文化激励可能,认为人们会因在小说中收获对抗现实危机的经验与方法而重拾信心,并获得愉悦。
出现这种多元的恐怖艺术悖论解读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美苏冷战之下紧张的政治环境。斯蒂芬·金在《骷髅之舞》中分析道,长期的核威胁与肯尼迪总统遇刺给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孩子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影院中的孩子们沉默了,死一样的寂静,我们呆坐在那里”[13](21),“我们被告知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但是也被告知我们应该在防空洞里准备什么、呆多久。……我们拥有的财富比历史上世界任何国家都要多,然而在我们的牛奶中却含有因核实验产生的放射性元素锶90”[13](23)。这种切实的死亡威胁使普通读者对恐怖小说的需求量激增,他们一方面沉湎于强烈的恐怖情境中以忘却现实,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小说中寻找对抗现实恐惧的经验。
在冷战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美国恐怖作家们(如彼得·斯特劳布等人)持有与斯蒂芬·金相似的观点。恐怖小说家们因此将现实恐怖因素扩大,以往并未出现在恐怖小说中的现实恐怖事件成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恐怖小说的新素材。
以斯蒂芬·金为代表的作家们对于恐怖艺术悖论的解读更多是依靠写作经验以及经历过现实威胁的人的切身感受,而哲学家拉斯·史文德森则从理论的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答案。拉斯·史文德森承认,从生理角度来讲,恐怖总是与好奇联系在一起的,这与保罗·纽曼的观点较为接近。但是拉斯·史文德森 并没有局限于此,他认为恐怖艺术吸引人的原因另有其他。在考察亚里士多德悲剧论中的恐惧与净化、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论崇高中的敬畏与兴趣、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理性批判中的恐怖与快感、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美学批评中的暴力与魅力之间的关系之后,拉斯·史文德森引用了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名言“我们……被艺术唤醒了沉睡的情绪,……唯有艺术,才能成全我们的圆满,才能使我们暂时忘却丑恶的现实”[14](78)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现代电影的论断“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庸、呆板、机械”来说明恐怖艺术悖论的答案来自多个方面。首先,恐怖艺术会使参与者直面恐惧并在艺术参与结束时产生战胜恐惧的成就感;其次,恐怖艺术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之下使参与者经历在现实生活中不想体验的危险,使其收获丰富的情感;最后,观者也会在阅读过程中因强烈的情节冲击与情感体验暂时逃离平庸的生活,并在阅读完之后因情境的巨大反差而重新获得生活的激情与信心。“恐惧是有力的当头棒,将我们从迟钝麻木中唤醒。”[14](93)
由于意识到早期精神分析理论对于恐怖艺术悖论解读的局限,对恐怖艺术悖论进行多元解读的研究者还包括一些精神分析领域的学者,如美国布莱顿大学教授吉娜·威斯克(Gina Wisker)。她在以弗洛伊德的“压抑论”为理论基础的专著《恐怖小说》(Horror Fiction:An Introduction,2005)中也特别指出,我们喜欢恐怖艺术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艺术中的恐怖与现实中的安宁强烈对比之下形成的对于现实的满足感,又有怪物最后被驱逐而产生的舒适感,还有恐怖艺术本身的叙事情节带给我们的乐趣[15](5,25−38)。
四、结语
除了恐怖艺术生产者与恐怖哲学研究者之外,由于恐怖艺术悖论还涉及读者的审美接受心理,所以心理学家也参与到恐怖艺术悖论的讨论之中。其中格伦·沃尔特斯(Glenn Walters)的解读最为详细。格伦·沃尔特斯在其学术论文《理解恐怖影片的吸引力》(“Understanding the Popular Appeal of Horror Cinema”,2004)中确定了恐怖电影引起观众愉悦的三个原因:首先是电影的“张力”(tension),这包括电影的情节以及导演在电影中制造的悬疑、神秘、血腥等元素,这是一种叙事上的吸引;其次是“相关性”(relevance),恐怖电影必须包含与观众切身相关的元素,如关于死亡的恐惧、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或表现与当地文化紧密相连的恐怖之物,这可以使观众感同身受,尽量消除文化上的隔阂;最后是“非现实性”(unrealism),尽管恐怖艺术近些年越来越模仿现实,但是通过摄像机的视角、配乐、黑色幽默的桥段,观众都能意识到他们正在观看的是虚假的形象与生活,恐怖电影中的恐怖与恶心等元素对人心态的负面影响被降到了最低。这三个原因共同作用使得观众可以在恐怖电影中获得愉悦。但是,正如诺丁汉大学教授马克·格里菲斯(Mark Griffiths)在他的评论文章《我们为什么喜欢观看恐怖电影》(“Why Do We Like Watching Scary Films”,2015)中所谈到的那样,“第三点(非现实性)与第二点(相关性)之间存在着些许矛盾”[16],在格伦·沃尔特斯的解读中,二者都是对于审美距离的强调,但是“相关性”强调的是距离的缩短,而“非现实性”强调距离的保持,彼此的释义中包含互斥因素,这也导致格伦·沃尔特斯的观点存在较大的争议。
目前西方学界关于恐怖艺术悖论的解读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特点,精神分析论、好奇论与多元路径论之间的争辩未曾间断。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对样本类型多有着严格的要求,或是某一类型的恐怖小说,或是某一阶段的恐怖电影,这种样本细化从侧面说明西方关于恐怖艺术悖论的研究正在逐渐深化与细致。但是,如果恐怖艺术悖论是一种在不同类型的恐怖艺术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在如此多的基于“个性”的解读之上是否存在某个具有普适性的“共性”答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随着以恐怖小说与恐怖电影为代表的叙事型恐怖艺术逐渐被评论界重视,关于恐怖艺术悖论的争论将会更加激烈。
随着我国学者对于恐怖艺术悖论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对当代西方学者解读恐怖艺术悖论的思路进行梳理,一方面可以揭示恐怖艺术悖论这一涉及多个研究领域的问题的复杂性与解决这一难题潜在的多维角度,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既可以依托某一现有结论来完善和深化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另辟蹊径,以类型化恐怖艺术作品作为研究样本,从与恐怖艺术悖论相关的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思路。
注释:
① 以英语为母语的当代西方学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恐怖艺术悖论的成果中对于“恐怖”采用了不同的表达词汇,主要有“fear”“terror”与“horror”,虽然三个单词在释义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但当时的研究者使用这些词汇时指涉的其实是同一个释义范围,即强调它们广义上都具有令人惊骇的“恐怖”之意。而且,尽管用词不尽相同,他们在书中所探讨的问题却是基本一致的。
② 弗洛伊德的这篇论文德文名为“Das Unheimliche”,英文版多译为“The Uncanny”,二者指涉稍有不同,前者强调“令人害怕”,后者在“令人害怕”的基础上多了“神秘”的意义。由于国内的译本多基于德文版与英文版,所以就有了多个译法,如《论恐惧》《论令人害怕的东西》《论神秘与令人恐惧的东西》等。本文采用的是常宏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的《论文学与艺术》(Writings on Art and Literature)中的译本。
③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的第一章与第四章中认为模仿与求知是人类的本能,不同的艺术采用不同的媒介、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方式对生活进行模仿,人类可以从模仿的成果以及观看艺术产品的过程中学到知识而获得快感。但是,在随后单独论述悲剧时,亚里士多德又暗示观看悲剧的愉悦来自所有激情耗尽之后的平静,并且在《修辞学》(Rhetoric)中他又给出了更多关于艺术愉悦与悲剧悖论的解释。因此,可以认为,关于艺术愉悦与悲剧悖论的原因,亚里士多德的答案是模 糊的。
④ 玛丽·道格拉斯在其经典之作《纯净与危险》中认为文化类属越界的后果就是“不洁”,而不洁之物常常被排斥,如她对《利未记》(Leviticus)中“海底的爬行生物”(龙虾)与“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作为犹太教不洁之物的解读。这里诺伊尔·卡罗尔借鉴了玛丽·道格拉斯对于跨界属物种在文化上受排斥的结论,引出他对于恐怖艺术中“怪物”的跨界属特征影响观众观看感受的推断。
⑤ 不止是《骷髅之舞》,斯蒂芬·金对于恐怖小说带给读者战胜恐惧的成就感的阐释还散见于媒体采访稿与他多部小说的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