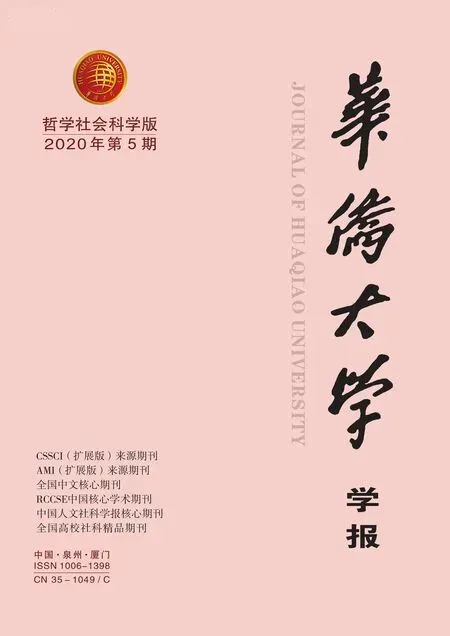艺术的“政治”生产与儒家审美理想
——《乐记》“审乐以知政”思想探析
2020-01-06蒋继华
○蒋继华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对音乐的起源、本质、功用等方面的大量论述,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基础。这其中,通过音乐彰显中国古代礼仪文化的重要性和丰富性,凸显音乐的意识形态蕴涵,成为贯穿整部作品的主线。实际上,《乐记》所论及的音乐不止于钟鼓之喧,而是超越了单纯的“音”,与“政”潜在相通,承载着独特的道德政治功能。“政治与美学本来就有相同的指向。在政治的概念中,就隐含着美学的概念;在美学的概念中,也隐藏着政治的概念。因此,美学不仅可以解开政治的奥秘,政治亦可解开美学的诸多奥秘……”(1)骆冬青:《政治美学的意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37—143页。政治与美学的联姻使得艺术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在这方面,《乐记》提出“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2)(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82页。,将政治视角作为审视音乐的重要视域,以音乐形式来表征政治伦理观念。无论是乐的生成、形制,还是乐的功能、风格,都体现向伦理政治和道德领域的迁移,即乐以政治的、伦理的方式“生产”出来,由此建构起从美学到政治的艺术生产模式,实现音乐与社会、政治的耦合,显现艺术的政治运作规律。
一 乐的生成:“乐由中出”和“乐由天作”
作为先民们生活劳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乐教的发生和发展一直秉持着有用原则,突出音乐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战国时期史官所写《世本》曾记载伏羲和神农作琴瑟等乐教事迹,反映了音乐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功用。自然,探究音乐的起源和生成,也离不开社会因素,即到社会生活中寻求音乐如何成为反映人类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这一点在《乐记》中体现尤为明显。
在论述音乐产生的本源时,《乐记》强调心、物、乐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乐由中出”和“乐由天作”的统一,从心物同构中寻求音乐之为音乐的因素。“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3)(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76页。音乐从哪儿来?《乐记》给出了明确的回答:音的产生,源于人的内心,而人们内心的活动,又归于外物的触发,即人心受到外物的影响而激动起来,最终通过声音反映出来。各种声按照条理次序进行组合,产生音,将音组合起来进行演奏和歌唱,并配上一定的舞蹈,形成乐。所以,乐源于音,音源于物对人心的触发。由此,乐生成的逻辑图式是:物—心—音—乐。
显然,乐的产生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与“礼自外作”相比,乐是从人的内心发出,即“乐由中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4)(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84页。人生下来是好静的,内心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在这里,“心”是基础和关键,心与物的异质同构获得审美愉悦,奠定了乐的产生。二是“乐由天作”。《乐记》秉承了儒家天人和谐的观念,以天地为思维两极,从礼乐入手,揭示礼乐相生与天地人之间的统一关系,将影响音乐产生的外物具体归结为“天”,即“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5)(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93页。在《乐记》看来,弄清楚礼乐与天地的关系,才能制礼作乐。由于物以群分,天地万物各自的体性不尽相同,与礼体现万物的地不同,乐显示创始万物的天。圣人正是依此制乐,顺应天意,调和人们的性情,实现天下大治。“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6)(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92页。如此,创造人和万物的天被人化了。“人可以以其情感、思想、气势与宇宙万物相呼应,人的身心作为的一切规律和形式(包括艺术的一切规律和形式),也正是自然界的宇宙普遍规律和形式的呼应……”(7)李泽厚:《美学三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82页。总之,《乐记》既肯定了心是物、音和乐得以存在的基础,指出音乐是人的思想情感的产物,又追溯了外物对音乐的影响,明确了音乐产生的“物感说”,体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在“物—心—音—乐”的关系中,《乐记》构建了心物同构的逻辑图式。《乐记》为何重视音乐产生过程中物对人心的触发?这主要涉及到治心与音乐教化以及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在《乐记》看来,乐的本源在于人心对于外界事物的感受,即外界怎样的感动人心,人的内心也就表现出相应的情感变化,如“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8)(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76—977页。。悲哀、快乐、喜悦、愤怒、崇敬等情感波动并非出自人的天性,而是人受到客观事物的激发产生的相应结果,所以统一民心而实现天下大治,必须调和能够影响人心的外界事物。对此,《乐记》提出“乐以治心”,其效果是“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9)(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029页。,即通过详审音乐,就能达到规范人的情感,提高人的内心修养,使人趋善守礼的目的,由此体现音乐的德性意义。治心与音乐教化无疑具有统一性。
在这个意义上,音乐虽是反映人类情感的艺术,但以独特功能感化人心,纯洁性情,产生潜移默化的道德力量,潜在地通向了礼,和礼治天下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所谓“乐者,通伦理者也”“知乐则几于礼也”(10)(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82页。,都强调懂得乐就接近于知晓礼仪。而如果对各种乐音不施以正确合理的引导,人心就会变恶,各种作乱欺诈、邪恶放纵、胡作非为就会出现,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为此,《乐记》提出需要采取一定的举措加以遏制,此即制乐制度。由于乐不同于政令、刑罚,其制作是一种政治事件,因此需要圣人或先王来完成:“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11)(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95页。先王制乐并赏赐有德的诸侯,固然与彰显君主伟业,展现君主道德光辉有关,但更与诸侯治下民众的安乐与否紧密关联,这实际上间接反映了诸侯的德行传播与治理能力。显然,乐的创制先天带有功利目的。总之,道德教化、社会伦理贯穿着乐的全部,凸显其丰富的政治内涵。在表现音乐的政治美学思想、吻合着时代政治需要方面,《乐记》的礼乐相济体现了儒家美学的本质特征,由此形成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
二 乐的形制:“异文合爱”
苏珊·朗格认为音乐是一种借助节奏、韵律传达人类情感的符号,体现生命结构的特征:“音乐揭示的是一种由声音创造出来的虚幻时间,它本质上是一种直接作用于听觉的运动形式。这个虚幻的时间并不是由时钟标示的时间,而是由生命活动本身标示的时间,这个时间便是音乐的首要或基本幻象;在这个幻象中,乐曲在行进,和谐在生成,节奏在延续,而这一切活动都是以一个有机的生命结构所应具有的逻辑式样进行的。”(12)[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9页。在朗格看来,音乐和人的生命活动、生命结构之间存在某种同构性,注重包括节奏、动态、韵律等在内的音乐结构形式的创造,对揭示音乐的本质和功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乐记》从关注乐的构造、音律、风格、声调等形制方面的问题入手,突出音乐作为人类情感形式的创造特性,提出了乐的“异文合爱”观,即通过创制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文采、节奏、声律等音乐结构形式,使人们互相亲近,和谐相处。由此,乐有着直接的现实功利目的,呈现政治与审美的互渗。
首先,乐的节奏韵律及声调等各得其宜,充满特定的政治隐喻。乐是如何兴起的?《乐记》从天地运行的规律出发,提出“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13)(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92页。。所谓“合同”,这里指万物相互聚合,形成总体上的平衡状态。具体来说,天地万物流动不息,互相联系又互相影响,圣人或先王循神而法天作乐,“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14)(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000页。先王依据五常德行、人的性情和音律度数,使乐的清浊高下各得其宜,安于其位,不互相妨害,所以乐器的色彩虽然五彩缤纷,乐舞的节奏韵律虽富于变化,但却井然有序,配合有度,体现天地的本性,也使得一切社会伦理关系都融合在乐中,规避天下欺诈虚伪之心和淫泆作乱之事。在这方面,《乐记》反复强调,钟鼓干戚等乐器舞具文质相杂,俯仰屈伸等舞蹈姿态变化多端,利于人们融洽共处,具备平和的德性:“钟、鼓、管、磬,羽、龠、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15)(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89页。“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16)(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004页。由此,乐的创制既体现了顺应天意的特点,又彰显先王之德的意义,标志着乐向伦理道德领域迁移,呈现伦理道德旨趣。这是其一。其二,乐的声调及风格以独特的方式表征社会政治。在《乐记》看来,乐的五声并非普通的乐音,而是反映着社会结构准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17)(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78—980页。同时,不同风格的乐音对人的内心情感和社会风俗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18)(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98页。。在古人的观念中,音乐与人的心性直接相关,乐音混乱,自然对人的情感心理产生某种影响,也反映出国家政治安危。这就需要先王制乐时,遵循“异文合爱”的音乐观,以奏出调和之音,使乐具备如礼一样的道德伦理职能。姑不论五音与政治的关系是否被泛化,但强调不同的声律形式和政治具有相通性,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声音就反映什么样的政治状况,即“审乐以知政”,却揭示了乐的社会学内涵。“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19)(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82—983页。先王创制音乐的根本不在于其满足口腹耳目的享受,而是能发出“德音”,教化百姓,使其学会做人。乐的政治隐喻性质凸显无疑。
其次,《乐记》强调乐的表演要凸显文采节奏,体现先王仁义之道。《乐记》认为乐教有君子和小人之别,如君子“得其道”,小人“得其欲”,即相对于君子从乐教中得到了仁义,小人则从乐教中满足了私欲。由于声音是乐的现象,文采节奏是声音的组织,所以君子用乐来表现内心活动时势必要协调文采节奏,这样放荡之心与邪恶之念不至于影响人心,人与人之间才能互相亲近,上下的关系才能和睦。“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20)(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015页。“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21)(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004页。古代圣王之所以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主要在于善于发挥乐的文采组织功能,这反映了乐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音乐要“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22)(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033页。。这种理想的乐曲以一个基调为调和之音,再配上各种乐器,其节奏合成为乐章,就能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充分体现乐的“异文合爱”性。此外,在乐舞表演中,舞者的步伐、情势、姿态以及刚强与柔和等和谐相宜,有助于显示君主的德尊地位。例如《大武》之舞:“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23)(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006—1007页。这段文字再现了《大武》舞者的步伐、表情和状态,从开始的击鼓、踏三次步到最后结束,突出表现武王施行仁义的壮举。又如在魏文侯和子夏关于古乐和新乐的对话中,子夏认为古乐演奏时,讲究舞蹈、唱歌、乐器的协和节奏:“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24)(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013页。古乐的演奏整齐划一,平和适中,起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用。由此,乐以独具特色的文采节奏参与社会现实生活,再现君子之德,而民众通过乐教明辨是非,感受乐带来的快感。
音乐形制中的“异文合爱”,充分体现了音乐创制作为社会治理之道,追求节奏和谐、井然有序、唱和呼应的审美形式,避免陷入散漫紊乱、放纵无拘、流荡邪僻的杂音之中,即通过不同的乐音形成和谐的曲调,包括刚强与柔和、曲折与平直等,实现艺术活动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当然,这是一种美善相乐、政治与审美相依的和谐状态,对提升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规范人际情感,调和人际交往,以利天下大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乐的功能:“乐以和其声”
“和”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审美形态。“和”原指远古一种和声的乐器,其观念可远溯至殷商,且从乐中显。周初,随着人文精神的跃动,“和”的意涵亦产生了变化,由宗教上的意义转为政治伦理性的概念(25)吴璇:《先秦音乐美学中的“和”范畴考论》,《学术交流》2007年第9期,第17—21页。。《国语·郑语》中史伯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26)陈桐生译注:《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73页。史伯强调创造事物的原则是“和”,“以他平他谓之和”意指将许多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使它们获得一种平衡。万物的丰盛,乃至社会存在的法则,都归于平衡、协和,已隐含着后来儒家所讲的中和思想。《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对此注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2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页。心里有喜怒哀乐的感情但不表现出来,这就是“中”;纵然表现出来了,能够有所节制和适度,这就是“和”。显然,“中和”观念推崇的是适度、适宜、不偏不倚。
《乐记》极为重视音乐的“和”思想,强调乐的作用就是“和”,提出“乐以和其声”等重要观点,阐明乐在调和人们的性情、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在《乐记》看来,相对于“礼”表现天地间的秩序,“乐”是根据天的道理而作,表现人与天地自然的协调(如“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以及万物化育生长、各得其所的本质。为深入说明这一点,《乐记》结合天地运行的规律来分析统治者制作乐的缘由:“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也。”(28)(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96—997页。对于人而言,乐教就好比四季寒暑交替,如缺失和过度就会引起社会动荡,损害世道人心,此所谓“教不时则伤世”。先王正是从乐的中和、适宜与人的行为的相辅相成中,创制出优美乐章。对此,《乐记》反复申明乐音之“和”与社会道德风俗以及国家政治的相通性:“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29)(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87页。“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30)(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98页。“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31)(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005页。由于乐是从人的内心发出,因此深入民心就会调和人们的性情,消除彼此怨恨,移风易俗,使普天之下得到安宁,即所谓“乐者,乐也”。这也正是圣人喜爱音乐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音乐并非某种单纯悦耳的声音,而是能引起人内心联想并应合的东西:“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32)(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020页。也就是说,对君子而言,欣赏音乐不只是听到铿锵之声,而是“有所合之”,即能从中生发联想,听出“弦外之音”,使音乐旋律与主体内心情感、道德人格相应合,发挥礼乐教化功能。这才是君子应有的要求。由此,《乐记》传承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和”精神,超越了狭隘的个人经验,将音乐的感知欣赏与生生不息的天地宇宙、现实人生相统一,进而升华为社会认知的理想图式,彰显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和谐品格,反映了东方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念,体现音乐强烈的现实关怀之功能。
阮籍在《乐论》中称“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33)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8页。。“和”表征着乐的和谐、适度、有序,不逾礼失德。以此推之,那些恣意心性、超越“和”乐常态的激昂、无度的乐调违背礼,自然就不为儒教所认同。对此,《乐记》指出“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34)(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003页。,与“和”乐对应的“奸声”“淫乐”放纵人的欲望,不合礼教,不利于移风易俗和天下皆宁的局面形成。《乐记》曾载:魏文侯问子夏,为何聚精会神听古乐就打瞌睡,而听郑国和卫国的新乐就不知道疲倦,子夏回答说古乐中和正大,君子通过其表现文治武功,达到修养身心、和睦家庭、安定社会的结果,新乐则违背尊卑有序原则,充满着放纵邪恶的声音,人受了迷惑所以就离不开它。关于郑音,指春秋时郑国的民间音乐。由于郑音有别于传统的庙堂之音,又称新乐,它从开始流行就一直受到非议。如《乐记》认为郑声可以亡国,对其颇有微词:“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35)(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81页。孔子曾提出,治理国家在音乐方面要用舜和周武王时的《韶》《舞》之乐,排斥郑国靡曼淫秽的音乐。在孔子看来,这种音乐不符合贵族阶级的道德要求。子夏亦认为“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36)(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016页。,反映了极力维护古乐、排斥新乐的思想。而为进一步防止新乐对古乐的侵袭,《乐记》提出“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37)(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005—1006页。,体现了以乐来和民心、利治理的价值取向,实现乐与德的互渗和统一。
四 《乐记》“审乐以知政”与儒家审美理想
人类最初的审美活动,总是离不开政治,或者说,在通达审美或艺术的道路上,终究绕不过政治。无论是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对诗和诗人的一番检视,还是中国古代孔子对《诗经》“思无邪”的概括,都强调政治与美学的共有指向——一种政治美学的内在发展逻辑。将政治与美学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而形成“政治美学”并用来指称人类艺术活动时,“政治美学”并不是政治与美学的机械相加,而是“在对政治的美学审视中,寻求政治表达的艺术手段与政治的美学目的”(38)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21—25页。,也就是说,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凸显审美的精神和审美的境界。在儒家乐教看来,音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人们所处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反映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的盛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39)(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78页。无论是“政和”“政乖”还是“民困”,都凸显乐不是单纯的声音,而是“德音”“仁声”。可以说,乐的生成或来源通向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存在着同构关系,即在抒发情志的同时,体现审美化的政治教化,此即“审乐以知政”之所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音乐与道德政治具有内在的相通性,与国家治理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其创制过程被赋予了政治的、道德的、伦理的内涵和功能。
这一切体现了儒家的审美理想:通过音乐的社会功能,在乐与德、乐与政的关系上追求一种礼乐兼济、美善统一的人格理想境界,使社会伦理秩序转化为个体内在的自觉要求。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一直追求社会理想与个体人格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发挥审美艺术的认识功能。孔子不仅强调诗教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的“兴观群怨”说,还强调乐教对个体的社会价值,视其为通达道德的必经之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40)(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4—105页。,即突出人格修养的最后完成路径是音乐。可以说,音乐最能表达个体心性的自由完满,对人的精神产生激励和净化的作用,《乐记》的“乐以治心”观即是以此为目标,实现教化社会民众和无暴力的王道政治的效果。对此,有学者指出:“政治的产生就在于心灵的混乱,其目标则在于‘治心’。而美学则正是‘治心’之学。”(41)骆冬青:《政治美学的意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37—143页。当然,作为“治心”的音乐,其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生产运作需要转化为个体的自觉要求,才能实现个体内在的情感陶冶,并进入自由的人生境界,发挥艺术的德性功能。孔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4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9页。,就是强调知识学习过程中乐在其中才能学有所成,儒家乐教无疑也要遵循这样的逻辑。同时,儒家也关注艺术活动中的“度”问题。《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4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8页。《韶》乐之所以受到孔子的推崇,就在于有美的形式,蕴含仁德的内容;《武》乐虽然形式完美,但道德内容不完备。荀子提出“美善相乐”观点,强调通过文艺的审美感染性引起道德行为,实施仁政教化。作为儒家最高的音乐美学理想,无论是“尽美尽善”还是“美善相乐”,都强调音乐欣赏活动与“善”的内在关系,指向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纯正性和完美性。而一旦美善关系起了变化,或者说美逾善僭礼,就不符合儒家的伦理思想标准。《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4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1页。在这里,孔子批评季氏僭用天子礼乐,表现孔子对与道德伦理密切相关的音乐要求非常严格。因为按照古代祭祀乐舞,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即八列六十四人进行乐舞表演,季氏以八佾之舞反映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事实。因此,音乐承载的不仅仅是审美功能,还有使人趋善守礼的道德功能,而且有时候这种道德功能甚至成为判定艺术价值的关键。例如《乐记》中《清庙》的制作:“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45)(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82页。《清庙》上边是用熟丝制的琴弦,下边是稀疏的孔,一个人领头唱,三个人应和,奏出的声音并不是多么悦耳。但在《乐记》看来,作为古帝王祭祀祖先的乐章,《清庙》的制作不在于多么悦耳动听,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享受,而是指向人的心灵深处,教育人如何做人,避免欺诈虚伪作乱现象的出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从音乐中不仅得到快乐、轻松的感受,而且应该感觉到音乐对其性情和灵魂的陶冶作用,“灵魂在倾听之际往往是激情起伏”(46)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0页。。黑格尔也指出音乐在浸润灵魂、超越现实羁绊中的重要功用: “如果我们一般可以把美的领域中的活动看作一种灵魂的解放,而摆脱一切压抑和限制的过程,因为艺术通过供观照的形象可以缓和最酷烈的悲剧命运,使它成为欣赏的对象,那么,把这种自由推向最高峰的就是音乐了。”(47)[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7页。其实,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论述与中国古代孔子提出的“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肯定音乐在塑造完美人格、陶冶人的情操方面具有的社会价值。“审美在形式上从属于道德法则,但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审美却似乎优于道德法则:道德法则不可能在个体之间创立积极的情感纽带。”(48)[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音乐作为审美形式,在涵咏主体德性的同时,承载着主体审美化生存的现实关怀,并通过构筑自我与他者存在的“积极的情感纽带”,建构自由完满的人性,使人摆脱世俗物欲的羁绊,成为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润滑剂和和谐社会政治图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先王为何爱好制作乐,并通过乐来实现社会的有序治理,礼乐文化为何成为儒家长期坚守的审美理想和精神。由此,《乐记》虽然是关乎音乐艺术的著述,但是一个礼化、道德化或者政治化的乐教体系,无论是乐的生成、形制还是乐的功能,其整个生产过程贯穿着“审乐以知政”理念,凸显了儒家政治美学的鲜明特征。《乐记》特有的意识形态生产指向深刻折射儒家文化的特质,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