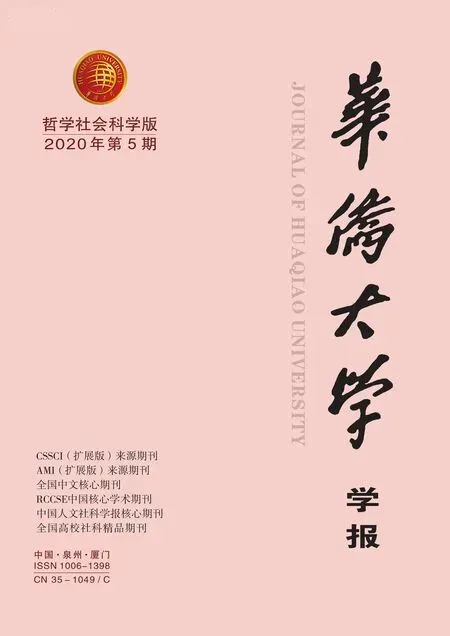王琦宗唐诗学倾向及其原因
2020-01-06刘美燕
○刘美燕
诗文注释是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途径,也是古代诗文研究的主要形式,它对注释者所处时代的诗学观念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今学界越来越强调诗学史研究要将诗文注释家纳入视野。王琦是康雍乾时期浙地重要的诗文注释家,他的《李太白诗集注》三十六卷、《李长吉歌诗汇解》五卷,是李白、李贺集最有影响力的注本之一。对他的诗学思想进行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清代浙地诗坛诗学状貌的认识。
王琦于雍正六年(1728)前后开始进行二李诗文的注释工作(1)王琦撰有《清贻堂剩稿》,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均有藏本(见拙作《王琦生平事迹小考》,《光明日报·史学》2014年4月23日)。《清贻堂剩稿》首一《琢崖公传》曰:“公既协注右丞集,复注李长吉歌诗,又辑《医林指月》若干卷,公故兼精岐黄也。公慨李供奉文集之注之未尽善也,于是梦寐太白于千载之上,搜遐剔隐以发难显之情。越三十年始镂板问世。其友人齐氏息园、杭氏堇浦、赵氏意林为之序。”观其意思,王琦一方面协助赵殿成注王右丞集,另一方面亦开始注二李诗,且其称《李太白诗集注》过三十年乃刊刻问世的。《李太白诗集注》杭士骏、齐召南为其写序时间均题为乾隆己卯(公元1759),王琦漫述题为乾隆23年(公元1758),此大约为其书版刻时间,往前推三十年则大约为1728年前后。,此时正是诗坛上主唐的格调派与法宋的浙派(2)清代之“浙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浙派”指由浙省人组成的以宗宋为基本特征的地域诗歌流派。狭义的“浙派”指的是生活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以厉鹗为首,以宋诗为基本诗学宗尚的杭州诗人群体。参见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本章所言“浙派”均为狭义的“浙派”。迅速崛起之际。王琦生活的杭州是浙派活动的中心,当时与王琦有交游的杭世骏、赵信、赵昱等都是浙派重要成员。我们一般认为这个时期的杭州乃至整个浙江诗坛都被宋风所笼罩,如蒋寅在《黄宗羲与浙派诗学的史学倾向》中就说:“而到康熙中……浙江诗家却仍坚守宋诗立场。”(3)蒋寅:《黄宗羲与浙派诗学的史学倾向》,《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第220—226页。但王琦却在《李太白诗集注》《李长吉歌诗汇解》中表现出明显的偏好唐风的倾向,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
一 王琦偏好唐风的倾向
(一)以两个唐人集子作为注释的对象
前人诗文集众多,他为何独独选择了李白、李贺两个唐代的集子?虽然他没有明确解释原因,但这其中的倾向性已经很明显了。他除了标榜盛唐的李白,对中唐的李贺也颇多赞誉之词。他对李贺诗的肯定与杭州诗坛前辈西泠十子对晚唐诗人的肯定一样,都是将其纳入儒家诗学体系中,将其看成是对风骚传统的继承。他在《李长吉歌诗汇解》序(4)(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页。中说:“长吉下笔,务为劲拔,不屑作经人道过语。然其源实出自楚骚,步趋于汉魏古乐府。朱子论诗,谓长吉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夫太白之诗,世以为飘逸。长吉之诗,世以为奇险。是以宋人有仙才鬼才之目。而朱子顾谓其与太白相去不过些子间,盖会意于比兴风雅之微,而不赏其雕章刻句之迹,所谓得其精而遗其麄者耶。人能体朱子之说,以探求长吉诗中之微意,而以解楚辞汉魏古乐府之解以解之,其于六义之旨庶几有合。”他认为朱熹评价李贺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得其精而遗其麄”的原因就在于他并不像大多数人一样只注意到李贺诗歌的雕章刻句、险怪之处,而能够注意到他的“比兴风雅之微”,他认为李贺的诗歌是合于“六义之旨”的。这和毛先舒对李贺诗的评价“设色秾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5)毛先舒:《诗辩坻》,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9页。极为相似。
(二)在注本中表现出以“味”为中心的诗美理想,而其对“诗味”的理解颇近唐诗审美趣味。
王琦的诗文注释以作者原意为旨归,为求客观,他的《李太白全集》《李长吉歌诗汇解》鲜少个人主观化的论断、赏析,在不多的这些条目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是“味”。如《李太白全集》卷五《塞上曲》:“洪迈选《万首唐人绝句》,分此诗为三章,顿觉无味,不若合作一首之善。”(6)(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93页。卷五《清平调三首》:“不知改‘云’作‘叶’便同嚼蜡,索然无味矣。”(7)(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304页。《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南园十三首》其四:“读者不会其故,只以用史汉故事视之,意味索然,有如嚼蜡。”(8)(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61页。卷三《谢秀才有妾縞练,改从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后生感忆。座人制诗嘲诮。贺复继四首》其二:“若订做碧玉破瓜后,不但对句直至无味,亦与前四句不相联署。”(9)(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102页。卷四《江南弄》:“酒中,饮酒方半也。倒卧者,酒酣倒地而卧也。南山绿者,悠然见南山之色也。徐文长以为山影入杯亭者,意以巧而反觉味短。”(10)(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143页。卷四《江楼曲》:“旧注谓滴将尽,盖以下五字相联作一解亦通。然意味殊觉短浅。”(11)(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159页。“味”成了他诗美理想的一个核心,解诗、品诗都力避无味、味短、味浅。
“味”是中国古典诗学中至关重要的审美鉴赏范畴。它从对食物的感官体验中脱离出来,广泛运用于诗文领域。诗味论从魏晋南北朝发端以迄元明清,论述者代有其人,然而每一个时代人对“诗味”的理解又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陆机、刘勰、钟嵘之“味”主要强调辞采之美。陆机批评那些缺乏辞采的“文”曰:“阙大羹之遗味”。钟嵘的“滋味”说则偏重于“风力”与“丹采”的结合。
唐代司空图、南宋反江西好唐风的张戒、严羽等人对诗味的理解强调的是具有唐诗审美特点的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包蕴无穷等元素。比如司空图提出的“韵外之志”“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美学概念,他在《与极浦书》中描绘的“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12)(唐)司空图:《与极浦书》,郭绍虞集注《诗品集解、续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2页。诗美境界,都是如此。
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也抓住了诗味含蓄不尽的特点,但他们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平淡之味。欧阳修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中评梅尧臣的诗说:“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13)(宋)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欧阳修诗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苏轼《评韩柳诗》中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14)(宋)苏轼著,孔凡礼典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09—2110页。
至于黄庭坚,则将诗味之厚薄与学问之浅深联系起来。黄庭坚《大雅堂记》曰:“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15)(宋)黄庭坚:《大雅堂记》,《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一六,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7页在他看来,如果不能深入地熟读《诗经》《楚辞》等经典,就不能领会到杜诗的意味,他显然是将诗之味寄于深厚的学问了。
可见唐音之“味”重情深、重意境,宋调之“味”则强调平淡与学问。
王琦论诗味强调诗人情感之幽微曲折,强调情景交融、含蓄蕴藉的意境美,强调诗歌的空灵美以及余味悠长之美。其审美趣味与司空图、严羽接近,趋向“唐音”,而与被严羽批评为语直、意浅、脉露、味短的“宋调”大相异趣。
1.以情感为基础
诗歌是否有“味”,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因素应该是情感。唐代皎然则从创作的角度提出有深味的诗应该“以情为地,以兴为经,然后清音韵其风律,丽句增其文采……”(16)(唐)释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268页。情是最基本的要素。张戒称赞古诗和苏、李、曹、刘、陶、阮诗“其情真,其味长”,也明确把“真情”看作“味长”的条件。王琦论诗味,也非常注重其中的情感要素。
《李长吉歌诗汇解》卷四《江南弄》“酒中倒卧南山绿”,王注曰:“酒中,饮酒方半也。倒卧者,酒酣倒地而卧也。南山绿者,悠然见南山之色也。徐文长以为山影入杯亭者,意以巧而反觉味短。”(17)(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143页。若依徐渭解,这句话纯是事、物的描写,虽然巧,但正如王昌龄所说:“若空言物色,则虽好而无味。”(18)(唐)王昌龄:《诗格》,引自(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88页。而若依王琦之解,则诗人形象、情感跃然纸上。
再如《李长吉歌诗汇解》卷四《江楼曲》“新槽酒声苦无力”,王注曰:“新酒已熟,槽床滴注有声,然饮之不能消愁,反苦酒之无力。旧注谓滴将尽,盖以下五字相联作一解亦通。然意味殊觉短浅。”(19)(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159页。王琦这里所云“旧注”应指曾益注。其解“苦无力”为槽床滴将尽,王琦嫌这样的解释使得诗歌“意味殊觉短浅”,他认为应指主人公苦酒之无力消愁。这二者最大的区别也就在于是否有主体的介入,是否有情感的跃动。在王琦看来这是诗歌是否有“味”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内容深刻而婉曲
严羽《沧浪诗话》论诗味曰:“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20)(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22页。四个“忌”,除了强调诗歌表达上的含蓄蕴藉之外,还包括了对诗歌内容、情感的丰富性的要求,诗“意”需深方有味。王琦亦偏好意味深长的诗歌。
《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南园十三首》其四“三十未有二十余,白日长饥小甲蔬。桥头长老相哀念,因遗戎韬一卷书。”王注曰:“此首疑咏一时实事。与张子房游下邳圮上遇老人授太公兵法,正绝相类。连下三首读之,皆是左文事右武功,其意可见。盖当元和年中,频岁征讨,一时文士受藩镇辟召,效力行间,致身通显者,往往有之。宜长吉知心驰而神往也。读者不会其故,只以用史汉故事视之,意味索然,有如嚼蜡。”(21)(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61页。这首诗用了张良遇黄石老授太公兵法之典故,如果诗歌只是单纯吟咏张良事,为什么会“意味索然”呢?无非伤其意太浅,内容不够深刻,言尽意亦尽,诗味自然索然。
《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三《谢秀才有妾縞练,改从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后生感忆。座人制诗嘲诮。贺复继四首》其二“碧玉破不复,瑶琴重拨弦”句,王注曰:“吴正子注:破不复或云合作破瓜后,众本作破不复,非也。碧玉,宋汝南王之妾,王宠幸之,作歌曰:碧玉初破瓜,相为情颠倒。‘不复’与‘瓜后’字相近而讹耳。”琦谓此二句皆是喻意,谓其改从于人如彼碧玉破而不可复完,如彼瑶琴重为他人鼓拨,以诮其此时感忆无益之意:“若订做碧玉破瓜后,不但对句直至无味,亦与前四句不相联署。”(22)(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102页。为什么王琦以为“碧玉破不复”比“碧玉破瓜后”诗味更浓?从后面的解释来看,无非也在于意深意浅的问题。“碧玉破不复,瑶琴重拨弦”可作喻意解,比喻其改嫁他人之后如碧玉破而不可复完,如瑶琴重为他人鼓拨。而若作“碧玉破瓜后,瑶琴重拨弦”,则纯是赋法,写其改嫁他人后,碧玉破瓜,郎情颠倒,瑶琴重弹。两相比较,后者意味自不如前者深长。其实吴正子所言并非没有道理,而且宋蜀本、蒙古本此处均作“破瓜后”,而王琦在没有文献依据的情况下作此判断,从注释学角度看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据此可见其诗美理想。
除了内容深刻,诗歌情感、脉络的委婉曲折也有助于诗味的深长。《李太白全集》卷五《塞上曲》“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五原秋草绿,胡马一何骄。命将征西极,横行阴山侧。燕支落汉家,妇女无华色。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23)(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291页。洪迈选《万首唐人绝句》将其分为三首,每四句一首。王琦曰:“洪迈选《万首唐人绝句》,分此诗为三章,顿觉无味,不若合作一首之善。”(24)(唐)李白著,(清)王琦注:第293页。若将此诗分为三首,每首也能表达完整的意思,第一首写匈奴犯边,第二首大将西政胜利归来,第三首休兵后之平静。但如此一来,每一首都让人有意短、意浅、意直之感,了无余味。而若三章合一,诗歌脉络委婉曲折,意味深长。
再如《李长吉歌诗汇解》卷四《夜坐吟》:“踏踏马蹄谁见过?眼看北斗直天河。西风罗幕生翠波,铅华笑妾颦青蛾。为君起唱长相思,帘外严霜皆倒飞。明星烂烂东方陲,红霞梢出东南涯,陆郎去矣乘斑骓。”(25)(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140—141页。在诗歌的末句,王琦注曰:“此句是回念前此去时之况,因其不来而追思之,遂有无限深情。夜坐者,夜坐而俟其来也。为君起唱长相思,君者,即指其人。通篇总是思而不见之意。徐文长以来迟去早为解,反觉末句无甚隽永。”(26)(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141页。徐渭对这首诗的解释为:“改笑为颦,正以夜易晓而陆郎遽别也。夜坐候客,来既迟去复早亦寓士难遇易弃意。”(27)(明)徐渭注,(明)董懋策评:《唐李长吉诗集》,《丛书集成三编》(第10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923页。根据徐渭的解释,这首诗故事的发展与情感的演变完全是按时间顺序排开。故事以男主人公姗姗来迟开场:“踏踏马蹄谁见过?眼看北斗直天河。”接着是男女主人公相处的场景:“西风罗幕生翠波,铅华笑妾颦青蛾,为君起唱长相思,帘外严霜皆倒飞。”男主人公来得本来就晚,时间又无情流逝,女主人公想到这里不禁皱了皱眉头,起身为男主人公唱起了长相思。当“明星烂烂东方陲,红霞梢出东南涯”(28)(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1998年,第141页。的时候,男主人公乘着斑骓离开了。这样平铺直叙的一个故事,读起来确实索然无味。
王琦认为“通篇总是思而不见之意”,末句是“回念前此去时之况,因其不来而追思之”。若如此解诗,则诗用6句尽情地郁积和酝酿情绪:女主人公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男主人公始终未来,她带着焦虑、失望和忧伤唱起了《长相思》曲,如果说这种焦虑和失望还带着一丝丝的希望的话,当天渐渐地亮起来,明星烂烂,红霞稍出的时候,仅存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希望破灭了,诗却没有戛然而止。女主人公想起了以前的光景,此时该是“陆郎去矣乘班骓”的时候了吧。情感的变化微妙而曲折,与徐渭解的平铺直叙比起来,确实更耐咀嚼,更加隽永。
3.情景交融、虚实结合的意境美
《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李凭箜篌引》:“吴正子注言:箜篌之声忽如石破而秋雨逗下,犹白乐天《琵琶行》:‘银瓶乍破水浆迸’之意。琦玩诗意,当是初弹之时,凝云满空,继之而秋雨骤作。洎乎曲终声歇,则露气已下,朗月在天,皆一时实景也。而自诗人言之,则以为凝云满空者,乃箜篌之声遏之而不流,秋雨骤至者乃箜篌之声感之而旋应,似景似情似虚似实。读者徒赏其琢句之奇,解者又昧其用意之巧。显然明白之辞而反以为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误矣。”(29)(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35—36页。
王琦这段解说特别值得注意。他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空山凝云颓不流”“石破天惊逗秋雨”“露脚斜飞湿寒兔”等句是实写当时的情境还是仅仅只是为描写音乐效果所作的比拟?也就是说是“比”的成分多一点还是“兴”的成分多一点?我们先来看看李贺集其他几个重要的古注本的注释。
吴正子的注以征引式为主,解说不多,这几个句子中只有“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有简略的说明。他说:“箜篌之声忽如石破而秋雨逗下,犹白乐天《琵琶行》:‘银瓶乍破水浆迸’之意。”(30)(唐)李贺著,(宋)吴正子注,(宋)刘辰翁评点:《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85页。显然是以“比”义来解释这个句子,认为这句话和白居易《琵琶行》中“银瓶乍破水浆迸”的写法一样,是用来比喻音乐的效果。
曾益《昌谷集》曰:“高秋音亮,言时良。空山响应,颓不流,行云遏也……其声如玉碎而清,如凤叫而和,不特有情者为之动,即芙蓉之舍露也,若泣,而香兰之开也,若笑……秋雨至骤,石破天惊,音将绝而急奏也……老鱼句,状指法之妙……结句即景零露夜滴,凉月微茫,时何闲暇。”(31)(唐)李贺著,(明)曾益注:《李贺诗解》,台北:世界书局,1991年,第3页。曾益认为“空山凝云颓不流”“露脚斜飞湿寒兔”即景而言,“石破天惊逗秋雨”为“比”,比喻弦音之急。
姚文燮《昌谷集注》:“至音声之妙,凝云言其飘渺也。湘娥言其悲凉也。玉碎凤鸣言其激越也。芙蓉兰笑,言其幽芬也。帝京繁艳,际此亦觉凄清。天地神人,山川灵物,无不感动鼓舞,即海上夫人梦求教授,月中仙侣,徙倚终宵,但佳音难覯,尘世知希,徒见赏于苍玄,恐难为俗人道耳。”(32)(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207页。姚文燮认为“凝云”句是“比”,比喻声音的缥缈;“石破天惊”句亦非实景,乃以天上神人之反应极写音乐之美妙;“露脚”句未解释。
从这首诗的阐释史看,“空山”句、“露脚”句说法尚不统一,既有以“比”目之者,亦有以“兴”目之者,“石破”句则无一例外认为是比喻句,用“石破天惊逗秋雨”这样一种具体可感的自然现象比喻难以言喻的箜篌之声。
这种共同的阐释倾向的出现是有渊源的。
汉赋名篇《七发》开启了以具体可感的事物写音乐的先声:“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蝼蚁闻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33)(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三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559页。这里的飞鸟翕翼、野兽垂耳、蚑蟜蝼蚁拄喙显非现实情景,而是通过罗列鸟兽虫蚁的反应从侧面渲染音乐效果。之后王褒的《洞箫赋》、傅毅的《琴赋》、马融的《长笛赋》、蔡邕的《弹琴赋》等在《七发》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对《七发》化虚为实的手法进行了极大的丰富。如王褒《洞箫赋》云:“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净厌瘱,顺叙卑迖,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谓。其仁声,则若飙风纷披,容与而施惠。”(34)(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第786页。在这段文字中,作者连续例举慈父畜子、孝子事父、壮士、君子、雷霆輘輷、飙风纷披来写洞箫的声音,以“若”字作为提示,“比”的用法就更明显了。
唐诗的创作受赋的影响很深(35)参看余恕诚、吴怀东著:《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118页。,唐代许多描写音乐的诗篇都受其影响,除了大名鼎鼎的白居易的《琵琶行》,其他如韩愈《听颖师弹琴》:“呢呢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36)(清)彭定求:《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812页。吴融《李周弹筝歌》:“始似五更残月里,凄凄切切清露蝉。又如石罅堆叶下,泠泠沥沥苍崖泉。”(37)(清)彭定求:《全唐诗》,第7898—7899页。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初调锵锵似鸳鸯水上弄新声,入深似太清仙鹤游秘馆。”(38)(清)彭定求:《全唐诗》,第2946页。
因此,前人不管是将“空山”句、“石破”句还是“露脚”句理解为比喻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尤其是“石破”句,紧接在“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39)(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35页。这一系列的比喻句之后,其作为比喻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然而王琦却力排众议,将这几个句子都视为景物实写,足见其审美倾向性。
如果单纯将这几句视为对音乐的描绘,固然很生动,但终究是说明性的文字。而经过王琦的解读,这首诗意境全出。初弹之时,凝云满空,就诗人的感觉而言,乃箜篌之声遏之而不流。随着音乐的流动,弦音愈高愈急之时,恰秋雨骤至,似乎音乐逗之而至。而至曲终声歇,则露气已下,朗月在天。音乐、大自然与人似乎融合在一起,以同一音律、同一节奏,共同响动,似景似情,即景即情,似虚似实,虚实相生,整首诗浑然一体,诗歌的意境于是产生。王琦这里没有使用“味”这个概念,但这分明就是司空图所描绘的那种“蓝田日暖”“良玉生烟”“思与境谐”浑然一体的境界。
前文所举王琦对《江南弄》“酒中倒卧南山绿”(40)(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143页。句的解说除了情感的因素之外,意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王琦以陶渊明“悠悠见南山”(41)(东晋)陶渊明著,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47页。的意境解诗,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包蕴无穷,特别能代表王琦的审美倾向。
4.朦胧空灵之美
空灵易生诗味,前代诗论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司空图所描绘的“蓝田日暖,良玉生烟”的境界里,已经包含了诗歌朦胧、空灵之美的追求。明代谢榛的诗味理论更是明确提出景不要太实,以虚致味。他说:“贯休曰:‘庭花濛濛水泠泠,小儿啼索树上莺’,景实而无趣。太白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景虚而有味。”(42)(明)谢榛:《四溟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49页。
《李太白全集》卷五《清平调词三首》其一的首句是“叶想衣裳花想容”还是“云想衣裳花想容”,王琦曰:“蔡君谟书此诗以‘云想’作‘叶想’,近世吴舒凫遵之,且云:‘叶想衣裳花想容’与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俱从梁简文‘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脱出。而李用二‘想’字化实为虚,尤见新颖。不知何人误作‘云’字,而解者附会《楚辞》‘青云衣兮白霓裳’,甚觉无谓云云。不知改‘云’作‘叶’便同嚼蜡,索然无味矣。此必君谟一时落笔之误,非有意点金成铁,若谓太白原本是‘叶’字,则更大谬不然。”(43)(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304—305页。王琦介绍了蔡襄、吴舒凫的观点之后认为“叶”不如“云”有诗味,具体原因他没有再进一步的说明,但就诗歌审美效果而言,“叶想衣裳花想容”质实,而“云想衣裳花想容”则多了空灵之美。
还有一个例子特别能够说明王琦这种审美取向。李贺《雁门太守行》“塞上燕脂凝夜紫”,王注曰:“旧注引《古今注》,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故曰紫塞为解。琦按,当做暮色解乃是。犹王勃所谓‘烟色凝而暮山紫’也。”(44)(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44页。王琦这里所说的“旧注”指的是吴正子注。这句话中“上”字吴正子本作“土”字,因此他以“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故曰紫塞”来解释这句话。王琦不取吴正子注而以王勃“烟色凝而暮山紫”为解。王琦的这种解法遭到了四库馆臣的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琦此注……亦不免寻行数墨之见,或附会穿凿,或引据失当,如《雁门太守行》‘塞土燕脂凝夜紫’句,旧注引《古今注》‘紫塞’为解,本不为谬,而琦必从别本作‘塞上’,引王勃‘烟光凝而暮山紫’句以就‘凝紫’二字。是岂塞上夜景耶?”(45)(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35页。四库馆臣以“附会穿凿”批评王琦此注,其实王琦自有他的考虑。《李太白全集》卷三《胡无人》也有“紫塞”(46)(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213页。一词,王琦就引《古今注》作解。那他为什么对这两首诗作不同的解释?比较《胡无人》“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与《雁门太守行》“塞上燕脂凝夜紫”两句,前者诗意很显豁,“紫塞”作为地理名词是毫无疑义的;而后者则因为一个“凝”字造成了特殊的艺术效果,“凝”的主语是什么?是土色凝还是烟色凝?吴正子以为是土色凝,土的颜色太红以至于发紫,这样的理解亦与字面义吻合,但从诗歌的艺术效果上看,稍显质实,缺乏美感。而若理解成“烟色凝”,诗歌整体意境就带有了点司空图所描绘的蓝田日暖、良玉生烟的效果。王琦选择了后者,这正是他的审美偏好使然。
5.有余味
“味”作为一个口舌感官概念用之于文艺审美感受之初就强调一种余音袅袅、余味悠长之美。《礼记·乐记》云:“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47)(清)孙希旦注,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82页。
在文学批评领域,从刘勰《文心雕龙》的“深文隐蔚,余味曲包”(48)(南朝梁)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96 页。,到钟嵘强调兴之“文已尽而意有余”(49)(南朝梁)钟嶸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6页。,到司空图“酸咸之外”的“醇美”之味,“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一直作为诗“味”的一个要素被关注。北宋魏泰则鲜明地提出“余味”论,并对之进行详细的阐述,他说:“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乎词,此所以感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唐人亦多乐府,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言尽意尽,更无余味。”(50)(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何文焕编:《历代诗话 》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2页。
《李长吉歌诗汇解》卷四《贝宫夫人》“秋肌稍觉玉衣寒,空光帖妥水如天”句,王注曰:“诗意本谓空光帖妥水如天,秋肌稍觉玉衣寒。一倒转用之。便觉有摇曳不尽之致。”(51)(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155页。王琦的艺术感觉很敏锐,“空光帖妥水如天,秋肌稍觉玉衣寒”与“秋肌稍觉玉衣寒,空光帖妥水如天”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一个因果关系复句,因为秋季天凉如水,所以身着薄衣的女主人公感觉到了寒意,这不过在是叙述一个基本事实,言尽意亦尽;而后者则将女主人公的清冷的形象置于广袤的宇宙天地之间,并随着广袤的宇宙无限延伸,读者的审美感受也随着无限延伸。
可见,王琦“诗味论”基本是对司空图、严羽等的承袭,其审美趣味趋向“唐音”而与“宋调”大相异趣。
(三)诗好自然,不喜雕琢
诗歌在初盛唐诗人手中大体自然醇厚,而经过杜甫、韩愈、郊岛等人的发展而至于宋人,诗尚尖新,雕刻痕迹越来越重。王琦则偏好具有唐诗风味的自然醇厚之美,这从他对李贺诗歌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来。李贺诗设色秾丽,雕章琢句的事实为世人所公认,然而在王琦看来,这并非李贺诗之精华,他说:“樊川序中反复称美,喻其佳处凡九则,后之解者,只拾其鲸呿鳌掷、牛鬼蛇神、虚荒诞幻之一则。以为端绪,烦辞巧说。差爽尤多……而朱子顾谓其与太白相去不过些子间,盖会意于比兴风雅之微,而不赏其雕章刻句之迹,所谓得其精而遗其麄者耶。”(52)(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3页。王琦还用“自然”这个标准去评价诗歌,《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二《金铜仙人辞汉歌》,王琦有评曰:“司马温公诗话:李长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奇绝无对。石曼卿对月如无恨月长圆,人以为勍敌,琦细玩二语,终有自然勉强之别,未可同例而称矣。”(53)(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 1998年,第67页。
二 王琦在宋风大炽的杭州诗坛上独尚唐音的原因分析
(一)宗唐派对王琦的影响
1.王琦与“西泠十子”之关系
王琦生当浙诗派在杭州诗坛上大行其道之时,他和浙诗派中坚杭世骏、赵昱、赵信等人亦有交游,但是他的诗学取向却与浙诗派大相异趣而与之前的“西泠十子”有惊人的相似。
“西泠十子”诗学观继承云间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并且他们的“温柔敦厚”偏于中庸和平之美,反对哀怨的“变风”“变雅”。
其二,扬唐抑宋,但宗唐的范围比之前后七子及云间派有所扩大,认识到四唐各有所长,尤其对华美的中晚唐诗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他们抬高中晚唐诗的策略是将其纳入风骚传统中,认为其“虽托兴于艳歌,实权于大雅者也。”(54)毛先舒:《赠王采生诗四首并序》《晚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1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00页。
其三,崇尚含蓄蕴藉之美。毛先舒《诗辩坻》总论说:“高手下语,唯恐意露,卑手下语,唯恐意不露。”(55)毛先舒:《诗辩坻》,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页。他不喜欢元白以及宋诗就在于他们把话说得太尽,缺少含蓄蕴藉之美。
这些观点与王琦之诗学观并无二致,那么王琦是否受到“西泠十子”的影响呢?“西泠十子”在清初杭州诗坛的地位甚重,张谦宜在《絸斋诗谈》中将其与历下、竟陵、云间相提并论:“历下、竟陵、云间、西陵,各有盛时。学者模拟声响,摭拾粉泽,皆假也。”(56)张谦宜:《絸斋诗谈》,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800页。毛奇龄则不无夸张地说,在“西泠十子”活跃之时,诗人学者“不敢以宋元之诗入西泠界”(57)毛奇龄:《柴征君墓状》,《西河集》卷一百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42页。。虽然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王琦出生的时候,“西泠十子”大多已谢世,但是他们对杭州诗坛的影响力依然没有消歇,受“西泠十子”影响的大有人在。
厉鹗在《懒园诗钞序》中说:“往时吾杭言诗者必推‘西泠十子’,十子之诗皆能自为唐诗者也。承其学者,吴丈志上、徐丈紫山师张先生秦亭,蒋丈静山雪樵、陈丈懒园师毛先生稚黄,沈丈方舟独师岭南五子,而说亦与十子合。诸君之诗,声应节,赴宫商欣合,故流派同而交宜亦笃。”(58)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34页。此外,洪昇先后师从陆圻之侄陆繁弨、毛先舒、柴绍炳、沈谦,受到西泠十子文雅忠爱、温柔敦厚诗教的影响很深。即便是偏宗宋诗的浙派都不能摆脱其光环的笼罩。厉鹗与“西泠十子”门人蒋静山、陈懒园、徐昌薇相友善,且从以上厉鹗《懒园诗钞序》对“西泠十子”的评价来看,厉鹗对这群诗坛前辈亦是相当尊崇,朱庭珍《筱园诗话》将“西泠十子”作为浙派之开端正是看到了他们对浙派的影响,他说:“浙派自西泠十子倡始,先开其端,至厉太鸿而自成一派,后来宗之。”(59)朱庭珍:《筱园诗话》,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2367页。
总的来说,在浙诗派风靡一时的时候,“西泠十子”的影响依然存在,正如厉鹗所说,其“流风故未坠也”(60)厉鹗:《蒋静山诗集序》《樊榭山房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33页。。而生活于杭州的王琦受其流风余韵之濡染也是很正常的。至少从王琦《李太白集注》《李长吉歌诗汇解》所引用的文献材料来看,他对毛先舒《诗辩坻》是很熟悉的。《李太白集注》卷七《扶风豪士歌》王琦引用《诗辩坻》评语1条,《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四《丛说二百二十则》收录《诗辩坻》评语6条,《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二《致酒行》引用毛先舒评语1条。
此外,《李太白全集》还引吴舒凫关于李白诗的校勘记3条:(1) 卷五《清平调词三首》其一的首句:“蔡君谟书此诗以‘云想’作‘叶想’,近世吴舒凫遵之,且云:‘叶想衣裳花想容’与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俱从梁简文‘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脱出。而李用二‘想’字化实为虚,尤见新颖。不知何人误作‘云’字,而解者附会《楚辞》‘青云衣兮白霓裳’,甚觉无谓云云。”(61)(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304页。(2)卷二十二《越中览古》“义士还家尽锦衣”句:“‘义士’,吴舒凫以为‘战士’传写之讹,谓越人安得称‘义士’云云,未知是否。”(62)(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1030页。(3)卷二十二《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句:“吴舒凫曰:《张良传》云: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太白正用其语,刻本改为‘天地皆震动’,天地何震动之有耶?”(63)(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1036页。三处校勘都是用理校法。
吴舒凫,名仪一,亦名逸,别名吴人,字符,更字舒凫,号吴山,钱塘人。著述有:《周易大象说录》《仕的》《吴山草堂集》《记豆词敲波词采苓词》(64)以上据民国李楁《杭州府志》,民国十一年铅印本。《徐园秋花谱》(65)《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七志一百二十二艺文三载录,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56页。《梦园别录》(66)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二载录,并称已散佚。。王琦所引3条校勘记未知出于何处。吴舒凫是有名的刻书家,抑或他曾经刊刻过李白集?
吴舒凫与“西泠十子”渊源颇深。他初居松盛里,后移居吴山之螺峰,与毛先舒衡宇相望。十二岁时在毛先舒寓与洪昇等诸名士相聚,与洪昇结下深厚的友谊。(67)刘辉:《论吴舒凫》,《戏剧艺术》1987年,第1期,第108—117页;华生《吴舒凫生平考——与刘辉先生商榷》,《戏剧艺术》1988年,第2期,第86—91页。王琦注《李太白全集》认真地参考了吴舒凫的校勘成果,可见他对于“西泠十子”及其周围诗人群体的思想、研究、著述较为熟悉,受其影响也在情理之中。
2.王琦与徐乾学之关系
王琦留下的生平资料不多,其交游、师承情况都不甚清晰。但清阮元《两浙輶轩录》(清嘉庆刻本)卷十一载有邵九皋的一首诗《怀王载韩之江右》:“朔风十月怯衣单,转念征途客子难。烽火五年行李倦,零丁八日肺肠酸。酒醒孤馆青灯落,月满前溪白蓼残。望断音书频极目,芦花无数雁声寒。”(68)(清)阮元:《两浙輶轩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55页。从这首诗看,王琦与邵九皋关系匪浅。
这首诗前有作者简介:“邵九皋,字翼雲,号鹤田,仁和副贡生,官常山训导,有《寓亝偶存》。宋大樽曰:鹤田性耽经史,喜振拔孤寒,从健菴、匠门两先生游,所交皆当时名宿。”(69)同上。健菴即徐乾学,邵九皋曾从徐乾学游,以王琦和邵九皋的关系,他是否也或多或少受过徐乾学的影响?虽不能肯定,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二)康熙中期以后,诗坛尽管仍然存在倾向性十分明显的偏好唐音或者偏好宋调两个阵营,但在很多人的诗论中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折衷唐宋的因子,唐宋之争趋于缓和与理性。
入清之后,诗坛兴起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唐宋诗之争。
一方面,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认为,诗歌与时运、士气紧密相关,而“万历之际,士大夫偷安逸乐,百事堕坏。而文人墨客所为诗歌,非祖述长庆以以绳枢瓮牖之谈为清真,则学步香奁,以残膏剩粉之资为芳泽。是举天下之人非迂朴若老儒,则柔媚若妇人也。是以士风日靡,士志日陋,而文武之业不显”(70)(明末清初)陈子龙:《答胡学博》,《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卷十四,《陈子龙文集》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24页。,而盛唐诗风的蓬勃朝气正符合他们的期待,他们提出学习盛唐诗“温厚之旨,高亮之格,虚响沉实之工,珠联璧合之体,感时托讽之心,援古证今之法”(71)(明末清初)陈子龙:《答胡学博》,《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卷十四,《陈子龙文集》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24页。。
之后,杭州的“西泠十子”也在云间派的直接影响下标举盛唐诗歌:“诗本无定法,亦不可讲法。学者但取盛唐以上,《三百》以下之作。”(72)(清)毛先舒:《诗辩坻》,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78页。他们对宋元诗评价甚低,毛先舒说:“宋诗俚露,不但言理,即叙事述情,往往而是,故不得谓汉后无颂而独以宋继颂耳。”(73)同上第1页。柴绍炳说:“宋习鄙钝,元音俚下。”(74)(清) 柴绍炳:《西陵十子诗选序》,毛先舒辑:《西泠十子诗选》,清顺治七年还读斋刻本。但与陈子龙不同的是,“西泠十子”宗唐的范围有所扩大。毛先舒论七言律曰:“唐初意尽句中,正用气格为高,盛唐境地稍流,而兴溢章外,不妨媲美。作者取裁,舍是奚适?中叶翩翩,亦曲畅情兴,必欲瓿覆大历以下,似属元美过差之谈。至于李商隐而下,予不敢道之。”(75)(清)毛先舒:《诗辩坻》,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54页。认识到初盛中晚四唐各有所长,他诗歌取径也较宽。他著有《晚唱》诗一卷,模仿李商隐、李贺、温庭筠、韩偓四家诗。此外,丁澎“诗学晚唐,独无拟古乐府”(76)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94页。;沈谦“其诗初喜温、李,后乃由盛唐以窥汉魏”(77)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卷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二人都以晚唐诗为宗。
此外关中李因笃等人亦重申七子派的宗旨,论风雅,论格调,以高廷礼为正宗,推崇“羚羊挂角,无迹可求”(78)(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6页。之美;岭南屈大均等人追踪七子派反宋论调,以为“诗之衰,至宋元而极矣”(79)屈大均:《荆山诗集序》,《翁山文外》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4册),第88页。,而在师法范围上又超越七子派的“诗必盛唐”,初、盛、中、晚并重,师法全唐诗;京师“燕台七子”张文光、赵宾、宋琬、施闰章、严沆、丁澎、陈祚明在顺治十二年到十三年间结社唱和,诗歌创作宗尚初盛唐诗,标榜复古诗风。
与此同时,一股宗宋的思潮也在悄悄涌动。钱谦益反对诗歌“限隔时代”,认为“天地之降才,与吾人之灵心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开元则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严羽卿、刘辰翁、高廷礼之瞽说,限隔时代,离格律,如痴蝇穴纸,不见世界,斯则良可怜愍者。”(80)(清)钱谦益:《题徐季白诗卷后》,《钱牧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563页。
黄宗羲则在两个基点上反对宗唐抑宋:首先,他以“诗以道性情论”(81)(清)王夫之:《船山全书》,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670,681页。为基础,认为诗歌只要抒写真性情,学唐学宋不必拘泥。其次,他提出“善学唐者唯宋”(82)(清)黄宗羲:《姜山启彭山诗稿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7页。,认为宋诗是对唐诗的继承、发展和变异,不应视宋诗为异物。他试图以此消除人们执着唐宋的论调,而合唐宋为一。
钱、黄二家论调看似齐唐宋,但在当时复古诗风浓厚的背景下,以此提高宋诗地位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在顺治及康熙初的诗坛上,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些提倡宋调的声音,但尚未形成强有力的潮流。康熙十年(1671),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编选的《宋诗钞》刊刻,吴之振携带进京,赠送给京中的诗人巨子,此书在京师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宋荦《漫堂说诗》云:“至余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矣。”(83)(清)宋荦:《漫堂说诗》,《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416页。至迟在康熙十八年(1679),京师乃至全国宋诗风就很兴盛了,毛奇龄在《徐宝名诗集序》中言及他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科时的情景:“长安言诗者……自称宋诗,誂膠焉诟明而訿唐,物有迂夸不入市者,辄以唐人诗呼之。”(84)(清)毛奇龄:《徐宝名诗集序》,《西河集》卷五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70页。顾景星写于康熙十八年的《青门簏稿诗序》则云:“今海内称诗家,数年以前,争趋温、李、致光,近又争称宋诗。”(85)(清)顾景星:《青门簏稿诗序》,(清)邵长蘅:《邵子湘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24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78页。自此,唐音、宋调二足鼎立之势形成,甚至还发生过主唐者与主宋者之间的激烈争论。
毛奇龄《唐七律选序》中记载了主唐派的施闰章与主宋派的汪懋麟的论争:“前此入史馆,时值长安词客高谈宋诗之际,宣城侍读施君与扬州汪主事论诗不合,自选唐人长句律一百首以示指趋,题曰馆选。”(86)(清)毛奇龄:《唐七律选序》,《西河集》卷五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465页。
王士祯《居易录》记载了力主唐音的毛奇龄与汪懋麟的论争:“萧山毛简讨大可生平不喜东坡诗,在京师日,汪季甪举坡绝句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语毛曰:‘如此诗,亦可道不佳耶?’毛愤然曰:‘鹅也先知,怎只说鸭?’众为捧腹。”(87)(清)王士祯:《居易录》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26页。
而到了康熙中后期,尽管宋诗热还在持续,但诗坛已经开始了对宋诗热的反思。康熙二十六年(1687),王士祯选刻《十种唐诗选》,次年选刻《唐贤三昧集》,宋荦《漫堂说诗》称他此举乃“力挽尊宋祧唐之习,良于风雅有裨。”(88)宋荦:《漫堂说诗》,《清诗话》,第417页。曾经由唐入宋的宋荦也开始批评尊宋祧唐之风气,他说:“近二十年来,乃专尚宋诗。至余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矣。孟举序云:‘黜宋者曰腐,此未见宋诗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诗之全,守嘉隆间固陋之本,陈陈相因,千喙一倡,乃所谓腐也。’又曰: ‘嘉隆之谓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盖意主救弊,立论不容不尔,顾迩来学宋者,遗其骨理而挦扯其皮毛,弃其精深而描摹其陋劣,是今人之谓宋,又宋之臭腐而已。谁为障狂澜于既倒耶?”(89)宋荦:《漫堂说诗》,《清诗话》,第416—417页。
可以说,在经历一场激烈的争论后,片面宗唐与主宋的弊端皆已逐渐地被认识到,这时的诗人们再来审视唐宋诗之争,大家的态度显然更加理性了。正如宋荦所说的,学唐者因为陈陈相因走向臭腐,学宋者若遗其骨理而挦扯其皮毛同样流于臭腐。
在康熙后期以至乾隆前期的诗坛仍然存在倾向性十分明显的偏好唐音或者偏好宋调两个阵营,但在很多人的诗论中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折衷唐宋的因子,表现出了反对强分唐宋的态度。
康熙末偏好宋调者除了宋荦之外,汪琬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国朝诗选序》中云:“古之为诗者,问学必有所据依,章法句法字法必有所师承,无唐宋一也。今且区唐之初、盛、中、晚而四之,继又区唐与宋而二之,何其与予所闻异也!且宋诗未有不出于唐者也,杨、刘则学温、李也;欧阳永叔则学太白也;苏、黄则学子美也;子由、文潜则学乐天也。宋之与唐,夫固若埙篪之相倡和,而駏蛩之相周旋也审矣。”(90)汪琬:《尧峰文钞》卷二十七,四部丛刊本。田雯也曾说过:“今之谈风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唐之杜韩,海内俎豆之矣。宋梅、欧、王、苏、黄、陆诸家,亦无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惟其生于宋也。”(91)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一,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95页。叶燮以源流、正变论诗,认为每个时代的诗都有其特性,后人学诗要能完整地认识诗史源流,见各代之所长,不能“执其源而遗其流”,也不能“得其流而弃其源”(92)叶燮:《原诗》外篇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30页。。查慎行亦是如此,尽管他宗宋趣味明显,但是在理论上仍明确反对唐宋分立,他的《吴门喜晤梁药亭》云:“知君力欲追正始,三唐两宋需互参。”(93)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l986年,第104页。而王士祯在康熙二十年左右主盟文坛,逐渐重返唐音,有以唐音救学宋之流弊的意思,但他对黄庭坚、苏轼等人的爱好始终没有改变。
雍正朝及乾隆前期活跃于诗坛的是主唐的格调派与法宋的浙派。沈德潜对当时诗坛宗宋的风气非常不满,欲以唐诗为正轨挽救宋诗热之弊。他在《许竹素诗序》中曰:“时吴中诗学祖宋祧唐,几于家至能而户务观。予与二三同志欲挽时趋,苦无其力。”(94)(清)沈德潜著:《归愚文钞卷》卷十四,汇雅电子图书,第118页尽管如此,他也不愿意以反对宋诗者自居:“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愚未尝贬斥宋诗,而趋向旧在唐诗。”(95)(清)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页
一向被学界称为“宋诗派”的浙派尽管在创作上趋于宋诗的抒情范式,重学问、好用典,但他们在理论上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宗宋或者排唐的言论。厉鹗认为“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96)厉鹗:《查莲坡蔗糖未定稿序》,《樊榭山房集·文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35页。,他反对立宗立派的行为:“自吕紫微作西江诗派,谢翱序睦州诗派,而诗于是乎有派。然犹后人瓣香所在,强为胪列耳,在诸公当日未尝断断然以派自居也。迨铁雅滥觞,已开陋习。有明中叶,李、何扬波于前,王、李承流于后,动以派别概天下之才俊,啖名者靡然从之,七子、五子,叠床架屋。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缀学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济南之余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巨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篇什虽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于此有卓然不为所惑者,岂非特立之士哉?”(97)同上。杭世骏也没有明确的轩轾唐宋的话语,他虽然偏好宋调,但却也不鄙薄唐风,在《张参议春晖堂诗钞序》中他称赞宗唐之诗人张卜臣:“上溯魏晋,宗三唐而祧两宋,归于清遒深亮而止,而犹以操觚率尔为兢兢。今读其诗,心澄语密,优柔而平中,治世之音安以乐。”(98)杭世骏:《张参议春晖堂诗钞序》,《道古堂文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4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9页。正是因为浙派中坚这种兼容的态度,杭世骏、赵信等人在为王琦《李太白全集》所作的序中对王琦的工作给予极大的肯定。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选《唐宋诗淳》,该选本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准则兼容唐宋,这是官方对唐宋诗之争所作出的调和。
正因为唐宋之争不再那么针尖对麦芒,王琦才能够在浙诗派活动中心杭州保持宗唐的审美态度。其实在法宋的浙诗派大行其道的浙地诗坛,宗唐者大有人在。王琦二注本的出现在当时并非凤毛麟角,诗坛复杂真实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