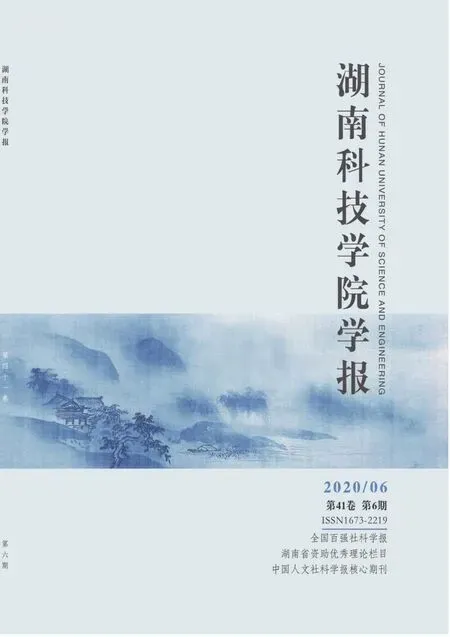论先秦道家以“虚玄”为中心的心性论之建构
2020-01-06李秀倜
李秀倜
论先秦道家以“虚玄”为中心的心性论之建构
李秀倜
(湖南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201)
先秦道家从性之“真”出发,并不采用善恶之类的人设标准来对物性乃至于人性进行定义。道家秉持“道”的思想,认为人的本原之“心”是“道”在人身上的映射,而“性”由“心”生,此二者都是内藏于人的,世人可以看到的是外显的“情”,而“情”却往往对外表现出伪饰。老庄针对这种遮蔽心性之“真”的伪饰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以“虚”“玄”为要旨的解蔽工夫。所谓“虚”,就是去掉人为造作而回归物之本然状态;而所谓“玄”,就是玄远深邃,即非世俗之智能所能探视的本原。先秦道家的人性论,正是以这种“虚玄”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即中止人为造作而至于“道”,故“虚”和“玄”俱是“道”的体现工夫,通过追寻“虚玄”而回归心性之“真”,才能最终走向道家的“自由王国”。
道家;人性论;自然;性情
对于人性的问题向来是中国哲学的重点,在中国,凡言“中国哲学”,必要涉及人性问题,而在近现代对于人性问题的讨论中,儒家以其基于对“人”的执守,以及先秦孟荀二子对于人性截然相反的认识成为了各家辩论的中心,也就是说,儒家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只停驻在“人”处。道家则对“宇宙”本源问题有着特殊关注,其学说中有关“人性”的思考则正深藏在这种关注之中,所以,其人性论往往在这种关注中隐而不显。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儒家与道家对于人性的讨论显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儒家的人性之善恶是将社会积习的价值判断附着于人性,而道家自庄子始,普遍讨论的人性显然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人性论。
何谓自然状态下的人性论呢?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此处的“自然”二字。先秦道家和后世的道教所倡的“自然”,都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于万物无为无造、无施无惠,任由其自我发展的顺应天道的规范,庄子名之曰“天放”,对于物性与人性之讨论,必须站立在此,不然,人与物将俱失其性。那么,处于这种自然状态之下的人性,显而易见是一种不受外界干涉的、天生自在的、没有受到雕琢修饰的真实的存在。这种人性,若放在《老子》文本中去,就是老子所向往之“婴儿”状态。这种人性,本来无所谓善恶,自然不能以“性本善”或“性本恶”来简单描述,若一定要用俗世道德层面的善恶来衡量,只能如王安石所言:“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原性》)[1]316这样一来,便引出了“情”,而“情”与“性”,又皆是庄子议题。事实上,在春秋末期的老、孔时代,人性源起与何为本性的论题尚处在隐含阶段,往往包含于各家思想之中。一直到了战国中后期,由公孙尼子、告子等人最先对这些论题进行了系统性论述,心性问题从此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显明化的论题。[2]69
和众多儒者认为“性善情恶”不同,通过审视告子、庄子乃至后世王安石等人对于人性的论述,不难发现他们实际上都属于广义自然人性论者。但在人性论史上,人们往往基于孟子泛价值主义的思维,从而形成了一种单一化的人性论史观,这也就导致了庄子的“性情不离”说长时间地被边缘化,后世儒者又割裂了性与情的联系,使心、性、情三分后各自为政,从而产生了重视性而忽视情的不良后果。[2]67而先秦道家人性论从“真”出发的思考方式,显然不同于同时期的儒家人性善恶论,去后世宋明理学之论也更远。如果将这一人性之“真”剖开来说,无论老子还是庄子,对于人性议题的讨论大多围绕于在于人最自然的“心”“性”“情”三者而展开的,即人性之“真”或“自然”是一个展开过程,而不是像儒家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先天的结果。而“真”或“自然”实际上就是“虚玄”工夫展开的结果。所谓“虚”,就是空虚无累之自然无为状态;所谓“玄”,就是玄同深远,不能为世俗智巧所探视的本原。在“虚玄”工夫的世界之中,一切儒家所宣扬的仁义孝慈等道德价值判断的行为都应当中止,而先秦道家的人性论,正是以这种“虚玄”为中心建构起来的,这是一种超越于人文主义而至于宇宙主义的立场。
庄子在《庚桑楚》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3]250
道若有若无,不可得见,人之所见唯其外显之德,故曰“道者,德之钦也”,即“道”通过“德”来表现。但“德”是什么呢?德者,得也,得之于道者为有德。这是“道”与“德”之互释。如果仅限于此,我们依然不知道“道”与“德”的所指,所以庄子进一步把“德”与“生”接通,即“德”是生命(即人与物之生命)所展现出的姿彩与光芒,而所谓生命的姿彩与光芒就是生之本原,即人与物之性自身。这样,庄子通过道→德→生→性,这样一条线索,不但钦定了人之性,更把人性与“道”关联起来,从而奠定人性之庄严大义。这样一条线索依然让人感觉还是一种人为的设定的路线,但道家在实际论证的时候却是依据“心”“性”“情”三个层面展开的,从而体现了道家人性论的工夫实践及其建构。本文将在陈鼓应先生庄子人性论的基础之上,再结合老子的思想,对道家“虚玄”之心性论进行探讨,以期揭示道家以“虚玄”为中心的自然人性论之本质及其建构思路。
一 无始与有归——玄不可言之道心
《老子》第五十五章云:“心使气曰强。”[4]146可见,“心”不是气,但“心”可驱使气,说明“心”是比气更高的力量。《庄子·人间世》云:“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3]50这说明,“心”,乃承天地之气而成,实则是“道”之映射在人。故此,谈道家心性之学,须先从论“心”开始。《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4]1-2“常无欲”以观万物之始生(“无”以“始”),“常有欲”以观物之终成(“有”为“母”),而这两者又分别是更高一级的“玄”的两面。“玄之又玄”者,道也。上文既已言明“心”与“道”实际为一,那么道之玄远意即心之玄远,不可捉摸,不能定名,亦不可言,即“道”之玄通过“心”之玄来表现。“玄”意味着“心”不是一种固定的存在,“心”在工夫中存在。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心”就是“性”之极?王弼注“玄”:“冥默无有也。”[4]2既然“无有”,自然不可称之。所以“玄”是“不可称谓之称谓”,它仅仅是对于“道”的形容,而非某一具体事物的定名。[4]5物之极远曰玄,道又以玄为称,所以是极远之极,如果比之人性,便可以认为,心就是人性之极,真实人性自心生出,这意味着“性”亦当在工夫中存在。
《老子》十五章中提到:“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4]33对于“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一句,苏辙在《老子解》中作出以下注解:“粗尽而微,微极而妙,妙极而玄,玄则无所不通,而深不可识矣。”[5]剔除了粗陋之后才能得到精要的认知,当精要的认知发展到极点就能窥见神奇,神奇之极延伸至玄远之境,而玄远之境无所不通达,其深远如此。“心”与“道”一,“道”既“深不可识”,则“心”亦当“深不可识”。我们可以知道“情”之善恶,但显然不可能洞见隐于玄远之境的“心”,但道家认为,不能基于情之善恶而论人性,须基于“心”之玄远来认定人性,故道家盛言“道心”之玄远。玄远意味着非世俗之智能所能描述与定义,是以道家盛言“不言之教”“大美不言”等。
老子云:“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四十三章)[4]120又庄子之语:“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外篇·知北游》)[3]234道家尚“不言”,在老庄的论述中,常常出现“不言”“不可言”此类词组,试问,道家不可言而喻的是什么?“心”与“性”显然存在着衍生关系,“心”既然是玄远不可识的,那么当我们试图将它纳入人性之真的讨论中时,必须要找到讨论它的意义所在,即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一个除了生出“性”外似乎别无他用的不可见之物。
《老子》在全书开篇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可以言表的正是“道”,更进一步说便是所谓“常道”。而天地之周转,恰好合于这个“常道”,所以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外篇·知北游》)[3]227此处不言之大美,正是“道心”之大美,“静水流深”,因为“道心”虚静已臻于极致,故言辞不能达其意,所以不如不言。对于“道心”来说,“不可言”的沉默只是口的沉默,而非心的沉默,因为语言只能描述世界之内的事物,但很明显,“道”和“心”已经是世界之外的存在了。[6]或许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道心”之玄妙,非圣人不言,只是世俗之人不可与言之罢了,是无以言。
“道心”虽深不可识,但是人也无法将它从生命中剥离,它诚然多变且复杂,却不能因为这样而试图用“仁义”等去规范它,这样恰好是在扰乱作为人“性”之始与作为其母之“心”,是悖逆自然而有为,“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庄子·外篇·在宥》)[3]116,即丧失了真性。唯有“法道”,才能全“心”,而“道”不可言,故心有大美,藏之而亦不能言,唯有在工夫中体会也。
二 任自然之本——化类齐物之至性
如果像孟子所说人性本善,那么依据道家的立场,教育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仁义礼智反倒会加害天真的本性。在道家看来,需要教育才能达到的“善”并非真实之“善”,一旦受到外物影响,必然会发生改变。而如果真性是“善”,那么“善”就是此人真实之本性,不须教化,自然有之。善与不善,俱是人性之“真”。道家之所以向往“婴儿”“赤子”之类的状态,恰恰因为在此时展现出的是最真淳的人之本性,在婴儿眼中,世间万物并无种类的差别,一切事物都是同一的,这也就是庄子“齐物”思想之所由,是老子“复归”想要回归的境界。“性”比之“心”,已有了定名。但是“婴儿”阶段,本性尚未受到礼俗的习染,“天真”犹在[2]79,这当然是道家况喻式的讲法,并非谓只有婴儿才有人性之真,通过一系列的修行,我们也能够保持或者恢复到婴儿般的天真至性。那么,我们将如何保持或者恢复这种天真至性呢?
第一要义,就是要学会“和光同尘”。在老子看来,若人性通“玄”,那么人将“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老子》五十六章)[4]148。保守而除争,将无显、无贱,故无偏争偏耻,可得玄同。天下之所贵者,唯不可得而已。可亲者可疏,可利者可害,可贵者可贱,唯不可得,故无所失。若使人性之光与尘和同为一,那么品类自化,既无所偏颇,自然无所伤。也就是说,同于“玄”者,不受亲疏、利害、贵贱的影响,人性本为一,而贵贱亲疏恰好是老子所反对的强加于人的分别。[7]
人们常常看重美玉而轻贱砾石,但是若将它们比作人性之质,在道家思想中,二者皆非可取之性,原因就在于它们给予了别人来衡量自己价值的机会,却没有想过将自己与大化混同,就如同儒家的人性善恶论一样,将世俗价值强加于自然之性上,这可以称为失其本“真”。
“和光同尘”并不是将每个人的不同个性抹消,而是说人的自然本性实际上应该处于一种温和平齐的、对于外界没有分别心的本真的状态下。所以道家的圣人,方正而不高傲,有棱而不刺人,坦率而不妄为,光明而不耀眼,以仁义行之,非为行仁义[3]75。也就是说,道家的圣人从来不向世人标榜有形的仁义,但他们的言行举止无一不符合真正的仁义,他们不是拒绝仁义,而是不屑于持有“行仁义”之名。
第二步,在柔和了咄咄逼人的锋芒之后,老子提出了人性复归的方法——“绝圣弃智”(郭店楚简版本《老子》该句作“绝智弃辩”[8],但与王弼传世本背后所蕴含的中止人为的造立施化之思想基本相同)。老子多次提出得道至性之人不受人之驱使的观点,在《老子》三十二章中,他再次强调“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4]81。有为者有名,那么便可以设法令他们为人所用。而朴近于道,有无为心,故无名。想要近道,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有守朴。智勇巧力,皆可为臣;朴之为物,不偏于一事,人有余而我若缺,故不能使我为臣。我抱朴而无为也,物何能累我真?欲何以害我神?故能得道。
随着社会秩序的日趋沉沦,人性也开始了不可避免地异化,智巧盛行、物欲横流,人们“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庄子·外篇·田子方》)[3]215这也正是老子所说的“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4]43仁、义、礼等等道德规范不过是真正道德丧失之后人们采取的补救措施,扭曲了人的本性,是“丧真”的人性,使个体的独立的自我意识被消解,虽然儒家构建的社会秩序有着对群体的认同与关怀,但这无疑是对个性的压抑,使人性呈现出了“伪”的一面。[9]当道盛行于世时,人们不需要外在的礼仪来约束,却能够自然行之,当以“仁义”为仁义的时候,说明仁义已经开始坏朽,自然真朴之“性”也随之无处容身,于是道心将失矣。
所以,为了挽救江河日下的人性,老庄后学历数抛弃圣智、仁义、巧利后人性将会向自然“复归”,认为只有去除外在的一切巧饰,向内寻求心灵的安顿,才有可能使已经产生异化的人性重新恢复婴儿般平和真淳的原本状态,无殊类,物齐同,有智巧而不用,守素朴而不失,是为回归至性。
三 致虚静之极——素朴空虚之真情
人性只有一个“真”字,真善或是真恶,每个人外显的善恶都是真情之流露。先天的人性是最真实的,不存在伪装。善恶是人性定后而生的“情”的修饰词,但“性”却是自然造化,无法改变,不可逆转。所以,一个有着恶之“情”的人即使一时向人们展示出伪善的一面,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其真实的恶。因为各人所受不同,故此,先天之“性”虽同,但“情”各有异,这也正是“性”之真实。
庄子与惠子“濠梁之辩”,究其内涵,其实也是在辩一个“真”:我心有一感,是真;你认为我心中应有一感,也是真。那么,我心中此一感若是真,就与你所认为我的感知相悖;而你的这种认为是你的感知,应该也是真实的,但这样一来,“真”与“真”之间也有了不同,这似乎形成了一个谬论。其实,“真”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指代含义,就如同本文所谈的“性真”一样,“真”就是人性的初始状态,它并不代表着“善”“恶”之类的价值判断,所谓“性”之“真”实际上也就是“情”之“真”。但这个“情”不是世俗的“情”,而是“本情”。所谓“本情”就是本性之情,即除去了人为造作与欲望之后的情,即生于“性”之“情”。
“情”生于“性”,“性”生于“心”,“心”如同“道”,玄远而虚,其有若无,其无若有,也正是如此,才能为无穷之用。庄子在《渔父》篇中记录了一段渔父与孔子的对话,其中,当二人谈论到“真”的时候,渔父如此回答孔子:“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3]332
为什么说“真”是“精诚之至”呢?是非不必论而自有分,没有后天的伪饰,这就是“诚”。虽然儒家所强调的“仁”“义”之中也有“诚”在,但很显然,道家强调的道与德,更加突出了行为和情感中的真诚。[10]而我们不难发现,“诚”的特点与自然的部分特性一致,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诚的基础正是自然。道家之所以强调自然,所强调的恰恰是道与德的“真诚无伪、真实无欺”。
人既秉“道心”,那么人性显然就是道性,故而人的本性就是自然,就是“真”。“真”即是婴儿之“常德”,不须妆饰,最天真自然不过。所以,精诚之所以能动人者,在它乃是一种真实的“情”,能引起人“性”之共鸣,也可以说,真情所带来的是人之“性”的振动,从而触及更深远的“心”,“心”与“道”相通,然后可以从在天之“道”那里得到回响。前文提到的观濠水之鱼的自在使庄子获得了“乐”的体验,根据物我相通的道理,庄子才得出了鱼之“乐”的推论,这个过程便是移情的运用。[11]在这样的沟通移情的过程中,人本身就和天地化为了一体,“两忘而化其道”,那么我们便不妨认为,这便是道家所向往的“吾丧我”的状态在现实中对待化思维的消融与物我一体、物我交融思维的充分彰显。也正在这个意义上,才会有庄周梦为蝴蝶的故事,也才会有庄周妻死,鼓盆而歌的可能性。
从老子的“上德若谷”(《老子》四十一章)[4]112到庄子的“唯道集虚”(《庄子·内篇·人间世》)[3]50,我们可以捕捉到道家对于道与德的一个重要定义——“虚”。庄子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论点:“虚室生白”(《庄子·内篇·人间世》)[3]51。他在此处将人的情与性所居之“心”同人生活起居的“室”类比,如果一间居室中满是杂物,必定会显得昏暗拥挤,而心也是如此。只不过,使居室灰暗狭窄的是凌乱繁多的杂物,使心昏昧的却是充满了伪饰的“情”。当情之“真”隐去后,人性也将会随之而变。不过,与其说人性“变”,不如用“藏”更加妥当,伪情横生,自然之人性必会被掩藏,但是并不会消亡。
显然,老子提倡的“复归”,便是一种“去伪存真”的方法,向人生之初的婴儿状态追溯,就好像清理掉室中尘芜一样,由繁入简,摒弃一切机巧、施为,从“有”再回归于“无”,而此时,情与性居留的“心”所又已恢复了虚空玄远,自然生出一片澄明。这一翦除心中邪妄的方法,道家称之为“内视”,至于“内视”的目的,一则在复性,一则在体道。
针对如何“复归”,庄子有“坐忘”说。这是一个超越“有”之境而达于“无”之境的进程,层层递进:先忘礼乐等外在规范,然后忘仁义等内在要求,最后“离形去知”,消除了身心的双重束缚——是谓“吾丧我”——如此一来,人可以同于大通,与天地并生。[2]41超越了虚伪诈巧的“我”,在不间断的超越过程中逐步接近大道,当最终超越人自身与此身所处现实的束缚之时,真实的“吾”也就脱离了智巧盛行的人间世,抵达了逍遥无待的自由王国。
由此可见,道家对于人性的看法,大致可以总结为这样一条线索:性生于玄远空虚之心,本来是任自然、齐万物的体道状态,但性之下又生情,而情在世俗世界常离开性而不受性之规导,故初真而后伪,这样,自然之性因世俗之情的表现而隐蔽,唯有涤除情之“伪”,还复其“真”,方能复自然之至性,虚静极笃,才可以得于道。
结语:唯真是性,唯虚通玄
玄者,心也,道也。虽有大美,但不可言与人。这就是庄子所说的“知道易,勿言难”[3]337。人性之真,岂言辩之巧能道哉?既然不能言,不可言,那么智巧将无用,若人能弃小智淫巧而守其真性,因而成之,则可以与万物混同而不特出,扫除尘芜,最终使心灵达到虚静的境界。当“虚玄”已在其位时,人性的真美也必将在这一时刻显现。唯真是性,唯虚通玄,老庄人性论本乎自然而立,以“玄”“虚”为表征,通过对不可言之道心的求索,不断将人们引领至其所向往的逍遥之境——“无何有之乡”。此处可体“道心”,可得“至性”,可表“真情”,是为“道德”也,以今人之语言之,则可谓“自由王国”也。
[1]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316.
[2]陈鼓应.庄子人性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7.
[3]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4.
[5]苏辙.老子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11.
[6]韩林合.虚己以游世——《庄子》哲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7.
[7]汪韶军.老庄自然和谐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62.
[8]彭裕商,吴毅强.郭店楚简老子集释[M].成都:巴蜀书社, 2011:1.
[9]魏涛.“真化”和谐对“礼化”和谐的超越及其意义——和谐视域下传统道家“真人意识”的反观与激扬[J].兰州学刊,2011(2):14-17.
[10]罗安宪.儒道心性论的追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30.
[11]王泽应.自然与道德:道家伦理道德精粹[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275.
B223.1
A
1673-2219(2020)06-0052-04
2020-05-18
李秀倜(1997-),女,蒙古族,河南洛阳人,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