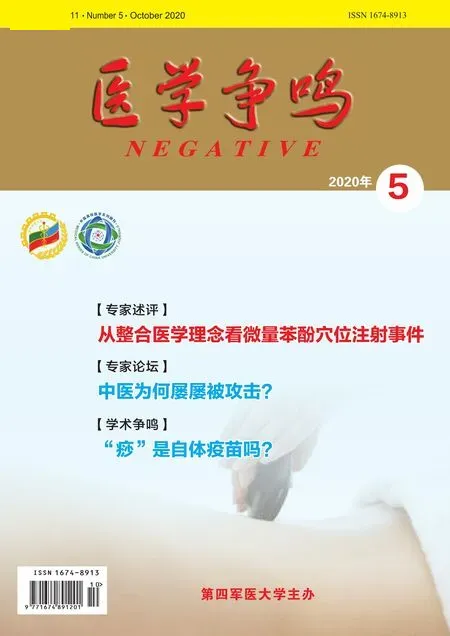国防生物科技的概念界定及发展建议
2020-01-05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卫生勤务与血液研究所卫生勤务研究室北京100850
徐 立(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卫生勤务与血液研究所卫生勤务研究室,北京 100850)
近年来,我国仁人志士相继提出“制生权”“制脑权”“制智权”等生物制权理论和以强生、仿生、防生、创生、再生为核心的“五生工程”[1-4],对国防生物科技的地位和作用鼓与呼,对以国防生物科技为先导的生物化军事革命进行战略研判。国防生物科技一词提出已有一段时间,但什么是国防生物科技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对国防生物科技的内涵与外延还存在许多模糊认识,国防生物科技研究的主体和发展策略亟待明确和统一。
1 界定国防生物科技概念面临的问题
界定国防生物科技的概念,既要直面和澄清对生物科技的模糊认识,又要考虑国防生物科技外延动态发展变化的特点。
1.1 国防生物科技研究主体错位
目前,提出、研究和倡导国防生物科技的绝大多数是军事医学研究人员,他们高瞻远瞩,看到了生物科技在国防领域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大力呼吁和倡导国防生物科技,这是有利于国防生物科技发展的,但也有不正确的认识,部分军事医学领域的倡导者将国防生物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视为已任,并试图将国防生物科技发展作为军事医学研究机构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和目标,偏离了军事医学研究的任务和方向,亟须指出和纠正。
军事医学是研究在军事活动中鉴定、保护、恢复和促进军队成员健康的理论、技术和组织方法的特种医学,是医学与军事学的交叉学科[5]。其中与生物科技关系密切的是生物武器的医学防护、生物医药。国防生物科技则是以战斗力生成和提升为目的,能催生新型作战空间、作战理论、作战力量、武器装备。所以,军事医学中应用生物学原理及技术、手段、材料开展生物武器防御、人体效能增强、意识干预研究及应用的内容属于国防生物科技范畴,其他主要用于伤病防治的普通生物医学技术不应纳入国防生物科技范畴。
军事医学研究人员掌握基本的生物学知识和技术,可以为国防生物科技发展提供基础的科技支撑。但是,生物医学只是生物学的一部分,并不能涵盖全部生物学。此外,军事医学毕竟是以伤病救治、健康维护和能力促进为基本任务、以军人健康和伤病为研究对象的,军事医学研究不能将国防生物科技发展中与军人健康和伤病无关的内容纳入研究对象和范围。国防生物科技很重要,军事医学研究人员可以呼吁和倡导,但不应该将国防生物科技发展全部视为己任,否则就会导致军事医学发展偏航。道理极其浅显:军事医学应该以研究治病救人为天职,而不能以研究作战为工作重点。
1.2 对生物科技的认识存在误区
界定国防生物科技的概念,难点和重点不是哪些生物科技能在国防领域应用,而是目前对生物科技的认识产生了较大分歧,存在将生物科技概念泛化和滥用的现象,将凡是与人、脑、生物相关的科技,甚至只要出现“生”“智”的字眼,如仿生、人工智能等,均纳入生物科技,无限制地扩大了生物科技的范畴,夸大了生物科技的作用,不利于聚焦未来国防生物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也突破了对生物技术的常规认知[6]。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2.1 突破对现代生物技术的认知常识 事实上,对生物技术已经有约定俗成的解释。1982年,国际合作及发展组织将生物技术定义为[7]:生物技术是应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原理,依靠微生物、动物、植物体作为反应器,将物料进行加工以提供产品为社会服务的技术。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目前一致公认的现代生物技术[8-11],是指人们用现代生物科学、工程学和其他基础学科的知识,按照预先的设计,对生物进行控制和改造或模拟生物及其功能,用来发展商业性加工、产品生产和社会服务的新兴技术领域,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胚胎工程、酶工程、蛋白质工程和发酵工程等。现阶段的生物技术大致可分为两大体系:一是生物的直接利用,即生物控制和改造技术;二是生物模拟技术。生物模拟技术包括生物机体和功能模拟技术,如用复合蛋白质构成的生物芯片,以及人工合成生物系统技术,如人造血液、人造细胞。1986年国家科委制定的《中国生物技术政策要点》明确指出,不能把传统农业和畜牧业都划入生物技术范畴。可见,生物技术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利用生物学的工程、技术、手段、方法、材料;二是对生物体(或者生物组织、细胞及其组分)的控制、改造或模拟,或是以生物体(微生物、动物、植物)作为反应器,对物料进行加工。这两个必备要素缺一不可。目前存在一种模糊认知,认为认识、模仿、保护、改良、杀伤、治疗、控制生物体或器官、组织、细胞的科技,即所有与生物有关、与人沾边的科技,都是生物科技,这显然是错误的。
1.2.2 把非生物手段的仿生学应用纳入生物科技 另一种模糊认识就是把生物科学原理、规律的应用,即仿生技术全部列为生物技术范畴。事实上,仿生学本身是一门交叉学科[8],涉及的科学领域极广,已经衍生出许多分支学科,如仿生电子学、航空仿生学、仿生化学、建筑仿生学和人工智能,等等。仿生学主要是研究生命物质的结构、能量、信息,特别是研究生物如何接受和加工处理信息的生物控制论, 为人-机系统、人造器官、人工智能等创造发展条件。仿生学研究需要生物学家参与,但是,仿生学并不全部属于生物学范畴。1995年中国科协主编的高技术丛书《生物技术》[11]明确指出 “至于用非生物材料为主模仿生物系统的人工器官、假肢等,属于生物医学工程的领域,而超出了生物技术的范围”。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利用生物材料、生物学手段方法对生物体的模仿才属于生物技术。例如飞机、声呐、雷达等均利用了仿生学原理,但飞机、声呐、雷达等在生产、制造及原材料使用上却没有应用任何生物技术,因此,我们不能称鸟类飞行的空气动力学原理、蝙蝠的回声定位原理等物理学原理为生物科学,更不能称飞机、声呐、雷达是应用生物科技的结果,如同我们不能称模仿草叶齿形边缘发明的锯子是生物科技应用的结果一样。因此,单纯利用仿生学原理,而在最终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及原材料使用上,未使用生物技术或生物材料的,不能称之为生物科技。
1.2.3 把非生物手段的脑科学应用纳入生物科技 随着脑科学的不断发展和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的崛起,神经科学家们正努力把脑科学研究向细胞和分子水平发展,产生了分子神经生物学、细胞神经生物学、系统神经生物学、行为神经生物学,以及认知神经生物学。但是,认识脑、模仿脑、控制脑不仅包括了生物学方法,还包括了大量其他技术手段,如号称脑科学四大技术、能在无创条件下研究人脑认知功能的经颅磁刺激、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术、脑磁信号,其中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术可以识别大脑思维信号,实现“读脑”,脑磁信号则是脑机接口输入信号的重要技术,可实现“脑控”,但这四大技术利用的均是物理学原理和方法,因此,也不能称这样的脑科学技术为生物技术[9]。同理,被很多人标榜为国防生物科技应用典范的控脑武器,如电磁波武器、声波武器和光波武器,均是使用物理手段控制大脑(生物器官),显然也不属于生物科技的范畴,否则,就可以类推出杀伤人体的普通枪炮也是应用生物科技的结果这一非常荒谬的结论。但是,利用生物技术研发的控脑药物、利用生物体产生的生物磁场对大脑进行的控制,则属于生物科技。因此,不能笼统地称脑技术就是生物技术。
1.3 国防生物科技的外延动态发展
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一样,具有高度的军民两用性,生物科技在科学原理、技术方法层面不存在军民之分,主要分别在应用层面。某项生物科技是否能应用于国防领域,取决于该项科学技术是处于萌芽阶段还是重大突破阶段,往往某项技术取得重大进展或突破关键瓶颈问题后,其应用领域也将随之大大拓展。此外,由于人类认识上的局限性,目前,生物科技在国防领域有明确应用前景的只是一小部分。但是,随着生物科学的不断发展进步和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生物科技在国防领域的应用范围必将不断扩大。某项生物科技在现阶段未发现其国防应用价值,但未来却有可能应用于国防目的,也就是说,国防生物科技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因此,界定国防生物科技的概念,必须坚持开放和动态发展的理念和原则,不能一成不变。
1.4 部分国防生物科技需发挥集合作用
实现某项国防应用目的和价值,有时需一类或多类生物技术共同发挥作用,虽然单独某项生物技术的应用无法看出其国防应用目的,但多项生物技术应用的项目累积叠加,却能够实现国防价值,则这一类或多类生物科技均属于国防生物科技。例如,单独的碳水化合物高效合成、固体废物快速转化利用等生物技术项目,无法看出其国防应用价值,但是多个这种生物技术项目即可实现构建新型生物圈的目的,因此,需将一类或多类生物技术同时纳入国防生物科技范畴,这也给界定国防生物科技带来了一定难度。
1.5 把国防生物科技视为多学科交叉
有人认为国防生物科技是将现代生物科技与军事、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等领域交叉融合,应用到国防领域的综合性科技[10]。可以看出,这一界定较为宽泛,过于强调生物技术而忽略生物科学的应用,未能突出和把握生物科技的本质规律和特征,强调国防生物科技是与军事、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等交叉融合的一种综合性科技,也未能突出生物科技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事实上,任何一种科技的发展都离不开其他学科的支持,例如,生命科学研究不但依赖物理、化学知识,也依靠其提供的仪器,如光学和电子显微镜、蛋白质电泳仪、超速离心机、X-射线仪、核磁共振分光计、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等,但我们不能称这些仪器设备为生物科技应用的结果。
2 界定国防生物科技概念的基本原则
2.1 尊重科学共识
国防、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均有公认的、较为权威的定义,国防生物科技的概念必须符合对国防、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的界定和科学共识,而不应无限制地缩小内涵扩大外延,特别是生物交叉领域,必须是以生物科技、材料在国防领域的应用占据主导地位才能纳入国防生物科技。
2.2 注重实际应用
界定国防生物科技的概念,应以是否具有明确和潜在的国防应用价值作为判定标准和遴选条件。比如,判断某项生物交叉技术是否是国防生物科技,除了判定某种武器装备研制是否应用该技术,还必须强调生物科技和生物材料的应用比例、阶段,以及是否能在国防领域产生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新材料、新工艺。
2.3 坚持军民融合
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一样,具有高度的军民两用性,生物科技在科学原理、技术方法层面不存在军民之分,主要分别在应用层面。因此,界定国防生物科技必须坚持军民融合原则,将生物科技民用研究纳入民用范畴,国防生物科技重点关注其在国防领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2.4 坚持动态发展
由于认识的局限,目前,生物科技在国防领域有明确应用前景的只是一小部分。随着生物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和人类对生物科技在国防领域应用认识和意识的不断提升,现在没有明确军事用途的某项生物科技,未来极有可能应用于国防领域。因此,界定国防生物科技的概念,必须坚持开放和动态发展的原则,不能一成不变。
3 国防生物科技概念的界定
界定概念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界定概念的内涵,即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共同本质属性,二是界定概念的外延,即概念所指的一切对象的范围。一般情况下,对概念的界定主要是明确概念的内涵,而对概念的分类,则可以明确概念的外延,而且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从不同角度反映概念的外延。
这也是对国防生物科技这一提法质疑较多的一点。事实上,任何一种科技在科学原理、技术方法层面均不存在军民之分,主要分别在应用层面,如同核技术,应用于核电站,就是民用技术,而应用于核武器,则是国防技术,至今也没有国防核科技的提法,信息科技催生了信息化军事革命,但同样也没有国防信息科技一说。但是,我军却有军用技术的种概念,以及军用生物技术、军用雷达技术、军用直升机技术、军用隐形技术、军用新材料技术、军用导航技术、军用计算机技术等属概念,但是,军用(事)和国防也不是一个层级的概念,国防不仅限于军事,还包括与军事相关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因此,从国防科技这一种概念来界定国防生物科技的内涵并不科学。
为澄清当前对国防生物科技的认识误区,在把握概念界定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将国防生物科技定义为:以生成和提升战斗力为根本目的,具有明确或潜在国防应用前景及价值,作为主要原理、方法、技术或材料,保护、改良、杀伤、治疗、控制有生作战力量,创新武器装备研发和控制的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群的统称。
3.1 国防生物科技的基本内涵
国防生物科技以促进新质战斗力生成为根本目的,能够催生新型作战空间、作战理论、作战样式、作战力量、武器装备[11-12]。
国防生物科技的核心是生物科技在军事及与军事相关领域的实际应用和针对性研究,只要在或能在国防领域实际应用的生物科技就可纳入国防生物科技,如核物理一样,应用于核武器、核动力武器装备则是国防核科技,应用于核电站、核医学则是属于民用核科技。
国防生物科技是一个集合概念,以生物科技的群体为对象,而非单纯某项生物科学技术的应用,也表现为多项生物技术综合运用才能达到某种国防目的。
国防生物科技是动态发展的,包括有潜在国防应用前景和价值的生物科技。
3.2 国防生物科技概念的外延
从国防生物科技应用范围来区分。
在作战理论方面,国防生物科技将重点研究在细胞、分子、基因等微观和超微观层次形成的新型作战空间、作战样式和制权理论。
在武器装备方面,国防生物科技将重点关注脑控控脑、脑脑通讯、新型仿生武器,以及新型生物材料在武器装备上的应用。
在作战力量方面,国防生物科技将重点研究新质作战力量建设,如利用生物技术进行人体机能改良的超级战士、改良驯育的动物部队等。
在生物安全领域,国防生物科技仅局限于军事生物安全,即以输入性传染病疫情、传统生物战剂,以及人为改造和制造的生物武器防御为研究对象[13]。对于普通的实验室生物安全、内源性传染病防控,则不宜纳入国防生物科技范畴。
在军事医学领域,国防生物科技仅局限于对核化生武器所致伤病,以及其他常规武器和新概念武器致伤的防治,不包括防治普通伤病的生物医学。
4 国防生物科技发展建议
厘清国防生物科技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国防生物科技的科学发展,建议如下。
4.1 国防生物科技评价要坚持客观公正
当前,正处于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前夜,中国科学院专家预测,未来科技革命将以生命科学为主导。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科技发展正处于大交叉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信息、生物、纳米、量子等前沿科技相互交叉融合发展,我们不能因为要研究国防生物科技,就片面地强调它的重要性,而忽略其他科技的地位和作用。制定国防生物科技发展战略,要找到主战场,占领主阵地,突出生物科技的主体地位。例如,虽然我军正在大力研究和发展军事智能,但实际人工智能研发中,生物学所作贡献的比例并不高。《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6》指出,人工智能的四个细分领域与计算机科学、逻辑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紧密相关,而与生物学的相关性历年来均最低。因此,对于不是以生物技术、生物材料为主要方法手段的生物交叉项目,应当由其他学科牵头,在研究过程中适当引进生物学研究力量,而不能以生物学专家为主牵头实施人工智能、生物计算机、武装机器人的研究,在这些领域,要强调生物科技的服务和服从的配属地位,不能喧宾夺主。
4.2 国防生物科技部署要坚持国防应用导向
当前,国防生物科技应用主要局限于生物医学范畴(生物武器防御),而国家和地方的生物科技发展则十分迅猛,领域之广、水平之高,远远超过军队。以脑科学为例,国家在脑控假肢、精神病患者的干预治疗等方面成果显著并已投入实际应用。因此,普通意义上的认识脑、模仿脑,以及以精神疾病防治为目的的保护脑等脑科学基础研究应依靠国家优势科研力量,不再纳入国防生物科技;纳入国防生物科技的脑科学应集中精力解决利用生物科技保护脑(防止敌军意识干扰)、增强脑、干扰脑等具有明确军事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实用方法手段装备的研究,要善于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已有技术手段方法,高起点、高标准,不能从零起步。
4.3 国防生物科技应用要注重科技创新驱动
借鉴国外经验,国防生物科技可广泛应用于武器装备研制、军用生物能源制造、人体效能增强、生物战防御等国防领域,但是,对于任何一种颠覆性科技而言,其最大的价值和应用前景在于对未知应用领域的探索和尝试,产生我有你无的新型作战理论、作战样式、作战装备,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不对称优势,处于领跑地位。目前,我国已经开展或计划开展的国防生物科技研究,均属于国外已经有明确军事应用导向的,是跟跑。主要原因在于,对新兴的、前沿的国防生物科技而言,传统的以军事需求为主导,即让部队提应用需求已经无法发挥应有作用,不熟悉生物科技的官兵、专家无法提出在哪些军事领域应用、哪些装备上应用,必须依靠生物科技本身推动国防应用。因此,生物科技在国防领域的实际应用需求,必须由掌握生物科技的专家提出,这最终取决于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专家是否具有强烈的国防意识,能否敏锐地洞察到其潜在的军事应用价值,正如将核裂变技术应用于研制核武器,只能由核物理学家提出一样。目前,生物科技在我军重点应用于生物武器防御、战创伤救治等领域,很少应用于研发武器装备、改良作战力量、创新作战理论,既有对生物科技在国防领域应用的重视不够,也有绝大多数掌握生物科技的专家,不熟悉部队、不熟悉装备、不熟悉作战,无法提出国防生物科技的应用需求;而绝大多数武器装备、军事理论专家又缺乏利用生物科技的思维和意识,极大地限制了国防生物科技的应用领域和实际发展。因此,建议设立专门的国防生物科技研究机构,并在传统军工科研、生产机构增加生物学专家,搞好生物学专家与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的有机结合,培养生物学专家的军事理论、技术素养,使其全程参与国防科研项目的选题、论证、实施和验收评估,确保生物科技全面应用到国防工业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