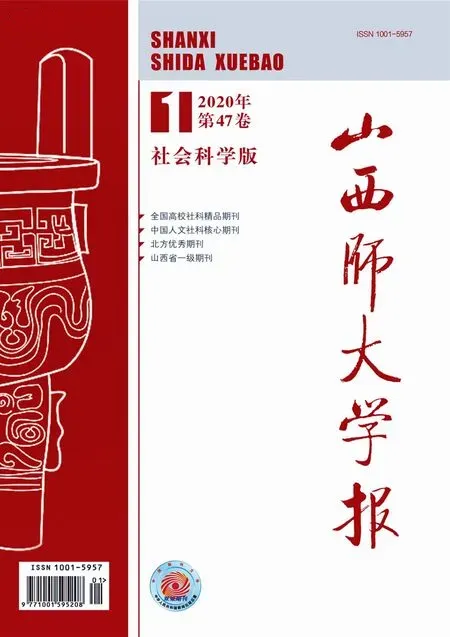历史辩证法是唯物史观活的灵魂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辩证思想解析
2020-01-03孙琳
孙 琳
(南京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95)
一
把马克思在著作中指出的“具体与抽象”“理论具体与理论抽象”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抽象—具体”辩证法,并将其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实际上是苏联教科书的说法,我们还需要进行更深层的思考。笔者不认为这是一个完整的表述。它也许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还不是历史辩证法。正如张一兵教授指出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并不等于他的历史辩证法,而只是辩证法分析的一个特殊环节。”[1]590因此,尽管它看起来确实具有一个过程,但是因为它的终点还是在于理论、理性,这就意味着它根本无法完成一个完整的历史的辩证的逻辑过程,也无法把握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真实意图。它虽然具有类似于辩证法中某种环节的意义,但是如果仅仅据此就把“抽象—具体”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完整表现,那就依然是在马克思所批判的在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无限的黝黯”中绕圈的伪命题。马克思对“具体—抽象”与“理论抽象—理论具体”这两条道路究竟是如何看待的呢?
首先是第一条道路:从具体到抽象。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并非毫无保留、全盘否定了这种方法。这个方法由于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因而马克思没有对其作出“科学”方法的正式判断,所以这可能会引起一些误会。马克思为何不对其作科学方法的论断呢?因为这里的“具体”特指现代形而上学的“具体”,因其缺乏社会历史性、反思性,充其量也只能是“表象”“直观”,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在内的“具体”都不过是“伪具体”。但是,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要把它丢弃到历史的垃圾桶中。马克思的意思是:如果脱离了处于交往之中的主体际的历史实践和由实践形成的社会关系来谈论“具体”,无疑是形而上学内部的“表象”“直观”。例如“人口”这个经济学中的“具体”,如果脱离了“人口的阶级”及其所依据的社会现实因素“雇佣劳动、资本”等,那也只能是稀薄的抽象和空疏的理智。而“雇佣劳动”“资本”等必须以“交换、分工、价格”等范畴为前提,否则还是空洞而混沌的“表象”。从根本上来说,这无非是从一个主观的无限性到另一个主观的无限性,黑格尔批判其为“坏的无限性”,并且通过思辨的辩证法对社会历史的客观化进程来为这种“坏的无限性”解毒。马克思对于“具体—抽象”究竟持何种态度,其实在原典《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不难找到答案。“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2]24究其原因,在于它缺乏了一种置身性的交往主体际的历史实践的视域。马克思的意思很清楚,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2]24。马克思谈论“交换”“分工”“阶级”范畴高于“人口”范畴,正是因为前者指出了“具体”——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工人劳动造就的庞大的异己力量对自身形成的统治的结果,而后者只能是越来越稀薄的“表象”的“规定”,而非对“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现实本身的“抽象”。所以马克思并未认可从简单的、无主体、无社会的“表象”到稀薄的“抽象”是科学的方法,那只是传统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所走过的道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不会是这种方法。“具体”,是现实的“起点”,同时是思维的“终点”。思维回到的“具体”不再是简单的、无主体、无社会的抽象的和空疏的“表象”。所以传统形而上学从空洞的“表象”开始的道路从一开始就不是科学的方法。
因此,这并不意味着从“具体—抽象”就是错误的方法。它有合理性。关键在于如何辨析平时说的“具体”,它必须区分清楚究竟是现代形而上学所说的“表象”,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说的“具体”。“表象”“直观”,由于缺乏社会历史性和实践反思性,因此“表象”不是“具体”。马克思的“具体”,是从置身性的历史实在主体的交往实践活动(也就是“史”之内涵)中产生的,它具有现实之根,以“铁的现实性”为抽象的根基。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生产一般”,“生产力概念与生产关系概念的辩证法”的观点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五个分篇的依据所在。关于这种合理性抽象,有几个典型的例证。
第一个例证是“生产一般”。马克思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2]9可见,抽象不是毒药,它也具有合理性。如果缺乏合理性抽象,那也无法谈论历史现实的发展,“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2]9只有把“生产”的概念从现实历史中抽象出来,才能发掘其中的“异化—物化”根源,也才能走向超越“异化—物化”的发展道路。
第二个例证是马克思对“生产力概念与生产关系概念的辩证法”的肯定。因为这合理抽象使即便是作为抽象的“概念”出现的辩证法也可以“不抹杀现实的差别”[2]34,因为合理抽象来源于现实的差别,并能够进一步确定现实的差别。
第三个例证则是五个分篇的依据。第一篇是作为“理论一般”,“理论抽象”出现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32。进而上升到第二篇的“理论具体”,即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依据”的各“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三篇则是对这种“理论具体”的科学性,即普遍性的论证。这五篇前后逻辑是一致的。接下来的笔记本[M-21]中列举的几个“范畴”,再次与此五个分篇相呼应。第一个范畴是“生产”,正是在高度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角度来统摄全篇。从“生产”范畴到各种“关系”范畴的进展并不存在逻辑的断裂,它们由矛盾辩证法推动,发掘了生产从异化到超越异化的道路是一致的客观规律,辩证法的根本要义就在于这种从自身出发(“生产的一般”)的自身超越性(“一般的生产”),这正是合理抽象的科学性所在。可见,马克思同样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的抽象方法。在此科学的抽象方法下,才能形成理论抽象(理论一般)——哲学——唯物史观;此后的“抽象—具体”则形成了理论具体——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定资产阶级社会的唯物史观。可以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普遍规律及其方法论参考,后者则进一步在具体的现实社会中运用前者方法论并印证和实现前者的普遍规律。两者之间是逻辑一致的,不可强行割裂其内部的这种抽象与具体的联系。因此,从“具体—抽象”的辩证法也是历史辩证法的一个特殊环节,但不构成完整的历史辩证法。在此,我们不得不感叹,马克思用词之精准。因此,他说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而不说把现实的“具体”蒸发为合理的“抽象”。
其次是第二条道路:从理论抽象到理论具体,同样典出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事实上,马克思在黑格尔幻觉之后的一段论述更为重要,其实也就四句话。第一句,提出问题:“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2]25说到底,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统摄者“概念”,在马克思眼里,是外在的、凌驾的,尽管能够自我产生的,却是与真实的现实具体毫无关系的。因此,从“概念”而来的“理念”尽管被定义为具体的差异性同一的全体,但是“理念自身本质上却是具体的,因为它是自己决定自己,从而自己实现自己的(自由)概念。如果概念,作为理念的原则,仅被当作是抽象的统一,而不是像它本来应该那样,被认作是经过否定的过程而回归其自身的主观性,那么,理念也只会是抽象的形式。”[3]400由于理念只能是“形式”,因此,黑格尔替代了“坏的无限性”的“真的无限性”也同样无法产生真正的“具体”。马克思指出,“具体”总是在“把直观和表象加工为概念”的过程中产生的,既然是过程,那就离不开实践参与,否则就不仅仅是“形式”,而且还只能是“抽象的形式”。因此,“具体”必须产生于真实的社会实践。但是实践也不是自明性的概念。到此为止,马克思的文字中似乎依然是关于思维具体的内容,思维具体也就是理论具体、具体总体。很明显,这只是必要的部分或环节,同样不能完整的代表着马克思思想的历史辩证法。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思维具体(理论具体)来源于何处?它不是自发产生的东西,也不是概念的捕获物,更不是一个终点,因而借此架构所谓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也仅仅局限在理论实践的范围内。
接下来的第二句话,马克思给出答案:“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整体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2]25因此第二句同样地但是更为明显地针对黑格尔以“精神”统治世界,进而形成绝对的“理念”的思辨观点。如果离开黑格尔哲学的专有术语来看待马克思的思想,那么就容易发生理解上的偏差,甚而如某些西马学者那样得出两个马克思的结论。事实上,无论是肉身还是灵魂,都只能有一个马克思。马克思在此再次很明确地提出与这种“精神”掌握整体世界不同的是,头脑以“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那么,什么才是“专有的方式”呢?
第三句,正是回答了以哪种“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的、理论的活动着。”[2]25—26可见,在此最为关键的部分才浮出水面,不是理论抽象与理论具体,而是“实在主体”。“实在主体”,完成了黑格尔式的以头着地的“实体即主体”的倒转。正如吴晓明教授指出的:“《资本论》方法的本体论基础是‘实在主体’(即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正是这一基础拒绝各种形式的‘外部反思’,而要求面向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并由之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之中。”[4]实践是实在主体的自我活动,在此基础上置身性的交互主体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如果真的有“实体即主体”,那不是“绝对精神”,也不是“类本质”,而只能是“实在主体”,即具有场域置身性的、历史的、现实的、交往实践着的实在主体,是在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的交往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主体。马克思有时把主体直接概括为社会,原因也在于此。“实在主体”,作为“实体即主体”,在“理论抽象”——唯物史观阶段,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来,此时再次提出,证明了马克思前后逻辑并不是割裂的。把同一个理论的普遍环节与特殊环节拆开,那是阿尔都塞的做法,就此而言,恐怕他不仅没有理解马克思,同样也没有理解黑格尔。把只有强大的历史才能支撑的辩证法牵引回实证的新知性科学之中,仅凭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科学的方法”就能完成所谓的科学的论证吗?这是抽象空洞的理智的虚弱病态的表现。
第四句,马克思便进一步挑明了这种思与史的辩证关系,至此才具有了完整的辩证法视域:“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26“主体”与“社会”必须作为“表象”的前提。“主体”作为何种向度才能是“社会”呢?第一,必须是面向社会的“实在主体”;第二,必须是面向社会的“交往主体”。现实的、交往着的社会主体及其在交往实践中构成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仅仅是人的本质,更是所有“表象”“直观”“理论”“理性”的“前提”。即便是马克思自己的“理论抽象—理论具体”,也必须以此为前提。
二
在“抽象—具体”辩证法中的最高环节“理论具体”,是“有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是现实的起点,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但是在思维中它只能是“综合的过程”,并且只能“表现为结果”。[2]25这意味着,“理论具体”再具体,也是有前提的,因此,“理论具体”只是一种历史实践的出发的思维的结果。
事实上,造就“具体”“现实”范畴的功臣首推黑格尔,无需否认,从“具体到抽象,再从理论抽象到理论具体”,实际上体现的也是黑格尔的逻辑理路。如果不能理解黑格尔,也就无法懂得马克思。逻辑学从潜在的“纯有”(又译“存在”Sein)开始,精神现象学则从“感性确定性”开始,一步步地实现了存在的真理即本质,本质的真理即概念,概念的真理即绝对理念。这是黑格尔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思维模式。然而,概念在实现其真理即“绝对理念”后就从未停止过,它还有更多重要的任务,比如它必须又返回和深入到“现实”的各领域之中,用以指导各种具体的现实的“理论具体”,以实现概念的使命。各种应用逻辑学,例如法哲学、精神哲学、历史哲学、自然哲学、宗教哲学等,展现的正是从理论抽象到理论具体的思维模式。这样,康德知性范畴的辩证法中的“单一—多数—全体”“肯定—否定—限定”“实体—因果—协同”“可能—现实—必然”的范畴辩证法三部曲在黑格尔的逻辑演绎中获得了历史的、现实的展现。实际上,西方哲学几乎都是这一思维模式,先从不具有社会历史性的事物的“表象”“直观”开始,一步步把“概念”和“一般”从“直观”和“表象”蒸发出来,而后再把在前一阶段形成的“概念”和“一般”的“理论抽象”具体应用到各个部门学科之中,形成一种“理论具体”。有的哲学家自始至终也没有完成第一步,例如胡塞尔,终其一生都在建构现象学方法的“理论一般”,他也计划再将这个“理论一般”付诸各个部门学科,然而在速度上未能跑赢岁月。在胡塞尔之后,马尔库塞写作了《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导言中直接点明了将现象学运用于存在领域的重要性;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交互主体”“生活世界”等概念也与晚期的胡塞尔密切相关,使之与社会交往的合理性相结合;在现象学与神学的结合方面,更有以海德格尔(1)1927—1928年,海德格尔曾两次以《现象学与神学》为题作报告,并在1964年将此文合并另外一篇论文《今日神学中一种非客观化的思与言的问题》进行发表,题目依然是《现象学与神学》。为首要创始人之一的现象学神学学派,影响深远。可见这一思维模式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
无疑,马克思在吸收了思辨辩证法的“理论抽象到理论具体”这一科学的以及必要的环节。与此同时,他对此进行了批判性超越。他批判黑格尔“陷入幻觉”,只重于构建理论体系,而把真正的现实抛诸脑后。把真实的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结果”[2]25,而不是“实在主体”的自我活动本身。由于“理论具体”的本质也是一种表象、思辨,因此马克思自始至终也未曾说过“理论抽象到理论具体”就已经是历史辩证法,它仅仅是在理论模式中的“科学”方法。上世纪60年代西马界爆发的科学与意识形态之争,也是因为同时存在着思维模式中的科学方法和社会历史现实之中的历史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没有辨明。如果不能把握马克思的理论逻辑,那么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且难以辨明的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已经形成了唯物史观的逻辑体系,我们可以说这是“理论一般”。在《伦敦手稿》《资本论》中,则是把广义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形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具体”“具体总体”。尽管逻辑理路与黑格尔相似,但是起点与终点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置身性的“实在主体”的自我活动构成的社会交往实践替代了“绝对精神”。尽管马克思自称是黑格尔学生,表明他对辩证法在某种程度的认可,但是逻辑起点与终点的转换决定了他与黑格尔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的本质区别。如果用总命题的视角来分析,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抽象”的总命题是“感性的人的感性活动”,不再是形而上学般的无休无止的解释世界,而是为了创造世界。感性的人的感性活动,就是置身性的“实在主体”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这一点在1845年就已经被马克思承认。“改变世界”是唯物史观的口号。马克思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工作多集中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何不继续唯物史观研究呢?是不是因为他的研究视域变化了呢?并非如此,这是从“理论抽象到理论具体”转变的需要。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具体”,它深入到资本社会现实之中,探讨置身性的“实在主体”在社会交往实践活动中的自我压迫、自我异化的原因所在。马克思尽管此时很少提及异化,但是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在谈论历史场域中“异化”的根源以及超越历史异化的必然性的原因,进而把“异化”深化为“物化”。哲学视野中的总命题“感性的人的感性活动”,这个“理论一般”“理论抽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进一步上升到了“理论具体”环节。但是总命题还是没有变,依然是“感性的人的感性活动”,这意味着现实世界是置身性的历史的实在主体的交往实践活动造就的颠倒的拜物教的资本世界。因此,从“唯物史观”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个“理论抽象—理论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然而,它必须生长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的现实肉身,并且与该肉身的成长、进步、发展保持一致,才能“支配”、引导历史现实的发展与前进方向。马克思哲学提出的唯物史观(“理论抽象”)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具体”),具有相同的总命题,相同的历史前提,相同的逻辑方法,它们前后一贯,是资本社会中处于具有支配地位的时代话语体系,不仅是中国,它对今天全世界的超越资本造就的物化世界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因此,真正的“理论具体”的发展必须与历史的发展相符合,这同时也表现为“范畴”的进展,即从简单范畴到复杂范畴的进展。“‘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2]29抽象思维中的理论具体、范畴,如果不具有一个置身性的前提,那只能隶属于现代形而上学的理论系统,而不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具体”。这个置身性前提就是具有历史性的“实在主体”及其交往的对象化活动所构成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这个历史条件,那么哲学革命还是与现代形而上学无异,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特质也就无法体现。
只有到此,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真实意图在于表述:历史的、发展着的、具有置身性的实在主体的交往实践活动(以下简称“历史的实践”)造就的、思与史辩证关系。思与史的辩证法,意味着无论是“具体—抽象”,还是“抽象—具体”都仅仅是一个特殊环节,还不是最后的或完整的环节,它需要上升到活生生的、生命的、交往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也就是历史实践,才能体现出现代社会的实在主体的真实面貌,才能具有不断发展、不断出场的生命力。历史的实践,是置身性的交往实践及此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真正的现实性的体现。也只有在历史辩证法中,才能完成由历史的实践所造就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那么,“具体—抽象—具体”思维模式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具有怎样的地位?我们不能过分抬高,也不能过于贬低,不能把它奉为活的灵魂,也不能把它全盘否定,否则便无法进一步把握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前文已经指出,“具体—抽象”“抽象—具体”都不是完整的历史辩证法。由于后者被指认是“科学”的方法,因此尤其需要加以辨析。如果我们回到那段马克思关于黑格尔幻觉的著名论述,字里行间不难发现马克思对“理论抽象—理论具体”的一个确切的看法:“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25“具体”在精神的再现,是“理论具体”,是必要的,否则任何理论都将是无。然而,“只是用来”,“但决不是”,这些关于程度的副词,就指明了“抽象—具体”这一对范畴的地位。如果借用黑格尔的逻辑学来分析,它们还处于本质环节,还不是最后的概念(真理)。当然,马克思是与黑格尔形式相似、本质不同的。马克思事实上也没有把“抽象—具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完成的方法论来看待。如果无法实现自由与必然在实践中的统一,就不构成历史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必须是思与史的、理论与历史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提纲》《形态》造就的哲学革命的本真意义也就在于此。它也是理论,但是通过具体的历史实践而产生并且能够进一步指导理论与实践的理论。我们不能抬高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至于替代整个哲学革命本身,也不能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价值忽略。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理论抽象—理论具体”在何种意义上是辩证法的呢?作为该模式终点的“理论具体”究竟有何意义呢?马克思说关于资本批判的“理论具体”仅仅局限于人类社会的“史前史”,但也不代表它毫无价值。作为理论实践终点的“理论具体”,对资本社会的各范畴及其关系的分析,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2]29。马克思概括了“范畴”及其抽象思维的进程(包括了理论抽象与理论具体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它其实是一个进程)的作用。[2]26,28,30,32“范畴”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在知性法庭中的成功运用归功于康德,在思辨辩证法中的成功运用被发挥于黑格尔,却唯有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方能实现了自身的意义——历史性。它产生于“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2]28,超越了与“某种特殊性”结合在一起的个体的规定性,并且就这个“抽象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2]29。“生产”“劳动”都是最一般的抽象的“范畴”。“范畴”的发展进程需要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它可以是对不发达(展)的历史现实的支配,同样也可以是对发达(展)的历史现实的附庸;它不是产生现实的东西,更不是现实本身。正如黑格尔用伦理的实现来偷换历史的现实,最终也只是投入上帝怀抱。但是由于它可以体现现实乃至对现实具有一种推动作用,因此也是必需的。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所撰写的所有著作、理论都是历史现实发展到高级阶段所具有的“范畴”关系所构成的“理论具体”。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一种资本高度发展的社会的现实肉身之上生长出来的“理论具体”。由于这些“范畴”关系规定了资本社会的特殊性内部结构的本质特征,因此笔者认为可以用“范畴(关系)辩证法”来指涉这种不同于历史辩证法的理论辩证法。况且,无论是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一般”阶段,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具体”阶段,“生产”与“劳动”这两个中心“范畴”都是存在的,并且是前后一致的。在“理论具体”阶段,围绕着“物化”对各种范畴关系进行了人体解剖,进而透视其他社会的范畴关系,获得猴体解剖的钥匙。可以说,资本社会的各个经济范畴都不再是现代形而上学的“表象”与“直观”,而是对“物化社会”的物象逻辑的“理论具体”的写照。任平指出:“交往实践观与物象存在论逻辑。以商品、货币、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等等物象为主线,《资本论》存在着从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经济范畴的演化序列。”[5]“理论具体”体现了一种范畴辩证法,“理论抽象—理论具体”则共同完成了理论实践辩证法。
当然也可以说,“理论抽象—理论具体”是一种理论实践,现实是一种历史实践。理论实践是历史实践的精华与体现,但是理论必须上升到历史实践,通过后者检验其是否具有真理性。所以不能用理论实践代替真实的历史实践。通过两者的共同作用才能构成思与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割裂历史,仅凭思维及其范畴就判断其可以生长出现实的肉身,显然是无本之木、无根之源,是有失偏颇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思维的进程必须符合历史的进程,思维才是有意义的。请允许我用以下的图表表述这种思与史的辩证关系:

置身性的历史实践(史)理论一般(理论抽象)—唯物史观理论具体—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实践(思)置身性的历史实践(史)历史辩证法(理论实践与历史实践相统一)
三
“具体—抽象—具体”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历史辩证法,更不可能是“活的灵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这个问题需要以意识形态的角度与方式来正面解答,正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那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可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因此,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而言,探讨代表他哲学革命即唯物史观的活的灵魂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可以更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深刻理解从哲学角度发掘出来的这个活的灵魂能够与时代保持高度一致、与意识形态保持完整一致的深层原因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延太广泛,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唯物史观的概念的具体内涵与外延做分析。唯物史观最宝贵的地方在于它的方法论,它的科学性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它的方法论。正如黑格尔所说:“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3]429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就是历史辩证法。因此,就方法论而言,历史辩证法正是唯物史观的“活的灵魂”。我们已经详细分析了“抽象与具体”的关系问题,并且指出它还不是完整的辩证法,因而也不可能是“活的灵魂”。进一步的分析需要把这种关系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对比,以此证明历史辩证法是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当然,也仅仅是在方法论角度才能称其为唯物史观的“活的灵魂”。
一系列的问题都从什么是历史辩证法这个问题开始。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指出了“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是具有历史现实性的、包含了丰富多样性内容的辩证法。马克思在此也提出了“概念”,难道是要回到黑格尔式的概念辩证法吗?显然不是。我们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在这里的“概念”与黑格尔“概念”的不同。黑格尔的“概念”有一种具有自身吸引力的“抓取”的含义,即通过矛盾的发展与运动“抓取”到“绝对理念”即“概念”的过程。“概念”是一切矛盾发生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是终结者;它是实体性的,同时也是主体的;它是综合的,同时也是分析的(2)“扬弃”正是既综合又分析的方法的体现。参见黑格尔《小逻辑》第426—42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它从抽象的或知性的理智开始,复又回到了“思辨的或肯定理性”[3]182之中:“思辨的真理,就其真义而言,既非初步地亦非确定地仅是主观的,而是显明地包括了并扬弃了知性所坚持的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正因此证明其自身乃是完整、具体的真理。”[3]184最终,作为完整而具体的真理、概念,它展现为圆圈形状的封闭式的纯思辨的运动与发展的一整套的过程全体的逻辑与方法。“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3]429我们说马克思剥去了黑格尔的思辨真理的“神秘外壳”——作为上帝的绝对理念,同时也重新定义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马克思如何重新定义黑格尔辩证法呢?并非全盘否定。黑格尔认为“方法是灵魂”思想,马克思并未提出异议。由于矛盾的进展原则就是辩证法,所以我们要抓住矛盾的中介问题来看待这个问题。黑格尔认为,反思与根据是矛盾的中介。而这个中介只能把矛盾带回纯粹的主观性和完整的思辨之中。马克思把这个中介转变为“对象化活动”(唯物史观),或者进一步说是“对象化劳动”(政治经济学批判),矛盾才能聚焦于真实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而具有了穿透力:“对象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做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2]186辩证法是矛盾的进展原则,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通过中介的转换获得了本质性的变化。思辨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新神,一切都是从社会历史的现实之根(实在主体的自我活动)开始。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断:“人们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理论的形成依赖于现实之根,但是理论形成之后如若不能继续深入到现实之根中,不能随着现实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那么理论就不能构成完整的历史辩证法,依旧是形而上学的无根之木,无本之源。
历史辩证法是历史的矛盾推动的。因此最后还有必要对矛盾这个概念作一解释。矛盾首先是现实的,其次启示的是在现实中能够把异于自身的事物包含在自身之中,并且能够通过自我否定来扬弃这种自身的异化,进而获得自身的发展的过程。原创者黑格尔谈道:“肯定物与否定物构成独立性的建立起来之有;它们通过自身的否定扬弃独立性的建立起来之有。这就是在矛盾中真正消灭了的东西。”[6]58“矛盾是一普遍而无法抵抗的力量,在这个大力之前,无论表面上如何稳定坚固的事物,没有一个能够持久不摇。”[3]180马克思完全赞同矛盾的方法就是自我否定、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辩证法以及辩证法是矛盾的进展原则。由于历史辩证法的四要素能够真正体现矛盾的进展原则,因此能够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活的灵魂——方法论。什么是历史辩证法的四个要素呢?历史的置身性的;实在主体的;内部发展的;交往实践活动的过程。其实,黑格尔的“矛盾”由于多了一重“绝对理念”的启示,最终沦为了新神学,这确实非常可惜。由于“抽象—具体”本身的自限性,即限于思维之中,它必须借助于历史现实这一强大肉身的无限递进,才能无限发展。
可见,历史现实的矛盾有两大特征:一是历史现实的有目的的自我否定;二是历史现实的无限的自我发展。历史辩证法保留了黑格尔矛盾的积极方面,但是不把它作为一个完形填空的必要手段。它是生成的、活动的,并且向往着自由、幸福、爱的植根于社会历史现实的方法论,而不是僵硬的、永恒的必然性力量和由自为引导的自在自为的概念。可以说,理论抽象代表了广义的唯物史观,理论具体则代表了具体的唯物史观,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它们作为理论实践与置身性的历史实践相结合,才能体现出完整的历史辩证法,进而使得历史与理论都得以不断敞开、不断生成、不断发展,在不断的出场中秉持永恒的在场。唯物史观的活的灵魂是历史辩证法,这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确认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正是完整一致的吗?不教条、不本本,面对时代的新场域,解答时代新问题,进而在置身性的历史实践中引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历史辩证法是唯物史观的活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