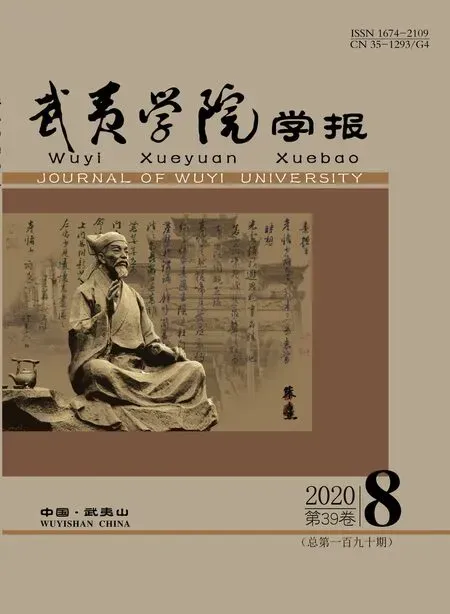人格权保护
——美国堕胎问题的启示
2020-01-02
(福州大学 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6)
一、问题的缘起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放宽了对堕胎的禁令,爱尔兰在2018年举行公投推翻了已实行35年的堕胎禁令,韩国宪法法院于2019年4月裁定废除长达66年的堕胎禁令。美国虽然在1973年就将堕胎合法化,但反对堕胎的声音不绝于耳,今年更是兴起一阵对堕胎实行法律限制的浪潮。美国阿拉巴马州在5月通过一项严苛的堕胎禁令,该法案禁止女性在怀孕的任何阶段堕胎,即使是被强奸和乱伦所致的怀孕也不准堕胎,且任何帮助女性堕胎的医生都将面临高达99年的监禁。之后由共和党控制的很多立法机构都通过了和阿拉巴马州同样武断的堕胎禁令,比如乔治亚州、肯塔基州通过了《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禁止孕妇在检测到胎儿心跳后堕胎,即禁止妊娠六周后堕胎,因为那时已可以检测到胎儿心跳。
美国对堕胎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生命派和选择派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使之从原本只是医学问题变成一个包括医学、宗教、政治、道德伦理等因素的复杂问题。堕胎问题涉及的主体主要是孕妇和胎儿,生命派和选择派也主要是围绕女性的生育权和胎儿的生命权来进行争论。堕胎问题背后牵涉伦理道德、宗教、国家政策等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并不单单是法律问题。堕胎背后的法律问题主要是人格权保护问题,即生育权和生命权这两种人格权的较量,如何才能更合理地保障这两种人格权,尤其当具体人格权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如何进行价值平衡和保障人格权显得尤其重要。
因宗教、政治制度等原因,堕胎问题在我国不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分歧。我国堕胎问题的分歧主要是我国计划生育义务与公民生育权之间如何权衡,一般不涉及胎儿的生命权和妇女的生育权之间的权衡。有人提出我国又不限制堕胎,谈女性生育权保护貌似多此一举了。事实果真如此?不限制堕胎,我国女性的生育权就得到极大的保护了?在生育问题上我国多为义务性规定,并不能称为一项权利,所以对女性的生育权保护仍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此外,我国虽然对堕胎问题未形成女性生育权与胎儿生命权之间激烈的伦理道德较量,但已对胎儿的利益保护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对胎儿的利益保护,尤其生命权的保护,对改变目前随意堕胎以及漠视、不尊重生命的现象也起到重要作用。
关于堕胎问题,美国在长期的争论中形成不少有益观点。因此本文对美国关于堕胎争论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挖掘生命派和选择派支撑己方观点的理由,从而分析当生命权和生育权这两种人格权存在冲突时,美国是如何进行价值衡量进而保护人格权的。放眼世界,回归本土,分析美国的堕胎问题,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国情,完善我国关于堕胎的相关法律,完善我国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
二、生命派和选择派的较量
(一)美国堕胎立法的历史脉络
美国在19世纪初时还没有限制堕胎的法律。到19世纪20年代以后各州才相继制定了禁止堕胎的法律,因为当时医疗技术并不发达且卫生水平也很低,导致女性因堕胎而死亡的概率较高。为了降低女性因堕胎的死亡率,也出于道德伦理、宗教等因素,美国开始出台堕胎禁令,马萨诸塞州是第一个通过堕胎禁令的州。在接下来的50多年,除了肯塔基州以外,其他州都制定了反堕胎法,规定堕胎是一种重罪,只有在为了挽救女性生命时才可堕胎。到了19世纪70年代,因为医疗水平的提高,女性因堕胎的死亡率大大下降,当初为了保护女性的生命、健康而制定的反堕胎法遭到质疑。此外,性解放运动和避孕药的普及,因意外怀孕而堕胎的人越来越多,但因各州禁止堕胎,致使女性不得不在卫生条件恶劣的“黑诊所”进行非法堕胎,这又导致女性的堕胎死亡升高率,与法律所要保护的女性法益的目的背道而驰。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女性追求更加平等、自由的法律地位,而生育自由是女性法律地位提高的重要体现,堕胎禁令限制女性的生育自由遭到女权主义者的反对。但当时对堕胎的争议主要是在医学上,并未上升到伦理道德和政治民主的高度。
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是美国堕胎问题争议中标志性案件。当事人诺玛麦科威是德克萨斯州人,21岁没有正式工作,离婚后没有抚养能力便将女儿交由其父母抚养,不幸的是此时她因被强奸而怀孕,这使她境地更加糟糕,便想要堕胎。然而德克萨斯州法律规定除非为了挽救母亲生命并且由医生建议堕胎才可以堕胎,于是她化名罗伊指控德克萨斯州的法律违背宪法。最终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认为德克萨斯州的堕胎禁令违反了宪法,宪法第九、第十四修正案的隐私权应涵盖女性生育自由,确立了女性堕胎的宪法权利。“罗伊案”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对堕胎问题的分歧形成了两个对立派别,即支持妇女享有堕胎权的“选择权”派和反对妇女享有堕胎权的“生命权”派,针对生命始于何时、女性是否享有堕胎自由展开激烈讨论。20世纪70年代之后相继出现了支持“生命派”的“阿克伦案”“韦伯斯特案”,支持“选择派”的“凯西案”“马德森案”[1]。堕胎也成为美国两党竞争时不可回避的议题,比如里根、布什父子坚决反对堕胎,克林顿、奥巴马则坚定支持堕胎,他们上台后都出台了相应政策。一般来说民主党偏向选择派,共和党偏向生命派。由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法案须经参议院和众议院同意,由国会制定联邦法律,国会便成为两派争论的主战场。因美国各党派的政治力量加入,使得堕胎问题在美国由简单的医学问题上升到政治民主的高度。争论愈演愈烈,2016的“妇女保健诊所诉科尔案”[2],到今年禁止堕胎浪潮,关于堕胎问题的争议分歧还将继续。
(二)生命派与选择派的争论论点
关于堕胎问题,生命派与选择派围绕着生命始于何时、胎儿是否有生命权及是否为法律关系主体、女性是否享有生育自由权、生育权是否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人的想法是会发生改变的,两大派别中的一些人在争论中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加入到对方阵营,有代表性的就是罗伊成了生命派的拥护者,而韦德转而认为女性应当享有生育自主决定权。很多事物都具有多面性与复杂性,而不是简单的对与错之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辩证看待双方争论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事物本质。
1.生命派的主要观点
支持生命派的主要是天主教徒、新教右翼。天主教认为生命始于受孕,因此胎儿拥有基本的生存权利,允许堕胎就是允许谋杀。随意堕胎就如同随意杀人,违背了基督教教义,是一种犯罪行为。生命派也尊重女性的生命权和隐私权,认为在对妇女生命造成威胁的时候,堕胎具一定的正当性,但没有明确说明正当性,也未说明胎儿与妇女生命健康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天主教还受《圣经》的影响,认为人是由上帝创造的,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人的生死。一些极端的生命派认为即使在强奸、乱伦、胎儿有残疾的情况下也不可以堕胎,因为人的生命是上帝赋予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都由上帝决定。同时他们认为性交和生育是上帝赋予的权利,性交只是一种生育行为,避孕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罪恶。天主教是美国最大的教会组织,拥有众多教徒,随着天主教实力不断扩大,其主张的观点也广泛影响着美国社会,使得美国反堕胎浪潮不断。
此外,传统秩序和传统价值的维护者认为,虽然在妇女生命健康遭受威胁时堕胎具有正当性,但是很多妇女选择堕胎并不是基于自己的生命健康,而是不想承担怀孕后带来的一系列负担责任。他们认为繁衍对人类延续至关重要,是人类的义务和责任,允许妇女自由堕胎相当于打断了人类正常的繁衍过程。如果法律允许妇女堕胎,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沦丧,影响人类的生存繁衍。如果堕胎合法化了,社会很可能形成一种不负责任的风气,而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极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一旦青少年形成放任自己的行为、推卸责任的处事态度,将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文明倒退,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生命派还用洛克的天赋人权思想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生而平等,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生命权是最基本的权利,任何与生命相抗衡的权利是不应当存在的。堕胎就是剥夺了胎儿的生命权,侵害了胎儿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相悖。
2.选择派的主要观点
支持选择派的主要是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新教主流派。选择派认为生命不是始于受孕,而是受孕后的一段时间。“人”应该指的是出生之后,胎儿未出生之前不能算是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人”不包括未出生的胎儿。也就是说法律上,未出生的胎儿不是法律主体,不享有法律权利。选择派也拿洛克的天赋人权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人的基本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生育自由权是最根本的人权之一,妇女只有在能自主决定是否生育时才享有完整的生育权,胎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不应为了保护所谓的人的利益而牺牲妇女的生育自由权。杰弗逊编写的《独立宣言》更加详细的阐述了洛克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3]。”选择派认为堕胎自由是妇女生育自由权应包含的内容,也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隐私权应包含的内容,堕胎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私密的事情,应当受到隐私权的保护。
选择派有一个有力论证,即茱迪丝·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在其论文《为堕胎辩护》(A Defense of Abortion)中所做的小提琴手思想实验[4]。有一个小提琴手患有肾病,需要与他血型匹配的人,将两人的肾通过医疗设备连接,通过血液传送药物,只需九个月他就会康复,到时就可以断开连接,而你因与小提琴手血型相匹配,被音乐爱好者绑架并将你们连接上,此时如果你断开连接他就会死亡。但是你必须同意这样做吗?或许有人认为牺牲九个月的自由换取一条生命是值得的。那如果不是九个月,而是九年或者余生呢?汤姆森认为:“生命权是很重要,但是有生命权不能代表有权任意使用别人的身体,即使这个人需要借此维持生命[5]。”回到堕胎问题,妇女作为自己身体的主人,在违背自己的意愿怀孕时,应该享有自卫权将“入侵者”胎儿驱逐以保护自己的安全。只有在妇女自愿怀孕时,妇女才需要对胎儿负责。正如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桑格所说:“没有权利支配自己身体的女人,不能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人;直到女人有权利自觉地选择是否做母亲,她才有资格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人[6]。”此外沃伦(Warren)在1973年发表的文章《堕胎的道德与法律地位》(On the Moral and Legal Status of Abortion)也强有力支撑了选择派的观点。沃伦总结出人应该具备五种特性:意识、推理能力、自我激发的活动、沟通能力、自我觉醒或自我观念[1],进而得出胎儿不具备以上特征,胎儿不是人,不享有人的基本权利,也不体现道德价值。既然胎儿非人,牺牲人的价值保护一个非人的价值似乎有悖常理。即使承认胎儿有生命权,堕胎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允许的,如果为了保护胎儿,而不顾妇女对身体的自主决定权,那么这个社会也将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
(三)两派争议的启示
审慎分析在“罗伊案”中及其案后生命派与选择派的争论点,双方思想的碰撞给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其实只要不是各方的极端支持者,双方的观点并不存在巨大的无法跨越的鸿沟。不管生命派还是选择派都承认胎儿的利益和妇女的权益都需要保护,只是在存在冲突时,双方侧重保护的不同罢了。“罗伊案”之后,虽然两派之间激烈争论不断,但该案确立的思想一直未被推翻。“罗伊案”以隐私权保护妇女的生育自由,确立妇女生育自由权的宪法地位。虽不承认胎儿为人,但认为胎儿的利益也需要被保护。因此联邦法院将怀孕划分为3个阶段,在怀孕前3个月可以自由堕胎;3个月之后,基于保护妇女的生命健康,可以对堕胎进行限制;7个月之后,胎儿脱离母体可以存活,为潜在生命的合法权益可以禁止堕胎,除非为保护妇女的生命健康[7]。联邦法院在3个阶段给予妇女生育自由不同程度的限制,为两种权利留下了一定空间,即保障了妇女的权益,也关注到了胎儿的利益,兼顾法律、道德伦理,符合法律利益也符合道德利益,这种判决思想应该存续下去。之后的“韦伯斯特案”“凯西案”等一系列案件不是对“罗伊案”的否定,而是在“罗伊案”框架内的动态调整,“凯西案”确定的不当负担原则仅是对妇女权利限制措施的合理性审查标准采取不同口径而已[8]。总之,“罗伊案”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来解决权利冲突问题,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堕胎背后的人格权保护问题
各国因政治背景、宗教文化不同,对堕胎立法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在人口稀少,人口老年化严重的国家,政府通常是鼓励多生而限制堕胎的,比如在俄罗斯会奖励多生家庭,并为他们颁发父母荣誉勋章。在人口密集的国家,政府通常是限制生育,将堕胎作为实行计划生育的一种手段,但公民往往倾向于生更多孩子。国外的立法、司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不可生搬硬套,需要结合本国具体国情,灵活地本土化。
(一)我国堕胎背后的人格权保护存在缺失
在建国初期,我国因战争而人口骤减,因此国家是鼓励生育和限制避孕的,并且严厉打击堕胎。在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发现人口增长过快,节制生育的观点被提出;从197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到1984年形成“全面推行一胎”的人口紧缩政策[9]。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突显,因此国家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政策总是根据国家的具体国情不断变化调整的。因文化、国情等因素,在我国关于堕胎问题讳莫如深,极少法条涉及。我国的生育制度呈现出一定的“工具主义”“唯理主义”观念之色彩,虽然该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但也形成了矮化生育权利、强调经济与社会发展之宏观目标优越于个人生育自由的固有逻辑,这显然不利于我国生育制度的法治化[10]。堕胎只被当成是控制人口的一种手段,一件平常而自然的事,人们没有注意到堕胎侵犯了胎儿的利益,忽视了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基本价值,更未去深究其背后引发的人格权保护问题。
无论国体政体存在多大差异,堕胎都是一国无法回避的法律问题。相对于国外为保障胎儿生命权、为权衡妇女权益和胎儿利益,经过大量理论论证,并专门立法,我国在立法上相关条文规定极少,在理论上的论证也较为欠缺。我国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和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母婴保健法》规定胎儿患有严重遗传疾病、严重缺陷、危及妇女生命健康的可以堕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通过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堕胎问题持宽容态度,只禁止性别选择性的堕胎,并且在生育问题上多为义务性规定,妇女的生育权并未得到很好的保障。堕胎虽然自由,但是生育权的观念在中国并未真正确立。对于胎儿利益保护,因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胎儿还未出生不能成为民事主体,不享有民事权利,民法总则仅规定涉及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将胎儿视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然而因为胎儿不是“人”,使得实践中大量侵犯胎儿利益的案件无法可依,给司法适用带来困难。可见我国对胎儿利益的保护还需增强,对于胎儿来说,不仅其未来的利益需要保护,某些现实的利益也需要保护[11]。
(二)增强堕胎背后的人格权保护
关于堕胎的问题,有学者指出《生育法》实施之后,法律上反而对堕胎行为加以认同,甚至有积极推动堕胎意味[12]。笔者认为,对于堕胎问题须采取谨慎态度,不可放任也不可强制,规定操作性强的法律,并引导人们树立尊重生命、尊重女性的观念,才有利于堕胎问题的解决,更好保障公民的人格权。
1.明确生育权和胎儿权利保护的法律规定
我国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似乎并未规定生育权。按有义务必然有权利来说,似乎也只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一规定为宪法上人格权的确立提供了规范依据。虽然没有直接规定生育权,但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应该是不证自明的。将法定化狭隘的理解成须有明确字样的规定,这无疑是取消了法律解释的存在,一般人格权的作用既然是保护未列举的人格权,其内容注定是向未来开放的[13]。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自由等方面,并且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予以特殊保护。宪法虽然未明确规定生育权,但不表示不保护。在美国,将生育权纳入隐私权的保护范畴。但我国隐私权受到“隐”与“私”的限制,与美国充任“一般人格权”功能的隐私权存有巨大差别[14]。在我国,隐私权与生育权是并列关系,都属于人格权,不宜将生育权纳入隐私权范畴。我国对女性生育权缺乏法律保护,要想真正提高女性生育权的地位,必须赋予其宪法的地位,而作为人权内容的生育权,赋予其宪法地位也是理所当然的[15]。在宪法上确立生育自由权作为基本人权保护,可以更好保护女性的生育权,但修宪程序严格不易达成。那要在宪法层面上保护未明确规定的权利,还有什么途径?一般有两种做法,第一是通过宪法解释在明示的权利中加以引申和扩张,使其能涵盖新的权利;第二是通过宪法“未列举权利”条款进行保护[16]。比如宪法第37条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身自由广义来说包括身体和行为的自由,那生育自由是妇女生育与不生育的行为自由,可以纳入宪法第37条来保护。但我国宪法不作为审判的直接依据,因此对生育权的保障还是应规定在民法中,规定在人格权编。《民法总则》第109条规定公民的自由和尊严受法律保护,可以起到一般人格权的作用,与宪法的第38条衔接,在民法规范中落实宪法所规定的人格尊严保护[17]。在民法中具体规定生育权的定义、行使的条件、受到侵害的救济等。
胎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但因其有发展成人的潜力,也不可忽视其权益。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暂时还不宜去纠结胎儿的宪法法律地位,也不必过多考虑胎儿的刑事法律保护,而应先重点关注胎儿的民事法律保护,关注对《民法总则》规定的关于保护胎儿利益的规定的解释[18]。《民法总则》规定胎儿在继承、接受赠与等视为出生,享有民事权利能力,那以后是否可以扩大到其他情形呢?拥有生命是拥有各种权力的前提,随意堕胎在我国法律上虽然还称不上侵犯胎儿的生命权,但保障胎儿的权益,给予其发展成人的条件,是法治社会应有之义。所以民法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应规定得更为具体、详细。
因为堕胎问题牵涉妇女和胎儿两方的权益,法律制定时必须考虑到当发生权利冲突时应进行利益衡量。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但生育对整个人类的繁衍和社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所以生育自由不应完全不受法律的限制,但对生育的限制以不逾越人性为最低限度。当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应当允许堕胎,显然母亲的价值是大于胎儿的价值,如果法律不保护现存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去保护未来潜在的生命,则有本末倒置之嫌。对此,可以借鉴美国的立法,对妇女在怀孕期间的堕胎自由予以不同的限制,同时给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避免生搬硬套法条造成案件的不公。
2.树立保护女性和尊重生命的观念
我国对堕胎并未严格限制,女性享有堕胎自由,但生育权观念在我国并未真正确立。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尽管倡导自由民主、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还是长期遭到贬低,女性的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父权夫权仍影响着很多人的观念,认为女性只能服从,女性最大的作用就是传宗接代,好像女性只是生育的工具。但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并且人只能被作为目的而不能被视为手段[19]。女性想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在经济上独立、事业上成功、平等参与国家各种社会事务,确实享有生育权是极为重要的。生育权是人之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乃是一种普遍的、固有的、不可转让的权利[20]。生育权是人格权,而人格权是以主体依法固有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以维护和实现人格平等、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为目标的权利[21]。如果女性不能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是否生育,那她就沦为实现生育的一种手段,就不享有完整意义上的人格权。堕胎自由属于生育权自由的内容,女性决定堕胎无论理由是否正当都是其行使生育权的表现[22]。如果要求女性必须提供正当理由才能堕胎,那么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生育权[23]。用法律来强迫女性做母亲是非人道的,被迫生育影响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使其生活和未来蒙上一层阴影。在一些案例中,还涉及因强奸、乱伦、婚外情怀孕的女性,以及青少年偷食禁果导致的未婚先孕,单亲母亲的情形,往往关系到个人耻辱。在中国生养一个非婚生子女往往是困难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困难,更主要的是人们观念上的排斥。比如因被强奸而怀孕的受害者,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嘲笑讥讽。而在美国,因性更为开放,未婚、单亲父母很多,受到的舆论压力要小很多。因此我国目前对堕胎持较为宽容的态度是可取的,但应树立女性生育权的观念,确实的保障女性生育权,而不是避而不谈放任之。
当前因早恋及婚前性行为导致的恣意堕胎已见怪不怪,但无可否认,堕胎手术与其他手术不可相提并论,它关乎到伦理道德等社会问题。很多时候选择堕胎并不是因为挽救妇女的生命,也不是因为胎儿患有严重疾病,只是为了甩掉包袱或者其他理由。当然女性享有生育权,并不必须为堕胎提供正当的理由。但如果允许毫无顾忌的堕胎必将导致社会对性的放纵,对生命的漠视、不尊重,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都下降。所以有必要在观念上纠正随意堕胎的态度,不把堕胎当儿戏,树立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观念,更加谨慎的对待堕胎。胎儿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但胎儿具有发展成人的潜力,法律有义务保护胚胎的利益。正如德沃金认为:“虽然胚胎不是宪法人,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它是一个具有相当大的道德和情感的重要实体……在一个政治社会里,如果堕胎已经成了一个不足为奇、与伦理不相关的事情,就像做一个阑尾炎手术一样,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是一个更为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危险社会[24]。”对胎儿的生命给予尊重,有利于树立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对道德风气的建设,而尊重、敬畏生命也是文明社会的价值基础。
四、结语
如果完全禁止堕胎,为此付出代价的主要是女性,她们会因为经济压力或者害怕而无法去堕胎合法的地方,最终可能会选择喝酒、吸毒或其他更糟的方式来自行堕胎。但同时也会让这些不被欢迎的胎儿付出代价,因为不受欢迎出生的孩子,他们很可能会遭受各种困难挫折,经历一个悲惨人生。法律赋予这些胎儿来到这世界的敲门砖,那他们出生之后,法律又打算怎样保障他们的权益呢?所以对堕胎问题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也不可完全禁止,极端的做法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导致严重后果。
讨论美国的堕胎问题,是希望能从他国得到经验教训,完善我国关于生育、堕胎的制度规定。通过这项问题研究,认识到我国人格权保护还存在问题,对女性生育权和胎儿生命权不够重视。为加强对人格权的保护,我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生育权以及生命权作为重要的人格权应该得到重视。在立法上,完善生育权以及胎儿利益保护的规定,唤起社会对女性生育权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对堕胎问题需慎之又慎,不可一刀切。当生育权和生命权发生冲突时,要结合具体案情,分阶段的关注双方利益价值,灵活地进行利益衡量选择最佳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护了妇女的生育自由权又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强调对妇女胎儿等弱势群体的保护,是为了实现实质正义[25]。只有尊重生命、尊重人性,保障公民的人格权,社会才能文明和谐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