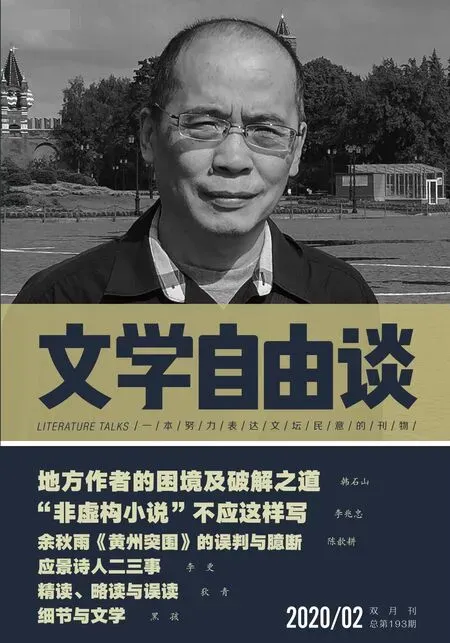精读、略读与误读(外两篇)
2020-01-02□狄青
□狄 青
我喜欢写东西比较早,读各种文艺书也挺早。以前的习惯是:总会把那些用我省下来的早点钱买回的书放到一边,先争分夺秒地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原因说来并不复杂,自己买的书是属于自己的,跑也跑不掉,什么时候看都可以;而借来的书总是要还的。其结果便是,自己的书数量日渐增长,没看的书也越来越多。甚至为读书还做过“年计划”,一年内要把哪些书读完,但计划赶不上变化。书在看,却做不到什么书都逐字逐句反复推敲,有精读也有略读。起初是为完成自己的“年计划”,后来就逐渐养成了某种阅读习惯。
古人讲“一物不知,君子之耻”。我也曾恨不得做到“于学无所不窥”,后来才明白,这种想法不仅虚妄,且无必要。多年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世上的书无论如何也是读不完的,即便博学如博尔赫斯、翁贝托·埃科等。埃科说过,凡为经典皆有再读必要,而我觉得,但凡经典都要精读。其实对于某些书而言,略读亦绝非无用,至少在需要它的时候知道到哪去找。读书人与一本好书的相遇经常也需要缘分的。
当年,梅兰芳对与戏曲有关的书便是精读,对新文艺的书便是略读。我以为这恰是作为一代戏曲表演大师最好的阅读方式。梅先生的藏书里,有明代崇祯年间的刻本《曲律》《度曲须知》《弦索辨讹》等,还有天虚我生的《学曲例言》及各种皮黄、越剧、秦腔,甚至鼓书和弹词戏本。这些都是他精读的书,有的还不止一遍。对于新文艺书籍,梅兰芳所藏也不少,但略读居多;精读的也有,比如徐志摩与陆小曼合著的《卞昆冈》、英国剧作家巴雷的《可钦佩的克莱敦》等。
多年前我曾买回一套精装《清史稿》,皇皇十二巨册,想精读却一直没做到,但略读还是收获颇丰,论及有清一朝,由此总能准确找到出处。略读看上去不求甚解,但如果对一个于文字敏感的人而言,往往能从字里行间慧眼识珠。与精读一样,略读的书也是越多越好。朱光潜先生拿到一本书,往往是先看一两页,如发现文字不好,接下来就只略读,如内容再不行则干脆不读。不用说朱光潜先生,一个人倘能被外界尊为读书人,那么他对一本书的直觉和评判总不会太差。
比起略读,最不靠谱的还是误读。误读也分不同情况。比如我,大概十六七岁时读过一些经典,尤其是那些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那时觉得自己好神气,别人没读懂的,被我一个少年读明白了。后来发现,好多我所谓读懂的,其实根本就没读懂,有的甚至完全是误读,与作家和作品所要阐释的本意不仅拧巴,甚至南辕北辙。这也是我成年后才意识到的问题。没办法,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重读。除了像我这种误读的情况,还有另外一种,因为比较迷惑人因而显得更“危险”,这就是搭所谓的“知识经济”快车应运而生的“阅读胶囊”。我甚至认为这是在人类阅读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阅读传销”。
所谓“阅读胶囊”,便是针对人们普遍希望快点提升、快点成功、快点幸福、快点减肥等等心理,把各种书籍提炼成一粒粒“胶囊”贩卖给读者(消费者),即“二手阅读”。但我对这些“阅读胶囊”的“疗效”实在存疑,它们令我想起儿时看过的小人书,原著四五个段落的内容,在小人书里甚至分不到一两句话。把《复活》《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样几十上百万字的作品,在不破坏原意的基础上浓缩成万八千字,我不知道谁有这本事,更不消说《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了,由此造成的误读显而易见。试想,当一部百八十万字的巨著被浓缩成一粒“胶囊”,像速效救心丸一样让你吞下,或许可以救急,比如有谁晒朋友圈谈论这部作品的时候你可以插几句嘴,但说到底不是个事儿,说这是“误读”已经是客气了。
对于阅读,我不是单纯的怀旧,也不是刻意去诟病任何新的阅读方式。虽然在社交网络时代,阅读正逐渐从一个独立、个体的行为变得更加社交化、功利化,但作为一个读书人抑或说喜欢读书的人,总该不与流俗妥协,不去攀附热门;否则,有读书的那点儿时间,倒不如去掺和点儿更热闹的活计。
文人、美食与小说
文人与美食自古相互成就。杜甫、苏东坡、陆游,甚至更早的伊尹、孔子,都是美食家。中国饮食讲究色香味俱全,“色”之所以被排在首位,大概与文人的审美介入密不可分。
说到文人与吃的关系,张翰显然跑不掉。《晋书》卷九十二《文苑列传·张翰》中记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见机。”张翰回乡其实是为避祸,但的确也为解“莼鲈之思”。早在辞官前,他便写有《思吴江歌》:“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思乡恋乡,美食是重要一环。当年梁实秋从美国回北京,放下行李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前门外煤市街的致美斋饭庄,吃了肚仁、肚领、百叶三种爆肚儿。他后来的大量文字都写到过吃,而《雅舍谈吃》将爆肚儿的来龙去脉更是写得颇为详尽。鲁迅也爱写吃,却非刻意,更不铺排,很少见他写在北京上海吃到的那些“大菜”。他在北京生活十四年,下过的馆子,叫得上名字的就有六十五家之多。鲁迅既有官差又兼教职,应酬多,有时一天三次换着样儿下馆子,俨然把北京吃成了第二故乡。但无论《孔乙己》里的茴香豆,还是《在酒楼上》的“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或是《阿Q正传》里讲阿Q瞧不上城里人煎的鱼,因城里人煎鱼只配切细了的葱丝,而未庄煎的大头鱼放的是半寸长的葱叶……鲁迅写吃非常节制,却又很有味道,往往简单的吃食也写得令读者心向往之。
老舍写小说,吃是他的“秘密武器”。比如《骆驼祥子》。小说从一开始讲祥子攒了三年钱买了新车,然后将买车的这一天定为自己的生日,决定在最好的饭摊吃顿饭。吃啥呢?当然是热烧饼夹爆羊肉。后来祥子被抓壮丁,逃出来后,又特意去吃了老豆腐。醋、酱油、花椒油、韭菜末调料齐全,且被热的雪白的豆腐一烫,香得使祥子要闭住气;他自己又下手加了两勺辣椒油,一碗下去,汗已湿透裤腰。他半闭着眼,把碗递出去:“再来一碗”——那感觉简直犹如重生。和虎妞结婚,虎妞给他做肉丸子熬白菜、虎皮冻还有下饭的酱萝卜,但祥子却“吃着不香,吃不出汗来”。而到最后,祥子堕落了,他决定“活在当下”,用仅有的钱吃大饼卷酱肉……其实不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许多与吃有关的描写,实则都与人物及时局变化密不可分。老舍爱吃,也爱请客,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最爱干的一件事是编排菜单,从凉菜到热菜反复斟酌,仿佛比写小说里的吃还要认真。
汪曾祺写吃也是把好手。在《迟开的玫瑰或胡闹》里,他把吃肘子写得出神入化:
吃肉,尤其是肘子,冰糖肘子、红焖肘子、东坡肘子、锅烧肘子、四川菜的豆瓣肘子,是肘子就行。至不济,上海菜的小白蹄也凑合了。年轻的时候,晋阳饭庄的扒肘子个有小二斤,九寸盘,他用一只筷子由当中一豁,分成两半,端起盘子来,呼噜呼噜,几口就“喝”了一半;把盘子掉个边,呼噜呼噜,那一半也下去了。
汪曾祺不止爱吃,也爱做。有一回他在北京蒲黄榆家附近的菜市场排队买牛肉,前面是个中年妇女,轮到她买的时候,她问卖牛肉的人牛肉怎么做?汪老不解:她既是买牛肉,为何却不会做?就将其请到一边,讲了一通牛肉的做法,从清炖、红烧、咖喱牛肉,直到粤菜里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丝等,惹得路人都驻足旁听。
那年在北京开全国青创会,我与余华同组。说起《许三观卖血记》,我说最喜欢他写许三观躺在炕上给睡不着的孩子们讲吃的那一段。余华说,那是他的真实经历。余华少时跟镇上一帮小孩儿疯玩,要是谁家吃了芦笋烧肉,谁家烧了蹄髈,其他几个孩子就围拢过去问,那孩子便一五一十地讲他家里的做法和尝到的味道,令孩子们频咽口水。
看孙犁先生写《吃菜根》:“今年冬季,饶阳李君,送了我一包油菜甜疙瘩,用山西卫君所赠棒子面煮之,真是余味无穷。这两种食品,用传统方法种植,都没有使用化肥,味道纯正,实是难得的。”读罢,如嗅到新棒子面的香气,嘴里仿佛还有甜疙瘩的鲜香。说实话,解馋不一定得是山珍海味,有时就是微妙复杂的味觉与视觉触觉的叠加碰撞,唤起的却是我们对过往的某种美好记忆,就像唤起普鲁斯特的那块“小玛德琳点心”。
创意写作的“先进性”
2016年,用笔名“加尔布雷斯”给出版社投稿的英国作家J.K.罗琳的书稿被退回,出版社建议她最好先去参加“创意写作课”的学习,然后再来写作,并给她推荐了学校。那时伦敦正有几所大学在招收创意写作短期研修班的学员;已经享誉全球的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曾参加某出版商搞的“模仿格雷厄姆·格林小说大赛”,结果在评委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只获得了第九名。国外的文学圈如此,当下的中国文坛也不例外,作家的名气被当作衡量作品能否被承认、受重视程度高低的重要圭臬,这一现象甚至已成为无法改变的“固态”。然而,大家同时也普遍认同这样一句话:作家是应该拿自己的作品去说话的,而非仰仗多年累积的盛名和出版商及媒体狂轰滥炸式的宣传。
事实上,包括沈从文、施蛰存、穆时英这些作家,当年在尚无名气时,稿件被退甚至石沉大海是常态。西南联大时期,物价飞涨,稿酬难赚,昆明报馆连吴宓、朱自清的稿子都退过——不是不好,因版面实在有限,只是要好中挑好。
据说,那时昆明有报馆学欧洲,专门给驻云南的盟军官兵出过“感恩节专号”等专刊,上面发有英文诗歌。这在当时来说,就是一种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的说法,我们耳熟能详,但在写作教育上与国际接轨,大约只是近几年的事。几十年来,据说欧美尤其是美国作家多半出自创意写作专业。这种作家的培养和速成方式,使得美国作家中再也见不到麦尔维尔、杰克·伦敦那种从惊涛骇浪里滚出来的作家,福克纳、海明威那样的也不可复制。作家都成了同学,经历亦变得越来越趋同。
在国内,创意写作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作家可以培养,写作人人可为”的观念被认可。很多院校成立了创意写作中心,本硕博创意写作人才培养渐成体系,学科发展势头强劲。有相当一部分创意写作专业的本硕博,其导师就是国内著名作家、著名文学评论家或各大文学期刊主编,因而这些人的写作很难说不带有“辨识度”。这实际上也造成一个问题,如同某些地方的官场,谁是谁的人,谁是谁的学生,谁是谁提携的,谁的作品“专供”哪些刊物,哪些刊物专捧谁,这些现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创意写作出现前后的最大区别在于,从前作家写作往往是不自觉的,是误打误撞的,是被生活驱使的,是对生活和内心的真实描摹与倾诉。而执创意写作的人则不然,他们是带有极强的当作家的目的性的,是刻意的,是把玩的,是有的放矢的,是用娴熟技术和技巧来截取生活切片为我所用的。他们无疑更能迎合这些文学期刊的选稿趣味。
虽然创意写作界大腕、《小说写作:叙事技巧指南》作者、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珍妮特·伯罗薇也认为,小说的过分技术化会损害创意写作本身,但对技术化的迷恋依然是许多接受创意写作教育者的“捷径”:如何布局、结构、推进故事发展,貌似精致,却大同小异。
同样作为一名写作者,就我所见,创意写作旗下作家作品的视野与格局都较小,大多是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切入现实,很难有更宏大的把握当下和历史的能力,思想上也缺乏创造力,太过注重个人感受。他们受各自导师的文学影响很深,且很难摆脱出来,因而,虽创意写作本硕博毕业生已多如过江之鲫,但其对文学的真正贡献尚未见到,且至今也未能形成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世界与艺术风格。
我们知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改革的重点,所追求的就是标准化。但文学创作显然不需要建立一套标准化的现代文学制度。在我看来,由创意写作衍生出的技术化写作,貌似时尚,实则保守。美国文坛冒出的帕拉尼克、理查德·福特、威尔斯·陶尔等创意写作的顶级操盘手,至少目前与福克纳、海明威还没有任何可比性,既没有被归入经典的作品,更遑论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往往对自己不熟悉的经验会降低要求,甚至会刻意逢迎,许多人对创意写作即如是,好像一说与国际接轨,一切便具有“先进性”了,殊不知在一面面显赫的文学大旗掩护下,一些东西和一些人很容易就变成一种烟花,绚丽一时,立刻就寂然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