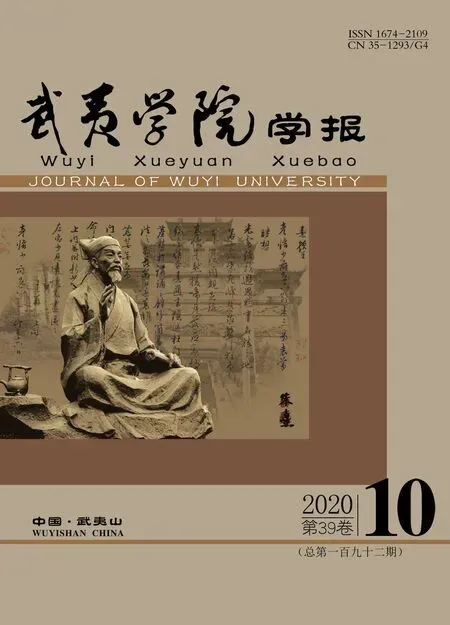继往开来:朱熹理学经典诠释思想发微
2020-01-02魏子钦
魏子钦
(西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120)
“生生”之儒学欲实现自身之生生,必不执于祖述,而是损益变革,与时偕行。儒家哲学与文化自先秦以降,几经沉浮,终至宋明,使之隆盛,此盛实依于宋明儒家,其中朱熹之功尤著。史书评价“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识者以为知言”[1]。朱子对经典终身地死而后已地注解,形成朱熹独特的理学诠释思想。有鉴于此,通过研读朱熹《四书章句》《朱子语类》等文本,以三教碰撞与吸收的学术视角与朱熹理学思想的哲学视角,考察朱熹经典诠释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完成[2],期以“真了解”朱熹,与朱子处同一境界。
一、“道学”的兴起与地位确立
“ 道学”一词,最早是在北宋庆历、皇祐年间的王开祖《儒志》 篇最章末开始使用[3],“ 道学”出现预示着一种新的学术风气与思想取向的发展,不过这种说法,当时学人并没有达成共识[4]。因为庆历、皇祐年间,经术式微,道学作为存在于士大夫间的学术话语与思想体系,在王开祖那里,只是敏感的发现这一思潮,而“道学”真正的崛起,还要等到十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后才能完成。
自中唐以后,汉儒看重的“ 五经”,其地位已大不如前。为重振儒学经典之声誉,唐代韩愈尤重《大学》。韩愈当世,佛教盛行,他认为佛教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精神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根基大相径庭。从儒家角度讲,佛教之种种是破坏儒家搭建的生活世界,所以韩愈以《大学》“修齐治平”之修身入手,从理论上反对佛教发展。韩愈的理论策略虽从政治、伦理上抗争佛教,但在中国社会里,排佛效果并不明显。李翱据此认为,欲与佛教对抗,须从人的内在精神入手。这样,既要从《大学》 开始,也要注重《中庸》,《学》 《庸》 的历史与文化使命逐渐上升。
随着“道学”或“理学”的兴起,“ 五经”在儒家经典的核心地位渐让位于“四书”,直至完全取代。这种转变,既是源于社会疑经思潮的盛行,即人们发现“ 五经”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作伪、辩伪等问题,对此提出质疑;也因汉唐经学化儒学受到佛老思想挤压而日益萎缩。到了北宋,宋明儒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四书”,以求发扬孔子大道与儒学正统之立场。[5]对儒家经典进行“内在超越”式地发挥与高扬。
理学开山周敦颐,从《中庸》《大学》中提取“ 诚”之范畴。张载更进一步,“ 学者信书,须信《论语》《孟子》… … 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6],通过学信“四书”,开启气学诠释进路。王安石则运用自身政治力量,将论孟二书举为科考之学,确立“ 四书”的官学地位。时至二程,以道自任,对学庸二册高度推崇,重构并阐发孟子性善之旨,强调性道不二、天道之理与仁义之性相互贯通,从“ 理”之本体发展出“ 格物致知”“主静涵养”工夫论。南宋朱熹,继程颐之学,综罗百代,著有《四书章句集注》,此书是朱子最主要的诠释性哲学著作之代表。朱子通过该书,系统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义理系统。此书问世,标志“ 理学化儒学”取代“经学化儒学”。
从总体文化流变看,“道学”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这不仅是儒家对佛教挑战的回应,同时是儒家对魏晋玄学的挑战的回应和消化。从唐到五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遭到极大破坏,宋初的士大夫儒者对五代风气十分痛恨,试图拨乱反正,重建失落的传统价值与人生理想,并对社会秩序作出切实有效的规范与整顿。在这个意义上,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知识、思想、信仰世界与价值体系的文化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恰好这种对经典文本的不断追问与根源性解释探索,是当时儒者士大夫中普遍的思想共识,这使古典儒学通过理学的发展而得以复兴。可以说,宋明理学对汉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大反省,并通过这种反省致力于儒学复兴。
二、“理一分殊”的本体架构
在宋儒之前,释家各派大谈体用,精思一多,如华严“四法界”“六相”,于此用力颇深。为使“ 四书”更好应对佛老挑战、重建儒门威信,宋儒开始设计“ 构建”儒家形上学。经过张载对“气”的发挥,至程朱理学则把“理”做为最高本体,把宇宙自然与儒家伦理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理学世界。
(一)朱子对“理一分殊”的思考
检寻《朱子语类》,便有将《睽》与“ 理一分殊”关联的对话:
问:“‘君子以同而异’,作‘理一分殊’看,如何?”
曰:“‘ 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这处又就人事之异上说。盖君子有同处,有异处,如所谓‘ 周而不比’,‘群而不党’,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处说,不必深去求他。此处伊川说得甚好。”[7](《朱子语类·睽》卷七十二)
《睽》卦下兑上离《象》曰:“ 火动而上,泽动而下”,意水火两相乖离。《象传)解:“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同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强调天人宇宙中睽中有合,合中有睽的关系。万物虽其性不同,却实有共通,下降到人事,也就是说,存在着《象传》所讲的“君子以同而异”之理。朱子并没有局限在象的固有之理,而是期向“ 天人宇宙”理境关系上之跃升,将《睽》与“理”关联。
那么,“ 理一”与“ 分殊”是怎样关系,事物分殊是怎样形成呢?
学生问“五殊二实”一段。… 又有‘四时错行,日月代明’,自有细小去处。‘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小德川流’是说小细底,‘大德敦化’是那大底。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 又云:“‘一实万分,万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处。”[7](《朱子语类·周子之书》卷九十四)
也就是说,“ 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7]朱子讲到分殊,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理,此理处处皆浑沦,“物之差别分殊在于阴阳五气,实为事异则气异,但潜伏之理同。”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朱子和儒家眼中的万物自然乃是一个生命整体[8],即“ 太极”,并非为分割的碎片孤岛。“理一分殊”不是物理式的分解,而是生命整合的“道之大全”。因此,每个人心灵都是一个太极,而且每个人又是独特的,自己的太极还能与其他人的太极相通。这一观点,是西方的主体观、客体观都不能解释的地方,只有像莱布尼茨“ 单子论”跟这有一些相近。只是莱布尼茨并没有想透这一层关系。因为他的单子论是封闭的,尽管每个单子有着各自的丰富。这可以说,每个单子都是一个太极,它们事先被调好,由上帝将他们同步进行,这与我们朱子或者宋明理学中所讲的“理一分殊”尽管一定地方相似,但还有着很大不同。因此,朱子的“理一分殊”本体架构,不仅只是讲由普遍和特殊,或整体与部分的系统调节关系,还是一种类似圆圈式“天人宇宙”的本体生命之嵌套关系,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共振、同构相叠、相息相关,一体充塞。这种关系,朱子引借“月印万川”,“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得这些道理。”[7]
就“ 理一分殊”而言,儒家“ 一贯”之语,亦关涉这一问题。朱子曾以散钱、索子之喻讥讽释玄。“贯”如散钱、“一”是索子。释氏“没一文钱,只有一条索子”。“不愁不理会得‘一’,只愁不理会得‘贯’。理会‘贯’不得,便言‘一’时,天资高者流为佛老,低者只成一团鹘突物事在这里。”[7]朱子依托“理一分殊”,建构一套包罗万象的本体体系,对抗佛老。既把儒家思想的道德主体性树立起来,又别于他门,超越仙释,使天理根源与道德主体相互融合,体用一如,天人不二。即使在气学、心学(陆九渊)的挑战激荡中,朱熹理学世界的根本及形上本体,也未根本地动摇过。
(二)“理一分殊”下的经典诠释
朱子将经学与理学融于一片,对经典中的概念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与发挥。经典诠释的终极指向是什么?朱子答案是“理一分殊”。
针对“《论》 不及《庸》”的问题,朱子解:“ 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无异。《论语》是每日零碎问。臂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说千言万语,皆是一理。须是透得,则推之其它,道理皆通。”[7]因此,此二书无别,“四书”亦无别。朱熹进一步解释:
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圣人千言万语教人,学者终身从事,只是理会这个。要得事事物物,头头件件,各知其所当然,而得其所当然,只此便是理一矣。[7](《朱子语类·论语九》卷二十七)
朱子讲“ 理本一贯”,如颜子之人可‘ 闻一知十’,但曾子之类仅能逐事根究。所以孔子告之曾子‘ 吾道一贯’。假如曾子不理会万殊之理,那么“ 一贯”者,又如何贯呢?又如‘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许多事,怎么“一贯”呢?所以学者戒慎恐惧而慎独,存省切己,步步考究,证见天理。“且如《论》《孟》,须从头看,… … 且自平易处作工夫,触类有得,则于难处自见得意思”[7]。朱熹在注解“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时,说“统而言之皆仁,分而言之则有序。… … 谓理一而分殊”[9]。解释“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论语·公冶长》 时,说:“ 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9]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注解四书并非只是为了注解四书。朱子注解四书是为更全面地面向现实世界与人生道德的实践考量,来讲人如何为人,人如何处理与人、自然万物关系之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朱子教人学会体认天道,回溯到自身生命,心灵世界的深处。
总之,朱子的“ 理一分殊”是从生命整体的立场上,通过注解经典的方式,试为人类创造理想的信仰世界,建立一套具有生命力的知识、规范与价值法则。一方面,在宋代之前,儒家虽出现“ 天人感应”,因其缺少系统的本体论思想,难在自身哲学体系上,与道玄“道本论”、佛家“本体论”抗衡。理一分殊的出现,凝聚了“ 天道性命”的诸多关窍,使朱子四书学诠释体系增添了本体架构的解释特色。另一方面,“ 理一分殊”的运用,道出理学视野下宇宙天人的本体关系,特别是诠释道德之秩序及其理想的形而上世界的问题。朱子把宇宙万物和人伦圆融道德于一片,提出了“ 以理为体,以万物为用,理本体作为万物存在的根据,存在于分殊的万物之中,万物即是本体之理的体现”[10]说法。这为儒学的本体论视域开拓发展空间,实现儒家哲学从宇宙论走向本体论叙事的重大学术思想转折。
三、“格物穷理”的工夫进路
朱熹注解经典,运用“ 理一分殊”本体诠释的解释构架,同时还使用“ 格物穷理”的工夫进路与之配合。这不仅是为应对佛老对儒学的思想挤压,也为实现亲历经典、学以成人的目的。
(一)朱子对“格物致知”的思索
“格物穷理”,首先表现在朱熹诠释《大学章句》上: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9]《大学》
为什么这样朱熹对“格物”有这样的说法呢?或许主要是缘于佛教与儒家的发展关系。佛教谈“ 空”、谈“无人相我”,离开现象世界,特别是离开了伦常日用,佛教认为通过摆脱现世物质,可以荣登彼岸。另外,自唐宋以来,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服务方式是通过科考制度进入官僚体制,完成治平天下的理想与使命,而且,君子之道在道不在器,“ 君子不器”,这一阶层首要具备的是以史为鉴,参政理政的能力,而不是学习专业性的生活技能。所以,朱熹提出“至物穷理”,强调不能离开世间事物来求理,也强调以格物的现实作用,指向心性修养,通过心性的修养,使士大夫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格物致知”是什么?汉人讲“ 格”释为“ 来”,朱子认为这种表述并不清晰。他认为“ 格物致知”是“ 至事穷理”,“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补大学格物传》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穷理则是“ 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达而及其所未达”[7]。朱熹说的很明确,“ 通过明白“ 今日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阶段,工夫久之,到了这个阶段,可达到“ 豁然贯通”“ 众物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境界。就格物本身说,格尽事物之理以“ 识仁”、以“明明德于天下”、以体贴天道之“理”。就“致知”而言,“致知”也是为了求其至极“天理”,汇至“ 本源”,“ 止于至善”。
那么如何止在“ 至善”呢?朱子认为至善不是别的,而是生生之仁。“学者须是求仁”[7],“仁是生生不已之意”[7],“仁是天理之统体”[7]。万物之仁表现在生生之上,人能自觉之仁爱,便将“格物”表露无遗。“《集注》说‘爱之理,心之德。’… … 其理谓之仁。… … 要识得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己上看有这意思是如何。”[7]朱子将人与万物在“理”之处以“生生之仁”相挂搭,有了生命的流动意味,格物之真义就此展现。在朱子对“ 格物穷理”诠释处看,朱子以“ 格物”为始,通过“明明德于天下”来求“止于至善”为根本要求,这是朱子注解“格物”的独特之处。从朱子对生命的观照问题看,朱子认为人们从生命整体意义理解世界,而非物理局部看待世界,朱子所讲之“ 格物”并非将人置于万物之外,而是将人放入万物之中,在生命文化的观照下体贴“生生不息”之天道,反求诸己,穷格自身。
(二)“格物穷理”下的经典诠释
如果说,在“四书”中,朱熹“ 格物穷理”为《大学章句》提供解释可能,那么,在其他三书中,《论语》作为源头,也有着朱熹理学的广阔诠释空间。
朱熹在《论语集注》的公冶长篇总叙处说:“ 此篇皆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盖格物穷理之一端也。”[9]此处二十七章,皆为“格物穷理”。《论语·子罕》言:“颜渊喟然叹曰:“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朱熹作注曰:“ 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9]《朱子语类》对此处讲法,更为透彻:“‘ 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见得周匝无遗。至于 ‘ 约我以礼’,又要逼向身己上来,无一毫之不尽。自古学问亦不过此二端,但须见得通透。”[7]
格物工夫“须是彻上彻下,表里洞彻”,不仅要“ 尽其全”,也要“至其极”。朱子看似教人“ 博文约礼”,事事向外做工夫不重心上,但是朱子对心的一边,一点也不马虎。“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7]此心虚灵不昧,万理具足。所以落实在人生实际的事为工夫看,朱子的话没有错。
“格物穷理”思想是朱子备受关注的,也是朱子诠释“四书”的点睛处。朱子讲,“格者,至也。”“穷得十分尽,方是格物。”他将“格物”视为“梦觉关”,穷尽事理,便会有了知识,不然,则如大梦一世,惶惶一生。“这样看“格物穷理”中含有一种知识性的发展,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这是知识性层面的事实展开,但是朱子的知识之学,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 求仁”,知识之学的最终指向是朝着包含对错、善恶的道德性层面的价值所展开的。“‘格物’二字最好。… … 凡自家身心上。皆需体验得一个是非。若讲论文字,应接事物,各各体验,渐渐推广,地步自然宽阔。”[7]这种对“格物致知”诠释注解之法这不是别的,而是实际体会、体验而得的道理。要把自己放进去,从自家生命中寻求意思,体贴人生,这是生命展现,是工夫修养的进路实践。
朱子提出:“操存涵养,则不可不紧,进学致知则,不可不宽。”[7]他早年着重将两者并列,而晚年则感到过去对“ 尊德性”的关注不够,而肯定应该“ 以尊德性为主”。所以说:“尊德性工夫甚简约,且如伊川只说一个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祇是如此,更无别事。某向来祇说得尊德性一边轻了,今觉见未是。”[7]朱子把“ 尊德性”和“ 道问学”相互关联,并通过工夫修养,深入到内在的心灵世界。因为“格物穷理”这种修养工夫如果失去“尊德性”的普遍观照,将导致“ 道问学”产生一种对象化活动的异化或扭曲。所以为修正这种话语模式,朱子认为需要体道(尊德性)活动,经由“ 道问学”向“ 尊德性”升入。[4]“ 道问学”在“ 尊德性”的光照下,可以免于知识系统建构所造成的执着跟染污,“ 上通于道必须经过体道的活动,使道的光照化掉知识系统的执著与染污。”[11]这也就可以理解宋明理学家为什么强调“ 德性之知”之因,“ 德性之知”是一个体道活动。相对地,“见闻之知”是人对存在事物的认知活动。
综上,朱子在经典诠释思想上兼采汉宋之学,通过“ 理一分殊”本体构架与“ 格物穷理”工夫进路对儒家经典成功地作出新诠释。古人言“ 合纵连横”,喻结构坚固,纵横交错。朱子的理学经典诠释思想亦可用“纵横”作比。“理一分殊”,可以说是纵向的贯通天人,而“格物穷理”,可以说是横向的关联一体。朱子经典诠释的思想在于人体会人之真实情感,在于实现人对人生的体知。“理,只是一理。… … 且如言着仁,则都在仁上。”[7]这种生命共同体之关怀,对生命的敬畏和仁爱,就是经典诠释的最终目的。
四、朱熹理学逻辑结构下经典诠释
“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千百年间“ 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 … 熹而始著”[1]。《续资治通鉴》 对朱子也做过总结:“ 熹自少有志于圣道,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为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自经旨不明而道统三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所著书为学者所宗。”[12]朱子会通佛老,传继道统,完成接续孔孟的使命。所传之道,为学之宗,在其思想体系与著书之中等待后人挖掘。如何解读此体系,可通过分析朱子使用的概念、范畴[2]讨论其学逻辑关系与结构。有学者表明,朱子理学逻辑可以解读为“ 理— 气— 物— 理”的模式[13],这是朱熹理学逻辑结构,也是其理学世界图式。
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理。[7](《朱子语类·周子之书》卷九十四)
“ 理”是朱子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赖“ 气”推扩,依“气”挂搭。其中“各物”是“理一”在现象界的展现,是“理”借“气”而化生。这也是说,“上推下来”,“理”—“气”—“物”(五行);从“下推上去”,“物”(五行)—“ 气”—“理”。朱子认为“理”借助于“气”化生了“ 物”后,又通过“格物穷理”的工夫进路,使“理”从而归复到“ 理”自身。
朱子“极注重心性与功夫”[2],在“理一分殊”与“ 格物致知”的诠释思想中,打通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的关窍,并通过理学逻辑结构对经典诠释问题作出进一步解读。其中,朱子主要遵循“ 分析语言”与“ 体验唤醒”的两条诠释路线解读经典。
一方面,运用分析、逻辑来讲究诠释经典的方法。在诠释道(理)的过程中,朱子区分“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自然”与“本然”之理,“生理”与“必然”之理。[14]通过对“理”的解读,朱子之“理”不同层面就此展开,使《四书章句》带有浓厚理学意味。另外,为更好体贴和诠释经典,朱子进一步说明“心”之问题。如《孟子集注》,朱子对孟子的“心”之分析,并以“体用关系”解释孟子性情学说,从体说,心是“神明不测”[9]之心;从用说,心是“知觉运动”[9]之心。朱子以“心”贯通天人,以“理”言说生生,体现儒家“一贯”之道,体现了人与万物之间,有着一种生命情感的内在联系。
另一方面,虽从概念上不能说,但实际上还是要“说”。这个“说”,是情感的生命的语言。生命本真之所在,此逻辑结构并非单纯的概念式,是落到了“ 生”的视域下思考。“理”是什么?“生理”又是什么?朱子讲这是生命创造之理,含生命真情。朱子《四书集注》,凡是遇到与人的生命、心灵直接有关的语言或难以表达的要害处,朱熹在作出言语解释后,常言“ 豁然贯通”“深体味之”“以身体之”“须实体察”“体之而实”[9]等体验唤醒,这是从生命体验中说出来的生命语言,这种体贴是随着人的感情生命表现出来的最基本的存在状态。
朱子将宇宙与道德贯通,“ 人是与自然界内在统一的德性主体,而不是与自然相分离的认识主体,目的是实现真善美的人生境界。”[14]这种境界所展现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一体化。生活世界并不只是一个概念的分析的世界,而是一个生活在大化流行的人文世界,且与自然世界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交流情感是维系这种联系的重要方式,体贴情感是这种联系的真实展现。在朱子理学逻辑结构中看到世界即是概念的,又并非仅是概念的,其中还包含着宇宙万物的生命一体化,这既是朱子经典诠释的思想展现,也是告诫后人的真情心言。
五、结语
在朱熹的经典诠释著作中,朱熹已将自己哲学性格完全展现,而待后世挖掘与思考。朱熹经典诠释思想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命的、实践的智慧哲思。钱穆先生讲:“朱子把理学家的一切说法,切实道先秦孔孟传统。只有朱子才能辟佛,把佛家尤为是禅宗的病根,都挖净尽了。”[15]
朱子经典诠释思想,一方面它作为中国近世化的文化形态,可以被看做是中国的中世纪文明和近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中间形态之一。另一方面,它的存在也与外来文化挑战有关系。当本土主流文化在面对他者文明进入时,都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发展过程。朱子通过深入探讨佛道思想,清扫儒学思想中的泛滥沉疴,实现儒学理论与范式的创新突围。所以,回顾当下,身处在更广泛的多元化的世界文化环境的儒家与儒学,又该如何发展呢?由此问题出发,再看朱熹理学经典诠释思想,或许可以从中寻找到一定的对当下“古代经典新诠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