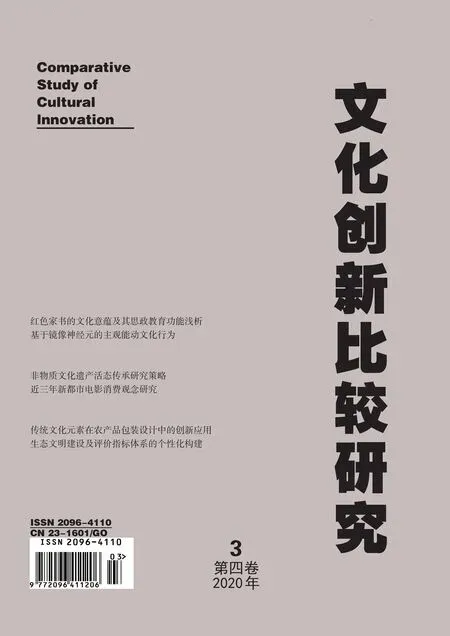1912-1949年日本满学研究特点及原因初探
2020-01-02钟华
钟 华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1912年和1949年对中日两国而言都有着及其重大的意义。1912年是日本大正时代的开端,是日本历史上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开启了新纪元。1912-1949年可以说是中日交流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随时代背景的转变及历史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日本的满学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和特点,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将这一时期切分为四个阶段分别进行考察和分析。
1 1912-1926年
1912-1926年期间,日本学者对满学、满洲的研究内容虽涵盖历史、建筑、语言、民族等,但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历史和游记方面。历史地理研究方面有稻叶岩吉于1913年在《满洲历史地理》发表的《清初的疆域》、《建州女真的原住地及迁驻地》、《汉代的满洲》;1915年发表的《前清宗室直领地禁买》等等。游记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于1912年出版发行的《满鲜之旅》,泷泽真弓于1924年发表于《建筑杂志》的《满鲜旅行日记》,以及西山荣久于1925发表于《东亚经济研究》的《满蒙及北支杂记》等等。
《满鲜之旅》中对当时的满洲境内的新京、哈尔滨、抚顺煤矿、奉天北陵、鞍山钢铁、大石桥迷镇山、旅顺忠灵塔、大连港码头等,主要城市、观光景点、主要矿藏、军事要地等都配有照片插图,做了较为详尽的说明介绍。同时对日本和满洲进行了对比,称之为「狭い日本と広い満洲、人口の課題に悩む日本と人口希薄の満洲、資源に乏しい日本と富源の満洲、工業国日本と原料供給国としての満洲」、并声称「この新興国が包蔵する豊富なる資源をいかに開発すべきか、又この産業を如何に振興さすべきかは、日満両国民の繁栄に至大な関係を有するのみならず、我等大和民族に課せられた天の使命である。」,「即ち、日本と満洲とを打って一丸とし、有無相通ずるときにこそ、日満両国はまったく鬼に金棒であり、この前途は祝福されるのだ」。从这本书的记载当中我们对当时日本的野心可见一斑。
日本这一时期的满学研究特点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1912年日本进入大正时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其前期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前所未有的盛世。并受欧战结束的世界大背景影响,民族自决浪潮十分兴盛,民主自由的气息浓厚。在经济上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中国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和巨额赔款,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并成长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兴起的同时,中国境内却战乱不断。“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北京,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掌控了北京政府,中国形成了南北共治的局面。清末的腐朽统治和“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动荡,给野心勃勃的日本创造了机会,东北地区丰富的资源也对其产生极大的诱惑。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日本当时对满洲的研究多为考察性质的研究也是在为之后的侵略做充分的准备。
2 1927-1931年
1926年12月25日开始日本进入昭和时代,同时也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黑暗道路。1927-1932年期间,日本满学的研究范围除继续沿袭之前已有的历史、地理、语言等之外,较为显著的是对满洲外交关系的研究,同时与大正时代相比研究范围也进一步拓展,也包含有少量的宗教及农业方面的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方面,影响较大的是与谢野宽的《满蒙游记》。与谢野宽夫妇1928年5月来到中国东北及内蒙一带旅行,回国后,于1929-1930年间先后在《横滨贸易新报》发表了《满蒙游记》,之后以夫妻合著的形式出版了单行本《满蒙游记》。对于满洲的国际关系研究方面主要有井上义孝于1927年在《外交时报》发表的《北满州与俄中关系》;石田千之助于1928年发表的《有关满洲的俄国文章(1)、(2)》、《欧美人的满洲研究回顾(1)、(2)、(3)》等等。宗教、农业等其它方面的研究有村田治郎1931年发表的《清初满洲喇嘛教建筑》、《满洲萨满教建筑》;村越信夫1927年发表的《有希望的满洲小麦生产》,《满洲天气谚语》等等。
在《满蒙游记》中,与谢野宽夫妇记录了由大连港登陆,游历大连、哈尔滨、长春等地的见闻。政治上,他们透露出对满蒙人民排日的不满;经济上担心不肯吃苦耐劳的日本商人在和中国商人的竞争中不利,认为满蒙的开拓,“非得树立一个在不久的将来,将甘于勤劳的日本农民和商人共三四百万人移民到这里的国策不可。” 游历过程中,与谢野宽夫妇不止一次陶醉于中国东北三省的美景,窃喜“满铁”任用了适合的贤达之才,感慨于日本和满蒙的“亲善关系”。
《满蒙游记》无疑在向日本国内人民宣传中国大陆的富足美好,获取民众支持其大陆策略方面起到了助推的作用。当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去考察时,发现与谢野宽夫妇游历满洲是“受邀”前往的,而发出邀请的正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日本在满洲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指挥中心。“满铁”自1909年成立以来,不断邀请日本著名作家、学者、艺术家到“满蒙”一带旅行,可以说这是其对日本国内进行宣传的重要战略。他们招待这些文化人和学者,向他们展示在日本的努力下,满洲已成为乐土天堂,要求他们回到日本后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游记,蛊惑国民,为今后进一步的侵略奠定民众基础,而受邀的文人学者无形中充当了军国主义的喉舌,为其侵略实质粉饰美化。这也是这一时期游记及对满蒙外交关系研究增多的重要原因。对满蒙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有良好把握的基础上,更有利于日本制定或调整对满蒙地区乃至中国的侵略计划。
3 1932-1945年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使其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傀儡伪政权伪满洲国成立。自1932年始至1945年日本战败,13年间日本对满洲的研究较之以往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在研究数量上,都创下了前所未有的新高。研究领域不仅涵盖语言、历史、政治、经济、考古、宗教、民俗、外交甚至还包括军事、农业、生物等等。据《日本关于东北亚研究成果选编》的不完全统计,发表在日本有关杂志、论文集上的满学研究论文有200余篇。
如青木富太郎1935年于《历史学研究》发表的《满洲考古学及东亚考古学》;秋叶隆1934-1944年发表的《满洲萨满教的家祭》、《鄂伦春・萨满思想》、《南满民俗采访之旅》等一系列宗教、民俗相关的论文;天野元之助于1932-1933年间发表的《满洲经济的发展》、《满洲佃农及其性质》等一系列经济类论文;有高严于1934-1942年间发表的《清代史概述》、《清代社会与汉人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满洲移民》等多篇历史相关的论文;有马驷马与1935年发表于《东亚经济研究》的《满洲奉天市金融机构》、井关孝熊1932年发表的《满蒙庶民金融机构》等经济类论文;伊藤秀一1933年发表的《满洲“金钱外交”的发端》等外交相关的论文;安倍健夫在1942年于《东亚人文学报》发表的《满洲八旗牛录的研究》等军事管理相关的论文;石山吉胤1937-1938年发表的《从农业的观点看齐齐哈尔的气象》、《北满气象与农业的丰歉》等关乎农业的论文;水野馨于1931-33年发表的《关于满洲的特殊鸟类》、《报春的满洲鸟类》等等关于满洲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究其原因,此时的日本已然完全占领东北三省,并逐步推进其大陆政策,实行对中国的侵略。日本组建伪满傀儡政权,一方面对东北三省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一方面以此为据点一步步扩大侵华战争,使得原本富庶的东北彻底沦为日本经济的附庸,成为其 “以战养战”的工具。本文认为此时的东北三省对日本来讲已是“囊中之物”,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对当时的日本而言势在必行,唯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满洲各个领域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日本更深远长久的占领统治。所以当时所处的深刻的社会背景成为这一时期满学研究兴盛的重要原因。
4 1945-1949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而此时的中国虽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却马上陷入国内战争的艰苦时期,直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迎来了新的曙光。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社会带来深刻影响。战后的日本民生凋敝,一片萧条。这一时期日本的满学研究也近乎陷入停滞状态,只有少量研究论文发表。如史学研究方面日野开三郎发表的《勿吉考》,《靺鞨七部考》;语言研究方面宫崎市定于1947年发表的《清朝国语问题的一面》等。
区域研究对文化发展、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等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不一定完全依托社会政治背景。但鉴于1925-1949年特殊的中日关系,同时结合不同的时间段,日本满学研究所呈现的特点,笔者认为这期间的日本满学研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即日本的对华政策密不可分。当然其中不乏本着文化交流的宗旨,刻苦钻研的学者,但受日本当时大陆政策影响者也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