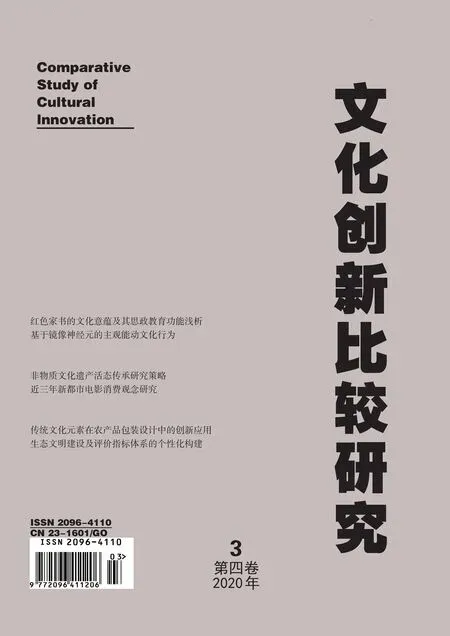英语隐喻性名量搭配教学研究
2020-04-14张雳王煜
张 雳 王 煜
(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
1 引言
语言类型学研究认为,汉语属于量词语言,名词通常没有单复数变化;英语属于名词单复数标记型语言,没有量词系统,并且这两种类型的语言不兼容,即一种语言不能同时是量词语言和单复数标记型语言(石毓智2001)。事实上,量词语言汉语也有少数单复数标记,如:“们”和“些”;量词没有成为英语的正式词类,但英语中也存在大量表量结构,如:“a qualm of tenderness(一股温情)”,“a fit of enthusiasm(一阵热情)”或“a tittering of magpies (一群喜鹊)”,“a clattering of choughs(一群红嘴山鸦)”等。
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介语阶段产出性词汇能力偏低已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研究发现学习者产出的词汇类符较少,词汇搭配的丰富性和产出的地道性都不尽人意(许子艳 2013),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动词和名词,对英语表量词教学关注不多。本文作者在教学中发现,英语学习者在中介语阶段英语表量词产出的能力同样偏弱。以翻译课上“a _____ of hope”的搭配训练为例说明,在某省属高校两个班级共66名英语专业学习者中,多数能用到 “a thread of hope”,少数较高水平的学习者能用到“a flash of hope”和“a glow of hope”或“a twinkle of hope”,极少有学习者能大部分产出以下英语母语者常用的隐喻性名量搭配:a crumb / flicker / flood / flutter / gleam / glisten / glitter / glimmer / light / ray / rush / shred / shimmer / sparkle / surge / thrill / throb of hope。“在这些隐喻性名量搭配中,表量词有隐喻性,其表量功能减弱,表意功能增强,具有激活名词所指事物的某种属性并使之得以突显的作用”(毛智慧、王文斌2012)。本文以对比分析英汉表量词差异为基础,总结其差异性对学习者的影响,并提出提高英语隐喻性名量搭配课堂教学效率的方法,进而为改进二外英语词汇教学方法提供思路。
2 英汉表量词对比
英汉量词表现出差异性。整体而言,作为量词语言,汉语的个体量词丰富而专用性强,但在修饰抽象名词时,如在情感域中的隐喻性个体量词层面,英语表量词更为丰富,并且词汇语义饱满;汉语在情感域多使用语法化程度高的“阵”与“股”。在集体量词方面,由于英汉语言类型的差异,英语方式动词类型多于汉语,又由于英语的时间特性,量词多属于动源量词,方式动词类型多直接导致了英语中出现大量富有动感、极具描写性的集体量词。在具体层面,由于在汉语中声音成分通常不参与动词词汇化,汉语声音类方式动词出现词汇空缺,使汉语相应的突显声音属性的动源量词缺失。
2.1 英汉表量词的功能
在英语中,“a book / two books”这样的表达不需要使用表量词,“book”在英语者的认知中是有边界的差异化个体,不需要表量词来个体化名词。但汉语必须用“一本书、两本书”来表达,即汉语在这种情景下使用量词计量是强制性的,并由此导致汉语此类个体量词的数量以绝对的优势超过英语。学界普遍认为,汉语的个体量词数量多且专用性强。“piece”可译为“篇 / 段 / 首 / 幅 / 桩 / 项 / 番 / 枚 / 个 / 件 / 块 / 张/ 条 / 卷 / 截 / 匹 / 片 / 出 / 枝”等,通用性强的英语个体量词“piece”多达20个以上的汉语翻译也为汉语个体量词的优势提供了佐证(王晓玲 2001; 孟瑞玲、王文斌 2017)。在例(1)、例(2)中,英汉在表达抽象名词的类属性时可使用光杆名词;但在例(3)、例(4)中,英汉表量词的使用是对“希望”个化的基础上对其计量,表量词的使用是强制性的。
(1)She never completely gave up hope.
(2)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科学的希望。
(3)Fans clung to a glimmer of hope that their team might score a last-minute touchdown to tie the game.
(4)只要存有一丝希望,我们就不能让这丝希望破灭。①
量词语言就是它所修饰的名词被标示为某一范畴的成员(Lakoff,1987)。这个定义说明了量词除个体化名词为其计量的功能外,量词还有标示名词为某一范畴的分类功能。 “量词是有意义的,量词表明了名词一些明显的可认知的或规定的特征。量词的语义是指量词指示的实体所具备的能感知的特征,即量词是认知主体与感知的语言上的联系” (Allan,1977)。 这种“明显的可认知的”或“规定的”特征即是量词对名词的“描述”。量词建立名词的描述性指称表述,突显名词所代表事物的某一方面,为交际提供描述信息” (Foley,1997)。这个定义指出了量词在交际中提供名词诸方面具体特征的信息功能。虽然量词系统表征了各种有差别的语义范畴,如有灵性、硬度、数量、社会地位等,但形状或许是其中最有典型性的,反映了人类与周围环境的互动(Langacker,1991)。上述定义强调了形状这一视觉属性具有典型性,并指出量词是说话人与客观事物互动的产物,换言之,量词是人对客观事物认知的产物。
研究者在对汉语量词发展历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观点:“从唐代到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的发展导致同音词数量减少,与之相伴的是量词的分类功能趋于弱化。量词作为个体标记是汉语量词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汉语本身内在的需要,分类功能是次要原因。现代汉语中量词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量词系统趋向简化,万能量词“个”有取代其它量词的趋势”(金福芬、陈国华,2002)。语料研究也表明了汉语量词至少在某些域中出现了简化的倾向,英汉情感域隐喻性量词的使用证明了这一趋势。汉语表情感的量词主要有“阵、股、丝、缕、团、片、线、场、番”等,在这些量词中,“阵”与“股”高频出现,虚化程度虽不能与“个”相比,但与这两个量词搭配的表情感类名词却涵盖了多种情感类型,如“一阵怒气/心酸、一股喜悦/哀愁”等(张雳、王煜,2012)。反观英语情感域隐喻性量词,与“阵”与“股”的语法化程度高相反,英语表量词词汇语义饱满,详尽地表现了认知主体对情感认知的多维视角。仍以上文中的与“hope”搭配的隐喻性表量词为例说明,英语者的认知视角分别集中在“希望”这一情感的“形状属性”(a crumb / shred / ray / light of hope)、“动态属性”(a flash / flicker / flutter /flood/ gleam / glisten / glitter / glimmer / glow / rush / sparkle / shimmer / surge / twinkle of hope)、甚至于“灵性”(a thrill / throb of hope)等。在汉语中,与“希望”搭配的量词少于英语,常用的只有“丝、线”等。总之,以个体量词见长的汉语在表达“情感类抽象名词”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语法化程度高的“阵”与“股”在情感域通用性强,有很强的搭配力,词汇语义虽没有完全虚化,对所修饰名词的描述功能却已然弱化,词汇语义饱满度远逊于相应的英语表达。
2.2 英汉语言类型差异对表量词的影响
孟瑞玲、王文斌 (2017)从英汉语对待名词与动词的差异分析了汉语的空间性特质和英语的时间性特质。汉语者对形状个体量词的大量使用,反映了汉语者倾向于借助形状这一视角,即通过量词所指名物的空间性来认知事物,这种对事物形状的心理或思维诉求,是对事物空间性的关切。而英语者对世界的认知是时间重于空间,这种对时间性的青睐与英语大量专用性强的集体量词直接呼应。英语繁复而专用性强的集体量词从汉语量词“群”的英译可窥见一斑,“群”的英译超过100个之多,主要有“flock/ horde / herd / swarm”等。研究者以集体量词“a run of salmons(一群鲑鱼)”、“a flock of birds(一群鸟)”、“a swarm of children(一群孩子)”为例,从词源、句法、语用、认知四个角度进行分析,发现这些英语集体量词在本源上均具有一定的动词性,其以动表意的特征明显,这与汉语量词中名量词突显的特点不同。在句法上,英语的“数 + 量 + of + 名”表量结构中各成分的语序相对固定,这种不可逆的一维线性特征,反映了英语者的时间性思维认知。在语用方面,这些动源量词表现出弱指称性,与汉语名量词不同,它们不能脱离表量结构单独使用指称相应名词,但脱离表量结构,它们可以被直接用作动词,上例中的“run,flock,swarm”都是名动兼职的词。从认知视角看,英语集体量词多数用于描述事物的动作行为,这又与汉语通过量词突显名词的形状大不相同(孟瑞玲、王文斌,2017)。
移动事件类型理论认为,英语属于典型的方式语言,即移动动词的词化模式主要是[移动+方式/致使](Talmy,2000)。语料调查表明,“由于英汉语对方式的概念化和词汇化方式不同,汉语方式动词类型没有英语丰富,或者说,汉语方式动词的语义区分没有英语细致”(李雪、白解红,2009)。汉语的方式移动动词没有英语丰富,与英语丰富的方式动词对应的是汉语的分析式表达,即“方式副词状语+移动动词”形式。英汉方式动词的差异也导致了动源量词的差异,作为典型方式语言的英语有着极为丰富的方式动词,为英语大量的动源量词提供了丰沛的储备。再以上文中表“动态属性”与 “hope”搭配的表量词为例说明,这些词大多属于名动兼职的词。英汉语移动动词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英语方式移动动词类型丰富,研究者还描述了英汉语方式移动动词在具体词化模式层面的差异,即具体层面的错合性和对应空缺。汉语中不存在英语中表达某些范畴的方式动词,例如表达“移动带有声响”的这类词。英语中拥有相当数量的这类方式动词,例如:“rattle,roar,spatter”等(李雪、白解红,2009)。在汉语方式动词词汇化过程中,“声音”语义成分通常不被包容,而以拟声方式副词形式出现。在英汉词典中,“rattle”被译为“咔嚓咔嚓行进”或“哇啦哇啦讲个不停”;含有声音语义成分的行为动词“gaggle”被译为“嘎嘎叫”;“slurp”被译为“出声地吃或喝”;“giggle ”被译为“咯咯地笑”。汉语多采用了“副词+动词”翻译这些含有声音语义成分的英语动词。英汉语方式动词词汇化在“声音”语义成分的差异也为“突显客观事物听觉感观属性的隐喻性量词似乎仅存在于英语,汉语中尚未发现此例”(毛智慧、王文斌,2012)提供了解释,这些英语表量词来源于方式动词,并包含声音语义成分,汉语中“声音”语义成分不参加词汇化,导致了汉语几乎没有突显听觉感官属性的隐喻性量词。在英汉词典中,“a giggle of schoolgirls”被译为“一群女学生”、“a giggle of presidential secretaries”被译为“一群总统女秘书”,量词突显的名词的声音属性消失殆尽,实属无奈之举,但“a gaggle of critics”被翻译为“一伙吹毛求疵的家伙”,为弥补汉语集体量词“伙”无法突显声音属性的不足,在名词前面添加了形容词。汉语量词无法突显“声音”属性的不足,是否表明汉语量词的描写性就在此方面先天不足呢?回答自然是否定的。汉语者耳熟能详的“听取蛙声一片”诠释了汉民族赋声音以形态的“描摹”专长,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语言的能量守恒性。
3 英语隐喻性名量搭配教学策略
3.1 英汉表量词差异与学习者困难
汉语繁复的量词系统主要表现在个体量词方面,这些词在英语中通常没有所谓的“对等词”,表量词虽然是英语的局部现象,但其集体量词和描写抽象情感的个体量词丰富而词汇语义饱满。英汉量词的差异导致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相应学习困难。“按照外语词汇发展模型,外语学习者词汇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形式阶段;在第二阶段,学习者通过强化外语词汇与对应的母语翻译词(或称为同“译”词)之间的联系,使外语词汇条目与母语词汇对应的信息激活。在第三阶段,外语词汇的各信息融合,与母语者相似”(Jiang,2000)。一般而言,学习者会较长时间处于第二阶段,在此阶段,母语词汇信息充当媒介。在例(5)到例(10)中,如果学习者以母语量词“点”为媒介学习目标语 “a speck of,a shred of,a grain of,a particle of,a morsel of,a morsel of,a crumb of”,那么可以预见,学习者在用目标语描述 “humor,interest,love,sense,fun,comfort”时,可能会局限于通用性很强,语义泛化的“a little”,很难产出描述抽象名词“微粒(shred)”、“碎片(speck)”、“细粒(grain)”、“颗粒 (particle)”、“小片(morsel)”、“碎屑(crumb)”形状的各种量词。
(5)He has not a speck of humour. 他没有一点儿幽默感。
(6)without a shred of interest无半点兴趣
(7)without a grain of love 没有一点爱
(8)He has not a particle of sense. 他一点都不明智。
(9)a morsel of fun一点乐趣
(10)a crumb of comfort 一点安慰
认知语言学视角的量词研究表明,英汉语表量词使用都有“一量多物(同一个量词可用来计量不同的事物)(王文斌,2008)” 和“一物多量(同一个有形事物,可与多个量词搭配,并接受这些量词的计量和描述)(王文斌,2009)”现象。在二语教学中,这些“一量多物”或“一物多量”表现为种类繁多的名量“搭配”。研究者认为“搭配”是“在某一语法型式下两个或多个词(特别是名词、动词 、形容词和副词)的反复共现”(濮建忠,2003)。在本文中,语法型式指的是量词修饰名词,搭配指与一名词反复共现的多个量词(一物多量)或与一量词反复共现的多个名词(一量多物)。例如,在“a lump of +n.”的名量搭配中,名词的选择并非完全开放式的,每个名词成员也并非都拥有相同的地位。在“lump”所标示的范畴中,有些成员更具有典型性,最具有突显性和代表性的成员即是该范畴的原型(王文斌、毛智慧,2009)。在“lump”与名词的搭配中,最常出现的是接受“lump”修饰的原型名词,例如,“sugar,butter,ice,coal,clay,lead,gold,earth,salt”等,但“lump”可修饰的名词却绝非仅限于上述原型名词,在修饰其它抽象名词时,“lump”表现出很强的搭配力,例如,“a lump of culture / depravity / discouragement / glory / happiness / misery / seriousness / toil”等。二语学习者只掌握表量词“lump”与原型名词的搭配还不能称作是学会了一个表量词。受汉语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产出的隐喻性名量搭配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较差。例如,受汉语“一线希望”的影响,学习者依赖相应的母语知识过度使用“a thread of hope”。
3.2 课堂教学中揭示隐喻性名量搭配的语义理据
“语义理据(motivation)是一种心理联想。通过事物的相似性,由一事物激发对另一事物的联想,是思维和认知过程在语言中的体现”(蔡基刚,2008)。具体而言,“词汇的语义理据指根据其原有意义推断出其新的或衍生的意义。隐喻是语义理据的一个重要源泉。语言中一般有四种常见的隐喻:拟人化隐喻、动物隐喻、从具体到抽象、通感隐喻”(束定芳,2000)。隐喻最大特点是“通过某类事物(始源域)来认识和谈论另一类事物(目标域)。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隐喻映射过程中,并非将始源域的所有特征都映射到目标域,而是有一个隐喻聚焦的过程。换句话说,始源域只有一部分特征进入焦点,成为映射的对象”(刘正光,2003)。上述四种隐喻方式在英语名量搭配中都有分布,例如,在“a pride of lions(一群狮子)”中,量词“pride”所表现的属于人的骄傲与尊严通过隐喻聚焦映射到狮子,属于拟人化隐喻;在“a gaggle of women(一群女人)”中,属于鹅的喧闹与叫声通过隐喻聚焦映射到女人,也表现了听觉到视觉的转换,既是动物隐喻也是通感隐喻;在“a speck of joy(一点快乐)”中,量词“speck”所表现的具体微粒形状通过隐喻聚焦映射到快乐,快乐因此有了可见之形,属于从具体到抽象隐喻。在这四种隐喻中,最常见的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隐喻,即人们用具体事物(量词)来认识抽象事物(名词),而“形状”与“动态性”是英语者认知抽象事物常见的维度和聚焦的视角。下面以“a lump of+n.”和“a burst / gust / rush / gush of anger”为例具体说明在课堂环境下如何揭示英语隐喻性名量搭配表量词的理据性。
在英语者的认知中,形状是最常见的突显焦点特征之一。例如,“lump”通常是“各种形体或大小的块或团(a piece of a solid substance of any shape or size)”,“固体性”是这个量词突显的特征之一,如“a lump of clay”等。在例(11)中,“lump”的“固体性的大块头的特征”得以突显。但随着“lump”语用范围的增大,其突显特征的涵盖范围也越来越大。在例(12),“lump”甚至可以表示非固体非坚硬的特征;在例(13)中,“lump”也可表示气体的形态。在“lump”与抽象名词的隐喻性搭配中,英语者通过类比的思维,把和“lump”搭配的名词的特征也赋予了这些抽象名词。由于“lump”描写的这些具体名词形状各异,虽然主要表现的是有硬度的固体性,但也可表示气体和半固体性,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在例(14)、例(15)中,这些抽象的情感在英语者的认知中,它们的形态不固定,并伴有多种物质特征的可能性。总之,“lump”与多种具体名词搭配的可能性为这个量词语用范围广,可与丰富的抽象名词搭配提供了解释。
(11)She’s a great,big,fat lump of a girl,and so on.
(12)She fell to the earth like a small lump of jelly.
(13)Risking the bullets,we saw the village crowned with great lumps of smoke.
(14)...and a lump of home-sickness came into his throat.
(15)...,though his character was fortunately leavened with a large lump of modesty.
除了聚焦“形状”,“动态性”也是英语者认知抽象事物所突显的特征之一,或“动态性”也是名量隐喻映射的焦点之一。名词所代表的静态意象和量词所代表的动态意象之间存在着互动的映射关系。在互动映射作用下,名词所代表的事物的行为动作动态特征通过动源性量词而突显和激活,并且其中名词和量词可以分别充当主语和谓语来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王文斌、毛智慧,2009)。 分析例(16)到例(19)当中的表量词“burst,gust,rush,gush”,我们发现这些动源量词都是名动兼职的词,它们都可以单独用作动词。这些动词的语义成分(见表一)都包含“爆裂、劲吹、涌、喷”等动作核心语义成分和“突然、大量”等表示力度的方式,这也与英语“愤怒”概念隐喻相符合,即“愤怒是容器里的热液体(ANGER IS A HOT FLUID IN A CONTAINER)”或“愤怒是危险的动物(ANGER IS A DANGEROUS ANIMAL)”。换言之,在隐喻性名量搭配中,通过映射作用,与愤怒的力度、强度相关的动态特征——冲劲得到了聚焦。
(16)Who shall say what hidden storms of grief and regret lie within that burst of anger?
(17)A sudden gust of anger caught her,anger against the man for whose sake she had one night shed so many bitter tears,whom now she so fierily hated.
(18)Anna felt a rush of anger come over her.
(19)Not even yet can I think without a gush of anger and shame of my visit to Brotherton.

表1 动词的语义成分分析
4 结语
表量词没有成为英语中的正式词类,比起动词、名词、形容词的教学研究,有关表量词的教学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但表量词是英语的局部现象,在英语中大量存在,有着很广的语用范围。本文在分析英汉表量词差异的基础上总结语言差异对学习者造成的困难,再以“a lump of+n.”和“a burst / gust / rush / gush of anger”为例,解析英语者认知客观事物时所聚焦的两个突显的重要维度——“形状”和“动态”。当然,英语者认知客观事物与关系时并不只囿于这两个维度,但正是这两种突显的认知维度导致英语中出现了大量描写性强的形状量词和动源性量词,表量词与名词之间的隐喻映射是量词的词汇理据。语言与思维假说认为,语言会“训练”本族语者选择能够适合某种概念化和容易在该语言中编码的事件或事物的特征(Slobin,1987)。“形状”和“动态”是英语者认知抽象事物与关系时两个突显的特征。这种思维与语言紧密相关,相应的语言/思维方式导致了观察事物的特定视角,这种特定视角很难被“重新训练”(Slobin ,1996),“很难被重新训练”在一方面说明了外语学习的挑战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外语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训练学习者像母语者一样的认知模式,而在隐喻性名量搭配教学中揭示表量词的理据性,分析英语者认知的视角聚焦,就属于这种训练。词汇是有生命的,它的理据反映了母语者认知世界的方式,探索词汇的理据性,是学习者与词汇的对话。
受应试教育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多采用机械记忆法学习词汇,这个方法在英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和完成短期学习目标是有效的,但随着学习阶段的深入,学习者如果不反思词汇学习策略而只用机械记忆的方法,不仅使语言学习枯燥乏味,降低学习效率,也无法掌握词汇深度知识和发展词汇丰富性,更无从建立起像母语者一样的词汇语义网络,会使学习更长期处在以母语为媒介的第二阶段,并导致最终的学习失败。从教师层面而言,在课堂英语隐喻性名量搭配的教学中,揭示英语表量词的词汇理据有积极意义,因为理据是认知的核心问题。记忆和使用有理据的知识要比任意的知识更容易(Lackoff,1987)。揭示词汇理据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激励学习者反思学习策略,积极抵御母语中介作用,对语言间的差异高质量注意,提升目标语语言意识,使得训练像母语者一样的认知模式成为可能。
注释
① 本文的汉语单语例证或译文例证参考了词典(英汉大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现代汉语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John,S.Trans.陆谷孙.柯林斯COBUILD英汉双解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本文的英语单语例证参考了英语句子搜索引擎(http://nyanglish. com/)或在线词典(http://www.idioms. thefreedictionary. com /glimmer+of+hope; https:// www. thesaurus. com / browse /gu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