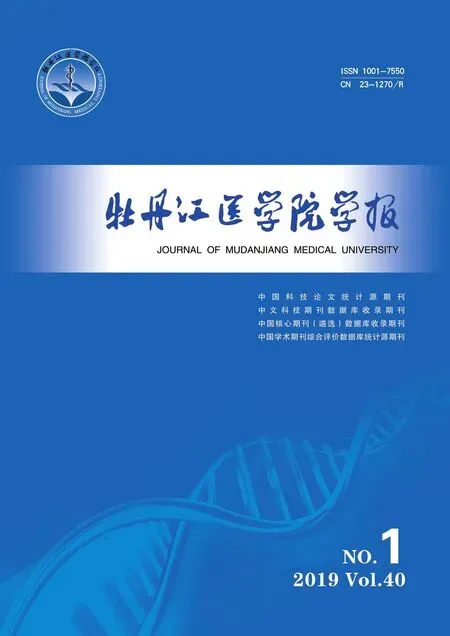社区意识研究进展
2019-12-30刘成祥魏娇娇
汪 玲,尹 皓,刘成祥,魏娇娇
(蚌埠医学院护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社区意识是社区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常被作为评判社区工作的首要标准,是目前社区心理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主题之一[1]。尽管国内外对社区意识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很多著作没有将社区意识作为明确的研究概念,社区意识研究呈现不清晰、不完整的面貌[2]。本人从社区意识内涵、结构与测量、相关研究进展以及影响因素、价值和趋势进行文献梳理和总结,以帮助研究者更全面的了解社区意识,提升社区意识研究在社区社会学中的地位和进一步研究,为社区决策制定提供参考。
1 社区意识内涵、结构与测量
1.1 社区意识内涵与结构社区意识又名社区心理意识或社区感,最初是由Sarason[1]引入到社区心理学领域,它被描述为一种社区的心理感受,“与他人相似的感知,与他人相互承认的相互依赖性,愿意通过给予他人或为他人做他人所期望的事情来维持这种相互依赖,这个定义包含了社区心理学的一些关键方面,比如一个个体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网络和结构中(“宏观系统”),而个体是相互依赖的(“微观系统”),随后许多学者对社区意识进行界定,其中最具影响力且被广泛接受的是McMillan和Chavis的观点,他们认为[3]社区意识是一种成员有归属感的感觉,一种成员对彼此和对群体有关系的感觉,以及一种共同的信念,即成员的需求将通过他们共同的承诺得到满足。McMillan和Chavis提出从四个维度来理解社区意识内涵,即成员资格、影响、需要的整合与实现和共享的情感连接,将社区意识的核心思想转换为可用于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研究和测量的量化指标。成员资格是指对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影响是指一个群体向其成员提供一种凝聚力的感觉,并使成员感到他们对群体中发生的事情有相互的影响。需要的整合与实现注重共同的需求、目标和信念,并且指出了成员寻找团体成员才能获得回报的必要性。最后,共享的情感联系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历史意识和对社区的认同之上的。近年来国内研究者[2]通过理论探讨和文献总结,对社区意识也做出新的概念界定,将社区认同、社区依属、社区凝聚和社区满意作为社区意识的四个基本特质。社区认同涉及社区对个人的符号意义和社会价值,即社区成为个人的自我认同对象的过程和程度; 社区依属是对社区的情感投入; 社区凝聚突出集体互动;社区满意则是以社区评估为内涵的情感形态。以上四个特质可以与麦克米伦和查维斯提出的社区意识模式形成对照,如“社区认同”类似“成员意识”, “社区依属”类似 “共同的情感联系”, “社区凝聚”类似“影响”和“需要的整合和实现”, “社区满意”也近似“影响”和“需要的整合与实现”。通过概念界定或其他分析手段,使社会学的“社区意识”研究更具系统性、完整性。从20世纪90年代起,研究者开始有针对性的把社区意识的概念运用到特定人群(老龄人、青少年、大学生、工作者)和场所(学校、工作场所、在线虚拟社区),形成了青少年社区感(adolescent senseof community)和学校社区感(school sense of community)等更细致的概念。
1.2 社区意识的测量在社区意识测量工具中目前使用较广泛的主要是社区意识指数量表(Sense of Community Index,SCI)和社区意识简表(Brief Sense of Community Scale,BSCS),其中社区意识指数量表是测量社区意识最常用的工具,该量表是由Perkins等(1990)为了评估麦克米兰和查维斯的理论而编制,共包括12个是非题项,4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3个题项,正确记1分,错误记0分,总分0~12分,Cronbach'α为0.8[4]。但有学者对该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模型拟合效果不佳[5]。2003 年,Long 和 Perkins 对 SCI 进行了修订, 形成了包含有社会联系、相互关注和社区价值三个因素,8个题项的“简明社区意识指数量表”(Brief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 简称 BSCI)[6]。2004 年,Obst 和 White 也对 SCI 进行了修订,删除了2个条目形成了包含10个条目4个维度的“社区意识指数修订量表”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Revised,简称 SCI-R)[7]。无论是后期修订的简明社区意识指数量表(BSCI)还是社区意识指数修订量表(SCI-R)均因条目所属维度与预设理论吻合度不高,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基础而受到学者们质疑。社区意识简表则是由Peterson和McMillan (2007)[8]基于社区意识四因素模型的基础上编制,该量表包含4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2个条目,采用Likert5级评分法,总量表和各分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8-9],但2015年在美国波多黎各洲的一项关于该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由于维度间的较强相关,原量表的4个维度被划分为2个维度,因此研究者建议每个维度至少包含3个条目,以避免模型参数的不一致及模型的不稳定[10]。近年来学者们基于社区意识内涵,编制形成了可以测量不同环境或者针对不同人群的社区意识测量工具,如学校社区意识量表[11];工作场所社区意识量表[12];青少年社区意识量表[13];城市居民社区意识指数量表[14]等,这些量表在相应的研究中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 社区意识研究进展
2.1 不同类型社区意识的研究在社区心理学中,研究者通常将社区意识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地域性社区意识(sense of geographic or locational communities)和关系性社区意识(sense of relational communities)。前者强调社区成员对某一特定地域(邻里、小区、学校、城镇、城市等)的依恋与认同;后者强调社区成员在以共同兴趣或利益结成的特定组织(工作小组、业余俱乐部、宗教团体、网络社区等)中的心理联系。近年来,研究者多集中于对关系性社区意识的探讨,也有学者在尝试地域性社区意识和关系性社区意识的比较研究或整合研究。
2.1.1 国外社区意识研究现状 一项对农村社区249名中年和老年居民的横断面调查显示社会支持和社区意识能够提高农村社区中老年居民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水平[15]。Seckman等(2014)[16]采用在线问卷调查的形式,以96名参加网上健康资讯课程的护理专业本科生为样本,调查结果显示:适度的社区意识与学生参与和学习成果之间存在积极关系,各种各样的学习活动,如维基、博客和讨论板都有助于促进社区意识,但学生们强调希望得到更多的教师反馈和互动。Blight等(2017)[17]针对276名Instagram用户和223名Twitter用户,调查其虚拟社区意识水平,结果显示Instagram用户比Twitter用户有更强的社交动机,两个网站用户的社区意识与社交互动和表达信息共享动机存在直接正相关。Asensio等(2017)以418名西班牙酒店员工为样本,分析员工在工作场所中的社区意识与职业倦怠综合症之间的关系,报告结果显示有更多的社区意识的人能够缓冲管理工作量和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具有高度社区意识的个人能够更好地缓解具有难以管理的工作量和发展疲惫之间关系的影响,相对于社区意识较低的个体来说[18],注意发展社区意识对于防止员工辞职,提高服务质量也很重要[12]。Sohi等(2017)[19]研究考察了宗教参与频率对156名印度锡克教徒社区意识和社会幸福感的影响,宗教仪式参与频率与社会幸福感和社区意识呈正相关。此外,还发现社区意识可以调节宗教仪式参与频率对社会幸福感的影响。
2.1.2 国内社区意识研究现状 牟丽霞等(2007)[14]对西方社区感的现状及趋势的描述以及高鉴国(2008)[2]对于社区意识理论的分析使得社区意识逐渐受到国内学者们关注并成为社区心理学的研究热点,国内社区意识研究多集中于对地域性社区意识的探讨。研究者于2018年对香港5个区的500名社区居民的一项横断面研究显示社区意识是感知环境与自我评价健康之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的社区意识在感知的物理环境与自我评价的健康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而在感知的社会环境与自我评价的健康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9]。宋贝(2013)[20]关于农村社区感的调查研究表明农村社区感与文化认同、宗教认同显著正相关,且不受社区客观环境因素影响,而受以邻里关系、社区归属、社区认同等为基础的社区人文主观情感因素的影响显著。罗念(2018)在对国内9所高校的1361名大学生的学校社区感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学校社区感整体处于中上水平,大学生的学校社区感与人际信任显著正相关,学校社区感和人际信任显著负向影响孤独感[21]。
2.2 社区意识的影响因素分析近年来影响社区意识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
在个体因素方面,研究者多关注的是社区意识同一般人口学特征、人格特征、个体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等的关系。一项针对居住在美国芝加哥地区的老年美籍华人的研究表明社区意识与老年人的年龄、性别、在社区居住年数呈正相关,与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呈负相关[22]。南美洲居民的社区意识与健康状况相关,社区意识较高的居民慢性病发生率较低,并能提高健康状况[23]。童婷婷等(2016)以348名高中生为被试,结果显示高中生大五人格与社区意识和心理弹性显著相关,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与社区意识显著负相关,学生的社区意识在神经质、严谨性、宜人性、外向性对心理弹性的作用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倡导教育工作者应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因材施教,帮助学生完善个人性格,发展社区意识,提高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使学生的身心获得良好发展[24]。当然影响社区意识的个体因素还有很多,诸如个体认知、应对方式、职业特点等,这都是研究者们今后需要关注的主题。
在影响社区意识的环境因素中,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社区的物质设施、资源、服务等客观条件以及社会交互因素如社会支持、社会参与、社会认同等。使用社区服务的香港新移民妇女往往表现出更强烈的社区意识,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低水平的抑郁症[25]。拥有更多的社区资源和设施,居民的社区意识更强,有助于建立居民与社区发展更强大的联系[26]。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支持性的学校环境中,对学生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例如:例如使用药物和暴力行为)的可能性更小,学校安全是学校环境的一个主要特征,学生在学校感知到的社区意识越高,对学校不安全的认知就越低[11]。老年人的社区意识与其社会活动(如看书、打牌、看电视等)的参与以及来自家人朋友的社会支持积极相关[22],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与社区活动的参与呈显著正相关,社区意识越高,参与的积极性和参与率越高,表现出较高的社区满意度,社区认同感、社区依属感以及良好的社区关系[27]。根据Lampinen和Suutala的研究探讨社区意识、组织承诺和服务质量关系时发现,社区意识培养了他们的自信,也培养了他们作为从业者的独立性,与同事之间的协作、关爱关系以及来自领导的欣赏能够有效地促进团队合作、与他人分享工作以及相互学习,有利于组织承诺和服务质量的提高[12]。
3 社区意识研究的价值及趋势
近年来对于社区意识进行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多体现在健康状况和社区活动参与两个因方面,同样也是该研究的趋势。
3.1 社区意识与健康状况社区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指示器[28]。研究表明社区意识与各种心理健康指标有关,包括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和孤独,能积极影响心理健康,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呈正相关[29]。很多研究显示不同人群中社区意识与健康状况存在一定相关性。一项关于青少年社区意识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强烈的社区意识与更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及较少的抑郁症发生率相关[30]。然而一项关于老年美籍华人社区意识、自评健康及抑郁的相关性研究则表明更高水平的社区意识与自评健康差或一般的可能性较低以及抑郁发生率较高相关[31]。社区意识与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存在显著相关,学生的社区意识越高,存在身心健康的风险越低[32]。
3.2 社区意识和社区活动参与社区参与依据其范围或领域的不同,分为社区经济参与、社区政治参与、社区文化参与和社区社会参与等方面。社区意识作为社区生活中很有价值的组成部分,能促进人们的社区参与行为,社区意识作为一种社区资源,其强弱应当成为社区建设成果的重要指标,在社区决策和建设过程中不能忽视这一关系[33]。强烈的社区意识能增强老年人参与的积极性并投入到社区建设中,可能是成功衰老的关键因素[29]。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可以允许他们在决策过程中发表意见,让人们感觉到他们在社区中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反过来也可以增强他们的社区意识[3]。社区意识对政治活动和志愿活动的参与同样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34-35],而在非洲裔美国人中,社区意识较高的居民身体活动的自我效能感更高[36]。参与水平高的学生同样具有显著较高的学校社区意识[37]。
4 不足与展望
社区意识自提出以来,国内外便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研究者多集中于对社区意识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对社区意识理论的探讨与分析较少,目前社区意识的研究中也并没有提出系统的、兼收并蓄的理论,这有待于国内外学者做进一步的探究。由于缺乏对社区意识概念的清晰界定,对社区意识测量工具也缺乏共识,如社区感指数量表(Sense of Community Index,SCI)也被用于考察虚拟社区意识[38],但与传统意义上的社区相比,虚拟社区存在成员数量更为庞大,团体异质性较强,人们对社区其他成员的了解较少等特点,因此在考察虚拟社区感时,SCI以及后期开发的BSCS均存在需要修订的题项[39]。因此,进一步澄清社区意识的概念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修订、完善现有测量工具或者开发新的测量工具,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对社区意识人群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学生、居民及工作人员的研究,在老年人群中对社区意识进行调查的文献很少,影响了社区意识研究的扩展。老年人作为社区生活的主体,考察其社区意识、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从社会心理层面揭示社区意识对社会行动的影响,进而有利于科学、高效地进行社区建设,实现社区的和谐发展。培养和加强成员社区意识也是我国社区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应该扩大对老年群体社区意识及其相关因素,如社区活动参与、健康状况等的研究,为社区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指导并提高其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