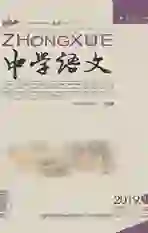论蘩漪“病”的隐喻
2019-12-27余齐永
余齐永
一、蘩漪的“病”
关于蘩漪是否真的有病,是许多读者和文学批评家们探讨过甚至依然在探讨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引发的争论,恰恰就表现了蘩漪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正如对于她刚出场时的描绘那样,苍白的脸色、大而灰的眼睛、眉目间的忧郁、瘦弱的胸等,都透露出一种病态,而这种病态的描绘之下,却又有着“更原始的一点野性”,让人“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常常透过自己或者他人的眼光在“有病”和“无病”之间切换,这也恰恰表现了她复杂而矛盾的性格,“病”在不同场景和语境中的出现,就起到了重要的隐喻作用。
1.逃避与反抗
蘩漪是一个果敢、大胆又叛逆的女性,但我认为,她初次登场时呈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的“病”,更多的却是一种刻意的逃避。她在周公馆里呆了十八年,也在这密不透风的环境里被闷了十八年,周朴园对于她来说应该只是一个发号施令的权威的存在,因此在周朴园从矿上回来的这些天,她称病将自己关在楼上,这既是面对“权威”的无奈,也是对无聊和乏味命运的逃避,不过这逃避之中也蕴含着一些反抗的意味。但是更为明显和激烈的反抗,是蘩漪称自己“无病”时的反抗。当蘩漪拒绝喝药并大吼“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告诉你,我没有病!”的时候,这种反抗几乎被推向了高潮,爆发出叩击心灵的力量,对所谓的绝对威严做出深刻的抗争,是个人意志与情感的追寻和抗争。
2.精神摧残的创伤
在戏剧的第四幕,蘩漪在遭受到爱情的彻底抛弃之后,她的情绪也被引向了高潮,“嗯——我有神经病”“我是疯了。请你不要管我”……这里的蘩漪说自己“有病”,是以疯的姿态来反抗周朴园的命令,但更是精神遭受巨大创伤之后变态心理的显现。在周公馆里,周萍的出现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活着的、敢爱的人,可此时周萍又亲自将她推回到令人窒息的死气之中,因而她陷入一种病态的、精神缺失的创伤之中。
所以说,蘩漪的“病”,不是一种客观的具象,而是一种隐藏着的强大的力量,是一种精神的“越狱”,这种力量是崇高的也是畸形的,她既隐喻了对压抑的、腐朽的家庭与社会的反抗,也隐喻了一个果敢的女人对爱的渴望和对自我人格的追求。
二、蘩漪的“病”与话语权力
在《雷雨》中,曹禺对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的愤懑和批判,体现得最好的地方,就是周朴园与蘩漪的“病”的对抗。
周朴园命令蘩漪喝药的那一段,是《雷雨》这部戏的经典桥段,它深刻而沉痛地揭露了封建大家长管制下的一个家庭的冷颤与悲哀。在周公馆里,无论是妻子,孩子,还是仆人,都活在周朴园的命令之下,周朴园站在周公馆权力的顶端,掌握着这个家庭里一切的话语权力,一切反抗和试图反抗最终都以可笑的失败告终,蘩漪在双重威逼的压力下痛苦地喝下了苦药,周萍在父亲的命令下向自己的继母也是曾经的情人下跪哀求,周冲在父亲的绝对威严中吞回了憧憬许久的请求……
用周朴园的话说:“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周朴园作为矿场的董事长,作为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追求的是体面,是尊严,而拥有这些的前提便是占据绝对的话语权,维持所谓的家族秩序。他用来维持家庭“圆满”的手段,就是以“病”为借口。蘩漪是反叛而刚硬的,在周公馆里对周朴园说“不”最多的就是她,因此她自始至终都在被周朴园逼迫着吃药看病,并被命令着给孩子们做一个听话的、服从的榜样。
凡是有违周朴园意志的,在周朴园那里便都作“有病”处理,因为病人难免会犯“糊涂”,所以病人的反抗并不能作为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因此,他便常常用“有病”来定义他人对他的违逆,以此来粉饰自己的绝对地位,甚至他会先给“病”下一个定义,再请大夫来诊断,比如他连蘩漪的面都没有见,就断定她有病,还独断地准备了药方。这既是他对家庭话语权力的霸占也是他最虚伪的掩饰裂隙的手段。是否真的有病,有什么病,严不严重……这些问题在周朴园那里都是无足轻重的,他看重的只是自己的尊严、权力,只是家人的服从和家庭门面上的秩序井然。因而几乎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在周朴园那里都曾有病,他曾对周冲说:“我看你的母亲,精神有点失常,病像是不轻。”(回头向周萍):“我看,你也一样。”
一旦周朴园的家长地位遭到挑战,他虚伪的“有病定论”就会立刻暴露无遗。在蘩漪淋着雨疯疯癫癫地从四凤家回来,并说自己有神经病时,周朴园慌乱了,因为真正的疯病是跳脱于精神控制之外的,是彻底挑战他的意志的,因此他一改以往认为蘩漪“有病”的说法,命令她:“不要装疯!你现在有点胡闹!”
在文学作品中,所有的病痛都是社会的病痛,在周公馆里,蘩漪的“病痛”也是整个家庭的病痛,更是周朴园的病痛。因而在戏剧的结局,那直指向死亡深渊的悲剧,并不是一场雷雨中的意外,而是这种病痛的扩大,更是对周朴园绝对话语权力的挑战和讽刺,他所要维持的最有秩序、最圆满的家庭,变成了最难以言说的、最支离破碎的面貌。
三、蘩漪的“病”与“向死亡存在”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提出:“向死亡存在。”他认为“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可能性。”也即是说,存在(生)必将走向死亡,当我们面对必然的死亡时,就会产生“畏”,而“本真的生存”就产生于这样的“向死亡存在”和“畏”之中。因为“死亡”和“畏”是他者无可替代的真实,只有在这种真实的冲击下,我们才能抛去一切的遮蔽,面对生存的真实,懂得生的意义。
或许我们可以说,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这样的视角之下,生存与死亡是辩证统一的,正是把死亡当作一种特殊的生命现象和生存方式来考虑,以此来规定人的存在意义和参照价值。
在第四幕戏中,蘩漪近乎疯癫的“病”,是一种长期受压抑受束缚的精神的死亡,她近乎声嘶力竭地要抛开被长久地贴在她身上的一切标签,那一刻,她不再是谁的妻子,也不再是谁的母亲,就像她對周冲高声说的:“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
长期受压抑的精神走向死亡之后,她迎来的是一个真正的活着的女人,是一个真正需要爱、懂得爱、敢于去追求爱的真实的女人。穆齐尔曾言:精神病人只患了一次病,而我们天天患病。在蘩漪过去的如死灰一样的精神走向死亡之后,她便从那种病态中抽出身来了,真正地去寻求内在灵魂的壮硕。与其他人物相比,她的状态或许最癫狂,最像一个疯子,但她的灵魂反而最热烈、最真实、最诚挚,这恰是灵魂与精神的生与变形,是真正意义上的“向死亡存在”。
蘩漪的“病”的变形,实际上也使得戏剧的悲剧性结局成为情理之中。四凤的死象征着无法再挣扎的绝望和走投无路的痛苦,单纯而乖顺的她承受不起现实的摧残;周冲的死象征着幻想的破灭,也许从一开始,他爱的就不是四凤,他爱的是理想中的对未来的憧憬,爱的是爱本身,当他发现社会和家庭与理想全然不似的时候,理想就幻灭了,年轻的灵魂陷入与年岁不符的,难以逃脱的迷茫;而周萍的死则是死于蘩漪的“生”,四凤的死和身世的明了对于周萍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但在我看来,这还不足以让他失去生命,而蘩漪的真实、热烈和重新燃烧的生命,才是周萍难以匹配与承受的镇痛。蘩漪在最“癫狂”的时候活成了最完整的人。
然而,因为周萍的死,蘩漪的“向死亡存在”也只是“存在过”而已。当一场爆炸般的雷雨之夜过去之后,蘩漪注定会陷入真正的“病”,因为支撑她的精神活过来的力量彻底消失了,这是一场如雷雨般有张力的向死而生,绚烂但并不永恒。
作者通联:江西景德镇市昌江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