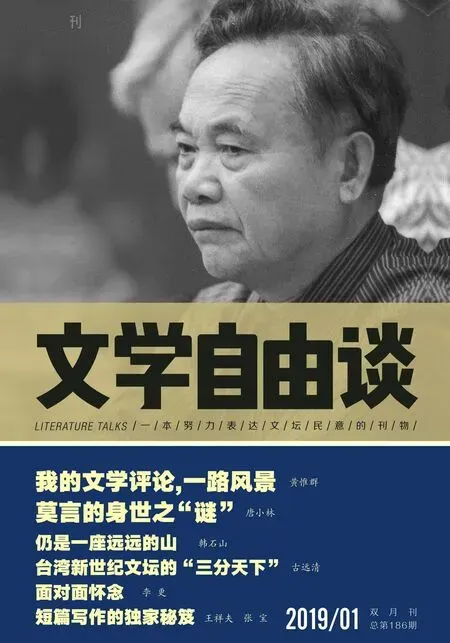为“译”消得人憔悴
2019-12-27杨振同
□杨振同
小张:
你好!再不给你回信简直就太不够哥们儿意思了,恐怕不是一句“罪过”就能搪塞过去的。到期末考试时间了,要出卷子,改卷子,还有没完没了的监考。本来想趁周末给你写信,嗐,谁知在写字台前一忙活那个稿子就什么都顾不上了,等终于译完那个一万多字的东西,我也累得再也不想敲字了。尽管老婆常抱怨计算机是我的“大老婆”,对“她”亲,对她不亲。她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用她的话说,我一发起“神经”来就这样,老婆孩子全不管,一心只译圣贤或不圣贤的书。
记不清是哪个作家的妻子说过,千万别崇拜作家,更不要嫁给作家,崇拜他的作品就够了。这说明给作家当妻子有多么苦。当作家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巨大享受时,他的老婆孩子却在遭受“冷落”。作家如此,搞文学翻译的也同样如此——只译了那么一点点小玩意儿,无论如何还和“家”沾不上边呢,所以就在家里猛劲儿“修炼”,争取早日修成正果,成名成家吧。写到这里,先把自己吓了一跳:搞翻译的人多如过江之鲫,但名气如傅雷者才有几人?所以看到你把老哥描写成“长袖善舞”的人,我只能报以苦笑,老哥远没有你说的那么潇洒。
真的很欣赏你的文笔,看你写给我的文字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凭我多年和文字打交道的眼光,我相信自己不会看走眼的。所以我就特别想和你谈谈对未来生活道路的选择。
干吗不选择搞文字工作,而要把你的才智浪费到这种枯燥、缺乏激情想象力,天天只和数字打交道的工作上呢?古希腊有一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言:“认识你自己。”我相信很多人看了这句话都会一笑置之,我还能不了解自己吗?可是仔细想想,往往最不容易认识的恰恰就是你自己。你目前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从事目前这种工作,也许三两年就能见成效,考个“师”级证书之类的东西。而搞文学创作,没准十年八年还不见起色。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漫漫长路,然而可能是一条适合你走的路,也许你人生的乐趣恰恰就在那艰难的攀登之中,走在坦途上你可能还觉得没意思呢。
我自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在来广东之前,我在内地一所中专教书。那是一个混日子的绝佳所在,没有中学的升学指标,没有大学的科研任务,上课时拿着课本去“念”就是了。工资不高,但在内地,那是一个全民事业单位啊,旱涝保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我偏偏不满足,鬼使神差地迷上了文学翻译。你知道,这玩意儿并不是谁都可以搞的。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英文资料奇缺,信息极端不灵。没有原文,就等于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文学创作可以天马行空自由想象,偏远乡村、繁华都市,都可以播下文学的种子;可是翻译如果缺少了原文和信息,简直就等于判了你死刑,是绝对不行的。加上我当时英文水平还很低,急需老师指导,但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从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我都不具备搞文学翻译的条件。
可是邪了门了,我就是想翻译。英文不行,苦学。没有老师指导,就买大量的英语学习刊物,如《英语学习》《英语世界》等,跟着刊物学;为了提高听力,我先后买过五个短波收音机,每天着了魔似地听外文广播。翻译没有原文,我自费订阅了美国的《读者文摘》和《国际短篇小说》杂志,从中选取翻译素材。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我买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苦苦钻研。说起来不怕你笑话,工作了二十多年,居然没有什么积蓄,屋里除了一片狼藉的书以外,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我这样说,为“译”消得人憔悴,不过分吧。
常言说:十年磨一剑。“面壁十年图破壁”,而我奋斗十年了,发表出去的还是那几个不起眼的小豆腐块儿,与我巨大的付出简直不成比例。翻译的东西大概能装一纸箱了,投出去大多石沉大海。我沮丧到了极点,我的自卑感绝不亚于那个丹麦老人笔下的丑小鸭。我对自己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信心,只知道不停地译啊,译啊,把那些发表不了的东西改了再改,真所谓只问耕耘,不计收获(不是不计,“计”也没办法)。就像那只丑小鸭,只知道在寒冷刺骨的河水里不停地游啊游……
我不知道2003年对我来说是不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不管怎么说,我投出去的东西有了声响。译文开始一篇篇被采用,上了《译林》,上了《外国文艺·译文》,2004年又上了《世界文学》和《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我写的一篇短文上了《外国文学》(那可是“学术论文”,算“科研成果”,评职称很有用的哟,尽管实际上狗屁不是)。这样,我在国内的外国文学刊物上差不多都算露过脸了。我译的东西甚至还在《香港文学》上露了一鼻子,发表了日本目前最走红的作家村上春树的一个短篇小说,后来时不时地还会在该刊零零星星发一点小东西。
发出去的东西就像嫁出去的姑娘,是“丑”是“俊”,我就不管了。
我大致算了一下,我出版了六本书,翻译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奈保尔的后期代表作《世间之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散文随笔集《故事开始了》等,发表的作品大概有两百多篇,三百多万字的样子;有的译作还被《青年文摘》等刊物转载。2005和2006年连续两年我译的作品入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精选》,我译的土耳其幽默大师阿齐兹·涅辛的小说《杰作诞生记》,还被选入了《外国名家幽默小说36篇》,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后来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名叫《小说中的小说》一书,又把这篇小说收了进去。我翻译的另一个短篇小说,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瞪眼》,在湖南的《文学界》(现在叫《湖南文学》了)发表后,选入《小说山庄》(2010—2011卷)和《她们笔下的她们》两本书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还有一篇小说,似乎值得一提,那就是《从土耳其来的侄儿》,本来是发表在英语学习类刊物《英语世界》杂志上的,可是很快被《青年文摘》转载,影响就出去了。本来我觉得它的“光荣使命”也应该完成了,没想到几年后居然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看上,选进了《文学翻译》教程。教材到现在年年都在印,想必是一茬又一茬的莘莘学子都从中受益了,这倒是当初没有想到的。
这似乎就是翻译作品的影响了?我想可能是吧。搞翻译的,不像搞创作,一朝成名天下知,搞文学翻译是什么都没有。古人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是无聊文人“自慰”的谎话,当不得真的。作品发表了,能有刊物转载,或有作品集能收进去,让作品再“潇洒走一回”,已经算是“影响巨大”了。至于文学评奖,基本没有文学翻译的份儿;大学里面靠翻译作品评教授?门儿都没有(这牢骚话我已经在好几篇文章说过多次,再说就有点像祥林嫂了,说多了,人家会烦的。还是打住吧。呵呵)。
所谓影响,大概只能影响到像你这样的文学青年。
如果说还有什么影响的话,可能就是:原来是使劲儿投稿,也没人理;现在偶尔还有人约稿了。
满足吗?老实说,有点。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了嘛?大概在变吧,在努力地变。
我清楚,这才只是一个开端,以后的路还很长。陪伴我的,还是那寂寞的青灯、孤卷。我也很清楚,翻译给我既带不来名,也带不来利,带给我的只有辛苦、汗水、泪水和那漫漫无际的寂寞。当然,偶尔也会带来一些阿Q式的心理满足,如此而已。
……不知不觉中,我写出了我的“译”路历程。谢谢你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把自己走上文学翻译的经历写出来。因为每个译者或多或少大概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要死要活的过程,不值得写。就像年轻时火一样的热恋和死一般的失恋一样,自己看是“轰轰烈烈”,而在别人看来,却稀松平常,除非你有琼瑶的本事,把你的恋爱故事写成骗小姑娘眼泪的言情小说。
写得太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写了这么多,写到这里我甚至都忘了开头的目的了。大概是跑题了吧。我是想劝你搞文学创作,也走上一条不归路吗?也想让你历尽艰辛而一无所获吗?也想害得你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吗?我究竟是何种居心?若是那样,真乃罪莫大焉!
我也说不清楚。这是最老实的回答。一方面,我觉得你是搞文学的料;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搞文学太苦了。我无法给你一个圆满的回答,只能这么漫无目的地瞎侃一通,至于你怎么理解,那就是你的事了,别到时候后悔了埋怨我就行。
怎么样?有空再聊吧?
希望我的信能给你带来好心情。
老哥:杨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