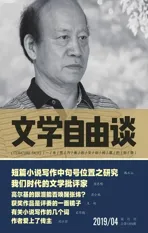“新批评”与“旧批评”
2019-12-27郭晓斌
□郭晓斌
我们现在倡导营造良好的文学批评氛围,可谓之“新批评”。这自然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因为它显示了对以往某些不良批评风气进行扭转的尝试和努力。但新的批评固然要抵制商业化、人情化的吹捧、晦涩的过度理论化的文风等等,却也不该是自说自话、凭空开拓,还需要回首和了解我们曾经的“旧批评”达到了什么高度,我们又该如何从中获取文学批评的方法和资源。
对于当下的文学批评来说,我认为最可借鉴的也许正是发端于五四运动的现代文学批评。这不仅仅因为现代文学史上名作迭出,文学批评也蔚为大观,还因为它们有着相似的批评对象,即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白话文学。当我两年前偶然读到京派批评家常风先生的书评时,我的这一想法再次得到强化。我确实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不客气地说,它们比当下我所见的很多书评都要动人得多,有力得多。常风先生在京派批评家里不算太引人注目,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但这绝不妨碍他是一位一流的文学批评家。不太知名的常风尚且如此,现代文学的批评风气和氛围由此更可以想见。
常风,原名常凤瑑,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1933年3月在《新月》发表处女作《那朦朦胧胧的一团》,从此开始他的文学生涯。常风是“京派”文学的重要作家, 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在散文、文艺评论、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等领域,都卓有建树。他是当时著名的书评家。他的书评分析细腻精到,文笔清新活泼,融鉴赏与评论于一炉,风格自成一家。
读了常风先生的书评后,我越发感到,我们的文学批评与其说要空无所依地一味求新,还不如沉潜下来,以谦卑的姿态去学习和承续曾经的批评传统。事实上,我们现在大多数的文学批评,连那个时代的“旧批评”都远远达不到。如果再说得刻薄一点,我们的目标也许不应在于求新,而在于恢复到原有的“旧批评”的水准。要达到这一点,已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我们不妨把常风先生的书评与当下的批评现状做一些对比,便可知道以上并非虚言。我们会发现,这些“旧批评”的确振聋发聩,常读常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新批评”,是文学批评的典范。怎样进行文学批评?什么是好的文学批评?在常风先生的书评中,我们无疑能够得到极大的启发。
“公正客观”四个字,相信哪一位评论家都会说到,听起来也简单容易,但我们可以看看常风秉持这样的立场,在文学批评上达到何等了不起的高度。
不妨以他对巴金、茅盾、老舍三位名家的批评为例。
对于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常风予以了严厉批评:“巴金先生忘记了小说并不是历史或传记,所以虽然小说也在实生活中取材,虽然也常以某一个实生活中的人物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却不必尽同于实生活中的。”但在同时,他又极为赞扬巴金的《俄国社会运动史》:“这部史话用极简洁的文字写极复杂的事实,达到相当的成功。巴金先生想将这书当作一部专门的著述,而又要大众能看,这真是一个不小的雄心。可是巴金先生的愿望竟达到了。”这与“希冀达到普遍而永久的大公无私”的李健吾严厉批评《爱情三部曲》的同时,又撰文高度肯定《神·鬼·人》如出一辙。
在评价茅盾的作品时,常风一方面肯定《蚀》三部曲“直至今日在茅盾先生的全部作品中,它还是最好的一部”,“这书描写范围的广博,人物的众多,题材之丰富于时代意义与精神,在新文学作品中是罕有其匹的”,但同时又直白地指出,关于《子夜》这部“最受人称赞的书”,“被认为我们新文学中最伟大的一部杰构”,“我们觉得我们愚暗的意见和一切高明的评论不敢苟同。我们愿意坦白率直地说:这部《子夜》是一个失败,一个大失败”。这不能不让我们惊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晓明、蓝棣之等学者怀着“重写文学史”的抱负,严厉批评《子夜》的弊病,颇引起学界的哗然和振奋,却不知文学史的这一笔无需改写,而应该是补写——早在《子夜》诞生之时,常风即已有这样敏锐清醒的判断!即便它被时人称为“我们新文学中最伟大的一部杰构”,常风依然不盲从习见,大胆断定它是“一个大失败”。而今,我们对于《蚀》三部曲与《子夜》得失的共识,与当年常风的见解何其相似!
对于老舍的小说,他认为:“作者的创作中最能引人发笑的要算《赵子曰》;而毛病最多的也要算《赵子曰》。小说中自然允许容纳笑料,自然也要人笑;但是这不是小说的唯一的,主要的目的……作者在以前的几部创作中,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都忽略了此点。所以不能获得他所应得的成功。”同时,他又高度肯定《离婚》:“在这本《离婚》里作者保持住他原有的一切长处,同时又顾到全篇小说结构的和谐。所以这本小说不惟是现在小说中的一本佳构,并且也是作者自己创作中的第一本完美的作品。”事实恰是,老舍曾多次表示《离婚》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他立意要幽默,可是这回把幽默看住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北平研究院的研究生推选老舍的最佳作品,大家一致投《骆驼祥子》的票,老舍却说:“非也,我喜欢《离婚》。”
这三个例子已足够说明问题。对比当下,对于名家的作品,有多少批评家能够进行有理有据、切中肯綮的赞扬,同时还敢进行有理有据、毫不留情的批评?而且,这些赞誉和批评绝非假意吹捧或哗众取宠,而完全是出于真诚和好意的公允评价。更加重要的是,这些评论不仅在当时就促进改善了文学风气,而且还经受住了时间的淘洗,至今读来仍觉精辟深刻。正如陈子善所说,这些评论“独具慧眼,褒贬得当,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来看,也是极富启发性的,大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和重新确定它们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我们当下的批评家下笔时,是不是也应该想想,自己的文章能否在大浪淘沙中长久地立下去?还是像许多时髦文字一样,转瞬之间风流云散?
常风还非常重视文本细读和作品鉴赏,在指出缺点或给予称赞时,常风不会进行大而无当的评论,而是会摘出一些具体的作品片段作为例证(有时甚至不惜大段引用),有的放矢。这样就能让读者更加信服,感受到作品本身的美感或瑕疵,而且也能够帮助提高读者的鉴赏力。在这一点上,常风与他的好友李健吾是非常相似的。比如在评论张天翼的小说《一件寻常事》时,常风就摘出主人公阿全那几句让人心酸的话,并一语中的地说:“这真是我们文学中‘带泪的微笑’。这一个短篇是一个大悲剧,闪烁着悲壮而伟大的人性爱。”在分析叶圣陶、巴金、陈铨等诸多作家的作品缺陷时,常风也举出了不少文本中的具体例证。而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似乎总喜欢宏观大论,对于内容、语言、技巧等的细致品读不屑一顾,却忘了文学作品首先是艺术,文学批评一定要建立在自己的艺术感受和作品品读上,而不应是不痛不痒的艺术概括和思想解读。在此基础上,好的文学批评应该会对作家本人有所启发,而且能够让读者了解和学会鉴别什么是好的作品,什么是不好的作品,但我们的文学批评在这一点上显然还做得远远不够。另外,常风的书评文笔极佳,个性鲜明,书评本身就是极具可读性与启发性的美文,耐得住反复品读,滋味绵长。现在的文学批评则越来越学院化,晦涩,理论化过重,术语缠绕且枯燥无味,仿佛是在写专业的文学论文,而不是评论文章。这样的文章怎么能引起作家和读者们的兴趣?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常风绝不因为自己是外文系出身,而盲从西典,轻视传统,体现出贯通中西的大视野与中西文学的融通、相互借鉴。正如吴小如所说:“专攻西方文学而又潜心于中国古典文学”,“一方面把西方文化介绍传播给国人,一方面更借鉴和利用西方的各色理论武器,来分析探讨我国古典文学中未经前人道破的奥秘和精髓。”常风不仅写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书评,还撰有《杜少卿》《〈人间词话〉》《关于苏曼殊》《马二先生》这类研究古典、近代文学的文章。在常风的文艺论文如《关于评价》《关于传记》《小说的故事》等中,都有关于中西文学理论、作品的比较或相互借鉴,而且在这些文章中,随处可见我们今天依然在谈论引用的伍尔芙、艾略特、瑞恰慈、福斯特等人的观点。这都彰显了常风贯通中西的宏阔视野与超前意识。他这种融汇中西的追求,同样是一种非常清醒自觉的努力,不能不让今天的我们叹服不已。他在《新文学与古文学》中说:“新文学纵然完全袭用了外国的形式与一切,既然是中国人用中国文字写作的,它不应该,而且不能,与中华民族过去的生命割裂开,它甩不掉那个延续的历史的传统……我们一方面创造新文学,一方面要研究古文学,就是要对那若干段落之间的划分界限特别注意,不要认为它们彼此截然无关系,而是要警觉它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新文学与古文学的融合,正在于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寻得一条理想的新路。吴小如对此的评论切中肯綮:“这是一个非常清醒的提法……我们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已开始全方位地接触西方文化(包括外国文学在内)。但在吸收过程中却产生了饥不择食和数典忘祖的弊端……这样一来,不仅使自己的新产品缺乏固有的源泉和土壤,以至于弄得先天不足;而且从‘横向联系’吸收过来的东西同样也是仅具皮毛的一鳞半爪,其后天也不免呈失调状态。”其实何止在吴小如评论的当时,即便在十几年后的今天,文学批评家以及整个学界迷信乃至胡乱套用西方理论的不良习气依旧严重。我们今天的批评家可以说对西方的批评理论烂熟于心,说来头头是道,但是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批评,有意识地吸取传统文化资源的又有几人?我们看不出来,与西方的批评相比,我们的文学批评的独特性在于哪里?民族性和原创性在于哪里?我们明知道自己陷入到影响的焦虑中,却仍然跟在西方理论后面亦步亦趋,不肯回望我们曾经走过的大道。相形之下,常风在四十年代便已有融汇中西的非凡见解和努力,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羞愧和敬佩。
此外,常风先生的批评文章中还有很多极富洞见的观点,比如对于欣赏距离的辩证把握,对于创作剪裁的思考等等,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细述。总而言之,我认为常风先生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面貌和地位,他的文学批评对于我们当下来说,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什么是好的文学批评?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新批评”?当我们在回顾常风这些老一代批评家的“旧批评”之后,相信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和感悟。至于能不能借鉴学习,能不能把现在的文学批评恢复到“旧批评”的水准,甚至超越“旧批评”,那就要看我们当代的批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