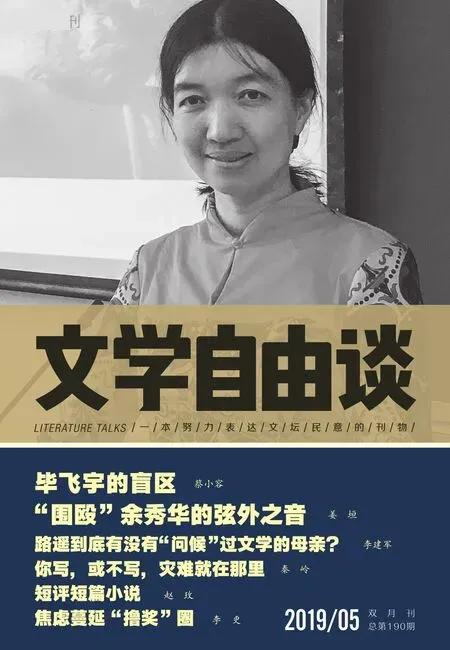焦虑蔓延“撸奖”圈
2019-12-27□李更
□李 更
有个地方作协的领导是位诗人,出版过几本小册子,都是自费——当然,说是自费,也是作协方面提供的资金支持,只要他凑够一定数量,当年作协的成绩单上必然有他的诗集,出版周期基本上以某个文学大奖的开奖周期为标准。只是他的数量非常有限,常常五年过去了还是凑不齐一本书的要求,只有把以前的作品翻出来、再加点新作品凑数——行业上管这叫“注水”。
这些当然是近年来十分盛行的口水诗了。因为从来没有走市场,没有在各种书店露过面,所以这位领导就莫名其妙地对当地多年来坚持走市场的作者进行不断封杀,说,让诗歌的归诗歌,让市场的归市场;还强调,诗歌一走市场就俗了。这让一干下里巴人困惑。甚至,这家作协的两个主席都是诗人,准确地说,写诗歌的人,他们虽然也有矛盾,但是在面对诗歌以外的写作者时,他们又马上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不写诗,无以言。其他文体的写作者为了分点“作协扶持”的残羹剩饭,也纷纷开始做回车键练习,怎么着也得弄点口水,没有口水就贡献点唾沫,此地遂成为远近闻名的“诗窝”,经济上不去,诗会频频开,自我颁奖、相互颁奖,不亦乐乎,但是离“国家级”仍然是十里堡与三十里堡的关系。于是大会小会研究、总结,得出结论:不是自己的问题,是别人不读书了。不读书自然就不读诗,属于池鱼之殃。
其实不仅是诗人,其他作家也有这样的困惑,尤其是小说家,尤其是长篇小说家。常常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影响甚至抵不上一个几百字的段子。
长篇小说,至少得三十万字吧?一般认为,四十万字比较标准,像《家》《子夜》《林海雪原》《暴风骤雨》《白鹿原》这样的。四十万字五十万字,怎么也得写个一年半载吧?三个月能够成书的也有,那不是网络写手也是现实主义大师了。很多,我知道的。也有十年磨一剑的,结果,写完了,也发表了,还出版了,若关系找对了,得奖都说不定。然后,就泥牛入海。好的结果,出版社让你走“馆配”,就是说服那些关系好的图书馆购藏几本;运气好的,还可以得到什么图书下乡、社科基金扶持的厚待。
不好的结果?直接送造纸厂化纸浆了。
那些靠作协经费出版的,一般会找关系买一点。有个作协的头儿遇到过这种事:对方叫他打个发票直接拿钱去,书都不要了。开始他还觉得哥们儿够意思,后来发现这个现象可持续发展,大有蔓延之势。细思极恐:这不是骂我吗?我差这几个钱?
有给面子的,好歹马上送上孔夫子旧书网,或者给马路上摆书摊的,只是,这年月,摆书摊的也跟熊猫似的成保护动物了。
没人读了。
以前,有个报人张季鸾说过,大意是报纸上的东西二十四小时作废。报纸讲究的是新闻的快,慢了就容易过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武汉一家书刊发行公司帮新华社老记者出版自选集,徐迟介绍我去找李普、李庄。他们一边积极翻找自己的文字,一边感慨:过时了,都过时了。我说,不会过时,这也是时代的痕迹。他们就笑:批林批孔行不行啊?批邓,行吗?
不光是新闻,文学也一样。我至今一直记得湖北有个叫辛雷的作家。1974年,家父李建纲从“五七干校”回武钢,领导让他再次负责工人的文学创作,除了具体帮助车间的写作者,还有就是联系省市的大作家来工厂深入生活;辛雷就是其中之一。他到武钢是为了写一部长篇小说,我记得是《月涌大江流》。我经常跟着父亲去武钢第一招待所去拜见他。他从“文革”前开始写,每年都因为斗争大方向的改变而不得不重写——那几年恰好是风云变幻莫测,一年河东一年河西。每次见面,他都要和父亲探讨走资派、造反派、逍遥派的身份,怕出政治问题。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离开武钢,也没有完工,因为他写的那一切全部过时了。
辛雷姓徐,网络上还能查到:徐辛雷,著有长篇小说《万古长青》,短篇小说集《长江上的战斗》,中篇小说《水上漂》,散文《曲水流杯记》《两条小鱼》《我是一个活着的人》,报告文学《实习生》《女钻探工》《石总工程师》……
就是没有这部《月涌大江流》。
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会面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诡谲,以至于计划完全跟不上变化。这是中国作家的悲剧。他们很多人无法跳出时代的束缚,只想着做时代的代言人,而不是像巴尔扎克那样的“时代书记员”。随着时代的波动,不同的时间段,居然会出现不同的叙事标杆,作家们如果缺乏必要的分析力、反省力,自然找不到一把可以量度各种时代场景的尺子。加上一部小说至少要写作几年甚至十几年,场景变化更加繁杂,往往你刚刚表现完一种场景,这标杆又随着时事的变动而变化了,甚至于完全相反了。这样的小说,自然是在写出的那一天就死亡了。
甚至根本没有写完的那一天。
今天的写作,对于很多作家来说,立竿见影、急用先学才更其重要。获得感,几乎是大家一致的追求。因为需要,所以焦虑。过去的焦虑来自于对时代风云的把握缺乏自信,现在的焦虑可能无一例外来自于对奖励的渴望。现钱,快钱,是一个可以望得到目标。肉身只能一次过,未有精神图来生。
这种焦虑,其实也是早就被人注意,或多或少也被一些作家所表现,但是像李洱这样沉默多少年去潜心研究努力表现的,似乎还是第一次。文人们通常都是去表现别人的,他们的镜子喜欢照着别人,而自己的种种,则常常是灯下黑。俄罗斯文学有大量的文化人自我分析自我反省的作品。如果沿着俄罗斯文学的路子走,一个是累,光是长篇小说的框架,就会让人生出“望山跑死马”之叹;一个是作家本人的知识储备——特别是哲学、美学、社会学的——不够。
李洱走的好像更接近于《洪堡的礼物》的路子。据说他的这部《应物兄》写作时间比较长。怎么表现近二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风貌?他有意识地弱化社会的政治性场景,这样可以合理规避一把尺子度量时代的狼狈,直接突出代表今天文化人、文学人的关键词:焦虑。
他在最近一次访谈中,直接就说出了自己对于长篇小说写作的焦虑感:长篇小说在试图与“碎片化”对抗。
“碎片化”,当然是指网络上的阅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作家们抱怨自己仍然在写作,可是,读者没有了。到哪里去了?他们认为都是智能手机惹的祸。阅读工具或曰文学载体的变化,造成体制内作家被成千上万地抛弃。甚至,他们认为,每天被微博、微信绑架的那些手机综合症患者,只是在打游戏、看图片。
现在终于有人知道,中国人的阅读不是少了,而是更加多了——打破了书本的束缚,阅读可以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海量的文字海量的信息,让中国人更加热爱阅读。传统的条条框框的报刊书本上的内容,早已经被人厌倦,甚至那些中规中矩的叙述、不痛不痒的议论、味同嚼蜡的描写,都让人昏昏欲睡。
我在二十年以前就说过,笔墨当随时代。这句话没有过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字载体,今天的载体,就是段子。
段子,似乎是今天的说法,其实早就存在,只是我们忽视了其存在的价值。小小说、微型小说、精短小说,换了马甲而已。近二十年,大量纯文学刊物濒临困境,没有政策支持,可能一天都活不下去。但是,微型小说刊物继续挺立在街头的报刊亭,包括那些形形色色的《故事会》之类。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学没有死亡,它只是变化了。
忽然看见一则信息,说,仅仅十几年,方便面输给了高铁,互联网战胜了扑克牌。许多巨头的失败,并不是被同行另外一家巨头击败的,而是被其他行业给击败了。比如说,当年诺基亚跟摩托罗拉一直在竞争,但最后谁都没有压倒谁,却双双被安卓、苹果给击败了;柯达曾经是盛极一时的胶卷老大,不过没有想到,最后却在短短两年之内就破产了——击败柯达的,同样不是富士胶卷,而是数码相机;而数码相机也好景不长,快要被智能手机击败了……最近几年,方便面在中国的销量越来越差,连康师傅这样的巨头日子都不好过了。方便面销量少了,其实跟高铁有关系。过去人们坐火车,一般要坐很久,大家最喜欢的食物,自然就是方便面。现在许多地方都通了高铁,绿皮火车已经越来越少人坐了。高铁的速度快了很多,许多人已经不需要在车上吃饭了,所以方便面的销量也就开始下滑。同样,以前旅行都喜欢玩的扑克牌,现在也被智能手机代替,而生产扑克牌的公司则濒临破产。
科技发展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直接改变文化存在的形式——注意,再怎么改变,也只是形式的改变,其中的灵魂仍然存在。
作为作家,只要你的灵魂还在,就不用担心形式的改变。那些失去读者的作家,你以为自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李洱对于“碎片化”的形势还是了解的,只是过于乐观。他认为长篇小说可以和“碎片化”对抗,实际上,目前年产量过万的长篇小说面对“碎片化”只能招架,勉强招架。因为某些系统仍然一副官老爷的态度,错过了与网络写手的相互认知、互相补短的窗口期。看看今天的影视剧就明白,大部分剧目的改编来自于网络小说,而作家们的小说如果不被影视剧纳入,其影响当然不能被有效放大,最好的结果,只有去各个大学的文学院,请求职业阅读者过目,然后作为分类垃圾处理。
以前,是网络小说写手希望被作协接受,天天盼“招安”;现在,许多作家则在跪请网络写手“受封”。
一个文学评论家告诉我,他这么多年其实就一直在做“垃圾分类”工作,谁叫自己吃的是当代文学这碗饭呢?“你是什么垃圾?”这是他面对所有值得怀疑的作品进行的拷问。是干垃圾?湿垃圾?可以回收的垃圾?不可以回收的垃圾?“大部分小说,”他笑得很阴,“属于不可回收的湿垃圾!”
显然,李洱是自信的,他已经找到“对抗‘碎片化’”的办法,就是把网络上的“碎片”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像影视剧中的植入广告,变成他长篇小说的一部分,然后去拿茅盾文学奖。
这不是抄写,是改编,或者叫移植。况且,网上的段子又无人认领,不存在版权问题——当年贾平凹的《废都》里也有民间传说嘛,而且,还是直接取《金瓶梅》的瓶子装他贾平凹的酒,一来继承了传统,二来汲取了民间文学宝库的营养。那么多的山歌还不是民间高人收集、传播的?
与其对抗,不如笑纳。这才是虚怀若谷、高风亮节。
有人说,《繁花》没有结构,就是“碎片化”的口语集合体。也许,就是这么无意间诞生了一种新的文本。
还有人说,《繁花》也好,《应物兄》也好,不经意间,中国文学出现了“撸奖体”。
也许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体制内作家的焦虑来自于读者越来越少了,起印数从五千册到四千册,这是最焦虑的时刻。到三千册两千册,也就无可奈何了。他们已经放弃市场的读者,纷纷寻找其他读者。先是挨家挨户到各个大学文学院送书,饭局不断,礼品不断,然后重点进攻各个作协的负责人,主要是评级、评奖的评委们。
也有一些有追求的作家在想其他办法。那年我在市场上买到两个作家的书,都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刷数量都是三千册。一部是余华的《活着》,一部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关键是市场销售非常不好,我还是在旧书摊上买的,五折。
后来,韩少功与张颐武打起官司,《马桥词典》不断再版。这以后,利用官司甚至利用负面消息炒作,成为书商的营销模式。韩少功是中国作家中最懂市场的人,也是最善于在文学里面发现新闻价值的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明白不能单纯地写小说,要有理论,而且要理论先行,所以他推出了“寻根文学”这个概念。他也是最早投入海南岛商业开发大潮的作家,在《海南纪实》的发行中,学会了利用质疑、争议吸引读者的目光。——顺便说说,文学官司有没有必要打?回答是肯定的。事实上,民国时期的作家为什么名气那么大,就是因为文学官司那么多。但是这些官司都是打笔仗。鲁迅的文学官司打得多,打得大,而且,得道多助,越打朋友越多。他赢在技巧,赢在语言。但文学官司如果闹到法庭上,就属于舞台表演了,嘚瑟的成分占了大头。所以,当看起来温良恭俭让的韩少功以厅长的身份勒令北京大学副教授张颐武去海口到庭应诉,喜欢韩少功的读者才发现,他骨子里还是那种“霸蛮子”。
余华则是读者们在慢慢的阅读过程中发现的大师,他靠读者的口碑宣传,使作品发行量暴涨。没有炒作,就没有故事。但余华是中国作家中故事最少的人,至少,目前还是这样。
那些写不出《马桥词典》《活着》的作家,人家调整好心态,注意力全部放在作协,彻底放弃市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个道理谁都懂。一些作协也知道礼尚往来,肥水不流外人田,每年评级评奖,作协内部优先,在编的又优先。这些活动成为许多地方作协的年终评奖,互相计较起来,评级评奖也是要放在年终奖的大篮子里面考虑的。
然后是作协外围。那些与作协相关人员走得近的,进入一杯羹利益均沾范围,该拜老师拜老师,该拜码头拜码头。最近二十年,中国作家尤其是诗人最大的进步就是不清高了;也许还有清高,但清高的方式变化了,身前一只手拒绝,表面拒腐蚀永不沾,背后一只手,则想方设法拉关系。
你想啊,申报下题材就有费用了,下生活采访又有费用,然后,刊物发表,买书号出书,出版以后还有座谈会,接着还有评奖,评奖完了还有评级……就像包介绍对象,包操办婚宴,包生孩子,还要包生儿子,一条龙。
所以,你还用得着去市场找读者吗?
随之而来的应该是和谐了吧?结果,一些地方作协却是好友反目,甚至大打出手,互相写告状信。你说僧多粥少,互相给点拳脚可以理解,可是这些年对作协对文学的支持力度已经很大了,甚至在一些作协已经是粥多僧少了,有的主席副主席“撸奖”撸到手软,一些地市级作协的奖甚至是专门为主席副主席设立的,你们还闹个甚?可是,但是,真是,内讧力度大的还就是那些得到财政扶持力度大的作协,甚至成正比关系:扶持大,内讧大。而且,情况还多半发生在某些“撸奖”大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