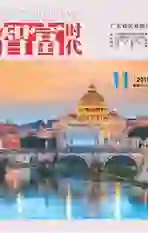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国家信用风险问题初步研究
2019-12-26李春南
【摘 要】2018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一千一百多种商品征收税率为25%的关税,当年7月初正式生效,中国政府随后宣布同等规模、与美方措施同时生效的反制措施,自此,世界上两个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之间贸易摩擦发展到新的阶段,直到2019年10月,发展到第三阶段。贸易战是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利益的平衡过程,也对多年来保持相对稳定的国际信用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对贸易战背景下的国际信用风险进行初步分析,提出主动应对防范建议,希望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行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贸易战;国际信用;国际金融;风险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世界各国全面走出战争泥潭,进入战后重建阶段。此后的70多年间,以联合国为中枢,中、苏、美、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主导,以维护国际社会总体和平安全、促进区域主权独立国家合作交流为基本宗旨,全面构建新型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建立政治互信,为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创造良好政治环境。同时,以1947年下半年在日内瓦签订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为起点,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也迅速建立起来,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1994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全面取代GATT,以提高世界各国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深度就业、扩大国民经济收入规模和不断增加宏观经济需求总量为宗旨,现有160多个成员国。几十年来,国际政治和经济两大体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既独立又关联。国际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有形规则的背后,是共性的国与国之间信用的输出和融合。其中,国家信用处于信用体系层次化结构的最顶端位置,是经济、贸易、文化等行业信用体系建立的基础,无形的信用体系不稳定,有形的商业贸易信用体系就无法摆脱脆弱和短暂的形态,随之而来的便是国际信用风险的加大,风险管理难度增大,成本提高,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国际信用风险问题的严重性。下面,从几个方面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探讨。
一、中美贸易战背景及国家信用的基本内涵
中美双方贸易战的发生有历史的必然性,本质上不是纯粹的经济利益之争,而是两个独立国家主体、两种社会组织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的博弈。
(一)中美贸易战的直接背景
2010年,中国GDP总值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越居世界第二,同年,美国的GDP达到15.5万亿美元,超过中日两国GDP总量之和,是中国的2.69倍,日本的2.89倍。此时,中日两国任何一方的经济体量均未对美国构成显著威胁。奥巴马政府对于中国的战略定位仍然是有缺陷的战略合作者,双方仍然能够在求同存异、相互受益的构架下开展正常的政治经济交往。但是,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步步为盈,综合国力明显提升,引发了美国的极度战略忧虑。特别是2015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制造2025》规划后,美国明显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巨大挑战。2017年中国GDP总量占美国19.38万亿美元GDP的65%;2018年中国GDP总量占美国20.5万亿美元GDP的69%。面对这样一个强劲对手,2017年1月执政的特朗普政府决定,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采取严厉措施加以遏制。策略是先从国际贸易入手,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经济围堵。于是,2018年6月正式宣布,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输美商品加25%的关税,同年7月6日生效,作为反制,中国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出口中国等额商品加征同样比率关税,且与美方加征时间同步。
(二)信用和国家信用的基本内涵
信用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般认为它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存在于个体和个体之间、个体和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不同主体之间的信用,形成时间、存在形式、持续时间和展现价值互不相同。从经济视野看,信用是在人类物质资料生产和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输出信任一方给予接受信任一方一定的经济资源者使用权的交换过程,并通过适当的契约形式表达双方的真实意愿。信用是有价值的,也是有成本的,可以长时间存在,也可以在短時间内消失。
信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国家信用属于前者,指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承担信用主体,在最高信用层次上推动政治经济走势和资源的跨国流动。国家信用的核心成立条件是相互需求、相互供给、共担风险、共同受益。也就是说,国家信用首先具有双向性和互利性。缺少任何一点,都无法建立和维持。
二、贸易战中中美双方国家信用的差异化表现
(一)中美贸易战的几个主要阶段
中美贸易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一是2018年7月上旬,双方各向对方价值5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25%的进口关税;二是2018 年 8 月初,美方宣布对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中方采取数量和质量相结合的策略宣布反制措施;三是2019 年5 月9 日,美方自2019 年5 月10 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税率由10%提高到25%;中方宣布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600 亿美元的部分美国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实施25%、20%、10%、5%的不同税率;四是2019年9月5日,美方提出对余下的3,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二)中美贸易战中国家信用的差异化表现
中美贸易战期间,双方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措施和节奏,也充分体现出差异化的国家信用应用方式。
美方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强调美方利益至上,中方利益必须服从、服务于美方利益,如果中方不同意,则威胁使用关税大棒逼迫中方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贸易欺凌心理和做法,而且,多次置国家信用于不顾,推翻双方磋商中已经达成的共识协议。非但如此,还以美国国家利益为轴心和标准,对欧盟成员国实施贸易制裁,退出多项联合国组织或协议,无任何国家信用可言,其行径动摇了二战以来国际秩序稳定基础,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人们在思考,如果国家信用得不到严格恪守,那么这个国家里,还有什么其它层次的信用是可信的。显然,如果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信任,也必然会影响到该国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与其他国家的有效接触和资源互动。
与美方相反的是,中方在贸易战的前前后后,一直以恪守国家信用为原则,有理有节,坚决不打贸易战第一枪,坚持最大限度地维护中美双方共同经贸利益,态度鲜明,前后一致:对于贸易战,我们不愿意打,但也不怕打;谈判解决,随时欢迎,有理有节,坚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这种态度,既是对国家利益的維护,也是对国家信用的尊重。大国地位,大国形象,不单是靠军事和经济力量来支撑和展现的,也离不开国家信用的承诺和坚守。很大程度上,维护国家信用,就是展现国家意志和决心,就是展现国家的政治韧性、经济弹性和行为理性。
三、美国国家信用风险的危害及有效预防
(一)美国国家信用风险的形成根源
国家信用风险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20世纪50—70年代冷战期间,美国和当时的苏联争夺世界霸权,过度追求军事装备数量和质量的绝对优势,形成两个超级大国,形成两大阵营,实际控制主要国际事务,在此过程中美国为了争取战略优势,主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欧洲国家保持战略合作关系,总体上信守国家承诺,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整个国际社会中国家信用体系的形成,有积极作用。
二是1991年12月,原苏联政治上解体,美国成了单极世界的主宰者,综合实力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再加上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动力,美国在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远远走在其他国家前列,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一方面利益于美国经济发展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宏观国际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美国日益加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不平等贸易规则,美元汇率操纵,绕开联合国对小国发动战争,等等。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体会到了单边信用带来的巨大利益,它要求其他国家必须按美国意愿行事,却对自己恪守国家信用边界模糊,双重标准。
三是联合国作为国际政治协调中心,现有管理制度还不能对国际强权政治形成有效的约束和管控,相反,多数情况下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操作国际社会,维护集团利益的政治工具,没有真正落实联和国宪章和宗旨,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不足。
(二)国家信用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古人说,人如果不讲社会信用,就不知道他能够在社会中如何得以生存发展。强调的就是人和人之间信用的重要性。具体到两个国家之间,信用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且社会影响也远比个人之间的信用大得多。这里所说的“影响”,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负面的。在国际舞台上有影响力的大国,重视和遵守国家信用,带头履行国际政治准则,一方面会为国际社会树立行为典范,展示大国风范,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增强话语权和信服力,另一方面,也会给当事国带来直接和间接国家利益,促进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推进双边和多边贸易发展,提升贸易便利化程度,加快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双边和多边互利共赢。
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特别是政治经济大国,经常忽视国家信用,将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总是凌驾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之上,则在本质上不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是人类社会从原始走向文明的退化,必将遭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致反对,是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大势,不利于自身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也不利于构建公平、和谐、友好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时间越长,影响越深,危害越大。
(三)国家信用风险的防范治理
国家信用风险是一切社会风险中的最大风险,代表的是国家意志和民族意识形态,其防范与一般的社会风险防范相比也有很大差别。首先,当事国家要摆脱局部、短期利益的约束,消除追求绝对利益、绝对优势的不对称心态,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走势,尊重各国主权利益,共同构建和平友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其次,要积极促进多边贸易发展,形成多极化世界,增加对单边力量的有效牵制力度,以均衡的国与国之间力量分布维持正常的国际秩序形态。最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加强多边政治经济合作,发挥整体优势,最大限度地孤立单边势力,迫使少数国家遵守国际准则。
四、结束语
信用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首先产生于个体与个体之间,最后延伸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的信用体系自然属性成份比较大,其产生范围、持续时间、体现形式和效用呈现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相比较而言,国家信用社会属性的特征更为明显,是单个国家信用的补集和交集,有很强的兼容性和耦合性,在当前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下,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推进国家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应用。
【参考文献】
[1]史思义.现代国际金融学[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
[2]王正义.国际政治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孟庆福.信用风险管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李春南(1987—),女,河北人,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在职人员高级课程研修班学员,金融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