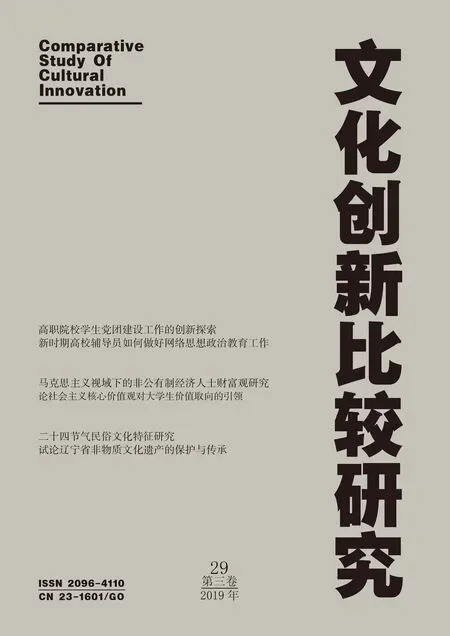从文学伦理学视角下解读电影《美国田园下的罪恶》
2019-12-26刘雯雯
刘雯雯
(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30)
电影《美国田园下的罪恶》是一部改编自真实犯罪记录的影片,从《美国田园下的罪恶》播出开始,让观众受到强烈的震撼,因其深远厚重的文学意义和回环往复的故事结构,深受观众的欢迎。虽然在研究《美国田园下的罪恶》方面,还未形成系统的阐释专著,甚至关于此电影的论文是少之又少,目前关于电影的论文能搜到的只有在期刊《电影世界》上2008年第九期发布的佩索阿的一篇题为“集体有意识犯罪《美国田园下的罪恶》”[1]的文章,但是此电影所包含的伦理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文学伦理学作为本土的文学批评方法,拥有着较高的文学阐释意义和价值,能够为细致研究文本提供良好的理论前提。文学作品本身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教诲世人,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加以解读,更需要深入发掘其教诲功能,给读者传达正面积极的榜样力量和道德模范,实现警示现实世界的目标。该研究主要是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入手,分析和阐述《美国田园下的罪恶》中所包含的伦理环境、伦理意识以及伦理禁忌方面的相关内容。
1 影片情节及主要人物介绍
影片 《美国田园下的罪恶》,原电影英文名是“An American Crime”,也有翻译是《美国式犯罪》,描述了一起发生在1965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宁静的田园风光下的真实的虐待儿童的事件,该影片的拍摄素材大量来自该案件的真实法庭纪录。16岁的西尔维娅是故事的主人公,她和妹妹詹妮被需要外出巡演的父母寄养在父亲临时认识的一位印地安娜寡妇格特鲁德的家中,压力颇大的格特鲁德自身共有6个孩子,5个是与前夫所生的孩子,最小的儿子(还是一个婴儿)是她同22岁的情人安迪所生。经济来源甚少的她急需依靠抚养这两个孩子来赚钱。原本她们只打算呆几个星期,但是过了很久,他们的父母仍然没有出现,而且连每周都会寄给格特鲁德家的20美元寄养费也没了消息。因此,为钱所困的格特鲁德开始不满,“教训”了这两个寄养的孩子。原本西尔维娅以为很快就没事了,没想到厄运刚刚开始。格特鲁德最大的女儿宝拉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西尔维娅,但是西尔维娅却在意外中为了保护宝拉说出了这个秘密,自此宝拉身边流言四起,气愤的宝拉向母亲诬告了西尔维娅,说西尔维娅欺骗大家,本身已经对西尔维娅和詹妮生气的格特鲁德怒意横生,决定必须惩罚这个“坏女孩”,西尔维娅被关在黑暗潮湿的地下室里被虐待,她的妹妹因为胆小没有帮助西尔维娅,放任西尔维娅被施以各种惨不忍睹的暴行,折磨她的不仅仅是格特鲁德一个人,还有她的5个大孩子,5个孩子的朋友以及邻居家一位暗恋西尔维亚的男孩[2]。
2 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主要用于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文学有关的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同传统的道德批评不同,它不是从今天的道德立场简单地对历史的文学进行好与坏的道德价值判断,而是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做出道德评价[3]。因此,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些观点来解释文学文本,可以让读者更好的理解文本,并从中获得一定的教诲意义,分清善恶。
3 电影《美国田园下的罪恶》中的伦理环境
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的伦理环境的分析。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3]。因此,我们需要回到主人公西尔维娅所在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分析她的伦理悲剧的根源。
二战后的美国进入到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成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国内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到西部和南部,经济呈现繁荣景象,但富裕的社会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印第安纳州处于美国的中北部偏东的地区,当时经济落后,每个家庭都迫于经济的压力,需要寻找各种途径挣钱,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经济压力的环境之下,西尔维娅的父母被迫把孩子寄养在另一个也急需挣钱养育6个孩子的寡妇格特鲁德的家中。同时当时政府鉴于二战中伤亡人数较多,大力提倡人口生产,人口激增带来社会分配不公,社会混乱,再加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父母及学校对孩子大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致使社会上各种道德沦丧的问题出现,比如格特鲁德的大女儿宝拉,19岁就被人骗,未婚先孕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经济压迫、城市动乱、社会风气不正,就是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之下,西尔维娅一步步陷入了她的伦理悲剧。
4 电影《美国田园下的罪恶》中的伦理意识
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解,由于理性的成熟,人类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人才逐渐从兽变为人,进化成为独立的高级物种。把人同兽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就是人具有理性,而理性的核心是伦理意识。[3]所以,具有伦理意识的人,是可以分辨善恶的人,而一个不辨善恶、不分黑白的人,根本称不上是一个具有伦理意识的人,只能说是一个受到自由意志控制的“兽”,兽性因子在他身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的人只会做出害人害己的事情,造成双方的伦理悲剧。
最初的格特鲁德也是一个有着强烈伦理意识的主妇,也是一个理性与善的象征,在她内心深处也有“善”的存在,她通过为邻居缝补衣服来补贴家用,对自己的孩子、寄养的孩子也是一视同仁,但是在西尔维娅的父母寄养的费用断绝,以及格特鲁德那个不务正业的情人来拿走她仅有的生活费用以后,她的经济状况陷入困境,此时为钱愁闷的她伦理意识开始混乱,兽性因子开始觉醒,心中的“恶”开始作祟,觉得这一切都是西尔维娅和詹妮的错,如果她们的父母按时给钱,就不会陷入现在的窘境,于是她毫无征兆地在地下室用鞭子“教训”了西尔维娅及詹妮。但是这还仅仅是悲剧的萌芽,在一次西尔维娅为了保护宝拉,说出了宝拉怀孕的秘密以后,感到受辱的宝拉向母亲告状,声称西尔维娅欺骗大家说她怀孕了,听到这些诬告后的格特鲁德心中的兽性因子蠢蠢欲动,想要找寻机会“教育”一下西尔维娅,就在这时,在室外聚餐的时候安迪同西尔维娅说了几句话,吃了醋的格特鲁德兽性因子完全爆发,人性因子向兽性因子做出了妥协,任由自由意志控制自己的行为,彻底失去了伦理意识,成了一个真正的“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加之之前的误会和愤怒,她笃定西尔维娅就是一个荡妇,一个失德的女孩,她需要好好“教育”一下这个“坏女孩”,并为自己的女儿讨回一个公道,她在众人的面前羞辱了西尔维娅,并让他的孩子们把西尔维娅扔进地下室,在地下室百般折磨西尔维娅,直到她的孩子发现了西尔维娅没有了反应,西尔维娅的事情才公布于众,虐待她的人也被送上了法庭。
5 电影《美国田园下的罪恶》中的伦理禁忌
在人类文明之初,维护伦理秩序的核心因素是禁忌。禁忌是古代人类伦理秩序形成的基础,也是伦理秩序的保障。[3]通过禁忌,人们可以对那些被公认的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进行约束,维护社会的秩序。
电影《美国田园下的罪恶》中所描写的违反伦理禁忌的事就是虐待儿童这个事件。“虐童”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社会话题,也是一个明显触犯禁忌、违背社会伦理秩序的事情。儿童是我们社会的基础,国家的未来,保护儿童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的国家,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也是具有伦理意识的人守住社会道德底线、遵守社会秩序的表现。人是社会中的人,处在社会当中,就要受到伦理禁忌的制约,破坏伦理禁忌自然就会受到惩罚。格特鲁德本也是一个遵守伦理秩序的理性寡妇,本本分分地养着自己的孩子和寄养的孩子,但是在多重原因的影响之下,精神不稳定的她最终冲破了伦理的禁忌,残害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导致了西尔维娅以及自己的伦理悲剧。“虐童”对于儿童的影响是深远的,也反映了社会上一些伦理意识缺失、破坏伦理禁忌的现象,这不仅是一个人的事,而且是全社会的事。这个残酷的“虐童”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虐童”事件频频发生,为了要杜绝类似残忍事件的发生,我们不仅要加强学校和家庭教育,使社会全体人民的道德文化素养得到提高,更要注重主体自身的伦理教育,使道德正气得到弘扬,让不道德的社会现象无处可存[4]。
6 结语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功能有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基本功能只能是教诲功能。文学的功能指的是文学作品自身所特有的影响读者和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效能。教诲指的是正面的积极的知识学习和道德教育。在知识学习和道德教育的关系中,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教诲,教诲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文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借助教诲的功能,从而帮助人完成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伦理选择过程[5]。该研究从伦理环境、伦理意识和伦理禁忌三个方面分析电影,旨在发掘出电影《美国田园下的罪恶》中所包含的深刻教诲意义,唤醒人们的冷漠,呼吁人们多关注儿童的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