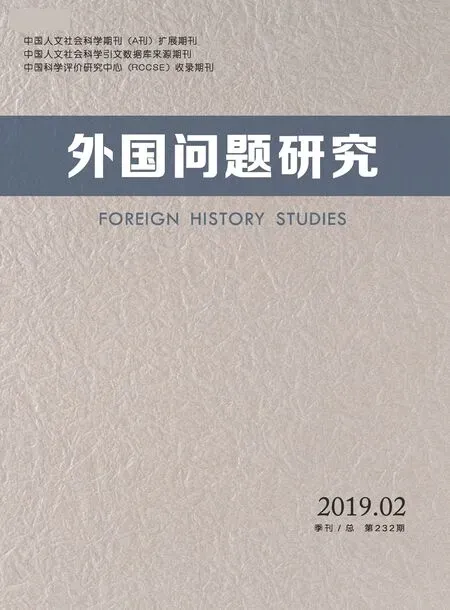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2019-12-26李枫
李 枫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蓄谋已久的安排下,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嫁祸说是中国军队制造的破坏事件,以此为借口,日本关东军突袭并占领了沈阳。在此后的四个月时间内,东北三省大部分地区被日军攻陷。为了更方便的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同时也为了掩盖其吞并东北的侵略行径,日本扶植溥仪为傀儡,建立了“满洲帝国”。1932年3月1日,溥仪出任“执政”的伪满洲国发表“建国”通电,至此,东北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在伪满洲国期间,日伪对中国东北进行了殖民地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一、法西斯文化统治与欺骗宣传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便开始了被日伪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展现在世人幕前的是“满洲帝国”,而实际操控者却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持续其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统治和掠夺,除了直接的军事占领,还有更为恶毒和隐蔽的在思想文化上的虚假宣传和皇国思想的奴役,以希冀达到麻痹东北人民,使其便于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因此,在伪满洲国统治东北期间,日本牢牢掌控和垄断着伪满洲国的一切文化组织机构。东北沦陷的14年间,东北的文化被日本殖民主义施行着全面的专制管理与垄断监控。而这种专制管理和垄断监控被日本殖民主义者美其名曰“官制文化”,而所谓“官制文化”的核心实质,就是殖民地文化专制和法西斯文化专制。①于湘泳、张守祥:《日伪时期的“协和语”新考》,《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年第6期。实施这种专制管理的机关单位是伪满国务院总务厅下属的弘报处。该机关的目的就是要钳制言论文化自由,充当日本军国主义殖民统治中国东北的舆论喉舌,全面指挥伪满洲国的宣传情报工作,以达到为日本发动和扩大对外战争宣传和服务的目的。
首先是控制言论机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便建立“满洲国通讯社”,简称“国通社”,直接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国通社”实质上就是日本通讯社在东北所设的分支机构。②张贵:《东北沦陷14年日伪的新闻事业》,《新闻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至1934年末,“国通社”的总社与支社共有17处,建立了囊括整个伪满洲国的新闻通讯网,彻底垄断了东北地区全部的新闻通讯机构与事业,由此剥夺了东北人民正常的新闻渠道和通讯自由,毒害东北人民的思想和对外知情渠道。而这种思想钳制越发变本加厉,1935年,日本殖民主义为了进一步垄断宣传机构,实施所谓“一个国家一个通讯社”的恶毒口号,进一步建立了集报道、言论与经营为一体的辖管新闻、通讯机构的专制机构——“弘报协会”,将新闻传统的法西斯式专制统治推向另一个高峰。①冯为群:《日本对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统治》,《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
对于报纸,日伪先是通过颁布《出版法》,由宪警对报刊进行检查和取缔。伪满初期,日本势力已在报界占上风,但没有控制全局,特别就发行量而言,中文报纸占绝对优势。随着日本对伪满洲国统治的日益巩固,在1941年,日本假借伪满洲国之手,先后颁布了所谓的伪满洲国《通信社法》《新闻社法》和《记者法》,实际就是为了便于日本殖民主义者对东北新闻界和报界的全面控制,以此彻底垄断了伪满洲国的新闻和报纸事业。为了控制报纸的发行,合并报社,建立了康德新闻社、满洲日日新闻社和满洲新闻社三大新闻社。康德新闻社合并了18家报社,满洲日日新闻社合并了3家报社,满洲新闻社合并了6家报社。其中只有康德新闻社采用中文发行,满洲日日新闻社和满洲新闻社都是采用日文发行。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其对伪满洲国的思想统治更为残酷,到1944年干脆将满洲新闻社和满洲日日新闻社再一次进行了合并,称其“满洲日报社”。②张贵:《东北沦陷14年日伪的新闻事业》,《新闻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
东北广播事业“九一八”事变前刚着手建立,伪满洲国建立后,由日本殖民主义者所垄断,建立起“满洲”电信电话有限股份公司,截至1941年伪满共有18个广播台。
除了新闻、广播事业的垄断,日本殖民主义还将魔爪伸向了出版事业,并且对此特别重视。伪满洲国建立后,一面着手削弱和打击民族出版事业,另一方面则加紧建立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垄断的出版机构,迅速建立起以全面掌控出版事业的机构组织。1937年,伪满洲国建立了“图书有限股份公司”,其核心作用便是用以出版服务日本对伪满洲国进行殖民奴化教育的学校课本教材,在东北推行所谓“国策”图书。1939年又成立了所谓“书籍发行股份公司”,协助伪满洲国施行严格的有利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出版审查制度,进而将东北的图书发行和图书进出口全面施行了垄断管理。1943年,再次建立了伪满洲国“出版协会”,更是毫无保留地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政治需要,全面管控整个东北的出版事业。正是在这样的集中垄断统治下,其他相对于服务日本侵略战争关系不大的出版物几乎全部被禁绝出版,对东北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滞阻作用。
日伪利用新闻、报刊、广播、电影、文艺等各种手段,进行欺骗宣传,鼓吹“东北与中原本土分离论”,掩盖伪满洲国的傀儡实质。日本殖民者为彻底吞并东北,变东北为日本本土的一部分,肆意篡改历史,炮制谎言,把自古以来与中原本土不可分割的东北说成是“满、蒙、朝三朝的天下”“明代以前,汉民族从未进人满洲”“汉族是持强侵入(满洲)的外来民族”“满洲自古以来是由同汉民族风俗习惯完全相异的满洲土著民族支配”,等。③王夏刚:《论抗战时期的中国东北史研究》,《大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王夏刚、曹良德:《抗战时期金毓黼东北史研究述论》,《大连近代史研究》2009年刊。日本一批右翼学者,诸如白鸟库吉、稻叶君山、矢野仁一等,无不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服务,在得到关东军的授意下,大肆鼓吹“满蒙”历史的独立性,蓄意割裂东北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从属性,先后发表并出版了诸如《满洲发达史》《满洲国历史》《满洲国史通论》《满洲国国民道德概论》等论著,把汉人与东北少数民族两千多年共同建设东北的历史污蔑成为“满蒙民族驱逐汉族人”的历史。④王夏刚、曹良德:《抗战时期金毓黼东北史研究述论》,《大连近代史研究》2009年刊。这种从分化民族关系的角度去歪曲东北的历史事实的行径,其目的就是妄图抹煞傀儡政权是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的罪责。
日本侵略者在鼓吹伪满洲国独立的同时,还在种族优劣上大做文章,鼓吹日本殖民主义者对“满洲国”来说是有功之臣,甚至宣称日本帝国主义是“满洲国”的主人。同时又为日本民族冠以多道五彩的光环,自诩为“天孙人种”、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所以理应为“满洲国构成的中核分子”“五族(日本、朝鲜、蒙古、汉、满)的光达者”“国民中最有为的种族”。这就把日本民族捧到超越东北其他任何民族之上的阶梯之顶,宣称必须由日本民族宣化诱导程度低的其他民族。这种公然以“主人”和“领导者”自居的日本侵略者的言论,充分暴露了侵略中国的野心。
在炫耀日本民族优越的同时,日本侵略者竭力污蔑中国人民。在满铁调查部的《满洲矿山劳动概况调查报告》中,污蔑中国人“不法、无知、愚昧,是满洲苦力”。在谈到文化时,日本侵略者更是大言不惭地自诩日本是“东方惟一的高文化”,污蔑和贬低中国文化是“低文化”,其颠倒黑白的手段令世人所不齿。而作为日本统治东北傀儡的伪满洲国则助纣为虐的替日本殖民主义鼓吹和助阵,其重要宣传媒体《旬报》甚至厚颜无耻地说:“所谓日满文化交流……就是移入日本文化”;更加令人气愤的是,居然还宣称“满洲国语”不是汉语,为此,还在1940年,专门成立了“满洲国语研究会”,妄图用日语同化汉语,力主将大量日语掺到汉语中,此手段非常歹毒,是企图取代中华文化在东北的文化地位,斩断东北与中国内地的文化联系,建立日本思想和文化的统治。①敖文蔚:《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谬论特点剖析》,《日本研究》1993年第2期。
二、“王道主义”与“惟神之道”
日本侵略者为使伪满文化更具有欺骗与麻醉人民的作用,向东北人民灌输所谓“王道主义”与“惟神之道”,以养成所谓“国民精神”。②李兵:《奴化教育与教育社会功能的反思》,《直面血与火——国际殖民主义教育文化论集》2003年刊。
“王道主义”与“惟神之道”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用来吞并中国东北的思想理论基础,被其简称为“王道”和“神道”。而所谓“王道”思想,是其推行、建立及维护其殖民统治秩序的中心指导思想,也是极为有利于其完成思想钳制的宣传手段。因此得到了日伪的大肆宣扬、传播、推广和“赞誉”,所谓的“王道主义”充斥在伪满洲国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中,被吹捧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善、最美好的政治体制。为了广泛宣传这种“王道政治”,伪满洲国各种舆论机构和单位组织都要对其进行美化与宣传,将其作为日常工作的重要任务。
事实上“王道主义”具有极大的反动性和恶毒用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制造便于统治的“良民”。以一种诱骗的方式让东北人民位于日伪统治政权俯首帖耳,对暴力统治循规蹈矩,变成殖民统治下的顺民。为便于这种宣传,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提出所谓“遵法修礼”“恭义顺睦”等愚民口号,在东北人民头上罩上腐朽的封建礼教的无形枷锁,使善良淳朴的东北人民不敢对日伪残暴统治和奴役宣传进行反抗和怀疑,只能循规守矩,不敢逾越“法度”,更加对所谓“王道社会”宣扬的各种规范、法律、制度、意识等信条和法度不敢违背,否则便是“大逆不道”,是违反伪满洲国同行的道德和法律的行为。
其次,消磨东北人的反抗意识,破坏任何有违日伪统治的斗争意志,让东北人民变成逆来顺受的奴仆,甚至是奴隶。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1931年的《王道救世之要义》中提出:人们要“正心”“修身”,尤其是青年人务必要“戒狂傲”“戒轻浮”,其中心要旨便是号召东北人民对于统治当局不得有丝毫反对之举,哪怕遇到不公正之待遇,亦要秉持“压制”之心,否则,社会将濒临“总破产”之局面。非常明显,郑孝胥的宣扬说教,是为了彻底泯灭东北人民的斗争意志,让人民逆来顺受,是麻痹和毒害东北人民的“砒霜”和精神鸦片。
最后,曲解爱国主义内核,鼓吹“对日亲善”,献媚日本殖民统治集团。对于日本殖民主义的统治,伪满统治者不仅不因其傀儡身份羞耻,反而竭力讨好献媚殖民者。郑孝胥一向主张所谓“亲仁善邻”,鼓吹满日之间应不分种族、不分国别,思想大同、共进共退,进一步提出“满洲”人应该“洗除爱自己国家的思想”,去爱“大众的国家”。而所谓的“大众的国家”其实质就是日本而已。
综合伪满洲国宣传的“王道主义”的表现可以看出,其内涵和实质不过就是把业已摒弃的封建思想糟粕与卖国主义的货色杂糅在一起,变身为一种愚民思想,灌输给东北人民,是封建主义和卖国主义混合在一起的畸形产物。
“王道主义”虽然为维护日本殖民统治炮制出许多“理论”和“思想”,但殖民主义者的欲望仍然没有得到满足,还要继续根深蒂固的扎根在民众基础土壤之中,从人民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宗教信仰和精神崇拜入手,更加深入的奴役和愚弄东北人民,企图让东北人民失去正常的思维能力,完全行首走肉的为日伪所控制,思想上完全的“皇民化”。为此,日本信仰的“天照大神”被移植到东北大地,摇身一变成为伪满洲国崇拜的偶像和所谓的“保护神”。1940年,日本安排溥仪第二次访日。溥仪只是按照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导演,向裕仁天皇表示要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伪满洲国祭祀,裕仁便表示同意,并立即把早已准备好的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交给溥仪捧回。溥仪回到长春后,把象征“天照大神”的三种“神器”供奉在特于宫内府旁修造的木造“建国神庙”之内。①彭超:《吉冈安直与伪满建国神庙》,《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
同年7月7日,溥仪率领一干人等在祭祀官指引下前往建国神庙拜殿,举行日本式的“镇座祭”,将日本的“天照大神”鬼使神差的“奉请”到伪满洲国,变成了伪满洲国的“建国元神”,更为数典忘祖的是,溥仪居然身着伪满洲国陆海军大元帅服,手执专事祭祀用的“五彩币”,以伪满洲国皇帝的身份对着日本三件“神器”礼拜再三,全程表现得毕恭毕敬。接着由祭祀官宣读祭文,先用汉语,后用日文,想是“天照大神”初来异土不习汉民语言,实在有必要把祭文“翻译”过来吧!就连日方军政要员也颇感滑稽,自我解嘲说:“用日满两种告文同时奉上实乃古往今来的第一次。”同一天,以溥仪名义发表了一个《国本奠定诏书》,宣称伪满洲国从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都是依靠“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因此必须以“天照大神”的“惟神之道”作为国本。②王文锋:《日本侵华罪证的新发现——伪满洲国建国神庙遗址的发掘》,《民国档案》2002年第3期。
随后,伪满洲国内便掀起了强迫百姓信奉“天照大神”的一系列拙劣的表演和强制措施,强迫勒令各级机关单位、尤其是学校等部门均要修建形态不一的“建国神庙”。据1945年统计,日伪在东北城乡建了大小日本神社295座。③体恒:《凄风惨雨国劫日狮子奋迅救难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法音》2005年第7期。在神社供奉“天照大神”的牌位,强迫要求人们定点定时的前去参拜,并且对参拜时的规程和仪态都做了硬性规定,每次经过时必须要行九十度的最为恭敬的鞠躬礼,不准有任何忤逆和不逊,如果稍有抵触和违背,动辄就会以“大不敬”的罪名予以惩处,更为严重者则会遭到逮捕或问刑,实行极为严苛的制度以推行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尤其是在各种庆典礼仪的时候,参与者必须要遥拜日本的“皇大神宫”和伪满洲国的“建国神庙”,还有同时背诵《国本奠定诏书》和《国民训》,奏唱伪满洲国国歌。④焦润明:《近代东北社会诸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而在各种宗教团体举行宗教活动前,无论其教规、教义如何,均要实行这些“仪礼”,以示尊崇“惟神之道”,不得有任何例外。这种规定还渗透到东北人民的日常习俗中。在举行婚礼时都要逐渐采取神前结婚方式,按照日本的传统,供奉“神官”发给的“神符”;即便不能到神前举行结婚仪式,也需要将旧式拜天地改为遥拜“建国神庙”。⑤焦润明:《近代东北社会诸问题研究》,第234页。
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麻痹东北人的斗争意志,彻底占领人们的精神世界,让其放弃抵抗,变成俯首帖耳的“良民”和“顺民”,采取了如上一系列强制性的神道崇拜活动。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充满了反抗,东北人民并没有在日伪虚伪的鼓吹和强迫的思想愚弄下彻底丧失思想意识。在伪满洲国统治期间,便采取公然或者隐蔽的方式对所谓的“建国神庙”等一系列日本神社加以破坏。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曾经遍布东北的神社瞬间便化为灰烬,人民对钳制了其14年之久的意识形态控制充满了抵触和反感,日伪所构想的对东北人民的思想统治只能是幻想而已。
三、殖民地奴化教育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对原有教育设施进行摧残和控制,关闭了原有大学和专门学校,扼杀了高等教育。对于普通教育也在保持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加以限制,重点进行了教材的删改,首先取消了“三民主义”课程,代之以《四书》《孝经》,接着是篡改了中国历史、地理、语文教材,删去了一切有关反对日本侵略宣传爱国主义的内容,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推广满铁公学堂所用教科书。从1934年9月起,开始推行所谓“国定教科书”,①布平:《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历史考察》,《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8期。这种教材以贯彻“建国精神”,愚弄民众,宣扬“日满不可分”和“忠君爱国”等为主要原则,传播弘扬儒教中“仁爱专制”思想,引导学生对伪政权忠诚,更要对日本“宗主国”忠诚,培养亲日、崇日的思想感情。并且,日伪将典型的法西斯皇道标签的“王道主义”援引和嫁接进入伪满洲国,妄图用日本的传统神话、宗教信仰的神道思想以及效忠日本天皇的“志士仁人”的典故来侵蚀和麻痹东北青少年的心灵;企图用封建糟粕的愚忠思想结合法西斯皇道思想,将二者杂糅为一体,进而变异和演化成为顺应殖民地统治的“国民文化”,为愚民政策服务,为殖民统治服务。
为进一步有利于其殖民奴化教育的施行和推广,随着殖民统治的时间愈久和日益强化,在日本侵略者的授意和指使下,伪满洲国进而提出了殖民色彩更为深重的“皇道教育”的方针,配合其出台和施行,于1937年5月公布《学制纲要》即“新学制”,从1938年正式实行。
“新学制”的宗旨,是培养日本侵略者所需要的俯首帖耳具有一定技术体格健康的奴才。它把学校体系划分为“三阶段二部门”。“三阶段”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二部门”即师道教育、职业教育。②李倩:《日据吉林时期的文化专制与奴化教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它的特点是,强调精神教育、劳作教育、实业教育,排斥预备教育,置重点于少年儿童的国民教育,而对中等程度以上的教育则以防止“学问游民”为名,实行严格限制。“新学制”首先缩短了修业年限,只有初等教育阶段依旧施行过去的四二制,而其他阶段的教育年限皆予以缩短,改中等教育阶段6年制为4年制,高等教育阶段4年制为3年制,整个修业年限全部学程只剩下13年,较比当时日本的学制整整短了5年的时间。对属于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的学校都冠以“国民”的字样,将初级小学校改称“国民学校”,同高级小学校明确分离作为完成教育,而将后者称为“国民优级学校”;中学取消初中、高中之分改名为“国民高等学校”,使之与大学直接相联。而对高等学校则采取严格的限制,根本意图是不让其真正的发展起来,只是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了扩大其对外战争的需要,因为战时日本扩大经济掠夺,急需技术人才,这才不得已于1939年前后,陆续增设若干高等学校。从而使高等学校从1937年的10所增加到1942年的20所。高等学校也实行“实务”教育,授课全用日语,在所谓“全寮主义”口号下,全部住校,以进行奴化训练。原来的师范学校改称师道学校,以培养具有所谓“新意识”的教师,并对原有教师进行“再训练”。职业学校主要是对国民学校或国民优级学校的部分毕业生进行2至3年的职业教育。③刘晶辉:《略论伪满洲国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显然,这种所谓的“新学制”完全是一种典型的殖民地学制,其典型特点便是学程短,程度低,其目的不是为了培养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而是为了培养皇国化的愚民和顺民,真正的用意是为了整体降低东北人民的文化素养和教育水平,让东北青少年儿童陷于愚昧无知的境地和状态,以利于日本殖民主义的统治和驱使。这种恶毒且卑鄙的教育手段的制定与实施,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实行殖民主义教育的严重罪行,是其侵略东北、奴役东北的重要手段与措施,标志着日本殖民者在东北建立的殖民主义教育体系的正式形成,是一种赤裸裸的法西斯化殖民性质的统治方式。①李倩:《日据吉林时期的文化专制与奴化教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伪满教育被纳入战争轨道,实施了战时体制。为了把伪满全部变成支撑侵略战争的战时劳动营,日伪强调所谓“国民之练成”,也就是从精神上、肉体上把东北人民折磨成为驯服的帝国主义战争奴隶。1943年4月1日,在设立伪军事部的同时,在伪民生部教育司的基础上,重新设立伪文教部。而新任伪文教部大臣是曾在关东州殖民学堂执过教的、素谙奴化教育的汉奸卢元善;实际上掌握伪文教部全权的次长,则是日本文部省专门派遣的天皇制“教育家”田中义男,曾任关东局教育部长,是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老手。同年10月,伪满政府专门设立一个文教审议会,名义上是由伪国务总理兼任会长,实际上掌控者完全是背后的日本人。所以其副会长由日籍总务厅长官和伪文教部大臣担任,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到会发表讲话,确立了战时体制下的教育方针是:明确建国本意,振兴坚定不移的国民精神,以贡献于战时下国家所需要的文教之振兴,将文教力量集结于大东亚战争的全胜上。这表明战时教育方针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推行“惟神之道”,把伪满洲国的一切都解释成“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庇,日本天皇之保佑”,以伪满洲国的“亲邦”地位,教唆东北的青少年学生,让其时刻与“宗主国”日本的步调保持一致,忘记国仇家恨,让其自觉地投身日本的对外战争行列,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置身于日本发动的“大东亚圣战”。②洪军、董辽:《伪满洲国的“惟神之道”》,《沈阳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二是教育必须为战争服务,“集结于大东亚哉争的全胜上”。根据这一方针,日伪当局推行所谓的“战时即应教育”,即根据战争的需要随心所欲地安排授业内容。尤其是伪满临近垮台的几年,由于侵略战争日益困窘,财力、物力、人力空前紧张,日伪政府便把学生驱赶出来参加各种“奉仕”劳役,还美其名曰“实习”,乃至终日停课,“支援圣战”。从1943年起,中、小学生每年都有一二个月或更多的时间,离开家庭被送到工厂或其他现场服劳役,高年级服劳时间尤其多。日本战败投降前夕,学生几乎天天都在服劳役。而且日本人监工和教师对学生非打即骂,使学生身心遭受摧残。以此为开端,实际上是将东北的青少年学生,变身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后备军和劳动服务的后勤补给者。同时,伪满政府又对各级学校实行兵营式管理和训练,各中等学校以上均配备现役军官充当军事教练,军事课和军训课列入必修课之中,成绩不及格者不予毕业。此时,还经常举行野营军训活动,或者拉进日伪兵营实行“入营制”,进行法西斯式的队列、射击、防空、隐蔽等军事训练,旨在“玉碎”关头,把青少年学生驱至前线卖命。
日本帝国主义在推行奴化教育的同时,又对各级学校的教师进行了“整肃”,逮捕和屠杀爱国教师,赶走籍属关内各省的教师。为了严防各级学校的学生和教师进行抗日活动,又派出大批日本人到各校掌握校政,监视师生的活动。因此,伪满时期的各级学校,经常处于恐怖的气氛中,无论教师和学生,随时都有被捕被杀的危险。伪满14年期间,已无从统计有多少爱国师生死在刽子手的屠刀和虐杀下,又有多少爱国师生遭受过迫害、毒刑和蹲监。日伪制造了多起逮捕案,其中有安东教育界大逮捕案、吉林教育界大逮捕案、通化教育界大逮捕案、沈阳教育界大逮捕案、对北满教育界爱国师生的迫害等,③车霁虹:《日本右翼宣扬“满洲国”是“王道乐土”之剖析》,《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3期。影响较大,涉及面较广。这些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教育界镇压和迫害的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