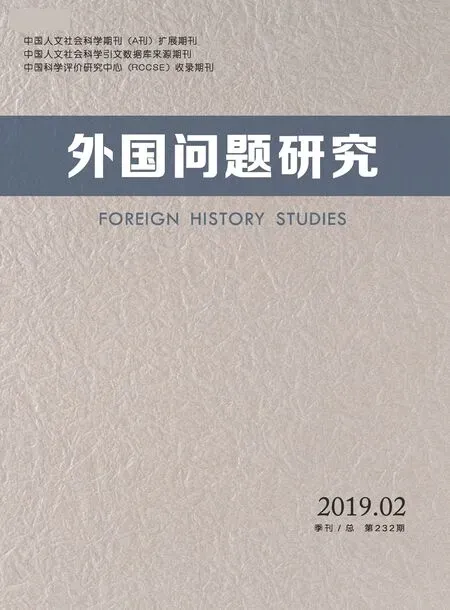日本在中东地区实施ODA政策的动因解析
2019-12-26江涛
江 涛
(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政府开发援助),最早为OECD(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提出的概念。日本在1947年通过的“和平宪法”第九条中明确申明完全放弃战争权利,也就放弃了以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的的权力。因此,日本政府将ODA作为其最为重要的外交政策手段加以使用。①外務省:《開発協力大綱の決定について》,2014 年,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1766.html。日本的对外援助始于1954年加入科伦坡计划,其后作为西方援助体系的一员积极参与了世界范围内的援助活动。通过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及之后的ODA实践,日本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援助、投资、贸易”三位一体的合作方式,成为了经济型援助的典型代表。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由非政府组织来实施开发援助有所不同,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决策和分配均由政府部门主导,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功利倾向。而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技术援助三部分构成了日本ODA的主体。
中东是世界上主要能源供应地之一,也是日本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地,2016年日本进口的原油约86%、天然气约24%均来自中东。②資源エネルギー庁:《資源外交の取り組みについて》,2018年5月,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enecho/shigen_nenryo/pdf/021_02_00.pdf。从地缘角度看,中东地区扼守连接亚欧的战略通道,是世界多种文明的交汇之地。中东地区对于日本的对外政策历来意义重大,安倍政府也将“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五大支柱之一。③外務省:《外交青書》,2018 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html/index.html,2018 年 8 月26日。日本在中东地区的ODA活动作为其对外战略政策最重要的实现手段,制定和实施的动因往往是内外动因要素之间动态变化的结果,而美国中东政策下的美日关系和日本的核心国家战略是内外动因的最为重要的要素。
(一)外在主要动因要素:美国中东战略框架下的美日同盟关系
20世纪50年代初生效的日美《旧金山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在获得法律意义独立的同时,又被捆绑进了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只能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至60年代,《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又被称为《新日美安保条约》)虽然适度松绑了对日本的限制但又在法律上明确了美国保护日本的义务。至此,日本只能完全依附于美国的庇护之下,把日美安保体制作为维系美日关系的核心,其外交策略也完全受制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区域战略。①冯瑞云:《论战后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东北亚论坛》1999年第2期。日本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虽然也企图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但其“日美同盟”中从属地位的身份使得日本必须首先要服从和配合美国的中东政策。
(二)内在主要动因要素: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与政治力量的整合
战后体制形成的对日本的“限制”,其反面就是日本对“限制”不懈地寻求突破。在完成了经济积累之后,成为“正常国家”、谋取更高国际地位,一直是日本核心的国家诉求。为达成这一诉求,除了在对外政策上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也必须首先不断对自身政治决策制度和政治力量体系进行整合。
二战后日本确立了西方议会式的代议机制,政党及其政治人物和官僚构成了政治决策中的最主要的行为体。1955年自民党成立后,开始了长达数十年(1955—1998年)的执政,形成了日本政坛的所谓“五五年体制”。自民党“一党优位制”下的长期执政,使得党派与官僚体系的深度结合、分工合作、共同参与政治运作。②李家成、郭忠厅:《日本政官关系发展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日本研究》2017年第4期。由于美国对日本进行政治顶层设计的初衷就是防止集权政府的再次出现,因此“小政府”在客观上也坐大了官僚机制,加上官僚具备优于政党及其政治人物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优势,使得日本政治运作过程形成了“官僚主导”模式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官僚在各自的行政系统内具有莫大的决策权。以日本的中东ODA政策来具体分析:60年代起,ODA资金作为国家财政支出预算中的单列项目由国会审核通过后,实施由外务省、大藏省、通商产业省及经济企划厅等政府机构来决定。特别是外务省,负责制定ODA合作领域的战略方向,在ODA的实施和资源分配方面掌握巨大的决策权。③蔡亮:《安倍内阁“积极和平主义”的三重特征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5期。这一体系保障了日本在首相更迭频繁、政局动荡的大背景下,国家对外政策实施具备相当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也使得ODA政策面对政治突发情况时往往调整迟缓、反馈滞后。因此,对于日本的ODA政策出台的内在动因进行分析时,仅仅从政党选举和政治家的立场主张的层面来分析是不够全面的。长期以来,日本政治决策过程中围绕“政治主导”还是“官僚主导”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政治博弈,总的趋势是由“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方向发展。④李家成、郭忠厅:《日本政官关系发展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日本研究》2017年第4期。
现有的对日本中东地区政策研究,大都将日本ODA视为实现能源安全保障而实施的手段,这一论断具有事实层面的缺陷,尤其是忽视海湾战争以来日本ODA实施手段的多样性与实施目的的复杂性。同时,都将日本的ODA决策机制简化为单一线性的整体来看待,尤其缺乏对日本ODA决策内部次要变因的相应考察和分析,也使得相关的论述显得单薄和片面。
日本政府将开发援助的发展历程归纳为了体制整理期(1954—1976年)、计划扩充期(1977—1991年)、政策理念充实期(1992—2002年)及时代应对期(2003至今)四个发展阶段。⑤外務省:《ODA50 年の成果と歩み》,2004 年、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pr/pub/pamph/pdfs/oda_50.pdf,2018年8月26日。本文则以日本的3份ODA大纲(1992年版、2003年版、2015年版)为节点,分析不同历史背景下日本在中东地区对外援助政策生成与实施的内外动机之间的动态关联性,进而解析日本对外政策及国家核心战略的发展变化脉络。
一、“和平主义”理念与经济利益寻求为主要目标的ODA政策(1954—1991年)
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完成了从煤炭到石油的能源转型,并且严重依赖中东石油。因为日本90%的中东进口石油都是购买自美国为首的西方石油跨国公司,与中东产油国并没有过多的交集,因此也比较忽视中东问题,在重大事件上只是简单地选择追随美国政策,几次中东战争中都是“亲以反阿”的立场。
1973年的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开展了“乞油”外交,在示好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也立即加大了对中东国家尤其是巴勒斯坦的援助,对比石油危机开始发酵的1973年和石油危机爆发之后1974年,日本对UNRWA(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与工程处)的援助额从1.1亿美元连翻数倍达到了5亿美元。之后对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提供了总额高达1400亿的日元贷款。①堀江正彦:《わが国のODAの基本態勢と中東地域援助の実体》,《中東研究》1997年第7期。此后的十年间对中东地区的ODA数额每年递增并在海湾战争前期达到峰值的27.297亿美元。②陈双飞:《发达国家经济援助的目标和实质》,《经济金融观察》2007年第9期。
日本在石油危机中的外交公关,表明此时对中东的战略处于无原则的状态,为了经济利益可以随时改变政治立场。石油危机期间的经济援助也成为日本在中东实施ODA的起点,而美国在石油危机的关键时刻没能给日本能源保障的承诺,也给日本上了深刻的一课,使其意识到了独立的中东政策的必要性。
石油危机后,日本开始从全球视角配置ODA资源,而中东的ODA的分配也相应调整,具体的实施更加有层次和侧重:不仅着眼于对重点石油输出国提供援助,也全面布局对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实施援助。日本根据中东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实际需求,对富裕产油国以技术援助为主;对收入高的非产油国提供低息贷款和技术援助;对不产油的低收入国家则既有有偿的低息贷款和技术援助还有无偿援助;对于贫穷的中东国家,日本考虑到对方的还款能力,主要提供无偿援助与技术援助。至20世纪90年代前,日本对中东提供的ODA中高达65%是有偿援助,而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分别为22%和13%。③J.A.Allan、Kaoru Sugihara:Japan and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London:Routledge,1993,p.105.同时,根据海湾国家的不同特点,日本不断丰富ODA援助的实施内涵,积极参与石油产业下游的制造工业,鼓励日本企业对海湾国家进行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在防止海洋污染、合作开发能源及治理沙漠等领域广泛援助,受到了海湾国家的积极评价。④中東経済研究所:《米ソの中東政策と日本の課題》,東京:総合研究開発機構,1990年,第3页。
应该说,能源安全是日本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却非唯一利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首相就阐述过能源安全只是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部分而非全部。冷战背景下苏联对阿富汗的武装入侵,伊朗革命及后续的两伊战争等事件使得中东政局更加动荡。此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全球范围内对峙较量,日本作为西方阵营中的盟友角色,配合美国赢得在中东地区的冷战胜利是比能源更为重要的战略利益。两伊战争也使日本意识到中东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充分利用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也能维持稳定的能源进口。更为关键的是作为战略盟友,在中东协助确立美国的主导地位,就可分享“美国治下的中东”红利。这就使得日本不再盲目笼络中东能源国家,即使在局部能源利益受到损害时,优先考虑的也是日美同盟关系下美国中东政策。
对于这一阶段日本ODA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应提及的是日本自身政治意识的觉醒。经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日本提高国家政治地位的意愿日益显现。ODA作为自身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地位的手段,其实施属性也渐渐从单纯追求商业利益转型为了越来越浓厚的政治意味。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不断扩大ODA规模,并于1989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援助国。从1990年到2004年,日本ODA累计总额占世界ODA总额的20%。这其中除了经济利益的考量,政治目的也变得越来越突出,日本将开发援助作为衡量对国际贡献的主要指标,来谋取相应的国际地位和身份。⑤朱艳圣:《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背后的战略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5期。在49届联大会议上,日本正式提交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申请,开始了谋取大国地位的“入常”漫漫历程。
纵观日本在海湾战争前的中东ODA政策,制定和实施基本恪守了“和平主义”的宪法准则,极力避免干涉受援国的内政、军事等政治问题,虽然援助的政治目的性在逐渐增强,但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还是主要方向。
二、后“和平主义”时期与政经并举的ODA实施调整(1991—2001年)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希望日本派兵直接参与海湾战争,然而此时日本的整体民意仍然坚持“和平主义”,国会中“反战”力量仍占多数,因此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其后日本提供的高达13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并未平息美国的不满,美国加大了对日本的政治打压。日本深知日美同盟是其国家安全的基础,在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体系”下,日本更是需要美国的保护。顺应新的政治形势,日本开始实施对ODA的战略调整。
1992年6月发布的日本新《ODA大纲》,阐释了如下基本原则:1.环保和开发相结合;2.ODA实施的非军事化;3.注意受援的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动向;4.注重引导受援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和导入市场经济机、保障基本人权和自由。①外務省:《旧? 政府開発援助大綱(1992年 6月閣議決定)》,1992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04_hakusho/ODA2004/html/honpen/hp203020000.htm,2018年8月26日。其中日本将极具政治色彩的“民主化”纳入了援助评价体系,是ODA政策战略转型的标志。海湾战争时期的外交失败使日本意识到单纯依靠经济手段进行政府援助开发的局限。并且因为自身的经济困局,不得不开始逐渐削减ODA规模。此外日本开始提出更加注重ODA的“质量”,而提高“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采取更加多元的实施策略,而受援国的政体民主性和人权状况,成为了甄别实施援助的重要判断标准。②外務省:《わが国の政府開発援助》,1993 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html.至此日本明确将ODA从经济手段转型为政治、战略手段进行使用。③大門毅:《平和構築論―開発援助の新戦略》,東京:勁草テキスト·セレクション,2007年,第46页。1996年通过的《PKO法案》为日本出兵海外扫除法律障碍,同年日本向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派遣自卫队参与了维和任务。虽然这是日本自卫队在“专守防卫”的原则下由联合国授权实施的维和行动,却标志着日本自卫队作为一支军事力量走出国门登上了世界舞台,为其“入常”打造声势,也为之后进一步军事化做了重要铺垫。
同一时期,不论是日本与沙特进行的卡夫吉油田的开发谈判破裂、还是放弃与伊朗进行了10年的IJPC项目,均体现了冷战后日本在中东利益谋取中价值判断的变化:不再将能源获得作为日本在中东的首要利益目标,更不会为了石油而无原则的向中东国家妥协。与之对照的,则是对美国中东战略的完全配合,不仅派兵参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更是为美国的“反恐战争”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援。这些均表明了日本完全没有独立于美国中东政策之外的有效外交手段。同时,日本内在的政治体制转变,掌权的“右倾化”政治势力也将实现“政治大国化”的梦想全部寄托在了美国身上。内外的动因变化最终促使日本中东能源战略越来越倚重西方来维系自身的能源安全。
日本中东ODA战略的调整,首先是因为90年代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和确认。1997年发表的《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下文简称为《新指针》),把两国间双边安全合作体制转型为了“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同盟关系。同盟的效力范围由“日本有事”扩大为“日本周边地区有事”,而“周边”的定义也扩大到整个亚太乃至波斯湾地区。日美同盟升级为了在世界广泛地区抑制区域冲突、协调应对共同威胁的战略安全协作体制。其后,日本国会通过了配合《新指针》的三个相关法案,为《新指针》的落实奠定了法理基础。《新指针》使得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也使日本能够名正言顺地以发挥“军事贡献”为名,积极实施自卫队的海外派遣,从而最终架空“和平宪法”,推动日本的“正常国家”化进程。④杨伯江:《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意味着什么》,《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6期。
这一时期关于日本ODA战略转型,还必须要提及的是随着“泡沫经济”负面作用的显现以及冷战后“美日同盟漂浮期”内日美在经济及政治问题上各种矛盾不断,日本从整体社会观念到传统政治结构均迎来了巨大的震荡。政党势力分化组合和强弱转换,以及国家政治决策结构的改革调整均直接影响了其国家战略的走势。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偏左政治力量尚可与保守政党抗衡,使得日本否决了直接派兵的决议。而在“改革派”联合政府的短暂执政时期,迫于美国政治压力以及国内“官僚”系统的掣肘,在政策制定上没能坚持自己本来的政治路线,反而导致了以社会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势力分化、瓦解,并在国会中彻底的边缘化,完全失去了对右翼政党的制衡作用。
90年代中后期,重新执政的自民党开始进行行政改革,强化政治人物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通过明确授予首相以提案权、废除政府委员会制、精简撤并官厅机构等措施,削弱了官僚与国会间的密切联系,强化了政党、政治人物在政治过程中的主导力量。自民党的行政改革使得“官僚主导”行政体制受到极大的削弱,“政党主导”的行政体制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①李家成、郭忠厅:《日本政官关系发展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日本研究》2017年第4期。1999年7月通过的《外务省设置法》,日本ODA结束了多年来的“四省厅”协作模式,同时外务省在ODA预算编制上的权限也被进一步限制,使得内阁成为了日本ODA决策与分配的完全核心。这是日本“令出多元”到“令出一元”的巨大转变,而“政治主导外交”的最大结果就使得日本ODA沦为政党意识形态的实施工具。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东ODA战略调整主要是为全力配合美国的“双重遏制战略”。ODA政策的实施重点仍是经济利益为主的原则,坚持了“不介入内政”的ODA理念。②長谷川雄一:《日本外交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東京:南窓社,2004年,第104页。但是随着国际上人权高于主权的“介入正当化”理念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这一论调也开始为日本所用,成为其提高政治地位诉求的外在伦理依据,并成为21世纪到来以后日本ODA战略转型的推动力。同一时期,随着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10年经济停滞,日本不再追求援助规模的扩大,仅在1997年日本就将ODA的预算削减了30%,此后更是不断缩小ODA的资金规模。同时,ODA的实施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更多的表现为了与政治、军事手段的共同运用。这一特征在接下来的21世纪初表现地更加鲜明。
三、“和平构筑”和ODA与军事行动的绑定(2001—2011年)
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对阿富汗及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都援引了“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着力强调其维护“民主·人权”的行为正当性。这给了日本当政者以相当的启示,从中提取并充实进了“和平构筑”的战略理念。同时由于日本长期的经济停滞,ODA的调整成为了必然。而“反恐”这一契机使得日本的军事力量得以“借船出海”,与ODA深度整合为新时期日本对外政策的标志性手段。
2001年“9·11”发生后,日本汲取了“海湾战争”的教训,及时主动地参与了美国的军事行动。日本国会也是全力响应,通过了《反恐特别措施法》等一系列法案,为小泉内阁的自卫队海外派遣铺平了道路。在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开始之后,日本虽然受“和平宪法”的制约无法直接参与,也是尽可能的承担了后勤补给与情报收集等任务。而在战后,日本主要与联合国一起主导“DDR”工作,实施了对阿富汗旧军人的武装解除与复员工作。同时对阿富汗实施了多种形式的援助,帮助其尽快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保障人民生产生活水平。③杉勇司、篠田英朗、瀬谷ルミ子、山根達郎:《アフガニスタンにおけるDDRその全体像の考察》,《HIPEC研究報告シリーズ》2006年1期。伊拉克战后的重建任务,日本提供了总额为5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的15亿美元为无偿的紧急援助,旨在建设伊拉克境内的基础设施,恢复民生。剩下的35亿美元是有偿贷款,援助伊拉克的中长期战后恢复。④ICA:《国際協力事業団年報》,2012 年,https://www.jica.go.jp/about/report/index.html。鉴于部分中东国家遭受严重的战争破坏已经威胁到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日本将ODA具体实施目标聚焦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恢复,给水项目及人才培训等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然而令世人瞩目的还是日本自卫队被派遣至伊拉克南部萨玛沃市参与了战后援建行动,这毫无疑问是违反日本“宪法九条”的行为,在实质上突破了有关日本集体自卫权的限制。但是,日本政府辩解为参与伊拉克的“复兴支援”的战后重建工作并非作战任务。
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援助主体的出现及区域外大国对中东国家的政治影响力的逐渐增强,日本单纯仰仗美国势力试图在中东地区发挥影响的外交方式进一步被弱化。①程蕴:《安倍内阁的中东外交:战略、地区秩序与困局》,《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日本为保障能源供给,在积极参与构建政治秩序的同时又重新着力强化与能源国家的经济联系。2006年,日本先后与卡塔尔、阿联酋等GCC成员国建立政府间经济联合委员会。2009年1月,与伊拉克签署了《日伊构建全面伙伴关系的宣言》,通过技术支援等手段换取伊拉克的能源供给承诺。
在中东秩序的构建方式上,日本政府一直试图通过接触合作的方式引导中东地区的“反美政权”接受美国控制下的和平。以此,2003年小泉内阁将“伊拉克人道主义复兴援助;中东和平问题;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对话”定义为了中东政策的“三支柱”。日本对伊朗和叙利亚等国都保持了接触,试图在中东地区构建独立于美国之外的影响力。小泉在2006年提出了“和平与繁荣走廊”倡议,利用日本提供的ODA,与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建立四方合作机制。首次执政的安倍内阁和其后的麻生内阁,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思考日本的中东政策,试图提升日本切入中东事务的外交实力。然而,这些不切实际的战略设想随着中东政治进一步的“碎片化”最终都是无疾而终,也证明离开了美国的主导,日本在中东缺乏单独推行其价值观的能力。
2003年出台的新版ODA大纲,“和平构筑”取代了传统的“开发援助”概念。其中重点提及了“人的安全保障”与“和平的构筑”,尤其强调“人”而非“钱”的贡献。日本将“和平构筑”的理念与ODA政策结合在一起,强调ODA的开展要以民主化、导入市场经济、维护基本人权为实现目标。同时,这也是假借ODA之名,为日本自卫队参与海外行动寻求合法性,标志着日本的ODA政策向经济·军事并重的重大转型。②外務省:《ODA 白書》,2003 年3 月19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html。
通过参与战后阿富汗与伊拉克重建的实践,日本政府进一步完善了“和平构筑”的内涵,在2005年的《ODA中期政策》中明确了自卫队在“和平构筑”中的地位,即自卫队与ODA是“车的两轮”,两者都是日本对外援助中的重要手段,共同运用,不可偏废,二者均是日本外交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一环。③外務省:《政府開発援助に関する中期政策》,2005年 2月 4日,https://www.fasid.or.jp/_files/library/kaigou/handout43_1.pdf,2018 年8 月26 日。至此ODA完全成为了日本寻求军事化正当性的手段。
日本参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给了自卫队出兵海外的契机,也使得日本借机完善了自卫队派遣的法理构建。2004年日本对伊拉克的自卫队派遣,并不是联合国授权的适用《PKO行动法》的维和行动,而是依据临时国内法案的军事行动。这使得日本政府可以在今后的类似状况下作为既成案例援引,成为对外军事行动的法理依据。
2003年后,日本的“小选区制”已经确立,这一制度的实施彻底改变了日本的政党格局。左派政治势力和小党派完全被边缘化。在经过数次选举和政党重组后,最终出现了“两大保守政党一朝一野”的局面,政治路线的争执也变成了“保守偏右”VS“保守中道”的论战。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日本国内的主要政治力量趋向一致,在对外政策上也很容易形成共识。出兵伊拉克决议的通过在90年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时,不论是民主党执政时期还是自民党重新执政时期,国内行政改革的方向都是坚持继续强化政党及其政治人物在政治运作过程的主导地位与作用,确立“政治主导”的原则的绝对性。这使得官僚系统的权利被不断削弱,首相及内阁的权利不断强化。这些都为安倍第二次上台后实现政治集权铺平了道路。
四、“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和ODA的彻底政治、军事化(2011年至今)
2011年“阿拉伯之春”浪潮席卷整个中东地区,打破传统的社会格局的同时,也使多个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内战与动荡。埃及的政局动荡、叙利亚危机、“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势力的泛滥、中东国家内部的战略竞争和地区博弈,都反映地区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由于自身国力下降,在中东地区采取了收缩战略。此时的日本被要求加大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力度,以填补美国在中东留下的权力真空。除确保日本的能源安全供应外,安倍政府也意图通过更深度地参与中东事务来推行其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理念。
为此,安倍在第二次组阁后连续三次出访中东国家,提出日本要与海湾国家建立“面向安定与繁荣的全面伙伴关系”,增加对中东国家的反恐援助,并提出所谓“中庸最善”的主张。2016年5月的G7峰会上,日本等G7成员国共同出台了《关于反对恐怖主义及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计划》,加强国际反恐协助。2017年9月举办的首次“日本—阿拉伯国家政治对话”,安倍明确将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列入了日本外交“五大支柱”。①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8》,2018 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html/index.html,2018 年 8月26日。日本除积极参与了叙利亚、伊拉克等国难民救助工作,协助联合国难民署对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及生活条件保障之外,也对难民接收国如土耳其等国提供了相当的援助。对于“阿拉伯之春”事件中心的突尼斯和埃及等国家,日本援助的重点放在了民生,教育,医疗,基础建设,人才培训等传统的ODA领域外,还将援助范围延伸到了此前很少涉及的受援国政治改革层面,更是将“选举支援”列为重点,积极指导受援国学习选举制度培训选举人员、熟悉选举运营,并对选举过程进行了相应的监督,以此来帮助中东国家的“民主转型”。②JICA:《国際協力事業団年報》,2011 年,https://www.jica.go.jp/about/report/index.html。
“官民一体”是日本为加速援助成果转化,加快援助效率,及解决官方层面资金短缺等问题而在近年来积极鼓励的一项政策。日本政府2011年1月通过的《新成长战略》中,希望日本企业参与埃及苏伊士运河的扩建工程;后来针对沙特的技术援助要求时,也强调要通过“官民一体”的援助方式来对接沙特的“2030愿景”。③外務省:《民間企業による官民連携案件の提案の受付について》,2008年,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072740.pdf,2018年8月27日。
2013年底,安倍内阁通过了日本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文件,明确提出在“积极和平主义”的前提下,战略性地利用ODA。2015年2月日本政府发布了新版《开发合作大纲》,“合作”取代了之前的“援助”。新ODA大纲首次允许为其他国家军队提供“非军事目的”援助,突破了日本60多年来未对军队提供过援助的先例。④刘云:《日本新ODA大纲与安全保障》,《国际研究参考》2015年第4期。这被认为是日本ODA政策的重大转变。修改ODA大纲与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并称为安倍内阁安全保障领域的“三支箭”。在《开发合作大纲》发布一周后,日本发布了“反恐”政策三大原则,其中就强调了通过建设性援助防止产生极端主义,日本ODA的“反恐”内涵由此确定。
2013年11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创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法案,进一步巩固和加强首相官邸在外交及防务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安倍内阁的各项政治改革使得日本的“政官”关系呈现“首相官邸主导、政官合作、政府高行政低”的特征,这使得首相权力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均得到极大的强化。⑤李家成、郭忠厅:《日本政官关系发展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日本研究》2017年第4期。政治过程中的“首相官邸主导”的政治模式已然成型。政治决策的权力更多的掌握在以内阁为首的行政机关手中,完全打破了战后“小政府”体制,转型为了行政集权制式民主。
2015年6月通过的《防卫省设置修订法》,正式废除日本战后长期实施的“文官统领”制度。从实际上解除了文职官员对军职官员的权力制约,确立了军职官员在自卫队行动的主导核心。而《新安保法案》的通过,正式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也使日本对美国支援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①松竹伸幸:《集団的自衛権の深層》,東京:平凡社,2013年,第20頁。意味着自卫队在事实上成为了具备战斗部队资格的准军队。标志着日本对于战后“和平宪法”的完全背弃。表明了日本安全政策和防卫力量建设越来越具有外向性、主动性和攻击性特点。②储召锋:《安倍内阁安全防卫政策评析—以日本三份安全政策文件为中心》,《日本研究》2014年第1期。
截止2014年,日本ODA数额下降为世界第四位,下降的同时则是在对外军事领域寻求不断突破。战略层面的日本中东外交政策作为构筑日本走向世界性大国的战略依托,在ODA实施的经济意味越来越淡化,而意识形态色彩却日趋浓厚,对于受援国内政的干涉度也越来越高。
结 语
日本的中东ODA政策从无到有,从经济利益为重到政治军事目的为主的发展路径,是对战后“和平主义”理念背弃的过程,其援助理论的发展越来越追求西方式的“民主化”和意识形态化,同时不断增加的附加条件使得援助的政治意味更加强烈。日本在中东的核心战略目标始终都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而是维护由美国霸权所构筑的中东秩序,从而使自己能够分享日美同盟关系下的盟友“红利”。
ODA政策作为一项外交手段是国家核心战略的外延和体现。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正常国家”、恢复“大国地位”是长久以来日本的核心政治目标。也是日本对中东援助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与“军事化”的根本原因。日本在中东ODA的数次战略调整,其外在动因的变化体现了“美日同盟”关系内美国出于了自身利益和政治需求,不断地打破战后体制为日本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松绑过程。美日同盟关系决定了日本必须接受美国的军事保护,无法实现对美关系的绝对平等。但日本通过逐渐增大自己在全球性范围内经济、政治、军事领域的影响力,来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承担更多责任;而美国则对日本谋取政治大国的行动予以支持,给日本更加平等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③苗华寿:《美日关系回顾与展望》,《和平与发展》2005年第5期。而日本在中东ODA的实施,其内在本质正是体现了这一利益交换过程。
中东ODA实施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因在根源上同样也是为摆脱战后体制这一核心政治目标而进行的内部调适。二战之后日本“和平国家”的角色设定不仅根植于坚守“和平主义”的民意土壤,更是建立在“和平宪法”的法理框架和行政体制对于集权政治制约的顶层设计之上的。因此所谓ODA战略调整的决策过程:其一体现在了选举机制下,右翼政治势力不断坐大、左翼中间政治势力不断式微衰弱,进而以各种中间法案在法理上不断架空“和平宪法”的核心内涵;其二体现在了以行政改革的方式,不断打碎“官僚主导”的行政体系,确立政党及政治家的决策优位,在整合国家行政系统的同时实现政策执行的“扁平化”,从而形成“行政集权制式民主”制度。
作为战后日本外交的最重要实施手段,ODA(官方开发援助)为提升日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将其经济能力转化为政治外交实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援助、投资、贸易”三位一体的经济型国家援助理念,从评估到实施的一系列严谨务实的对外援助制度及援助评价体系,对我国实施对外援助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