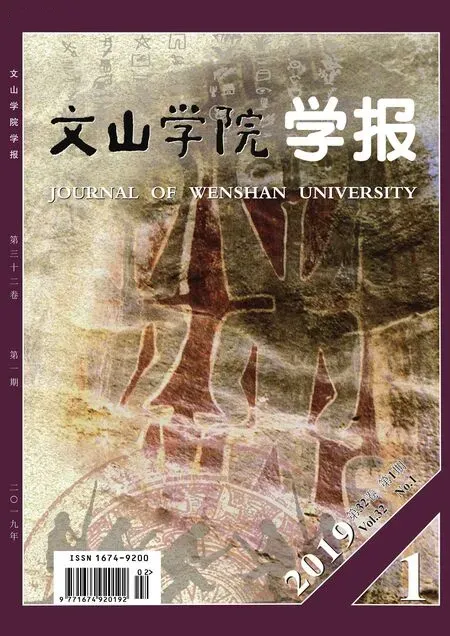托尔斯泰死亡书写的一致性与升华
——以《三死》与《伊万·伊利奇之死》为例
2019-12-26聂思沁
聂思沁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一、托尔斯泰与死亡的书写
死亡是每个人必然会遭遇但终其一生只有一次经历机会的体验,这一矛盾形成人类的生存困境。托尔斯泰则把这一人类生存困境化成对死亡和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在1876年2月21日的信中,他写道:“生活中除了死亡之外,没有任何东西。”[1]在1883年的《我的信仰是什么?》一文中,他则提到:生与死对他而言不再是坏事,他体验到了生的幸福、快乐;在1887年著名的《论生命》中,他则更是直接点明:死亡不可避免,爱让人超越死亡,获得生命的意义……实际上,这一思考又与其对死亡的书写密不可分。托尔斯泰在其小说创作中形成了丰富的死亡书写:《三死》中贵妇人、老马车夫和树之间不同的死亡,《战争与和平》中安德列公爵静穆、庄严的死亡,《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卧轨之死、列文哥哥的恐惧之死,《伊万·伊利奇》中伊万·伊利奇孤独、痛苦的死亡等等。托尔斯泰对死亡的直视和虔诚的书写,常被描述为:“以纯洁的灵魂面对死亡”[2]。
在《生活之路》这部充满哲理性的随笔集中,托尔斯泰则直接表明:“铭记死亡将有助于灵魂的生活”[3]。对托尔斯泰来说:清楚死亡的状态能够帮助人明白生命的价值,才能逼迫人进行有意义的灵魂活动;反之,如果忘记死亡的事实,人的生存则会因此黯然失色、浑浑噩噩、一无所获。在托尔斯泰众多的小说中,《三死》和《伊万·伊利奇之死》是托尔斯泰直接以“死”命名,创作出来的关于死亡的书写和沉思,较好地代表了托尔斯泰对于死亡的清醒意识与智慧。
虽然很多评论家对于《三死》和《伊万·伊利奇之死》都十分赞赏,但是他们对《三死》与《伊万·伊利奇之死》之间包含的托尔斯泰死亡沉思的一致性往往忽视或视而不见。实际上,《三死》与《伊万·伊利奇之死》都贯穿了托尔斯泰的博爱思想和生命不朽思想。早期创作的《三死》,主要描写了两个人物的死亡(形成对比)与一颗树的死亡(形成象征),已经大概展示了托尔斯泰的死亡哲学核心——博爱的人生是幸福的,博爱让人生命不朽。托尔斯泰在晚期的《伊万·伊利奇之死》中,继续实践着这一哲学思考,他让饱受临死痛苦的伊万·伊利奇获得了“爱”的智慧,并且通过对伊万·伊利奇临死前的所做所为、所见所感的详细心理书写——对死亡的恐惧、对生理病痛的害怕、对过去生活的重新反思,以及“众人皆醉我独醒”下对周围亲友的观察,暴露了芸芸众生在日常教育下,遮蔽死亡的各种缺陷,如麻木、平庸、脆弱等等。可以说,相较于《三死》的短小、急促、扁平的表现,《伊万·伊利奇之死》融入了托尔斯泰几近一生的丰富生活历练和思考,呈现出了更加包罗万象的丰富性。
二、《三死》:“爱他人”和生命不朽
《三死》的主要构成是三个生命的死去,一个是早已病入膏肓的贵妇人,她面黄肌瘦、焦躁不安,十分恐惧、害怕死亡,一直在心里幻想着能够在生命逝去之前,扼住命运的咽喉,为此,在严寒的冬天里,她一意孤行地逼迫丈夫送自己去国外进行疗养。一路上贵妇人因羡慕具有健康气息的女仆、丈夫、大夫而怨天尤人,因不满丈夫对自己的病情漠不关心而怒气冲冲,尽管丈夫对自己已经几近百依百顺。贵妇人甚至直到临死之前仍指责自己的丈夫没有去请神父说的神医女郎中来看病。发现表姐吻她的手,她还生气地指责道“不,吻这儿,只有吻死人才吻手。”[4]157另一个是躺在驿站火炕上,病到已经行动不便了的老马车夫赫韦多尔因自己占着火炕的位置,害得大家没有床位而于心不忍、羞愧难当:“纳斯塔西娅,你别生我的气,”[4]152“我很快就会把这地儿给你腾出来的。”[4]152在临死之际应年轻马车夫谢廖加的请求,还把自己的新靴子送给他,条件只是:希望在自己死后谢廖加能够给自己立块墓碑。最后一个是一棵树,本来谢廖加已经忘记了对老马车夫的允诺,但是周围的农民不断提醒他要恪守诺言。因此,一天谢廖加来到森林,砍倒一棵树,将把这棵树做成十字架墓碑立在马车夫的坟头。
表面上,这篇小说故事叙述简单、结构明了,但是小说字里行间又构成一种极微妙的张力,小说中最突显的便是三处人物的死亡书写,并且十分巧合地分别对应着贵妇人、马车夫、树的死亡,形成了一种深层的隐喻结构与象征意味,由此可见托尔斯泰的匠心独运。
第一处是在第三节的最后,小说写贵妇人在听着神父庄严肃穆的念经声中死去,紧接着便出现一段叙述者的疑问:“但是,即使现在,她是否真的懂得这些伟大的诗句呢?”[4]157
而后,第二处出现在第四节开头,小说这样写道:“过了一个月,在那位死者的坟墓上,建起了一座石砌的小教堂。马车夫的坟头仍旧没有石碑,坟头上,只有绿油油的小草破土而出,这座坟头乃是一个人曾经存在过的唯一标志。”[4]157
这两处,第三节的最后很明显是作者在质疑、否定贵妇人听懂了《圣经》;第四节的开头则很明显能发现托尔斯泰设置了巧妙的对比——贵妇人坟头上虽然建有教堂,但是并不算其存在的标志,老马车夫就算坟头没有正式的墓碑,坟头只是长了些小草,却被托尔斯泰肯定这是马车夫曾经存在的标志。一个人存在的标志,亦即你以前是否存在过?判断你存在与否也就是看你的存在有意义与否。如果一个人被认定没有存在过,那么他过去的人生也就没有意义。因此结合这两处对比的内容和结构,可以清晰感受到小说人物背后暗含的托尔斯泰的评价:贵妇人的人生没有意义,老马车夫的存在是有意义的。那么,老车夫的人生意义为何会被肯定而贵妇人的被否定?为何否定贵妇人之死的时候常常伴随的是与基督教相关的意象?为何用“唯一标志”——小草,来肯定老马车夫的死亡呢?
第三处,在小说最后,年轻的马车夫谢廖加到森林里砍树,为老马车夫做墓碑。小说连续出现大段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谢廖加砍完树,自然本应是悲戚的、哀悼的,至少不至于是欢乐的。可是小说一反往常,使用了“陌生化”笔法,自然在这里呈现一片生机盎然的场景:“鸟儿在密林里扑腾,仿佛在窃窃私语,在诉说自己的幸福;苍翠欲滴的树叶在高处快乐而又平静地低声絮语,而那些活着的树的枝叶,则在那棵倒下的死树上慢慢地、庄严地迎风摇曳。”[4]159并且,值得一提的是,为给老马车夫做墓碑而被砍倒的树与长在老马车夫坟头的草都属于植物,植物春去冬来,虽然会枯萎、凋零,但是一年一度春回大地之时,总是能够重新焕发活力,生机勃勃。那么植物与老车夫之间的死是否有某种关联呢?
托尔斯泰于创作当年所写的一封解释其写作题旨的信,对上面四个问题给出了部分解答。托尔斯泰在信里写到:“三个生物死去了——一个贵妇人、一个农民和一株树。贵妇人既可怜又可厌,因为她一辈子撒谎。她所理解的基督教并不能解决生与死的问题。那个农民死得很安静,就因为他不是基督教徒。他的宗教是终生与之作伴的大自然……,是他跟整个世界和谐相处的,不像那个贵妇人,她跟整个世界是凿枘不和的。那株树死得安静、诚实、漂亮。因为它既不撒谎,也不做作,既不害怕,也不惋叹。”[5]67托尔斯泰在信中谈论了自己对三种死亡的价值判断,在判断中也表达了自己对信仰、死亡、人生意义的思考。正如上面已经证明的那样,在信中托尔斯泰否定了贵妇人的死亡,肯定了老马车夫的死亡。进一步地来说,托尔斯泰在信中批评了贵妇人所信仰的“基督教”,而对老马车夫所亲近的大自然以及树所代表的大自然表达了赞赏。因此要解决上面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和自然观。
纵观托尔斯泰的一生,很容易发现,托尔斯泰虽然很小就接受了基督教教育,但是他本人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持有清醒的批判态度。托尔斯泰从十六岁起就不再去教堂做礼拜,21岁起就自称“虚无主义者”[6],到1855年他宣称自己要建立一种符合人类发展的新宗教,这种新宗教“是剔除了盲目的信仰和神秘性的基督的宗教,是不应许来生幸福,却赐予现世幸福的实践的宗教”[7],并认为这项任务任重道远,必须穷尽一生去完成。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基督教思想,而且对于托尔斯泰而言,没有什么现世救赎、来世复活,没有什么上帝拯救,任何一种宣扬救赎与仪轨拯救的学说,都是与生命的意义脱节的。具体来看托尔斯泰的“基督的宗教”,用罗曼·罗兰赞赏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时代的宗教意识就是通过人类博爱来实现幸福”[8],即博爱思想。因此可以理解,《三死》中的贵妇人,她临死前见到教堂,只是出于仪轨救赎心态,画十字祈求,那么在托尔斯泰看来她便只是一个依靠宗教仪轨救赎的基督徒,并没有领悟到信仰的核心、生命的真谛,故她恐惧、焦躁地死去,她的死亡被否定、被与基督教意象伴随。与之相对比的老马车夫,死前尽管身体痛苦万分,但是老马车夫临死前仍是替他人着想:为自己占据他人的火炕之位而不好意思,见青年马车夫谢廖加没有马靴,把自己的新马靴送给了他。老马车夫真诚地奉行托尔斯泰信仰的“爱他人”的思想,故老马车夫死前十分安详、宁静,他的死亡、人生意义受到托尔斯泰的肯定。
进一步了解托尔斯泰的自然观。托尔斯泰作为一位以描写大自然而受世人称道的作家,有着其独特的自然观。整体而言,托尔斯泰笔下的自然拥有着一种善和美的品质。就如他在自己的读书随笔中表明的那样:大自然“始终向我们展示着我们所寻求和期望的真善美”[9]。另外,同样是在托尔斯泰谈这篇小说创作意图的信里,托尔斯泰谈到:“昨天我去了买下来的林子,现在我正在采伐它。在那里白桦树正在发芽,夜莺巢居其间。它们谁也不知道,现在它们是公家的,还是我个人的,对正在砍伐这件事情它们也漠然置之。树被砍伐光了,还会长出来,至于谁砍伐它们并不想知道。”[5]69从中,我们看出托尔斯泰在树的身上寄寓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法则,树的生命能够超越时空的存在。小说中,树被用来做老马车夫的墓碑,树与老马车夫的死亡都有一种泰然。于此,显而易见,通过树、小草为代表的自然的描写,托尔斯泰意在给予老马车夫的生命同自然一样的性质,即老马车夫是善的、美的,他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他的有意义的生命也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亦即博爱的生命可以永垂不朽。“唯一标志”亦可以看出是托尔斯泰寄予的生命超越之美。
三、《伊万·伊利奇之死》:生命本真的揭示、“爱他人”和生命不朽
《伊万·伊利奇之死》是托尔斯泰的晚期之作,主要描写了俄罗斯贵族伊万·伊利奇从生病到死亡的遭遇与心灵历程。正是这一死亡心路历程的详细描绘,让《伊万·伊利奇之死》在《三死》的基础上,拥有了更具丰富意味的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揭示。这里的本真,既是指日常生活中人们遮蔽死亡的生存状态,又是指人类生命必然及死的事实。小说共分为十二节,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三部分,分别是:伊万·伊利奇跟随周围环境成长、渐渐丧失生命本真;伊万·伊利奇突然生病,开始痛苦地明白死亡事实,孤独地观察周围人的麻木生存状态,清醒地审视自己过去“不对头”的生活;伊万·伊利奇在死前见到朴实善良的农民格拉西姆,获得儿子的一吻,感觉到爱,明白“爱”对于人生的意义。整部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等腰三角形的构架,两等腰交汇的顶点则是伊万·伊利奇突如其来的生病,两腰与三角形底边相交的两个点则分别是伊万·伊利奇因生病而体验领悟的真理:生命本真状态与博爱思想。
伊万·伊利奇不是什么圣人,也不是心狠手辣的坏人,只不过是俄国最普通的一名贵族,或者说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常人,一个被平常生活遮蔽了自我的普通人。他本来出身良好、性情温和、彬彬有礼,公事上公正无私,只是一路的为官生活与贵族交际,让他渐渐丧失身上的自我气质,顺从自己生活圈的生活状态,亦步亦趋地学习上流社会身居高位的人的行为方式生活。他开始好色玩弄权术,是因为这在他的圈层的人们那里并不认为是不好的,他之所以娶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乃是因为那些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伊万·伊利奇总是不知不觉地被外界所同化,从上流社会的生活来领会自己的生存,名义上是自己在生存,实际上变成异己在生存,自己只不过是他人的影子,因为生活方式恰恰涉及到的就是人如何活着的问题,海德格尔曾就指出“Authenticity is not so much a matter of the ‘content’ of a life as it is the ‘style’with which one lives.”[10](本真不是生活内容的问题,而是关于人生活方式的问题。)因此,伊万·伊利奇唯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马首是瞻,丧失自己的存在,必然导致他离生命最该有的“本真”越来越远。但是托尔斯泰给与了伊万·伊利奇一次与众不同的体验,让他原本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获得了原来绝不可能体会的生命哲学。
这些改变源自于伊万·伊利奇的一场生病。伊万·伊利奇面临生病带来的生理痛苦和死亡可能,且这痛苦和死亡仅仅是他所独享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并不在本然的意义上经历他人的死亡过程,我们最多不过是‘在侧’”[11]。伊万·伊利奇去看医生,他只想从医生那里知道他自己病情的危险性,而医生却永远只是告诉他病情,这让伊万·伊利奇自己心里模糊感觉:心情沉重,情况不妙,自己可能在面临生死问题。但是医生,也许还有所有的人都对此感到无所谓。而这一担忧的确如他所料。回到家,妻子并不耐心听他一五一十地讲述病情。在他生病期间,妻子仍热衷外出拜访,对他的生病也表示出一种漠视和指责。而同事对他表现出的是一种想让他让位的态度,并将他排斥出他最爱的文特牌局。可以说伊万·伊利奇在医生、家庭与社交上的被拒绝,让伊万·伊利奇感到旁人并不理解他的生病与痛苦,他隐约地尝到了和体悟到了“个体死亡的不可通约性与不可‘代理性’”[12]。
由个体死亡的不可通约性,伊万·伊利奇感觉到痛苦与孤独,也因此加深了他对死亡的认识,他的死亡意识由模糊变成了清晰。内兄来访,对伊万·伊利奇的憔悴面容反应奇怪,以及内兄与妻子谈论“他已经是死人了”[4]116,让伊万·伊利奇受到打击,同时这一旁人的眼光刺透他的疼痛,让他明白自己在经历的不是盲肠的问题,不是肾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问题。随后他进一步地反思日常教育中的死亡三段论。但反思的结果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伊万·伊利奇会死才是最真实的。但毕竟过去生活对于死亡的遮盖性太强,因此即使在伊万·伊利奇探到了死亡的事实后,他还是苦苦挣扎、回避,而越是挣扎、回避,生理上的痛苦越加难受,越发地把他拉回现实来面对死亡事实,这也是这部小说中为何出现了许多“黑洞”和“光明”意象的原因。
可能托尔斯泰也可怜这个普通但又可怜的平常人,之后托尔斯泰安排了善良、朴实的农民——格拉西姆,出现在伊万·伊利奇面前。格拉西姆出身低微,作为仆人的他很清楚每个人都是要死的,他细心、真诚、无怨无悔地照顾伊万·伊利奇,这让伊万·伊利奇认为,只有农民格拉西姆才明白他的处境,同时在死亡意识的逼迫下,伊万·伊利奇更加痛苦地看穿周围虚伪的一切和自己过去的一切。他感到最受不了的就是虚伪——周边的亲友明明知道他要死了,却一再安慰他只要安心治病,就会好起来;伊万·伊利奇痛苦地反感大家都在说谎,都在掩盖生死问题。他逐一地检查人生,他回忆起儿童时的美好,回忆起儿童之后快乐消失的成长历程,他发现:生命刚开始的时候有点亮光,后来越来越暗,越来越迅速。他又进一步开始反思:生活到底哪里不对头?他的人生到底哪里错了?他发现:过去的生活乃是按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认为是对的方式生活,过去的生活都不对头。他仔细观察妻子、女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他们身上,伊万·伊利奇发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由此他明白“这一切乃是一个掩盖了生与死的可怕的大骗局”[4]141。可以说,伊万·伊利奇在发现自己面临死亡、明白生命必然及死的基础上,探到了日常生活中人们掩盖死亡、逃避死亡的事实。死亡对伊万·伊利奇敞开了生命本真的存在,同时,生命本真的存在也藉由《伊万·伊利奇之死》向读者敞开。但讽刺的是,这一事实、这一骗局在伊万·伊利奇死后的其众友身上,依然是“风雨不动安如山”般的存在——同事、好友听到伊万·伊利奇死讯,首先想到的就是伊万·伊利奇之死能够给他们带来的职位升迁与变化。其次,庆幸死的只是伊万·伊利奇而不是他们,他的死只是个例外,这种例外绝对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最后,一切照旧如故,伊万·伊利奇的死绝不会阻碍他们打文特的规矩。实际上,小说开头的描写与小说后面伊万·伊利奇的感悟,两者间构成了强烈的补充与讽刺,众生“遮蔽死亡”的揭露因此更入木三分,生命本真的敞开因此更彻底。
生命本真向明白生死之谜的伊万·伊利奇敞开,可是伊万·伊里奇并不能立即直视他一生都错了的事实,并且在托尔斯泰眼里,伊万·伊利奇仍没有寻找到人生意义的钥匙:伊万·伊利奇为自己开脱,认定自己的一生乃是正大光明的。于是托尔斯泰惩罚着在他看来并未完全苏醒的伊万·伊利奇,让伊万·伊利奇饱尝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生理痛苦,“他感到他的痛苦在于,他正在钻进那个漆黑的洞穴,而更痛苦的则是那个洞他钻不进去。”[4]142并让伊万·伊利奇明白让他痛苦不堪的就是:“他认定他的一生是正大光明的”[4]142。伊万·伊利奇因此不得不去质疑自己以往的人生。在这里,伊万·伊利奇犹如《忏悔录》中的托尔斯泰,开始真正审视自己过去生活的意义,伊万·伊利奇成为了托尔斯泰人生意义思想的化身。最后,伊万·伊利奇醒悟:原来自己的一生都是错的,但还来得及拯救——宽恕他人。不使别人痛苦,自己也就摆脱了痛苦,宽恕的一瞬间让生命的意义豁然开朗,死也因此再也没有死。显而易见,伊万·伊利奇找的这种宽恕他人、为他人而不为己的思想,实际上就是“爱他人”的思想,亦即博爱思想。另外,生命的意义固定不变,没有死,其实也就是一种超越死亡的表达、人生意义永恒的表达。如此看来,《伊万·伊利奇之死》的博爱思想、生命不朽的思想与《三死》中的没有什么区别,可以说几乎如出一辙,托尔斯泰关于死亡的沉思有着一脉相承性。
四、结语
从《三死》到《伊万·伊利奇之死》,托尔斯泰的死亡书写,并没有如有的学者所言:晚期的创作就必然会叛离早期的创作——“托尔斯泰从惧怕死亡、逃避死亡、对死亡充满了困惑到后来用爱来驱赶死亡的阴影、获得幸福的生命观的转变”。[13]相反,托尔斯泰的死亡书写一直存在着一致性。于死亡书写中一直都融入了他的“爱他人”思想,即博爱思想,以及生命不朽的思想。并且随着托尔斯泰自身的成长与人生经历的丰盈,其死亡书写呈现出精彩的升华,达到对日常人们普遍生存境遇揭示的丰富意义,并明确向人们阐明:失去了死亡意识的人生是可怕的,没有了死亡思考的人生是扁平的,思考死亡也就是思考生存,思考死亡也就是思考人生的意义。换成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向死而生”。这是这部小说超越《三死》的伟大部分,也是许多研究者提出《伊万·伊利奇之死》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相契合的重要原因。
托尔斯泰在他的死亡书写中,一直都在正视死亡、探索死亡哲学、追寻人生意义。相比之下,现代人何尝不知道人终一死,现代人又何尝不明白:“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可现代人极少有人去认真思考死亡、正视死亡、追求人生意义,更多的是掩盖了死亡、忽视了对人生意义清晰地思考。现代人太急太忙了,急着挣钱、忙着消费、急着健身、忙着熬夜、急着感官娱乐、忙着悠闲消遣、急着争分夺秒、忙着胡思乱想、急着追名逐利、忙着贪图享乐……无关紧要的琐屑占据了人的一生,虚无缥缈的幻境劳累了人的一辈子,生活似乎一直都是身不由己、无法把控。尽管有时,恍然醒悟:时间都去哪了?人生都怎么过的?难过、自责、反省,但是这些情绪没持续多久,生活又依旧回到原来的轨迹。人一生或多或少在一个套子里伪装自己,这个套子里没有死亡概念,没有深入的人生意义思索。直到死亡来临,一生就要逝去,幡然醒悟,所有的不真实的东西脱落,人成为最真实的自己。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伊万·伊利奇的幸运,绝大部分人等待的只是可怖的死亡和无意义人生的到此终结,这是死亡对于人一生遮蔽死亡、忽视人生意义思考的极大讽刺。
最近一则名为《健康本该如此》的广告火爆微信朋友圈。几乎每一个现代城市的年轻人都能从这则广告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于是大家纷纷回应:扎心,健康本该如此!这则广告从当代中国社会的年轻人常见的生活内容出发——“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听说手机屏幕辐射大,你换了张绿色的壁纸;你在凌晨3点转发遥远城市有人猝死的新闻,再给自己定了五个起床闹钟……”[14],配合一大批令人震惊的健康数据——“中国皮肤病患超过1.5亿人,中国青年近视率世界排名第一,中国每年猝死人口高达55万……”[14],一层一层戳痛当今中国社会普通人透支健康的痛点。而对于大众,无节制地透支健康何尝不是在遮蔽生死呢?遮蔽生死某种程度何尝不是在遮蔽人生意义的思索呢?因此在这样一个“遮蔽死亡”有增无减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人生意义思考不怎么受重视的时代,重温托尔斯泰的死亡书写,认识人生的不足,也是事不宜迟、刻不容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