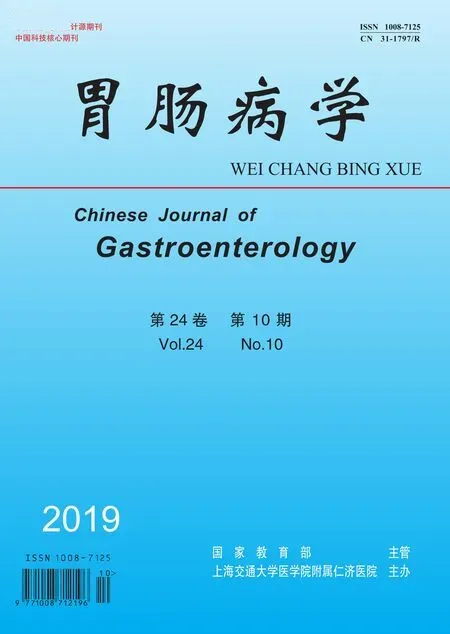消化道真菌在克罗恩病中的研究进展*
2019-12-26尹娟庞智
尹 娟 庞 智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消化系疾病与营养研究中心(215008)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其发病机制复杂,病因学不明,目前普遍认为环境、微生物等因素诱导遗传易感个体的肠道对微生物产生异常免疫应答导致的慢性炎症与IBD发病有关。遗传易感无菌动物并不表现出结肠炎症状,表明微生物是IBD发生的必要条件[1]。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发展,近年涌现出大量研究应用16S宏基因组测序分析CD患者消化道中复杂的微生物组成和菌群失调现象。同时,关于真核生物中的机会致病真菌与IBD发病和慢性化相关的报道也日益增多。与非CD患者相比,CD患者的抗真菌抗体水平更高,甚至在疾病确诊前即已表现出差异[2-3],支持这一群体存在真菌菌群失调的观点。本文重点从病原学和宏基因组学角度综述近期真菌在成人CD患者中的研究进展。
一、肠道真菌与宿主免疫系统的关联
肠道真菌种类受宿主遗传背景、卫生状况、生活方式、抗菌药物的使用等多种因素影响,最常出现于人体肠道的真菌为青霉属、念珠菌属和曲霉属[4]。研究[5]表明食物来源对肠道真菌菌群组成有显著影响,主食动物性食物与主食植物性食物的人群肠道真菌菌群差异显著。尽管在DNA水平检测,真菌菌群在肠道微生物中的占比仅约0.1%~1%,但其平均体积为细菌的100倍以上,肠道真菌的生物总量及其对肠道微生态的作用可能被大大低估[6]。
定植于肠道的真菌与宿主免疫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对维持宿主肠道健康极为重要。固有免疫受体如C型凝集素受体(dectin-1、dectin-2、mincle等)、Toll样受体(TLR2、TLR4等)可识别真菌胞壁β-1,3-葡聚糖。Dectin-1可通过CARD9激活细胞内信号,诱导T细胞向Th1、Th17细胞分化以及相关炎症细胞因子产生[7];通过与肠道微生物间的作用调控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分化,从而调节肠道免疫稳态[8]。关于真菌通过C型凝集素受体在IBD中作用的研究较为多见。Dectin-1缺失小鼠对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的结肠炎更为敏感;dectin-1基因多态性(CLEC7A)与UC病情重症化显著相关[9]。高表达dectin-1以及其他C型凝集素受体的CX3CR1+单核吞噬细胞可应对多数共生真菌,通过Syk信号通路启动适应性抗真菌免疫应答,该细胞功能受损的小鼠更易被念珠菌属诱导发生肠道疾病;CD患者存在CX3CR1编码基因错义突变,并与抗真菌应答受损相关[10]。因此,肠道真菌菌群稳态与肠黏膜免疫平衡密切相关。
二、二代测序技术的发展对肠道真菌微生态研究的促进作用
近20年来,不依赖于培养法的二代测序技术的发展使研究消化道中难以培养的微生物成为可能。对真菌的分析系针对其高度保守的内部转录间隔区(ITS1或ITS2)。不同测序平台使用的策略各有其优势。Illumina测序平台使用的循环可切除终止测序法策略同聚体错误率低;454焦磷酸测序法可测序1 000 bp的长片段,解除了测序的长度限制;而SOLiD(sequencing by oligonucleotide ligation and detection,寡核苷酸连接和检测测序)方法使大规模平行测序成为可能。Illumina测序的准确性大于99.5%,其他连接酶法测序如SOLiD准确性大于99.95%[11]。研究者可根据实验需求选择合适的测序平台。
运算软件的不断发展,使计算出差异小于1%的OTU(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运算分类单位)成为可能,MED(minimum entropy decomposition)还可分辨近缘物种的真正差异和测序误差[12]。生态学分类概念被用于区分微生物种群,如alpha多样性分析的shannon和simpson指数被用于计算样本内物种多样性,而beta多样性分析可评估样本间多样性。未来16S与ITS测序策略的整合,加之对复杂的细菌与真菌混合群体数据分析方法的发展,将促进对真菌在健康和疾病中所起作用的评估工作[13]。
三、真菌在C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应用二代测序技术检测CD发病过程中的肠道菌群组成,可发现患者肠道细菌与真菌菌群组成多样性相关,细菌与真菌菌群失调亦相关[13-14]。与健康对照者相比,CD患者结肠活检标本的真菌菌群生物多样性更大[15],炎症黏膜真菌丰度和生物多样性增加更为显著[16];粪便真菌菌群中白念珠菌、棒曲霉、新型隐球菌数量显著增多,且粪便真菌生物多样性与血清C反应蛋白(CRP)和CD活动指数呈显著正相关[16]。Hoarau等[17]发现,CD患者与其无病一级亲属相比,热带念珠菌丰度显著增高,并与CD生物学标志物抗酿酒酵母抗体(ASCA)水平呈正相关,但真菌总体生物多样性减少。Sokol等[18]分析了IBD患者的粪便样本,发现其担子菌门/子囊菌门比值较健康个体升高,酿酒酵母占比降低,白念珠菌占比增高。Liguori等[19]的研究显示,CD患者黏膜相关菌群中银耳亚纲Cystofilobasidiaceae科家族和光滑念珠菌过量,炎症黏膜真菌总体数量增多,炭角菌目存在于炎症黏膜,酿酒酵母和指甲绒黑粉类酵母则存在于非炎症黏膜。这些真菌只是路过菌还是与肠黏膜免疫相关,亟待深入研究。但上述研究均支持成人CD患者肠道真菌生物组成丰度大于健康人群的观点。
人体内真菌生态失调与内稳态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一动态变化很可能比真菌感染更常发生,从而对宿主免疫系统产生持续影响[20-21]。近期研究表明共生真菌白念珠菌和酿酒酵母可驯化宿主免疫系统,该作用与真菌胞壁多糖几丁质有关。分离自白念珠菌的几丁质可通过促进巨噬细胞分泌抗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0(IL-10)抑制炎症反应[22]。以酿酒酵母几丁质预处理小鼠,可诱导小鼠对抗白念珠菌引起的致命感染;经特定酿酒酵母菌株处理的人单核细胞,由脂多糖(LPS)刺激引起的促炎细胞因子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分泌增多,杀菌能力增强;分离自CD患者粪便样本酿酒酵母的几丁质含量显著高于环境中酿酒酵母的几丁质含量,可能在肠黏膜促炎细胞因子分泌中起调控作用[23]。
共生真菌在淋巴细胞再循环和诱导宿主免疫耐受中发挥重要作用。人类出生后RALDH+树突细胞(DCs)从固有层被招募至肠系膜和外周淋巴结的过程依赖于共生真菌。以抗真菌药物处理SPF级小鼠,可导致其外周淋巴结中的RALDH+DCs显著减少;而予小鼠外源性热带念珠菌可增加其外周淋巴结中的RALDH+DCs数量[24]。由此推测生命早期肠道微生物群对免疫系统的发育至关重要。有研究[25]报道,健康人群外周血中存在真菌特异性Treg细胞扩增,其表型和功能特征均与胸腺来源的Treg细胞相同。小鼠小肠派伊尔结DCs识别白念珠菌诱导免疫耐受,此过程依赖于真菌诱导产生的2,3吲哚胺双加氧酶(2,3 indoleamine dioxy-genase, IDO)[26]。免疫耐受DCs产生的IDO促进色氨酸代谢成为活化T细胞芳烃受体的底物,从而促进Treg细胞产生[20,27]。根据上述结论推测,CD患者白念珠菌等共生真菌比例变化可调控外周血Treg细胞数量和免疫耐受。
目前对真菌在IBD发病中的作用机制并不明确,但研究[9]证实dectin-1基因与UC疾病严重程度相关,dectin-1缺失小鼠对实验性结肠炎易感。CD患者抗真菌抗体水平升高,ASCA IgG和IgA被认为是CD诊断和疾病进程预测较好的生物学标志物[2-3]。基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的研究[28]发现IBD与宿主抗真菌免疫相关。鉴于成人CD患者存在明显的真菌菌群失调,共生真菌对肠黏膜免疫系统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生命早期免疫系统发育受真菌影响显著,因此易感个体童年期真菌菌群组成对生命后期疾病风险的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亟待开展更多基础和转化研究深入探索真菌菌群失调与CD发展间的因果关系。
四、CD患者肠道真菌菌群失调与现行治疗方案的关系
现行CD早期有效治疗方案为使用抗体靶向特定炎症相关分子以减轻慢性炎症,TNF-α、IL-12/23和白细胞黏附分子为常用治疗靶点。靶向TNF-α的抗体主要有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赛妥珠单抗,优特克单抗则是首个靶向IL-12/23 p40亚基的抗体。条件致病真菌如白念珠菌相关免疫反应有TNF-α、IL-17、IL-23等参与[29-30]。因此上述CD治疗方案与真菌感染(组织胞浆菌病、酵母菌病、球孢子菌病以及其他机会致病真菌感染)有关[31]。临床试验中,与安慰剂相比,抗IL-17A单抗(苏金单抗)治疗组患者粪便炎症介质增多,发生黏膜皮肤念珠菌病的风险增加[32]。纳入14篇文献共1 524例IBD患者的系统综述表明,IBD患者最常见的真菌感染为念珠菌属感染(903例),多数感染发生于抗TNF-α治疗6个月内[33]。
迄今尚无IBD抗真菌治疗的临床试验开展。理论上,靶向IL-17、IL-23、IL-22、TNF-α细胞因子途径可减轻促炎反应和急性黏膜损伤,但也同时导致共生真菌减少,机会致病真菌丰度增加,这为IBD患者临床检测到病原真菌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特别是Th17细胞因子,如IL-22可直接调节上皮抗微生物相关基因表达,包括肠上皮细胞Reg3γ以及Paneth细胞等的抗微生物产物。这些黏膜分泌物减少可促进黏膜表面真菌生长和定植。虽然上述现象并未被常规检测到,但已有研究数据表明某些免疫靶向治疗可致真菌负荷增加。由此可提出下述假设:IBD相关免疫反应部分是由病原真菌所驱动,特定治疗方案可能缓解消化道对病原真菌的免疫反应[13]。
五、益生真菌在IBD治疗中的应用
共生真菌对宿主免疫功能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目前在CD的临床治疗中,布拉酵母菌已被用于缓解肠道炎症的辅助治疗。近年来,其机制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作为一种益生真菌,布拉酵母菌可增强宿主肠道对病原菌的免疫反应,限制CD、UC以及难辨梭菌结肠炎等病理性炎症反应[34]。布拉酵母菌培养上清液可直接抑制CD患者由LPS诱导的髓样DCs及其促炎细胞因子分泌[35]。有研究[34]发现,布拉酵母菌可提高肠道总IgA水平。在小鼠结肠炎模型中,喂饲布拉酵母菌可减轻组织学炎症反应,抑制白念珠菌在肠道定植[36]。
另一见诸报道的益生真菌为乳酒假丝酵母。口服乳酒假丝酵母可缓解实验性结肠炎,伴肠系膜淋巴结Treg细胞和调节性DCs增多以及固有层Th17细胞减少[37]。随着高通量二代测序技术的发展,未来研究或可关注肠黏膜或粪便样本菌群分析中益生真菌的鉴定及其临床应用。
六、粪菌移植(FMT)与IBD
FMT最早系用于治疗复发性难辨梭菌感染,可重建肠道菌群内稳态[38]。目前关于FMT在IBD治疗中的应用已成为研究热点,但结论不一。一项关于FMT治疗IBD的系统综述显示,17.4%~60.4%的IBD患者经FMT治疗后获得临床缓解,UC患者和CD患者的临床缓解率分别为22%和60.5%[39]。目前关于FMT用于UC患者的研究更多。最近一项多中心、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表明,多供体FMT可诱导活动性UC临床缓解和内镜改善,FMT后微生物多样性增加并持续[40]。当前关于FMT供体与受体粪便微生态的研究聚焦于细菌组成,尚无研究关注真菌组成在FMT治疗前后微生物多样性变化中的贡献。随着真菌菌群分析方法的改进,真菌分析将在分析FMT供体与受体肠道微生态变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七、小结与展望
IBD病因学研究强烈支持如下观点:环境因素的改变可影响宿主肠道微生态,增加遗传易感宿主的IBD发生风险,继而影响疾病进展。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细菌菌群失调在IBD发病中的作用,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数据表明真菌菌群组成在此过程中亦发生显著变化,消化道中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微生态环境成分的相互作用。综上所述,人类消化道中真菌菌群多样性的改变以及特定真菌种类丰度的变化在IBD发病中起有一定作用,未来IBD相关研究应更加关注真菌在IBD病因中的潜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