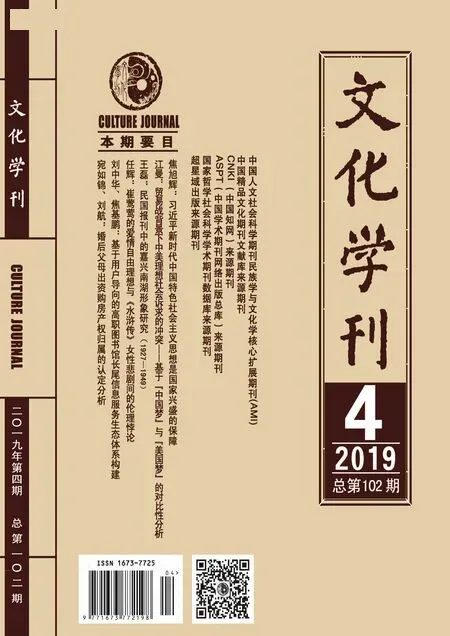崔莺莺的爱情自由理想与《水浒传》女性悲剧间的伦理悖论
2019-12-26任辉
任 辉
一、性爱、婚恋伦理基本内涵的原理解析
禅宗有偈语曰:“砍柴担水,无非妙道”。也就是说,即使是平常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可能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但是,实际上从社会各学科来说,这种说法确实极为有道理的。比如从马斯洛的“需要”心理学理论来说,作为“人”这个族群种类来说,其“饮食”“安全”和“生殖”这三大本能之中,蕴藏了丰厚的哲思。简单的吃饭问题,就包含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这两大目的性分水岭式的人生领域。“婚恋—性爱”这样的类似于动物交配式的人类情感性活动,也存在着“精神—情感—审美”和“物质—生殖—功利”这样截然对立的目的性差异。前者是精神享受和情感交流的过程,后者则是纯粹的物种繁衍的本能性程序化过程。
依据马斯洛的说法,人的性爱活动可以使人达到“高峰体验”,这是人的“需要”层次之中“爱”的需要的体现。同时也是“自我实现”的基础条件和表现之一。但是,要达到这样的需要层次,前提必要条件两大要素:一则是性爱双方必须是自由的、能够意志自主的人。也就是说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成员一定要具备福柯在《性经验史》所重点强调的人的“权利”要素。如果双方在这个层面上不对等,那就很难进入这样的精神境地(在此是要忽略个案的)。二则,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要具有情感意识和精神需求。如果没有这个精神要素作为支撑,性爱双方的性爱活动就演变为了单纯的生殖、繁衍活动。
我们也可以以之为基础延展来理解这样的性爱活动:个体性的自由的情感交流活动进一步扩展到一个族群的大范围之内,一个群体是否具有这样“性爱—婚恋伦理”,这也是衡量其整体精神能量是否具有有序性,以及精神能量是否可以正常释放以及释放的性质和程度的标准。而这个准则的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精神-实践”学说:《共产党宣言》里的历史辩证的“自由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而且社会组织结构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史观和实践理论基本原理,人固然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本质更应该是“自由”的,人本身就是目的。这正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方向的文明史观:“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
如果整体性的精神能量是能够得到这样的保障,就意味着其“性爱—婚恋伦理”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言的,其基础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而非“动物生殖性的”,这就符合了基本人性,而且这个原理是具有普泛性的。人性,或者人们的“类本质”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这就是马克思有关于“人”的学说的基本原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的内涵。[4]而这个“总和”就是它的普泛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于社会实践和生活、艺术鲜明的对照,中国古典名著《西厢记》崔莺莺对于自由爱情的追求与向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正是对于个体自由的美好憧憬。“崔莺莺现象”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其间在明清名作之中具有广泛性反映。比如《聊斋志异》《牡丹亭》和《倩女离魂》文学戏剧作品等等。这一类的作品有人冠以“个性解放”的名由,未免有些牵强了。一种文化的质地要有所变化,必须要有其变化的根据和文化渊源。盲目命名并没有多大的理论意义。但是“精神解放”作为人的类本质来说,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是总会间或性有所显示的,其程度如何则是要看具备条件的历史特性。人,毕竟不等同于动物,总要有精神含量,也总会有所释放。但是这种释放的途径一般来说就是动物性本能行为。连孟子都认识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第十九章》)也就是说,正是人的理性提升了人的动物性行为的功能和意义。但是我们说,提升的程度则要看历史发展所造就的文化背景。诸如“崔莺莺现象”这样的朦胧的对于自我个性的自由地追求,就是人的精神、情感的或者说是人性的大胆突破,尽管难能可贵,但也不可能不受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具有完全实现的可能性的。但是也作为了历史见证,在艺术作品之中间或性的显示了当时的历史文化氛围。也正因为艺术源于生活,所以,生活本身会给予艺术以更多、也更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的材料支持。
作为压抑人性、反人道的反例来说,同期类似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特别是《水浒传》则给予了更多、也更为鲜明的艺术证明。《水浒传》里的女性形象和性爱描写,则是赤裸裸的诋毁性、反人性的。这部名著不仅仅把女性的婚恋情感裁决权全部剥夺,而且是把女性作为低劣甚至是恶劣的动物来塑造形象的,同时也是把性爱当做纯粹的生殖活动来叙事的。但是也很具有悖论色彩的是:潘金莲的恶毒却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一个事实:人是精神性物种,人的精神能量是十分巨大的。其受到压抑的力量越大,则反弹的力量也就越强。二者是成反比例关系的。所以,百年来 “潘金莲式悖论”困扰了人们许久。这就是中国古代“性爱—婚恋伦理”的终极性困惑,而这样的困惑既是古代人们所无法走出的,也是今人很难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的。
所以,当“崔莺莺”遇到“潘金莲”的时候,新的悖论就又再次发生了:在婚恋、性爱心理需求要求得到平等的时候,人们遇到的却是牢不可破的时代道德文化的铁藩篱。如果是成功者,那也仅仅只能说是侥幸,而且是带着枷锁的侥幸。更多的则只能是“宝黛”“梁祝”“焦(仲卿)刘(兰芝)”之类的人间悲剧。看《长生殿》之悲剧也足以让人无限感慨:即使是贵为社会顶层的皇族,在这个层面上其结果也未必比平民强多少。《三国演义》里“刘安杀妻”的故事虽则是虚构的故事,但是艺术概括的逻辑前件从来就不会是空穴来风的。丰富厚重的历史事实支撑材料成为了艺术活动最为重要的根源之一。
而更为可悲的是,作为同类的女性对于这一类文化的自我认同感——虽然说是女性群体的集体无意识的认同。这样的归化感,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力的心理文化机制,直至同室操戈、互相践踏、自相残杀,这就更具悲剧色彩了。比如《孔雀东南飞》里的焦母,史实中的吕后等等。
“性爱—婚恋伦理”是一个社会群落的重要联结与平衡纽带,体现着其社会机制的基本发展状况。崔莺莺、杜丽娘等这些中国古代艺术名著里的人物,所表达和追求的是人类共有类本质的基本情感,是对美好的人生希望的憧憬和向往。这种爱的情感和“尊重”“归属感”和 “成就感”等心理需求一样,是共有人性的基本内容。而《水浒传》等名著里对女性和性爱诋毁性甚至是污蔑性叙述这一类糟粕性内容,是男权社会性别歧视的极端体现,也是古代社会一种浓重的固有封建文化的展示,说明封建伦理纲常和家族宗法制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择取这二者相对比,以这个角度来解析其恒久性的固着性文化精神能量的内蕴,可以充分显示出这种古代文化的本质性特质。
在《水浒传》里,众多女性的反面形象,且不说是不是基于真实文化的基础的事实,或者说是在多大的程度上依据了历史原貌来进行艺术概括的。即使是真实的实际生活凝缩,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终极追问,造成这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什么。
其实原因并不难以归纳,无非就是两条:一是正常生理欲望的驱使,二是人性禁绝太深太久所引起的畸形反弹。前者这是人类历史最为常见的历史现象之一,深层次的意义很难拓展,而后者则就不然了。人的精神和意识思维等心里要素是活性的,对于欲望的控制、对于正常的心理需求均难以达到有效抑制的时候,走极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不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就这一点来说,女性是这样,男性也亦然。《水浒传》里仅仅“吃人”的描写就有四处,梁山好汉们对敌甚至于对普通百姓的有悖于基本人伦的“残杀”“屠戮”描写更有多处。笔者更是以欣赏和肯定的角度来叙事的。所有这一切均不是正常的心理状态和反应,然而,所有这一切就是这样一种深切的文化模式和类型的深层次描绘。
其实,在男权社会里,作为性别一极的男性一样是受害者,双方并没有赢家。更为可悲的是,本来是受害者的一方,却有可能再转回头成为害人者,就像俗语所云:“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所以,艺术写实和历史文化真实是互相映衬、互为对照的。
二、《水浒传》:一曲女性的悲情哀歌
经典名著《水浒传》述说的是梁山英雄好汉抗争黑暗社会和腐朽统治者的故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更是一曲女性的悲情哀歌。
在中国古代宗法封建社会里,女性的地位要远远低于男性,甚至几乎可以说女性缺少基本的社会地位,她们往往被看成是男性的附属品而依附于男人,没有价值、尊严和自由,却又往往饱受各种摧残与压迫而不得基本的人生幸福。《水浒传》整部小说虽然小说对女性的着墨不多,但是各种类型的女性也都简单地涉及到了。小说中被作者略写的用于做男性陪衬的几个女性依然是很值得关注的重点,她们的悲剧值得我们深切地品味和思考、反思。小说对这些女性的悲剧性描述多是古代社会最底层女性的真实写照,“淫妇”情爱的悲剧,“巾帼英雄”事业上的悲剧,“毒妇”与娇弱女子生活中的种种艰辛与无奈,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些女性的悲剧都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之中女性特有的社会角色、地位与社会身份。
《水浒传》成功塑造了富有个性、情感丰富的各类各色女性形象。她们处于社会的不同阶层,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但是很值得深思的是:无论是真实的生活还是虚构的小说,女性似乎都很难走出那个悲剧的命运,那样一种文化宿命,而这种悲剧宿命的根源就在于纲常伦理的封建文化意识把女性彻底打压到了社会的最底层,而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男尊女卑”观念。她们对于美好的情爱婚姻、对事业得追求甚至对于普通生活的向往,结局却无一不让人痛心。相反,她们的躯体备受摧残与奴役,她们的精神也被反复折磨与牢牢地禁锢。出现在《水浒传》中的女性,无论美貌多情还是英武坚贞,无论狠毒刻薄还是娇柔软弱,最终都以悲剧的命运收场。这既是现实的真实写照,也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人们(当然也包括作者在内)对女性极端歧视甚至是仇视的畸形心理的重要表现。
《水浒传》塑造的悲剧女性主要可分为这几个类别:一是“淫妇”类,比如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郓城县天香楼的头牌妓女阎惜娇,生于七月七日的风韵寡妇潘巧云等等;二是女豪杰英雄类,比如母夜叉孙二娘,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三是道德败坏、心肠狠毒的妇人和一些娇弱女子,比如王婆、刘之妻、金翠莲等。只是这些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生结局:没有一个逃出悲剧的命运。
《水浒传》中女性的情爱悲剧主要典型地体现在这几个人物形象上:潘金莲、阎惜娇、潘巧云以及贾氏。这些女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遵守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道德标准,全都不守妇道、瞒夫偷情、勾结奸人。她们都有着美貌的外表与淫荡狠毒的内心。为了追求违背伦理道德的爱情,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都不择手段、残杀亲夫。她们都有着一样的共同的悲剧结局:都因为“淫荡”而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在作品中,这些女性被描述为美若天仙,又恰逢妙龄之时,而在美丽的外表之下却深藏着不可见人的污秽恶毒。作者似乎是故意将这些淫荡狠毒的妇人描写成如此美丽的形象,以此来有意无意地传达着一个这样的信息:貌美如花的女子似乎总是天生淫荡,狠毒绝情,属于“红颜祸水”。
“红颜祸水”其实是一种极其懦弱的迁怒心理。在一个社会群体之中,人们的权力与责任应该是对称的:即有多大的权利就应该肩负起多大的责任。掌控权力的人如果把失败的责任推卸给他人,完全是一种道德卑劣行为。但是我们看历史,恰恰这样的行为和言论却是极为平常的。正如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阿金》里一针见血地指斥:“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旦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的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绝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5]这种带有普泛意义的社会文化现象确实很值得人们深思、反思。
在《水浒传》所展现的社会现实里,“红颜祸水”与昏庸腐朽的贪官、横行乡里的恶霸一样,共同将那些好汉们逼送上了梁山。
及时雨宋江的逃亡之路由杀害阎婆惜开始。阎婆惜恩将仇报,对宋江步步紧逼,最终宋江被逼无奈手起刀落,要了阎婆惜的性命。
而武松为了替兄报仇,倒提着潘金莲的脑袋,硬生生地剖取了潘金莲的五脏,又割了潘金莲的头颅,将其供养在大郎的灵前。
杨雄与石秀皆因潘巧云的命案而投奔梁山:当杨雄发现潘巧云与和尚通奸之后,在翠屏山直接取了其性命,并割了她的舌头、取了五脏心肝挂与树上。
这些英雄好汉对“淫荡”妇人的憎恨至极,报复之心却丝毫不让与对方,甚至更为残忍。他们将一腔怒火喷向了手无寸铁又道德沦陷的女子身上,使这些女子死的那样悲惨而似乎又理所应该。比如宋江、武松、杨雄和卢俊义,这四位英雄好汉都是因为手刃了淫妇的性命而被迫一步步走上了梁山的道路。淫妇们的生命铺就了他们通往梁山的道路,淫妇们的生命铸就了好汉们生命的转折点。其实,在情感上宋江们也是一个悲剧,也同样做了性的奴隶。人类正常的情感是双方互换互通的。如果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不仅对于双方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而且性行为也是“动物—生殖”性的实用性行为。而一旦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了他(她)人的痛苦之上,其人生也将可能随之成为悲剧,所以,在这样的文化情境里,没有谁会成为赢家。
《水浒传》这部小说对女性悲剧性命运的描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女性悲剧的一个真切的写照与缩影。自古代父系社会开始以来男性就占据了社会的绝对主导地位,女性只能成为男性的附属品。随着儒家“三从四德”和“男尊女卑”等社会藩篱维护男性统治地位的文化意识的加固,女性的屈从地位便成为无法更改的既定事实。《水浒传》中描写的女性形象,或是美貌多情的,或是坚贞英武的,或是贪婪恶毒的,或是弱小无助的,但是结局却如出一辙,都落得个悲悲惨惨的下场,这既是对古代封建社会女子艰难处境和造就这种结局的文化大背景的一种真实写照,更是对封建宗法制度和社会伦理道德思想对女性极端歧视与践踏的一种明证。在所有的文学名著之中,《水浒传》这部小说中所体现的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摧残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与其说这是一场人物悲剧,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悲剧。
三、崔莺莺的爱情理想与时代悖论
王实甫的《西厢记》被视为中国古代剧作的经典巨擘,曾被誉为“北词之首”“诸曲之冠”,且与长篇小说《红楼梦》并称为中国文史上“情爱”类作品的双壁。因为如果说《红楼梦》与《金瓶梅》在“家庭-情感-性爱”伦理这个内容上属于一脉相承的话,那么在故事性的结局上则与《西厢记》为互补:一个喜剧,一个悲剧。《西厢记》并以“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成为后世文学作品重要主题,且此语也成为世人爱情生活的经典名言,也使得该戏剧成为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之一。
首先,《西厢记》的成功之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成功的塑造了崔莺莺这一经典人物形象。“《莺莺传》中崔莺莺形象光彩夺目,体现了我国古代女性渴望爱情,追求独立的女性意识。”[6]作品对崔莺莺人物性格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描写,凸显了崔莺莺这一人物形象生动的人物性格、复杂的心理活动和女性在恋爱中所特有的细腻、容易多变的感情表达特征。
其次,中国古代名句“有情人终成眷属”固然是人们历来所希冀的完美结局,然而历代文学作品中对此几乎从未有过正面反映,甚至大多只是相反的悲剧。《西厢记》可以说是开先河之作,在真正意义上正面的表达了这个对美好愿望的深切赞同和向往,并以此同时赞扬了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爱情自由而敢于大胆反抗封建权威的精神和行为。
《西厢记》表达了反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进步主题,使其成为元杂剧中的典范代表。戏剧冲突的巧妙安排,语言的生动细致,结构的逻辑严密,人物形象的塑造均有其特色。《西厢记》中的男女主角张生和崔莺莺生动饱满的形象描写表现出作者不凡的创作水准,人物刻画得张弛有度,生动形象,尤其把崔莺莺的性格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崔莺莺这一人物形象在作品中塑造的主要成功之处,源于其勇敢无畏的反封建思想。崔莺莺身为大家闺秀,和杜丽娘等知识女性一样,本应恪守封建礼教的约束,做个大门不迈的千金小姐,享受寂寞而空虚的闺房生活。然而她内心对于情欲和爱情的追求却使得她背离了封建礼教的制度与约束,虽然身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却仍未丧失本心,无时无刻不渴望着爱情。自从与张生佛殿前偶遇,莺莺便点燃了爱的火焰。从那以后莺莺便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青春,并不是说在偶遇之前她没有青春和生命,而是她的青春年华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没有生机与希望。她虽然不安于被禁锢的生活,去无奈地在封建礼教的约束下变得娇惰。佛前偶遇把她的青春和生命惊醒了。她自己的描述:“往常见个外人,氲的早嗔。但见个个人,厌的倒褪。从见了那个人,兜的便亲!”因之,便“坐又不安,睡又不稳,登临也不快,闲行又闷,镇日价情思睡昏昏。”[7]
与张生的初遇唤醒了莺莺尘封已久的生命激情,使得莺莺对生活本身有了新的感悟和思考,这是莺莺反抗意识的初现。从这以后莺莺便对于封建礼教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并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崔莺莺与张生彼此一见钟情,莺莺更竟然在父丧期间大胆爱上张生,确实表现了非比寻常的勇气。特别是《酬韵》一折中莺莺追求爱情的一颗心则更体现出旺盛、炽热的少女情怀。在她收到张生墙角吟诗以表达心中的爱慕之后,莺莺也和诗回应,并在诗中莺莺把自己的压抑已久的思春情怀和对张生的好感和盘托出,毫不避讳。莺莺对张生的爱慕虽然直爽却又委婉含蓄,性格多重又复杂。当爱情来临之近,她情窦初开,流露出少女所特有的羞涩,表现了她虽然对美好的爱情充满向往,却又不肯轻易流露出真情的迟疑和忧虑,对于礼法一言一行甚至连思想都要受到约束的钳制的清规戒律依然是小心翼翼,保持了高度警惕。然而对于像莺莺这样的知识女性,一旦下定了决心“礼法”无法禁锢住她们的心,有时候还会适得其反,更会激起她们强烈的反叛心理,正如郑光祖《倩女离魂》杂剧中张倩女所说:“你不拘钳我可倒不想,你把人越间阻,越思量。”[8]后来面对老夫人的出尔反尔,她已经不能忍受下去,她责怪母亲毁了自己的前程,开始踏上毅然决然的反抗道路。到《赖婚》和《听琴》时,她再也不能按捺自己的愤怒之情,公然在众人面前诅咒自己的母亲。《赖婚》一折中老夫人为了维护家长制的绝对权威和个人意愿,逼迫莺莺拜张生为哥哥,由此引来了莺莺的强烈抵触。老夫人让她给张生敬酒时张生却不肯吃,莺莺全然不顾老夫人的威严愤怒地当众把杯子扔给了红娘,以示对于母亲的无声抗议。
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带有所有制性质的绝对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之中,其影响和约束力是无所不予涵盖的。它不只体现在各种各类的社会关系上,也体现每一个群体和亚文化系统之中,当然也存在于在老夫人身上和莺莺的灵魂之中,这主要体现在她在争取爱情婚姻自由的勇敢行动,同时又难以放下大家小姐的架子,常流露出犹豫反复的一面。例如“闹简”“赖简”等表现莺莺“假意儿”的喜剧场面,足以反映她内心的犹疑、挣扎、矛盾与痛苦。而在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里,张生终与莺莺结成秦晋之好,这是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他们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艰难异常艰难的抗争过程中争取来的,所以才更真实感人、才更弥足珍贵。“尽管这种结局形式没有脱离男女受情关系中某种固定的悲欢模式”。[9]
这是人们都愿意看到的、符合常人审美习惯和生活观念的圆满大结局,但我们不得不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夫贵妻荣、姻缘美满的尾巴以及家庭组合形式,也依然是囿于宗法制度和纲常伦理的框架之内。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扣在二人头上的许多类似于“对于封建礼教的叛逆、反叛”“对封建阶级与社会的公然反抗”“女性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得个人权利”等议论,“剧中崔莺莺勇于捍卫自己的爱情,实际上也就是捍卫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之类的论说,不是说一定不含有其中的成分,但是如果夸大了崔莺莺反抗与追求的意义和性质则并不可取。因为很显然:同质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不可能产生异质的文化元素。
所以我们也应该看到,崔莺莺的反抗和大胆追求,仅是寻求人性、人的本性的朦胧突破,并不意味着具有完全的自觉、自主性,并不含有理性的自我意识。仅仅是在封建礼教的大框架下的一定程度的背叛,更谈不上“挑战”。她与杜丽娘、林黛玉甚或是刘兰芝等女性的爱情追求如出一辙,甚至与普通百姓小人物在严格的封建礼教下私下偷情的行为也并无本质不同,尽管其精神也是可嘉的。这与人们常说的自我意识、性权利、婚恋自由的觉醒、突破宗法制度下“情感—婚恋—家庭”伦理的异质性精神不完全是一回事。所以,过分夸大这种行为的意义并不可取。
再者说,尽管宗法礼教何等森严,但是《西厢记》等盛赞和向往美好爱情的作品依然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这说明基本人性内核的精神力量是何等强大。同时也同样说明了这样一个悖论:这种人性所要突破的恰恰就是人们自己在古老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的这种礼法制度和伦理规则。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一类作品称赞女性主动追求个人爱情生活幸福的行动,我们可以称赞为青春期的人们在有限范围之内性冲动之中追求幸福的勇敢行为,与《水浒传》之类的对于女性的诋毁性描写相颉颃、角力,也是从另外一个维度对于自主性世俗性爱、婚恋伦理的肯定和突破,彰显了人性的魅力,很值得赞许、也是很难能可贵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叹,中国古代的“家庭-婚恋-性爱”的绝对男权性、伦理性质的复杂性和历史顽固性。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在古代中国,存在着各种要求妇女服从、尊敬和献身于她的丈夫的规定……在这种一夫多妻的社会里,妻子处于一种竞争环境中,她的地位与她提供快感的能力直接相关。”[10]于此,虽然我们当然不会去同情《水浒传》里面的恶妇、毒妇,但是至少可以尝试着去理解她们,理解她们所处的文化环境。
四、结语
《水浒传》所要宣扬的、《西厢记》崔莺莺所要突破的是带有所有制性质的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礼法等级制,随着岁月的增长已经越来越绝对化、极端化和精致化,并在两个维度不断深化、扩展:一是对外,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每一个细节;二是对内,深入到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内心最深处而成为一个社会族群的集体无意识,概莫例外。
这些作品更深刻、更充分的反映和体现,是其间人的“物质—精神”这两大领域的分化:古代封建绝对等级制结构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扩展人们的精神领域,只是在“物质—实用—世俗”的线性维度上直线发展、延伸。比如《水浒传》里王婆所传授西门庆的“潘驴邓小闲”五字诀。这五个字是古代社会“泡妞”秘诀,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文化浓缩性的侧面。但是我们看,这“五字诀”全部都是“需要”理论层次之中“本能”性内容,属于“物质—实用—功利”动物生殖性质的,缺失的是“精神—情感”的内涵。当然了,脱离物质性的、具有彼岸世界精神的文化特质,即使是在《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聊斋志异》等著名小说中也是罕见的。即便是《西厢记》《长生殿》和《倩女离魂》等经典情爱戏剧之中,也充满深刻的悖论:美丽的爱情憧憬仅仅是美好的理想,能够实现与否,则完全不取决于个人。退一万步说,即使他(她)们成功了,所希冀的生活内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异质的生命内涵——理性生活主体的精神内涵是完全缺失的。除非是个案,比如“宝黛”佛老性思想的生命存在意识,可惜又是一个悲剧而已。社会实际生活的例子不妨举一下陆游和唐婉的真实故事和《柳如是别传》对应的历史内容,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上述理论的最好诠释。
与同期的西方名著相比,是无比之比。《十日谈》、《巨人传》和《坎特伯雷故事集》、《十字军骑士》和《堂吉诃德》等作品严格意义上说都是文艺复兴的作品,但是反映的却是中世纪生活生活内容,正如明清名著反映的是“汉唐两宋”社会生活的内容一样。也就是说,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其实是具有传承性的,前后并没有质的区别。而如果就十五至十七世纪东西方同时期战争和爱情这两方面的经典名著进行对比的话,区别就在于其主旨是否是理性的、人道的,其人物形象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论述的“自由”“自觉”和“自主”的这样的特质。所以我们说,一旦缺少了这样的逻辑必要性前件,其结局也就是必然的、决定性的悲剧和悖论。所以,同时期的西方这些文学艺术作品所蕴含的内容,除了一些政治性的元素之外,也富含《西厢记》之类的爱情、婚恋和性爱方面的内容。若把双方予以对比,则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十日谈》《巨人传》等名著里面的爱情、性爱内容并非是仅限于理想和希望所系的虚幻的现实;而《十字军骑士》等战争题材的作品,表现的核心是人性的、理性的和人道理想的,并非是以惨无人道的赤裸裸杀戮为题趣和宗旨的。
于此即可以得出基本的结论:一则,一个社会族类深厚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其基本文化内涵、特性和伦理准则,且涵盖了这个社会生活的全部细节,而“性爱—婚恋伦理”是其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这个伦理的主体内核就是“自主”与“自由”的理性要义。二则,在“性爱—婚恋伦理”之中,决定个体双方是否幸福的准则和全部内涵的,是其间所含有的精神内涵的有无与多寡,也即马克思所论述的“精神-实践”学说原理。而决定着这方面内涵的却又是社会文化大背景这个前提。这个背景不仅在细节方面决定了这个社会之中的每一成员个体的“情爱-婚恋”甚至是全部的生活是否是幸福的,而且也决定着其“幸福”的本质内涵以及历史发展趋势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