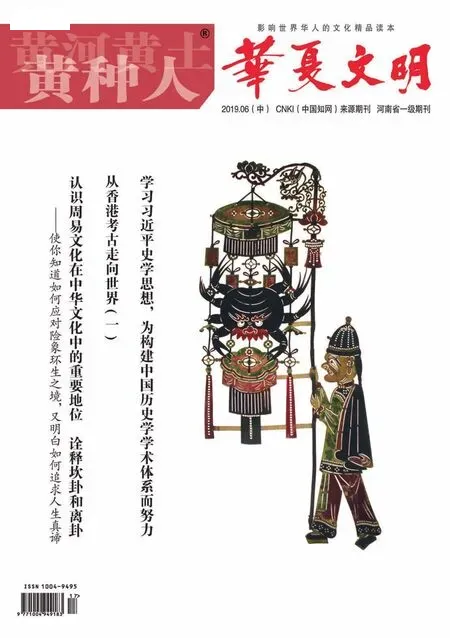学习习近平史学思想,为构建中国历史学学术体系而努力
2019-12-26李伯谦
□李伯谦
习近平同志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多次讲到历史科学,2019年1月2日,他在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信件中,则是最为全面、系统、集中的一次。在这封贺信中,他对历史科学的性质、地位、价值、作用,特别是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我有幸应邀参加成立大会并聆听了这封贺信的内容。
贺信明确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并向广大历史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任务。作为一名考古学家,一名历史科学工作者,我倍感光荣,同时也深知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我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既涉及材料、理论方法,亦涉及必要的手段。
就材料而言,除了传统的文献史料,亦需重视野外调查发掘的考古材料,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材料,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材料。而传统的文献史料中,不仅应包括由文字记载形成的历朝历代各种史书和材料,如正史、野史、类书、笔记、谱牒、墓志、卜辞、金石铭刻等,同时亦不可忽视从各种古代传说和神话中发掘“史实”的素地。在我看来,文献史学(包括口耳相传下来的传说、神话),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材料和考古学材料是构成历史学学科体系的三种主要来源,三者密切相关,缺一不可。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倡多学科联合攻关,我们将过去视为不可信的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碳-14测年结合起来研究,确定了河南龙山文化王城岗大城城址可能即“禹都阳城”,新砦期可能是“后羿代夏”留下的遗存,二里头可能是“少康中兴”至夏桀灭国时期的遗址,以王城岗大城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新砦期遗存—二里头文化代表了夏文化发展的三期,文献上讲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朝国家夏朝是客观存在、不可否定的。
就理论方法而言,马克思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是最重要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察事物、分析材料无往不胜,往往可以从看似杂乱无章的现象中发现规律、揭示本质。但要将最高的指导思想和琐细的材料联系起来却困难重重,没有适用于特定时段、特定地域、特定范围、特定问题的中介理论或曰中程理论作为桥梁,美好的愿望就很难实现,对此俞伟超曾经进行过深刻的分析。中程理论从哪里来?我认为来自实践。回顾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依据对考古材料的研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说;多元一体的发展道路,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类型说;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区文化相互作用圈理论;严文明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多样性、统一性及中国古代文明重瓣花朵式结构理论;我们提出的由考古学研究过渡上升到历史学研究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神权与军权—王权两种模式以及通过融合、同化不断发展壮大的滚雪球模式;等等,都可以认为是这种中程理论。当然,中国考古学从诞生至今,不断吸收、借用了许多国外的考古学理论方法,这是事实。但这些理论方法只有与中国的考古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促进中国考古学发展。
就手段而言,大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方法融入考古学,使中国考古学发生了重大变化:碳-14测年技术使过去只能靠地层叠压和遗物类型学判定的遗迹遗物的相对年代转化为绝对年代;DNA分析技术使得通过古代人类遗骸判定其种属和族属成为可能;食性分析技术可以通过古代食器上的残留物判定死者生前的饮食及其居地,通过孢粉及土壤分析可以判定古代种植的作物和环境;等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对古代社会文明发达程度的认知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科技考古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科技考古研究室目前已成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文物考古机构的“标配”。
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历史学各分支之间的整合,亦需要汲取其他人文学科乃至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有关成分,使之融汇一炉,达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分彼此的程度。当然,这种学科、学术体系亦需要通过与国外的交流,将之传播出去,让别人认识进而理解,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的话语权。
历史研究包括考古学研究在内,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关起门来孤芳自赏、自得其乐,而是像习近平同志希望的那样,要“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政治服务。我在《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的启示》一文中曾提出“文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等八点启示,作为党和国家制定政策方针的参考,既是响应习近平同志的号召,也是表明朝着这一方向继续努力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