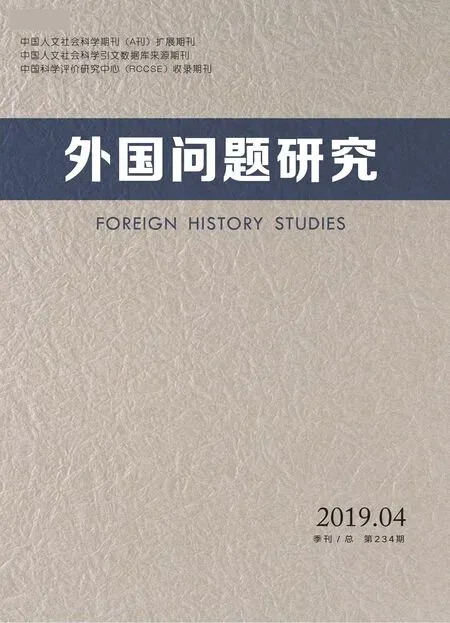一战后日本的西原借款善后策与日美博弈
2019-12-26孙志鹏
孙志鹏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作为近代日本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的政治意义自不待言,一战结束后其在外交上的“对美协调”路线亦格外引人注目,不少研究者以日本加入新四国银行团、西伯利亚撤兵、决定参加华盛顿会议等作为典型例证,将其作为20世纪20年代日本政党政治潮流下“协调外交”之滥觞。(1)参见沈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与日本在华新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新生、矢板明夫:《论20年代日本的“协调外交”》,《日本学刊》2000年第4期。陈月娥:《近代日本对美协调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何為民:《1914年—1921年における日本の満蒙政策:大隈内閣から原敬内閣までを中心に》,《現代社会文化研究》37,2006年。五百旗头真编著:《日美关系史》,周永生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祝曙光:《徘徊在新、旧外交之间——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交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陈伟:《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但对原敬内阁而言,其成立伊始面临的第一个外交考验是如何处置备受非议的西原借款,其善后过程的多变性与利益诉求的复杂性并非“协调”一语可以统括。日本学者所谓“协调中的扩张策”偏于强调日本外交的主动性,对来自美、英的外交压力考虑不足。(2)服部龍二:《東アジア国際環境の変動と日本外交:1918—1931》,東京:有斐閣,2001年,第20頁。胜田龙夫虽述及原敬内阁的西原借款善后过程,但对此事之于一战后日本外交之意义语焉不详。(3)勝田龍夫:《中国借款と勝田主計》,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72年,第196—223頁。故此,本文拟以日、美、中三国档案史料为基础,以西原借款善后策为中心,从外交困境、主动协调、顺势扩张、退守底线等层面探讨一战后日本外交之文脉及其特征,借此明晰原敬内阁在面对日美博弈的情况下采取“对美协调”与“对华扩张”的补偿逻辑,勾勒出一战后日本“势力圈外交”之地域向度,对于理解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而言似亦有所裨益。
一、“天佑”终结:一战末期日本的外交困境
一战爆发后,元老井上馨欣喜地称之为“大正新时代之天佑”。(4)井上馨侯伝記編纂会編:《世外井上公伝》第五巻,東京:原書房,1968年,第367頁。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径直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不但谋求山东和“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更欲控制整个中国,但这一要求遭到了中国与美、英等国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完全实施。继大隈内阁而成立的寺内正毅内阁认为这种“赤裸裸地强迫中国接受”(5)鈴木武雄監修:《西原借款資料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第168頁。的侵华政策难以奏效,遂以“大战景气”为支撑,在经济上推行投机性的“日元外交”,通过西原龟三向中国段祺瑞内阁提供了8笔共计1亿4500万日元的西原借款,攫夺了银行、电信、铁路、森林、金矿等广泛利权。(6)孙志鹏:《西原借款述评》,《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
一战末期,日本外交在国内陷入内争困境,在国际上面临被“孤立”和“围剿”的危险。国内:外务省、政友会、横滨正金银行、大仓组等势力集团,不满于寺内内阁以大藏省和三银行(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为主轴的对华借款政策,不但对后期的西原借款谈判进行抵制,而且暗中策划以政友会为中心实现政权更替,寺内内阁的“日元外交”将走入穷途末路。国际:俄国出现十月革命,主张废除秘密外交,以往与日本共同“防卫满蒙”的日俄密约面临崩溃;大战行将结束,美、英、法等国将改变“无暇东顾”的局面,势必回归中国,强化在华利权,日本将失去“独霸”中国的有利局面;自大隈内阁提出对华“二十一条”后,中国国内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增长,国民对于即将召开的战后和平会议报以殷切期待,欲借参会之机,废除外国在华特权,(7)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42页。日本自不免于外。
1918年9月29日,以政友会为中心的原敬内阁成立,但就在前一天,即寺内内阁的最后一天,在东京,日本三银行与章宗祥一口气签订了三份合计6000万日元的铁路和参战借款合同。寺内内阁利用对华借款进行经济扩张的政策,反而是在其任期最后一天达到了顶峰,不得不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也充分反映了日本在一战结束前企图大捞一笔的投机心理。作为首届民党内阁,原敬所面临的第一个外交考验即是如何对藩阀派“超然内阁”的外交遗产进行善后,其核心便是西原借款。10月10日,被寺内内阁看好的中国代理人段祺瑞,在直系和奉系的联合反对中被迫辞去总理职务,寺内内阁的援段政策再次遭遇挫折,设想中的“日中亲善”前景黯淡,日本即将面对一战以来最大的外交困境。
就在段祺瑞下野的当天,芳泽谦吉(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立即向内田康哉(外务大臣)提出了一份预防性的报告,叙说西原借款的大致成立过程,特别指出因其政治性质,已经引起国内外之非议,同时为了撇清日本驻华使馆人员的责任,刻意强调驻华使馆并未积极参与借款,前内阁“对于借款之事仅仅是通知使馆而已”;同时,芳泽指出,过去的借款仅以曹汝霖一人为商议对象,虽然曹氏“最近作为机敏的青年政治家闻名于中央政界”,但其势力只不过是北洋派之一部,况且随着今日之政权更迭,曹氏目前是否能维持自身势力尚未可知,一旦失势,借款之前途令人担忧,日本必须预先采取善后方针加以应对。(8)《西原氏関与ノ対中国借款ハ其性格ニ鑑ミ曹財政總長失脚ノ場合之ガ善後措置至難ナルベキ旨予メ稟申ノ件》(1918年10月10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七年第二冊下巻,東京:外務省,1969年,第934—935頁。可见,作为在华第一线的外务省驻外官员,芳泽敏锐地感觉到过分依靠个人关系与秘密手段成立的西原借款,不但存在资金回收困难的可能,还会引发国际舆论的非难,所以提请内阁预备善后之策。原敬在最初投身新闻界之时,就鉴于西方之经济、工业实力,主张日本应和欧洲列强保持密切关系,投身政界后又见识到美国的实力,尤其是充分认识到美国在一战期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1918年夏就预言“战后的世界属于英美”(9)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4,東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第412頁。,故而料想日本绝难再有一战这种“天佑”良机,再加上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动,修改前内阁的对华借款方针乃成自然之势。
二、主动协调:修改对华方针和取消两大借款
根据芳泽的报告,1918年10月19日,在外务省官邸,首相原敬召集各大臣协商西原借款善后事宜,议决了今后日本对华借款的基本原则与西原借款的具体处理意见。
关于前者,确定了“不再以实业借款之名进行政治借款,避免以借款助长中国内乱之非议”。关于后者,涉及四类借款:关于吉黑林矿借款,因俄国已经依据日俄协约提出抗议,日本应尽快对俄解释,将其变成“日俄间的共同事业”,即尽量不触犯日俄协约,与俄国一起维持“满蒙利权”;关于铁路借款,首先应使外务省与大藏省协商一致,尽快促成具有国防战略之吉会铁路正式契约的签订,其次利用“满蒙”四铁路与山东二铁路垫款尚未支付完毕的机会,先选择开原—海龙线、济南—顺德线与中国政府缔结正式契约,再依次建设;关于制铁厂借款,该契约尚未签字,今后方针是尽快打破中国的铁矿国有主义;关于币制借款,应立即促使中国政府中止“金券条例”,重返币制借款的正常渠道。(10)《対支借款跡始末ニ関スル方針要綱》(1918年10月19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七年第二冊下巻,第936—938頁。这一“要纲”可视为原敬内阁西原借款善后策的最初形态,其中既有对西原借款积极赞同者,如铁路借款;亦有暂时观望者,如吉黑林矿借款;更有方针不甚明了者,如制铁厂借款;还有积极反对者,如币制借款。可见,原敬内阁对西原借款已经签订合同的部分,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反对态度,仅对尚在协议中的但明显触犯欧美在华利益的币制改革借款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反对态度,而对在西原龟三和曹汝霖间签订了草合同的制铁厂借款(11)山本四郎編:《西原亀三日記》,京都:京都女子大学,1983年,第270頁。只是提出保留意见。
10月29日,原敬内阁正式通过《对华借款善后备忘录》,明确了新的对华借款方针。其宗旨是:“对华借款会招致列强猜疑,进而在大局上不利于帝国的对华立场;若只援助中国政界的一部分势力,会存在因这一势力的消长而立即对借款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危险,对这一切都要避免。”(12)《対支借款善後ニ関スル覚書》(1918年10月29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七年第二冊下巻,第946頁。随后加以具体说明,准备规避一切助长中国内乱的借款,不再以实业借款为名进行政治借款,避免与列国的冲突。
此外,寺内内阁时期“朝鲜组”(首相寺内正毅、藏相胜田主记、密使西原龟三)为了垄断对华借款,特意提高了大藏大臣的对外借款权限,同时专设了大藏省驻外财务官,直接受大藏大臣指挥,目的在于弱化原本属于外务省及其驻外使馆的借款参与权,直接且迅速地贯彻秘密借款政策,多数借款只是在签字后根据程序通知驻华使馆备案而已,俨然无视外务省的外交权能。为了避免大藏省对外务省权限的挤压,防止“二重外交”体制重演,原敬内阁在修改对华借款方针的同时,通过修改驻外财务官制度、厘定外务省与大藏省的机构功能,重新确立了外务省中心主义,谋求日本外交渠道的统一。
在10月19日的《要纲》中明确指出:“今后特殊银行团进行与西原相关借款的交涉,必须事先与外务和大藏两省协商。”(13)《対支借款跡始末ニ関スル方針要綱》(1918年10月19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七年第二冊下巻,第938頁。此外,在驻华财务官小林丑三郎向新任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所提出的电文后,特意批注:“(1)列国在中国的角逐,从领土获得主义到铁路铺设主义,从铁路铺设主义到铁路借款主义,从铁路借款主义到普通借款主义,不断变迁。……鉴于我国对华外交的演变,对华借款作为我国外交的重要部分,绝不可将之委任于财务官一人之手。(2)公使馆与财务官并非对等的机构,财务官附属于公使馆,需按照公使的方针意图开展工作。”(14)《対支借款方針ノ件》(1918年10月28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七年第二冊下巻,第946頁。
在这份电文中,小林还回顾了中国政府公布“金券条例”后引发的抗议问题,虽然日方认为抗议背后有梁士诒(旧交通系)联合芮恩施(美国驻华公使)合谋排斥曹汝霖(新交通系)的政争因素,但在英、法、俄、美共同反对币制借款一事上也不得不退让。因为,币制借款优先权一直为国际银行团所拥有,正如英国舆论所言:“日本为中国发行金券提供了大宗借款,违反了善后借款协定”,让“门户开放”失去意义。(15)《日本ノ対中国借款ヲ非難スル北京通信ニ関スル在倫敦森財務官来電送付ノ件》(1918年10月22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七年第二冊下巻,第942—943頁。日本与中国秘密商议币制借款触犯了列国既得利益,加之该借款尚未签约,原敬内阁最先主动否定的就是币制改革借款。这是原敬鉴于美国对日“不信任”并试图修复日美关系的一种缓和手段。(16)塚本英樹:《日本の対中国借款政策と幣制改革:第二次改革借款と幣制改革借款併合問題》,《日本歴史》2014年10月号,第63頁。
随后,收缩西原借款的焦点就集中在制铁厂借款之上。11月8日,山本达熊(农商务大臣)向原敬提出制铁厂借款的处理意见,要点有三:(1)日本铁矿贫乏,中国铁矿储量丰富,中国可作为日本的铁矿供应国,但当前急务是促使中国取消铁矿国有主义,而非急于对华借款;(2)借款草合同中未载明具体的矿山区域,也未明确借款用途的监督方式,将来都会产生弊端;(3)设立制铁厂与开发矿山周期都很长,中国短时间内能否向日本提供大量铁矿尚属未知之数。(17)《支那製鉄廠ニ対スル借款契約ニ関スル意見》(1918年11月8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七年第二冊下巻,第948—949頁。12月24日,阁议通过制铁厂借款案,指明:“关于本年9月17日阁议决定中国设立制铁厂借款一案,不仅在前内阁时代日中秘密交涉期间未能达成协议,而且鉴于和各方面的关系,从全局着眼,该案对日本并非有利,中国方面也没有准备重开谈判,望暂时停止。”(18)《中国製鉄所設立借款案ニ関スル件》(1918年12月24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東京:原書房,1965年,第477—478頁。虽然西原和曹汝霖已经在四个月前签订了制铁厂借款草合同,而且控制中国的制铁工业和铁矿供应也一直是日本的侵华计划之一,但是原敬内阁在经过如上“广泛”而“慎重”的考虑之后,为了得到更加切实的利益并与列国维持“协调”,最终不得不“忍痛割爱”,主动中止了制铁厂借款。
鉴于一战后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动,为了防止日本变成“孤岛”,原敬内阁在成立后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以作为西原借款基本构想(19)孙志鹏:《二重外交与西原借款基本构想的挫折》,《东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4期。的两大借款为中心,对前内阁的对华借款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希望借此赢得国际舆论的好感,摆脱日本“独霸”中国的外交形象,以便被列国重新接纳。
三、顺势扩张:延续参战借款和推进借款利权交涉
原敬内阁虽然在对华借款总方针上做出了“协调”的姿态,在具体政策上取消了西原借款的两大借款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敬内阁对华外交政策的全面收束。若将原敬内阁对已经签字的西原借款的善后方针与此作一体观瞻,便可明了原敬内阁在与列国有利益牵绊的借款上进行主动协调之外,暗中却积极推进日本在西原借款中的既得利权,即一面攻击寺内内阁对华政策之失败标榜“协调”外交,另一面却将寺内内阁从中国劫取的利权敛入囊中。从逻辑上看,这一政策正是大隈内阁以降日本侵华政策之延长线,可谓顺势扩张。
参战借款成立以降,便招致各种责难,芳泽谦吉亦在前述报告中特别注明:“本借款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从实际上来讲,纯粹是政治借款,四国银行团有理由提出抗议,显而易见将来会导致国际舆论非议。”如果按照原敬内阁协调主义的新对华借款方针,参战借款属于应该被立即取消或暂停的借款,但在10月29日的阁议通报中却有如下说明:“陆军大臣(田中义一)认为二千万日元的参战借款,系按照其用途监督的方法严格执行,故作为例外。”(20)《対中国借款善後方針ニ関スル閣議決定通報ノ件》(1918年10月29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七年第二冊下巻,第947頁。无论是作为平民出身的宰相,还是作为以民党力量成立的内阁,二者依然缺乏对日本陆军事务的发言权,20年代日本的“协调外交”或“币原外交”最终被“自主外交”或“田中外交”所取代,正肇因于此。无论如何,原敬内阁在实际上延续了寺内内阁的援段政策。
如果说延续参战借款是原敬内阁迫于陆军的压力,那么在吉黑林矿借款问题上,则完全展现出原敬内阁顺势对华扩张的政策底流。在10月19日“要纲”中,吉黑林矿借款因日俄协约之故,采取了暂时观望的对策。11月11日的三省协商中,延续了这一决定,即:虽然日俄协约将来有可能被废止,但就目前而言,还不可让列国认为日本有意趁俄国遇难之际图谋私利;小幡酉吉(驻华公使)若受到中方派遣林矿技师的催促,需采取迁延之策,暂停派遣。(21)《対中国借款問題ニ関スル外務大蔵及農商務三省会議ノ議事及決議ノ件》(1918年11月11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七年第二冊下巻,第953—954頁。原敬内阁此后一直遵循这一“协调”政策,但日本向来觊觎吉黑两省森林和金矿,此事并未结束。时至1921年4月,在“俄国国情变化和日本对俄关系突然改变”的情况下,便开始“积极地讲究本借款活用之途”“援助和指导两省的事业经营”,更投下事业资金,派遣调查班对两省的森林金矿进行“周密地调查”。(22)鈴木武雄監修:《西原借款資料研究》,第377—378頁。也就是说,当原敬内阁感觉不能通过日俄协约维持“满蒙”势力圈后,立即抛弃了日俄“协调”,采取了单独开发“北满”资源的策略。
另一个能够体现原敬内阁顺势扩张的案例是有线电信借款。该借款成立于1918年4月,日本通过该借款获得了中国全国有线电信的财产及其收入担保权,并有派遣技师监督指导中国有线电信事业改良的利权。由于2000万日元的电信借款绝大多数流用于军费和政费,(23)北村敬直編:《夢の七十余年——西原亀三自伝》,東京:平凡社,1965年,第185頁。投入电信事业者仅120万日元,电信改良事业自然搁浅。随后在该借款契约基础上,中国交通部与东亚兴业会社签订了1500万日元的第二次有线电信借款契约,架设了山东芝罘至上海的海底电线。(24)鈴木武雄監修:《西原借款資料研究》,第375—376頁。按照契约,日本对此线拥有监督权,掌控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可谓落实了寺内内阁时期电信借款所获之利权。
催促中国政府与日本尽快签订吉会铁路借款正式契约的谈判是原敬内阁最典型的顺势扩张表现。当初西原在与曹汝霖谈判吉会铁路借款期间,因奉行“日中亲善”,准备抛弃历来外国对华铁路借款之利权获得主义,“约定将一切积弊铲除,成一模范合同”(25)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3页。,故在预备借款契约上明确规定“准照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日订定之津浦铁路借款合同”(26)《交通部抄送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致财政部咨》(1918年6月22日),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六卷,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321页。,放弃了铁路会计和运输两主任的利权,仅保留推荐技师长的利权,这明显与日本一贯的对华铁路借款政策不符。有鉴于此,芳泽谦吉在前述报告中特意备注:“根据间岛条约的明文规定,吉会铁路的铺设方法应与吉长铁路一致,但该契约规定应与津浦铁路一致。……为了确保债权者的利益,今后要解决运输与会计两主任的聘用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吉会铁路是联结朝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横贯线,对于日本的大陆政策意义非凡,修建该路是日本陆军的一贯主张,原敬内阁亦深知此点,很早就做出了加快与中国谈判签订正式契约的决定。
1918年12月14日,根据外务省指令,芳泽谦吉向中国外交部部长陆徵祥提交了要求进行吉会铁路借款正式契约谈判的照会,同时会见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面陈此事。1919年1月8日,陆徵祥回复日本可以开始吉会铁路借款善后谈判,并选任交通部顾问权量为中方交涉委员。随后,自1919年1月2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开始,直至11月18日第十二次会议,中日间围绕会计和运输两主任聘用问题争执不下,即使小幡酉吉连续施压,“中国方面态度依然顽强”,其间又因五四运动之影响,中国反日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交通总长曹汝霖被迫辞职,中方任何谈判者都不敢甘冒“卖国贼”的风险。因此,日本在用尽一切手段都无法获取预期利权的情况下,1920年5月不得不宣布暂时停止谈判,留待日后解决。(27)鈴木武雄監修:《西原借款資料研究》,第379—389頁。“满蒙”四铁路和山东二铁路面临同样问题,随着吉会铁路借款谈判的暂停,两者亦随之中止。
虽然日本在极力推进的吉会铁路借款正式契约谈判上遭遇中国民族主义的抵抗而未能获得任何成果,但原敬内阁致力推进借款谈判本身就是对寺内内阁经济侵华政策之继承和顺延。正如内田康哉在回答众议院议员望月小太郎的质疑时所言:“前内阁所订借款之中,如山东铁路延长线、满蒙四铁路、吉会铁路等属实业借款者,如其用途真实则并无妨碍,现正在商订正约中。”(28)《預算委員会議録(速記)第六回》(1919年1月28日),衆議院事務局:《衆議院議事速記録》第41回,東京:大藏省印刷局,1919年,第75—76頁。即一反“协调”外交之阁议,延用寺内内阁之方法,借口“实业借款”,力求获得更加确实之铁路利权。
四、退守底线:围绕“满蒙除外”的日美博弈
巴黎和会期间,虽然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得到中国之追捧,奉为弱国外交新理念,但一战后“帝国主义”理念尚未褪色,日本凭借与英、法之间的秘密协定并以退出和会相威胁,逼迫美国最后在山东问题上不再支持中国,可以说美国在与日本的争锋中打了败仗。不过,美国并未就此收手,遏制日本的远东战略依然未变,随后即以新银行团为工具掣肘日本,上演了一场日美博弈的剧幕。
一战前,国际银行团曾规定“六国财团合同的条款不再适用于工业和铁路贷款”(29)《在东方汇理银行办事处举行的六国财团的会议记录》(1913年9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外债档案史料汇编》第2卷,1988年,第73页。,因此日本借此漏洞乘机推行西原借款,在华获得七条铁路(吉会铁路、山东二铁路、“满蒙”四铁路)之利权,超越英、美,成为中国铁路的最大债权者。美国对此形势十分了解,虽曾在1916年单独给中国大量贷款,但尚不及日本,且中国向美国商议借款时国际银行团便“从中作梗”(30)《顾维钧关于美组织新银团事致外交部函》(1918年7月21日),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一卷,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173页。,所以准备以组建新银行团的方式,在经济上牵制英、法并遏制日本。一战期间,日本曾向美国提议共同进行以烟酒税为担保的对华借款,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1864—1928)回复说:“美国政府希望合作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不含任何政治目的。”(31)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7,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7, p.121.对日本带有政治目的的借款防范有加。1917年11月,美国国务院决定首先组织新的美国银行团。(32)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7, p.153.1918年6月20日,兰辛向威尔逊建议由美国发起组建新的国际银行团,并特意强调在日本大举对华借款时,美国却没有任何贷款给予中国。(33)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8,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pp.169-170.两天后,兰辛致函美国银行家,建议美国的私立银行给中国贷款。7月8日,美国银行家向国务院提出加入四国财团(美、英、法、日)的前提条件是:“财团的成员应将他们现在享有的进行贷款的任何约定经营权让与中国或让与财团,并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对中国的一切贷款应被认为是四国财团的业务。”翌日,国务院复函:“本政府当竭力使这种放弃约定经营权的愿望能付诸实施。”(34)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8, pp.173-175.7月10日,兰辛向协约国发出组建新国际银行团的邀请,加入条件之一就是让出所有已经取得的对华借款优先权,将此作为新银行团的共同事业。美国此举正是针对日本假实业借款之名、行政治借款之实的贷款。(35)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8, p.187.
1919年3月,英国对美国的邀请表示同意,同时通知日本驻英大使:“英国政府已授权英国财团参与建议中的国际财团工作,并且对具有政府担保和所有今后公开发行的中国公债,不论其为工业方面的、行政方面的或财政方面的,保证给以全面的官方支持。”(36)《英国外交大臣寇仁勋爵致日本代办》(1919年3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外债档案史料汇编》第2卷,第105页。5月6日,外相内田康哉提议:“未来美国必然会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此乃大势所趋,日本不如就此加入新借款团,在对华投资上密切日美合作,在大局上将欧美的资本势力导向有利于我之方向才是上策。”(37)《米国提議ノ対中国新借款団ニ関スル件》(1919年),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八年第二冊上巻,東京:外務省,1970年,第234頁。5月11日,新四国银行团在巴黎议决了总体方针,正式确认了其成员需要让出借款优先权和约定经营权。5月20日,日本同意加入新银行团,但强调:“日本对满蒙具有地理和历史上的特殊感情及利害关系。上述关系不仅多次为英、美、俄、法各国所承认,而且在签署现今之借款团规章时,我也提出过保留满蒙之事,所以想排除在满蒙新借款团之外。”(38)《米国提議ノ対中国新借款団ニ関スル件》(1919年),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八年第二冊上巻,第245—246頁。即加入新银行团的前提是要保证“满蒙除外”。同日,内田康哉指示驻法大使松井庆四郎:“关于山东、福建,不必持保留意见,可赞同美国之意见”,“关于满蒙问题,必须明示我方主张”。(39)《米国提議ノ対中国新借款団ニ関スル件》(1919年),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八年第二冊上巻,第247、266頁。正如臼井胜美所言,日本这是在和英美做交易:“即使最后牺牲了山东、福建,也可通过英国等国势力圈的开放,在整个中国扩展经济活动。”(40)臼井勝美:《日本と中国:大正時代》,東京:原書房,1972年,第164頁。6月18日,日本正式向英、美、法三国提出了“满蒙除外”的要求。
对日本的提议,三国财团均表示异议。英国认为日本的要求会“在其他国家引起类似要求的复活”(41)《英国外交部给日本大使的备忘录》(1919年8月11日),上海市档案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外债档案史料汇编》第2卷,第144页。,如法国对中国西南部、英国对长江流域的除外要求等。这显然违背了新银行团“用相互合并优先权和取舍权的办法来消除在中国的一切特殊的利益范围”(42)弗雷德里克·V·斐尔德:《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吕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28页。的提议。美国甚至提议排除日本,由美、英、法三国组建新银行团。(43)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9, pp.454-455.面对三国的压力,日本内部出现了意见对立:一是主张加入新银团,挽回一战后日本的孤立地位,“区区满蒙问题,要在实力竞争之如何,此时无条件加入可也”;二是坚持“满蒙除外”,认为美国成立新银行团之真正意图,“在置中国于国际管理,在日本自无利益”。(44)《国务院关于日本当局对新银团分为两派致财政部公函》(1919年8月20日),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卷,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192页。最终“国是论”占了上风,日本依然坚持“满蒙除外”,并于8月27日将此意见转告美国。(45)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9, Volume I, 1919, pp.454-455.
11月20日,英国提醒日本:“如果作为领土上的要求,英国政府不能接受将南满和内蒙古东部排除在西方财团的活动范围以外的要求”,日本在内蒙古东部的“南面边界实际上已将北京包围,并侵占了直隶省”。(46)《英国外交部给日本大使的备忘录》(1919年11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外债档案史料汇编》第2卷,第145—146页。1920年3月16日,美国国务院回复日本大使:“为日本经济与政治上安全之故,谓洮南至热河之铁路以及其通海之支线,必须由日本独自建筑掌管,则美国政府实有未能遽信者矣。”(47)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0, Volume I,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0, p.513.同日,日本向英国提出“满蒙除外”的三条说贴,第三条指出:“吉会铁路、郑洮铁路、长洮铁路、开吉铁路、洮热铁路及由洮热铁路之一点至一海口之铁路,或为南满铁路之支线,或为南满铁路之挹注线;且此等路线不特与日本之国防有重要关系,抑亦在维持远东之治安与秩序为一有力之要素。”(48)《日本大使致寇臣伯爵节略》(1920年3月16日),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卷,第214—215页。3月21日,英国再次强调:上述保留条件第三条所提位于南满铁路以西的三条铁路,英国政府不能相信必须由日本单独建筑和加以控制,规定特别区域,必致发生各国承认利益范围之说。因美英与日本各不相让,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不过,尽管英国人认为“日本人毫无疑问怀有对中东路、东蒙和北满的企图”(49)《蓝普森致寇松》(1920年4月5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二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99页。,同时却指出“南满”与朝鲜毗邻,一直被日本视为重要地区,英美可在此对日让步,但内蒙古必须从保留条件中删除。美国虽然不愿接受这种地区性“领土例外”的保留,但也准备做出一些让步。
在历次交涉谈判中,日本感受到美、英的坚持力度和强大的外交压力,为了维护“协调”外交的大局,也不再坚持“概括主义”(50)服部龍二:《東アジア国際環境の変動と日本外交:1918—1931》,東京:有斐閣,2001年,第20頁。的“满蒙除外”。1920年5月11日,日本在得到“新银行团决不致有侵害日本国防与其经济生存之任何行动”的保证下,最终同意以“列记主义”的方式,有条件地让出“满蒙”地区的两条铁路线,即一直为美、英所反对之深入“东蒙”和华北的“洮热线”和“洮热线间一点至某海港”的铁路,并在此基础上加入新银行团。(51)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0, pp.556-557.9月8日,新四国银行团正式成立。此后,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中日间缔结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其中规定:“关于青岛济南铁路二延长线之让予权,即济顺线、高徐线,应令开放为国际财团共同动作,由中国政府自行与该团协商条件。”(52)《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政府公报》第2251号,1922年6月9日,第7页。
可以说,美国通过成立新银行团和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先后逼迫日本在“东蒙”和山东地区让渡了通过投机性的西原借款劫得的四条主要铁路线,基本上达到了在远东遏制日本扩张的战略目标,为巴黎和会期间的败仗扳回一局。另一方面,日本不得不在“协调外交”的名义下退守底线,仅保留了西原借款中的吉会线、长洮线、吉开线三条铁路,勉强保住了“南满”这一传统势力范围,吐出了在大战期间以趁火打劫方式获得的诸多利权。这也说明,20世纪20年代日本所谓的“协调”外交路线,与美国的亚太政策尤其是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根底上是水火难容的,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极限。(53)周颂伦:《战前日本协调外交遭遇困境原因探析》,《北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综上所述,从原敬内阁的西原借款善后策中可以看出,鉴于一战后日本面临的外交困境,原敬内阁通过修改对华借款方针、取消作为西原借款基本构想的两大借款等方式展现出与列国主动协调的一面,同时却在延续参战借款、独自开发吉黑两省林矿、续签电信借款合同、推进吉会铁路借款谈判中凸显了其顺势扩张的政策底流。美国为了维持远东均势,采取了伙同英国遏制日本的战略,以组建新银行团和召开华盛顿会议的方式逼迫日本节节退让,最终使日本不得不采取退守底线之策。在三方博弈过程中,当日本让出山东、福建甚至“东蒙”而退守“南满”并声称绝不可再让时,美、英对日本的遏制战略也在“南满”边界戛然而止。可见,一战后日、美、英三国共享的对华外交政策思维正是“势力圈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