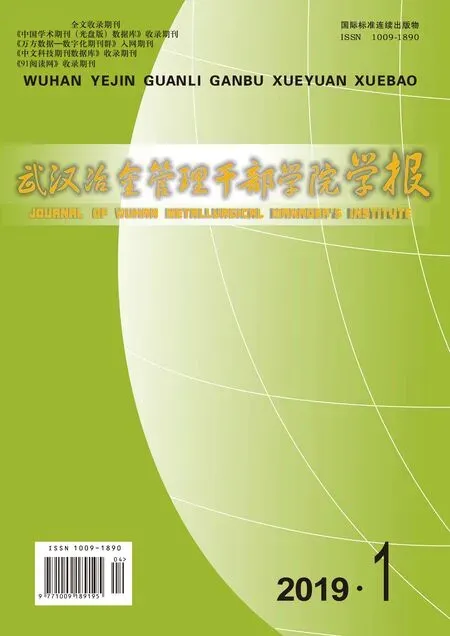论生态破坏侵权的法律属性
2019-12-26程奕翔
程奕翔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我国于2009年修订后的《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中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014年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环境保护法》将污染环境与生态破坏两种行为并列规定,认为生态破坏不属于污染环境,而《侵权责任法》中只明确规定了环境污染行为属于环境侵权,并未提及生态破坏行为。
有的学者主张生态破坏侵权应属一般侵权,抽象的“生态破坏”不具备特殊侵权责任事实要求的相对确定范围;部分学者认为生态破坏侵权应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相关归责原则,但未在缘由及具体立法指导上达成普遍共识。
一、重新审视“生态破坏”的必要性
(一)立法对生态破坏的界定存在模糊
首先,在2015年开始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前十七条都在围绕着环境污染进行规定,而未提及生态破坏的具体适用法律;第十八条规定,本解释适用于审理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民事案件。对第十八条展开分析,“污染环境”与“破坏生态”之间所使用的是顿号,通常适用于并列词语之间或者某些序次语之后的停顿。因此,可得知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民事案件可适用本解释,但如何具体适用、是否应当完全按照因污染环境行为提起的诉讼而适用无过错责任等制度尚无从知晓。
其次,在2015年开始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多个条款都将污染环境行为与生态破坏行为一并列出,规定适用相同的规则。但以上条款中均无影响案件归责原则的实质性规定,对于是否都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因果关系推定等制度并未明晰。
同时,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制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法的注释法典中,对于《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注释也仅提到了环境污染的相关内容,而未提及生态破坏行为是否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
最后,在适用于当前司法实践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侵权责任纠纷部分并未提及生态破坏侵权,而仅是对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进行了规定和细化分类。尽管法院不得以当事人的诉请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没有相应案由可以适用为由便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但从该规定中也无法得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生态破坏侵权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的具体意见。
(二)司法实践中对生态破坏的认识存在分歧与困扰
结合民事案件的案由规定,并通过初步检索发现实务中常将生态破坏侵权责任纠纷归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由后,笔者最终以“生态破坏”、“民事案由”、“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进行检索,共得到了43份裁判文书。通过查阅这43份裁判文书,笔者发现实务中存在规避认定生态破坏行为为侵权行为,而尽量以环境污染行为来认定侵权行为的情况。同时,“生态破坏行为”出现在裁判文书中的次数也远远低于“环境污染行为”。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环境污染行为较生态破坏行为的定义更加明晰、更易判断,且《侵权责任法》未明确规定生态破坏侵权属于环境侵权的缘故。
此外,人民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对于生态破坏侵权常适用与环境污染侵权相同的归责原则,但普遍将案由直接确定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如在陈江鹏与陕西中能煤田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示了生态破坏行为造成损害的侵权责任纠纷应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相关规定,该案中所发生的损害是由于生态破坏行为所造成,案由应确定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在杨乐村三组与重庆龙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为《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第三级案由;本案中双方发生之法律关系的内容为:被申请人龙珠电力公司修建或扩建水电站,申请人认为该行为导致生态环境破坏造成损害,主张龙珠电力公司清除倾倒在涪江中的渣土、修建永久性防洪堤、赔偿杨乐村三组因修建水电站导致1998年洪水冲毁杨乐村三组耕地的损失及利息。由于目前并没有生态破坏纠纷的案由,一、二审法院根据法律关系性质和诉求,确定本案案由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并无不当。”
笔者赞同人民法院对于生态破坏侵权适用与环境污染侵权相同归责原则的做法,但认为人民法院将生态破坏侵权的案由直接确定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的做法有误。依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以及《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对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并列规定,生态破坏责任纠纷不属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不应归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由下,而应适用作为二级案由的侵权责任纠纷。
综合上述内容可得知,立法对于生态破坏的模糊界定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于生态破坏认识的分歧与困扰,明晰生态破坏侵权行为的定性及其相应的归责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二、生态破坏侵权的定性
(一)生态破坏的定义
有的学者称生态破坏为环境破坏,是指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自然环境,过量地向环境索取物质和能量,使得自然环境的恢复和增值能力受到破坏的现象;或指人类不适当地开发利用环境,致使环境效能受到破坏或降低,从而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事实。有的学者认为生态破坏是指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环境的一个或数个要素,过量或不适当地向环境索取物质和能量,使它们的数量减少、质量降低,以致破坏或降低其环境效能、生态失衡、资源枯竭而危及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现象。
在上述学者们所下定义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生态破坏应指人类不合理或不适当的开发利用环境,以致环境效能遭到破坏或降低,从而危及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现象。而对于行为人故意破坏生态环境,而无开发利用环境的主观目的的行为,属于当然的生态破坏行为。
(二)生态破坏侵权应作为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
有的学者认为,行为人破坏生态的行为应属于污染行为的一种。对此,笔者并不认同,生态破坏相对于环境污染,在行为特征上具有显著的区别。
1.生态破坏行为的形式更多样
环境污染行为通常是向外界排放一定的物质或能量;而生态破坏行为的形式和方式多种多样,如采伐森林、开采煤矿、开垦荒地等等,常常表现为对环境中物质或能量的获取与采集。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环境污染行为区别于生态破坏行为的本质特征。
2.生态破坏行为的致害过程更加复杂
因环境污染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无须建立在对环境造成损害的基础上,该行为所排放的污染物可以直接经由环境媒介到达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暴露点,进而对受害人人身或财产利益造成损害;而生态破坏行为首先要对于生态造成破坏,进而才能影响到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利益。在无环境损害的前提下,生态破坏行为不可能对他人造成损害。将生态破坏行为直接视为环境污染行为,实则是忽视了生态破坏行为对于社会公共利益侵害的必然性。
3.生态破坏行为后果更易预测
环境污染行为往往是对于已知技术使用而产生的未知后果,而部分生态破坏行为却是对已知自然生态规律的违背,行为人有更大的可能性可以预知到自己行为的危害后果。故生态破坏行为人对于损害后果发生的故意或过失心态往往较环境污染行为人更大,且受害人也更易判断危害后果的发生可能性,采取预防措施以阻止危害后果的发生或降低严重程度。
4.生态破坏行为的救济主体存在缺失
环境污染行为都有直接的受害人,可由受害人自行提起诉讼、寻求救济;而生态破坏行为在仅造成了环境生态破坏、无直接受害人时,缺少了受害人这一在侵权责任纠纷中关键的救济主体。
因此,鉴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在各个方面的显著差异,不应将生态破坏行为纳入环境污染行为的种概念,生态破坏侵权应作为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
(三)生态破坏侵权与环境污染侵权存在一定关联性
生态破坏侵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其与环境污染侵权都是环境侵权的具体行为方式,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关联。
1.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可以互为因果
生态破坏行为与环境污染行为同样都会对于环境造成损害。因此,严重的环境污染行为可以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导致生态破坏现象的出现;生态破坏行为可以降低自然界的自净能力,从而导致环境污染行为结果的加剧。
2.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都可对于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环境污染行为存在对于环境先造成污染,进而间接对于受害人人身或财产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此时的环境污染行为便已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生态破坏行为对于个人利益造成的损害的前提便是已对于环境造成了损害。因此,上述两种行为均可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3.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具有相对一致性
生态破坏行为的最终结果是导致生态遭到破坏,而环境污染行为的最终结果是导致环境遭到污染。因此,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都同时作为了其行为的形式与最终导致的结果,二者具有相对一致性。
三、生态破坏侵权应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相关归责原则
(一)生态破坏侵权不应适用一般侵权的归责原则
有的学者认为生态破坏侵权应适用一般侵权归责原则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将《环境保护法》与《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表述作同一理解,有利于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且2015年开始施行的《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一条也强调了只有环境污染行为才可以构成环境侵权;第二,“生态破坏”存在难以抽象共性标准的问题。
对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并不成立。
首先,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可得知,解释与适用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应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2014年发布的《环境保护法》与2009年发布的《侵权责任法》同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前者较后者属于新法,且为适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特别法。出于维护法律体系协调统一的目的,应以《环境保护法》第64条的规定为准,将《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环境侵权事实扩大解释为环境污染行为和生态破坏行为。
其次,在2015年开始适用的《环境侵权司法解释》中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了该解释适用于审理因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民事案件,其第一条也并未规定只有环境污染行为才可构成环境侵权。
最后,生态破坏相较于环境污染,前者的行为形式与致害过程确比后者更为复杂多样,难以抽象共性标准。但正是因此,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地位不平等时,受害人一方会更加难以证明因果关系、加害人过错的存在,更加需要法律的倾斜保护,而并非回归一般侵权的归责原则。至于对生态破坏行为的判断,则可借助相关学科知识及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来加以解决。
(二)生态破坏侵权应适用与环境污染侵权相同的归责原则
生态破坏侵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其与环境污染侵权之间存在的关联使得生态破坏侵权具备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相关归责原则的基础。
首先,在生态破坏侵权中也存在着双方地位不平等的情况。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经常在信息掌控、经济实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环境污染侵权中对于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需求同样存在。
其次,生态破坏中也存在“合法破坏”现象,可能对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如森林采伐行为,只需获得相关的行政许可,即可合法的对树林进行采伐。但该行为也可能对于生态造成破坏,进而损害相关当事人的人身或财产利益,需要无过错责任制度的适用。若不适用,将出现加害人因其生态破坏行为获取了较大经济利益,却不需要对其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违背民法上公平原则的情况。同时,为减少“合法生态破坏”侵权之诉的出现,提高司法效率,有关行政机关在给予行政许可时便应要求申请人对未来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提供预案或补偿措施,并在之后严格监督申请人对相关预案或补偿措施进行落实。
再者,在最高法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发布前的司法实践中,生态破坏类案件与环境污染类案件的裁判之间也存在共性,两者都强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恪守现行的诉讼时效;且2014年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第64条已将《侵权责任法》第65条所适用的原因行为范围扩大为了“污染环境行为”和“破坏生态行为”两类。
最后,对于尚未造成个人人身或财产损害,仅对社会公益造成损害的生态破坏侵权,也同样应适用与环境污染侵权相同的归责原则。此类案件中同样存在上述“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合法破坏”等情况,与已造成个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生态破坏侵权的不同之处仅主要在于救济主体的缺失,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已经解决了该问题。此时的环境公益诉讼,也恰恰符合相关学者所提出的环境公益诉讼不宜涉及任何私益的要求。
四、结语
为解决当前立法对于生态破坏行为性质的模糊界定所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生态破坏认识的分歧与困扰、维护法律规定之间的统一以及适用合理的生态破坏侵权归责原则,应将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视为并列的两种不同的环境侵害事实,并在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加以明确。同时,生态破坏侵权应作为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相关归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