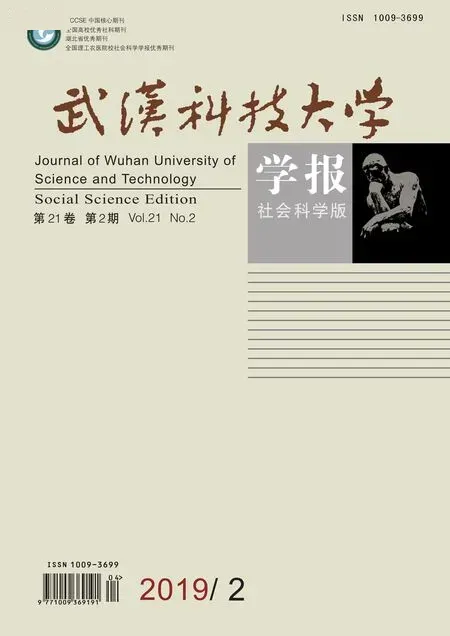后果最大化及其异议
2019-12-25龚群
龚 群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近代以来的道德理论,将行为的道德评价看成是道德实践的首要问题,而一个行为的道德地位即正确或错误、好或坏是由动机或行为过程中的规则或行为后果所决定的吗?一般认为,行为的道德地位或对行为的道德评价仅仅取决于行为的后果,我们称之为后果主义的道德理论。不过,由于后果主义理论的发展,除了将行为的后果唯一地看成是行为道德地位的决定因素的行动功利主义(或称“行动后果主义”“直接后果主义”“简单后果主义”)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功利主义,如规则功利主义(或称之为“准则功利主义”“规则后果主义”)等。规则功利主义虽然也强调后果事态所具有的对于评价行为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认为规则在决定行为后果的内在价值意义上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而行动功利主义在后果最大化方面也具有典型性,因此,我们在此的讨论也主要集中于行动后果主义。
一、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
行动功利主义(act utilitarianism)是布兰特(Richard B. Brandt)最先提出,布兰特认为,行动功利主义“大致是这样一个观点:行为者的责任(在客观意义上)在于,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履行一个特定的行为,当且仅当履行这样一个将(实际或可能)产生一种意识到的事态,这个事态与行为者可能履行的其他行为相比较,将产生最大化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worth)”[1]。也就是说,行动功利主义认为一个行为者的客观责任就在于履行将实际产生可意识到的最大化内在价值的事态。斯马特(J.J. C. Smart)是当代重要的行动功利主义者,他在《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Utilitarianism:ForandAgainst)一书中,对于行动功利主义的界定是:“大致地说,行动功利主义是这样的观点:一个行动(an action)全部的好或坏唯一地依据它的后果,即该行动对全人类的存在者(或一切有知觉的存在者)的福利(welfare)产生的效果(effect)。”[2]4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斯马特的定义将人类行为实践者的任何一个行为的后果都与全人类所有存在者的福祉联系起来,从而提出了一个与古典功利主义不同的后果论概念,在边沁(Jeremy Bentham)等古典功利主义者那里,一个行为后果的好与坏,主要是看这个行为对自己将产生怎样的苦与乐的后果。斯马特强调:“为了建立一种规范的伦理学体系,功利主义必须诉诸他与其对话的其他人共同持有的根本态度,他诉诸的情感是可普遍化的仁爱(generalized benevolence);即寻求幸福的意向,或无论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寻求对所有人类或对所有有感觉的存在者而言的好的后果。”[2]7这里的“好的后果”是在两方面的意义上来讲的:一是好的最大化后果,如有A、B、C三种行动方案,A的后果价值为1000,B的后果价值为900,而C的后果价值为800,那么,我们应当选择的是最大化后果的A方案;二是最小化坏的后果,即在某些特定的处境或情境下,可能进行行动选择的方案,只有在较坏和最坏的后果中进行选择,如A、B、C三种方案,A不理想,B更不理想,而C最不理想,无论选择哪种方案,都可能产生不理想的结果,那么,我们应当选择那个带来坏结果最小的情境或行动方案A,也就是说,行动功利主义要求的是选择较坏而不是最坏的后果,实际上,在可比较的情形下,这也可以看作是最好的后果。斯马特所界定的行动后果主义,是当代后果主义讨论的基本出发点。
后果主义不仅仅是把行为后果看成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事态,而且把行为的正确与否或好与坏看成是其后果是否最大化好的后果。因此,后果主义一般又可看作是一种后果最大化的理论,这个“最大化”服从于“最大化价值的原则”,这也就是布兰特对行动功利主义的上述界定所表明的,行动后果所要求的是“最大化内在价值”,或者以公式化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一个行为应当被履行,当且仅当它的后果是内在地好于其他可选项时;一个行为是错的,当且仅当它在可选项中并不是比其他选项更好时。正如谢夫勒(Samuel Scheffler)所说:“行动后果主义要求,每一个行为者在所有的情形中,以这样的方式去产生他在那个情境中所能产生的最高序列的事态。”[3]1前面已述,最大化好的后果不仅可从最高序列或相比较的更多好的后果意义上讲,也可以从相对最小坏的后果意义上讲。换言之,后果主义对于行为正确与否或好与坏的判断,就看是否能够产生最大化好的后果和最小化坏的后果,当然,这样的选择仍然是有一个总体性背景(overall background)的。
斯马特从全球视域提出了一个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概念,辛格(Peter Singer)则把这个概念具体化了。1972年,辛格发表了著名的论文《饥荒、富裕和道德》(Famine,AffluenceandMorality)[4]。他写作这篇论文的背景是:1971年的孟加拉地区发生了饥荒,持续的贫困、飓风和内战使得孟加拉地区至少900万人口陷入极度贫困的难民状态之中,他们缺乏食品、住所和医疗救济。然而,生活在富裕国家的多数人对发生在远方的、如此众多人口的贫困和死亡却是无动于衷。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如此冷漠而没有道德义务感呢?辛格的观点是,距离产生了人们的冷漠感。辛格举了一个例子:一个路人路过一个池塘,有个小孩落水了,如果你不下池塘去援救,那么,那个小孩可能就会淹死,而你下池塘去援救,也不过就是会弄湿你的衣服。辛格认为,遇到像这样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任何有点道德义务感的人都会施以援手,他把这称之为“不牺牲任何可比较的道德重要性”[4]。这也好比是孟子在提出“四心说”中所说的例子:一个路人路过一个村庄,在村庄的路口上,有一个小孩正在井边玩耍,但他很有可能会爬到井边而且有掉进井里的危险。你看到这样的情景,你自然会施以援手,使那个孩子脱离危险。你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你要讨好这里的乡亲,也并非是你要讨好这个孩子的父母,因为你是外乡人,你并不认识谁,你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你的恻隐之心。辛格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只要这个世界上发生灾难或人们在遭受苦难、饥荒,那么,任何一个有点经济能力的人都有义务进行援救。辛格说:“如果我们有力量阻止某种坏的事情发生,因此并不牺牲任何可比较的道德重要性,在道德上,我们就应当这样做。”[4]他认为,相比较我们的衣服被弄湿了这件事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孩子的死是非常坏的一件事。
在后来几十年中关于后果主义后果最大化的讨论中,人们认为这是辛格所提出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从而也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案例。在辛格看来,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表明这个原则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辛格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按照这个原则来行事,那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甚至我们的世界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怎样理解这一点呢?在他看来,他只是提出了“不牺牲可比较的道德重要性”,而没有把距离问题放在里面。这是因为,虽然你是走在你看见的小孩落水的路边,因而你去救了他,但重要的不是你的距离,而是你没有牺牲可比较的重要性的东西,所以你才去救了他。他认为,无论是十尺距离远的邻居的小孩还是几千英里外的孟加拉的难民,这个原则都适用,或者说没有区别。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里的最大问题是距离问题,即他所举的例子是我们身边可能即将发生的不幸,而孟加拉的难民则是远在天边。他说:“某个人在物理意义上与我们接近,所以我们个人与他有接触这一事实,可能使我们更可能去帮助他,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只是应当帮助他而远离我们的人则不应当帮助。如果我们接受不偏不倚、可普遍化、平等或不论什么原则,我们就不应当歧视那些仅仅因为他离我们很远或我们离他很远的人。”[4]换言之,我们不应由于距离的原因而不去援助那些需要援助的人。假设我们所处的位置离那些穷人很远,而我们又不能亲自前往那些灾难发生的地区从而并不能判断那里的灾民或难民急需什么而不去帮助他们,辛格认为这是托词,尤其是在信息这么发达的全球化时代,并且,救援组织的专家不仅描述了那里的紧急情况,而且这些救援组织能够像你帮助你身边的人一样,把你所捐助的物资送到那些急需的人手里,因此,我们已经没有距离的理由来为这样的区别对待进行辩护。
辛格认为,也许这里还有第二个问题,即从众心理,并且这种心理会使得我们的义务感降低。即如果和我处于相同地位或处境中的他人并没有对那些处于危难中的人给予援救,我自己如果什么也没有做,那么也不会感到多么内疚。可以想像一下:假设在我路过那个小池塘时,旁边的路人都无动于衷,那么,如果我不去救那个落水的小孩,我可能也不会有多难受。辛格认为,人越多而义务越少这个观点很荒谬。换句话说,由于群众越多,我就越可以逃避责任或义务,持这种观点的人却没有看到,像穷困、污染这些问题每个人都是被平等地卷入其中,它并不会因为有了他人,我就没有责任,也不会因为有了他人,我就不会受到污染的危害。但是,从近年来我国所发生的道德冷漠、见死不救的事情来看,从众心理确实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辛格不认为人越多就越没有责任,他认为,这样的责任是人们所无法逃避的。面对孟加拉如此大量的难民,我们每个生活富足或家境宽裕的人都有责任。在他看来,假设我们富裕国家每个人为孟加拉难民捐赠5个英镑,那么,所有孟加拉难民的食物、住所和急需的药品都可以得到满足。而且,假设人人都一样,因此我没有义务捐赠比他人捐赠5个英镑更多。富裕国家的人只要捐赠5个英镑,这也就是辛格所说的“没有牺牲可比较的道德重要性”的捐赠。辛格认为,这只是一个假设的前提,虽然如果如此捐赠,结论肯定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假设的前提无疑是得不到满足的,因为不可能人人都为孟加拉难民捐赠5个英镑。那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因为只有少数人会像我那样捐赠5个英镑。但是,这样的结果也就意味着不可能提供足够的食物、药品给难民。而为了可以救助更多的难民,我们(有义务感的人)的捐赠就应多于5个英镑。那应当捐多少呢?辛格说:“那意味着处于相同处境中的每个人,应当尽可能多地捐赠,至少达到这样一个临界点:给予更多的捐赠将使得捐赠者以及他所抚养的人处于严重的苦难中,甚至超出这一点而到达边际效用点:在这里,给予更多捐赠将引起捐赠者和依靠他的人更大的苦难,如同他要阻止的发生在孟加拉那里的灾难一样。不过,假如每个人都这样做了,无疑将会比给那些难民带来的好处还多,当然这样某些牺牲就是不必要的。”[4]辛格从开始的“不牺牲可比较的重要性”论证到了只要是不因捐赠而过着难民般的日子,在道德上都是合理的。辛格在这里提出,现实地看,由于有的人并不会真正去捐赠那些处于危难中的人,因此,我们这些已经有了这种义务感、责任感的人就应当多捐赠,否则,像孟加拉难民的困境就不可能真正解除。在这个意义上,你最大化地帮助那些处于危机、苦难和死亡边缘的人,但你自己并没有因此而过着难民般的生活,因此,实现了后果的最大化。由此我们可知,辛格确实很好地诠释了斯马特的后果最大化概念。
不过,辛格自己也意识到了如果要捐赠到那个不至于使自己变成难民的临界点可能要求太高了,因为这可能会使得捐赠者和依靠捐赠者生活的人过着几乎像难民那样的生活。因此,辛格提出区分两种版本的义务原则:强版本和弱版本或更适中版本。强版本是:“要求我们阻止某些坏的事情发生,除非这样做我们将牺牲某些道德重要性的东西。而这似乎是要将我们(的生活)降到边际效用的水平。我也要说,强版本似乎对我来说是正确的。”弱版本或更适中的版本是:“我们应当阻止某种坏事发生,除非我们这样做,我们不得不牺牲某种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4]但这样讲与前面强版本的区别又在哪里呢?辛格说:“就更适中版本而言,它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自己降到边际效用的水平。”[4]“边际效用”是一个经济学用语,指的是对某种物品的消费量,每增加一个单位额外增加的满足程度。在边际效用中,自变量是某物的消费量,而因变量是满足程度或效用。所谓“降到边际效用的水平”,即边际效用达到最大化之后,不再产生边际效用。如10 000元的资金,对于某个百万富翁来说,他自己消费它产生一种边际效用,假设是10,但如果捐赠给10个难民,使得他们能够摆脱饥饿甚至死亡,那么,这个边际效用可能是10 000,即自己消费的1000倍。然而,如果要我将我的资产全部捐出,那意味着我要成为难民,从而我的边际效用成为了负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合理的。即使是要我一次性捐赠10万元,也将影响到我平时的偏好性消费,如我不能再去打保龄球或高尔夫球,因而我的消费的边际效用就下降了。辛格这里讲到两种版本的捐赠,都是以边际效用为标准,前者降到边际效用的水平,使得自己的可捐赠资金的边际效用达到最大化,即最大化的捐赠,而后者则是在不降低自己消费水平(不降低自己的边际效用)的前提下进行捐赠。换言之,所谓“牺牲某种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是因标准不同而不同的。只要我们感到因为自己的捐赠而将牺牲某种可比较的道德重要性的东西,那么,捐赠也就要停止。然而,即使是按照弱版本的原则去最大化我们的行动后果,辛格认为,我们的生活也将发生巨大变化,西方社会所追求的消费社会的生活速度就会降下来,甚至完全消失。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把金钱花费在那些琐碎的东西或品位的追求上,而不是去救助难民、帮助穷困者。在他看来,西方社会追求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本身的方向就错了,因此,除了保障自己的必要生活资金之外,其他的资金都应拿来救助处于危难或死亡边缘的人,全球贫困状态仍然很严峻①②,贫富差距巨大③。然而,无论是强版本还是弱版本的捐赠义务原则,都是辛格对当代人的过高要求,试看几十年来,富裕国家的富人们有多少做到了这样呢?
二、完整性异议
从全球视域来看待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既有拥护者,也有批评者,并且是招致了当代哲学界众多异议。首先,后果最大化是一个比较概念,即只有存在可比较的选项才能称之为是否最大化了。换言之,后果最大化也就意味着必须在行动前进行预先比较,如边沁就为后果最大化提出了苦乐计算,然而,如何才能做到在不同选项之间进行比较选择?因此,人们认为后果主义没有可操作性,从而导到自我挫败。其次,一个最重要的异议是完整性(integrity)异议。前文已经指出,后果主义的道德评价所要求的是,在可选行动的后果中,后果为最大化好或最小化的不好,这两者都可称之为“后果的最大化”。后果最大化是在什么维度上讲的呢?这就是“总体性背景”意义上,那么,什么是总体性背景呢?在这里,我们应当联系前文已述斯马特对行动功利主义的界定来讨论,事实上当代西方伦理学界也是从这个维度来讨论的,也就是说,最大化好的后果是从全人类一切存在者的福祉的维度来衡量或评价的。这样一种要求,被批评者称之为是一种严苛性(extreme)要求。以下案例,包含了后果主义的方法,也是人们对其批评所设的案例:
阿夫鲁特是发达国家的一个富裕公民,她已经给慈善机构进行了有意义的捐赠。她正坐在她的书桌前,桌上放着支票本。在她前面有两本小宣传册,一本是介绍有声誉的援助机构,另一本是当地剧院公司的。阿夫鲁特现有的钱,或者够捐赠给慈善机构,或者够买一张戏票,但不能两者都做。因为她喜欢戏剧,她买了票,虽然她知道,如果她把钱送给慈善机构,将产生更好的效果。[5]
从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要求来看,阿夫鲁特的决定和行为没有产生最大化好的后果,因而不是一个在道德上正确的行为,从后果主义的要求(demanding)来看,必须谴责阿夫鲁特的行为。批评者认为,后果主义的这个要求太严苛,它违背了我们的常识道德。从常识道德来看,人们有着自觉捐赠的义务,但同时也有着可以不捐赠的自由。慈善捐赠的行为不在应当履行的义务之列,而是超义务(the supererogatory)的行为。所谓“超义务”,即这样的行为是好的,但并非是常识道德上的必然要求。然而,如果把这样一类行为看成是在道德上必须履行的行为,如果不履行在道德上就是不正确的,这意味着我们把这类行为并不看成是超义务的。换言之,以后果主义最大化好的后果来要求,我们就取消了道德中对超义务的理解,或超义务也就不存在了。
再看一个案例:
我很想去看一部名为《世上最快的印安摩托》的电影。但考虑到其他人的贫穷和后果主义的要求,我很不情愿地把我用来看电影的钱捐赠给了慈善机构。第二天,我还是想去看这部电影,但又是同样的结果。我想去看这部电影已经好几年了,我是一个新西兰人,电影中的英雄是一个被视为偶像的新西兰人,他展示了传统新西兰人的品格。我正在修复一辆老沃克斯豪车,电影中有我很想看的关于老沃克斯豪车的镜头。但是,我仍然感到应当遵守道德,虽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进一步考虑了后果主义的要求,意识到修复一辆老沃克斯豪车需要很大一笔钱,于是我把车卖了,并把钱捐赠给了慈善机构。我还是一个园艺爱好者,这是体现我的创造力的主要地方,而且我很喜欢户外活动。但是这一活动花费很大。我又放弃了园艺活动,改种一点蔬菜。但是我意识到,一个更穷的人正在路边卖菜,因此,我又放弃了种菜。慢慢地我变得越来越可怜。[6]
对于这样的案例,即个人所具有的后果论特征,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是这样概括的:“考虑一下富人应当送给穷人到底多少的问题。对绝大多数后果论者而言,这个问题超越了国界。既然我知道其他绝大多数富人只会给出一点点,对我来说会难以否定;如果我几乎给出我的全部收入的话会更好。即使我给出了十分之九,但是所剩的那十分之一中的一些如果让非常贫穷的人享用的话,行善会更多。后果论于是告诉我,应该给出我的几乎所有的收入。”[7]④换言之,彻底的后果论者从所有资源的最大化好的后果考虑,当然也就是行善所救助的人越多越好。
这一案例和帕菲特的概括说明的是,后果论或许要求我们给出全部的钱财,要求我们成为一个纯粹的行善者,而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事事都按照后果主义的最大化好的后果要求来生活,那样,我们所有的生活计划都可能会被打乱,即我们生活或生活计划的“完整性”就被破坏了。针对后果主义的最大化好的要求的严苛性批评首先是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提出来的,而后来的人们对于后果主义的严苛要求问题,大多是从后果主义的严苛要求破坏了人们的生活计划从而破坏了人们的完整性这一进路来发问的。上述两个案例,就是批评后果主义严苛要求的不同著作中所举的案例,这样的案例可能是真实的,但也可能完全是一种思想实验,这一实验虽然并非是在生活实践中发生的,但却是符合逻辑的,即如果按照后果主义的严苛性要求来生活,则必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德莱夫(Julia Driver)说,当一个人本来可以喝更便宜的麦片粥而将省下的钱寄给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时,她却买了百吉饼做早餐,我们因此说她道德上是坏的或者说她做了道德上的坏事,那人们都会觉得这样说是荒谬的[8],但从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好的道德要求来看,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这样的严苛性要求,不仅是破坏了个人的完整性,而且也使得个人异化了,这种异化表现为行为者本人无法以他自己的生活计划来规划自己的生活。德莱夫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麦克很有爱心,非常关心他人,每年他都会把收入的25%捐赠给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以及其他慈善机构,以缓解世界上的苦难。麦克当然还可捐更多的钱。但捐更多的钱会给他的生活带来非常严重的消极后果,虽然如果他捐了更多的钱,他的生活还是会比那些他救助的人更好。而从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好的道德要求来看,麦克如果捐比现在他所捐更多的钱,这正是后果主义所要求他做的。
后果主义从行为后果对全人类存在者的总体效用(overall utility)来评价人的行为的道德意义和确立其道德地位,在于后果主义从一种非个人而不是从行为者的视域来进行价值评价,这也就是一种行为者中性价值(agent-neutral value)的立场。行为者中性价值立场又称“不偏不倚”(impartial)的价值立场。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对于价值评价,首先有一个在不同的位置(立场)进行评价的问题。当有人说事态A是好的或事态A比事态B好这类判断,这取决于判断者所处的位置(立场),这类似于某人某个时刻在地球的某个位置正在看日落时所发出的判断——“太阳正在落山”[9]。如果你不在那个时刻和地球的那个位置,你不会认同他的这个判断,但如果你也就在他身旁,那么,这个判断对于你和他都是适用的。在道德或价值判断中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A足球队与B足球队进行比赛,最后B队获胜,你因为是B队的球迷而发出你的判断:“B队获胜太好了!”这是因为你是从你的立场(位置)出发,如果你的同伴和你一样也是B队球迷,那么,他们也会认同你的判断;但如果有人是A队的球迷,他们可能会对这场球赛结果感到失望,而对你所发出的对B队的赞扬会感到愤怒,因为他们不认同你的判断。那么,有没有所有观察者或评价(判断)者都一致认同的评价或判断呢?像前面所说的那个“太阳正在落山”的判断,如果我们给出观察者的具体时间、地点,如“在秋天的北京时间下午六点,我在北京的香山,这时太阳正在落山”,也就是说,在地球的X点上,太阳正在落山,这是一个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态的确切的判断。对于这样一个判断,具有时间和太阳运行常识的所有人,都会同意这样一个观察判断⑤。阿玛蒂亚·森指出,在道德和价值判断中,不仅有在相比较意义上的、可比较的不同事态的好与坏的判断,而且也有大家都认同的判断,如“饥饿和巨大的痛苦不论发生在谁身上,对于任何评价者来说,都是道德负价值的事态”[9]。当我们说,痛苦和苦难发生在某个人身上,这是与行为者相关的(agent-relative)负价值,但当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件不论发生在谁身上都是一件坏事时,就不仅仅是因为发生在某些人身上,这里只是指事态的发生,而不论发生在任何行为者或行为主体身上,其道德性质都是一样。不像“行为者相关”的负价值涉及到对人的伤害,“行为者中性”(agent neutral,或译为“行为者中立”)的价值仅仅指这样一种不关涉到特定个人的价值或负价值。在这里,就排除了对于具体行为者的相关背景的参考而唯一考虑事态,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行为者中性”或“行为者中立”的评价。
行为者中性的价值评价是与行为者中心(agent-centred)的价值评价相对而言的。里奇(Michael Ridge)说:“行为者中立性的后果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所有价值是行为者中立性的,就是说,事态的价值是与特定的行为者不相关的,虽然这些行为者对于特定的事态来说都有着具体的关系。尤其是,一个价值是行为者中立性的,恰恰就是这种情形:在原则上,对于某个特定的行为者来说,这个价值没有不可取消的背景参照、没有任何具体的可参照的背景,而一个价值在原则上涉及到这样的背景则是行为者中心的。”[10]以斯马特对于后果主义后果最大化的定义来说,行为者中性的价值立场是一种以全人类的存在者而不是以某个特定的行为者为背景来评价事态。谢夫勒说:“功利主义从一种非个人的立场来评论世界状态,从而使得行为者与其对自己正在从事的行为计划和履行的承诺相异化。”[3]8如果发达国家的一个富裕公民阿夫鲁特是一个后果主义者,那么,她就应当将她那份钱捐赠给慈善救济机构,这样,她的钱就能够到达那些急需物质资源来解除饥饿的人的手中,因而也就能够帮助那些处于绝境中的人。然而,如果她还是把那份钱买了她喜欢看的戏的戏票,那么,从后果主义的道德观点看,这不是一次正确的行为。这是因为,后果主义的行为中性的道德评价,排除了所有的行为者本身的任何背景参照,而唯一地以行为对于全人类的所有存在者的福祉影响或效用来进行评价。对于喜欢“老沃克斯豪车”的“我”来说也是如此,从后果主义的行为者中性的评价原则来看,这个行为者几次放弃了对于自己来说有重要意义的计划,而将钱捐赠给了慈善救济机构,因而是最大化了这份资金的效用,从而在道德上是正确的。然而,这两个案例都说明,如果遵循后果主义后果最大化好的原则来行事,那就必须破坏个人的完整性,很有可能,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也处于无法在道德上得到辩护的地步。当然,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仍然有无数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其中甚至还有无数人处于饥饿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事事都从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好的原则来考虑,可能处于发达国家或较发达地区的我们也许什么事情也无法做好。并且,正如谢夫勒所说,按照这样的道德要求去行动,它会使得我们与我们的人生规划相疏远、相异化。不过,像这样从全人类存在者的福祉视域来看待行为后果的道德追求,确实是一种理想而完美的道德要求。但是,这两个案例所揭示的问题,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后果主义的实践可行性问题,这确实是向后果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不过,后果主义确实会有这样的困境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后果主义该如何改进?
三、威廉斯的个案问题
我们知道是威廉斯首先提出,如果按照后果主义的严苛要求来行动,那就要破坏个人的完整性,因此,我们先转向威廉斯的讨论。威廉斯提出了两个著名的案例。
个案一:乔治刚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但他很难找到工作。由于他的身体原因,他失去了很多他本来能胜任的工作岗位。为了生活,他的妻子不得不外出工作。但这样又产生了很多问题。他们有几个小孩,照看小孩成了严重问题。一位老化学家知道了他的处境,他说能让乔治在某个试验室得到一份报酬较高的工作,但实验室的工作是把研究应用于制造化学武器和生化武器。乔治反对制造化学武器,所以他拒绝接受这样一份工作。然而,老化学家继续劝说他,说他自己也不热衷于这一工作,而如果乔治拒绝接受这一工作,实验室肯定会找到一个与乔治同龄的人,而且这个人不会受到乔治那样的良心自责的约束。如果委任这个人来从事这一研究,那样他可能要比乔治以更高的热情来从事这项研究。老化学家不是出于对乔治和他的家庭的关心,而是出于对那个有极端热情的人的某种恐惧,他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影响来说服乔治接受这项工作。而由于乔治深爱着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也表达了某种意见,依据妻子的意见,他得出结论,把研究应用于制造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并不是一种特别的错误。那么,乔治应作出怎样的决定?
个案二:吉姆来到南美的一个小镇中心广场上。广场靠墙处站着一排(20个)被捆着的印第安人,大多数印第安人看起来非常恐惧,只有少数印第安人面无惧色。他们前面站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其中一个是负责的上尉。上尉问了吉姆许多问题,当他知道吉姆是由于考察植物偶然来到这个地方后,向他提出要他亲手处决其中一个印第安人,上尉乐于将此作为一个特权来尊重到访者,那么作为对他的敬意,其他印第安人将被释放。当然,如果吉姆拒绝了这一要求,这20个印第安人都将被枪毙。那些被捆梆的印第安人和村民们知道这一情况后,他们显然恳求吉姆接受这一“殊荣”。那么,吉姆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2]97-99
威廉斯对这两个案例进行了分析,他重点讨论了这两个案例中行为者的感情。在威廉斯看来,这就是后果主义后果最大化好的道德要求破坏个人的完整性。乔治在心理情感上是抵制去可用于制造化学和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工作的,而吉姆在情感上无疑也不会乐意充当杀手,然而,在后果主义(功利主义)后果最大化好的道德要求中,根本就没有情感的地位。但我们与世界的联系,我们与他人的共在,都在于我们的情感。威廉斯说:“以一种纯粹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些感情,它们就像是与我们的道德自我毫不相干,也就是说,因此失去了行为者的道德身份(同一性)的感觉,以一种近乎直白的说法(in the most literal way),失去了完整性。”[2]104在威廉斯看来,从严格的后果主义观点出发,那么,吉姆就应当把他自己的情感看得一钱不值。乔治的案例有点不同,乔治爱他的妻子,并且,他的妻子应当关心他的完整性,但后果主义很不情愿接受这种看法。那么,怎么理解第一个案例中的后果主义标准的运用呢?我们认为,从后果主义最大化好的后果的道德标准出发,如果从乔治所从事的制造化学武器的实验来看,其总体后果(从全人类的存在者的角度看)必然是不好的,但从乔治的家庭困境来看,乔治接受这份工作对改善他的家庭经济状况的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乔治可能会自我安慰,即使是我不从事这项实验,也会有他人从事这项实验,因而在涉及他人的总体后果上应当是没有差别的,但是,由于增加了乔治家庭的幸福,从而从后果最大化好的价值追求来说,后果主义的道德对此是持赞成态度的。威廉斯还认为,一个真正的、彻底的后果主义者不会有这些情感,因为他会把这样的与后果主义后果最大化好的要求不符合的情感看成是非理性的,而且如果当他发现他自己有这些情感时,他会不考虑这些情感,而情感本身只是有这些情感的人的体验。这表明后果主义者与他们本来希望顺应的日常道德或常识道德相分离。
其次,威廉斯认为消极(negative)责任是后果主义的后果论的一个问题。所谓“消极责任”,即在一定的情境中即使我们不做什么也会产生相应的责任。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威廉斯认为:“两种情景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如果行为者不做不能够同意的事,那么,别人也会做。”[2]108并且,别人做了,那结果会比当事人自己做了更坏,这两个案例的情形都是如此,当然吉姆案例中的情形更明显。威廉斯指出:“后果主义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很强的消极责任学说。如果我知道,如果做X,那么将产生结果O1,如果我不愿意做,将产生O2,O2的结果比O1更坏,那么,我应当对O2负责。”[2]108如对吉姆来说,如果他拒绝印第安人及其亲朋好友的请求,这些人会说,你本来可以阻止它的。然而,威廉斯认为,此事如果要让吉姆负责,只是满足了非常弱的条件,因为我们肯定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是吉姆促使了这件事情发生。如果由于吉姆的拒绝,上尉对他说“我别无选择”,那么,上尉就是在撒谎。在威廉斯看来,在这个案例中,不是吉姆的意图而是刽子手的意图起了主要作用。我们不应当根据吉姆的意图对刽子手的影响,而应当根据刽子手对吉姆的决定产生的影响来思考问题。当然,威廉斯并不认为吉姆在这个事件中不负有任何责任,在我们看来,威廉斯的观点是吉姆并不负有主要责任。然而,后果主义恰恰就是要把主要责任放在吉姆头上。威廉斯认为,在这样一个事件中所隐含的是,行为者对这个世界负有无限责任,这个无限责任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而后果主义把这样的无限责任强加在行为者身上是没有道理的。
威廉斯进一步指出,这两个案例所表明的是,一个事件的后果是由多种意图起作用而产生的结果。那么,一个后果主义的行为者应当具有怎样的行动规划?无疑是可欲求的最大化后果。然而,威廉斯指出,要实现可欲求的最大化后果,不仅仅在于行为者怎样去执行他的规划,还在于他自己的以及其他人的更基本的和低层次的规划。这些规划是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朋友等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欲望,某人可能还有学术上、文化上以及其他方面的兴趣追求等,威廉斯认为这些规划是第一序级的规划,如果后果主义的规划不与这些方面的规划相关联,那么将无法起作用。在威廉斯看来,一个人在这些方面的承诺是贯穿一个人终生的,从而这也是人的最基本欲望。还有与人生的基本欲望相关联的人们所支持的某些事业,如消灭化学武器以及对非正义、野蛮和屠杀的仇视的性情品格,等等,威廉斯指出,与这些性情品格可关联的规划不能看成是低层次的,它自身就是最主要的规划,如果不把这些因素纳入后果最大化或人生幸福的考虑之中,那么,行动后果主义就会像边沁的功利主义那样被人们指责其浅薄无知。而在对与非正义、野蛮和屠杀进行谴责相关联的事业意义上,人生并非仅仅是追求幸福。而后果主义也应当同意,最大限度地增进幸福并非意味着仅仅是追求幸福,与其相反,人们必须追求其他事物。而像对非正义、野蛮或屠杀的谴责,在某些情况下,是行为者在深层次上真诚的意图和态度倾向,他把它们看成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他生命追求的目标。而当后果之总和是根据那种由其他人的意图部分决定的效用结构发挥作用时,要求行为者放弃他自己的规划或倾向,那就是荒谬的。因为“在一种真正的意义上,这就是使他与他自己的行动和他自己所确信的行动之源相异化……而这忽略了他的行动和他的决定应被看作是来自于他自己最认同的态度和规划的行动和决定,因而最直白地说,这攻击了他的完整性”[2]116-117。在威廉斯看来,人生由各种规划所构成,后果主义的最大化好的后果只是其高层次的规划,并且是由许多层次或基础层次的规范所支撑的。同时,人生也并不仅仅只有追求自己的幸福的规划,还有其他非幸福追求的规划,这些构成了人生的重要部分。当然,我们的社会行动与他人的行动分不开,但是,如果在我们的行动中,由于他人的规划或决定影响到了我们的规划或计划,从而将影响到最大化的总和效用,因此我们就将不得不放弃我们自己所确信或承诺的东西,那么,这就是对自己的异化。或者说,损害了我们自己的完整性。正如莫尔根(Tim Mulgan)所说:“这是很重要的:不要误解了‘完整性’这词。这里没有指涉一个好生活的可分离的有价值成份,或者道德正直。宁可说,威廉斯在同样方面说到人的完整性,是如同我们谈到一件艺术品的完整性一样。生活的完整性是它的整体、统一性或形式。”[11]
威廉斯就上面两个个案的讨论提出了深层问题,即认为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好的要求损害了人的完整性。然而,人们的问题是,除了后果主义,一个正常的道德理论不会对人的行为提出要求吗?我们应当看到,任何道德理论都会对人的行为提出道德要求,并且,任何正常的道德理论都会认为,按照它们的标准或者要求去做,就是在道德上正确的行为或好的行为。那么,按照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好的要求去行动,难道就是错了吗?威廉斯回答,因为它破坏了人的完整性。而它之所以破坏了人的完整性,有人认为是因为它的要求过于严苛,如在阿夫鲁特和喜欢“老沃克斯豪车”的“我”这两个个案中所显示出来的问题。但以威廉斯所列举的两个个案,都难以说是这样一种“严苛”,这两个个案所表明的都是后果主义的要求与个人的道德品性不相符合。换言之,我们怎样知道乔治和吉姆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人?因此,如果吉姆虽然是去南美考察,但他本就是一个有着罪恶本性的人,那很有可能就想亲手杀人,那么威廉斯的问题也就不存在。因此,虽然威廉斯谈到了人生的规划,但实际上认为后果主义对人的完整性的破坏是在两个方面:一是如果事事都遵照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好的道德要求,那么,我们自己的生活规划就必须放弃,或者是,只以后果主义的最大化好的后果来要求自己的行动。如面对成千上万乃至上亿人处于饥饿状态中,后果主义要求我们捐赠除维持我们的生活必需之外的钱财,后果主义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最优选择。换言之,难道有任何道德理论不要求人们为了他人的利益作出一点牺牲吗?如关怀伦理以母亲形象强调的对人的关爱,不就是母亲对其子女的爱吗?而这种爱恰恰是以或多或少的牺牲为前提。但是,按照后果主义的标准,可能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如果说直接从事救济工作可能对于解救这些处于饥饿状态的人更好(后果最大化好),那么,我必须放弃我的哲学研究工作,我所有的人生规划都将被打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后果主义的要求是一种严苛性要求。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后果主义的要求,即卡根(Shelly Kagan)称之为“极端主义”的后果主义。二是在威廉斯所说的第二种意义上的完整性,即对一个人的品格品德的损害,其前提首先就在于行为者本身具有什么品格品德,其次则是如果按照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好的要求去行动,则可能产生对其品格品德的损害,因为违背了人们对其自身行为的道德要求。正如查佩尔(Timothy Chappell)所说:“完整性是一种德性,这种德性是真诚地与自己的真正价值观一致,而拒绝通过假装或因懦弱而接受的价值观。”[12]换言之,如果某些行动要求不符合我的价值观,那样,我不会假装或惧怕什么而违心地去做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做的事。卡根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与她自己的道德观一致行动的行为者,在行动中体现的是她自己。这样一种统一(unity),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整体的要素。”[13]与自己的道德观一致,其前提是能够自我作主,因此,完整性又是与自主选择前提相关的。即如果一个行为者不具有自主选择或是在真正受到强制的条件下的行为,并不代表行为者自己的真正意愿,那么,这样的行为并不可以说是自主的行动,因而虽然也是违背了行为者自己的道德品性,但对于这样行为的主要责任并不是行为者应当承担的。
完整性异议是对行动后果主义(行动功利主义)的最严重挑战。它表明了行为者价值中立与行为者中心价值具有不可避免的冲突性。一个从行为者中立的价值立场提出的如此崇高的道德价值要求(从全人类观点看的后果最大化),在行为者中心价值面前所遭遇到的困境,表明了人类道德复杂的内在结构。这说明我们不可能完全回避行为者的中心价值所在,因而也就预示着行动后果主义的价值追求不可能没有限定条件,而后果主义伦理的发展也是在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