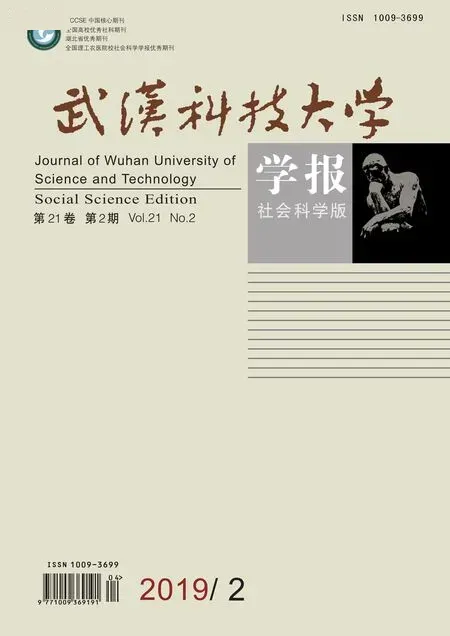戏剧演出的“非特有”媒介属性
2019-12-25胡一伟
胡 一 伟
(南昌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戏剧演出媒介不是特意为演出而存在的,其“非特有性”是指演出的文本符号载体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所用之物没有什么不同的特性。T·考弗臧(柯赞)(Tadeusz Kowzan)在论戏剧的十三个符号系统时,道出了此种“非特有性”:
“戏剧充分地利用那些在现实生活和艺术活动中的以人们间的交流为目的的符号系统,并不断地从自然界、从社会生活、从各行各业和艺术的一切领域中提取符号加以运用”[1]。
赵毅衡不仅将演出媒介的这种“非特有性”视为演示叙述体裁的一个重要特征,还阐述了身体以及日常物品转换成了演示媒介的前提条件——经由框架隔断,或带上了框架标记。换言之,戏剧演出所用的媒介体现了它从物(事)到符号(物-符号)、从“寻常”到“特用”的转换,这一转变过程影响了符号文本的意义生成。
一、作为物-符号的戏剧演出媒介
大多数符号媒介都有其物质性源头,一旦该符号媒介被使用,它便带有了“物-符号”的功能(兼具使用性和表意性),可以向任何一端(物或符号)靠拢。演出媒介亦是如此,其“非特有性”正体现了它与现实生活中事、物之关联——舞台上的事、物与日常生活经验中的事、物没有差异,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少会像舞台演出一样来使用演出媒介。关于这一点,诸多学者早已察觉。
于贝斯菲尔德在比较文学剧本与演出剧本中的物体功能时,揭示了演出媒介由“物”到“符号”的转换:
“物体是具体的存在,既不是舞台外客体的某一方面的图像造型,也不是客体本身。它不是某一现实的图像,而是具体现实本身,如演员的身体及其产生出来的一切结果,它表演(它动、它跳、它表现),戏剧的绝大部分便存在于身体这个表现——演出体,不管戏剧文本是否明确地考虑到这一点。同样,物体也有戏可做,它被表现、被展示、被构成或被毁掉,它是炫耀物体、表演物体或生产物体。戏剧物体是游戏物体。它还是重新注入语义的对象,这种语义重注工作在我们看来是戏剧获得意义的关键过程之一。如此,用一物体来表演,比如一支武器,可以产生意义。”[2]
这即是说,实存于日常生活中的物,可被重新注入语义存于舞台之上。
柯赞在分析戏剧符号系统时,指出了演出媒介的“非特有性”——戏剧所用之媒介符号,包括自然事物和人工符号。一旦它们呈现于舞台之上,就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义,这也是柯赞从自然符号与人工符号两个方面,对演出媒介符号的意义作进一步阐述的原因。
俞建章等在分析艺术符号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时,也提到了媒介的“非特有性”(尽管他所比较的是语言符号与艺术符号,但笔者认为它同样适用于艺术符号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造成二者的区别在于,它们所处的意义系统不一,所处的“位置”、组合的“顺序”以及展示的方式不同。就语言与艺术在符号形式上的区别进行具体说明:二者之不同与其所处的不同符号系统的意义有关,在语言系统中,涉及到词序、词法(词汇限定);而艺术系统则强调“表现作用”,即需要对符号文本周边的意义进行联想与想象,它没有明确的指涉(就语言符号系统相比较,它的指涉是间接的、衍生的,需要被补充、被修正),也不受句法秩序限定,并在交流作用之下重新建构文本,以传达意义[3]。从对语言与艺术符号系统之间的比较,以及对艺术符号系统表意功能的阐释中,我们也可推出艺术符号(戏剧演出符号)与日常事物之间的差别。
在媒介材料问题上,海德格尔(M.Heidegger)则从更广泛意义上给了我们较为透彻的看法:他认为,一件艺术作品首先是一件物,正如一幅绘画作品可以像煤、木料等运来运去一样,与其他事物并无根本性区别(均有物的特征,且其物质性十分“稳固”)。因而,艺术作品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反过来说:
“建筑存在于石头之中,木雕存在于木头之中,绘画存在于色彩之中,语言艺术存在于话语之中,音乐存在于声音之中。尽管艺术作品是被制作出来的,但它表达的并不仅仅是物,它将某种有别于自身的东西公诸于世,它明显是种别的东西,尤其明显是种隐喻。在艺术品中,制作物与别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希腊人称之为sumballein,作品是一种符号。”[4]152
尽管海德格尔很少提到艺术作品的形成(“创造”)过程,但他承认了艺术作品是一种“制作物”,而从物转为艺术品需要经过一个“去蔽”(unconcealedness)的过程。此处,海德格尔所指的“去蔽”并不是指对多余物的剔除,而是类似一种原始崇拜——“神庙站立之地即真理发生之地,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正确表现或再现了某物,而是所存在之物作为一个整体被导入去蔽性之中,并继续保持在那里”[5]56。这即是说,海德格尔所说的“去蔽”并不耗尽(耗费)媒介材料,只是将材料纳入形式中——“雕塑家以自己的方式使用石块,就像石匠使用石块一样,但雕塑家并不耗尽石块……画家使用颜料,也不耗尽颜料,而是像说话者或书写者那样随用随忘,使词句在诗中成为真正的词句”,此时,材料与形式早已融为一体(物的因素“进入”了作品),材料退隐了,“没有留下任何作品材料的痕迹”[5]47-48。
笔者认为,海德格尔弃绝过度地技艺化,强调媒介的自然属性(作为自然物、日常生活中的物),同样也可说明演出媒介的“非特有性”。此外,当代一些艺术理论在媒介材料上所持有的三种不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媒介的“非特有性”——马塞尔·迪尚对媒介所持有的“憎恶”态度(反对为艺术而对媒介材料进行特意加工);约翰·凯奇对媒介材料所持有的“奉承”态度(希望噪音等自然声响也变成音乐);克罗齐对媒介所持有的“中立性”态度(强调心理形象的启示作用,物质载体对传达心理形象只具有辅助性的作用)。
不论是反对制作加工媒介,直接将日常生活中的物纳入艺术文本中,还是强调将日常生活中的物进行转化,它们均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艺术(戏剧演出)媒介“非特有性”的妙处。由此,在一些艺术作品中,迪尚常用“现成物品”代替对媒介材料的加工;凯奇在《4分33秒》中不让钢琴发声,而“奉承”剧场中的自然声音(用其替代钢琴之声)。不论是自然物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物,它们均可以不被加工、雕琢而成为艺术的媒介,即体现出媒介的“非特有性”。
上述揭示演出媒介符号的物质属性的论断还可进一步地勾勒出非特有演出媒介本身经历着的一些转变——从物(自然物、日常生活中的物)转变为符号(符号-物),从使用意义转变为实用意义,也即演出文本中存在着物(事)的功能、意义相转换的过程。这一演变转换的“动作”既是历时性的,亦是共时性的。如,于贝斯菲尔德从物体不同的表现阶段(产生与消亡)总结出在不同时代、流派的戏剧展出时,“物”的功能是不同的:古典戏剧中的物体多是“功能的”,很少是修辞的,也从来不是生产性的。只是到了近现代,物体才在生产中得到了表现,它不止具有生产性,甚至是一种“产品”——尤其是在当代,“物体总以‘自然’的方式被表现,对取自自然的物体和文化使然的物体(即人类生产的结果)并不作区分,直到近几十年来(布莱希特)才看到物体与原始用途脱离,转向生产功能”[4]160。
近代剧本和导演对物体运用中可体现这种转变,如从产生人际关系(物左右人物关系)和产生意义(重新注入语义或制造某种规约性,颠覆物体作为“产品”出现的事实,使它反过来成为意义的源头,成为劳动和劳动者关系的一种比喻)。两方面来看,日常生活中的物一经转变,“台上的人不再被动地接受物体,不再将它看做环境、布景或者提供给他的工具,他制造它、运用它,并改变它、摧毁它……比如对垃圾的运用、作为无产者从中捞取可资利用的这一现实的图像,又如改变物体的用途(“梯子”变成“桥梁”)、或将日常生活中的物体运用于戏剧”[4]160-161。此时,“物体”呈现出其流动性意味——变为其他媒介,传递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物所不具有的意义,或表现人与事物之间的特殊关系,这就比原有的实用物更具有多义性和创造性。
柯赞则是从横向(共时性)来比较同一物(事)在不同世界(自然世界与舞台世界)中的功能与意义。他基于安德烈·拉兰德对符号的划分方法——自然符号(其与物、事的关系,由严格的自然法则决定,它不是有意图发生、参与而存在的,而是因人们对它的感知、解释而成其为符号的)与人工符号(其与所指物、事的关系,基于人类意图,为指示某物、事或以交流为目的的),得出戏剧表演所用的媒介符号均属于人工符号的范畴(是有意图的产生的)。
这是因为“即使所谓的自然符号,也需要观察者‘有意识’的推理活动,以便连接符号-工具与所指。不管怎样,在系统阐述更进一步的原则时,即阐述舞台上明显的自然符号的‘人工化’问题时,它对科赞是有用的:观众把自然符号转化为人工符号(如瞬间的闪电),这样,他就能使符号‘人工化’。即使那些符号仅只反映在生活中,它们也会成为剧场中的人工符号;即使它们在生活中没有交流功能,在舞台上它们也必然会获得这种功能”[6]。但仅从符号的发生是否有意图性这一依据并不能清楚地解释所有问题,即不能因此就说在演出中不存在自然符号:
“戏剧的手段和技巧是深深地植根于生活的,所以,把自然符号从戏剧中整个地排除是不可能的。在演员的语调、发音和表情中,严密的个人习惯是与有意图地创造出来的情调紧紧相联的,有意识的动作是与反射运动混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自然符号与人工符号是混和着的。”[1]
在柯赞看来,舞台上可以同时出现按照人物角色设定要求或由导演意图而生成的符号(人工符号),以及由演员即兴、遇突发状况呈现出来的符号(自然符号)的,此处,他是以扮演老人的青年所制造出来的颤抖声音,与高龄演员自身所具有的颤音作对比,揭示出二者之间的关联。
由于它们均与戏剧符号的意指作用有关,柯赞在分析符号系统时,对动作、发型、小道具等意指层次问题展开了说明。其中,动作符号系统可以代替、指涉其他事物,成为第二层次的符号;揭示与人物有关的文化背景及所处情景状态的发型,具有多种意指价值;小道具在发挥生活中的实用性时(第一层次意指作用),也有第二层次意指作用。舞台装置亦是如此,但它们往往不是单独起第二层次意指作用的,需要在多个符号媒介的组合作用下构成“物-符号”。
不论是从符号客体或意指角度出发,还是从自然符号与人工符号角度对戏剧演出的媒介符号系统或性质展开分析,他们先将目光投向了戏剧演出媒介符号的构成——符号的物质性源头,它主要包括自然事物、人工制造的器物和“纯符号”这三类。受戏剧演出叙述体裁特征的影响,原本不是为了“携带意义”的自然事物可通过演出中某些不可预测情况、即兴情况进入演出文本(呈现出来);原本不是用来“携带意义”的那些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物可以在被展示的情况下变成演出的一部分(被赋予意义);而为了向观众展示并与观众交流互动,演出文本中也充满了纯粹表意符号,如语言、表情、姿势等这类不需要接收者加以“符号化”的媒介,它们可以是实用的或非实用的,但均与人的身体性密切相关。
由此可以说,演出文本中的各种媒介符号并非特制的,因为它可与日常经验中的事、物一致,具有使用性;即使它单纯地作为意义载体被制造出来,但它是具有身体性的媒介符号,也并非是特制的。演出媒介的这种“非特有性”,使媒介符号具有多层意义价值——使用性意义(作为物)、实用意义(物-符号)、艺术意义(作为符号),并在无形中丰富了演出文本的意义。
然而,多种意义的实现以及不同意义价值之间的转换,与叙述隔断(展示框架)是有关联的。海德格尔在论媒介材料(尤其是对“物”的理解)与艺术品形成(艺术作为无蔽的真理而发生的一种方式)时,从某种更为抽象的角度提及到了类似隔断或框架的作用,并以梵高的《农鞋》为例展开了说明。
在海德格尔看来,处于画框中的农鞋没有确定的空间(鞋无所归属、非劳动所用,非农妇所注意),我们无法说出它在哪里(田野还是家中),一旦将画框中的农鞋作为现实中的农鞋去看待时,艺术作品中的物则成为经历着光照中的物,它的存在也就愈“真实”(这种“真实”并非模仿的真实,“不意味着因为它正确地描绘了某些东西,而在于农鞋作为器具的存在显示出所有的东西作为一个整体——世界和大地处于它们的反作用中——所达到的无蔽性”),最终真正地显示出了“仅仅是物”的物[5]56。
这里,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对“物”的理解不应停留于“像它们所是的那样存在”(to let a being be as it is)的表象,而应接近那种躲避思想的“质朴之物”(unpretentious thing),画框中的物便属此类。而无论是对真正“仅仅是物”的物的呈现(或艺术品),还是对于一种意义的构成(或真理的构成),这一具有框架隔断性质的画框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更好地让物体“去蔽”(自然不事雕琢),并重构意义(不同于现实世界)。
笔者认为,阿尔托的残酷戏剧,格洛托夫斯基提倡的“艺乘”、质朴戏剧,布鲁克的“空的空间”中对媒介的实践、运用与海德格尔在媒介技艺方面的抽象论述,有其共通之处——哪怕是画面留白、舞台空间空无一物,还是画面满格、舞台上摆满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在类似框架隔断的作用下,它们被重构着意义,或真正地呈现“仅仅是物”的本真。换言之,戏剧演出(甚至整个演示叙述)中的物-符号关系的转换也经历了“去蔽”的过程。即非特制的物/符号一旦带上了框架标记(再现中的进一步再现、被二度媒介化[7]),会改变其意义。比如,进入一度框架具有实用意义,进入二度框架带上了艺术意义。
二、媒介“特用”与意义生成
在分析了媒介符号的非特有性后,自然物如何符号化,带上实用意义或艺术意义,以构建演出文本的意义,是接下来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先从几类常见的媒介谈起,论述舞台实践中事、物的“特用”与意义构成。
(一)被“特用”的事、物
演出体裁所用的媒介均具有“非特有性”,即都可视为被“特用”的媒介,这里主要从以身体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类型说起,来看单个媒介符号的“特用”与意义生成问题。
关于身体及其延伸的媒介。从身体自身的功能来看,演示框架中的言语、歌声、吼声等功能与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不同。譬如舞台上重复的慢动作或者类似“上吊”“杀戮”等举动不会经常在日常生活中无故上演,却时常通过叙述框架呈现出来,如目连戏《男吊》《女吊》《调无常》中,演员使用吊绳的表演让人胆颤心惊,同时也为其精湛表演叫好。而这些舞台上频繁发生、显而易见的行为(被转换后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将叙述框架凸显出来。即使有时演员会走下舞台来到观众当中,与观众接触,他们的犯框之举也会将原有的叙述框架标显出来。例如,《狄俄尼索斯在69年》中曾有过一个场面:穿着十分暴露的女演员走到观众当中,身体躺在观众的旁边并开始抚摸他们,并延伸触摸的部位。虽然演员将其行为延伸到了舞台之外,但展示维度会随着演员行动范围的扩大而扩大。而其抚摸的动作与日常生活中抚摸的含义自然也有所不同,正如台上“咬”的动作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咬”一样。
从以身体为中心展开的媒介功能来看亦是如此,灯光、场面、道具、衣着等演示性媒介与日常经验所用之物无异,但它们在演示性叙述中的作用却与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在演出中,导演会利用光影对身体的投射制造特殊效果——从舞台空间投射到屏幕(幕布上)可以是平面抽象的线条,也可以呈现3D立体的动态效果,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不会时常这样使用。在实验戏剧或杂技魔术表演时,我们可与动物一起演示,虽然动物依旧是动物,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不仅不常见到,也更不会与其共处,特别是在与蛇、丛林狼、熊等具危险性的动物“合作”的情况下。在身体的配备上,我们不会在平日的生活中使用面具、化舞台妆容或装扮成特殊人物(女扮男装等)。
关于身体的承载。承载身体性媒介的空间同样属于演出的媒介符号系统。空间是人的空间(活动的空间),但这个空间的范围是抽象意义上的。即承载身体性媒介的空间并非指实体的空间(建筑空间、剧场空间或舞台空间),而是活动的、会发生变化的空间,是以演员行为显现出来的空间。这即是说,“特用”不仅包括以身体为演示性媒介之“特用”,还包括承载着身体性的演出空间之“特用”。其中最常见的媒介“特用”方式便是巧妙利用或布置空间场景,通过作用于观演距离(关系),使得原有空间(尤其是实体空间)发生质的变化。譬如:重新安排或改造演出空间,使观众和演员可以随意活动,表演者和观众角色转换的可能性将达到最大。以法朗克·卡斯托尔夫(Frank Castorf)导演的《记录列车机车号》为例。演出是在舞台上进行的,但有所不同的是,后台为观众搭建了一个脚手架。观众若要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必须横越舞台(而此时舞台上已装上了建筑用的灯)。先到“观众席”的人可以观察到后来的观众如何踉踉跄跄穿过舞台,甚至把一些台上装牢的建筑用灯扯断的举动。也就是说,早在进入剧场时,观众就各自在扮演角色了:后来进场的观众,在早已安顿就坐的观众的面前,担当了表演者的角色(不论他们是否愿意担当这一角色)。为了能成为观众,他们先必须成为表演者,但在舞台的后台上,他们曾经也被人当作过观众。该例中的演出场地未曾变形,“舞台”依旧是演员“经典的”行为场地,但是观看区域与展示区域发生了变化。
在《狄奥尼索斯在69年》中,观众可以决定自己与演出中心区的距离——随意调节他们与表演者及其他观众的距离,选择观察事件的视角。演员也不只局限在过去的汽车工厂的中间部位(围着黑色橡胶垫子),而是必须在整个演出场地走动。因此,整个演出空间的走动易使观众占据演出中心区的位置,并“加入到故事中去”。当然,展示空间的缩小也能使观众转换为表演者,如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的《公社》(1970-1972)(该戏讲湄莱发生的偶然事件)一剧中,一位演员(詹姆士·格雷弗斯)偶然地选出15名观众,让他们走进演出场地中间的一个圈子作为湄莱的村民。倘若观众走进圆圈,演出继续,倘若不听指挥,演出等待中止。该剧把演出空间缩小到舞台上的一个圈,观众一旦踏进圆圈,转瞬成为表演者。不管是让观众和演员随意活动,或试图让观者卷入戏中,上述三例所占用的实体建筑空间并未发生变化,但在展示空间的布局安排上有意模糊生活区与舞台区的界限,改变了原有舞台空间的使用性甚至实用意义。
在媒介“特用”方面的大致概括中,我们可以发现,诸种巧用(“特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使之转换为演出的媒介符号的方法均有异曲同工之效——让寻常事物带上符号修辞意义(寻常事物作为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存在于演出符号文本之中)。奥塔卡·齐克在《戏剧艺术美学》中也有过类似结论,他认为戏剧艺术在方方面面都是形象的艺术,演员代表戏剧角色,布景代表故事发生的地点,灯光亮度用以表示昼夜更替,声音代表事件或心情,纵使是实体的建筑结构物——舞台,也是为了代表其他东西(草地、集市、广场等)而存在,即舞台的形象功能并非由其作为实物的建筑结构所决定。其中,叙述框架是媒介从“寻常”到“特用”的关键一环,它不仅能把身体和物件这些日常物品转换成演示媒介(“脱离了它们的‘实在’语境,转换为符号”成为被叙述的故事的一部分,即“特用”),还能将演出空间被“特用”(如展示空间的特殊利用——混淆日常生活与演出舞台界限等)的情况呈现出来[8]。
(二)“带表情的”媒介与意义生成
“带表情的”媒介指一种容易卷入人们情感的媒介。这一理解受麦克卢汉对媒介的分类(冷热媒介是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划分的标准,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及对视觉媒介和听觉媒介的论述影响,尽管国内对其关于冷、热媒介划分的标准有诸多争议,但本文主要从其对媒介指标的考察来看“带表情的”媒介问题。先从麦克卢汉对冷热媒介的定义讲起。
麦克卢汉对冷热媒介的划分主要以感官作用(可感知渠道的种类)、数据饱和程度(信息饱满或匮乏,清晰与模糊)、卷入或参与的程度、媒介特性(排斥与包容)以及社会作用(“部落化”与“非部落化”)这几方面为依凭。且不论他在划分媒介类型、与对具体媒介性质的理解上,是否和现代人理解媒介有一致性,其划分的指标——媒介的感官作用、参与度和媒介特性对笔者论述“带表情的”媒介均有启发性意义。比如,媒介的感官是延伸一种感觉还是多种感觉;参与程度的高低;媒介的排斥性与包容性对意义的生成有直接作用,而多种感官的延伸、参与程度高、媒介的包容性则容易卷入人们的情感,促使媒介“带上某种表情”。由于视觉与听觉是人类感官渠道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两类,且诸多学者在论演出的媒介系统时,已经涉及到从视觉与听觉角度考虑媒介性质(如在对戏剧演出系统展开分类时,将语言、语调,音乐、音响效果归为听觉符号;表情、动作、调度、化妆、发型、服装、小道具、装置、照明为视觉符号,等等)。因此,下面主要从视觉媒介与听觉媒介来论述由媒介引发人们的情感卷入情况与文本意义生成问题。
1. 视觉媒介
演出中,视觉媒介的作用是最为直观和突出的,这一媒介包括演员在身体上的一些表现(肢体动作、表情等),演员的外形(妆容、发饰、服装等),舞台的环境(道具、装置、灯光照明等)。它们通过自身的形状、线条、颜色等因素影响情感,以及作用于人们对媒介文本意义的解释。
例如,在服装方面,它对卷入人们情感的作用与仪式有关。最早的戏剧性服装实质上是礼仪式的衣服。具体来说,早期演员们所穿的类似长袍一样的服装,起源于酒神赞美诗歌里,牧师吟唱时穿的山羊皮,这一服装源自许多原始的以神为中心的仪式;而喜剧演员的服装和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森林之神的服装,需要显露阳具,也说明了仪式对戏剧服装的影响作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演员为增强仪式化的效果,穿了增加他们高度的厚底鞋;中世纪欧洲扮演圣经故事的牧师,穿上了他们的神圣的白长袍,亦是同理;经典的日本能剧的演员服装直至今日都是来自宗教精神。此时,服装那古老和原始的作用,恰好使得演员和观众分开,让演员一穿上,就有了不同一般的身份[9]147。可见,服装所具有的仪式性作用能引发人们的某些特殊情感,如信仰、迷狂等,一旦情感浸入,则很可能会影响演出文本的意义生成过程。
当然,现代的服装也有此功能。周宁在论述现代服装设计的四个独立作用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服装通过卷入观众情感作用于文本意义的生成这一现象。即,他总结现代的服装设计有四个独立的作用:
“首先,和它古老的起源一样,它至少保留了一点古老的牧师和巫师召唤仪式的魔力。哪怕是今天的服装,总是要给人看出一种最基本的剧场感。第二,总的来说,一场戏的服装要告诉我们台上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不仅要表明剧情的历史时期和地点,还要含蓄地体现出有关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服装’(costume)一词的词源含有风俗和习惯的意思,同样,服装显示出居住在不同世界的人穿衣服的习惯。第三,个别的服装能传达人物细微的个性,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角色的职业、财富、年龄、阶段身份、爱好、自我形象。更微妙地,服装还能暗示角色的罪恶、美德,以及隐藏着的希望或恐惧。”[9]149
无疑,这里的服装是被“特有”了的,它所具有的“召唤仪式的魔力”“最基本的剧场感”以及暗示习俗价值观、隐藏情绪等特点,会通过观众的情感感知作用于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之中。
在灯光照明方面,媒介也有类似功能。导演R·威尔逊曾用光线计算机①改变演出现场的气氛,以达到演出预期的效果。他所用的这类灯光(亮度、变化的速度和频率)是不及人感觉到光线变化的程度的。人的有机体对光线的反应特别敏感,而这种光线,不仅作用于眼睛,也作用于皮肤,即光线通过皮肤而突入到观看者的身体,通过观众的身体影响他们的心理状态。也即,随着光线的变换、频率的改变,观众的心理状态经常断断续续地变化。对于这种变化,观众自己可能暂时无法察觉,也不会有意识地注意到它,更不会去控制它。威尔逊利用光线的这种特性,是因为观众在看威尔逊的演出时喜欢进入这样的气氛,这种气氛在演员有意的和明显的缓慢动作的基础上,具有很大的心灵影响力,观众进入这一气氛的倾向也会得以增强[10]173。
2.听觉媒介
演出中,听觉媒介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它是无形的,是观众闭上眼睛不看演出也无法回避的一类媒介。这一媒介包括由演员说出来的文本(语言、语调等)以及来自其他声源的声音效果(音乐、音响效果等)。其中,音乐就被亚里士多德视为戏剧的第五项要素——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戏剧也是要吟诵的,虽然吟诵这种表现形式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遗留下来的音乐成分,仍然可以在现今大部分戏剧中直接找到,其余的少数戏剧中间接地保留了这一因素[9]40。
当乐声直接出现在戏剧中时,它的表现形式是千变万化的。戏剧演出中最常见的方式是插入歌曲,过去常见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现代在乐于采用表现派技巧的作家(如布莱希特)的作品中也比较普遍。许多自然主义作家喜欢巧妙地把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写进他们的剧本,有时甚至不惜让他们的角色在舞台上弹奏其中片段。契科夫和田纳西·威廉斯也曾在他们的剧中大量使用背景音乐,加强效果。比如在契科夫的《三姐妹》中,观众可以听到场外军乐队演奏的进行曲,威廉斯在《欲望号街车》中涉及了从隔壁舞厅里传来的舞曲,在《蜥蜴之夜》中也安排了从小酒吧传过来的音乐。另外,导演也频繁地临时加进一些音乐——有时是为了在中场或者开演之前制造一种气氛,有时则是为了烘托剧情本身。在剧场演出过程中,音乐能发挥的渲染力是众所周知的,它在调动观众深层情绪方面发挥的效用,也就是编剧和导演们不敢掉以轻心的原因之一[9]40。
当然,音乐并不只限于既成的歌曲、曲调,还包括某些声音的“混响”——“间接地讲,音乐存在于所有戏剧作品中,存在于所有声响的节拍中。这些声响即使不成调,也能交杂混响而构成一个特殊的‘乐谱’——不是音乐的协奏,而是声音的交响。演员发音的声调、脚步声、唉声叹气声、大呼小叫声,以及火车鸣笛、铃声大作、隐隐约约的击鼓声、枪声、鸟兽叫声,甚至隔壁房间里的交谈声和夸张的特效音响(如心跳声、喘息声,或者冥冥之中的天外人语等),常常都是作者、导演和音响师在情节、人物、对话、主题之外偏爱运用的手段,谱写成舞台交响曲,烘托剧情”[9]40。从更为广义的角度来看,戏剧的可说性、可演性、流畅性也可视为听觉媒介达到的一种特殊效果。譬如,剧作家在创作时,须尽可能地要求听觉效果协调一致,因为声音的节奏韵律能帮助实现轻重缓急。在组构人物对白时,时常使用摇篮曲般轻柔的声音、快速急切的妙语、低沉的悲叹、闪光的警句、致命的诅咒、重要的停顿、撩人心弦的窃窃私语等手段营造出一个独特的时空感受[9]95。
在诸多声音的环绕下,观众的身体会变成所听到的声音的共鸣体,与所听到的声音一起振荡。并且,一定的声音还能消除掉身体上存在的疼痛,这一点仪式声音的作用最为明显。因此,“对于声音,观众或听众只能自我防卫,比如把自己耳朵捂住。观众对于各种声响(就像对各种气味一样)一般来说是没有抵抗能力的,同时,身体的界限也不存在了。当声响/噪声/音乐使观众(或听众)的身体变成它们的共鸣体,在观众(或听众)的胸膛里共振,给其添加身体的疼痛,使观众(或听众)起了鸡皮疙瘩或导致内脏的混乱,这时,观众(或听众)不再把他听到的当作传入到他耳朵中的东西,而是把这一切声响当作一种内部生理的过程来感觉了,而这经常会释放出‘海洋般的’感觉”[10]173。声音通过“入侵”观众的身体,以共振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听觉场域,在这个过程中,观众的情感被媒介卷入其中,演出文本意义的生成也在无形中受这一听觉场域的影响。
概言之,在视觉、听觉媒介构成的视听场域(或空间)中,观众的接收方式与意义建构的方式是不同的。借用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的“统一场”概念,来说明这种意义建构方式之不同。海森堡的“统一场”与整个场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和作用有关,即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可以随时发生改变,是“共时的”“即时的”,并非事先安排好,按线性排列的;要素之间的关联,会使得它们所发挥的作用通通诉诸于“感性”(又称为“有机性的”“神经性的”作用)[11]。以此来看视觉媒介,我们会发现人们对视觉媒介的接受过程是呈线性发展的,是有先后顺序的,其空间场域是由线性关系组织成的连续体,“属于统一和相互关联的那一类”[12]。听觉媒介形成的空间场域则与其不同,因为声音的传播是流动的,不存在聚焦点,它可从任何一处向人们涌来。所以,听觉的场域,是海森堡说的那一类“统一场”,它可任各种感觉在其中相互碰撞、激荡,它是非线性的、断续的、流动的[13]。此时,在不同媒介场域的作用下,尤其是媒介渠道对观众的感知作用(如“直接的感觉到情感形式”[14]),将作用于演出文本的意义生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