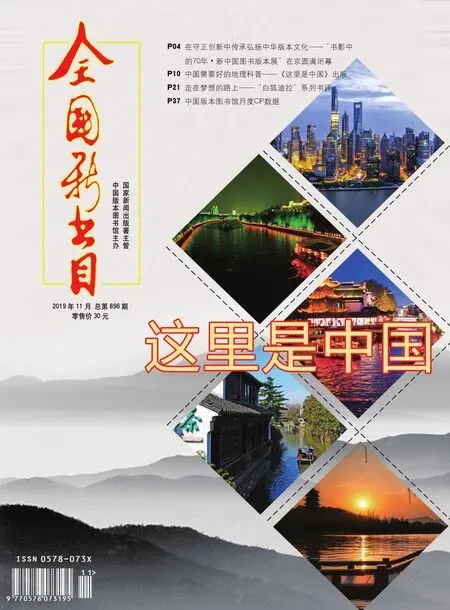憋屈的开锁人和幸运儿
——《DNA是如何发现的?一幅生命本质的探索路线图》出版
2019-12-24赵时佳
◎文/赵时佳

《DNA是如何发现的?一幅生命本质的探索路线图》
吴明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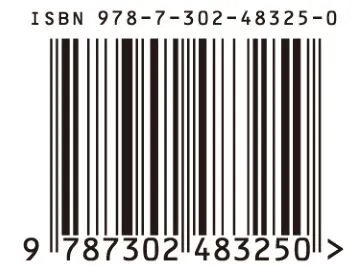
看美国大片的观众,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调侃“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这里的变异指的自然是改变人体的DNA,比如蜘蛛侠就是被一只受到放射性感染的蜘蛛咬伤,改变了自己的DNA,从而获得了超能力。那么咱们口中所说的DNA究竟是什么呢?
《DNA是如何发现的?》一书就为读者揭开了DNA的神秘面纱。
从书名不难看出,这是一本科普文,而且是一本书名字看起来一点也不有趣的科普文,看到这里,或许有很多人已经开始皱眉头了。因为科普文被人们敬而远之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作者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世界里,他们试图用通俗的语言去阐述问题,结果却事与愿违,这主要因为他们的核心关注点是在技术的发展,而普通人一看到满篇的技术名词,立刻会引发起畏难情绪。
而这一本《DNA是如何发现的》却不一样,这本书的写作方法,类似于当年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两人都是站在大行业的角度去阐述事物:黄仁宇通过经济、政治事件,以及思想史等角度,用大历史观来解读一个特定的年份;吴明则通过人、事、材料、技术等内容,用“大科学史”的方式来解释一个新学科的诞生。这本书也是目前国内第一本讲述DNA发现过程的图书。
这本书总共可分为11个章节。从1866年的豌豆杂交试验开始讲起,逐步进入核素的发现,再到确定遗传信息的载体是DNA,最后转到今天人们对DNA的认知。这里面涉及遗传学、化学、微生物学、物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内容,而地理位置上也从欧洲辗转到北美洲,各领域的大师学者们先后奉献了自己的心力。
在这一系列的发现和坚持的故事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么两个人的故事:憋屈的开锁人和幸运者。
憋屈的开锁人是指孟德尔。
他出生于1822年的奥地利,从小家境贫寒,连大学也是只上一半便被迫去谋生。从理论上来说,这样一个人是很难在学术上有什么成就的,但是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为了谋生,孟德尔跑去修道院做了一名修道士,在此期间他进行了大量的农业试验,比如他在修道院的土地上种植了将近3万棵植物。
在种植这些植物的过程中,他有了一个发现:通过嫁接培育出来的植物,其生命力往往比原来的植物更加顽强。这让他非常好奇,于是他开始一步步地追踪这个问题。

孟德尔和奥斯瓦德·西奥多·艾弗利
虽然他大学只上了一半,但在大学期间他也接受了系统的科学实验知识,于是他开始用数学方法对自己的试验做统计。最终他发现了显性法则、单一性单位性状和分离法则。他的发现相当于创立了观察遗传现象的新方法,即便是到了今天,他的遗传学方法也依然在使用。
这样一个划时代的方法,也许你会觉得一定让孟德尔功成名就了,但事实恰恰相反。孟德尔过得挺憋屈的,他的这些重大发现,在当时被长期忽略了,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原因,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因为学术论文的发表地点非常重要。孟德尔虽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料,但只向一个博物学会做了宣讲,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论文,使得他的论文含金量被平台所稀释了。
第二,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孟德尔的价值,甚至觉得孟德尔的观点只是诸多奇谈怪论之一罢了。包括他的老师,也认为孟德尔的观点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因为他的观点太前卫了,而能够证明他观点的证据核素,在四年后被发现了,但是孟德尔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结果忽略了翻身逆袭的机会。
如果要站在现在的角度去评价孟德尔,他一手打开了遗传学大门的锁,但是缺乏彻底打开的机会。所以说,他是一个憋屈的开锁人。
书中另一个先驱奥斯瓦德·西奥多·艾弗利,作为幸运者虽然和孟德尔都有着牧师的职业背景,但两人的境遇却截然相反。
首先说一下为什么他们都有同样的牧师背景,因为当时牧师进入学术界的机会比较多,同时牧师可以有大量的时间去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艾弗利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过一段时间的医疗队长,待战争结束后,开始研究乳酸菌和结核菌。研究乳酸菌是因为他认为这有很高的商业开发价值,而研究结核菌是因为他有同事就是因为结核病去世的,可以说结核病在当时属于致命的主要疾病之一。
总之,虽然艾弗利淡泊名利,从来不做公开演讲和宣传。但在他生前,曾经一度因为在免疫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成为诺贝尔奖的提名候选人;在他去世后,世界上几乎任何一本涉及分子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和生物工程学的学术著作都会对他的贡献大加赞扬。
那么他为什么能获得这么高的荣誉呢?
除了作为科研人员特有的坚持之外,还有三点重要原因。
第一,他的研究工作有着强硬的后台: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在二战期间,当时全世界许多研究机构、大学都遭到了空前的浩劫,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却可以同和平时期一样,保持正常运转。可以说艾弗利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幸运者之一。
第二,艾弗利为人处世十分厚道,理解同事在科研上的偏执态度,尊重别人的选择,这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
第三,当时学术领域虽然有时候也会对艾弗利的观点持有怀疑态度,但和孟德尔时期相比,已经进步了很多,人们可以接纳不同意见。

[书摘]
《DNA是如何发现的?一幅生命本质的探索路线图》

生物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20世纪50年代,分子生物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这和信息科学的诞生在时间上如此巧合,信息科学中使用的一些术语,如程序、编码等后来都在遗传学中利用上了。当前人们似乎认为分子生物学已经到了“最后开花结果”的阶段了。须知,分子生物学的真正目的不在于创建能够在地球上生活的一些新型生命类型,以便为人类提供高质且数量充分的产品;分子生物学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基因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来揭示人类、动植物的生理过程,以及细胞分化,胚胎发育,生长、衰老直至死亡的全过程。就是说,要对生命时间阶梯的机理按正确顺序进行全方位追踪。即便生命本身现在仍然是一个奥妙无穷、深不可知的秘密,人们一旦将其和分子联系,进行综合分析,那么就有可能接近其终极秘密了。
因此,人们主张先不考虑生命是否已知或未知,我们抄近道,直接来认识生物分子——看来这可能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在进行这类研究时,可以考虑研究分析逐级爬升的生命时间阶梯的结构,这样就能够认识愈来愈复杂的生命过程。
生物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人类自身,弄清楚人类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把构成自己知觉和个性特征的物质基础弄清楚。其实,人类对自己的大脑知道得太少,例如神经解剖还十分粗略,神经生化只有零星资料,更不用说有关信息的贮存、加工、提取等一系列活动的机理了。
过去的200万年,人脑体积增大了3倍,其中负责计划、决策的大脑新皮层增大明显,大脑的信息贮存量却很难估计。这些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实早在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立体结构模型后,德尔布吕克就曾预言过:“双螺旋及其功能不仅对遗传学而且对胚胎学、生理学、进化论甚至哲学都有深刻影响。它对现代人的深远影响莫过于几乎人类的一切性状都可能有部分的遗传学基础。这不仅限于各个人的体质,而且还包括智力或行为特征。遗传素质对人类非体质性性状,特别是对智力的影响正是目前争议最多的生物学与社会学问题。”
2013年,美国还公布了脑科研计划,以探索人类大脑的工作机制,绘制脑活动全图,并且最终开发岀针对大脑不治之症的疗法,此计划启动资金1亿美元,可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媲美。此项计划由瑞士洛桑理工学院的亨利·马克拉姆牵头,并由87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研发团体承担任务。目前中国学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原院长饶毅现在的研究领域是“社会行为的分子和细胞机理”。美国有40多所大学、100多个课题组从事这一颇具前瞻性的研究课题,人们对未来充满好奇。
生物学不仅要研究人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还要研究人的本质以及在宇宙中的地位。当然这还要借助其他学科,这几乎将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且包括人类自身的种种尝试。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活动,但在漫长征途的苦苦跋涉中,人类无法规避这些活动。那些第一代分子生物学家都早早地转向神经分子生物学前沿去开拓道路了,随后进入这一领域的不乏他们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过去物理科学、化学科学和生命科学之间实现过富有成效的互动,在分子遗传学和免疫学的精确知识方面取得突破,即解开分子密码,今天这种互动在了解人的神经系统方面看来有可能取得相似的突破性进展。神经分子生物学一个最重要的技术发明是光遗传学,就是用光来操纵分子。我们只要沿着现在的研究思路走下去,做更多的实实在在的研究实验,就是下一个突破口所在。
恩格斯早就预言过:“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发生的分子和化学的运动。”恩格斯预言的那一天不就是综合了各学科、各个领域研究成果的总和吗?到时候,只需在相应的表格上打几个钩就能实现,像组装电脑那样方便;研究开发人的大脑潜质,因材施教,推进DNA编辑技术。
人类还可以模拟人类大脑中全部860亿个神经元,以及将这些神经元连接起来的100万个神经突触的功能,到时候,可以建成一个“即插即用”的大脑,可以把它拆分,找出脑部疾病的原因,也可以借助机器人技术开发一系列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甚至还可以戴上一副虚拟现实眼镜,以体验“另类大脑”的神奇之处。
我们错失了前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但抓住了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机遇,让我们伟大的祖国跃升为工业和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但是,现在面临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选择,而第六次科技革命很可能是在生命科学、物质科学以及与它们交叉的领域出现。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内容和发展有以下五大学科:
(1)整合与创生生物学,可解释生命本质;
(2)人格信息包技术,包括人脑的电子备份与虚拟再现;
(3)仿生技术,即人体仿生备份和躯体仿真;
(4)创生技术,包括创造新的生命形态和生命功能;
(5)再生技术,生物体的体内体外再生。
由此可见,上列五大学科在很大程度上都涵盖了生命科学的内容,正像诺贝尔奖诸多奖项中,生理学或医学奖固属生命科学范畴,而化学奖中获得诺贝尔奖的从1901年以来,截至2018年,共颁发了110次,有180位获奖者,但其中一半人次是因为生命科学、生物化学的内容而获得的。
生物学发展的启示——学习历史
老一代分子生物学家,亦即那些用生物学概念来解释大肠杆菌及噬菌体的一代宗师,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先用综合意义上的学说形式提出自己的概念,在有了实验数据后,他们的这些概念才会被人们接受,再经过实验检验,但从中仍可能找出有某些片面性或不完善之处,这是一切概念、学说和理论可能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概念也好,学说也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标上了时空条件限定的烙印。现在这些老一代分子生物学家皆先后作古了,以原核生物作为研究材料的黄金时段也跟随他们一起走进历史。他们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认识到,决定大肠杆菌及噬菌体遗传性状的基因数目有限,只有将真核类生物的染色体结构和功能一步步地搞清楚了,将基因的结构和功能搞清楚了,才能再来揭示动植物乃至人类的生理过程,以及细胞分化,胚胎发育,生长、衰老直至死亡的全过程。真核生物比原核生物更加复杂,研究难度更大。
以后的科学史学家如何叙说我们今天的生物学呢,他们在研究我们现时的历史时,在有些事情经过若干年后,他们会从中判断出我们正在错过的或被我们低估了的力量倾向和趋势。爱因斯坦知道牛顿那时尚不知道的一些事儿,今天我们知道爱因斯坦那时尚不知道的一些事儿,明天的人将知道我们现在尚不知道的一些事儿。对于科学史学家而言,无论修史、治史,还是教史、读史,倘若大家都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就恐非所宜了。修史、治史、教史和读史徒知事实,无补于全局。善修、治、教和读史者,观既往之得失,以谋将来之进步,于全局有利。在博大精深的科学论说史这类历史遗产面前,学以致用、引以为鉴,只是研读科学史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意义。一个真正的科学史研究者不仅要鉴史,还要鉴人、鉴事、鉴细节。
说到底,就是要鉴出什么样的时空条件、什么样的知识背景等诸多要素同时被激活、启动,才能迸发出灵感的火花,让思维发生质的升华。细碎处的故事、空白处的讲述,才能真正反映历史的原貌。我们站在50年后的今天,追忆50年前的一幕幕情境时,会很自然地与书中那些科学先驱们感同身受:时而为他们与DNA分子仅有半步之距,终因一念之差失之交臂而惋惜;时而又为他们向着DNA分子步步逼近,眼看就要成功而欢呼雀跃。我们在不经意间享受到乐趣,在无意中营养了身心,这未必不是一种读阅科学史的优雅心态。读史还可以得到心灵的慰藉,让心灵充实,不惧黑暗,让人淡定、独立。
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马赫(Mach,E.)通过实验得出了气流的速度与声速的比值,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马赫数,以Ma表示,Ma=1126Km,就是340m/s,汽车跑不了这个速度,大多数情况是用来表示飞行器的飞行速度。用爱因斯坦自己的话说:“马赫才真正是广义相对论的先驱。”他早在1872年就曾告诫他的徒子徒孙们,“要寻找启示,只有一个办法——学习历史”。他的这套认识论科学哲学思想对当时的科学界一代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普朗克、爱因斯坦早年都是马赫思想的信仰者,约尔丹(Jordan,M.E.C.)、玻尔、海森伯格、薛定谔、泡利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马赫思想的影响。时过百余年,他的这番话对当今的生物学家或许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