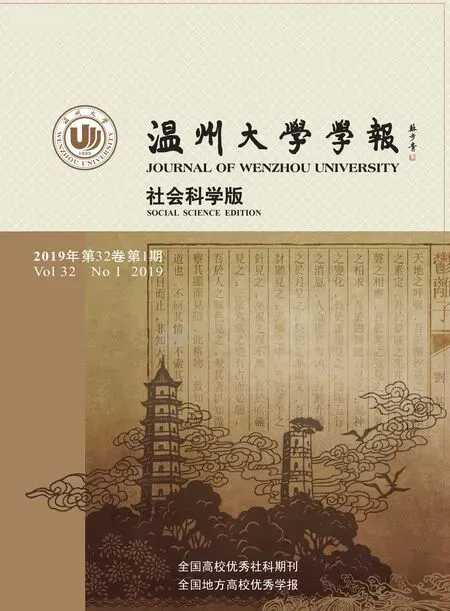谢灵运山水诗中的赏物模式
2019-12-23洪之渊
洪之渊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一、谢灵运诗中的“物”
拙文《郭象玄学与东晋赏物模式的确立》[1]176-186中着重论述了郭象玄学与东晋赏物模式及山水诗发生间的重要关联。赏物模式具体而言呈现为人与物之间的何种关系?此种赏物模式又是以何种书写方式呈现于山水诗作品?限于篇幅,该文未能具体论述,为此,即拟以谢灵运诗为中心,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推求。
谢灵运诗中16次出现“物”这个词,推究其用法,大致包含两类。一是作为现象而实存的外界事物,如《岁暮》:“运往无淹物,逝年觉易催。”[2]22《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2]118二是指世俗红尘,如《过始宁墅》:“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2]41《游赤石进帆海》:“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2]78而谢灵运在其诗中所表现出的对于“物”的态度,亦由此可分为两类四种。在此,更多关注的是第一类即作为现象而实存的外界事物。
当面对着作为现象而实存在的外界事物时,谢灵运所表现出的态度可分为“感物”和“赏(玩)物”两种。从《诗经》时代开始,中国诗人对外界景物的捕捉和描写,大抵采用“兴”,亦即触物起情的方式,并由此而形成为强大的“感物”文学传统。钟嵘《诗品序》中的一段话,便是对此极精妙的说明:“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3]1什么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钟嵘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3]28诗人因受到外界景物的感触,而产生了喜怒哀乐这种情感上的变化,并将此种情感投射于风景之上,并诉之于诗歌之中。在谢灵运的《岁暮》诗中:
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运往无淹物,逝年觉易催。[2]22
诗人的忧时伤生之嗟和惨淡岁暮之景互为投射,交叠出一份浓浓的悲凉情绪,以发端的“殷忧”为骨,灌注于全诗之中。这样一种情与物之间的交感,也正是谢灵运在《邻里相送方山》中所说的“含情易为盈,遇物难可歇”[2]40。而诗中的“运往无淹物,逝年觉易催”,显然是脱胎自《古诗》中的“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两句对于魏晋时诗人是极为熟悉的,且也是极易引发其岁月徂矣的生命共感。《世说新语·文学篇》载:“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4]同时,“殷忧不能寐”一句,也恰是汉末魏晋诗人常用的套语模式。这些正说明谢灵运早期诗作中的“感物”,是对于此前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延续。
谢灵运诗中,更富于诗人独特意味的是诗人有意识地、自觉地去践行着新型的人、物间的关系及由此而开创的新型文学书写方式即“赏物”或“玩物”。因为在这新型的人、物关系之中,人由物所引发的是一种强烈的、审美上及哲理上的愉悦之情;用谢灵运的诗句来表达即是“景夕群物清,对玩咸可喜”①参见: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创作的古诗《初往新安至桐庐口》。[2]47。此类句子尚有“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②参见: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创作的古诗《登江中孤屿》。[2]63、“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③参见: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创作的古诗《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2]118和“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④参见: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创作的古诗《石门岩上宿》。[2]183等。那么,究竟什么是“赏物”?“赏物”和“感物”的区分又在何处?这两者间最为根本性的区分就在于观物方式的改变。此种改变,是分别而又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即由时间性向空间性的转换,和由共相化向殊相化的转换。
二、赏物行为中的心、物关系
小尾郊一在《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中论及魏晋文学所表现的自然时曾指出,“利用秋的季节感,由秋景兴起悲哀与忧愁,又将悲哀与忧愁寄托于秋景,这种描写方法,在魏晋文学中到处可见”[5]33,他又说,魏晋以后的文学作品在描写秋天的时候常常出现《月令》式的景物,这是因为“在描写秋天的时候,代表秋天的景物已经在当时人们的头脑中固定了,所以不织入这些景物,便不成其为秋天描写。因此,与其说是直接接触描写了秋天本身的景物,还不如说是对秋作了观念性的描写”[5]54。在感物传统中,诗人对于外在的事物以流览的方式作为诸种类别一一列举,呈现出它们在时间性上的共相,并以此来构建成心与物所交感而成的强大情感场。诗人所关注的是身边甚或是意念中有些什么事物,而不是身边有怎样的作为具像而存在着的事物,这就决定了某一事物得以呈现其殊相的具体属性(如线条、色彩、音响等)及其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和观察点上、与同处于此一空间中的它物互为主体和背景的交相映发的特定视像,往往是淡出于这些诗人的视野之外,由此进一步决定了这些事物,在诗人们的文学书写中,也往往是做着套语式的陈列和组合。
那么,“赏物”所体现出的又是一种怎样的心、物关系呢?赏、玩和弄三个词之间往往连用,什么又是“味”呢?赏和玩都带有欣赏、玩味的意思,“味”字包含了名词性和动词性这两种相联而又相承的含义:某客体所具有的能引发主体对此客体强烈的渴求接近、进入、趋同的欲念和行为的质素,我们将之称为名词性的味,也就是“滋味”,而该主体因“滋味”而引发的行为,又具体呈现为他对于客体的认知、理解、体验,而终至于融合无间的有序而又循环往复的展开过程,这一动词性的展开过程,称之为“品味”。同时赏和玩又与“弄”字连用,沈祖棻先生在分析张旭《山行留客》中“山光物态弄春晖”一句时,曾对“弄”字作出很精彩的阐析:“(弄)是指一种自我的或及物的柔和、亲切、愉快的动态,通过这种动态,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或人与物之间融洽无间的关系。”[6]也就是说,在赏物这一心、物关系中,人对于物的品味过程,是一个柔和、亲切、愉快的动态过程,并且体现出了人与物之间融洽无间的关系。另外,还可补充的是,在“弄”之中,就其空间性的意义而言,人与物之间并不仅仅局限于视觉的关联,它同时也包含着一种身体性的因素即身体上的接触与爱抚。无论是“弄花香满衣”、“弄儿床前戏”,还是“明朝散发弄扁舟”,诗人表达的其与物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目所绸缪的,同时更是身所盘桓的,也正是这一层身体性意义的存在,使得其所传达出人、物或人、人之间的关系更富于一种深深的沉潜、无限的融合意味。就“弄”字时间性的意义而言,又包含有长时段的绵延性存在。
在赏物行为中呈现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有三个方面。首先,某一具体的物所具有的能引发主体对此客体强烈的渴求接近、进入、趋同的欲念和行为的质素。就山水景物而言,这些质素包括了深度、颜色、形状、线条、运动、轮廓、外貌等;同时,这些质素之所以能成为质素而被主体从它所处的整体性空间中所关注和提取,其原因恰在于通过整体性的空间对其的支托和滋养以及通过处于该空间中的其它事物对其的映衬对照,而呈现出其迥异于它物的具体殊相。这种殊相,只有当该物仅仅作为并成为某个具体时空点的该物自身时才方始得以呈现,也就是说这种殊相,它必定是呈现为某个具体的富于其独特意味的视像,而不是从某种类别中所抽象出的共相或意念。其次,主体对于对象的赏玩,是一种长时间的凝视。这一赏玩又包括了定点透视和定点流观两种方式。为此,需将流观和前所述及的感物传统中的流览区分开来。流览只是扫视,一瞥;而流观则是在视线移动中的凝视,因为“观”本身就带有细看的意味,《论语·为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又《论语·颜渊》:“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在这两句话中,观和表细看的“视”、“察”等词同义并用。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正是定点流观的典型写照。赏玩也可以是伴随着身体的移动而进行,亦即通常所说的移步换景。在移动的过程中,对象互为主体的连续性的呈现。最后,在赏玩的过程中,主体深深地沉浸于由物所引发的强烈的审美愉悦之中,忘怀于现世世界的存在,从在世的烦忙与烦劳中解脱出来,至臻人与物融合无间之境,并由此升华为对人生在世的哲理性感悟,而当诗人将此赏玩过程及体验转换为文学书写时,则必然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地在文本中呈现出来即:山水景物的富于其独特意味的视像、诗人以定点或移动的凝视对山水景物的赏玩、诗人在山水景物中所获致的审美愉悦乃至于哲理感悟。这三个方面正构成为山水诗写作主流范式的基本要素。而正如前贤所早已指出的,此种主流范式恰是经由谢灵运的诗歌而得以确立。那么,在谢灵运的笔下,又究竟是以何种语言文字上的手段而将这些要素组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呢?
三、秩序化的空间整体
钟嵘在其《诗品》中说:“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3]18-19王士祯《带经堂诗话》亦云:“迨元嘉间,谢康乐出,始创为刻画山水之词,务穷幽极渺,抉山谷水泉之情状。昔人云:‘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齐以下,率以康乐为宗。”[7]这两段话指出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特点及成就。
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2]41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2]63
长期以来日本对农业注重于价格支持,价格支持部分在农业补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随着WTO谈判的进展以及日本国内农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日本农业补贴政策从农产品价格支持为主向直接支付制度为主转变[10]。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2]83
苹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从斤竹涧越岭溪行》)[2]121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2]191
以上这些诗句所描绘出的,正是一种客观化的秩序性的并且是当下呈现着的空间整体。景物们总是相互依存着来共同构成一个富于层次感的秩序化的和谐空间:春草生于池塘之侧,禽鸣变于园柳之中;云儿拥抱着阳光,天空、瓯江之水,清澈地融为鲜活的一体;萍草摇漾于深水之上,而蒲草,则挺立于浅浅一湾;春深,原野绿的越发深沉;岩高,云层白中又透着凝重。在其笔下,景物之间形成内与外、上与下、远与近、大与小、深与浅的层次映衬,并有着动与静、光与影、声与色及诸种极鲜明对比色的交相辉映。在这些景物的组合时其所使用的语言技巧也同样值得注意,首先表现为对句法的大量使用,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曾说:
谢氏,俳之始也;陈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极也。[8]
大量对句的使用,使景物呈现出富于均衡而对称的效果。同时在对景物组合的描写时,谢灵运所喜欢使用的五言诗的节奏形式。五言诗的节奏组合主要有两种方式即二一二和二二一,亦即标准音步—非标准音步—标准音步或标准音步—标准音步—非标准音步。在这两种节奏形式中,谢灵运更喜欢使用二一二的节奏;同时,这中间的非标准音步,谢灵运喜欢使用一个经过精心锤炼的动词来做景物间的联络和贯穿,并由此而捕捉事物细微的、甚至是潜在的瞬间情态,这使得其笔下的景物组合,并非是机械地并立在一起;而总是活泼泼地富于生气地作着动态地呈现着。这些语言技巧的使用显然在提示刘宋新变在题材和内容上表现出的山水诗的形成及在语言形式上的唯美化走向,这并非是判然两分,相反,这两者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互促互动的共振关系。
如果去探寻这种富于层次感的整体性的来源,那么可以追溯到屈原作于颠沛流离的旅途中的作品《哀郢》《涉江》《怀沙》等。屈原开创的这一传统,经由两汉时期的楚辞作品及行旅赋的进一步发展,在魏晋六朝时期衍变为数量庞大的行旅诗创作。谢灵运的山水诗是完整地记述了其的经行过程,这些诗歌与魏晋以来行旅诗之间的关联就值得去关注。
魏晋以来行旅诗中的整体性空间,充满着哀愁和悲凉的情绪,“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诗人将自身强烈的主观情感投射于外物之上,使得万物皆著我之色彩。但在谢灵运的诗中,呈现的并非是这种主观的、激烈的情感,在其的笔下,情感的方向较之于行旅诗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扭转。在这些诗句中,诗人之主观的情感自我深深地退隐于背景之中,在诗之舞台上,只有这些景物自身原样自足地、自然而然地浮现着。当诗人面对着这样的景物时,当他经历过苦苦寻觅而面对着这样的景物时,他已然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共同融于生机自足的宇宙和谐之中。
在曹植《赠白马王彪》中:
踯躅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9]297
公元223年7月,在魏文帝曹丕的逼迫下,曹植不得不匆匆离开他所眷恋着的洛阳,回到那被他视之为牢笼的甄城。政治的失意、前途的渺茫、任城王曹彰的暴死及和白马王彪的不得不道路宜宿止……种种的人生艰难险恶,使得他眼底,尽是悲凉的秋风、凄恻的鸣蝉、萧条的原野、衰颓的斜阳和那急急惶惶奔走着的孤独的鸟兽。这诸般景象,无往而不是他痛苦愤懑之情的凝结。
而在公元423年,同样是满怀失意之感的谢灵运,在他来到永嘉一年之后,写了著名的《登池上楼》,这首诗的前半部分,牢骚愤懑的谢灵运尽情地倾吐着自己人生的矛盾和痛苦,直到以“衾枕昧节候,搴开暂窥临”两句为承转,才引出了对景物的描写:
表面上这只是对新春景象的摹写,实则是玄机自现:孟春之际,旧岁的寒风和故阴都已荡然不存。新草方生,则旧草已灭;新声既鸣,而前声永逝。人皆以有生必灭而黯然不已,却不知一切有为法,尽在无因无果、生生灭灭的永恒轮回之中。据此以观,则人生所谓的种种苦乐穷通,皆为虚妄,亦由此万化所蕴含之玄机,而彻悟“遁世无闷”的人生境界。
四、细微的瞬间情态
既注重于一种整体性、层次性的空间构形,同时又注重于捕捉事物细微的、甚至是潜在的瞬间情态,这一描写模式来自于曹植在邺下时期所作的宴游诗。曹植是谢灵运素所敬服的诗人,钟嵘在其《诗品》中就说谢灵运诗来源于曹植。
公子爱敬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放志意,千秋长若斯。[9]49
在曹植的《公宴》诗中,在中国诗歌的发展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既标志着诗歌写作传统的重大变革,又对此后诗歌发展起着极深远的影响,无论就其词法、句法、篇法、空间构形方式乃至于主题等各方面而言都是如此。单就这首诗对谢灵运最为直接的影响来说,前人早已指出,谢灵运诗中的“菰蒲冒清浅”里的“冒”字,就是来自于该诗中的“朱华冒绿池”。
在曹植诗中,整体性空间的构建,往往是以视点的移动来呈现,而在谢灵运的诗中,则多采取移步换景的写法,伴随着具体的时间流程的显示,使得他笔下的空间,无疑更富于一种立体性、流动性和变化之美。在《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中的典型语段如下:
在傍、陟、过、厉、登、陵、乘、玩、企、挹、攀、摘等一系列动词的引领下,各种各样的风景迅疾地展现在眼前,如大海的波涛般此起而彼伏。或弯曲、或高远、或湍急、或险峻、或盘旋、或摇漾、或挺立,自相映发,共同构成一幅富有动感且姿态万千的立体图像。
善于构建富于层次感及秩序化的和谐空间;并且透过风景的流动而感悟人生的真意所在,这正是谢灵运山水诗的典范所在。也是其和陶渊明诗歌在本质上的共通之处,然而他们的诗歌却又各具个性特点。在那个时代双峰并峙、各呈异彩,形成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分野,为此后中国诗歌的空间描写树立了各自的典范。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10]76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10]247
陶渊明以上脍炙人口的诗句中,光线的迷朦、景物的亲切熟悉、线条的柔和、色彩的素淡、是陶渊明诗作的境界。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从斤竹涧越岭溪行》)[2]121
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过始宁墅》)[2]41
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2]118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2]191
谢灵运的诗作中,隐天蔽日的茫茫昏暗、人迹未至的幽谷密林、峥嵘层迭的峭岩稠岭、然而却又有远淡近浓的诸种极明艳色调的随类赋彩。较之于陶渊明,谢灵运笔下的山水,又是何等的幽深、孤峭而又明丽。显然,谢灵运诗中所呈现出的这种逐新好奇之风,更符合晋宋人的审美品味[1]179-180。无独有偶,在中国第一篇山水画论《画云台山记》中,同样可以发现顾恺之对鲜明色调、险绝山势、幽邃洞天的强调[11]。拙文《郭象玄学和东晋赏物模式的确立》中也指出《画云台山记》中的对于景物空间的诸种配置方式,和谢灵运山水诗空间布局的类似之处[1]184。顾恺之和谢灵运,作为中国山水画和山水诗确立期的关键人物,其在赏物模式上的趋同,显然并非偶然。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撰文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