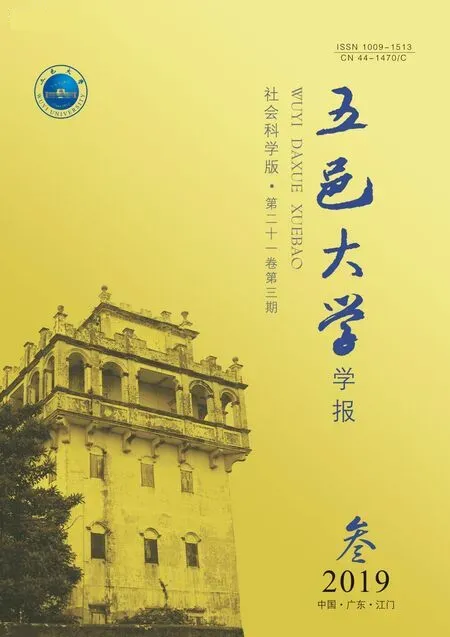陈垣《陈白沙画像与天主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2019-12-21吴珺
吴 珺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明末清初,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士就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礼仪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被称为 “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中国传统礼仪与天主教教义之间的矛盾,其中一个方面表现在他们面对中国祭祖祀孔截然不同的态度上:以利玛窦 (Matteo Ricci)为代表的传教士立足于中国传统,认为天主教徒可以参与祭祖祀孔活动;而以龙华民 (Niccolo Longobardi)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祭祖祀孔活动属于偶像崇拜,违背了天主教义。
康熙四十三年 (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Pope Clement XI)发布 “教皇终极禁令”,禁止天主教徒从事中国祭祖祀孔活动。次年,多罗(Carlo Tommaso)携此禁令来华,遭到康熙帝质疑,多罗被监禁在澳门。陈垣说 “康熙四十四年,罗马教宗派使臣多罗来华议礼,不合,多罗被禁于澳门”[1],指的正是此事。 “中国礼仪之争”对欧洲产生的影响左右着天主教徒的传教手段与方式,沈定平指出:“为遏制 ‘中国礼仪之争'在欧洲的负面影响,耶稣会士特别注意通过自己的著作,向欧洲宣传足以同基督教文明相媲美的中华文明”[2]。
“中国礼仪之争”是世界宗教史上著名的历史事件,陈垣 《陈白沙画像与天主教士》一文便描绘了西方天主教精通天算、音律、绘画的 “技巧三人”山遥瞻 (Guillaume Fabre Bonjour)、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 马国贤 (Matteo Ripa) 在“中国礼仪之争”的背景下赴华效劳的图景。他们本身肩负着传教的使命,却在多方面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在重大历史背景下的碰撞与对话。
一、山遥瞻与地图测绘
陈垣 《陈白沙画像与天主教士》一文对山遥瞻的记载很少,只说他 “精天算”[1]、 “出差云南,病卒”[1]。这里的 “天算”,指的是天文历算。
葛剑雄在 《看得见的沧桑》一书 “成功的引进——清初的全国地图测绘”一章中说:“从1708年至1717年,康熙向全国各地派遣了一支支测绘队,测定了包括台湾、海南岛、外蒙古在内的641个地点的经纬度,主持的西方传教士有雷孝思、麦大成、汤尚贤、杜德美、费隐、奥古斯丁、冯秉正、潘如等,潘如在测绘途中病死于滇缅边境。中国方面参加的主管官员和专家有穆克登、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那海、李英、照海等人,辅助人员多达二百人。测绘工作不仅得到各地在人力物力方面的全力资助,而且广泛收集、参考了已有的地理资料,进展顺利。”[3]这里提及的潘如应是陈垣文中的山遥瞻。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指出: “徐宗泽著 《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举其汉名为 ‘潘如',盖译音,而墓碑作山遥瞻,当可信也。”[4]《正教奉褒·教士姓名华洋合璧》指出: “潘如:山遥瞻,Guillaume Fabre Bonjour,1669/1670—1714,OSA。”①此外, “潘如在测绘途中病死于滇缅边境”与 “山遥瞻出差云南,病卒”可相互印证。
山遥瞻出差云南,是为了对云南进行测绘以绘制 《皇舆全览图》。从1708年开始,在康熙的指挥下,包括山遥瞻在内的众多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官员通力合作,他们利用西方先进的天文观测技术,结合星象三角测量的方法与经纬度法对中国的版图进行实地测量,并采用梯形投影法进行绘制。到1717年,他们初步完成了 《皇舆全览图》的绘制。此次地图绘制,外国传教士运用了当时西方先进的测绘技术,促进了近代制图学在中国的发展。葛剑雄说:“在西方以地圆为基础的经纬度测量制图方法产生后,中国的传统制图法已明显落后了。……这是一次成功的引进——在康熙的主持下,任用外国专家,以西方的最新技术测绘成了中国最精确的全国地图,又培养造就了中国自己的测绘专家。而拥有这项技术和人员的西方国家还没有能力或来不及完成大地测量,画出如此大范围的精确地图”[3]。
山遥瞻在云南病卒,后来雷孝思 (Jean-Baptiste Régis)替他完成了云南的测绘。方豪 《中西交通史》载:“山遥瞻绘江西、广东、广西,后卒于云南边境孟定。(康熙)五十四年 (1715)雷孝思抵云南,以竟山遥瞻之业。倪蜕 《云南事略》、赵元祚 《滇南山水纲目·序》及 《道光云南通志·凡例》,皆有关于云南地图测绘之载记。雷孝思自云南归来时,费隐又病,乃代其测绘贵州图;(康熙)《贵州余庆县志》卷一 《舆地志》亦记费隐测绘事”[5]602。
二、德理格与 《律吕正义》
陈垣 《陈白沙画像与天主教士》称德理格“精音律”[1], 并承担 “ 《律吕正义》 纂修之役”。[1]德理格纂修 《律吕正义》的经过及其取得的成就在方豪 《中西交通史》第四篇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有一些记载,还提及了德理格为纂修《律吕正义》所作的准备,认为德理格对 《律吕正义》之贡献最多。他还指出:“德氏在参加编纂此书前,即在宫中讲授西洋乐理,实即为此书作准备”[5]627。
与德理格一同编纂 《律吕正义》的还有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 (Thomas Pereira)。德理格是在1708年徐日升逝世后,成为皇宫里的音乐教师的。他在宫中讲授西洋乐理,为宫廷演奏乐曲、举办音乐会,并修理、保养乐器等等。德国学者海因利希·盖格尔根据意大利传教士毕天祥 (Luigi Antonio Appiani)的叙述得知德理格能够演奏不同的乐器,如斯宾耐琴、羽管键琴、管风琴、小提琴等等,盖格尔甚至认为 “德理格在17、18世纪之交中国的宫廷音乐文化中被视为欧洲音乐文化在中国最重要的代表人物”。[6]116盖格尔还说: “在德理格生活的时代,中国天主教传教士的思想、观念从古典文学教养的生活文化和价值评估出发。通过他们广泛的知识、个人的魅力,他们在中国学者阶层里找到了朋友和保护人,从中得出结论,有可能缓慢地在中国社会推行基督教。”[6]117由此可知, 德理格在中国宫廷讲授西洋乐理等行为,都与肩负的传教使命有关;而作为音乐百科全书式著作的 《律吕正义》,也成为了沟通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史的一座重要桥梁,它是西方音乐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雏形。
我国的历史典籍对 《律吕正义》多有记载。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八载 《御定 〈律吕正义〉》五卷、《御制 〈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其简明扼要地介绍了 《律吕正义》的组成部分及各部分的主要内容,谓 《律吕正义》“剖析微芒,发千古未有之精义”。[7]《清史稿》 对 《律吕正义》的记载,主要体现在 《律吕正义》的编撰、应用及校勘等方面。如卷九四 《乐志》曰:“取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及意大里亚国人德里格所讲声律节度,证以经史所载律吕宫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均字谱,赐名曰 《律吕正义》。兰生、廷珍等皆赐及第, 进官有差。”[8]2748卷二九〇 《王兰生列传》曰:“王兰生,字振声,直隶交河人。少颖异。李光地督顺天学政,补县学生,及为直隶巡抚,录入保阳书院肄业,教以治经,并通乐律、历算、音韵之学。光地入为大学士,荐兰生直内廷,编纂 《律吕正义》、 《音韵阐微》 诸书。”[8]10272据此我们知道,《律吕正义》是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官员共同编撰的。卷三四〇 《张照列传》曰:“上以朝会乐章句读不协节奏,虑坛庙乐章亦复如是,命庄亲王允禄及照遵圣祖所定 《律吕正义》,考察原委。寻合疏言:‘《律吕正义》编摩未备,请续纂后编。坛庙朝会乐章,考定宫商字谱,备载于篇,使律吕克谐,寻考易晓。民间俗乐,亦宜一体厘正。'”[8]10494谓 《律吕正义》用于审定音律,使得乐律和谐,另外,从应用方面看,它不仅服务于宫廷乐章,对民间俗乐也同样适用。
此外,《清史稿》卷四八五 《何梦瑶列传》载何梦瑶利用御制 《律吕正义》研究八音协律和声之事。卷五五〇 《戴梓列传》载戴梓通晓天文算法,参与纂修 《律吕正义》,但与南怀仁等西洋人观点不合。卷五六〇 《梅文鼎列传》载 《律吕正义》成书后,康熙帝认为梅文鼎留心律历多年,便遣他的孙子瑴成寄去一部,请其审读。吴振棫 《养吉斋丛录》卷二〇也记载了此事,曰: “康熙壬辰,诏修乐律、历算诸书,以皇子董其事。复勅下江南督臣,征梅文鼎之孙瑴成入侍。 《律吕正义》成,驿致江南,命文鼎校勘。”[9]
清代学者还利用 《律吕正义》去解释我国先秦著作,如 《孟子·离娄上》曰:“师旷之聪,不以六律, 不能正五音。”[10]475焦循 《正义》 引 《律吕正义》曰:“丝之为乐,其器虽十余种,而弦音所应,不外乎十二律吕所生五声二变之音。夫十二律吕之管,既分音于长短而不在围径,则弦音似亦宜分于长短而不在巨细矣。……总之以各弦全分之音,与各弦内所分之音,互相应合为准,是以不外乎十二律吕所生之七音也。”[10]477焦循对 《律吕正义》有着这样的评价:“以六律正五音,即以律和声以律平声也。《律吕正义》已得音之精微,近时学者研求实学,多有自得之解,略附于后:王氏坦琴音云:‘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盖以六律六吕三分损益、隔八相生之理,正此五音也……'”[10]479—480
在清代的典籍中,存在记载 《律吕正义》的一些零散史料,可见于赵慎畛 《榆巢杂识》上卷《历算名家》[11]、朱彭寿 《安乐康平室随笔》 卷一[12]、陈康祺 《郎潜纪闻三笔》卷一一 《卢明楷以精于乐律受知》[13]、昭梿 《啸亭续录》 卷一 《本朝钦定诸书》[14]、 王文清 《锄经余草》[15]、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 卷五 《述琴》[16]、卢文弨 《抱经堂文集》 卷二 《圣庙乐释律序》[17]、李光地 《榕村语录》卷二八 《治道》[18]、康有为 《长兴学记·学记》[19],此外还可参见 《清稗类钞》第一册 《卢明楷以精乐律受知》[20]、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卷一[21]、《清儒学案》卷一七五 《律吕正义阳律阴吕二均十四声说》[22], 等等。
三、马国贤清廷供奉诸事
(一)马国贤在清廷供奉的时长
陈垣 《陈白沙画像与天主教士》一文提到:“马国贤西名理拔,在内廷供奉十年,雍正元年回西洋,创建圣家修院于纳玻理府,培植传教中国人材, 殊有名。”[1]
陈垣说马国贤 “在内廷供奉十年”,主要是根据马国贤回忆录的记载。马国贤于1711年抵京,于1723年返意。马国贤说:“这样我们在1711年1月1日进入了九江府 (Kiaou-kiang-foo)……最后,我们在正月五日,大约是中午的时候到达了这个国家的首都。”[23]88—90, 马国贤离京返意时间在回忆录中也有所记载:“克服了不用细说的种种障碍之后,1723年的11月15日,我终于带着我的4个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离开了这座 ‘巴比伦'——北京”[23]116。
如果马国贤于1711年1月5日抵京,于1723年11月15日返意,那么他在清廷供奉的时间将近13年。马国贤回忆录的英文题名为Memoris of Father Ripa,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李天纲将此翻译为 《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而这些与陈垣所说马国贤“在内廷供奉十年”有出入。陈垣当是举其整数。
(二)马国贤与陈白沙画像
两广总督赵弘灿在奏稿中说:“臣等乃以本地配飨孔庙理学名臣陈献章遗像,令伊摹仿。今将马国贤所画陈献章遗像,一并进呈御览”[1]。
据马国贤回忆录的记载,总督一开始要求他临摹的不是陈献章遗像,而是 《孔子见老子图》。马国贤说:“总督后来送来一幅表现孔子拜在李老君(Lee-lao-keno)偶像前的画像,希望我画一个副本送给皇帝。因为不能做这种偶像崇拜式的事,我马上赶过去解释清楚。”[23]33马国贤认为, 孔子拜在老子面前等同于一种偶像崇拜,而天主教禁止教徒敬拜神以外的任何人。
马国贤说:“当我告诉他我的宗教不允许我临摹这幅画像,他表示道歉,说他不知道我们的教义。他还补充说会给我另外送一幅。经过相当长的谈话后,我告别了。出于尊重,他把我送到门口,随后又送来了一幅画像。”这幅画像就是陈献章遗像。[23]33陈献章是岭南地区唯一从祀孔庙的人,李天纲在 《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导言部分提到:“岭南明儒陈献章 (白沙)的画像,是‘配飨孔庙'的灵位像,也具有 ‘宗教意义',按理也应该禁止,马国贤只得把他作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 画了下来”[23]7-8。
陈献章本来也是中国明代重要的哲学家。黄宗羲说:“先生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自得故资深逢源,与鸢鱼同一活泼,而还以握造化之枢机,可谓独开门户,超然不凡。”[24]4陈献章高扬 “宗自然”的旗帜,以 “宇宙在我”②的学说引导人们发掘自我价值,冲破了程朱理学僵化的藩篱,独开明代心学的门户。 《明史》卷二八二 《儒林列传》曰:“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异说” 指的便是心学。[25]又,黄宗羲说: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喫紧工夫,全在涵养。”[24]79可见陈献章在明代心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马国贤拒绝临摹 《孔子见老子图》到把陈献章当作一个哲学家画了下来,我们能看到,清代初期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凸显的差异:孔子拜见老子,并问礼于老子,被西方天主教徒简单地等同于一种偶像崇拜,而在传统中国视野下,孔子拜见老子会被解释为儒家与道家的思想交流。而马国贤来到北京遭遇诸多困扰,使得他最终离京返意,也都是中西文化差异背景下 “中国礼仪之争”的产物。
(三)马国贤在中西美术交流中的贡献
陈垣认为马国贤在培养传播天主教的中国人方面享有盛名,但在绘画方面成就却少被人提及,是因为其绘画作品少有流传。陈垣说:“然人言清初西洋画家,多举郎世宁、艾启蒙,而不举马国贤者,因马国贤作品流传较少也。”[1]但是,马国贤在清代初期中西绘画交流史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在康熙尚未见到马国贤之前,便对他的绘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曾传旨曰:
西洋技巧三人中之善画者,可令他画十数幅画来,亦不必等齐,有三四幅随即差齎星飞进呈。再问他会画人像否,亦不必令他画人像来,但问他会与不会,差人进画时,一并启奏, 钦此。[1]
据马国贤回忆录的叙述,康熙对马国贤的绘画水平是满意的。马国贤为了迎合康熙的审美需求,去画一些他并不拿手的风景画,康熙很满意。马国贤说:“很高兴我取得了如此的成功,以致于皇上非常满意。因此,我就不间断地画到4月份,皇上下令说可以把我的作品拿去刻板了。”[23]48康熙对马国贤的人物画也表示满意,马国贤说:“皇上有一次看见了他要我画一幅满族人的画像,就说非常像。……为了表示他的满意,他随后就送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这是他经常重复的一种恩赐”[23]56。
马国贤在中西绘画交流中较大的贡献之一,在于把铜版画及其制作技术介绍到中国来:
我说我懂得一点光学,还懂得一点在铜板上用硝酸腐蚀的刻版艺术的原理。皇上听说这些,非常高兴。虽然没有做过,我还是准备试一下。皇上立即命令我开始刻印,在最短的时间内,我用点阵的方法,在一块涂上灯烟炭黑的板上绘制地形图,为硝酸腐蚀制版作了准备。我刚刚做完这些,皇上就急着要看。因为在版面上预备好的东西看起来非常漂亮,皇上非常高兴,命令中国画工画出地形图,以便我能在日后刻印。地图刚刚完成,就和原图一起,让皇上观看了。他表现出相当的兴奋,为复制品如此完美地接近原件,没有任何差异而感到吃惊。这是他第一次看见铜版雕刻画,中国人自己大致的作法,是把画固定在木板上,然后用雕刻刀把二者一起刻出来。[23]57—58
马国贤在这里运用的是硝酸腐蚀制版的工艺。在此之后,他改良了铜版画的雕刻工艺并刻印了《热河三十六景图》、《热河四十景图》与 《皇舆全图》,它们的刻印都使康熙非常满意。这些在马国贤的回忆录里都有所记载:
陛下知道我的雕版工艺获得了一些进展,决定要印刷一批采自他亲令建造的热河行宫的《热河三十六景图》。[23]63
同一时期,我继续改进雕版工艺。陛下看见我最近一版制出的一些版本后,说它们都是“宝贝” (Pan-pei)。他当场命令我印制 《热河四十景》图,准备把它们和一些诗文合为一册,作为赠送给满族亲王和贝勒们的礼物。[23]71
因为对我把整个 《热河三十六景图》装为一册的方式很满意,他还命令我用同样的方式雕刻一套 《皇舆全图》。[23]77
上述的一些,可成为马国贤在中西美术交流史中所作贡献的注脚。而马国贤在清廷中得以施展才华并在改良雕版工艺技术上取得一定成就,与康熙皇帝对他的赏识与鼓励有很大关系,试举一例。雕版工艺技术改进的难度是相当大的,马国贤说:“这种雕版的任何程度的小小改进,都花费了我大量的劳力。”[23]62在制造印刷机的时候, 马国贤 “遭遇了无数的困难”[23]63,当他请人造出来一台时,“机器工作了,印出来的效果却是一塌糊涂,惹得太监、官员和宫廷里的其他人们的大笑并加以嘲弄, 这下我的麻烦和混乱都全了。”[23]63而康熙皇帝却对此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马国贤说:“陛下看了我的雕刻印版作品,尽管它们都十分灰淡,可他却是充满善意地谅解了。他甚至宣布说它们都非常好”[23]63。
四、结 语
综上,以陈垣 《陈白沙画像与天主教士》一文为线索,我们得知在 “中国礼仪之争”的背景下,西方天主教 “技巧三人”山遥瞻、德理格、马国贤在各自领域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文化既有交流,也有碰撞。其中,精通天算的山遥瞻为 《皇舆全图》的制成贡献了力量,他运用了西方先进的天文观测技术、星象三角测量法与梯形投影法对地形进行勘测并对地图进行制作;精通音律的德理格与中国官员共同编修 《律吕正义》,他结合西方天主教的思想,在清廷广泛地传播了欧洲音乐文化;精通绘画的马国贤让康熙皇帝看到西方精美的铜版画,他利用硝酸腐蚀制版的工艺制作铜版画,并改良了铜版画制作工艺,刻印了清代中国美好山河的图景。而在对待表现儒家与道家思想交流的 《孔子见老子图》的态度上,马国贤认为这是一种偶像崇拜,违背了天主教教义,最终用陈献章的画像代替了他本要临摹的《孔子见老子图》。
(本文在写作与修订过程中得到庞光华先生、匿名评审专家与编辑老师的批评指正,谨致谢忱)
注释:
①OSA是Order of St.Augustine的缩写,即天主教奥斯定会,参见韩琦、吴旻校注:《正教奉褒·教士姓名华洋合璧》,中华书局,2006年,第382页。
②《明儒学案》卷五 《论学书》载: “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来今,四方上下,都一齐穿纽,一齐收拾,随时随处无不是这个充塞。”见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第二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