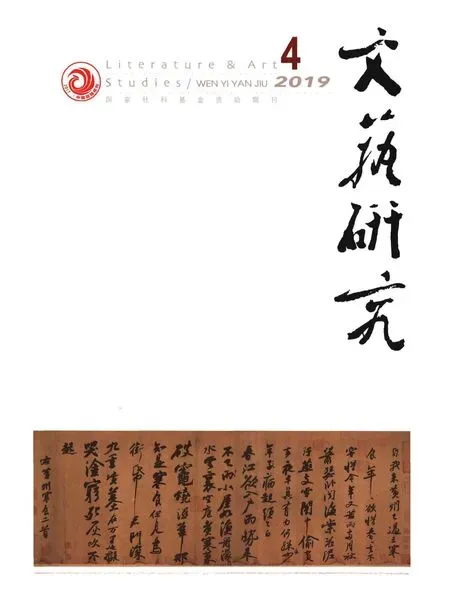韵意所向寓其心
——苏轼书法创作意境论
2019-12-21张锦辉
张锦辉
苏轼“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①,作为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最具艺术生命力的天才,除诗、词、文外,在诸多领域亦取得非凡成就。作为书坛“宋四家”之首,苏轼不但有超凡的书法创作实践,而且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书法创作理论。在他的书画题跋、论书诗、札记以及其他著述中保留有不少涉及书法创作的言论,呈现出独到的书学见解与主张。在书法创作中,他不愿受成法束缚,自称“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②,这与其以书写意、听笔所致而不顾及“法”的论书思想相一致。他在追求书法创作自然纯真、自由无束的同时,也对书法作品的构成要素、书家的素养心态以及如何书“意”等,都提出了一己之见,把晋人“尚韵”之风提升到新的高度,不仅求“韵”,而且追“意”。本文试图探讨的是,苏轼如何追“意”,“尚韵”和“尚意”之风又如何在苏轼的书法创作中得以合二为一。
一、法书要素
有关书法作品的构成要素,古人早有论及,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当属南朝王僧虔,他在《笔意赞》中曾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③,认为书法作品由内在的“神采”和外在的“形质”两大元素构成。“神采”是书法作品墨之浓淡、笔之选择、纸之各异、线条粗细及笔画结构组合中蕴含的韵味、透出的情趣、奠定的格调、营造的意境,皆显飘逸脱俗之气韵,居第一位;“形质”是指书法作品点、画、线条及结构布局的形态和外观应具姿致萧朗之风度,居第二位。依此二者构成独特的清华雅淡风貌。此论反映出当时书坛审美的主流追求,是对晋人“尚韵”之风的高度概括,影响了之后历朝书法的审美趋向。
苏轼在继承和发展王僧虔“神采”和“形质”说的基础上,结合长期书法实践,在《论书》中把书法的构成要素概括为五个方面:“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④直接将王僧虔的“神采”进一步细分为“神”与“气”两大块,“形质”分为“骨”“肉”“血”三个方面,使王氏论书观点得到更直观和具体的申说。在苏轼看来,书法作品这五要素互相关联,整合依存,缺一不可。下面从“神采”和“形质”两部分⑤,对苏轼书法创作五要素加以阐释。
(一)神采,包括“神”和“气”。以“神”论书并非始于苏轼,除王僧虔外,南朝梁人袁昂说“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古今书评》)⑥,唐人张怀瓘说“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书议》)⑦,窦蒙说“神,非意所到,可以识知”(《字格》)⑧。苏轼以“神”论书,将“神”视为书法创作的第一要素,与他在诗画中重视“传神”的思想相一致。“传神”,前由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他在《魏晋胜流画赞》中说:
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趣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⑨
此后,“传神”成为传统艺术理论和古代诗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重要命题,书家、画家抑或诗人、诗评家均将其作为创作的终极目标。苏轼在论书中把“神”列为首要构成元素,显然受到顾氏“传神”论的影响。而如何“传神”,苏轼虽未明确道出,但从其《传神记》中依稀可见:
传神之难在目。顾虎头云:“传形写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颧颊。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眉与鼻口,可以增减取似也。……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头云:“颊上加三毛,觉精采殊胜。”则此人意思盖在须颊间也。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⑩
在他看来,只要能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风采,“得其意思所在”便可,无需“举体皆似”,也就是说“形似”并不是“传神”的必要前提。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其二中苏轼又言:“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⑪可见,“传神”之关键在于要“取其意气所到”,至于其他则大可不拘小节,故在评价张旭草书时,他说:
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书唐氏六家书后》)⑫
张旭擅草书,追求狂放自由,将内心喜怒哀乐皆通过笔、墨、纸、砚等外在之“器”映现,所以其草书某种程度上就是激情的宣泄和喷发。苏轼一语中的,用“颓然天放”四字对其置评,就在于它传递出放胆抒情、散怀尚意的传神状态。此外,苏轼主张“作字要手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韵,于静中自是一乐事”(《记与君谟论书》)⑬。
“神”作为书法作品构成的最核心元素,把其他要素有机统合在一起,是作品灵魂和书家主体精神的显现,“入神者,尽性以至于命也”(《东坡易传》)⑭,书家只有寓意于笔、以字抒情、情景交融,方能传神。
“气”常用于表述人的精神面貌,如气质、气概、气度等。作为中国诗学中的理论术语,“气”最初则指运行于天地万物间的物质性的东西。“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遁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原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国语·周语上》)⑮后来“气”之内涵发生变化,常指人之精神状态和道德境界,《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载: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⑯
进入两汉,“气”又被思想家和哲学家赋予新的意义,成为天地(自然)间生成演化过程中的一环,“道”要生成万物,“气”则是必须要经历的环节,《淮南子·天文训》载:
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抟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⑰
所以后来苏轼说“阴阳一气也”(《东坡易传》)⑱。而“气”开始走入艺术,作为书画作品构成关键要素和主要评价标准则始于南朝谢赫,谢氏在《古画品录》中提出著名的绘画“六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⑲置“气韵”于“六法”之首,且指出不同于其他五法。
“气”对书画而言更为抽象,亦更为关键。苏轼论书也借用“气”这一概念,将其与“神”一样视为书法创作的必备元素,共同构成书法作品的内在意蕴层。在《题颜公书画赞》中,苏轼提出了自己对“气”的认识:“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小大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⑳这里的“气韵”指书法作品在整体上给人带来的节奏感、力量感和生命感,也就是书法作品呈现出的阳刚之美。“气作为构成书法作品运动感的整合性元素,从作品生成的角度看,它是书家书写活动时间性动作过程在作品中的反映。”㉑可见“气”通常与书家个性、书写习惯密切相关,宋人李之仪在《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中谈及苏轼作书时说:
东坡每属词,研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缀,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议者或以其喜浓墨行笔迟为同异,盖不知缔思乃在其间也。杨文公与人对弈饮酒,次人或以文为请,即以方角小纸,蝇头细字,运笔如飞,而与饮弈不相妨。……二公皆一时异人,固未易优劣。要之,东坡之浓与迟,出于习熟,而文公之小纸细字,亦非有所必也。㉒
黄鲁直亦指出苏轼作字“疏疏密密,随意缓急”(《跋东坡书帖后》)㉓,在《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中,黄氏如是说:“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㉔苏轼平时作书要求甚严,从墨的浓度、纸张的选择到握笔姿势、行笔缓疾等无不讲究,形成了独特的作书习惯,而这些都将成为“气”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关系“气”的生成。
有学者指出,“‘气’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中是一个具有元理论性质的主干范畴,‘气’观念渗透在中华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或曰神理意趣,实为理解认知包括文艺在内的中华思想文化的‘命门’”㉕。苏轼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气”这一传统诗学术语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将“气”列为书法构成尤其是“神采”方面的关键要素,可谓抓住了书法创作的关捩,这使“气”在书法创作中具有了非凡的价值,担负连接“神”与“骨”“肉”“血”的使命。
(二)形质,包括“骨”“肉”“血”。晋卫夫人在《笔阵图》中对“骨”与“肉”有着独到的认识:“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㉖以人物精神比喻书法创作,也就是注重书法作品的生命气息,说到底就是把字写“活”,融入书者的思想感情、生命感触、创作心态等。此后,王羲之、萧衍、李世民、孙过庭、张怀瓘等都有过类似言论,尤以唐太宗李世民说得最具体、最精彩:“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以副毛为皮肤,副若不圆,则字无温润也。”(《指意》)㉗写字作书如果没有神态、筋骨与圆润感,就是没有生命气息、没有把字写活,自然也就不能成为上乘的书法作品。
在论书中最早提及“骨”者,当属东汉赵壹,其《非草书》中说:“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㉘除了介绍汉代书家杜度、崔瑗、张芝等草书创作外,赵壹重点阐明了草书的学习以及不同书风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等问题。此后钟繇、卫夫人亦对此有相关阐述。苏轼在继承前代书家理论及创作的基础上,不仅将“骨”这一思想运用到书法中,而且将其列为书法创作的构成要素。在他看来,“骨”指书家之字要写得神气爽朗,笔法遒劲有力、有精神。在《次韵子由论书》中他说道: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矉,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讥,不独子亦颇。书成辄弃去,谬被旁人裹。体势本阔落,结束入细麽。子诗亦见推,语重未敢荷。尔来又学射,力薄愁官笴。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夥。何当尽屏去,万事付懒惰。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世俗笔苦骄,众中强嵬騀。钟、张忽已远,此语与时左。㉙
“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是苏轼书法创作思想的典型表现。“端庄杂流丽”的书风要求书法体态端庄,气象和谐,又不乏圆润流美。同样,苏轼更强调书法的骨力,不过他认为刚健挺拔的骨力不宜外显,而应体现在敦厚秀美的外形之中,极力反对筋骨外露的瘦硬书风。如《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载:
兰亭茧纸入昭陵,世间遗迹犹龙腾。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稜。……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㉚
在论及颜真卿与徐浩父子书法时,苏轼提倡藏筋力于圆润浑厚之中,力求于字外见真力而不以锋芒毕露、棱角突出为尚。所以他也不赞同杜甫“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㉛的说法:“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可见苏轼是提倡雄健肥劲的书法骨力的。
苏轼不仅要求书家作字体现“骨”,还要求字得包含“肉”和“血”。后两者是指书作构成之点画的浑厚和墨与水组成的色泽与形态,“血生于水,肉生于墨,水须新汲,墨须新磨,则燥湿调匀而肥瘦得所”(丰坊《书诀》)㉜即是。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肉”不仅仅是生命光泽的一种外在表现,同时还能使生命主体具有丰腴圆润之感,所以历代书家对其格外关注,“下笔用力,肌肤之丽”(蔡邕《九势》)㉝,“体磊落而壮丽,姿光润以璀璨”(索靖《草书势》)㉞,不论是“肌肤之丽”还是“姿光润以璀璨”,皆强调书法要表现“肉”之美感,即外在的生命光泽和丰腴圆润,如此方可“骨丰肉润,入妙通灵”(王僧虔《笔意赞》)㉟。苏轼在《题自作字》中说:“东坡平时作字,骨撑肉,肉没骨,未尝作此瘦妙也。宋景文公自名其书铁线。若东坡此帖,信可谓云尔已矣。”㊱平时自己作字偶尔也会写出“瘦妙”之形,为何?因为苏轼书法主要的美学风格是“骨撑肉,肉没骨”的丰腴肥润。其实,作为书法形质要素的“骨”“肉”“血”是不可分割的,“骨”“肉”以“血”而成,以“血”而活,三者是显示书作“内蕴”与“形质”的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神”“气”构成书法作品的内蕴层,直接关涉作品意趣,是书家的精神品格及其外在显现,涵括其性情气质、道德修养及才学抱负等精神因素,在实际的书法创作中则表现为点画线条及其空间组合的总体和谐。追求意趣、抒写性灵始终是苏轼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骨”“肉”“血”构成了书法创作的形质层,也就是笔、墨、纸、砚等外在之“器”在字中的表现。“苏轼由于对书法外在之‘器’的特性有着透彻的了解和掌握,能使四者相互配合,并做到人器合一,所以‘器’不是其进行书法创作的外在桎梏,反而促其精神自由遨游,既消除了‘器’与‘器’的对立,也淡化了‘器’与手、‘器’与心的对立。”㊲这从根本上说,促进了书法作品意趣的产生。可见,一幅成功的书法作品是这两个层面的有机融合。“神”与“气”是“骨”“肉”“血”的升华和目的,“骨”“肉”“血”是“神”与“气”的基础和表现,五者缺一不可,相互协同,最终提升了书法作品的意趣。当然,书法意趣的获得,除了具备最基础的条件——创作技巧精熟外,创作心态亦至关重要,书家之道德修养和审美趣味能否直接融入书作,皆取决于此。
二、素养心态
素养心态与书法作品意趣的萌生息息相关,所以苏轼论书极为重视书家之素质修养与作书心态对书法作品的意义与影响。在古代书法理论史上,提倡作书写字需注重提高书家学识修养者当首推苏轼。宋人李昭玘曾有言:“昔东坡守彭门,尝语舒尧文曰:‘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跋东坡真迹》)㊳这段话虽不能确认是苏轼原话,但由于李昭玘与苏轼同朝并为苏轼所知,所以转述还是足具真实性的。苏轼在论述中明显将书法与作书之人的品格修养对应起来,在他看来,作书之人的见识、学识、人品是书家立身之本。在《题鲁公帖》中,苏轼提出了“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的著名观点:
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书乎?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云。㊴
在他看来,正是“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所以“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对书家而言,一幅作品不仅仅是线条笔画的简单组合,实则是书家内心之“道”的呈现,正所谓心正则笔正,心不正则笔不正。苏轼重视书家“识”“见”“学”三方面的素质修养,足见他对书家道德学识、审美眼光和思想认识的重视。在《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中,苏轼曾言:
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㊵
时人只知欣赏文同的画,而对其道德文章却置之不闻,苏轼认为这是舍本逐末,尤感可悲。
苏轼论书亦主张兼论书家之生平,这其实与孟子所云“知人论世”㊶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中苏轼指出:“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㊷书法作品好坏及价值高低往往并不直接取决于字之线条粗细、墨之浓淡、大小美丑,而是书家赋予作品的思想、格调、意蕴决定着作品的高下。苏轼行书代表作《黄州寒食诗帖》之所以备受历代书家赞誉,其缘由便在此。书家道德学问方面的素质修养直接决定着书家的思想认识,进而影响着作品所表现的“德”,苏轼认为书家作品要以德为本。
此外,苏轼认为书家除手上功夫,也就是书写技艺——“学”以外,还必须注重认识的深刻程度和眼界的开阔程度,即“识”与“见”,最终形成道与艺合,技道两进。书法作为造型艺术,自然可以和诗词文赋一样体现书家的思想情感、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唯此书法作品才能现“意”。在《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中,苏轼曰:“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㊸明确道出书法可以传意,可见苏轼对作书者人品的重视。书作一旦写好,也就沾溉上了作书者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品质。
对于创作心态,苏轼注重作书者当时自然、平坦的心境。他在《题笔阵图》中如是说:“笔墨之迹,讬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惟颜子得之。”㊹书法以笔、墨、纸、砚之“器”和主观之“道”完成,作书者不应被外在之“器”禁锢,更不可为刻意求形而忽视“道”,如此才可能达到书法高致的境界。换言之,书法高致的境界并非难以企及,主要取决于书者的心态。对此,苏轼要求“足以为乐”,他在《宝绘堂记》中说: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塚。……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㊺
苏轼以自己从小对书画的看法和独特的亲身感受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君子可以寓意于物,但不能留意于物,否则就会执著沉迷,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给书家创作带来消极影响。这实际上涉及到“度”的问题,对于万事万物要注意“度”的把握。
总之,苏轼具有深厚学识和满腹才华,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虽历经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官场失意等诸多不幸和挫折,但始终保持乐观豪放心态,这也在其书法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黄庭坚说:
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书,其毫劲多似之。(《跋东坡自书所赋诗》)㊻
黄庭坚将东坡书法概括为姿媚、圆劲和沉着,这其实正是苏轼人生少年、中年和晚年三个时期情感的再现。如少年期代表作《治平帖》,笔触精到、字态妩媚;中年期代表作《黄州寒食诗帖》,诗句苍凉沉郁中饱含旷达,书法跌宕起伏、气势阔大、一气呵成,元人鲜于枢称之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天下第三行书”;而晚年期以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为代表,笔墨老练、意态闲雅、结字极紧。三个时期苏轼书法作品的风格意趣截然不同,更与书家素养心态紧密相联,成为书家书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书作意境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诗歌没有新意境,便失去了生命,好比一截枯木,不能引起人的兴趣了”㊼。然意境并非是诗词等文学作品的专属,书法等造型艺术亦不例外,苏轼在论书时也要求书家注重书作意境的建构。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作品的意境应当传神。需要指出的是,前文论法书要素,对“神”之论述主要从其作为书法构成要素角度阐释,此处所说“传神”更多倾向于对整幅书作意境生成而言。唐代以降,受审美潮流影响,文人书画普遍追求神似,所谓“神会”,“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沈括《梦溪笔谈》)㊽。苏轼更把“传神由人物画推及花鸟、推及诗文,使之成为中国艺术表现主体个性气质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观点”㊾。苏轼《北齐校书图》载:
庭坚曰:“书画以韵为主,足下囊中物,非不以千钱购取,所病者韵耳。”收书画者,观予此语,三十年后当少识书画矣。㊿
“以韵为主”即书画以“传神”为审美高格,只有识得书画的气韵精神,才算真正看懂并得以体认理解。苏轼对此加以强调,就在于其直接关乎意境的生成。
“意”,《说文解字》言“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可视为创作主体内心的声音。在书法创作中,“意”是书家通过造型各异的字形表现出来的情韵。书家建构的“书境”,必须传递出书家之心和书家之神。这也就是苏轼为何在书法创作中强调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主体情感融入其中的缘故,如其草书《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江上帖》,行书《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二帖》,楷书《前赤壁赋》《祭黄几道文》等。故后人在欣赏苏轼法帖时,总能从中触摸到其心境与情感。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苏轼说:“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之所以喜爱钟繇、王羲之的书法,当然除了他们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飘逸自然、潇洒奔放魅力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情感与笔墨载体完美统一,令整幅作品充满神采。在评隋智永禅师书法时,苏轼曰:“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可谓对智永禅师的书法赞不绝口,其源便在于它传递出了出家人闲淡旷达的精神,骨气通达,意趣横生,如陶渊明诗歌般恬淡洒脱。对这种“潇洒放逸”的审美态度的高度肯定,亦反映苏轼的内心之意,这正是他追慕向往的那种超然物外的自由境界。传王羲之所作《自论书》云:“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所得其妙者,事事皆然。”苏轼书法虽宗二王,但却不被其束缚,相反他更强调书法点画之间要传神,这样无法言说之“妙”自在其中。而在评价张旭草书时,如前引“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苏轼赞其“意态自足”,自是看重书家之意趣的充分展现。在《石苍舒醉墨堂》一诗中,苏轼曰:“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法艺术由晋发展至唐,作书规范和法则日益成熟完备,虽然在形式方面有力推动了书法的发展,但谨严的法度却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说约束了书家“意”的挥洒,限制了情、志、趣的抒发,这就形成了“意”与“法”的对立冲突。苏轼对此问题的要害有所意识:“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众所周知,颜真卿楷书端庄雄伟,如《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清远道士诗》等,行草书则气势遒劲,如《祭侄稿》《裴将军帖》《争座位帖》等,在书法史上,他的贡献不容忽视,尤其是所开创之“颜体”书风,成为数代书人争相学习的典范。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书家,难道书法就已堪称完美?苏轼结合当时的审美倾向以及自己的作书实践,对以颜真卿为代表的唐书“尚法”之风利弊辩证看待,并提出自己的书学思想,其目的便在于开创一种更加自由萧散的书写方式和审美范式。质而言之,苏轼在书法创作中坚持对“意”的追求,实质就是对自由的追求,由于他“提倡创作的自由精神,不愿受成法所拘,要求抒写胸臆,听笔所致,以尽意适兴为快,因而他作书时不顾及法的存在”。如作于晚年的《答谢民师帖》《渡海帖》《江上帖》等,完全不顾及工拙、丑妍的得失,率意而为,以致后人有如此评价:“东坡尺牍狎书,姿态横生,不矜而妍,不束而严,不轶而豪。”
其次,苏轼认为书意应当注重“自然天成”的创作意境。“自然”源于道家哲学,是道家思想的精髓,《老子》六十四章曰“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魏晋开始步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自然”也开始向文学艺术领域浸润,至南北朝时已屡屡出现在时人著述中,如蔡邕《九势》、刘勰《文心雕龙》、阮籍《乐论》、钟嵘《诗品》等,无不提倡“自然”,反对有意强为。“自然”自此成为文艺的普遍审美追求之一。
降及赵宋,虽然主权不断受到外族政权的侵扰,但“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程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陈寅恪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开创了迥异于“唐型文化”的“宋型文化”,相应地孕育出的审美思想较之前朝呈现出独特的审美特点——自然质朴、平淡素雅。苏轼亦受此审美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书画创作中,追求自然,反对精雕细琢和务奇求深。从书法意境生成层面来看,“‘自然天成’体现为一种自然、无意追求、无目的而又合乎规律的神妙境界”。在论书抑或实践中,苏轼格外重视“自然天成”的审美境界,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说:“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自然天成”的书境其实也是一种作书的心态。苏轼说: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评草书》)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是苏轼书法创作自由随性心态的反映,然而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对书家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如其所言,书家首先不能“有意于学”,即作书不能带有功利之心,其次不能过分追求书写效果,如此方能“自出新意”,否则就无法达到“不践古人”的书写境界,也难以写出无意而为的佳作。在《跋王巩所收藏真书》中,苏轼云:“然其为人傥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在书法创作中苏轼注重直观感受,即自由随性的创作心态,也就是所说之“无意于佳”和“无意于济否”,这样才能“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小篆般若心经赞》),写出好字来。
崇尚自然,欲从中感悟自然天成的道理,可以说是当时质朴与平淡素雅审美思潮的反映。而苏轼所说“自然”,对书法言即指寻求事物本来面貌而不过多加入人为雕琢和修饰。“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天工”是一种妙造自然、浑然天成、无需雕琢的自然之美。苏轼青睐于此:“瞿塘迤逦尽,巫峡峥嵘起。连峰稍可怪,石色变苍翠。天工运神巧,渐欲作奇伟。”(《巫山》)在《北齐校书图》中,他说:
画有六法,赋彩拂澹,其一也,工尤难之。此画本出国手,止用墨笔,盖唐人所谓粉本。而近岁画师,乃为赋彩,使此六君子者,皆涓然作何郎傅粉面,故不为鲁直所取,然其实善本也。
在绘画技法中“拂澹”所以最难,盖因要在保持自然纯朴面貌的前提下赋予色彩,稍不注意,画之本真状态便会丧失,可见在其眼中自然天成才是最美。苏轼将骨力遒劲、血肉饱满的抽象点画线条升华至超然意境,可以说是将自然天成自我化。赏欧阳修书法,“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跋刘景文欧公帖》),赞张旭草书“颓然天放”,就是去掉过多雕饰,还原其“真”,就是为人本真质朴,为文作书有真情实感。总之,苏轼在书法上追求的正是其所谓之“合于天造,厌于人意”(《净因院画记》)的审美理想。
余 论
“韵”,指书法所散发出的飘逸气质、深远情趣,也就是神韵、韵味。“晋韵”是当时书坛任情适性、崇尚自然,追求萧散简远的审美风尚的代表,有学者断言:“东晋艺术的最高成就不在文学,而在书法。”一定意义上说,“尚韵”作为当时书坛审美的标杆,它既是两晋时期整个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时代的产物和表现。其崛起标志着书家人文精神的觉醒,在书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书法作品由此从注重实用性正式走向更加注重书家个人精神体现之路。在“尚韵”书风推动下,书法创作的审美特质渐渐增强,尤以“二王”萧散洒脱、飘逸自然而又含蓄细腻的高超书艺为代表,影响深广。及至宋代,苏轼追求超轶绝尘的书境,质而言之即求“韵”。前引《书黄子思诗集后》:“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潇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接着苏轼说“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其实他所言“潇散简远”“简古”“淡泊”,正是“韵”味之旨。书法的点画线条、墨之浓淡、纸之选择、字体之变化,正是有了“韵”的贯注,才会呈现出一种生机活泼的状态和生命的力度美。故黄庭坚对东坡书评价极高: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跋东坡墨迹》)
朱熹亦大加赞叹:“东坡笔力雄健,不能居人后……而其英风逸韵,高视古人,未知其孰为后先也。”(《跋东坡帖》)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道出“易”与书法的共性,都是以“意”为本。“意”是书家内心真情实感在书法作品中的体现,重“意”代表了书法在宋代发展的新方向。明人董其昌在论述晋以后书法特点时曾说:“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书品》)可以说是对晋及以后之书风的经典论断,清人梁巘、周星莲亦持此说。古人这些精彩见解无不道出宋人书法的一个事实,即“尚意”。作为“晋韵”之后产生的一种新的书法美学风范,“宋意”在“森严的唐法和绝俗的晋韵面前能闯出一条‘尚意’的新路来,诚属不易”。宋代“尚意”书风追求书境的建构,强调书家创作素养和心态的自由,其实质就是随心所欲冲破各种“法”的束缚和禁锢,由“心”出发,将心之所向之美焕发笔端。在苏轼看来,“意”就是用来表达主体精神、思想和愿望的。落实到书法创作中,他强调书法创作者的主体地位以及精神层面的领悟,而不是其他的客观因素以及物质的传递,最佳境界正生发在“韵”与“意”的完美统一中。
宗白华说“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原本基于实用目的而书写的文字,却以其特有的书体形象给人带来艺术的审美享受,于文字内容之外显示出作书者特有的情怀和精神意趣,也就是苏轼所说的“字外意”。当然,这里的“意”是“意有余之‘意’,决不是‘意义’的‘意’,而只是‘意味’的‘意’。……而‘意味’的意,则并不包含某种明确意识,而只是流动着一片感情的朦胧缥缈的情调”。苏轼书法亦重意,就在于“意”成为他在书法中表现出的一种闲适状态和至高趣味。进一步说,在笔者看来,“他独具匠心的用笔与清淡旷达的心胸相契合,出奇制胜的笔法与抖擞质气的品格修养相映衬,超轶绝尘,痛快沉着,由道技两进到心手两忘,完成了由有意到无意、由有法到无法的内在超越”。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实现了“晋韵”与“宋意”的融合。这一境界就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苏轼书法中“韵意合一”的超逸至境,既在尽美中有平淡、萧散之意,同时也产生无穷的生动之感,为宋代“尚意”书风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但丰富和左右着当时书坛主流风向,而且对后世书法创作与书法理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① 钱钟书选注《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9页。
② 董其昌著、屠友祥校注《画禅室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③ 王僧虔:《笔意赞》,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
⑤ 为了便于叙述,这里采用王僧虔“神采”和“形质”的说法,具体论述则是从“神、气、骨、肉、血”五个方面展开。
⑥⑦⑧㉖㉗㉘㉜㉝㉞㉟ 《历代书法论文选》,第74页,第146页,第266页,第22页,第120—121页,第2页,第506页,第6页,第20页,第62页。
⑨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8—189页。
⑭⑱《东坡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第120页。
⑮ 左丘明撰《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
⑯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2页。
⑰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245页。
⑲ 潘运告编注《中国历代画论选》上,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㉑ 李放:《苏轼书法思想研究》,南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㉒ 李之仪:《姑溪题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102页。
㉕ 党圣元:《“气”与建安文学》,载《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㉛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50页。
㊳ 李昭玘:《乐静集》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㊶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51页。)
㊼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㊽ 沈括:《梦溪笔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㊾ 张皓:《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