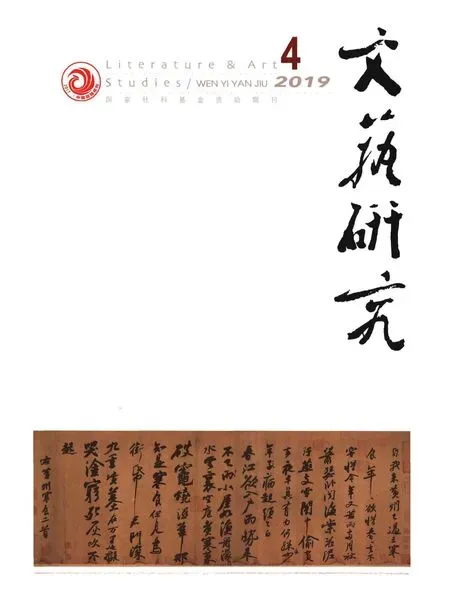《新青年》杂志批判旧剧功过平议
2019-12-21胡星亮
胡星亮
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有诸多“冤假错案”。其最大者,莫过于指责1918年《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6号(“易卜生号”)、第5卷第4号(“戏剧改良号”)批判中国旧剧,是要“完全消灭旧剧”①,是“全盘西化”②,是“民族虚无主义”③。
一个世纪以来,对于《新青年》杂志批判旧剧,学术界争议不断。可以说,这是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争议时间最长、观点交锋最激烈的一桩学案。公正地评价这桩百年学案,对于深化20世纪中国戏剧史研究,对于民族戏曲的传承和发展,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新青年》批判旧剧与百年争议
“五四”时期《新青年》对于中国旧剧的批判,百年来不断引起争议和受到批判的,主要是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的几段偏激言论。
在《新青年》上率先刊文批判传统旧剧的是钱玄同。钱玄同盛赞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壮举,并以胡适提出的“思想”“情感”和“文学上之价值”为标准去评论戏曲,指出:“至于戏剧一道,南北曲及昆腔,虽鲜高尚之思想,词句尚斐然可观;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为有文学上之价值也。”“又中国戏剧,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其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④故论及现代中国的戏剧发展,钱玄同张扬西方话剧而批判中国旧剧,并以其惯有的偏激言词说道:“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说不像话的话全数扫除,尽情推翻,真戏怎样能推行呢?”⑤
刘半农在论述其改良戏曲主张时,不仅批判钱玄同所列举的“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和“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等“戏之劣处”,还偏激地指出:“凡‘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中国文戏武戏之编制,不外此十六字),与一切‘报名’‘唱引’‘绕场上下’‘摆对相迎’‘兵卒绕场’‘大小起霸’等种种恶腔死套,均当一扫而空。另以合于情理,富于美感之事代之。”⑥
胡适批判旧剧的核心观点,是从文学进化角度谈中国戏曲发展的白话化、通俗化趋势,认为“今后之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白,亦未可知”⑦。胡适肯定传统旧剧“从昆曲变为近百年的‘俗戏’,可算得中国戏剧史上一大革命”,然而他又指出:“此种俗剧的运动,起源全在中下级社会,与文人学士无关,故戏中字句往往十分鄙陋,梆子腔中更多极不通的文字。俗剧的内容,因为他是中下级社会的流行品,故含有此种社会的种种恶劣性……况且编戏做戏的人大都是没有学识的人,故俗剧中所保存的戏台恶习惯最多……到如今弄成一种既不通俗又无意义的恶劣戏剧。”他还将脸谱、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看作是过去时代留下的“遗形物”,认为“这种‘遗形物’不扫除干净,中国戏剧永远没有完全革新的希望”。结论是:“扫除旧日的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⑧
《新青年》批判旧剧遭到戏曲界的反攻。尤其是张厚载,他逐一批驳,认为胡适“所主张废唱而归于说白,乃绝对的不可能”,刘半农鄙弃的“乱打”乃是“极整齐极规则的工夫”,钱玄同反感的“脸谱”也“分别尤精,且隐寓褒贬”⑨。在《我的中国旧戏观》一文中,张厚载更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戏曲的虚拟性、程式化、乐本体等艺术特征:(一)“中国旧戏是假像的”,用“抽象的方法”表现世间的万事万物,使人“指而可识”;(二)中国戏曲的唱念做打都“有一定的规律”,它“自由在一定范围之内,才是真能自由”;(三)“中国旧戏向来是跟音乐有连带密切的关系”,而唱曲比说白更能表达感情,于“人类性情”和“社会风俗”更有“感动的力量”。结论是:“中国旧戏,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社会急进派必定要如何如何的改良,多是不可能。”⑩
《新青年》的这场旧剧批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戏剧)界和传统戏曲界都有不同反响。新文学(戏剧)界大致有两种声音。鲁迅、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洪深、向培良等人赞同《新青年》批判旧剧,其观点如沈雁冰所说:“中国旧戏是行不下去了,总得改良;这是大概对于旧戏没有癖嗜的人们相同的意见。怎样改良呢?这也有一个大概相同的答案,就是‘借西洋戏剧已有的成绩做个榜样’。”⑪宋春舫、田汉、余上沅、赵太侔、黄远生等人对于新、旧两派各有批评,提出了既不同于《新青年》派也不同于张厚载的见解:提倡话剧,改良戏曲。宋春舫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批评张厚载的言论是“囿于成见之说,对于世界戏剧之沿革,之进化,之效果,均属茫然”;也批评《新青年》派的主张是“大抵对于吾国戏剧毫无门径,又受欧美物质文明之感触,遂致因噎废食,创言破坏”⑫。
《新青年》的批判来势凶猛,传统戏曲界大受震惊,纷纷撰文为旧剧辩护,也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主张改良,一部分主张保守本来面目。后者即保守派极力抵拒《新青年》的批判,其观点大都如同张厚载,更多为唱腔、脸谱、打把子辩解,再三声言改良戏曲“多是不可能”。前者即主张改良派,如齐如山、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金悔庐、徐凌霄、刘守鹤、马肇延等,他们强烈感受到,传统旧剧在现代中国“要想打开一条路,非得从全貌着手计划不可。‘念白’表明情节,‘做工’辅助不足,利用锣鼓的声音来表现剧情的紧缓,振作观众的精神,使台下不知道台上是真、是戏,喜乐悲哀都要使看客同情,那才叫戏剧呢”⑬!不再只是从唱腔、脸谱、打把子等技艺层面谈论戏曲,同时注重“剧情”中所体现的“精神”和“同情”。因此,有感于晚清以来戏曲日渐衰微,1932年,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国剧学会”,程砚秋主持的音乐戏曲研究院创办《剧学月刊》,都强调改良戏曲,为戏曲在现代中国社会、在世界戏剧大潮中寻求生存空间。
不难看出,对于《新青年》批判旧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戏剧)界和传统戏曲界大都持肯定态度,出现完全负面评价是从40年代开始的。
抗战时期,因为日寇侵略激起国人强烈的民族感情,在此特定语境中引发的“戏剧民族形式”论争,使《新青年》批判旧剧又被重新提起。有比较中肯、辩证的评价,然而也有尖锐的、否定性的意见。前者如柯仲平指出:“‘五四’时期产生的新艺术,是对于中国艺术传统的一次否定,在这次否定过程中,是使内容更加丰富了。到了抗战时期,却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在这阶段上,会使艺术到一个较高的综合。”⑭后者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庚的观点。张庚认为《新青年》“那时对于中国戏剧运动的意见是:完全消灭旧剧,从全部接受西洋戏剧中间来建设中国的新戏剧”,认为“‘五四’在文化上所贡献的是向西洋学习了许多近代的思想和技术,‘五四’并没有创造出自己民族的新文化,因而也没有创造出新戏剧来”⑮。这是新文学(戏剧)界自身第一次尖锐地、否定性地评价《新青年》批判旧剧,并且这种评价随着《新青年》主将陈独秀、胡适等在20世纪中叶长期被批判,而少有人为其辩护。当然,情况也不尽然。1959年,戏曲家任桂林这样评价《新青年》杂志批判旧剧:“破除了对于旧戏曲的迷信,揭开了戏曲改革的新的一页,这就是‘五四’时代的大功绩。”⑯
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新青年》批判旧剧的评价更为复杂。戏曲界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新青年》批判旧剧,已经少有如周信芳、徐凌霄、马肇延、柯仲平、任桂林那样比较辩证的评价。在新文艺界,既有夏衍、陈白尘、董健等坚守“五四”戏剧精神而仍然肯定《新青年》批判旧剧者,也有不少论者站在批判《新青年》的立场上。批判者继续20世纪40年代所谓《新青年》“完全消灭旧剧,从全部接受西洋戏剧中间来建设中国的新戏剧”的批判思路,并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认为《新青年》杂志批判旧剧是要“将它尽行抛弃,完全以西洋的戏剧来取代它”⑰;认为批判旧剧是“以西学作为惟一的标准”,是受“五四前后所形成的全盘欧化和反传统的影响”⑱;认为批判旧剧是“把欧美戏剧看成是唯一最佳的戏剧形态”,“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过于草率、过于简单化的进攻”⑲;甚至认为《新青年》批判旧剧是“民族虚无主义”,并且产生“颇为恶劣的影响,这种影响还颇为长远”⑳。总之,《新青年》批判旧剧是要“完全消灭旧剧”,是“全盘西化”,是“民族虚无主义”。
二、《新青年》批判旧剧着重批判什么
关于《新青年》对旧剧的批判,首先必须弄清楚两点:一是《新青年》是否整体批判中国传统戏曲;二是《新青年》批判传统戏曲着重批判什么?
关于第一点,可以肯定,《新青年》不是整体批判中国戏曲,而是批判晚清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发展。《新青年》派并不否定民族戏曲艺术,恰恰相反,在视戏曲为旁门左道、不登大雅之堂的封建传统观念深厚的旧中国,是他们首先在北京大学设立“元曲”科目教授戏曲。当社会上某些顽固保守者攻击此事时,身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愤然撰文反击。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这两篇著名的新文学运动发难文章中,胡适和陈独秀更是一反封建传统文学观念,把元明剧本列为中国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新青年》批判旧剧,就连最偏激的钱玄同都没有否定杂剧、传奇等古典戏曲,而是指向“今之京调戏”。这一点,其实在当时社会已经成为共识,认为古典戏曲尚能“劝善惩恶,抒写性情”,晚清以来“戏剧之劣,离奇怪诞”,舞台上“今日之社会,遂演成盗贼凶残淫恶鬼怪之社会”㉑。
关于第二点,表面上看《新青年》批判旧剧,似乎都是针对戏曲的唱念做打艺术表现的,然而,其根本和实质却是针对戏曲艺术形式所包含的思想情感。仍以钱玄同为例。钱玄同对于旧剧“全数扫除,尽情推翻”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其批判立足点却是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所张扬的“思想”“情感”和“文学上之价值”。他正是由此批判晚清以来戏曲“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实际上,“五四”时期批判旧剧都是着重这个层面,因为人们认识到旧剧“形式上的‘家法’”背后是更严重的“精神上的‘家法’”:一是“荒诞主义”,它“汩没人生高深的理想,引诱社会迷信狐鬼神仙,却忘记了真实的生活”;二是“崇古主义”,它“阻碍进化的机会,销磨个人的特性,造成复古的思想”;三是“训教主义”,它“将三皇五帝以来习俗上所认定的公案,翻出来作道德的标准……这种训教主义简直就是专制主义”㉒。周作人也因此把旧剧看作是中国传统“非人的文学”的“结晶”,声言“中国旧戏之应废”㉓。这其中的情形沈雁冰看得极为透彻。他认为“中国旧戏非改良不可”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旧戏的艺术如脸谱等等有点要不得;一是旧戏的思想要不得。”如何改良?他说:“舞台艺术更是现在一般热心者所要努力改良,不过我以为若不先从思想方面根本改革中国的戏剧,舞台艺术等等都只是一个空架子,实际上没有多大益处。”㉔
更重要的是,对于晚清以来戏曲的批判其实并非从《新青年》开始,清末民初梁启超、柳亚子等人先后发起戏曲改良运动,对于晚清以来的戏曲展开过激烈批判,并且不只是新文化界批判,戏曲界自身同样也在批判,甚至是更为激烈的批判。
批判什么?作为“五四”戏剧运动的前奏,清末民初戏曲改良运动也是着重批判旧剧的思想内涵。无论是新文艺界,如欧榘甲批判旧剧舞台“红粉佳人,风流才子,伤风之事,亡国之音”,陈独秀批判旧剧演出神仙鬼怪、富贵功名、诲淫诲盗是“俚俗淫靡游荡无益”,周剑云批判旧剧“多妖神鬼怪之状,淫靡谑浪之音,猥亵不堪之态”,许啸天批判旧剧“纳全国人民之思想、事业俱出于淫亵劫杀鬼神之一途,于是中国人民奄奄无生气”㉕;还是传统戏曲界,如汉血、愁予批判旧剧“神仙鬼怪之荒唐,功名富贵之俗套,淫邪绮腻之丑状”,齐如山批判“吾国演戏,有许多淫词浪态之剧,实在是有伤风化”,扬铎批判旧剧“既失规劝之旨,杂进靡曼之词。世道人心,慆淫邪僻。台榭歌舞,妖冶谑浪”㉖等等,他们都是批判晚清以来旧剧演出的思想内涵的鄙陋不堪、伤风败俗,及其毒害民族国家、百姓大众的严重情形。
同样地,清末民初批判旧剧有时也“恨屋及乌”,连同戏曲艺术表现也一并予以批判,出现如认为“演旧剧者,台步古怪,化装离奇”㉗,甚至有“梨园优伶,驼舞骡吟,淫词亵语,丑态百出”㉘,“以一群无学问、无道德、无人格之伶人,演一派无价值(淫戏、迷信戏)无来历(旧戏多荒诞不经)无理由(皮簧、梆子岂古人之谈话乎)之旧戏”㉙等言词。比《新青年》更早,这是文艺界第一次偏激地批判戏曲艺术形式。
更有甚者,1914年前后,新剧界和旧剧界各是其是、相互菲薄,还出现了冯叔鸾《戏剧改良论》所说的“今之言旧剧改良者,动辄曰废去演唱”㉚的激烈情形。“废去演唱”即是胡适所谓“今后之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白”。新、旧剧界曾围绕戏曲改良是否“废去演唱”展开论争。冯叔鸾在上述文章中强调“旧剧之精神在演唱”,比张厚载更早,对戏曲艺术的“乐本体”有深入阐释;恽铁樵、蒋兆燮、严独鹤等人为《鞠部丛刊》作序,再三声言“唱不可废”㉛。实际上,新、旧戏剧的矛盾冲突自清末民初就已开始,激烈程度今日难以想象。这是文艺界第一次偏激地提出要“保护新剧,推翻旧剧”㉜,比《新青年》更早,且不是个别言论。从论者“吾兹之所谓戏剧进化,非普通一班废止旧剧、专谈新剧之说也”㉝可以看出,在1914年前后,这是一股不小的思潮。
梳理清末民初以来对于旧剧的批判,不难发现,贯穿其中的批判锋芒都是指向旧剧陈腐落后的思想意识,涉及戏曲艺术表现的,大都是“恨屋及乌”的愤激之语。又因为晚清批判不够彻底,旧剧情形依旧,故“五四”时期展开了再批判。如欧阳予倩所说,“今日之剧界,腐败极矣”,“中国旧剧,非不可存,惟恶习惯太多,非汰洗净尽不可”㉞,并且这种批判在“五四”之后相当长时期都持续着。如1926年前后,强调中国戏曲在世界剧坛具有独特魅力的“国剧运动”派,也认为“旧剧变成了纯艺术……只能供给感官的快感,缺乏了情绪的触动……已成了畸形的艺术”㉟,对于旧剧思想意识同样给予尖锐批判。
对于旧剧的批判,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所转变。此时,一方面是新文化界仍然批判旧剧,但是也从戏剧的救亡、启蒙着眼,看到戏曲演剧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可以联合或采用旧剧去鼓动和启蒙民众;另一方面,在民族危难面前,旧剧界不再演出那些思想意识陈腐落后的剧目,而是以演剧参与到民族解放运动中来。30年代初,左翼戏剧家联盟要求采取“新演剧的形式或民间传统演剧的形式”,“积极利用在过去民间娱乐中占极大优势的庙戏与社戏”;抗战时期,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强调“各种新的旧的地方的戏剧之互相影响互相援助,必能使中国戏剧艺术在相当年月后达到更高的完成”㊱。此后,新、旧剧界没有再发生尖锐的冲突,开始携手并进,共同推动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
三、《新青年》为什么要批判旧剧
《新青年》批判旧剧肯定是偏激的,且不乏外行之论,然而,更需要和更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作为对于戏剧少有研究的非戏剧界中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和社会改革者,《新青年》的重要作者为什么要批判旧剧?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这桩百年学界公案。
关于《新青年》当年的文学批判,茅盾(沈雁冰)这样说,《新青年》“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他们对于文学的议论。他们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旧文艺”。接着,他从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展全局出发指出:“这是‘五四’文学运动初期的一个主要的特性,也是一条正确的路径。”㊲
茅盾的论述精辟、深刻。事实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正是着重从文化批判立场去审视旧剧的。他们认为晚清以来中国走向衰微,文化问题是症结,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走向振兴和现代化的障碍,所以“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㊳。也因为戏剧较之其他文学样式更具社会效应,于是《新青年》杂志1918年6、10两个月先后推出“易卜生号”和“戏剧改良号”,力求通过激进的戏剧革命来推进中国戏剧的现代化。以救亡为目的,以启蒙为途径,以反传统为形式,是《新青年》批判旧剧的根本立场。
显而易见,《新青年》不是从戏剧艺术角度,而是把中国戏剧现代化与中国社会、思想和人的现代化结合起来去审视和批判旧剧的。如刘半农说:“从事现代文学之人,均宜移其心力于皮黄之改良,以应时势之所需。”㊴这也是《新青年》所代表的“五四”文学(戏剧)的现代精神,它对于传统戏曲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此后,不仅是新文学(戏剧)界,戏曲界也将“应时势之所需”作为旧剧改良最重要的方面。1932年,戏曲理论家刘守鹤批评旧剧界“不肯使戏曲跟着时代前进,这是中国戏曲艺术一个危机”㊵;1947年,戏曲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痛感(平剧)再不加以适当改革,必定要没落的,而首先得把平剧的内容改得适合潮流”㊶等等,都是从救亡、启蒙出发对于旧剧的批判。
晚清以降,中国出现两种思想危机:民族救亡危机和价值取向危机。是救亡图存激发了梁启超、柳亚子等人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建构启蒙国民大众的“现代民族戏剧”及其运用戏剧张扬民族国家意识的愿望。他们看到戏剧在社会变革中不可替代的开启民智的作用,感到传统旧剧在严酷现实面前的尴尬和无力,从而将社会变革与戏剧变革结合起来:“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㊷柳亚子从“开民智”和民族“独立”“自由”出发,呼唤人们用演剧“运动社会,鼓吹风潮”,以“翠羽明珰,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㊸即为典型。汪笑侬的《党人碑》等改良戏曲获得热烈赞誉,也是因为其舞台演出“具爱国之肺肠,热国民之血性”,能够起到“大声疾呼,而唤醒国民于梦中”的作用㊹。然而,清末民初以来的戏曲改良不尽如人意,至“五四”时期,戏曲界整体上落后、陈腐的情形依旧。这样,时代对于戏剧的社会需求与戏剧发展现状就形成一个巨大矛盾。既然旧剧在当时还无力应对现代中国社会,还不能承担“代表一种社会,或发挥一种理想,以解决人生之难问题,转移误谬之思潮”㊺的使命,于是,《新青年》就在精神层面上强调借鉴西方戏剧的根本意义,注重以西方戏剧的现代精神作为中国戏剧现代化的方向。
田汉认为胡适等《新青年》同人正确地估定了京剧代替昆曲的“革命性”,也正确地批判了京剧“到如今弄成一种既不通俗又无意义的恶劣戏剧”,缺点是把中国戏剧发展看成“由歌剧到话剧”㊻。田汉的文章触及《新青年》批判旧剧一个最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主张引进西方话剧,甚至主张把戏曲改良成话剧?
这就牵涉到晚清以来中国戏剧发展的根本问题,即如何创造现代中国所需要的戏剧。清末民初的思路,首先是改良戏曲;后来看到戏曲改良不尽如人意,就引进西方话剧,或是直接把戏曲改良成话剧。很明显,《新青年》派就是看到旧剧不能“应时势之所需”,从而主张借鉴西方话剧,主张把戏曲改良成话剧。实际上,钱玄同所谓戏曲“脸谱派”,刘半农所谓戏曲“恶腔死套”,胡适所谓戏曲“遗形物”,这些对于戏曲绝对外行的文化先驱者,用了绝对偏激的言词来批判戏曲表现形式,绝对不是要故意丑化戏曲的艺术表现,而是出于要“推翻”这些表现形式而把戏曲改良成话剧的思考。这一点,即便是批评《新青年》派“大抵对于吾国戏剧毫无门径”的宋春舫,都看得清清楚楚。他说:“激烈派之主张改革戏剧,以为吾国旧剧脚本恶劣,于文学上无丝毫之价值,于社会亦无移风易俗之能力。加以刺耳取厌之锣鼓,赤身露体之对打,剧场之建筑既不脱中古气象,有时布景则类东施效颦,反足阻碍美术之进化。非摈弃一切,专用白话体裁之剧本,中国戏剧将永无进步之一日。”㊼
为什么《新青年》派主张借鉴西方话剧,进而要把戏曲改良成话剧?就是因为话剧更具现代精神,更符合现代中国的社会需求和审美需求。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戏剧变革的根本缘由是救亡与启蒙,戏曲也在努力进行,但就社会效能而言,“自然是新戏比旧戏好,为什么呢?因为新戏情形较真,感化人的力量比旧戏大”㊽。齐如山作为戏曲家,他对于话剧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关系的论述更具说服力。其实这种看法在当时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所以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主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欲以社会、家庭、学校等方式施行文艺、公民、卫生、生计四种教育,以疗治中国愚、穷、弱、私四大病症,他们在河北定县农村以戏剧作为文艺教育,也鉴于“旧剧在今日的农村虽仍是很盛行,然而它没有时代精神,对于现代这个时代是极不适宜的”,因而“要把现代的话剧装上农民可以接受的内容,介绍到农村”㊾。
《新青年》派要“推翻”旧剧的表现形式,主张把戏曲改良成话剧,当然与其机械进化论思维有关,但是在深层却是包含着他们从思想启蒙角度对于戏剧发展的思考。梁启超曾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㊿这也是晚清以来中国戏剧发展的趋势。晚清戏曲改良注重社会教育,就已经出现“编情节甚多,故讲白长而曲转略。以斗笋转接处,曲不能达,不得不借白以传之”的情形。与此同时,戏剧界认识到话剧表现社会人生的独特效能,又出现创建话剧或把戏曲改良成话剧的趋向。1904年,就有戏剧家“为中国普通社会开通智识、输进文明计”,呼吁学习日本,提倡“演剧之大同,在不用歌曲而专用科白是也”。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代自日本考察回国的吴荫培向光绪皇帝上奏折,提出应予改良的五条“当务之急”,其中一条就是戏剧改良:“戏剧宜仿东西国形式改良。将使下流社会移风易俗,惟戏剧之影响最速。日本演戏,学步欧美……说白而不唱歌,欲使人尽能解。中国京沪等处戏剧已渐改良,惟求工于声调,妇孺不能遍喻。似宜仿日本例,一律说白。”民间与官方在这一点上的“共谋”,造成当时“将旧戏改为新剧”的不小声势。强调现代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的《新青年》派,主张“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白”,正是清末民初以来这股启蒙思潮的继续和发展。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青年》派要偏激地“推翻戏曲”即批判戏曲的艺术表现了。在具有深厚传统亦具有严重保守性和排他性的中国剧坛,他们提倡话剧,“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矫枉过正即是这种压抑下必然出现的变革心态。刘半农后来说得很明确:“正因为旧剧在中国舞台上所占的地位太优越了,太独揽了,不给它一些打击,新派的白话剧,断没有机会可以钻出头来。”而当话剧站稳脚跟之后,对旧剧就“不必再取攻击的态度;非但不攻击,而且很希望它发达,很希望它能够把已往的优点保存着,把已往的缺陷弥补起来,渐渐的造成一种很完全的戏剧”。1930年梅兰芳去美国演出,胡适特地撰文,阐释戏曲“种种历史上的遗形物都以完美的艺术形式给保存并贯彻了下来”,并且认为“正是这种艺术上的美经常使原始的常规惯例持久存在而阻碍它进一步成长,也正是这种戏剧发展和戏剧特征的原始状态更经常地促使观众运用想象力并迫使这种艺术臻于完美”。
四、如何评价《新青年》派批判旧剧
显而易见,《新青年》批判旧剧不是就戏曲论戏曲的学术讨论,而是一场在戏剧领域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运动,目的是促进中国戏剧的现代化和中国社会、思想及人的现代化。故评价《新青年》批判旧剧,也不能就戏曲论戏曲,只有从救亡启蒙、民族振兴的角度,把它放到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进程中予以考察,从戏剧发展战略的意义上去分析,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其一,关于所谓要“完全消灭旧剧”。
首先必须明确,《新青年》批判旧剧是激烈反传统,但不是要“完全消灭旧剧”,也不是要“割裂民族戏曲传统”。《新青年》对于中国旧剧的批判和对于西方话剧的推崇,是一场源于思想启蒙的戏剧运动,其目的如胡适所说,是要“重新估定旧戏在今日文学上的价值”以“再造文明”,即创造中国现代戏剧。这场戏剧运动振聋发聩,连戏曲界的先进者都充分肯定《新青年》对于包括旧剧在内的“中国旧有的文化施行一种毫不容情的总攻击”,认为“这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实在是一种划时代的进化的凭证,不但不容吾人随便加以蔑视,反之,在求一国文化的复兴、改造与突跃的进展上,在求增加东西各民族间的精神上的了解与夫实现将来的‘大同国际’这一理想上,我们都必须要把无论东西中外的文化精神沟通一致,而以彼此的优点熔化于一炉,因而可以创造出一种更进步、更优美、更成熟的新的文化”。现代戏曲发展的事实证明,正是这场批判促使戏曲界在世界戏剧格局中审视、反思自己的传统,进而把西方戏剧精神衔接到自己的传统里,扩大了戏曲的思想空间和表达维度。
所憾者,《新青年》派不加辨别地把西方戏剧作为价值评判标准,把传统旧剧与现代戏剧完全对立,要从推翻旧剧入手去开启中国现代戏剧,并且他们对于戏曲确实是外行,行文用词又带谩骂,这些都造成了恶劣影响,导致新文化界对于戏曲的轻视态度。继《新青年》之后,陈大悲等开展“爱美剧”,沈雁冰等倡导“民众戏剧”,以及夏衍、郑伯奇等张扬“普罗戏剧”等等,都把批判戏曲作为开路的先导。这就使戏曲在长时期里没有进入新文化界的视野。如此,戏曲界除部分先进者外,其整体衰败、没落的情形是比较严重的。
然而尽管如此,这场批判并没有“完全消灭旧剧”或“割裂民族戏曲传统”。相反地,批判触及到戏曲发展某些根本问题,引起国人对于旧剧的深刻反省。批判冲击了传统戏曲的封建思想意识,冲击了传统文化的惰性和保守性,赋予戏曲以新的生命力。戏曲界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一点。最值得体味的是冯叔鸾的观点。冯叔鸾当年也是挺身反驳《新青年》对于旧剧艺术表现的偏激批判,可是后来,他看到戏曲界终日醉心于唱腔、脸谱、打把子,“听说有人主张改良旧戏,便以为是不可能的事”,他又批评这些人“再也不能跳出圈外,来看一看旧戏根本上的得失”。什么是“根本”?他强调首要的是“主义要合于现代思潮”。即便是在旧戏迷所陶醉的唱念做打艺术表现方面,戏曲界先进者也都感受到这场批判的强烈冲击。徐凌霄指出,“从前之旧戏迷对于戏剧亦很少有正确的认识(名伶技术、老伶故事,是枝节不是本体)”,经过这场批判,“旧伶迷曲迷们亦渐渐把目光移转到戏剧的组织艺术的整个上来了……所以攻击‘旧剧’者,也未尝不是中国戏剧的功臣”。透过这些著名戏曲家的论述,可以强烈感受到《新青年》抓住的正是戏剧艺术的“根本”和“本体”,也可以强烈感受到一种“现代戏曲”正在挣扎中新生的气象。现代戏曲实践正是这样发展过来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田汉的《江汉渔歌》、欧阳予倩的《梁红玉》、杨绍萱和齐燕铭的《逼上梁山》、马健翎的《血泪仇》等剧本创作趋向成熟,尤其是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的舞台演剧将戏曲表演艺术推向高峰。如此,何有“完全消灭旧剧”或“割裂民族戏曲传统”?
准确地说,《新青年》派批判旧剧不是为了推翻传统戏曲,而是要为中国现代戏剧建构一个新的体系和精神,要把戏曲和话剧都纳入到这个新的体系和精神之中共同发展。
其二,关于所谓“全盘西化”。
《新青年》派批判旧剧的偏颇激进,即如当年他们鼓吹废掉汉字改用拼音文字,鼓吹读西洋书而把中国古籍丢进茅厕一样,确实有“全盘西化”的嫌疑。关键是要弄清楚为什么《新青年》批判旧剧那么偏激,弄清楚其偏激批判是否真就导致了“全盘西化”。
如上所述,《新青年》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视野下,去批判旧剧和促进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这种现代化其实在清末民初就开始了:“戏剧何必分新旧?日新又新,事贵求新,应新世界之潮流,谋戏剧之改良也。新剧何以曰文明戏?有恶于旧戏之陈腐鄙陋,期以文艺、美术区别之也。”《新青年》顺应时代大潮,紧紧抓住的也正是“应新世界之潮流,谋戏剧之改良也”。而当时旧剧还难以承担“应新世界之潮流”的使命,那么,批判旧剧、改造旧剧,或者把旧剧改良成符合现代中国社会需求和审美需求的话剧,就在情理之中。中国戏剧的现代建构,保存固有血脉和接纳世界新潮是并列的,但是,由于古老的民族要走出封闭,当务之急是全力打开自己的现代世界视野,进行根本性的改弦更张;加上戏曲传统的惰性力量强大,不如此激烈批判,就不足以引起社会的重视和反省。
此即胡适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社会,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新文明。《新青年》批判旧剧,甚至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矫枉过正、偏颇激进,都是这种“片面的深刻”,不能脱离具体语境去评价,也不能就其自身是否“全面”“公允”来评价,而要从它对于中国戏剧现代建构所起的作用来判断。应该说,正是这场批判给中国戏曲带来诸多新的质素,促进戏曲走向现代,促使中国戏剧和戏剧理论趋向深刻和全面。《新青年》派并非真要彻底否定戏曲,也并不认为戏曲可以被彻底否定掉,其主张更多的是促进戏剧现代化的文化战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批判并没有使中国戏剧“全盘西化”,而是走向现代化。
经过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充满自信力,对于包括戏曲在内的民族文学艺术的态度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亨廷顿说过,非西方社会在现代化早期是“西化”促进现代化,现代化后期是现代化推动“去西化”。故不能用今天保守理论的正确去否定早期激进理论的合理性,更不能说我们今天要弘扬民族戏曲艺术,就认为《新青年》批判旧剧是完全错误的。柯仲平的看法比较辩证,传统戏曲在现代发展需要经过“否定之否定”,才能成为现代戏剧。中国话剧发展也是这样:“过渡期的戏剧总不免彻头彻尾地挂着西洋风味,来日的戏剧自必充满我们这一民族的生命力。”
其三,关于所谓“民族虚无主义”。
“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对包括戏曲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包括话剧在内的西方现代文化的推崇,是被某些学者视为“民族虚无主义”的主要原因。批判《新青年》者忽视了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即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不能满足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人民生存的基本要求而必须有所改变,必须走向世界而充分接受西方现代文化。也就是说,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更多是在传统之外变革和发展的。在传统之内发展较易看到传统正面的东西而有利于传统的延续,在传统之外发展则更多是反传统而改变传统,或是促使传统向现代转型,都面临着对于传统的批判、扬弃、变革的严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其保守性、排他性强大,故《新青年》反传统自然激烈,所以评判《新青年》批判旧剧是不是“民族虚无主义”,首先必须弄清楚《新青年》的批判是出于什么目的:是要诋毁民族戏曲艺术,还是另有其他重要缘由?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如上所述,《新青年》批判旧剧是从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中国戏剧现代化出发而展开的。正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导致《新青年》激烈地批判旧剧,而他们的激烈批判又有力地推动了运用戏剧参与救亡和启蒙的现代戏剧运动。显而易见,“五四”先驱者激烈批判中国旧剧和大胆引进西方话剧,是力图以西方戏剧矫正中国传统戏剧的缺陷,其文化策略是:“以抛弃传统文化的方式认同民族国家,以援引西方文化资源的方式抵抗西方文化殖民。”这也是晚清以来、尤其是“五四”时期先驱者批判旧剧的主要缘由。试想,世上哪有为了救亡启蒙、民族振兴的“民族虚无主义”?
清末民初以来,整个中国都处于“新旧对峙”“新旧挣扎”之中,中国一切学说“非适合世界现势,不足促国民之进步”。故20世纪中国任何理论,都要把它放在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去审视和评价。能促进中国社会、思想和人走向现代的,是进步的;反之,则是落后的、反动的。就《新青年》批判旧剧来说,张厚载虽然从戏曲艺术层面来说是内行,但是他对戏剧与时代、现实和人的关系懵懂无知;《新青年》派尽管对戏曲艺术是外行,然而他们正确地把握住了戏剧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正确地把握住了戏剧发展的“根本”和“本体”,从而推动传统戏曲走向现代、走向世界。
《新青年》批判旧剧,其实质是《新青年》派的救亡、启蒙而追求现代化的“反传统”的变革意识,和张厚载等人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反—反传统”的认同意识之间尖锐冲突,从而导致的传统与现代、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此时,“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因而偏颇和过激都是存在的,但是,《新青年》的批判不是要“完全消灭旧剧”,不是“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
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思想、人的现代化和中国戏剧的现代化,传统戏曲在当代中国的使命和我们对传统戏曲艺术的认识,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我们在继承“五四”的同时又要超越“五四”。继承“五四”,就是不能因为时代变化而否定“五四”现代戏剧精神;超越“五四”,就是对传统旧剧批判的绝对主义倾向应该矫正。没有继承的超越,容易蹈空;没有超越的继承,容易停滞。应该是,坚持启蒙现代性的“激进”观念又能尊重传统的价值,在批判传统的惰性的同时发掘和转换传统中的现代质素;坚持传统戏曲美学的“保守”观念要懂得现代的意义,不能简单地与传统拥抱而失落现代意识。如此,才能创造真正的现代戏曲艺术。
①⑮ 张庚:《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载《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3期,1939年10月。
② 参见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页;王元化《〈学术集林〉卷七编后记》,《学术集林》卷七,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475页。
③⑰⑳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论》,第636页,第636页,第636页。
④ 钱玄同:《致陈独秀》,载《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
⑤ 钱玄同:《随感录》,载《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
⑥㊴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载《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
⑦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载《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
⑧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载《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
⑨ 张厚载:《新文学及中国旧戏》,载《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
⑩ 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载《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
⑪㉔ 雁冰:《中国旧戏改良我见》,载《戏剧》第1卷第4期,1921年8月。
⑫㊼ 宋春舫:《戏剧改良平议(1918)》,《宋春舫论剧》,中华书局1923年版,第264—265页。
⑬ 周信芳:《答黄汉声君》,载《梨园公报》1930年8月29日。
⑭ 柯仲平:《介绍〈查路条〉并论创造新的民族歌剧》,载《文艺突击》第1卷第2期,1939年6月。
⑯ 任桂林:《“五四”运动和戏曲革新》,载《戏剧研究》1959年第2期。
⑱ 王元化:《〈学术集林〉卷七编后记》,《学术集林》卷七,第323页。
⑲ 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第474—475页。
㉑ 杜鹃:《戏剧与社会》,载《梨影杂志》第2期,1918年10月。
㉒ 涵庐(高一涵):《我的戏剧革命观》,载《每周评论》第10号,1919年2月23日。
㉓ 周作人:《论中国旧戏之应废》,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
㉕ 参见无涯生(欧榘甲)《观戏记》,《清议报全编》第25卷,新民社1903年版,第162页;陈独秀《论戏曲》,载《安徽俗话报》第11期,1904年9月10日;周剑云《负剑腾云庐剧话》,载《繁华杂志》第1期,1914年10月;许啸天《我之论剧》,载《新剧杂志》第1期,1914年5月。
㉖ 参见汉血、愁予《〈崖山哀〉(〈亡国痛〉)导言》,载《民报》第2号,1906年5月;齐如山《观剧建言》,京师京华印书局1914年版,第5页;扬铎《汉剧丛谈》,法言书屋1915年版,第1页。
㉗ 汪仲贤:《新剧丛谈》,《新剧史·杂俎》,新剧小说社1914年版,第30页。
㉘ 曾中毅:《说吾校演剧之益》,载(南开)《敬业》第1期,1914年10月。
㉙ 周剑云:《〈新剧考〉序》,《新剧考》,中华图书馆1914年版,第1页。
㉚ 冯叔鸾:《戏剧改良论》,《啸虹轩剧谈》,中华图书馆1914年版,第2页。
㉛ 参见周剑云主编《鞠部丛刊》,交通图书馆1918年版,第1—3页。
㉜ 秋风:《新剧界之对抗力》,载《新剧杂志》第2期,1914年7月。
㉝ 瘦月:《戏剧进化论》,载《新剧杂志》第2期,1914年7月。
㉞㊺ 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载《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
㉟ 赵太侔:《国剧》,载《晨报副镌》1926年6月17日、24日。
㊱ 参见《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载《文学导报》第l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载《抗战戏剧》第1卷第4期,1938年1月。
㊲ 茅盾:《导言》,茅盾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页。
㊳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㊵ 刘守鹤:《确定演剧的人生观》,载《剧学月刊》第1卷第5期,1932年5月。
㊶ 梅兰芳:《身段表情场面应改善 改革平剧需要导演》,载《星期六画报》第53期,1947年5月17日。
㊷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清末民初“小说”概念包括戏剧。
㊸ 亚卢(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载《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号,1914年10月。
㊹ 佚名:《编戏曲以代演说说》,载(天津)《大公报》1902年11月11日。
㊻ 伯鸿(田汉):《中国旧戏与梅兰芳的再批判》,载《中华日报》1934年10月21日。
㊽ 齐如山:《新旧剧难易之比较》,载《春柳》第1年第2期,1919年1月。
㊾ 《农村戏剧》,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4年版,第4、5页。
㊿ 梁启超等:《小说丛话》,载《新小说》第1卷第7期,19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