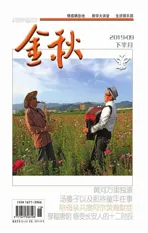少年时,不懂爱情
2019-12-19北京从维熙
◎文/北京·从维熙

说起来真像是一场梦,说得确切一点,那是我的一场童真年代的“糊涂梦”。
我于1946年从农村到北平求学,插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一天,我们正排队准备进课堂时,站在我后排的同学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我不知何意,便回过头去好奇地寻找笑源。就在这时,一位名叫刘惠云的女同学,朝同学们大声喊道:“笑!有什么好笑的,人家是从农村来北平求学的,你们就……”我立刻不安起来,因为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来自乡下,难道同学们是在笑我?果不其然,当我把目光投向同学们时,后排的男同学都在对我嬉皮笑脸。女同学虽然大都把视线转向别处,但也有忍不住掩面而笑的。我正不知所措时,刘惠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从维熙同学,他们笑你裤子后边破了一个小洞,你放学回家后缝一下就行了……”我脸红了,顺手一摸,立刻抬不起头来了——因为在农村我们习惯于不穿内裤,显然是露出了臀部,才引起同学们的嬉笑。我从小自尊心很强,因而当时晕头涨脑,不知如何摆脱困境。最后,还是教我们国文课的关老师把我叫进办公室。我说我要请假回姥姥家,让姥姥缝补我的裤子。关老师剪了块胶布,贴在我裤子的破洞之处,然后拉着我的手,一起走进教室,让我跟她去上语文课。讲课之前,她批评了嘲笑我的同学,表扬了刘惠云的果敢。大概是为了树立我的自尊,关老师说我虽然来自农村,但作文是班里的标杆云云。从这天起,我知道了穿内裤的必要;从这天起,我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字——刘惠云。男同学在私下耳语时,都不称呼她的名字,而称呼她的绰号“刘白美”。
小学毕业,我到了东城内务部街的二中去读初中。在同班同学中遇到同乡学子谭霈生,我曾向他倾吐过这段丢人现眼的少年经历,以平息内心之痛。当时,我没有想到男女之间的任何事情,只是当作我的一次耻辱,直到我再次碰到她,才感到她对我的一片真情。有一次,学校去颐和园春游,胸前戴着女三中校徽的一队女生从我们身边经过。我刚迈过颐和园大门高高的门槛,就听见一声呼喊:“喂!前面走的是从维熙同学吗?”我听声音有些耳熟,回过头来一看,脸立刻红涨起来——呼喊我的竟然是曾为我打抱不平的刘惠云。
我走出队列,心跳如同擂鼓地说:“是你,你考上女三中了?”
她两步追了上来:“你上男二中了?”
两校同学对我们侧视而笑地走了过去,我和她便落在人流的后边。不知为什么,我不敢直视她,因为当天她脸颊嫩白,脖子上围着一条玫瑰红的围巾,与穿着一身黑色学生装的我,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我向她表达了迟到的谢意:“在小学时,感谢你为我这个‘小土包子’说话!”
她说:“当年我之所以为你鸣不平,是因为我感到你比城市的学生真诚。”
虽然此时天气还很凉,但我的额头还是滴下汗珠,正当我用袖口擦汗的瞬间,她伸出手来低声说:“让我们握个手吧,我们还没握过手呢!”
在我和她握手的刹那间,我朝队伍望去,看见同班同学都在回头看着我们俩,我顿时不知所措了。无奈之际,我失礼地说:“同学们都在等我,我得去追赶队伍了,再见……”说完,我转身就跑。她在我身后说:“我知道你在二中上学了,我会给你写信的,你要注意查收信件……”一幕颐和园巧遇的戏剧,虽然匆匆收场,但接下来上演的“糊涂梦”,更使我内疚至今。
春游归来不久,我当真接到她的一封来信,信封上标注的地点是西四北大红罗厂她家的地址,信中除回忆同学友情之外,还约我有时间和她一块儿去看一场电影。她说不用我回她的信,请用电话回答她的邀请,她在信尾留下了她家的电话号码。我虽然属于不开窍型少年,但毕竟在北平耳濡目染了几年,仅从她家中装有电话,就可以断定她是官宦家庭的娇女——因为在1947年,电话还是个稀有物,同学们家中装有电话的几乎没有。当时我就读的二中,只是传达室装有一部供学生使用的电话。
我记得给她回电话时,拨号的手一直在哆嗦。她在电话中显得异常兴奋,约我星期日在西单商场旁边的蟾宫电影院见面,那儿正在上演美国电影《出水芙蓉》。我立刻一头雾水,因为从我来到北平之后,还没有进过电影院。怎么办?不答应,对不起她的真情;答应下来,又觉得胆怯。因为在童真年代,异性对我来说是充满了神秘感的不可知物。最后,我还是鼓足勇气说了声“好”。但应约之后,我便后悔了。我虽然身在名校二中,但是除了作文达标,代数曾得过零分,是班里理工科的低能儿,这不是“黄土”混充“朱砂”吗?
无奈之际,我只好又去求救于同乡学友谭霈生。他说他在颐和园看见过她的身影,人长得漂亮不说,还曾对我有过恩惠,我没有理由逃避。我请求他陪我一起前往蟾宫电影院,我再给他买一张电影票,为我壮胆。霈生说:“这不是给人家下不来台吗?人家看中的是你,我去只会扫人家的兴,而成为你们俩中间的‘绝缘体’。我不能去!”我缠着他死活不放,最后,他出于乡友之情和少年时代的好奇,极为被动地答应在星期天与我一起奔往蟾宫电影院。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俩出现在她面前的情景。她蛾眉高挑,生气地说:“票是事先买好的,现在没有票了,你们俩进去看电影吧,我家里还有事!”说罢,她便转身走了。我的一场“糊涂梦”到此收场。
后来听说在北平解放前夕,她随父母去了台湾。岁月如白驹过隙,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和谭霈生今天都已浪里白头(他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已退休)。当我们俩通电话时,我还不忘提及此事。我说:“你没忘记我的那场‘糊涂梦’吧?”他答:“怎么能忘记呢,不怨天,也不怨地,怨我们在童真年代不懂爱情,我去了,真的充当了‘绝缘体’,欠下了人家的一片情!”
也算是命运的巧合吧,生活给了我一个补过的机会。1988年年初,台湾诗人痖弦把一封向我约稿的信函寄到了中国作协,当时他主编台湾《联合报》副刊,说要在春节期间刊出大陆作家的专版,希望我能尽快给他写一篇文章。我苦思冥想了许久,突然忆起少年时不懂爱情的往事,便写了篇名为《寄梦》的文章给《联合报》。其文意是向我少年时代的刘惠云同学问好,祝福她事业有成,并有个美满幸福的人生。到了1998年,中国作家一行出访宝岛台湾时,我还不忘询问痖弦此事,他说《寄梦》的文章发表后,没有收到相关的信息,很可能她已离开台湾,到不知哪个国家去了。我说:“不论她飘到哪儿,都像她的名字一样,是一片关爱弱者的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