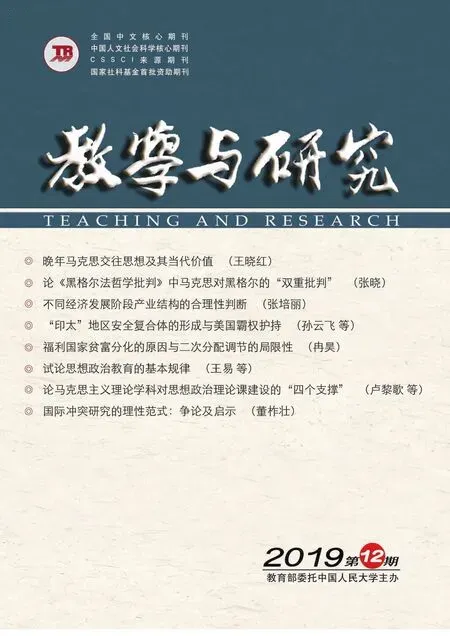事实·理论·策略:鲍曼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2019-12-18
作为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思想家和资本主义老牌斗士,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 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先后出版了“现代性三部曲”“后现代性三部曲”和流动的现代性系列,(1)现代性“三部曲”有:《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后现代性“三部曲”有:《后现代伦理学》《生活在碎片中:论后现代道德》《后现代性及其缺憾》;流动的现代性系列包括《流动的现代性》《流动的时代》《流动的恐惧》《流动的生活》等。对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产生重要影响,(2)贝克的自反性现代性理论深受鲍曼著作的影响。参见[德] 乌尔里希·贝克、[英] 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25、252页。甚至被誉为“当代西方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3)Peter Beilharz,“Reading Zygmunt Bauman:Looking For Clues,Tlues”,Thesis Eleven,Volune54,August 1998:25-26.虽然鲍曼写作主题不断变换,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是一以贯之的,其目的在于探究和揭示资本主义钳制乃至封闭人类选择可能性空间的运作机制。立足于资本的视角分析现代性的生成及其转型,是鲍曼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果说鲍曼对第一期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沉重的资本主义”,那么他对第二期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轻快的资本主义”,(4)[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90页。“沉重的资本主义”又称“福特式资本主义”,“轻快的资本主义”又称“后福特式资本主义”或“全球资本主义”。鲍曼把至今为止的现代性历史分为两期,即“现代性/后现代性”,后来又改称为“稳固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则是“轻快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鲍曼晚近写作主要关注后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主题,其实质是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全面批判。在他那里,“轻快的资本主义”甚至是比“沉重的资本主义”危害更大也更难对付的一种资本主义。鲍曼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不仅是贯穿其晚近著作的一根红线,而且具有多维立体的特征,既有事实层面的实证批判,也有理论层面的悖谬分析,还有操作层面的策略揭示。鉴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仍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的最主要思想武器,这一批判对于当今中国正确认识和有效抵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事实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实践后果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陷入空前的滞胀困境,具有强烈国家干预色彩的凯恩斯主义备受批评,于是作为凯恩斯主义的替代理论的新自由主义迅速走上历史前台,其间经历撒切尔、里根主义的强力推行,苏东剧变时的急遽扩张,特别以“华盛顿共识”出台为标志,新自由主义最终实现了由学术理论、经济政策到范式化、意识形态化的转变。“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5)[美]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3页。新自由主义核心理念是贸易自由化、定价市场化、财产私有化、责任个体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依靠个人和企业的自由,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世界经济政治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也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在鲍曼看来,今天全球化的世界并非如新自由主义宣传的那般美妙,而是一种单向度的全球化,为极少数权力资本赚取财富带来空前便利的同时,给人类绝大多数人口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一是全球普遍失序。在鲍曼那里,全球化不过是混乱无序的代名词。全球化传递的最基本信息就是世界事务处于无中心的失控状态,社会变得动荡不定、无法把握,灾难常常不宣而至,令人猝不及防,危险和恐惧弥漫于全球各个角落。在他看来,当前世界混乱无序状态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我们周遭世界的变化是反复无常的。如人们的工作、生活模式及社会秩序常常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瞬间消失,突如其来的变化具有令人无法理解的非逻辑、非理性的特征。其二,世界事务虽具有自生自发的自然性特征,但并非自然原因所致,而是人为制造的结果。在这点上,鲍曼与吉登斯、贝克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吉登斯和贝克更多地把原因归结为如科技等现代性机制本身的自反性,而鲍曼则明确指认不受约束的全球性资本是罪魁祸首。三是全球失序状况至今未见有变好的迹象。鲍曼忧心的是,现实中为应对全球无政府状态而采取的绝大多数举措,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加剧了全球乱象,并使之进一步固化。他认为,现代性曾经是一大进步,承诺使人类摆脱恐惧,它不仅将终结所有的意外和灾祸,也将终结所有的幻觉和不公正;“但是,原本以为的逃离路径却变成了漫长的迂回之途。五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时代再次成为恐惧的时代。”(6)[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恐惧》,徐超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二是贫富空前极化。鲍曼在其著作中运用大量实证材料对新自由主义宣扬的“滴涓效应”,即富人有钱最终也会让穷人受益的观点进行揭露和批判。在他看来,凡是新自由主义化的地区,贫富差距总在以空前的速度扩大。首先,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一国或地区内部各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都在扩大。鲍曼在《全球化》(1998)中提到,世界前358名全球亿万富翁的总财富相当于23亿占世界人口45%的最穷人口的总收入,只有22%的全球财富属于占世界人口大约80%的发展中国家。(7)[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7、68、63页。后来他在《此非日记》(2011)中又写道,尽管一些贫穷国家在追赶富裕国家,但全世界范围内最富和最穷的个人之间的鸿沟还在持续扩大。(8)[英]齐格蒙特·鲍曼:《此非日记》,杨渝东译,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108页。“全球化是一大悖论:它对极少数人非常有利的同时,却冷落了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或将他们边缘化了。”(9)[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7、68、63页。其次,新生穷人境况极其悲惨。鲍曼注意到,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所谓“X一代”两极分化趋势明显,他们中大部分人都遭受过失业的体验,患抑郁症的人日渐增多。(10)[英]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谷蕾、胡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并且,今天的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了社会位置,成了名副其实多余的人,因而被排除在道德义务之外,被贴上懒惰和犯罪等标签,不断遭受侮辱和监禁。更可怕的是,全球化使得冗余人口数量呈几何级攀升,几乎人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多余。鲍曼的《废弃的生命》(2005)一书集中记述了诸如经济移民、难民等我们这个时代被排斥群体的悲惨命运。
三是政治日益崩溃。一般来说,政治意味着协同一致的集体行动,意味着公共事务和私人忧虑之间的相互转换,是人类集体解决自身困境的唯一有效途径。鲍曼认为,“我们从未像现在一样需要政治,因为现在政治已经变得很困难、而且丧失能够架起桥梁的大部分能力了。”(11)[英]齐格蒙特·鲍曼、凯茨·泰斯特:《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话》,杨淑娇译,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第146页。当前的政治溃败主要源于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无能,即资本可在全球范围内移动,而政治只能停留在地方,这种不对称性的权力结构反过来又迫使地方性政治进一步放弃其社会职能,从而在根本上损害了政治信任和政治存在的基础。“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被摧毁了,主权和独立被剥夺了,政治阶级被消除了,它也就成了那些大公司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保安部门……。”(12)[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7、68、63页。在鲍曼看来,当前形形色色共同体的兴起,不过是现代西方民族国家政治走向衰落的一种应急反应和替代物,它们无论口号多么迷人,皆与以往民族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不具有后者的经济社会保障功能。(13)[英]齐格蒙特·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郑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6页。在全球层面,“政治真空一次又一次邀请了暴力协商”,(14)[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7、86页。全球政治权威的不在场使得暴力与恐怖主义的界线变得模糊,这表明反恐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在生活层面,因价值基准权威的缺失,“许多邻里和家庭暴力都把侦查战策略应用到了生活政治”,并且伴随民族国家对政治建构雄心的放弃,种族和宗教边界也变成了侦查战(在没有规范的情形下,通过战役或暴力进行侦查之意)双方的另一个战场。(15)[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7、86页。美国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主导者并没有阻止自己成为蔑视人权的元凶或帮凶,各个地方的民主也未能阻止人民退回到自己的私人庇护所。(16)[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9页。
四是人伦关系恶化。在鲍曼看来,全球化带给人类的首先是一个伦理挑战。全球化让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具有远距离后果,我们所作所为都与他人命运相连,这意味着在伦理上我们每一个人要对他人负责。但现实则是另一番情形,失控的世界让人类重新回到霍布斯世界,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野蛮状态。(17)[英]齐格蒙特·鲍曼:《怀旧乌托邦》,姚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 23页。首先,逃避责任成了当代人主导的生活策略。今天“避免为后果负责是新的流动性带给自由流动、不受地方限制的资本的最令人垂涎、最珍贵的好处”。(18)[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第10页。正是资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才使全球陷入失序混乱状态。当恐惧无所不在时,逃脱一切束缚和责任,以最大限度保持灵活性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如今极端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泛滥成灾与此背景不无关系。其次,对排斥的恐惧使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全球化带来的冗余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激增,而以往处理冗余人口的通道已被堵塞,“各个社会都越来越将排外实践针对自身的人民”。(19)[英]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第70-71、114页。第三,消费社会的兴起加速了人类伙伴关系的解体。鲍曼认为,当代全球化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消费者是一种特殊的群体,他们是“感觉追寻者和经历采集者”,世界和他人的关系主要是美学上的关系,追求的是最大刺激和瞬间满足。在人际互动中,双方同时都是消费者与被消费的对象,毫无道德责任可言。值得注意的是,消费本身也是最具私人性的,当一切问题的答案贴上了价格标签,并且可以通过购买获得,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不仅没有必要,甚至变得不可理喻。事实上,在鲍曼那里,当前脆弱的人际关系与我们面对邪恶时的无力感是相辅相成的。商场巨人安然公司轰然倒台,原因就在于公司“你死我活的工作文化”摧毁了雇员们的士气和内在凝聚力。(20)[英]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第70-71、114页。
二、理论解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悖谬逻辑
身为社会学家,鲍曼批判的影响力主要还是体现在其独特的理论分析上,即立足于“陌生化”的理论策略,娴熟运用多种思想和话语体系,层层撕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伪装,揭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悖谬。
一是运用“资本分离论”批判“普惠论”。鲍曼在吸收了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社会起源于“家庭和生意分离”思想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现代资本分离的思想,从资本的视角解读现代性历史。在鲍曼那里,现代性在其近四百年的发展中,共发生过两次大的资本分离,每一次分离都深刻影响了现代性历史进程。第一次资本分离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其中以英国最为典型,资本因脱离伦理的束缚获得了空前自由,这次分离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有详尽的描述;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特别是福利国家在发达世界的普及,资本最终走向与劳动结盟,其破坏性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得到了规制。当代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二次分离”,资本借助于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其在全球自由流动的梦想,但至今未见其有被规制的迹象。(21)[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第67页。鲍曼把资本与民族国家、资本与劳动力相结合的现代性称为“稳固的现代性”,把资本与民族国家、资本与劳动力相分离的现代性称为“流动的现代性”。在他看来,现代性之所以从“稳固阶段”转向“流动阶段”,最主要的还是资本逐利的本性使然:当思想观念而非体力、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成为资本利润的主要来源时,(22)[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238页。对于资本而言,维持原先资本与劳动力相结合的模式,既无利可图,也束缚了自己的行动,因此采取去捆绑式的“脱身”策略,既可以享受“治外法权”的特权,无视任何行为后果,又不必支付管理成本。总之,从资本与地方及劳动力的结合到资本与地方及劳动力的分离,绝不是如新自由主义宣称的那样出于“滴涓效应”的普惠式动机,而是资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调整其统治策略的必然结果。
二是通过对“政治的解构”批判“解放论”。新自由主义宣称今天人们所能享受的自由“除了还需要在某些地方略加调整之外,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我们所能想象之完美境地”,(23)[英]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3、64-65、69页。社会生活的私人化或个体化就是人的彻底“解放”。在鲍曼看来,新自由主义宣称的自由只是人的行动不受外在干预的自由,也就是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或权利自由,(24)[英]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3、64-65、69页。但权利自由或法律上的自由毕竟不是事实上的自由,自由由权利上升到能力,须以必要的资源作支撑。对穷人而言,没有财富的再分配,自由再多也无意义。问题在于,资源的再分配惟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实现,而当新自由主义把“现实存在的自由,被解释成不存在政治权威强加的约束”时,资源再分配的任务就被永远搁置了。即使对那些具有选择能力的人而言,在当前政治衰败的条件下,所谓“选择自由在扩展”也必定是不实之词。鲍曼强调,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个人选择总会受到两种约束机制的限制,即选择议程和选择法则,前者规定选择的范围,后者明确何种选择优先。从现代性历史来看,立法是设定选择议程的主要工具,教育是确定选择法则的主要媒介。但在鲍曼看来,“现今的政治制度正置身于这样的过程之中:或明或暗地放弃(至少是在削弱)其在议程与法则设立中的作用”,(25)[英]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3、64-65、69页。决定人们选择范围的真正权力已经落到瞬息万变的市场手里。同样,当今的选择法则也主要由市场压力来塑造。无论在选择议程还是在选择法则方面,个体都没有更大的发言权;新自由主义“不过是将个体从政治公民转变为市场消费者”,通过自由选择的借口以达到让所有人服从市场暴政之实的目的。(26)[英]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3、64-65、69页。
三是通过“文化多元论”批判意识形态“终结论”。在鲍曼那里,由现代知识阶层最先提出的、后被新自由主义尊崇为“政治正确性”神圣准则的多元文化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终结一切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为全球性权力资本的统治服务。其一,多元文化主义宣称没有一种选择优于其他选择,即使存在我们也无从知晓,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批判不再被认可,社会反思工作便告终结,其实质是把“差异”绝对化,为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鲍曼是“文化多元论”的拥护者,在他那里,文化多样性不仅是人类生活的本来样态,也为生活选择开启更多的可能性;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只是事情的“起点”,其价值只有通过对话才能确立起来,而今天多元文化主义的诡异之处恰恰在于把“起点”视为“终点”。其二,多元文化主义在当前条件下极易演变为多元共同体主义,从而使社会隔离和分裂状况进一步加剧。一般来说,文化是以共同体为单位的,在当前全球处于不安全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文化就成了堡垒的代名词。文化差异“在狂热的防护墙与导弹发射台的建设中”被用作了建筑材料,“居民每天都要证明他们坚贞不渝的忠诚,并有意避免与外来者的亲密接触”;“即使相互交流,往往也是把枪管当电话使用”,因为保卫共同体优先于所有其他责任。(27)[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6页。因此在鲍曼看来,多元文化主义不过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屈服性的和解宣言”,是一种与以往意识形态全然不同的新型意识形态,不仅放弃了对社会进行质疑的使命,也是当前寻求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主要障碍。
四是运用“两种生活论”批判“无可选择论”。鲍曼援引布尔迪厄的观点,指出当前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再也没有社会的拯救”“我们都是天定的个体”已经成了我们时代无处不在的强势话语,其意在强调:个人要勇敢地承担其处理一切事务的责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在鲍曼看来,新自由主义“无可选择”的训告,其本身就是一种先定的选择,正是这种设定,预制了人的选择范围和社会走向。人的行动和据以行动的条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人之行动的条件是不能选择的,若我们说某事不可改变,那就意味着把某事纳入“条件”领域,结果我们在这件事上真的不能做任何事情,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28)[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第10、13、30页。事实上,人的行动和据以行动的条件之间的界线并非截然清晰的,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共生关系。我们关于生活的叙事即“所述的生活”,自一开始就干预了我们现实生活即“所过的生活”。鲍曼指出,当前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无保障状况主要源于失去控制的全球性资本自行其是,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只能是全球性的政治行动,而新自由主义则号召人们依靠个人力量来寻求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使问题的源头离我们越来越远。在他看来,一切表述不仅开启某些可能性,同时也会关闭其他一些可能性,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叙事阻止了人们“彻底地追踪把个体的命运与作为的社会进行运作的方式和方法连接起来的各种纽带”,(29)[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第10、13、30页。要打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首先需要我们对当前的人类处境进行重新表述。
三、策略揭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惯用伎俩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迅速蔓延,并且仍是当代西方主导性意识形态,既有现代性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社会矛盾激化和经济技术条件变化的背景,除此之外,其在运作过程中采用的相关策略技巧也是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概括起来,鲍曼在其论著中直接或间接提到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策略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动荡化策略。当代全球化最令人忧心的莫不过是社会生活动荡不定,生活路标和定位点不停变化,社会犹如流体一般,变动不居、难以把握,长期性的生活规划和行动遭到遗弃,时刻准备变换生活策略、时刻准备背信弃诺的灵活性成为最高的生存策略,生活由一段段的小插曲所组成,它们无法组成有意义的序列,这就是鲍曼描述的流动的现代性生活的大致场景。可以看出,这一场景很难产生协同一致的集体力量和政治行动来对抗全球性资本。这就是鲍曼所指出的,“动荡不定则成了建立全球权力结构的主要障碍,也是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技巧。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采取了处心积虑的‘动荡化’策略,它是由超民族而且越来越超地域的资本初发其端,并由几乎毫无选择的地域性的国家政府小心翼翼地加以实施;这一结果也部分地因为权力争夺和自我防御的新的逻辑沉淀下来。”(30)[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第10、13、30页。鲍曼把当前全球无政府状态归因于全球性经济权力与地方性政治权力之间的不对称性,因而他一再呼吁,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全球性政治平台的搭建。问题是,当今社会的动荡不定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个体分化力量,当被袭击的恐惧弥漫四周、挥之不去时,一种自我保存、自我防御的逻辑,即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地方性方案和个体化方案,自然就会优先于所有其他方案,其结果只会加剧社会的分隔和分裂,使协作和联合的前景更加渺茫。这当然是权力资本最想要的结果。大卫·哈维同样也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制造、危机管理、危机操控,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精心的再分配表演。(31)[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第169页。
二是简化策略。这是指新自由主义把某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任务和要求,简化为其中某一项内容和任务以转移矛盾焦点、维持现实秩序的一种策略。鲍曼指出,在迅速全球化的今天,现存政治制度确实无法保障确定性,他们经常做的是将人们对不可靠、不确定、不安全的普遍焦虑简化为其中的人身安全问题。(32)[英]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第5页。这种简化策略的好处有二:一方面有利于重建现实政治的合法性,毕竟经济已经全球化了,经济生活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已超出政治能力所及范围,而人身安全则属于法律和秩序的对象,也是现存政治唯一能见成效的领域;另一方面,在安全大旗下,人与人之间、共同体之间的猜疑、割裂会进一步加剧,重建公共领域和集体行动不会进入议事议程,人们的注意力会被引向与搭建全球政治平台完全相反的方向。如对恐怖主义、千年虫等事件的夸大宣传,其本身就是自我实现的。在鲍曼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政治上的安全战略无非是要处理动荡化策略所带来的诸如经济移民、难民、单身母亲、吸毒者、刑满释放人员等副产品,对他们进行集体施暴,把他们非道德化、罪行化乃至刑事化。“使陷于过度焦虑中的社会能够有信心地说出恐惧是什么,怎样缓和这种恐惧”,(33)[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李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第137页。不仅可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扩大政府的权力;更重要的是,“目睹穷人的境况也牵制了不穷人的人们,并使他们不越雷池一步”,不敢去想像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更不用说去试图改变现存的世界。(34)[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第145、143页。
把贫困简化为饥饿是新自由主义简化策略的另一种表现。鲍曼指出,当前主流媒体“把贫困和匮乏这一问题仅仅化约为一个饥饿问题。这一策略可谓一箭双雕。贫困的真正规模被有意地贬低了(8亿人永远处在半饥饿状态,而大约40亿人——占据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生活在贫困中)。(35)[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第63、70页。除此之外,把贫困等同于饥饿,也掩盖了贫困的其他方面,如恶劣的生活条件、疾病、文盲、种族仇杀或战争、家庭解体、社会联系削弱、毫无前途和低下的生产力等,这些是不可能通过增加食物供给加以解决的。(36)[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第63、70页。并且,一幅幅令人恐怖的饥荒图,工作及工作场所的消失,地方性贫困的全球原因之间的所有联系也都被谨慎地回避了,观众在电视里甚至看不到一件劳动工具、一块耕地或一头牛。另外,鲍曼还发现,新自由主义对贫困的讨论,通常是在纯粹经济领域的认知框架下进行的,但贫困也不完全属于经济问题,它们也悄无声息地掩饰一些东西,如新生穷人在全球秩序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37)[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第145、143页。
三是转换策略。这是指新自由主义利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将一种情境或问题转换为另一种情境或问题,从而成功地实现回避主要矛盾和问题目标的一种策略。新自由主义较为典型的做法,就是运用贝克等西方社会理论家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来讨论当代全球化过程中的危险和恐惧问题。而在鲍曼看来,“通常,将注意力从危险转移到风险不过是另一种托词,是一种逃避问题的企图,而不是达至安全行为的办法。”(38)[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恐惧》,第12-13、13页。风险是可计算的危险,我们可以对现有可知的导致风险可能发生的各种因素和条件进行评估,测算出不幸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概率,由此为即将采取的行动制定预案。问题是,现如今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生活情境类似于“在雾中行走”,能够计算出来的危险都是集中在可见的、已知的且在近处的危险。“但是到目前为止,最可怕、最令人恐惧的危险正是那些不可能或极端难以预见的,那些始料未及,很有可能无法预见的危险。”(39)[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恐惧》,第12-13、13页。如此,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总是在忙于计算风险,而把更重要的关切即全球不确定性的来源置于一旁。事实上,贝克自己也认为主流话语这种回避“不可计算之威胁”的做法很具有反讽意味。(40)[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第230页。
把不平等的经济问题转换为有差异的文化问题,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惯用手法。文化差异是将具有不同行为习惯的人相互区别开来的东西,这种解释至少是当代西方正统社会科学的重要支柱之一。但在鲍曼看来,这里存在着很多误解或误导。不同类型的人遭遇不同的命运,几乎都被解释为是这些不同类型的人拥有的不同选择偏好、倾向导致的结果。简言之,不同的文化决定着不同的命运。鲍曼指出,众所周知,癌症患者的死亡率与他们的收入紧密相关,癌症患者中富人的死亡率比穷人患者明显要低很多,其存活时间也比穷人更长,在对其相关原因的解释上,主流媒体一般都倾向于做文化分析,如指出穷人比富人抽烟更多,但从不提比戒烟更困难的因素,如慢性营养不良、低下的生活条件,或者无法支付一次性治疗所必需的费用。(41)[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第53-56、56页。新自由主义通常用多元文化主义或更具普遍性的文化主义来解释青少年犯罪、反社会行为以及恶劣的学校表现的高发率等现象。在鲍曼看来,“这是故意为‘我们’和‘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希望相互融合的残酷事实做一个掩饰罢了”。(42)[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第53-56、56页。
四是自由策略。这是指新自由主义通过倡导个人自由、废除一切限制个人自由的做法,从而瘫痪政治行动以维护权力资本特权的一种策略。(43)[英]泽格蒙特·鲍曼:《自由》,杨光、蒋焕新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2页。鲍曼指出,当代全球化进程“与多数反面乌托邦的设想相反,既没有因独裁、屈服、镇压和奴役而导致一败涂地的结果;也没有因总体秩序内私域的‘扩张’而引发出一塌糊涂的结局。结果恰恰相反,人们,或正确或错误地,对现实中存在着的那些限制人的行动和选择自由的枷锁和束缚,正在迅猛地被加以清除,表示怀疑。秩序的可靠和坚固,是人类自由力量的典型产物和结晶”。(44)[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7、8页。在鲍曼看来,通过“自由”来实现维护统治的目的,这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大卫·哈维也高度认同这一观点,他说:“自由”已成为一把“精英打开走向民众的大门”的钥匙,“任何将个人自由提升到神圣位置的政治运动都有被新自由主义收编的危险”。参见[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第41、43页。构成文化的是“提议而非禁令,是建议而非规范”,规范调节政治已被刺激需求的政策所取代,寻求快乐变成了维持现实秩序的主要手段。(45)[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第194页。在他看来,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拆除限制公民自由的藩篱,让公民获得自由,为的是让他们能够个别地或集体地为他们自身设立藩篱,而不是被迫地走向个体化,这种自由“自我设限”的观点已全然不为人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一直把“所有限制都是禁止”“任何自我设限的尝试都被视为通往集中营的第一步”当作至理名言加以宣传。(46)[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第89、94页。他认为,当前的政治经营者和文化代言人,几乎都放弃了作为社会评判终极基准的“公正模式”,而一致赞同“人权规则/标准/尺度”,乃是这一策略的具体表现。(47)[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第89、94页。人权原则的实质在于,尽管自由权利可以独立地被享受,但它们不得不通过集体来争取,且惟有集体争取才可能得到承认,于是就有了共同体划清边界和严密防守的热情,这种“承认之战”不仅会因忠诚的测试沦落到对个体进行控制的地步,在当前规范权威机构缺失的背景下,也在促进着分隔和分裂以至最终封闭对话的大门。(48)[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第89、94页。
结 语
出于分析的需要,我们把鲍曼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从三个维度分开梳理、介绍,事实上,这三个维度在鲍曼的写作中并非独立的,而是相互补充、互相确证地有机融合在一起的。
纵观鲍曼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我们发现,无论立足哪种维度,鲍曼始终没有脱离马克思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分析框架。在事实维度,鲍曼对当下社会不公的极度厌恶和新生穷人命运的深切同情,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在理论维度,鲍曼资本分离理论的底色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和世界历史理论,其两种生活理论也不过是马克思“人既是历史剧中人也是历史剧作者”的翻版;在策略维度,鲍曼所揭示的四种策略无不体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特别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原理。正是运用了马克思唯物史观这一根本方法论,鲍曼的批判才显现出在认知经济全球化、应对新自由主义挑战方面的当代价值和启示。这些启示主要在于:首先,在世界认知上,强调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大多与全球性资本和地方性政治的不平衡性有关,而着力维护这一结构性失衡的正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次,在路径选择上,倡导建立以对话和协商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全球性方案,拒绝重回过去的、单边主义的地方性甚至个体化的解决方案;再次,在应对新自由主义的策略方法上,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狡黠之处在于通过人类自由的名义实现了总体秩序固化的目的,强调舆论上的话语解构和实践中为每个个体自尊自立提供必要的生存保障等在抵制新自由主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因受后结构主义解构策略的影响,鲍曼在贯彻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方法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彻底性,在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出有力批判的同时,并未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替代性方案,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批判的力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危机,提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集中表现为风险生产社会化与风险解决办法私人化之间的矛盾,脱离财富再分配的人权模式和文化主义政策不过是强化资本全球统治秩序的重要策略等观点,对当代发达社会的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在如何走出全球化困境的道路选择上,过于强调主体选择的不确定性,而弱化了唯物史观中的必然性逻辑,对作为未来理性化担纲者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失去信任,寄希望在不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唤醒人的道德责任来恢复被遗弃的公共领域,重建全球范围内经济与政治的平衡,实现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联合,这在当前全球化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需要我们加以审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