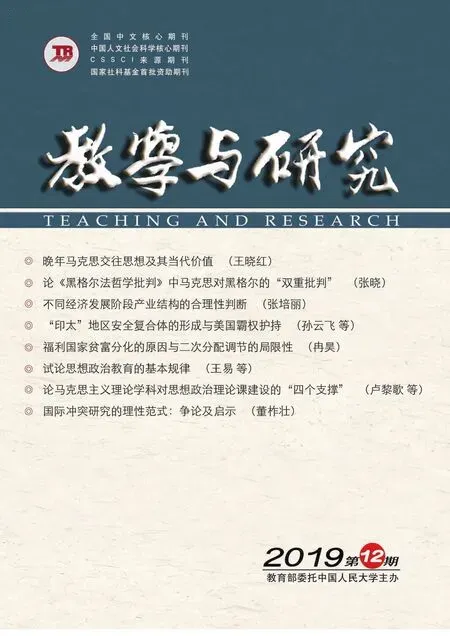晚年马克思交往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
2019-12-18
长久以来,学界主要关注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交往思想,对晚年笔记中的交往思想极少关注。事实上,交往乃是马克思终其一生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晚年马克思在其早期交往理论的基础上,在“人类学笔记”(即《古代社会史笔记》)《历史学笔记》等文献中,发展了其交往理论,拓宽了其研究范围,深化了唯物史观理论。本文立足于晚年马克思的笔记群,尝试梳理和概括出交往的类型、交往的形式等问题,并就其当代意义进行初步探讨。
一、交往类型的多角度分析
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范畴仅仅被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正在形成中的生产关系概念,是一个不成熟的、将会被替代的过渡性概念。(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88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实践和人的发展问题讨论的深入,尤其是随着哈贝马斯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为主旨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提出,国内学界开始重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并且持久不衰,提出了诸多新看法新见解。关于交往的内涵,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交往是唯物史观中的重要范畴,“交往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形式”等概念不同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关系”的雏形,而是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丰富的内涵,其中包含了生产关系。(2)参见林剑:《交往范畴与唯物史观》,《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许斗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形式”理论新释》,《东南学术》1999年第2期。另有观点认为,交往作为活动性范畴是与关系性范畴相统一的,交往关系与生产关系虽然有联系,但是有根本的区别,二者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概念和范畴。(3)唐踔:《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23页。
事实上,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曾对“交往”概念做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他指出,社会都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决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不能自由选择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社会形式。生产力发展的阶段不同,交换和消费形式也不同,相应的社会制度、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也不同。“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 ‘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9页。“Verkehr”一词在德文中意义极为广泛,主要是指交通、运输、通信等物流方面的意义,也指交换、流通以及男女交合之意。英文的“commerce”一词主要是指商业、贸易,尤指大规模的商品贸易。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交往和实践是人类的两大主体活动,二者互为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交往具有非常宽泛的意义,是指交往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和交往活动。交往关系既是交往活动的前提又是交往活动的结果,二者也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晚年马克思曾在不同场合使用交往概念。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角度,将马克思的交往概念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根据交往内容,交往可以划分为两性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指出,男女之间的交往是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直接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了直接的统一性。在原始交往过程中,两性交往为主导,起支配地位,血亲、姻亲交往是主要的交往形式。发展到文明交往阶段后,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道德、军事、科技等等内容)成为两大基本类型,物质交往是核心,是其他交往的基础。
第二,根据历史时期,交往可划分为原始自发的交往和文明的自觉的交往。晚年马克思重点关注了原始交往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交往。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等晚年笔记中,马克思认识到,人类一诞生就必须过群居的生活,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在自然界中求得生存,人类社会在此基础上产生。为了对抗自然或者共同的敌人,原始社会的不同群体之间会发生互动、进行交往,包括争夺食物和生存空间等等。在为了更好地生存所发生的一切互动和交往中,两性交往、血亲和姻亲交往是原始交往中最稳定的交往方式。“在血缘亲属关系的基础上组织成氏族”,(5)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7页。氏族经历了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演进,又发展为胞族、部落和民族。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则更多地关注了自觉文明交往中的战争、国际贸易等交往形式的历史作用。马克思指出,原始交往和文明交往并非毫无关系,“原始交往遗传给文明交往的许多基因,如家庭、种族等等,它本身虽不在文明交往史的参照系之中,却给文明交往留下了许多印记,影响了不同文明的形成和特征。”(6)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原始交往活动、交往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工具都对后来的文明交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明交往总是在原始交往的遗迹下进行的交往。
第三,根据交往空间,交往可划分为内部交往与外部交往。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并且,每一个民族自身的发展,“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7页。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外部交往的作用随着人类社会所有制形式的演变和发展愈益增强。比如奴隶社会的形成,“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7页。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形成亦是如此。晚年笔记中,马克思对外部交往(殖民、战争、联姻、国际贸易等)这一交往类型进行了多角度考察。
第四,根据交往主体,交往可以划分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交往。晚年笔记中,马克思详细摘录了最初的原始群的杂交状态,从杂交转变为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血缘家庭,(9)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第142页。发展为普那路亚家庭,再到氏族组织的产生。原始社会状态下,两性交往,个人对共同体(氏族、胞族、部落、家庭)的依赖性交往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文明交往阶段,则发展出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交往。《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认真考察了三十年战争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分析了主权国家的兴起、交往主体的变化。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言,从16世纪开始,“民族国家基本上取代了近代以前的政治组织形式,如城邦、部落和帝国。与此同时,市场成为组织经济关系的基本方式,取代了互惠、再分配与帝国统治经济等其他交换形式。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贯穿着数百年来的历史,它们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逐渐成为决定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性质与动力的关键因素。”(10)[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第五,根据交往范围,交往可以划分为狭隘的原始公社内部交往(两性交往、血亲和姻亲交往)、扩大的地域性交往、世界性交往与普遍交往。晚年马克思考察了原始交往向文明交往的演化发展,考察了在这一演化过程中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从原始社会局限于血缘关系的狭隘的群体交往、原始公社间的交往,发展到古代的民族内部交往和扩大了的跨民族交往,也就是地域性的交往,再到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后的世界性的交往,最后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普遍交往。这里,普遍交往比世界交往更具有抽象性和广泛性,是一个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的广泛的、深度的交往。世界交往则更强调对地域性限制的突破,主要是与建立在地理大发现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第六,根据交往手段,交往可以划分为暴力交往与和平交往。晚年马克思充分认识到暴力交往这一交往的类型在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晚年笔记中重点考察了战争、掠夺、抢劫等暴力形式在历史不同阶段产生的不同影响。
第七,根据交往各方在交往过程中的作用,交往可以划分为主动交往、被动交往和互动式交往。在前两种交往类型中,交往双方或多方体现更多的是一种主客体关系,在互动式交往类型中,交往双方更多的是一种互主体的关系。晚年马克思重点关注了资本主义民族和非资本主义民族之间的主动和被动交往关系。
二、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和多样性考察
交往都是在一定物质生产条件下的交往,交往方式因此具有历史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晚年马克思探讨了交往形式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战争、宗教等多种交往形式进行了阐释,尤其关注了战争这种特殊的交往形式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仅就晚年马克思重点关注的交往形式做一番较为整体的考察。
(一)战争——交往的特殊形式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9页。《资本论》中也明确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1、861页。换言之,战争作为一种暴力交往的典型形式,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双重作用。战争的形式和原因多种多样,有阶级战争、殖民战争、侵略战争、宗教战争、商业战争、民族战争、农民战争等等。
第一,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深刻阐释了战争在原始社会状态下发挥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技术的进步、文明的到来。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特别重视技术对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重要作用。在分析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财产部分,马克思特别关注了战争技术的发展。他看到了,在此阶段,除了继续使用弓、箭、矛、棍棒、燧石刀和斧,以及石制的工具外,战争防御方面的技术进步了,建造了一种印第安人很难攻破的大房屋,发明了填塞棉花加以缝制的斗篷作为防箭的补充工具和双刃剑等。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和生产空间,为了占有最好的地盘,“斗争加剧了。战争技术发展了,对勇武的奖赏增加了”,这些变化“表明文明时代即将来临”。(13)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第184、157页。另一方面,它成为社会向更高级阶段发展的阻力,阻碍着群婚制向对偶制家庭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战争诱因的不断增强和武器的不断改良,野蛮人的战争要比蒙昧人的战争毁灭更多人的生命。并且,由于在战争中,战斗任务都是由男人来承担,从而造成了女人的过剩,这就“加强了群婚所造成的婚姻制度,阻碍了对偶制家庭的发展”。(14)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第184、157页。
第二,早期的古罗马贵族发动的战争,一方面推动了高利贷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造成了农民的破产和农奴的产生。马克思指出,罗马贵族为了阻碍平民的劳动条件的再生产,以使他们变得贫穷而终于破产,所以不断进行战争,强迫平民服兵役。这里,战争一方面充实了罗马贵族的仓库和地窖,使其藏满了掠夺来的货币,另一方面使平民的再生产条件不断萎缩或丧失,导致贫穷化,也就是变为自己的债务奴隶。贵族不是把平民所需的商品如谷物、马、牛等直接给他们,而是把对自己没有用处的铜借给他们,从而榨取惊人的高利贷利息。在查理大帝统治下,法兰克的农民也是因战争而破产的,他们除了由债务人变为农奴外,再没有别的出路。(15)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7页。
第三,《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的国际战争实例来说明战争这一暴力交往典型形式产生的原因和作用,分析了其对于西欧社会结构的演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世界历史的形成的巨大作用。他指出,最初的战争源于财富和权力、领地和霸权的争夺,还有教派之间的冲突和阶级矛盾等。侵略战争、阶级战争、宗教战争是主导。随着地理大发现带来的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国际贸易的扩大,为了资本的扩张、生产的扩大而发生的宗教战争(穿着宗教的外衣)、商业战争、殖民战争成为了战争更为主要的形式,它们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发展,推动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第四,晚年马克思特别关注了商业战争,其作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法和形式,通过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即国家权力,大大缩短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的时间。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7和18世纪的商业战争源于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世界市场的开辟。销售市场的开辟所带来的利益的争夺,使得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地方性的斗争发展为全国性的斗争,又发展为世界上的普遍的争斗。商业战争的开始当属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即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566—1609),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除此以外,马克思还特别提到了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为英国商业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建立了新的市场,获取了在中国的贸易暴利特权,从而为当时已经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棉纺织业的扩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伴随着生产的极度扩张,信用和虚拟资本也因此发展起来。
第五,中国、美国等国家内部的阶级战争、国内战争给资本主义的生产扩展带来了巨大影响,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当时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马克思分析指出,“中国的内战(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引者注)妨碍了英国纺织品在中国的销售”,美国的独立战争则使英国的棉纺织业生产过程由于原料缺乏和昂贵(棉荒)而中断。(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25、144-145页。换言之,战争使原材料进口国家和出口贸易国家的市场紊乱,从而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缩减或中断。
(二)宗教改革、宗教政策
晚年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宗教改革、宗教政策这一交往形式与社会形式的演变和文明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首先,他指出,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不断推动着教派之间、阶级之间交往关系的调整、推动着社会关系的变革。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看到了传教士对于古老部落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影响。(17)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第260页。在古老的部落中,财产和酋长职位在氏族内继承,酋长的外甥(姊妹的儿子)处于后继的世系中(处于氏族中)是有保证的。但在传教士们看来,不让儿子继承是不公正的,这就推动着母系向父系的过渡,推动着氏族原则的最终瓦解。由于传教士及美国当局的影响,儿子可继承父亲的职位,子女可以撇开其他同族人而获得遗产的大部分,氏族成员可以选举酋长,而且可以罢免他。
《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认识到,宗教改革对于封建制度的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第3册中,他详细摘录了16世纪宗教改革初期的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政治情况,1532年第一个宗教和约时期德国发生的新教徒的分裂、骑士反对诸侯的战争和农民战争等事件。他分析指出,法国、德国等大陆各个君主国为了对付意大利这个“实行寡头政体的、善于做生意的共和国”,结成了康布雷联盟,这是“王权反对威尼斯资本实力”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制伏资本即资产阶级的祸患;制伏这个产生于封建国家、还带有封建痕迹的君主国。在宗教上的反映就是教廷和宗教改革的斗争。”(18)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页。这场争斗的历史背景主要是美洲的发现、殖民地的开拓、金矿和银矿的发现、大陆国家需要钱来供养常备军等等。在这之后,德国对于整个欧洲史来说就由主导变为次要的了,英国(也包括法国等国家)通过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国际贸易、工业革命等等逐渐确立了其在近代欧洲史上的主导地位。
其次,马克思探究了开放、宽容的宗教政策与保守狭隘的宗教政策对于国家稳定和发展产生的不同作用。《印度史编年稿》中,马克思充分认识到宗教政策对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摘录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Akbar,1556—1605)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事件时,马克思着重分析了阿克巴所采取的宽容的宗教政策,指出他是一位大力促进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的伊斯兰教君主。“他本人(指阿克巴)对于宗教问题不存成见,因此采取宽容态度。……他还废除过去一切印度教徒必须一律向伊斯兰教政府缴纳的,‘Jizya’即人头税”。(19)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3、34、36、44页。阿克巴在位时,印度教徒的两个伟大的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译成当时莫卧儿宫廷使用的官方文字——波斯文。并且,阿克巴统治时期,其现行法律是印度教法典和伊斯兰教教义的一种结合。“阿克巴参考伊斯兰教习惯及曼奴(Manu)法典修改了刑律”。(20)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3、34、36、44页。正是这一宗教政策加上经济、政治和文化艺术的改革,才使得德里成为当时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为繁华和最大的一个。与阿克巴开放宽容的宗教政策不同,阿克巴之子日汉喆(Jahangir)恢复伊斯兰教为国教,另一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则恢复向印度教徒征收人头税,并多方迫害印度教徒,致使印度教徒对其怀恨在心,最终奥朗则布的势力开始低落下去,莫卧儿帝国开始一蹶不振。(21)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3、34、36、44页。马克思以编年记叙的方式对比评论了不同的伊斯兰教君主的不同宗教政策所带来的不同结果。
(三)迁徙和移民
迁徙和移民也是晚年马克思关注的一种交往形式。首先,他探讨了早期移民的重要社会历史作用,指出早期的移民促进了土地所有制的变革,私人土地所有制出现,原始社会瓦解,文明民族和国家产生。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充分认识到迁徙和移民对于氏族组织、古代公社的瓦解,对于文明和国家的起源的重要推动作用。他分析指出,人员流动、平民阶级人数的迅速增长加速了氏族的崩溃和国家的产生。移民、迁徙、收养外人入族等人为的因素,破坏了氏族血统的纯洁性,打破了氏族的纯粹形态。战争、征服和经济交往所导致的迁徙和移民,导致了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出现,这些“新来移民占据了公社荒地和林地的某一地段,并将它加以耕种”。(22)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第38、129页。公社所有制因此缓慢地自行分解,私有制和阶级出现,民族和国家产生。
早期的移民还推动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分析指出,由于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不同,东半球与西半球最初的生产方式也是不同的,东半球从驯养动物开始,西半球则从种植玉蜀黍等植物开始。马克思摘录了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的例子,说明了谷物的种植一方面是由于饲养家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与向西方迁移有关的”,(23)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第38、129页。这就推动了畜牧业向农业这一生产方式的转变。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移民对世界市场开拓、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英国从 17 世纪以来就向北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新大陆大量移民,18 世纪后期规模急剧扩大。仅1830 年,英国就向海外移民6 万人,1842 年达到 13 万人。(24)[英]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602页。1849 年,由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特大金矿的发现,离开英国的人数高达 30 万。1853年至 1880 年,英国人外流多达 246.6 万人。(25)[英]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99页。外来移民既为新大陆各个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产业后备军,同时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法和工艺技术,移民成为了新大陆各国引进科学技术的手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移民向其他地区扩张,移民开垦世界上新的地区,建立殖民地,从而把未开化的部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移民推动着资本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最终成为全世界的支配力量。
(四)殖民交往
晚年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中对殖民这一交往方式都进行过历史考察,尤其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和《印度史编年稿》中,对西班牙、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印度和非洲、美洲等国家地区的殖民,对这些地区的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和当地人民生活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第一,殖民交往对于殖民国家而言意义巨大,尤其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殖民制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指出,殖民制度极大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和航运的兴盛。殖民地既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提供了销售市场的保证,也为货币资本因市场垄断而实现了成倍增长和集聚。这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马克思在此以荷兰为例充分阐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1648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荷兰直接依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夺取巨量的财宝,并最终转化为资本。马克思接着强调指出,繁荣的背后,“荷兰的人民群众在1648 年就已经比整个欧洲其余地区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穷,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64页。
第二,殖民交往对于被殖民国家而言,后果是多样、复杂的。马克思曾以印度为例,对西方的殖民交往的双重性作用做了阐述,认为殖民主义虽然给被殖民地区的人民带来了苦难,但在客观上推动了殖民地的社会进步,动摇了东方“传统社会”的根基,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一方面,它破坏了旧的社会结构,使殖民地国家和人民遭受长期的奴役和掠夺;另一方面,它摧毁了殖民地国家的自然经济,打破了其野蛮的、孤立的状态,推动了其向现代文明世界的转型和发展。但是到了晚年笔记中,尤其表现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和《印度史编年稿》中,马克思更多地从否定的意义上来谈殖民交往。他通过历史性考察被西方殖民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原始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解体过程,认为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并非是唯一的,东方社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走出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社会发展道路,然而,殖民对当地整个社会结构的摧残却是永久性的、不可弥补的。
第三,殖民交往造成整个国际分工的不合理、国际贸易的不平等和世界体系发展的不平衡。西方世界的强制性、掠夺性的殖民交往,将殖民地作为其廉价原材料的供应地,长期霸占和掠夺,资产阶级不仅给殖民地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并且造成了东西方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平等,造成了整个世界体系发展的不平衡,并影响至今。
(五)暴力掠夺
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马克思看到了“暴力掠夺”这一特殊的交往方式对于早期私有财产的扩大和私有制的确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指出,武器和衣服最早成为私有财产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私有财产的范围由于个人的私人活动创造的物品为个人据为己有而日益扩大。个人亲手栽培的树木,他自己“驯养的”动物等等,或他用暴力抢夺来的物品,首先是奴隶和妻子,就是这样的物品。在这里,马克思特别加了自己的评注:[jusQuiritum! ]也就是古罗马的全权公民——魁里特的权利。(27)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第4页。
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辩证分析了暴力掠夺方式的双重作用。他详细摘录了16世纪末英国政府支持的弗朗西斯·德雷克(“老实说是一名海盗,是继葡萄牙人麦哲伦之后第二个完成环球航行的人”)的“新海盗远征”。因为,“这些在和平时代靠烧杀劫掠得来的财宝使英国人和荷兰人着了魔”。从这时起,西班牙的所有土地和财富都被认为是可供普遍抢劫的猎物;不久以后,海上就布满了英国和荷兰的海盗。在政府的支持下,德雷克已经以皇家海军将领的身份在海上行动,他还被封为从男爵。通过强盗式的暴力掠夺,英国、荷兰等国家积累了更多的货币财富,加速了本国的资本积累和发展。另一方面,德雷克的新海盗远征也给西印度群岛等地带来了灾难:圣地亚哥被烧毁,圣多明各及卡塔赫纳被洗劫,佛罗里达的沿岸地带被抢掠一空。马克思因此评价其“暴行累累”。(28)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7页。当然,马克思还看到了这种交往方式所带来的各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德雷克从弗吉尼亚给当时的欧洲人带回了抽烟的习惯。
(六)联姻
晚年马克思指出,联姻一方面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推动了民族间的融合和统一,促进社会的发展。在《印度史编年稿》中,马克思在摘录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的历史的时候,详细梳理了阿克巴统治时期(1556—1605),他提到,为了维持同斋浦尔和马尔华尔的友好关系,阿克巴迎娶了刺日普德族的两个公主。(29)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第32页。阿克巴通过与他族联姻这样一种方式,实现了其政治和军事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和联系,改善了不同民族之间的邦交关系。
联姻也是实现领土扩张、权力统治、建立联盟等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在摘录15世纪末16世纪初期马克西米利安执政后期德国的政治情况时指出,马克西米利安意图“利用联姻使这两个国家(匈牙利和捷克——引者注)隶属于他的王室”。(30)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3册,第77页。通过谈判,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女玛丽亚与匈牙利和捷克的国王拉迪斯拉斯七世的儿子,即后来的国王路德维克二世订婚,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斐迪南同拉迪斯拉斯七世的女儿安娜订婚。当这一联姻的计谋失败后,马克西米利安又试图通过选派代理人的方式获取对两个国家的实际统治。
(七)国际贸易——全新的交往形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驱动和地理大发现的外在条件的保障,推动世界市场形成,地区的贸易为真正的国际贸易所取代,这样一种全新的交往形态使人类交往的范围在大工业的基础上具有了世界性质,使人类交往的主体由个人、城市向民族国家转变。
《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专门探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国际贸易的出现,以及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他深刻指出,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建立源于资本本性的要求。资本的产生和增殖需要,以及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驱使资本要不断克服民族的、地区的限制,不断寻求和扩大交往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改善交通以扩张商业关系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正是资本逐利的内在本性和外在竞争促动着地域性交往向世界性交往的转变,推动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着交往范围的扩大和交往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交往的普遍化也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新的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出现积累了基础,埋下了炸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地雷。
三、交往思想当代意义的整体审视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的今天,普遍交往、世界交往早已成为经验事实。通过对马克思晚年交往思想的探究,有助于我们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有效应对全球化的时代大潮,正确认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改革开放,也有助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的更好的发展。
(一)正确认识及有效应对全球化的理论工具
学界普遍认为,全球化发端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成为一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作为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背景存在并发生影响。关于全球化的概念、形成、本质、发展趋势等问题,众说纷纭,尚未达成一致认识。我们或可把它概括为:肇始于经济领域的、各国家、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互动中运行的过程和趋势。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马克思是有“全球化”思想的。我们今天遇到的全球化问题,并非什么新鲜事物,马克思早就对此进行了研究。正如约翰·卡西迪所言:“‘全球化’是20世纪末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的时髦语词,但在150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它的许多后果。”“现代经济学家们又碰到这些问题,他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步马克思的后尘。”(32)[美]约翰·卡西迪:《马克思的回归》,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页。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全球化”的概念,但并不代表他没有全球化的思想。早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有关世界历史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规律的一般性说明;晚年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对于生产、分工和交往的发展带来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国际贸易的拓展、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不是对全球化问题的具体解答,却是对全球化基本理论的重要阐述。因此,学界将其称为全球化理论的奠基者是非常合适的。
其次,马克思的交往观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到以经济全球化为主导的“全球化”概念的西式语境、西方主导。马克思在《资本论》《历史学笔记》中都充分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历史、全球化,必然带来国际分工的不合理、国际贸易的不公平、东西方差距等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一词更具有西方话语霸权中的“一体化”背景,即指“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科学技术的全球联网、生态环境的全球联动”。马克思的交往、世界交往概念,凸显的则是一种以物质性为基础,并带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y)的以互相“承认”和尊重各自“自我认同”基础上互动“交往”,互通有无的“交换”性的“交往”。(33)章仁彪:《“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交往”何谓又何为?》,载唐踔:《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4页。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全球化正是资本自行增殖的本性在全球扩张的趋势表现,其本身具有萨缪尔森讲的“双刃剑”(Double edge)的两面性:一方面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生态、能源、战争等诸多全球性问题。
最后,马克思的交往观有助于我们有效应对全球化。全球化既然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我们需要在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做出适合我们国家的战略选择。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化的积极推进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实现资本扩张的目的。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把握好“选择性进入”问题,也就是要在全球化过程中,首先要维护好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好自身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特色,同时要积极融入全球化,积极扩大交往,提高加入世界历史进程的水平和程度。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提出及深化的理论依据
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战略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认为,在世界交往的推动下,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整个国际形势的制约,与世界历史发生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必须融入全球化的潮流。邓小平审时度势,认识到“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而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44页。新一代党的领导人习近平同志在国内国际不同场合旗帜鲜明地宣示了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的坚定意志,并对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作了深入阐释。(35)《习近平谈改革开放》,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1月14日。中国只有不忘改革开放初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往,长期坚持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上总结的九条宝贵经验,才能吸取各民族的一切“积极成果”,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又稳又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此外,我们还需澄清以下问题:坚持依附理论拒斥经济交往,还是融入全球化潮流加强世界性交往?依附理论坚决拒斥经济交往,认为其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落后的根源,要想摆脱依附地位,不发达国家或第三世界应该与发达国家断绝任何交往。这一观点是片面的,马克思早就分析指出,从全球化的形成来看,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但是从其发展趋势来看,全球化的实质又是共产主义的。虽然融入全球化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这一潮流,要顺应历史潮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36)丰子义、杨学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4、167页。
(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视角
地域性交往向世界交往、普遍交往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并且,“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6、169页。换言之,不可抗拒的全球化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已经从根本上改变和塑造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方式。人只有在普遍的、世界性的交往中,在完全进入世界历史后,才获得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全面发展的条件与可能,获得了实现最普遍最全面的个人自由的可能。
在信息化的今天,我们还要处理好网络交往(38)对于网络交往这一概念的内涵,学界仍存在争议。西方学者多使用“计算机媒介沟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称CMC)“互联网沟通”(Internet Communication)“计算机媒介互动” (Computer-Mediated Interaction)“互联网使用行为” ( Internet Use Behavior)等概念。国内学界一般都认为,网络交往是以计算机为中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交往方式,是传统交往方式在信息化时代的拓展和发展,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参见陈秋珠:《赛博空间的人际交往——大学生网络交往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0页。这一新型交往方式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网络交往的自由性、多元性、隐匿性、无中心等特点,确实能为交往主体提供相对公平、自由、高效的表达环境和交流空间,但同时也带来了网络暴力、道德失范、自我认同危机等诸多问题,网络交往需要更加规范化和理性化。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网络只是交往的一种新型方式而已,交往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要认真分析网络交往的特点、探讨其对马克思交往观的发展、研究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路径,使其真正成为拓宽人的交往空间、交往范围,变革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重要手段。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源头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不确定期,世界要往何处去,国际交往的准则应当如何确立,是每个国家都要思考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实现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发。(39)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25、414、508页。这一理念与马克思交往思想的内在本质、价值目标和实践道路是一致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晚年马克思交往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习近平同志站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新高度,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深刻认识到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性交往的不断深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民福祉的可能性、必要性选择。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它不单纯是理论层面的国际交往理念,更是实践层面的国际准则;它不仅仅是一种外交理念,更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外交等各个领域,并得到众多国家大力支持和推广的价值观;其对人类文明走向做出的前瞻性科学研判,为全人类的交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