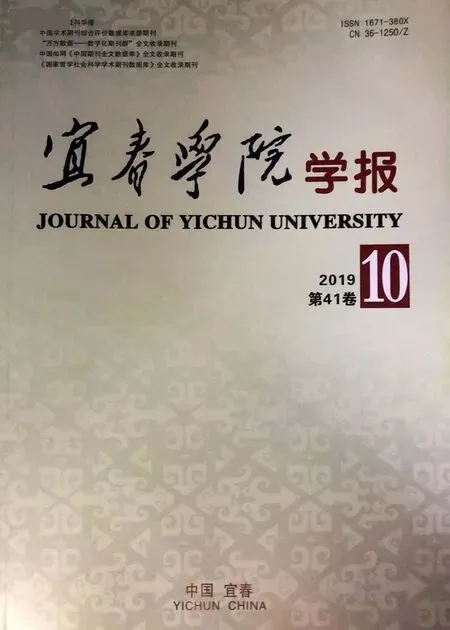论宋高宗时期御试策
2019-12-16史婷
史 婷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殿试,即覆试,皇帝亲策于殿,故又名御试、廷试、廷对。御试策是殿试的产物,其主体由制策和对策两部分组成。由皇帝亲拟或执事大臣代拟,并以帝王名义发问的策问称为制策,其期于通达时务。士子们则在廷殿答策,指陈当世之急务并提出解决办法。
近年来,学界渐渐加大了对科举试策这一文体的研究,特别是其中的御试策,其蕴含的独特的文学价值逐渐被研究者发掘。何忠礼对宋代殿试制度及科举文化进行了研究。祝尚书对宋代的三级考试分别论述,在此基础上增补了一些宋代考试文体的章节,将科举考试制度和考试文本紧密结合,更为完整地展现了宋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方笑一对宋代的御试策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考虑了御试策的文本形式,对其话语进行了分析,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
一、高宗时期御试策统论
宋徽宗宣和七年,金人入寇。天下勤王之师主帅非人,战事失利,北宋军队节节败退。靖康二年夏四月,金人虏帝及皇后众人北归,府库畜积,洗之一空,国家被破坏殆尽,北宋灭亡。五月,康王赵构于南京即位,南宋建立。本与大统无缘的赵构,此时成为宋王朝唯一的希望。然此时政权屈辱南逃,人才流失严重,高宗既失宗室,又无子嗣。南宋蒙昧,主孤内危。
高宗急于问政,意图选拔贤才,并获得有效的治国措施。亲策于庭,这是其最务实的政治举措。因其特殊的社会背景,这一时期御试策往往含义深刻,耐人寻味。宋高宗在位的35年间,科举取士一如祖宗之时。据《全宋文》统计,高宗御集英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多达十次,现存制策及士子们的对策如下表所示:

制 策时 间对 策《试礼部奏名进士制策》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胡铨《御试策》《试礼部奏名进士制策》绍兴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张九成《状元策一道》《试正奏名进士制策》绍兴五年八月二十二日黄中《对策》汪应辰《廷试策》《试礼部奏名进士制策》绍兴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陈诚之《论中兴策》秦熺《对策》《试礼部奏名进士制策》绍兴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刘章《廷对策问》《御试礼部奏名进士制策》绍兴十八年四月三日董德元《廷对论起晋唐之陵夷接东汉之轨迹策》王佐(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七)《试举人郑闻以下制策》绍兴二十一年闰四月十七日赵逵《御试策一道》《试礼部奏名进士制策》绍兴二十四年三月八日张孝祥《御试策一道》曹冠《对御试策》秦勋《对策》《试礼部奏名进士制策》绍兴二十七年三月八日王十朋《御试策》《试礼部奏名进士制策》绍兴三十年三月九日梁克家(缺)
高宗制策及士子们的对策主要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民生四方面的内容,覆盖面比较广,但论点相对集中。从试策可以看出南宋初期的社会现状以及统治阶层的政治举措及治理效益,其间不乏有爱国志士的对策为国家的恢复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高宗时期御试策的思想内容
(一)政治之臧否
国初,金虏不断滋事,国家对外无力抗争侵犯,朝政内部又如同一盘散沙,加之深患“恐金病”的高宗亲信佞臣,对贤良方正之士极不重视,陈东、欧阳徹之辈被杀,更是开祖宗杀谏臣之先河。
建炎二年,高宗制策说:“外患未弭,盗寇尚多,而追胥有程。择守令以厚牧养,责按廉以戢贪暴。”[1〗(201册,卷4447,P231)看似高宗两年间在任人方面有作为,然收效并不可观。胡铨《御试策》指出朝廷“牧之以不贤之守令,扰之以不才之按廉,是由疾已深而投之冶葛”,为官者不贤不才,旷其职业,失为人臣子、为民官员的本分,这是统治者用人的重大失误,如此“祇速其死耳”[1](195册,卷4301,P71)。高宗制策又说:“刑赏不足以振偷惰之气,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之心。”[1](201册,卷4447,P232)胡铨指出今日朝堂无可用肱骨之臣,以致“蕞尔丑虏,皆为劲敌”[1](195册,卷4301,P76)。此时李纲、宗泽去国不久,我们能从御试策中看出胡铨对二人遭遇的惋惜和对高宗任人不清的痛彻之情。
在金军不断进逼下,高宗建炎三年遣杜时亮及宋汝为赴金军以请和,屈辱致书粘没喝,以“削号”“称臣”屈辱求生。在绍兴二年的殿试中,高宗制策竟将这一偷安行为奉为“勤民”之举,而此时民心已然尽失。高宗这般颠倒黑白,不断转嫁自己的怯懦行径,勤民之“勤”,不过空谈。后张九成在答策中借金虏有必亡之“三势”,一一剖析,指出欲灭金虏,当先结民心,依次运用越、秦、高祖之计,必将实现大业。同时,在任人方面告诫高宗要“笃恭俭,谨用人,明赏罚,已收天下之心”[1](183册,卷4031,P422)。高宗时期“严赃吏之诛,而未能革贪污之俗;优军功之赏,而无以消冒滥之风”,加之“吏员猥并,失职之士尚众”[1](202册,卷4467,P112),张九成因此在选人问题中提出了具体措施,宜用辟举法。这一举措可精选吏员,有很强的操作性,或多或少能够冲击权臣专权之态,对朋党的形成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能否在南宋初这一复杂的现实中顺利运作,则成为难题。汪应辰于御试策也指出,人才的弊端在于空谈之风盛行。
绍兴八年,朝廷闻徽宗逝世,高宗以“谅阁罢殿试”。[2〗(选举二,卷一五六,P3628)十一年“绍兴和议”签订,十二年高宗以“中兴”之策问于下,陈诚之建议休兵息民,以任贤、纳谏、崇俭为上策,蓄力俟时。此时战之无益,确无再战之必要。十五年,高宗制策指出要以德行和智略治国,令士子们上变风俗之策,刘章指出当任用真儒,始终如一。此时距和议签订已有四年,高宗稍得喘息,从制策中亦能看出其“保治之道”,与之前处处发时弊而问的策问大有不同。二十四年高宗问治,张孝祥指出了休兵息民之际国家依旧弊端丛生,“宴安之毒可怀而苦口逆耳之言难入”[1](253册,卷5694,P360),奸小当道,致使“人主耳目雍蔽”。[3〗(卷七十五,P804)利未兴,害未除,取士须务实。二十五年,秦桧逝世。处在权臣和金虏双重压力下的高宗此时颇为轻松,二十七年,其制策指出“奸弊未尽革”“财用未甚裕”“人才尚未胜”“官师或未励”[1](204册,卷4533,P274)四大时弊,王十朋指出这些问题皆因高宗权柄长期下移所致,秦桧长达十七年的擅权,是国家机构陷于瘫痪,其精心编制的关系网几乎将皇帝架空。
高宗时权臣把持朝政,选人用人皆其措置,如此,左右皆权臣之党,致使“中外远近无敢忤权臣者,以故忠义解体而君上之势孤也”[1](195册,卷4301,P79),且其党羽多为长奔竞者,常常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国家利益。因此,统治者能否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为国运之关键。秦桧集团覆灭,此时不仅是高宗的喘息之机,更是南宋王朝新的契机。王十朋提出皇帝要以“揽权”为出发点,建议高宗要揽育才取士之权,同时察百官,明黜渉,以《春秋》和祖宗之法为鉴,加之帝王修身正己,则天下大事可“不动声色而为之”,可见其对朝政之事尚有一线希望。
(二)军事之兴颓
靖康之变以及之后接连不断的战乱对本就不精锐的南宋军力造成了更严重的削弱。建炎二年,高宗制策指出今“外患未弭”而“军事未张”,胡铨答到:“士卒死边野之外,妇哭其夫,母哭其子,寡妇弱子抱负轊车,望冤吊哀于千里之外,塗悲巷哭,怨痛徹天。”[1](195册,卷4301,P80-81)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是无法估量的。加之军事对抗需要大量兵力支撑,朝廷大力募兵,以致流民丛生,内盗兴起,造成“兵纵而不戢”[4](卷七十八,P1286)的局面。临时凑数的兵力,缺乏武将整饬与正规训练,反而造成冗兵之弊。绍兴二年,高宗制策又指出盗寇和军吏的问题,张九成说,叛逃或遁行军士,“其横行于州郡,啸聚于山林者,类皆军兵耳。”散兵游勇之徒,太平时“帖首妥尾,惟上之令。不幸中国多故,朝廷权轻,何尔动辄怨怒耶?而一夫倡乱,百夫从之,百夫倡乱,千万人从之”。[1](183册,卷4031,P422)据记载,仅这一年军乱、盗贼、起义之祸多达九次。
金兵进犯、奸臣当道、军力贫弱。胡铨御试策对此一语中的。在国家无事之时,军士该为国力后盾,有事之时,当为前锋,然此时军士成为国家累赘,统治者的各项治军举措往往使其自困。十一月,庐州守臣李会降,后和州等各地守臣或降,或弃城走,惟有芗城胡铨团结丁壮力保庐井,带领民兵固守到底。朝廷平日里豢养的‘大将’,一味屈服于金虏,致使军心严重动摇。绍兴五年,汪应辰在答高宗制策时也指出军队之弊,“教习击刺,叫躁号呼,有如聚戏。金鼓旗号,白梃小队,皆效敌人,节制荡然,虽其将帅莫敢自保。”[1](215册,卷4779,P220)这些利己主义者,战事稍有不测,或投降为虏之用,或出逃占据一方为霸,一地遇有战事,或支援散漫,或相互扯皮,胜则争先邀功,败则互相推诿。
军事颓弱,或寡而不精,或冗而不练。“选练未精而军多冗籍”[1](202册,卷4467,P112)是其常态,富平之战、淮西之变即是明证。和议之后,息兵休民之举也无实际效用,统治者苟且偷安,无心自治,军队散漫,缺乏有效管理,军事力量也无多大改变,在御试策中有明显的反映。因统治者极力避战,绍兴中后期制策及御试策中几乎对军事问题避而不谈。
(三)民生之得失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1](188册,卷4148,P319)民生问题是高宗朝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南宋初经过连年战乱,“余民之存者十无二三”。[5](卷十一,P116)金兵进犯,烧杀掳掠,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此时土地兼并严重,随高宗南下者,妄图取得一时之安,大肆掠民,以贡其乐。然巨大的国用开支却加重了百姓的痛苦,加之貊乡鼠壤,猿穴坏山,百姓受到的盘剥是之前的数倍不止,“生寡食众,入少用多”[1](195册,卷4301,P72)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农贫而多失职”[2](食货上一,卷一七三,P4170),遂为盗贼,熊克《中兴小纪》说:“民不堪命,则据险结党,抗拒县官,既免征徭之苦,且获攘掠之利,故多去为盗。”[6](卷九,P5)
人民越发贫困,仅东南地区的赋税,从南宋初年到绍兴末,猛增六倍之多。据记载,“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至“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置之钱,凡六千余万缗”[4](卷一九三,P3239-3240),加之“金人入侵的烧杀掳掠,游寇、溃兵、官军的抢夺破坏”[7](P51),劳苦农民几乎无法生存。三十年间,劝农之举常有,买牛借种之事随处可见,但“屡遭兵火,宰杀殆尽”[8](食货一,P5966),百姓压力依旧巨大。朝廷虽以拉拢和限制富户为减役之举,然未有实效,各级官吏反而生发出更多赋役名目,巨额赋税仍被转嫁到百姓身上,百姓往往被“剥肤椎髓”“膏血无余”[4](卷一二五,P2040)。饥饿遍野,甚至到了食人的地步,如胡铨说:“窃见一二年来,东南之民困于军兴,前岁大旱,人至相食,虽亲父母手杀其子食之”,即使遇丰年,“比他岁所入十倍,然官敛其七八,民存二三,生理萧然,卒有水旱,民无一年之储。”[1](195册,卷4303,P101)
建炎二年,高宗制策指出其恤民之举为“薄赋敛”,然“田亩未安,旱蝗害岁”,百姓的压力依旧巨大。胡铨对策指出高宗施政的弊端在于所任官员的失职,导致“陛下命令为民而下,虽十常六七,而壅遏诏书者十常八九矣。是陛下有恤民之诏,无及民之惠。”且赋敛也并未真正减少。绍兴二年的制策反映了同样的问题,“招诱以弭盗,而盗贼犹炽”。[1](202册,卷4467,p112)张九成在其御试策中引唐太宗故事说明民困于赋敛不得已而为盗贼,故要“戒藩方”“罢武尉”“苏凋瘵”,消灭蠹民之虫,以安抚民心。
《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四年九月,因检放官渎职,致使民生流离冻馁。五年,高宗以减赋而实惠未孚于下问策。汪应辰指出朝廷的欺民之举不会改善民生,建议“省官以节俸稍,屯戍营田以宽力役,平准、均输以佐赋入”[1](215册,卷4779,P219-220),以恢复民生。然如何实行及收效是否可观,就不是纸上谈兵这样的易事了。赵逵也在御试策中指出要摒弃私利,远离奸佞,以德化民,收取民心,其为治之本。
“绍兴和议”之后,南宋稍得喘息之机,宋金双方相持数年,然高宗并未以暂时的安定为休养生息的契机,其志有余而气不足,不“以刚大为心”,反而“遽以惊忧自沮”[1](183册,卷4031,P416),并非中兴之君,“继体守文则有余,拨乱反正则不足”。[3](卷七十六,P808)高宗偷安之时,“搜揽珍禽,趋驰骏马”[1](183册,卷4031,P427),民生日益凋敝。后有诗歌讽刺统治者迷醉的生活,说绍兴时经济颇康裕,然而此种“康裕”之势,多为搜刮暴敛而来,经济恢复所得仅为少数。但“君相纵逸,耽乐湖山,无复新亭之泪”,故林升诗讽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9](卷二,P12)高宗“偷安忘耻,匿怨忘亲”[2](卷三十二,P612)之丑态,可见一斑。
(四)经济之损益
“天下之费,莫甚于养兵。”[8](食货三,P6005)大力募兵致使“府库丹匮,军费倍滋”[1](201册,卷4447,P231-232),加之军士骄奢之习未悛,私枉之俗尚胜,社会风俗败坏,经济持续颓敝。胡铨说:“以今征役之久,动至累年,较之《春秋》三时而返者,不已大甚乎?则库藏竭而军费滋,自不足怪。”他以为今之大病乃“兵冗而坐食,师老而费财,加之生寡食众,入少用多”,且“按兵法,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以日计之,费以如此,况今旷日弥年,兵连不解”。张九成也指出中兴之本在于“刚与俭”,批判高宗奢靡之举。绍兴五年,高宗因以简练之法治兵而冗食未革为虑,然此为军费紧张的主要原因。汪应辰《廷试策》指出,“至于冒请月俸,虚糜气廪,蓋有诡名而请者矣,蓋有以使臣之名而请者矣,蓋有借补官资而请者矣”[1](215册,卷4779,P220),因此需先振纲纪,革冒滥之风气,然后施之以屯戍、营田、平准、均输之法,则可行矣。
高宗自和戎十多年以来,按照国家正常的发展规模,此时当仓廪富实,贯朽粟陈。然现实并非如此。绍兴二十七年,高宗制策说财用未甚裕。王十朋《御试策》指出平日国用浪费大,无名之费耗财,皆为息兵休民之际经济依旧贫弱的原因。据统计,高宗渡江后郊赏数额巨大。“建炎二年,用钱二十万缗,金三百七十两,银十九万两,帛六十万匹,丝绵八十万两”[10](甲集卷十七,P379-380);到绍兴元年,仅越州诸军犒赏高达六十万缗;四年,建康增至二百五十九万缗,如此高额,是府库的一项巨大开支。高宗一直是一个耽于享乐之人,自身及后宫开销也十分巨大。据记载,高宗对金称臣后,开始大兴土木;其母每年开销巨大,多至“钱二十万缗,帛二万一千匹,绵五千两,羊千有八十口,酒三十六石”[4](卷一四六,P2354);其妃生活更是奢侈,尝“恃思骄侈,盛夏以水晶饰足蹋”[10](甲集卷一,p31),可见其奢靡程度之深。加之除了根据和议连年对金上贡高额财物外,韦太后每年要向金朝皇后贡献大量礼物,还要赏赐金使称之为“密赐”的额外之财,“金使白金千四百两,副使八百八十两,袭衣襟带三条,三节人皆袭衣塗金带,上节银四十两,中下节银三十两。”[4](卷一五一,P2423)如此,国家财用紧缺便不难理解。本朝官员贪蠹,“左右近习与夫贵戚之家,第宅池馆,穷极华美,田园邸舍,连亘阡陌”[1](214册,卷4764,P344),即使多年未用兵革,天下财物也不被国家掌握,仅秦桧一人暴敛之财就多于国库数倍,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其家富于左藏数倍。”[4](卷一六九,P2772)因此,国库积蓄并无多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宗朝前期战乱频繁,统治者疲于应付战事,无力发展经济,致使国家综合实力远远落后于北宋时期。和议之后稍得恢复之契机,但统治阶层借之穷奢极侈,贪贿成风,一味苟安,无意在举恢复大业,经济发展几乎再无可能。
高宗一朝三十年来,朝廷所进行的各项措施,并未改变病变的肌理,而只是在表皮做文章。纲纪不振,奸佞误国,加之统治者无心政事,再好的举措也无法使颓弱的国力恢复。其所做的努力仅是为了满足其偷安的需要,对于恢复大业,也只是口号式的提及。从三十年间的制策中可反映出高宗的焦虑之情和恢复之志都只是模式化的表演,一切以安抚为主,毫无长远打算,只要金虏不危及到自身性命,在高宗眼中一切弊病皆为次要矛盾。王夫之《宋论》说,高宗“得孝宗而授之,如脱桎梏而游于阆风之圃”,[11](P201-202)怯懦的性格跃然纸上。统治者不作为的心态,使文人士大夫们反应各异,或怒其不争,痛斥之;或哀其不幸,祐护之;或顺其心意,妄为之;或隐匿远遁,独善之。战、守、和成为士大夫与群小近习争论的焦点,然只图求得一夕之安的高宗,不战而气馁。可称臣,可割地,可上贡,对于士子们的态度,顺其昌,逆则亡。这在御试策中表现十分明显。
三、高宗时期御试策的特点
在南宋初这一历史背景下,高宗的制策及士子们的对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针对性极强,逻辑理性突出。制策为皇帝针对时务而发问于读书人,旨在选拔人才,统治者更希冀通过此举能够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故皇帝所问之事,皆为国家当下亟待解决的弊病,士子也需根据制策所列问题作答。制策所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生各个方面的问题,范围极其广阔,士子们一般分条作答,给出相应的意见或建议。且殿试作为最高层级的考试,能进入集英殿的读书人,皆为人中之佼佼者。其御试策理性思维突出,逻辑清晰,下笔富有气势,结构满是经纶,显示了高超的文学素养和史学素养。
第二,事实明晰充分。“作策者,嗜古则不俗,从今则不戾,参任以变,会通其观,古可以通于今,今可以程乎古。”[12](后编卷之五,P11)作为最高阶层的策问,制策或亲拟,或代拟,但都通过皇帝授意而发问于士,所问涉及社稷诸多方面,对于时弊的提出也一针见血。士子们的御试策旁征博引,句句入理,以圣训道,传扬正统,指陈时事,以古见今,议论明晰充实,使皇帝无反驳的余地。如胡铨御试策开始直接批判高宗不以民众的利益为转移,而一味质询皇天之弊,指出失民心则失天下的道理,以《春秋》为训;王十朋亦指出要以《春秋》为法而谨戒之;汪应辰御试策以“反求诸己”为出发点,以儒家圣人之言、先辈圣王为借鉴对象,悉数陈之,力求所提出的观点和见解深刻,具有启发性。
第三,情感充沛,理顺辞畅。皇帝制策与有司策问最大的区别在于“以情发问”,其制策中往往包含着十分浓郁的焦虑感,读来易令人生恻隐之心,可以激发士子们的爱国热情,使所学所想毫无保留地陈于皇帝面前。士子们的对策则“为情造文”,文字思想掩盖不住士子们迸发的情感,这使得御试策理顺辞畅,且不同策文反映的情感存在差异。离祸乱越近,御试策所表现的感情更加强烈,悲愤之情呼之欲出。相较而言,建炎二年胡铨的对策感情十分浓郁,陈述极其详实、痛彻、激烈,读来确有国破家亡之感。此时离靖康之变不过六年,又连外虏遭侵压,国势沉郁之气比较明显。而绍兴二年张九成的对策,情感亦极其强烈,运用比喻的修辞,诉说不论何时都为社稷而忧心,加之以铺陈的写法,极具感染性和煽动性,读来如泣如诉,极其感人。其后汪应辰等人的对策确有情意,却不如胡铨等激愤。
第四,语言技巧突出。御试策作为官方最高级别考试的产物,具有双重性质,其一方面美刺时政和帝王,一方面努力寻找一种情感上的平衡状态,由此“产生了独特的言说技巧和修辞策略”[13](P74)。我们可以看出,胡铨、张九成、汪应辰、王十朋等人皆对时弊有着直接的批判,语言也十分犀利,但策文中又有刻意夸大皇帝事业、贬低自身之举,这其中除了等级束缚,更多的是士子们要将颂圣与劝上巧妙融合。如张九成策文有“澄江泄练”“夜桂飘香”[1](183册,卷4031,P426)之语,确于传统时文的严肃感有别。如此安排,无疑是在为自己的“僭越”之举找台阶,话语技巧极高。
高宗时御试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家纷乱之际,抗敌御辱当为第一要务,然奸小误国,人心涣散。士子对策能够凝聚心力,鼓舞士气,宣扬了其大公无私的浩然正气。而且对正统文化的传扬起到了作用,有利于改善社会风俗,稳定社会秩序,树立正统观念,抵制不良之风的影响。同时,统治者通过御试策,既选拔了大量人才,又获得了治理国家的思路和方案,这一选拔手段一直为元明清统治者采用,直至清末科举制废除。而此时的御试策,亦为我们研究高宗一朝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