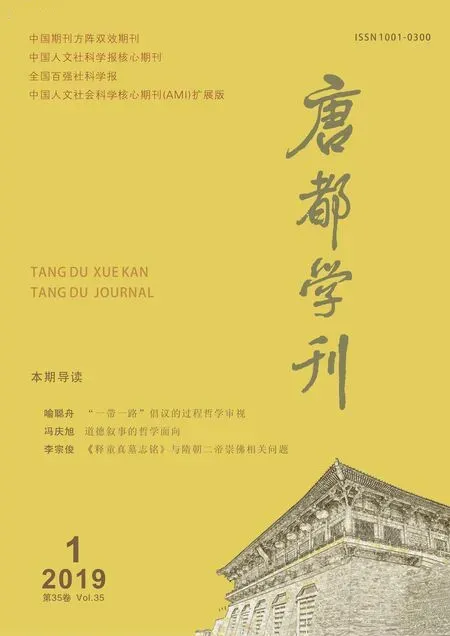动物与人之间的互动
——《恋爱中的女人》三组意象评析
2019-12-16陈敬玺
陈敬玺
(西北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27)
劳伦斯在1913年1月写给好友恩尼斯特·柯林斯的信中对自己的创作原则有这样的说明:“我确信,只有通过重新调整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通过使性爱获得解放而变得健康,英国才能从它目前的萎靡之中解脱出来。”其时,他正在着手创作《两姊妹》这部探索“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力作。《两姊妹》后来被分成两部,即分别在1914年和1916年定稿的《婚戒》(也就是《虹》)和《恋爱中的女人》。
《恋爱中的女人》[1]围绕着一种有趣而复杂的性力动态体系(sexual power dynamic)来展开故事情节[2],即每一个主要人物身上都表现出某种施虐、受虐的倾向和行为。杰拉德·克里奇试图主导其情人古德兰·布朗温,古德兰的姐姐厄秀拉则不断努力地去超越情人拉帕特·伯金。整部小说都充斥着暴力和斗争,四个主要人物不仅参与身体和精神的暴力行为,而且似乎还乐在其中。杰拉德无疑是典型的施虐狂,而另外三人在不同场合也表现出受虐与施虐的倾向。
受虐与施虐,现在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而受到热议,在一百多年前却属于私密的话题,很少有人触及。劳伦斯尽管不避世俗,但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还是使用了简洁而隐晦的方式,即把施虐的对象设置为动物而非人。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里基于主导欲和占有欲的固有斗争具体而形象地映射在动物的身上。动物成了人类暴力的承受者和接受者,成了表达男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象征符号。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有以下三组动物意象。
一、受虐的阿拉伯牝马
杰拉德一定要让这匹牝马学会不怕噪声和机械的本事,所以强迫她在过火车的时候紧靠铁路站立着。马吓坏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紧张对峙于是出现。不远处的古德兰与厄秀拉目睹了这一场景:
遮蔽在路堤之间的火车缓缓地闷声开过来。那牝马不喜欢火车,开始往后退缩,好像那来路不明的噪音伤害了它。但杰拉尔德硬生生地把马拽了回来,让它头朝向道岔口。火车发出阵阵轰响,汽笛不停地尖叫。牝马感到透骨的惊恐,浑身颤抖不已,并像弹簧一样往后退缩。杰拉尔德脸上闪过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又一次不可抗拒地把马拽了回来。[注]D.H.Lawrence,Women in Love,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2011.引文皆为作者根据该版英文原文做出的译文。
牝马发疯似的往后逃,但杰拉德下狠心要驯服她、主导她,并不惜使用鞭抽、脚踢之类的暴力,让马不能远离铁路。“古德兰看着。牝马身上渗出了血,古德兰脸都吓白了。接着,闪亮的马刺无情地压落在滴血的伤口上。”古德兰受不了血腥场面而晕厥过去了。这场遭遇无疑是暴力性的,但对杰拉德和古德兰来说也是性爱性的——简直就是一场暴力性侵犯:
杰拉尔德一发狠劲儿,用力加紧马身,就像是快刀刺入心脏,硬生生让马转了回来。牝马口喘粗气,大声咆哮,两只鼻孔呼呼冒气,一张大嘴豁然洞开。太让人倒胃口了。然而,杰拉尔德丝毫没有松懈,而是带着一种近乎机械般的残忍和利剑般的迅捷死死勒住牝马。人和马都因为使劲儿而大汗淋淋,不过人看上去还是很镇定,好似一缕清冷的阳光。
这一插曲完全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施虐性的强暴,因为马刺猛烈插入牝马体内却又违背其意愿。杰拉德暴烈残忍而又平静自若,他从这种强暴行为中得到乐趣,就像主宰自己身边之人的命运那样感到快活,因为他赢得了斗争并在取胜过程中展示了自己男性的权力。牝马若是还扮演着人的角色,杰拉德也一定从击败或支配这人的行为中感到无穷的乐趣。因此,我们可以把杰拉德看作是一个施虐者,或者至少是一个把性当作压制工具的控制欲极强的人。
杰拉德与牝马的相持其实是他与小说中其他人物之间斗争的一种隐喻。马可以是伯金,因为杰拉德一直试图将伯金置于一种服从的境地。这从二人赤身裸体进行的那场颇具同性恋意味的摔跤比赛中得到明显的印证。不过,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是:牝马扮演着古德兰的角色。古德兰后来成为杰拉德的妻子,她在与杰拉德的多次遭遇中几乎是场场必输,但与牝马一样,她虽输犹喜。杰拉德对牝马施加的残暴,古德兰十分反感,却又感到兴味盎然。她义愤填膺,头晕目眩,“好像有什么东西深深地刺进了心里”,而当最为疯狂的暴行(马刺连续夹击马身几近性高潮)来临时,她终于晕倒过去了。苏醒过来,发现一切都差不多已经回归平静,事件本身成了一种扭曲的追忆。比起先前火车刹闸的咔嚓声和牝马的尖叫声,一切都显得出奇的宁静,耳中传来的只是“惊魂未定的牝马发出的急促喘气声”。古德兰憎恶暴力,不过在强加于己身的这一场景中她其实也经历了一次性体验。牝马就是她的替身,将来杰拉德也会对她如法炮制,强迫她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想方设法去支配她,征服她,为她当家做主。牝马的惨痛让她激动不已,说明古德兰在内心里期待杰拉德如此待她。她乐意服从,乐意成为他的妻子。
事隔几天后发生的争论,进一步说明了牝马与古德兰(或许所有的女性)的二位一体关系。厄秀拉指责杰拉德对马过于残暴,杰拉德便跟她就男人的权利问题吵了起来:
“为什么要施加无谓的折磨呢?”厄秀拉问道。“为什么要让马一直站在道岔口呢?你完全可以顺着路退回去一些,用不着经历惊恐呀。马背都给你弄得流血了,太恐怖了!”
杰拉尔德身子一紧,回答道:
“我得利用马,而为了让我完全放心地利用,它就得学会忍耐噪音。”
“为什么要忍耐呢?”厄秀拉急了,大叫道。“马是活物,为什么要它忍耐呢?只是因为你要它忍耐吗?马有权自己做主,正如你自己有权做主一样。”
“这我可不认可。”杰拉尔德说道,“我认为马活着就是让我去利用,不是因为马是我买来的,而是因为天道本来如此。人弄来一匹马随意使用,这要比跪在马面前求它为人做事以履行其神奇天性顺理成章得多啊!”
“身子一紧”是上次他与牝马间的性投入之残留,对厄秀拉指责的回应则是他对性张力的强调。“我得利用马”中的“利用”一词可以从不同层面来加以理解。古德兰与牝马二位一体,杰拉德必须利用她。对于杰拉德的残忍行为,古德兰一开始是很生气的,但明显不像姐姐那样义愤填膺,所以只是静静地听着他的辩解。杰拉德驭马驯马曾让她经历了某种喜悦,所以她开始质疑姐姐对其暴烈方式的指责。杰拉德似乎觉得世上存在着“天道”,居于上层的男人可以在必要时使用暴力对待居于下层的生物。古德兰既然与牝马二位一体,杰拉德就对她拥有控制权,因为她在“天道”之中居于下位。这样的世界观让杰拉德相信:他有权对她随意地使用暴力。
二、反抗的兔子俾斯麦
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建构人的行动力,这在抽打宠物兔俾斯麦的事件中再次得到印证。古德兰与杰拉德的妹妹温妮弗莱德要抓住兔子并将其关进笼子,但兔子吓得直挣扎。像牝马一样,俾斯麦与人斗起来,但不一样的是,兔子斗赢了。古德兰两只胳膊抱住兔子,而兔子力大无比:
兔子壮得叫人称奇,她(古德兰)只能将其抓在手中,不知如何是好。她满脸通红,愤怒得如同乌云冲顶,浑身颤抖,就像风雨中的小屋。她完全垮掉了。没头没脑的挣扎、兽性十足的愚行都让她怒火中烧。两只手腕被这野物抓得伤痕累累,胸中不禁涌上一股狠劲儿。
就在古德兰马上要输给俾斯麦的时候,杰拉德来了。杰拉德对“她愠怒残暴的情感爆发”感同身受,便试图在她输掉的地方重新获得成功,用暴力彻底制服兔子。杰拉德有能力控制局面,因为他对残暴的感觉已经习以为常。古德兰对杰拉德驭马驯马的方式本来且喜且怒,讨厌他对马的支配和主宰,不过在此时,她已经接受了强者利用弱者的观点。她努力去控制兔子,因为她相信兔子比她弱小,但她做不到。兔子又要出击反抗,杰拉德赶紧过来帮忙:
身子长长的野兔又猛然一蹬,四脚张开在空中翻腾,简直就是恶魔。……杰拉尔德紧绷着身子,不停地颤抖,暴怒无比。突然,他退后一步,腾出一只手来,老鹰抓小鸡般地卡住兔子的脖子。怕死的兔子立即发出刺耳的尖叫,身体剧烈地扭动起来,并在最后的挣扎中撕扯杰拉尔德的手腕和衣袖。兔子白花花的肚皮朝天,四只脚乱蹬一气。杰拉尔德提着兔子抡了一圈,然后将其卡在胳膊下面。兔子畏畏缩缩地蜷着身子,杰拉尔德脸上露出了微笑。
杰拉德再次成为动物的主人,俾斯麦陷入死一般的深度昏迷,过了好几分钟才弱弱地苏醒过来。这一次,古德兰对人与动物间的暴力互动并没有感到恐惧,而是对兔子的最终制服感到欣喜不已。她的态度在这两个事件中有了变化,因为与俾斯麦的争斗表明她已经接受了杰拉德的观点。
收拾完兔子后,杰拉德和古德兰的眼中都露出了胜利与性爱的神情。杰拉德对兔子实施了权力而且用的是暴力手段,其无与伦比的权力和阳刚之气在此得以充分地展现:“他看见她苍白的脸上一双眼睛黑如夜色,整个人简直就像是仙女下凡。兔子经过拼命的挣扎还在尖叫,似乎把她那意识的面纱都给揭开了。杰拉德看着她,脸上那道发白的电光一下子强烈起来。”这次经历,对于杰拉德和古德兰都具有催情的作用,而在他们对比各自伤痕的时候,情爱的感觉成分就更加明显和充分了。俾斯麦在二人身上留下的抓伤无疑具有某种隐喻性的性爱意义:
“一共有几处抓伤?”他(杰拉尔德)一边问一边伸出白皙结实的胳膊,上面布满一道道血红的伤痕。
“真可恶!”她大叫道,涨红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可怖的景象。“我的伤倒不算什么。”
她抬起手臂,洁白光滑的肌肤上露出一道深深的血红伤口。
“简直就是恶魔!”他惊叫道。不过,透过她丝般柔滑的小臂上那道长伤口,他对她似乎有了了解。
“了解”(knowledge)这个词曾经是性经历的同义词,故事叙述的语气和俾斯麦的语义指向都暗示词语的这一用法。古德兰的伤口催发了杰拉德的情欲,使他在想象中认为,俾斯麦用爪子撕裂古德兰的肌肤差不多就是自己在与古德兰做爱。二人不久便成了恋人,这样说想必令人不安,但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事件也催发了古德兰的情欲。古德兰支持杰拉德的权力,即有权对兔子、对自己施加那种先天的权力,于她迷途知返之时在她“洁白光滑的肌肤上”划下“深深的血红伤口”。此时的古德兰已经变成性受虐的角色,或者至少是接受了自己低人一等的服从地位。
古德兰开始认同杰拉德的“天道”,并用“天道”来为杰拉德伤害俾斯麦的行为开脱。她甚至痛骂兔子:“简直就是笨蛋!”“简直就是一道令人作呕的菜!”俾斯麦属于弱小动物,理应温顺地服从其人类主子。古德兰把背离常规的兔子视作笨蛋,并赞同使用施虐性的暴力让俾斯麦回到其正常的顺从地位。这种变化被杰拉德发现了,因为古德兰不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感受。看完杰拉德痛打兔子,“古德兰扭曲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她明白自己把内心的感受完全暴露了”。对这次经历,古德兰从内心上是喜欢的,而且默认了杰拉德的层级体系。这就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继续。古德兰对杰拉德的暴行不再憎厌,对其个性的残忍面也开始接受,两人的关系自然更加牢靠。事实上,随着故事的进展,两人的确越走越近了,不过,也并非没有艰难痛苦的阴影。假如古德兰愿意接受杰拉德的层级体系并生活在其中,那么她自己又处在什么位置呢?杰拉德通过行动表明,自己就是位于层级体系最上层的那一个,那么古德兰也就只能占据一个较为低级的位置。杰拉德一而再地声明,对于比自己弱小的生物他是乐于使用暴力的,古德兰当然也不例外。
杰拉德驭马驯马、痛打兔子,就是他与古德兰之间关系发展的象征。他努力去征服她,因为他想成为二人关系中的主导力量。他试图像驾驭牝马那样去驯服和控制她,但古德兰竭力抗拒这种驯服和控制。驭马事件固然催发了古德兰的情欲,但对杰拉德得寸进尺的行动她还是采取了断然拒绝的方式。牝马尽管受到马刺的夹击还是猛烈地抗拒杰拉德,这是对古德兰初次拒斥杰拉德及其观点(把古德兰与牝马视同一体)的预示。不过,对于杰拉德这个人以及他与自己的关系,古德兰在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她接受了杰拉德的暴力,甚至对此还有所期待。这在俾斯麦的身上得到了体现。兔子在笼中度日,比起多少有些自由的牝马更像是杰拉德的囚徒,施加在它身上的暴力足以将其置于死地,结果俾斯麦就比牝马更加的服从和谦恭。古德兰对杰拉德的观点从部分地拒斥一转为完全地接受,这在牝马和兔子两个动物行为之中得到了象征性的表现。
三、和谐的公猫米诺与野母猫
《恋爱中的女人》中还有一个动物之间互动的插曲,即发生在伯金家的公猫米诺与一只野母猫之间的争斗。不过,争斗的象征意义不是男性对女性的控制,而是表明一种需要:寻找一种平衡,一种男女两性关系中的平衡。从表面上看,两只猫的行为与杰拉德和牝马、兔子并无二致,因为公猫也使用暴力去制服母猫。米诺见了母猫,昂首阔步地朝她走过去。厄秀拉和伯金站在门廊下看着戏剧开场,并时不时地指指点点。没有人直接参与争斗,但事件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也很能说明问题。两只猫的互动似乎也引发了某种夺取主导权的斗争:
一只毛茸茸的灰色母猫蜷缩着身子悄悄爬上了篱笆墙。小公猫米诺脸上带着一副男人般的冷漠,昂首阔步走到她跟前,母猫则谦卑地匍匐在他面前。流浪猫那一双绿宝石般的眼睛里充满野性,向上仰望着公猫。公猫漫不经心地俯视着她,母猫又往前爬了几步,继续朝后门走去。……小公猫迈着纤细的双腿昂首跟在母猫的后面。突然,公猫给了母猫一个粗野的耳光。母猫逃出几步,便像一片落叶一样顺从地蜷伏在地上。米诺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而是眨着眼睛看风景。突然,母猫鼓足劲儿,悄然移开一点,再一点,眼看着就要像梦一样地消失掉。可就在这时,灰色君主一下子跳到她跟前,轻柔潇洒地给了她一记耳光。母猫立马顺从地躺下,再也不动弹了。
米诺对野猫的行为与杰拉德对牝马、兔子的行为明显地相似。公猫控制着整个局面,对母猫实施一种“主导权”并通过表面上的暴力声明其“优越”的地位。公猫用爪子击打母猫,一如杰拉德用马刺来控制牝马,击打其头部来制服兔子。在对别人实施主宰的欲望上,米诺似乎表现出很多与杰拉德相同的特点。
说米诺“用爪子拍打”象征其主宰野母猫的那种欲望,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但厄秀拉肯定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她把公猫看作是杰拉德:“简直就像杰拉德·克里奇对付那匹马——一种霸欲——一种真正的权力意志(原文为德文)——太卑鄙,太下作了!”对此,伯金则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对于米诺来说,他就是要把母猫带入一种完全均衡的稳定状态之中,也就是与一个雄性个体建立起一种超然的、负责任的亲密关系。你看,要是没有米诺,她只是一只流浪猫,一个时而可见的毛茸茸的混沌碎片。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权力意志,一种能力意志,而“能力”在这儿用作动词。
伯金为米诺的行为辩解,声称这只是其“权力意志”(原文为法文)的表现,这种权力意志可以驯服野猫,使之进入一种平等的关系。伯金认为,米诺与杰拉德不一样,它施加一定的权力是为了保证一种稳固的结合。也就是说,米诺并不想控制野猫,只是想驯服她,让她能够享受一种积极的、稳定的关系。这种看法在文本中得到了印证:其一,米诺的行为并不像杰拉德那么猛烈。猫的行为是轻松的,简直就是嬉戏——对米诺来说,打斗更像是一场游戏。杰拉德对牝马和兔子的行为却是猛烈的,丝毫没有嬉戏的成分。米诺确实是打了野猫,但不能将其视为暴力,因为它并没有使劲儿地打击,而只是闹着玩儿似的拍打。米诺用爪子打野猫,“击打”的前面总是加上了“轻轻”或“悠闲”之类的形容词,这与杰拉德的击打(总是与“迅速”“凶狠”“无情”之类的形容词连用)是不相同的。其二,米诺拍打用的是“一只白色的嫩拳头”,明显属于玩耍的性质,其本意并非要对野猫造成任何伤害。
最后,米诺与杰拉德在目标上也有区别。杰拉德斗争的对象是两只动物和古德兰,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权去支配不如他强大的生物,寻求的是完全控制他们并成为他们的主人。米诺及其替身伯金却不是这样。米诺虽然伸张权威,但并不想完全控制与征服野猫。伯金家的猫放走了野猫,使之依然自由自在,把握自己的命运。厄秀拉认为米诺的行为太残忍,因而瞧不起它,伯金却不这样看:“不。……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他不是以大欺小,只是在向那只迷途的野猫表明她必须把他视为自己命运的一部分。……我完全支持他,因为他想得到超好的稳定”。伯金在这里触及了小说的主题:为了维持关系平衡,双方都需要斗争来建立起各自的个性和权力。假如双方都保持平等的权力和掌控力,这种斗争便会走向没有占有意味的平衡。当然,一方可能多有一点掌控权,但不足以代表任何实质性的不平等。但是,作为关系中的一方一旦壮大起来,要去掌控另外一方,占有的状态就会出现,结合也就因此被毁灭。杰拉德是这样。他要支配古德兰,将其物化为自己的“财产”,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健康。伯金的前妻赫米恩也是这样,因为她要在婚姻中控制伯金。厄秀拉与伯金则是在开始一种属于自己的新型关系,两只猫的关系便是他们这种关系的折射。权力之争是有的,但谁也不去完全征服或者控制对方。这样的冲突是健康的,因为它在两人的关系中既容忍依赖也容忍独立,结果便出现了一种更为开放、灵活的联系。小说中,厄秀拉对伯金越来越依赖,越来越不那么“野”了。他们在达到那种平衡的过程中虽然有争斗,但争斗中没有暴力,所以他们维持着各自的独立和身份。争斗只是他们寻求正确平衡状态的一种手段。两人享受着平等的婚姻关系,其中没有半点占有的色彩。伯金说对了:两只猫之间的关系与杰拉德和牝马、兔子的关系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健康与正常的结合。
四、结语
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尤其是性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施虐、受虐倾向与行为,在劳伦斯的时代还不被人们公开谈论,所以他采取了间接迂回的方式,即以动物为意象和载体,通过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互动来加以暗示与折射。动物在劳伦斯的笔下因此成为一种象征符号,即用“某一事物来代表或者表示别的事物”[注]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其《文学理论》中对象征有这样的定义:它是一个逻辑学术语、数学术语,也是一个语义学、符号学和认识论的术语,还被长时地使用在神学世界里……使用在礼拜仪式中,使用在美术中,使用在诗歌中。在所有上述领域中,它们共同的取义部分是“某一事物代表、表示别的事物”。[3]。
在《恋爱中的女人》里,动物实际上是男人最深层、最阴暗的欲望之容器,这些欲望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受到压制,但在与动物邂逅之时便会浮出水面。人与动物的互动可以用来解释人物性格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杰拉德·克里奇对牝马和兔子的行为是残暴的:他用马刺夹击牝马,用拳头猛击兔头并差点儿将其打死。但他相信这是他的权力,因为二者都比他弱小。两种动物都是古德兰的替身,这种支配性的行为也就可以施加在她的身上。因为他拥有古德兰,所以可以对她为所欲为。两人都因为暴力而激起欲望,也都从争斗中得到性满足。人物性格间对暴力的施虐、受虐需求,可以借助“动物替身”的运用而得到充分的探讨。
弗洛伊德在随笔《狼人》和《图腾与禁忌》中指出,人对于动物的暴力斗争有着长久的恐惧心理,这表明人渴望得到性爱中的被动位置。与之相反,对动物施加伤害的欲望所凸显的是俄狄浦斯式叙事框架中的一些有趣问题。劳伦斯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不同的个体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得一种平衡。米诺猫的那段插曲给我们的暗示是:双方可以借助一种体系不时地表现出施虐与受虐的心理倾向。正是通过持久斗争的观念,人与动物才能够达成一种权利的平衡。